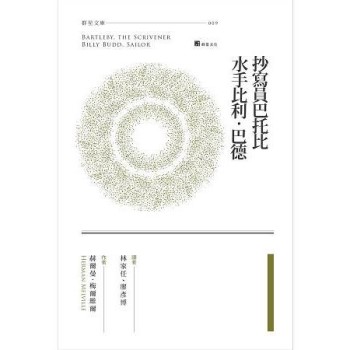摘自〈抄寫員巴托比〉
我這個老人年紀相當大了。近三十年來,我工作的性質讓我能和一些看似有趣、甚至奇特的人有非比尋常的接觸;而我所知的這些人,他們的故事至今還沒有人寫過─我指的是法律文件抄寫員,或說代筆人。不管是在工作上或私底下,這樣的人我都認識不少,如果願意,我還能說出各式各樣的軼事,這些故事可是會讓好脾氣的紳士聽了淺淺一笑,而多愁善感的靈魂聽了則會暗自垂淚。但相較於巴托比的人生,其他抄寫員的故事我會草草掠過。
巴托比是我見過、聽聞過的抄寫員當中最奇特的一位。也許我能完整寫出其他人的生平,但對於巴托比可就沒辦法了。我相信,沒有任何線索能詳實道盡此人的一生,這是文獻上無可彌補的損失。巴托比是那種你在他身上探查不出任何東西的人,除非你有辦法從最源頭處探尋一二。不過在他這個例子裡,能找到的也是微乎其微。除了在這個故事的結局裡將出現的模糊傳聞之外,透過我這雙感到訝異的眼睛所見識到的巴托比,就是我對他所知的一切了。
在介紹我與這位抄寫員初識之前,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我的員工、我的生意、我的辦公室,以及大致的環境會比較恰當。因為若要充分了解這位即將出場的主角,這類描述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我在年輕時就由衷深信,最簡單的生活方式便是最好的人生之道。因此,儘管我的職業是眾所周知的急忙、緊張,有時候甚至堪稱混亂,但我卻不為之所擾,生活依然平靜。我是那種沒什麼企圖心的律師,從不對陪審團高談闊論,或是想方設法吸引大眾讚賞,反而是沉浸在舒適隱蔽的靜謐當中,在有錢人的契約、抵押、地契等業務上做點輕鬆舒服的生意。
認識我的人無不認為我是個非常「無害」的男人。已逝的約翰.賈可柏.阿斯特,他可不是什麼浪漫的傢伙,他就會毫不猶豫地斷定說我為人的第一個特點就是謹慎自持,第二個則是按部就班,有條不紊。我提這些不是因為出於虛榮,只是單純地記錄下我曾經受雇於阿斯特的事實。我承認,他的名字我喜歡一提再提,是因為這名字念起來圓潤滑溜,聽起來清脆響亮。我也不客氣地說,我不是不知道阿斯特對我的好評。我的業務量在這段小故事開始前的那段時期,已經大量增長起來,我配得了一間平衡法院主事官(Master in Chancery)的老辦公室,這樣的老辦公室如今在紐約州已不復存在。這地方不至於讓人難以忍受,反而非常舒適好用。我很少發脾氣,更不會陷在對違法犯紀行為的憤慨情緒當中。不過,請容我魯莽地說,我認為新憲法突然粗暴地撤掉主事官辦公室,根本是草率之舉,因為我的生計都仰賴此處的收益,雖然那短短幾年收入也沒多少。不過說這些就離題了。
我的事務所就在華爾街某某號的樓上。事務所的一端可見到寬廣天井的一堵白牆,從建築頂部貫穿到底。這番景象與其說平淡無味,倒不如說它缺乏風景畫家筆下所謂的「生機」。不過,要是如此,那麼事務所另一端的景致至少是個對比。那個方向的窗景能一覽無遺地看到一大面高聳的磚牆:一面因歲月而顯得黯淡、陰影永遠退不去的磚牆。你無須望遠鏡,就能看到這面牆的暗藏之美,但就為了近視眼的人方便,這堵牆築得和我的窗櫺只有十步之遙。由於周圍大樓非常高,加上我的事務所又位在二樓,這堵牆和我事務所之間的空間,活脫脫就像是一座方形的大蓄水池。
巴托比出現之前的那段日子裡,我雇了兩個人來當抄寫員,此外還有一個可靠的男孩當辦公室小弟。第一個人叫「火雞」(Turkey),第二個叫「鉗子」(Nippers),第三個則叫「薑汁餅」(Ginger Nut)。這些看起來都像名字,不過這種名字你在電話簿裡通常是找不到的。這些其實都是綽號,是我這三名員工口頭上互相給對方取的稱呼,而這些綽號也反映了他們各自的樣貌和特質。
火雞是個矮胖的英國人,年紀和我相近,也就是六十出頭。他的臉色在早上是細緻的紅潤,可是一旦過了正午十二點、也就是他的午餐時間,那張臉就會像是一座耶誕節時塞滿煤炭的火爐那樣漲紅起來,而且一直紅下去─不過,似乎會逐漸減弱─直到下午六點前後;一過了六點,我就再也看不出這張臉的主人了。這張臉似乎隨太陽而紅漲,在正午時分達到高峰,繼而隨之落下,隔天再度升起、登頂、落下,它起落的規律和不減的紅光正如同火紅的太陽。我在人生路上見識過許多奇怪的巧合,但當中最特別的,莫過於當火雞的臉色紅潤發亮到最高峰之際,就在這臨界點的瞬間,我發現他當天隨後的工作能力竟會被嚴重地打亂。我不是說他懶散,或者無心工作,不,絕對不是。這裡的問題是,火雞從這時起往往太有活力了。他整個人開始變得詭異,情緒激動、慌慌張張、心浮氣躁。拿筆沾墨水台時,動作粗心大意。事務所檔案文件上的墨滴污漬,全都是他在正午十二點過後滴到的。
事實上,火雞在下午時不只粗心大意,讓文件沾染到墨滴,搞得一團糟,有時甚至更過分,非常吵鬧。在這樣的時刻,他的臉一樣會益發紅潤,就像是在無煙煤裡添進了成堆的觸煤。他會用椅子發出惱人的噪音,打翻吸墨用的沙盒,修理鋼筆時會不耐煩地把筆折斷,再突然氣急敗壞地把碎片全朝地上扔,而且站起來傾身越過桌面,把紙張打得亂七八糟,模樣非常難看。像他這樣上了年紀的男人竟然有這種舉動,教人看了真是非常難過。
不過,對我而言,火雞在許多地方還是非常有用。每天正午十二點之前,他仍是工作狀況最穩定、動作最快的員工,能用他人難以企及的方式完成大量工作。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對他的怪異舉動還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雖然我偶爾也規勸他。不過,一到下午,這個在早上不僅最是彬彬有禮、最溫和,且對他人還恭敬無比的人,只要受到丁點兒刺激,就會變得口無遮攔,甚至狂傲無禮。
我非常看重火雞上午的工作表現,況且我也不打算就這麼失掉這個員工,但他一過十二點之後的暴怒模樣卻又讓我很不自在。我身為一個性好和平的人,也不希望自己對他的好言相勸卻惹來他無禮的反駁。於是,我在某個週六中午(他的狀況在週六通常會更糟糕)便極其委婉地暗示,說他現在年紀也大了,也許可以把工作量做點刪減;簡言之,就是他每天一過中午十二點就不必上班,吃過午飯後就能回家休息到午茶時間。可是,他不要,他對自己午後的工作非常堅持。
火雞的臉色漲紅到簡直讓人看了難受,他站在事務所的另一頭,手上拿著長尺揮舞著,情緒慷慨激昂,說如果他在上午工作表現得那麼有用,那麼到了下午,這裡不就一定也少不了他嗎?「先生,我隨時聽候您差遣。」火雞這時候說,「我自認是您的得力助手。我上午忙著分配我的工作進度,下午則是勇往直前地克敵制勝,如此這般!」他拿著尺用力朝前戳了一下。
「可是,火雞啊,你看看那些墨滴。」我親切地說。
「是沒錯。可是啊,先生在上,您看看我這頭髮!我年紀也大了,先生啊,相較於這滿頭白髮,在這暖和的下午,我在紙上滴了一、兩滴墨水留了痕,也算不上什麼嚴重的事情吧。就算把紙給弄髒了,我這把年紀可是很光榮的。先生在上,我們倆都老了。」
火雞這樣套交情拉攏,我實在難以抵擋。我知道他無論如何是不想離開的,於是,我決定讓他留下,不過也打算讓他在下午只經手一些沒那麼重要的文件。……
我這個老人年紀相當大了。近三十年來,我工作的性質讓我能和一些看似有趣、甚至奇特的人有非比尋常的接觸;而我所知的這些人,他們的故事至今還沒有人寫過─我指的是法律文件抄寫員,或說代筆人。不管是在工作上或私底下,這樣的人我都認識不少,如果願意,我還能說出各式各樣的軼事,這些故事可是會讓好脾氣的紳士聽了淺淺一笑,而多愁善感的靈魂聽了則會暗自垂淚。但相較於巴托比的人生,其他抄寫員的故事我會草草掠過。
巴托比是我見過、聽聞過的抄寫員當中最奇特的一位。也許我能完整寫出其他人的生平,但對於巴托比可就沒辦法了。我相信,沒有任何線索能詳實道盡此人的一生,這是文獻上無可彌補的損失。巴托比是那種你在他身上探查不出任何東西的人,除非你有辦法從最源頭處探尋一二。不過在他這個例子裡,能找到的也是微乎其微。除了在這個故事的結局裡將出現的模糊傳聞之外,透過我這雙感到訝異的眼睛所見識到的巴托比,就是我對他所知的一切了。
在介紹我與這位抄寫員初識之前,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我的員工、我的生意、我的辦公室,以及大致的環境會比較恰當。因為若要充分了解這位即將出場的主角,這類描述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我在年輕時就由衷深信,最簡單的生活方式便是最好的人生之道。因此,儘管我的職業是眾所周知的急忙、緊張,有時候甚至堪稱混亂,但我卻不為之所擾,生活依然平靜。我是那種沒什麼企圖心的律師,從不對陪審團高談闊論,或是想方設法吸引大眾讚賞,反而是沉浸在舒適隱蔽的靜謐當中,在有錢人的契約、抵押、地契等業務上做點輕鬆舒服的生意。
認識我的人無不認為我是個非常「無害」的男人。已逝的約翰.賈可柏.阿斯特,他可不是什麼浪漫的傢伙,他就會毫不猶豫地斷定說我為人的第一個特點就是謹慎自持,第二個則是按部就班,有條不紊。我提這些不是因為出於虛榮,只是單純地記錄下我曾經受雇於阿斯特的事實。我承認,他的名字我喜歡一提再提,是因為這名字念起來圓潤滑溜,聽起來清脆響亮。我也不客氣地說,我不是不知道阿斯特對我的好評。我的業務量在這段小故事開始前的那段時期,已經大量增長起來,我配得了一間平衡法院主事官(Master in Chancery)的老辦公室,這樣的老辦公室如今在紐約州已不復存在。這地方不至於讓人難以忍受,反而非常舒適好用。我很少發脾氣,更不會陷在對違法犯紀行為的憤慨情緒當中。不過,請容我魯莽地說,我認為新憲法突然粗暴地撤掉主事官辦公室,根本是草率之舉,因為我的生計都仰賴此處的收益,雖然那短短幾年收入也沒多少。不過說這些就離題了。
我的事務所就在華爾街某某號的樓上。事務所的一端可見到寬廣天井的一堵白牆,從建築頂部貫穿到底。這番景象與其說平淡無味,倒不如說它缺乏風景畫家筆下所謂的「生機」。不過,要是如此,那麼事務所另一端的景致至少是個對比。那個方向的窗景能一覽無遺地看到一大面高聳的磚牆:一面因歲月而顯得黯淡、陰影永遠退不去的磚牆。你無須望遠鏡,就能看到這面牆的暗藏之美,但就為了近視眼的人方便,這堵牆築得和我的窗櫺只有十步之遙。由於周圍大樓非常高,加上我的事務所又位在二樓,這堵牆和我事務所之間的空間,活脫脫就像是一座方形的大蓄水池。
巴托比出現之前的那段日子裡,我雇了兩個人來當抄寫員,此外還有一個可靠的男孩當辦公室小弟。第一個人叫「火雞」(Turkey),第二個叫「鉗子」(Nippers),第三個則叫「薑汁餅」(Ginger Nut)。這些看起來都像名字,不過這種名字你在電話簿裡通常是找不到的。這些其實都是綽號,是我這三名員工口頭上互相給對方取的稱呼,而這些綽號也反映了他們各自的樣貌和特質。
火雞是個矮胖的英國人,年紀和我相近,也就是六十出頭。他的臉色在早上是細緻的紅潤,可是一旦過了正午十二點、也就是他的午餐時間,那張臉就會像是一座耶誕節時塞滿煤炭的火爐那樣漲紅起來,而且一直紅下去─不過,似乎會逐漸減弱─直到下午六點前後;一過了六點,我就再也看不出這張臉的主人了。這張臉似乎隨太陽而紅漲,在正午時分達到高峰,繼而隨之落下,隔天再度升起、登頂、落下,它起落的規律和不減的紅光正如同火紅的太陽。我在人生路上見識過許多奇怪的巧合,但當中最特別的,莫過於當火雞的臉色紅潤發亮到最高峰之際,就在這臨界點的瞬間,我發現他當天隨後的工作能力竟會被嚴重地打亂。我不是說他懶散,或者無心工作,不,絕對不是。這裡的問題是,火雞從這時起往往太有活力了。他整個人開始變得詭異,情緒激動、慌慌張張、心浮氣躁。拿筆沾墨水台時,動作粗心大意。事務所檔案文件上的墨滴污漬,全都是他在正午十二點過後滴到的。
事實上,火雞在下午時不只粗心大意,讓文件沾染到墨滴,搞得一團糟,有時甚至更過分,非常吵鬧。在這樣的時刻,他的臉一樣會益發紅潤,就像是在無煙煤裡添進了成堆的觸煤。他會用椅子發出惱人的噪音,打翻吸墨用的沙盒,修理鋼筆時會不耐煩地把筆折斷,再突然氣急敗壞地把碎片全朝地上扔,而且站起來傾身越過桌面,把紙張打得亂七八糟,模樣非常難看。像他這樣上了年紀的男人竟然有這種舉動,教人看了真是非常難過。
不過,對我而言,火雞在許多地方還是非常有用。每天正午十二點之前,他仍是工作狀況最穩定、動作最快的員工,能用他人難以企及的方式完成大量工作。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對他的怪異舉動還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雖然我偶爾也規勸他。不過,一到下午,這個在早上不僅最是彬彬有禮、最溫和,且對他人還恭敬無比的人,只要受到丁點兒刺激,就會變得口無遮攔,甚至狂傲無禮。
我非常看重火雞上午的工作表現,況且我也不打算就這麼失掉這個員工,但他一過十二點之後的暴怒模樣卻又讓我很不自在。我身為一個性好和平的人,也不希望自己對他的好言相勸卻惹來他無禮的反駁。於是,我在某個週六中午(他的狀況在週六通常會更糟糕)便極其委婉地暗示,說他現在年紀也大了,也許可以把工作量做點刪減;簡言之,就是他每天一過中午十二點就不必上班,吃過午飯後就能回家休息到午茶時間。可是,他不要,他對自己午後的工作非常堅持。
火雞的臉色漲紅到簡直讓人看了難受,他站在事務所的另一頭,手上拿著長尺揮舞著,情緒慷慨激昂,說如果他在上午工作表現得那麼有用,那麼到了下午,這裡不就一定也少不了他嗎?「先生,我隨時聽候您差遣。」火雞這時候說,「我自認是您的得力助手。我上午忙著分配我的工作進度,下午則是勇往直前地克敵制勝,如此這般!」他拿著尺用力朝前戳了一下。
「可是,火雞啊,你看看那些墨滴。」我親切地說。
「是沒錯。可是啊,先生在上,您看看我這頭髮!我年紀也大了,先生啊,相較於這滿頭白髮,在這暖和的下午,我在紙上滴了一、兩滴墨水留了痕,也算不上什麼嚴重的事情吧。就算把紙給弄髒了,我這把年紀可是很光榮的。先生在上,我們倆都老了。」
火雞這樣套交情拉攏,我實在難以抵擋。我知道他無論如何是不想離開的,於是,我決定讓他留下,不過也打算讓他在下午只經手一些沒那麼重要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