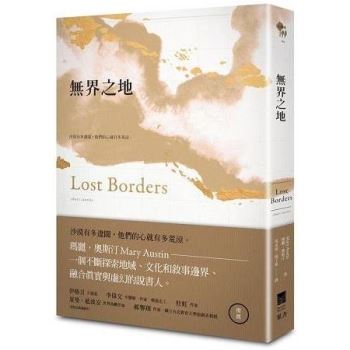那片土地
當派尤特人(Paiute)向西穿過內華達山的屏障時,他們迫使休松尼人(Shoshone)的殘餘勢力陷於孤立,不得不向南遷徙到死亡谷(Death Valley)和莫哈維沙漠邊緣。他們也將瓦紹人(Washoe)圍困於太浩湖(Tahoe)四周,然後在兩者之間來去自如,在融雪匯集的內華達溪谷建立自己的領地。他們確實適合這麼做,因為他們的族名源自於「派哈」(Pah),意思就是水,和他們位於「大盆地」(Great BAsin)的兄弟族人──猶特人(Ute)──不同。
最後,他們越過科恩河(Kern River)和金斯河(Kings River)穿過的峽谷,占領了所有聖華金(San Joaquin)東部坡地,但以小型氏族和家族群體為基礎,定居在山艾樹取代松樹之處,以及內華達山斷層上的沙漠。他們和在東北部毗鄰的猶特人聯手,與南部部落一起橫掃了大部分神祕、荒蕪之地,接下來你會聽到的故事就和這些地區有關。
部落之間和部落氏族之間根據自然的地標明確劃定界限,例如山峰、山頂、溪澗,以及從內華達山腳下開始向東不斷綿延的水潭湖泊。從那裡,朝任何方向走,在一星期路程的範圍內全都是不適合居住的地方。邊界原本應當延伸到科羅拉多峽谷,卻無端消失在沙地和糾結混亂的山脈之間。印第安人為這個國度取了非常有意義的名字──「無界之地」。印第安人的命名方式簡潔有力,而且向來信實,因為它們幾乎如實描繪出當地樣貌。
不過,這個名字的意義不僅於此。因為法律的效力僅僅依附於地理邊界,不會逾越;它緊貼著地標,就像帽貝附著在岩石峭壁上一樣。我相信大多數人制定法律是為了安全感,是為了自己而訂。他們像盲目的蟲子般推擠前行,對抗種種限制,像攀援植物攀附周遭溫暖牆壁般尋求安全感。他們為了確保自己神智清明,用許多法規來自我約束,並且形成小團體。
在那個法律與地標失去作用的所在,渺小人類的靈魂逸出身體,宛如滲出木桶的水滴,慢慢消散在沒有邊界的地方。
在那個良知界線瓦解的所在,沒有常規,人的言行只為了滿足欲望,其他的一切幾乎無關緊要。確實如此,儘管我很難讓你相信。在那裡,在那個靈魂和感覺的界線像沙暴中的痕跡般模糊的所在,我目睹了連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事。那正是你在那個地名具有意義的國度可能會見到的,例如「大籃子」(Ubehebe, 阿比赫比火山口)、「水源之地」(Pharanagat, 法蘭納格山)、安息泉(Resting Springs)、亡者之谷(Dead Man’s Gulch)、喪禮山(Funeral Mountains)。這些地名召喚、誘惑著你。它們向來具有的強烈真實氛圍,就像鄰居失火時刺痛你雙眼的濃煙。
沿著已知的路徑前進,感官因周遭巨大且虛無的單調而迷惑。一望無際的白色鹽鹼灘,令人目眩;方山地形遺世而獨立;小得可憐的裸露灌木叢稀稀疏疏,其間躥出貧瘠的山脊;幽黑的松樹群高聳於光禿的山頂──日復一日,大自然彷彿以某種神祕的方式讓你無法看清她的真實面貌。
你可能這樣持續旅行好幾個星期,卻無法到達任何地方,無法看見任何人煙,或闖進他們群聚的所在,看看他們,和他們一起推推搡搡、開懷暢飲、尋歡作樂。屬於那個國度的每一個故事,都帶著當地生活方式的色彩,漫長黯沉的路途在這裡暫時中止,短暫出現的熱情,就像從炎熱荒蕪低處升起的花崗岩山脊,在白雪堆積的彎道之間閃爍著蛋白石般的光影。
在地界之外的,是叫做「顫抖的沙丘」(Shivering Dunes)的地方,以及宛如箱籠般的峽谷。沙丘那令人目眩的起伏沙堆在風中蠕動著,漂移著,變動著,隱約發出沙沙的磨擦聲;刻畫在峽谷四周黑色壁面的象形文字屬於某個被人遺忘的民族,在正午時分看起來宛如星光。
那裡有湖泊,湖水清澈,像冰一般晶瑩透明,封固的純鹽晶體深度大約有一人高。高個子湯姆・巴希特從某個目擊者那裡聽來了幾個故事,並且告訴我其中一個。
有一群移民在漫長、空曠的荒涼谷地裡艱苦前行,經過沒有水源的山脈,來到像這樣的閉塞鹽鹼窪地。他們不想花那麼多時間繞過它,認為鹽層表面足以支撐他們破爛的馬車和瘦弱的隊員。然而,當他們來到湖中央,鹽層突然變薄,走在前面的人陷了進去,身體被困在鹽層底下,很多人無法爬上來,其中有一個是女人。
多年之後,目擊者又回到那個地點。在那之前,由於接連經過幾個熱氣蒸騰的夏天,整個湖面結成了鹽塊。目擊者告訴湯姆,他遠遠就看見那個女人的裙子的紅色亮光,等到他終於來到女子身旁時,看見側著身子倒下的她被封在晶體裡,隨著冰上升,出現在阻塞的水流之中。純粹的荒漠緊緊靠著狹長的山谷窪地和不規則的乾涸河床。每座高聳入雲的山上都有些樹木,鹿和大角羊以大石間的高大草叢為食。那一年,來自全國的探礦人像突然湧入的蜂群般接踵來到圖諾帕(Tonopah)。印第安人帶口信給我,在熱河(Hot Creek)和阿瑪古薩山(Armagosa)之間,因為人們紮營時距離水潭太近,大角羊渴死在山岬上,牠們垂死之前,頭部總是朝著遭人類侵犯的泉水的方向。
在無界之地的國度裡找不到水源時,那是很好的指標:在牛羊倒下的地方,無論牠們已成為骨骸或乾屍,頭部幾乎一律朝向可能會有水潭的方向。只不過,這樣的提示並無法阻止人們上路。我相信,我相信這主要是因為在人類大腦中,死亡與美麗以不可思議的方式並存。就像男人總輕易相信漂亮的女人大多是冷酷無情的一樣,輕柔的蛋白石迷霧會不會出賣你?藍色山脈上的虛幻深淵、點綴其間的鮮豔風蝕山崗、遠處消融於山頂的日暮紅光,或因天鵝絨般紫色薄暮掩映而變冷的山峰,還有群星,它們是否會背叛你?
請記得,因為依隨身體力量的生命脈動和節奏而進入沙漠、毫無緣由地愛上它、放下一切野心、擺脫舊習、忽視家人的,大多數是男人。他們的女人像憎恨那土地般莫名地憎恨生活;那土地微微泛白的棕色無窮盡地延伸,四周圍繞著灰暗陰霾的藍色山丘,邊緣潛藏著如海市蜃樓般若隱若現的蒼白水影。曾經,在艾迪翁達泉(Agua Hedionda)有一個女人──不過你也不會相信的。
如果這個沙漠是個女人,我很清楚她的模樣:胸部高聳,臀部寬厚,膚色黃褐,頭髮也是黃褐色的,蓬鬆濃密,順著完美的曲線滑下;她的嘴唇像斯芬克斯般豐滿,但眼皮沒那麼沉重;她的眼神靜定,如空中發亮的珠寶。這樣的容顏,應該會讓男人願意服侍她而不帶私欲;她寬容的心,應該會讓他們的原罪消失。她充滿渴望,但不是一無所有;她堅忍包容,但不輕易動心──不,即使你獻出所有土地,她也無動於衷,絲毫不會逾越自己的欲望。如果你深深切開帶有這片土地痕跡的靈魂,就會看見像這樣的特質──我現在就可以向你證明。
當派尤特人(Paiute)向西穿過內華達山的屏障時,他們迫使休松尼人(Shoshone)的殘餘勢力陷於孤立,不得不向南遷徙到死亡谷(Death Valley)和莫哈維沙漠邊緣。他們也將瓦紹人(Washoe)圍困於太浩湖(Tahoe)四周,然後在兩者之間來去自如,在融雪匯集的內華達溪谷建立自己的領地。他們確實適合這麼做,因為他們的族名源自於「派哈」(Pah),意思就是水,和他們位於「大盆地」(Great BAsin)的兄弟族人──猶特人(Ute)──不同。
最後,他們越過科恩河(Kern River)和金斯河(Kings River)穿過的峽谷,占領了所有聖華金(San Joaquin)東部坡地,但以小型氏族和家族群體為基礎,定居在山艾樹取代松樹之處,以及內華達山斷層上的沙漠。他們和在東北部毗鄰的猶特人聯手,與南部部落一起橫掃了大部分神祕、荒蕪之地,接下來你會聽到的故事就和這些地區有關。
部落之間和部落氏族之間根據自然的地標明確劃定界限,例如山峰、山頂、溪澗,以及從內華達山腳下開始向東不斷綿延的水潭湖泊。從那裡,朝任何方向走,在一星期路程的範圍內全都是不適合居住的地方。邊界原本應當延伸到科羅拉多峽谷,卻無端消失在沙地和糾結混亂的山脈之間。印第安人為這個國度取了非常有意義的名字──「無界之地」。印第安人的命名方式簡潔有力,而且向來信實,因為它們幾乎如實描繪出當地樣貌。
不過,這個名字的意義不僅於此。因為法律的效力僅僅依附於地理邊界,不會逾越;它緊貼著地標,就像帽貝附著在岩石峭壁上一樣。我相信大多數人制定法律是為了安全感,是為了自己而訂。他們像盲目的蟲子般推擠前行,對抗種種限制,像攀援植物攀附周遭溫暖牆壁般尋求安全感。他們為了確保自己神智清明,用許多法規來自我約束,並且形成小團體。
在那個法律與地標失去作用的所在,渺小人類的靈魂逸出身體,宛如滲出木桶的水滴,慢慢消散在沒有邊界的地方。
在那個良知界線瓦解的所在,沒有常規,人的言行只為了滿足欲望,其他的一切幾乎無關緊要。確實如此,儘管我很難讓你相信。在那裡,在那個靈魂和感覺的界線像沙暴中的痕跡般模糊的所在,我目睹了連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事。那正是你在那個地名具有意義的國度可能會見到的,例如「大籃子」(Ubehebe, 阿比赫比火山口)、「水源之地」(Pharanagat, 法蘭納格山)、安息泉(Resting Springs)、亡者之谷(Dead Man’s Gulch)、喪禮山(Funeral Mountains)。這些地名召喚、誘惑著你。它們向來具有的強烈真實氛圍,就像鄰居失火時刺痛你雙眼的濃煙。
沿著已知的路徑前進,感官因周遭巨大且虛無的單調而迷惑。一望無際的白色鹽鹼灘,令人目眩;方山地形遺世而獨立;小得可憐的裸露灌木叢稀稀疏疏,其間躥出貧瘠的山脊;幽黑的松樹群高聳於光禿的山頂──日復一日,大自然彷彿以某種神祕的方式讓你無法看清她的真實面貌。
你可能這樣持續旅行好幾個星期,卻無法到達任何地方,無法看見任何人煙,或闖進他們群聚的所在,看看他們,和他們一起推推搡搡、開懷暢飲、尋歡作樂。屬於那個國度的每一個故事,都帶著當地生活方式的色彩,漫長黯沉的路途在這裡暫時中止,短暫出現的熱情,就像從炎熱荒蕪低處升起的花崗岩山脊,在白雪堆積的彎道之間閃爍著蛋白石般的光影。
在地界之外的,是叫做「顫抖的沙丘」(Shivering Dunes)的地方,以及宛如箱籠般的峽谷。沙丘那令人目眩的起伏沙堆在風中蠕動著,漂移著,變動著,隱約發出沙沙的磨擦聲;刻畫在峽谷四周黑色壁面的象形文字屬於某個被人遺忘的民族,在正午時分看起來宛如星光。
那裡有湖泊,湖水清澈,像冰一般晶瑩透明,封固的純鹽晶體深度大約有一人高。高個子湯姆・巴希特從某個目擊者那裡聽來了幾個故事,並且告訴我其中一個。
有一群移民在漫長、空曠的荒涼谷地裡艱苦前行,經過沒有水源的山脈,來到像這樣的閉塞鹽鹼窪地。他們不想花那麼多時間繞過它,認為鹽層表面足以支撐他們破爛的馬車和瘦弱的隊員。然而,當他們來到湖中央,鹽層突然變薄,走在前面的人陷了進去,身體被困在鹽層底下,很多人無法爬上來,其中有一個是女人。
多年之後,目擊者又回到那個地點。在那之前,由於接連經過幾個熱氣蒸騰的夏天,整個湖面結成了鹽塊。目擊者告訴湯姆,他遠遠就看見那個女人的裙子的紅色亮光,等到他終於來到女子身旁時,看見側著身子倒下的她被封在晶體裡,隨著冰上升,出現在阻塞的水流之中。純粹的荒漠緊緊靠著狹長的山谷窪地和不規則的乾涸河床。每座高聳入雲的山上都有些樹木,鹿和大角羊以大石間的高大草叢為食。那一年,來自全國的探礦人像突然湧入的蜂群般接踵來到圖諾帕(Tonopah)。印第安人帶口信給我,在熱河(Hot Creek)和阿瑪古薩山(Armagosa)之間,因為人們紮營時距離水潭太近,大角羊渴死在山岬上,牠們垂死之前,頭部總是朝著遭人類侵犯的泉水的方向。
在無界之地的國度裡找不到水源時,那是很好的指標:在牛羊倒下的地方,無論牠們已成為骨骸或乾屍,頭部幾乎一律朝向可能會有水潭的方向。只不過,這樣的提示並無法阻止人們上路。我相信,我相信這主要是因為在人類大腦中,死亡與美麗以不可思議的方式並存。就像男人總輕易相信漂亮的女人大多是冷酷無情的一樣,輕柔的蛋白石迷霧會不會出賣你?藍色山脈上的虛幻深淵、點綴其間的鮮豔風蝕山崗、遠處消融於山頂的日暮紅光,或因天鵝絨般紫色薄暮掩映而變冷的山峰,還有群星,它們是否會背叛你?
請記得,因為依隨身體力量的生命脈動和節奏而進入沙漠、毫無緣由地愛上它、放下一切野心、擺脫舊習、忽視家人的,大多數是男人。他們的女人像憎恨那土地般莫名地憎恨生活;那土地微微泛白的棕色無窮盡地延伸,四周圍繞著灰暗陰霾的藍色山丘,邊緣潛藏著如海市蜃樓般若隱若現的蒼白水影。曾經,在艾迪翁達泉(Agua Hedionda)有一個女人──不過你也不會相信的。
如果這個沙漠是個女人,我很清楚她的模樣:胸部高聳,臀部寬厚,膚色黃褐,頭髮也是黃褐色的,蓬鬆濃密,順著完美的曲線滑下;她的嘴唇像斯芬克斯般豐滿,但眼皮沒那麼沉重;她的眼神靜定,如空中發亮的珠寶。這樣的容顏,應該會讓男人願意服侍她而不帶私欲;她寬容的心,應該會讓他們的原罪消失。她充滿渴望,但不是一無所有;她堅忍包容,但不輕易動心──不,即使你獻出所有土地,她也無動於衷,絲毫不會逾越自己的欲望。如果你深深切開帶有這片土地痕跡的靈魂,就會看見像這樣的特質──我現在就可以向你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