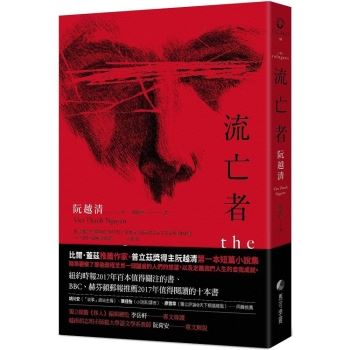戰時年代
一九八三年夏天,在花太太闖進我們的生活前,母親做的事沒有一件能讓我意外。她每天的例行公事就和地球的轉動一樣毫無驚喜,先是早上分別在六點、六點十五分和六點半的時候前來用力敲打我房門,直到我醒來為止。待我走出臥房時,她已著裝完畢,穿著一成不變的短袖襯衫和配好的粉彩色裙。同樣的衣服她有七套,如果穿的是洋紅色,我就知道是星期一。在我們出門前,她會關上電燈,檢查爐火,拉了拉黑色的鐵窗,確保它依舊牢固,而且一定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上了車後,再囑咐我鎖好自己的車門。
而當父親駕著奧斯摩比、我在後座看起自己的漫畫時,母親會開始化妝。十分鐘後,等我們抵達聖派翠克時,她就已經化好了妝,頰上腮紅融合著底妝。香水是最後一道步驟,在兩側頸間各噴一下。令人頭暈目眩的梔子花香味跟隨我走進柯曼老師的暑期輔導教室。在這裡,我每天有七個小時只能說英文。我喜歡上學,就連暑期課程都喜歡,感覺像是離家度假。所以每到下午三點,我總是會有些沮喪,因為得走過四條街,前往父母開的雜貨店:新西貢賣場。店裡很難聽到英文,只有越南話說得震天價響。
爸媽鮮少離開他們的崗位,兩座收銀檯如衛兵般包抄在賣場入口兩旁。店裡總是擠滿了客人,因為這裡是聖荷西少數有在賣越南人日常用品和家鄉味的地方,像是茉莉香米、八角、魚露、紅辣椒。客人總是和母親殺價個沒完,什麼東西都能討價還價,從被我假裝是黃色氪星石的冰糖到冷凍庫裡的各種肉類;從豬排、眼珠閃亮亮的鯰魚到一條條的牛肚和一包包洋菇般又小又軟的雞心都一樣。
「我們不能賣電視晚餐就好嗎?」我有次問。用越南話說電視晚餐比較簡單,因為越南人就把電視叫「ti-vi」,但其他我想要的東西就沒有對應的越南名可稱呼了。「或是波隆那香腸?」
「什麼香腸?」母親皺起眉,「如果我不會唸,客人就不會買。現在,快給我去罐頭上打標價。」
「反正他們只會要妳算便宜啊。」我早就懷疑母親不總是對的,現在我十三歲了,終於開始有膽子回嘴,「他們幹嘛什麼都要殺價?為什麼不人家標多少就付多少?」
「你是要當那種買什麼都乖乖照標價付錢的人嗎?」母親義正嚴詞地問,「還是要為真正的價值抗爭奮戰?」
我也不確定。我只知道,在新西貢賣場,我每天下午的工作就是在罐頭和商品包裝袋上印標價。當花太太向母親自我介紹時,我就是跪在地上,在母親身後的架上找印臺。花太太和母親一樣年近五十,全身上下穿著同色系的衣裳:白鞋、白夾克、白長褲,臉上大大的墨鏡幾乎要遮去大半張臉龐。就當母親替她將結帳商品裝袋時,花太太開口了:「親愛的,我正在為反對共軍的抗戰活動募款。」我對祖國基本歷史的了解程度就像對亞當和夏娃的故事一樣:一九七五年,共產黨自北越入侵南越,將我們一路驅逐出了太平洋,逃至加州。我對那場戰爭已無記憶,但花太太說其他人還沒有忘。他們此刻正在泰國叢林裡訓練一支由前南越士兵組成的游擊隊,準備反攻越共,煽動不滿的人民起身反抗共產黨政府,引發革命,收復越南共和國。
「士兵需要我們的支持。」花太太說,「而我們需要您這般的善良公民援助。」
母親用腳跟搓著腳踝,絲襪發出窸窣的摩擦聲。她膝蓋後方的絲襪裂了一條縫,但在裂到腳跟之前她一樣照穿不誤。「花太太,我也希望自己幫得上忙,但現在日子不好過啊。」母親說,「經濟衰退,油價又上漲,買氣大不如前嘍。我們家女兒又上大學了,每年學費簡直跟房子頭期款沒兩樣。」
「我生活也很吃緊。」花太太把玩著她包包上的銀色鎖釦,開了又關,關了又開。她無名指上戴著細細的金戒,指甲上的紅蔻丹如新車烤漆般光滑閃亮。「但人言可畏啊,聽說平太太的事兒了嗎?就因為她吝於捐獻,大家都說她是親共人士,還揚言要抵制她的店呢。」
母親也認識平太太,她在市中心西區開了間友朋美容院,就在幾條街外,但母親還是將話題轉移到六月炎熱的天氣和金價上。花太太附和說現在確實很熱,臉上掛著微笑,露出一口銅牆鐵壁般的齒牙。她朝我瞥了一眼,然後對母親撂了這麼一句:「想想吧,親愛的。收復故土是個偉大而崇高的理想,能為抗戰盡分心力我們都該感到光榮。」
「白痴。」等花太太離開後母親這麼嘟噥。那晚,當我們沿著第十街開車返家時,媽又對爸說了一次白天發生的事,他那時人在收銀檯前,忙到沒時間分心聽她們說話。聽她說到游擊隊三個字時,我腦中浮現蓬頭垢面的男人身影,一身破破爛爛的虎紋迷彩服,臉上蓄著未刮的鬍子,被蚊蟲叮著滿身是包,靠喝雨水,吃野豬和蚜蟲維生,用刺刀和波羅蜜練習近身戰鬥。我在後座開口問:「妳打算給花太太多少錢?」
「一毛也不給。」她回答,「這簡直是勒索。」
「但他們在抵抗共產黨啊。」我說;來自中國、北韓、古巴的共產黨人和桑定民族解放陣線都威脅要從國界南境滲透入侵,雷根總統在ABC世界新聞上這麼解釋過。「我們不該幫忙他們嗎?」
「戰爭已經結束了,」母親用疲憊的語氣回答,「不用再打了。」
我氣壞了,因為花太太的出現就是戰爭尚未結束的最好證明。她不知用了什麼法子,一路從舊西貢跟來了新西貢。更重要的是,我在牙醫診所時讀了《新聞周刊》,知道我們現正面臨一場對抗蘇聯邪惡帝國的史詩鉅戰。母親的答案已經讓我夠不開心了,父親的反應更是讓我一肚子火。
「戰爭或許結束了,」他說,小指頭在耳朵裡挖呀挖,「但只要付上一筆小小的封口費,我們日子就會輕鬆許多。」
母親一語不發,只是五指在座椅扶手上輪番敲打。我知道她會想辦法說服那個動作總是慢條斯理、有著一雙如烏龜般耐心眼神的禿頭父親。當天深夜,我匆匆倒了杯水,正要從廚房跑回房間時,恰巧聽見母親在關上的房門之後想方設法要打消父親的念頭。但我無暇偷聽。我們最近才在柯曼老師的課堂上讀了〈厄舍府的沒落〉 ,因為怕會在漆黑的走廊上撞見殭屍,我只能快步經過他們房間,聽見母親的聲音從門後傳來:「更困難的事我都應付過了。」
恐懼要比好奇心來得強大。我關上房門,鑽進被裡,不停打著哆嗦,把暑期班的教科書通通推到一旁。我先前已經剪下棕色的購物紙袋,包住它們當封面,並在上頭草草寫上「數學」和「美國歷史」。或許母親指的是二次大戰結束前的那場饑荒,那時她才九歲。去年,電視晚間新聞報導了衣索比亞面臨的饑荒,母親一聽到,立刻對正在替她拔白頭髮的我說起另一場饑荒。「你知道我村子裡有十幾個小孩就這樣活活餓死嗎?」她說;儘管很顯然我怎麼可能會知道。「老人也是,有時就這麼死在街上。有一天,我還發現以前常玩在一起的一個女孩死在她家門口。」說完,母親便陷入沉默,只是愣愣瞪著電視上方的牆壁,我也沒有答腔。這種故事我聽多了;再說,我也沒那心思發問,只要找到一根白頭髮,她就給我五分錢。所以我全神貫注在這任務上,每一根白髮都讓我離下一期的《美國隊長》又近上一分。
日子一天天過去,母親再也不曾提起花太太,但那女人已在她心中投下不安的種子。母親開始會在夜裡作帳時絮絮叨唸,過去這時候,她通常是聚精會神地記錄當天每一張收據。我們會坐在餐桌前清點現金,用紙將銅板綑成大小有如鞭炮的一捲,然後在個人支票、像大富翁假鈔的食物兌換券以及失依兒童家庭扶助計畫發放的黃色兌換券背面蓋上新西貢賣場的地址印章。我用一臺比我們家轉盤式電話還要大的計算機計算總額。機器嗡嗡作響,我從來不用望向鍵盤,每一個數字的位置我都了然於心。只有在這時候數學才是我的拿手強項。
結帳時,母親轉述她聽來的傳聞,說是前越南共和國的士兵不僅是在泰國境內組織了一支游擊軍隊,在美國這兒也拉起了一道祕密戰線,打算要推翻共產政權。不過,比謠言更可怕的是還有個身分不明的攻擊者對位於園林市的越南報社投擲燃燒彈(編輯不幸身亡),在維吉尼亞州還有另一名編輯與妻子兩人在自家門前慘遭槍殺(凶手一直沒有落網)。「他們只是把許多人早在私下談論的事公開說出口。」母親說,手指在溼海綿上沾了沾,「和共產黨握手言和恐怕也不是什麼壞事。」
我把數字寫進帳本,自始至終不曾抬頭望過一眼。父親和我穿著T恤和短褲,母親卻只套著件薄薄的綠色連身睡衣,底下沒有穿胸罩。她沒發現自己的胸脯會像淺灘裡的海葵一樣搖晃,每次瞥見那對淒涼的深色乳暈和像我食指一樣粗的乳頭,我都會尷尬不已。母親的胸部和我班上女生的完全不同──起碼我上週從土田艾美襯衫釦子縫隙偷看到的景象證實了我的想像。她的乳頭粉嫩堅挺,就像我手中的鉛筆擦頭一樣。我沒有抬頭,兩眼依舊緊盯帳本,說:「但妳老說共產黨是壞人啊。」
「看吧!」父親哈哈大笑,「你果然有在聽。有時候,我還真搞不懂你藏在那副笨重眼鏡之後的腦袋在想什麼。」
「共產黨是很邪惡,」母親指尖掃過一疊二十元現鈔。她連小學都沒有畢業,外公逼她留在家裡照顧其他兄弟姊妹,但就算如此,她數錢和心算的速度還是比我用計算機快上許多倍。「這點毫無疑問,他們不信神,也不信金錢。」
「但他們相信要把別人的錢搶過來,沒收充公。」父親說。他常提起他的汽車零件用品店,而據他兄弟所說,在共產黨的控制下,店裡已經沒有任何零件可賣。我們以前就住在店鋪樓上,有時候,我會想,現在會不會有共產黨的小孩睡在我床上;如果有,那個小紅衛兵又都讀些什麼樣的書、看什麼樣的電影。《美國隊長》就不用說了,絕對不可能,但他一定看過天行者路克和黑武士用光劍決鬥吧。《星際大戰》的錄影帶我都看過十幾遍了,如果那國家連一次都不給人民看,難怪需要革命。不過母親是不會贊同的。她用紙條將那疊二十元鈔票綑起,說:「我和花太太一樣痛恨共產黨,但她要打的是一場永遠不可能贏的仗。我才不會拿錢打水漂,白白支持一個不可能成功的目標。」
父親起身,將桌上所有鈔票、銅板、支票和食物券通通掃進他每天早上都要背去美國銀行的塑膠皮斜背包。爸媽將賺來的錢部分存在銀行,部分捐給教會,部分匯回去給越南的親戚。他們每隔一段時日就會捎來一封薄薄的信,信裡寫滿密密麻麻的困境,我媽說,簡言之就是沒錢沒食物沒學校沒希望這類的悲劇。這些親戚和爸媽自身的經歷都讓他們深信沒有一個國家能免於災難的侵襲,所以他們還將部分賺來的錢偷偷藏在家裡,以免哪天有什麼可怕的災禍從天而降,一把將美國的銀行消滅得乾乾淨淨。母親將一捆又一捆的百元現鈔包在塑膠袋裡,黏在馬桶水箱的蓋子底下,米桶裡還埋有狗牌大小的黃金。她的玉鐲、二十四K金項鍊、鑽戒則是通通鎖在一只攜帶式的防火保險箱中,又把保險箱藏在屋子底下供水管電線通過的夾層空間。為了轉移宵小的注意,她還布置了些聲東擊西的誘餌,在前門邊的書架高層放了一大只塞滿錢幣的沉重玻璃花瓶,還擺了對黃金手鐲在她梳妝檯上。
她擔心家裡被人打劫的憂慮在去年十月得到了證實。那是個平凡無奇的星期二夜晚,有人敲起家門,那時父親在廚房,剛打開爐火,我比已換上睡衣的母親早幾步來到門前。我從貓眼看出去,只見一名白人說:「有您的信件。」如果他說的是越南語或西班牙語,我絕對不可能開門,但因為他說的是英文,所以我就開了。說時遲那時快,他左手在門上一頂,硬是闖進屋內。那人看上去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一頭稻草似的羽毛剪髮型,長到髮尾落在磨損的牛仔外套領口邊緣。他不比母親高上多少,但體格稍稍結實了些。一開口,聲音就像橡膠鞋底在體育館地板上發出的摩擦聲,刺耳尖銳。
「閃開。」他說,滿頭是汗,右手握著把槍。即便幾十年過去,我依然能清楚憶起那把槍的模樣。他手抖個不停,揮舞著那把點二二黑色手槍,跨過門檻,踢翻門前成堆的鞋子,忘了把門關上。事後,母親推斷他應該是個生手,大概還是個急需錢用的毒蟲。他槍口在我面前掃過,瞄準母親,喝令:「妳會說英語嗎?給我趴下!」
我退開,母親高舉雙手,說:「Khong, khong, khong!」 爸出現了,停在廚房和前門之間。歹徒將槍口轉向爸,命令:「給我趴下。」爸也舉高雙手,跪在地上。「別開槍。」爸用英文說,聲音細如蚊鳴,「求求你,別開槍。」我從沒在教堂以外的地方見父親下跪過,也沒看過媽怕到簌簌發抖,以致滿腦子只有對他們的同情。我知道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他們被人這般羞辱。像是察覺我的思緒般,那人默默將槍口向我轉來,我便也乖乖跪下。現在只剩我媽還站著,背抵在牆上,剛卸完妝的臉上沒有半點血色,胸脯在睡袍之下劇烈起伏,宛如兩尾鰻魚的頭顱,嘴裡只是不停喊著「不」。那人槍口依舊瞄準著我,說:「小鬼,你媽是有什麼毛病?」
母親放聲尖叫。除了她自己之外,所有人都嚇傻原地。她往前一撲,用手推開槍口,肩膀重重撞向歹徒,瞬間奪門而出。搶匪朝門口的書架踉蹌倒去,裝滿錢幣的玻璃花瓶摔落在地,砸個粉碎,一分錢、五分錢、十分錢的銅板和玻璃碎片灑得到處都是。「老天!」那人驚呼。父親趁他轉身望向門口時跳了起來,朝搶匪背後撲去,將他推出門外,然後用力關上家門。「砰!」屋外傳來一聲尖銳短促的槍響,子彈打在人行道上,反彈射入郵筒旁的牆壁裡。幾小時後,警察將子彈挖了出來。
星期日早晨,在我們去教堂前,母親會用英國的百利髮乳和一把黑色王牌平梳將我頭髮梳成服服貼貼的中分頭。這髮型難看死了,活像電影《一窩小屁蛋》裡的阿爾法法,但我沒有抗議,就像警方把母親從鄰居家帶回來時我什麼也沒說一樣。「是我救了咱們一家大小性命,你這膽小鬼!」她衝著爸大吼。我們坐在餐桌前,父親對幫忙做筆錄的警察露出虛弱的笑容。她又揪起我的耳朵,怒罵:「我是怎麼跟你說的,千萬不要給陌生人開門!你就老是把我的話當耳邊風。」那名警察請我幫忙翻譯一下她說了什麼,我揉揉耳朵,回答:「她只是嚇壞了,警察先生。」
一九八三年夏天,在花太太闖進我們的生活前,母親做的事沒有一件能讓我意外。她每天的例行公事就和地球的轉動一樣毫無驚喜,先是早上分別在六點、六點十五分和六點半的時候前來用力敲打我房門,直到我醒來為止。待我走出臥房時,她已著裝完畢,穿著一成不變的短袖襯衫和配好的粉彩色裙。同樣的衣服她有七套,如果穿的是洋紅色,我就知道是星期一。在我們出門前,她會關上電燈,檢查爐火,拉了拉黑色的鐵窗,確保它依舊牢固,而且一定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上了車後,再囑咐我鎖好自己的車門。
而當父親駕著奧斯摩比、我在後座看起自己的漫畫時,母親會開始化妝。十分鐘後,等我們抵達聖派翠克時,她就已經化好了妝,頰上腮紅融合著底妝。香水是最後一道步驟,在兩側頸間各噴一下。令人頭暈目眩的梔子花香味跟隨我走進柯曼老師的暑期輔導教室。在這裡,我每天有七個小時只能說英文。我喜歡上學,就連暑期課程都喜歡,感覺像是離家度假。所以每到下午三點,我總是會有些沮喪,因為得走過四條街,前往父母開的雜貨店:新西貢賣場。店裡很難聽到英文,只有越南話說得震天價響。
爸媽鮮少離開他們的崗位,兩座收銀檯如衛兵般包抄在賣場入口兩旁。店裡總是擠滿了客人,因為這裡是聖荷西少數有在賣越南人日常用品和家鄉味的地方,像是茉莉香米、八角、魚露、紅辣椒。客人總是和母親殺價個沒完,什麼東西都能討價還價,從被我假裝是黃色氪星石的冰糖到冷凍庫裡的各種肉類;從豬排、眼珠閃亮亮的鯰魚到一條條的牛肚和一包包洋菇般又小又軟的雞心都一樣。
「我們不能賣電視晚餐就好嗎?」我有次問。用越南話說電視晚餐比較簡單,因為越南人就把電視叫「ti-vi」,但其他我想要的東西就沒有對應的越南名可稱呼了。「或是波隆那香腸?」
「什麼香腸?」母親皺起眉,「如果我不會唸,客人就不會買。現在,快給我去罐頭上打標價。」
「反正他們只會要妳算便宜啊。」我早就懷疑母親不總是對的,現在我十三歲了,終於開始有膽子回嘴,「他們幹嘛什麼都要殺價?為什麼不人家標多少就付多少?」
「你是要當那種買什麼都乖乖照標價付錢的人嗎?」母親義正嚴詞地問,「還是要為真正的價值抗爭奮戰?」
我也不確定。我只知道,在新西貢賣場,我每天下午的工作就是在罐頭和商品包裝袋上印標價。當花太太向母親自我介紹時,我就是跪在地上,在母親身後的架上找印臺。花太太和母親一樣年近五十,全身上下穿著同色系的衣裳:白鞋、白夾克、白長褲,臉上大大的墨鏡幾乎要遮去大半張臉龐。就當母親替她將結帳商品裝袋時,花太太開口了:「親愛的,我正在為反對共軍的抗戰活動募款。」我對祖國基本歷史的了解程度就像對亞當和夏娃的故事一樣:一九七五年,共產黨自北越入侵南越,將我們一路驅逐出了太平洋,逃至加州。我對那場戰爭已無記憶,但花太太說其他人還沒有忘。他們此刻正在泰國叢林裡訓練一支由前南越士兵組成的游擊隊,準備反攻越共,煽動不滿的人民起身反抗共產黨政府,引發革命,收復越南共和國。
「士兵需要我們的支持。」花太太說,「而我們需要您這般的善良公民援助。」
母親用腳跟搓著腳踝,絲襪發出窸窣的摩擦聲。她膝蓋後方的絲襪裂了一條縫,但在裂到腳跟之前她一樣照穿不誤。「花太太,我也希望自己幫得上忙,但現在日子不好過啊。」母親說,「經濟衰退,油價又上漲,買氣大不如前嘍。我們家女兒又上大學了,每年學費簡直跟房子頭期款沒兩樣。」
「我生活也很吃緊。」花太太把玩著她包包上的銀色鎖釦,開了又關,關了又開。她無名指上戴著細細的金戒,指甲上的紅蔻丹如新車烤漆般光滑閃亮。「但人言可畏啊,聽說平太太的事兒了嗎?就因為她吝於捐獻,大家都說她是親共人士,還揚言要抵制她的店呢。」
母親也認識平太太,她在市中心西區開了間友朋美容院,就在幾條街外,但母親還是將話題轉移到六月炎熱的天氣和金價上。花太太附和說現在確實很熱,臉上掛著微笑,露出一口銅牆鐵壁般的齒牙。她朝我瞥了一眼,然後對母親撂了這麼一句:「想想吧,親愛的。收復故土是個偉大而崇高的理想,能為抗戰盡分心力我們都該感到光榮。」
「白痴。」等花太太離開後母親這麼嘟噥。那晚,當我們沿著第十街開車返家時,媽又對爸說了一次白天發生的事,他那時人在收銀檯前,忙到沒時間分心聽她們說話。聽她說到游擊隊三個字時,我腦中浮現蓬頭垢面的男人身影,一身破破爛爛的虎紋迷彩服,臉上蓄著未刮的鬍子,被蚊蟲叮著滿身是包,靠喝雨水,吃野豬和蚜蟲維生,用刺刀和波羅蜜練習近身戰鬥。我在後座開口問:「妳打算給花太太多少錢?」
「一毛也不給。」她回答,「這簡直是勒索。」
「但他們在抵抗共產黨啊。」我說;來自中國、北韓、古巴的共產黨人和桑定民族解放陣線都威脅要從國界南境滲透入侵,雷根總統在ABC世界新聞上這麼解釋過。「我們不該幫忙他們嗎?」
「戰爭已經結束了,」母親用疲憊的語氣回答,「不用再打了。」
我氣壞了,因為花太太的出現就是戰爭尚未結束的最好證明。她不知用了什麼法子,一路從舊西貢跟來了新西貢。更重要的是,我在牙醫診所時讀了《新聞周刊》,知道我們現正面臨一場對抗蘇聯邪惡帝國的史詩鉅戰。母親的答案已經讓我夠不開心了,父親的反應更是讓我一肚子火。
「戰爭或許結束了,」他說,小指頭在耳朵裡挖呀挖,「但只要付上一筆小小的封口費,我們日子就會輕鬆許多。」
母親一語不發,只是五指在座椅扶手上輪番敲打。我知道她會想辦法說服那個動作總是慢條斯理、有著一雙如烏龜般耐心眼神的禿頭父親。當天深夜,我匆匆倒了杯水,正要從廚房跑回房間時,恰巧聽見母親在關上的房門之後想方設法要打消父親的念頭。但我無暇偷聽。我們最近才在柯曼老師的課堂上讀了〈厄舍府的沒落〉 ,因為怕會在漆黑的走廊上撞見殭屍,我只能快步經過他們房間,聽見母親的聲音從門後傳來:「更困難的事我都應付過了。」
恐懼要比好奇心來得強大。我關上房門,鑽進被裡,不停打著哆嗦,把暑期班的教科書通通推到一旁。我先前已經剪下棕色的購物紙袋,包住它們當封面,並在上頭草草寫上「數學」和「美國歷史」。或許母親指的是二次大戰結束前的那場饑荒,那時她才九歲。去年,電視晚間新聞報導了衣索比亞面臨的饑荒,母親一聽到,立刻對正在替她拔白頭髮的我說起另一場饑荒。「你知道我村子裡有十幾個小孩就這樣活活餓死嗎?」她說;儘管很顯然我怎麼可能會知道。「老人也是,有時就這麼死在街上。有一天,我還發現以前常玩在一起的一個女孩死在她家門口。」說完,母親便陷入沉默,只是愣愣瞪著電視上方的牆壁,我也沒有答腔。這種故事我聽多了;再說,我也沒那心思發問,只要找到一根白頭髮,她就給我五分錢。所以我全神貫注在這任務上,每一根白髮都讓我離下一期的《美國隊長》又近上一分。
日子一天天過去,母親再也不曾提起花太太,但那女人已在她心中投下不安的種子。母親開始會在夜裡作帳時絮絮叨唸,過去這時候,她通常是聚精會神地記錄當天每一張收據。我們會坐在餐桌前清點現金,用紙將銅板綑成大小有如鞭炮的一捲,然後在個人支票、像大富翁假鈔的食物兌換券以及失依兒童家庭扶助計畫發放的黃色兌換券背面蓋上新西貢賣場的地址印章。我用一臺比我們家轉盤式電話還要大的計算機計算總額。機器嗡嗡作響,我從來不用望向鍵盤,每一個數字的位置我都了然於心。只有在這時候數學才是我的拿手強項。
結帳時,母親轉述她聽來的傳聞,說是前越南共和國的士兵不僅是在泰國境內組織了一支游擊軍隊,在美國這兒也拉起了一道祕密戰線,打算要推翻共產政權。不過,比謠言更可怕的是還有個身分不明的攻擊者對位於園林市的越南報社投擲燃燒彈(編輯不幸身亡),在維吉尼亞州還有另一名編輯與妻子兩人在自家門前慘遭槍殺(凶手一直沒有落網)。「他們只是把許多人早在私下談論的事公開說出口。」母親說,手指在溼海綿上沾了沾,「和共產黨握手言和恐怕也不是什麼壞事。」
我把數字寫進帳本,自始至終不曾抬頭望過一眼。父親和我穿著T恤和短褲,母親卻只套著件薄薄的綠色連身睡衣,底下沒有穿胸罩。她沒發現自己的胸脯會像淺灘裡的海葵一樣搖晃,每次瞥見那對淒涼的深色乳暈和像我食指一樣粗的乳頭,我都會尷尬不已。母親的胸部和我班上女生的完全不同──起碼我上週從土田艾美襯衫釦子縫隙偷看到的景象證實了我的想像。她的乳頭粉嫩堅挺,就像我手中的鉛筆擦頭一樣。我沒有抬頭,兩眼依舊緊盯帳本,說:「但妳老說共產黨是壞人啊。」
「看吧!」父親哈哈大笑,「你果然有在聽。有時候,我還真搞不懂你藏在那副笨重眼鏡之後的腦袋在想什麼。」
「共產黨是很邪惡,」母親指尖掃過一疊二十元現鈔。她連小學都沒有畢業,外公逼她留在家裡照顧其他兄弟姊妹,但就算如此,她數錢和心算的速度還是比我用計算機快上許多倍。「這點毫無疑問,他們不信神,也不信金錢。」
「但他們相信要把別人的錢搶過來,沒收充公。」父親說。他常提起他的汽車零件用品店,而據他兄弟所說,在共產黨的控制下,店裡已經沒有任何零件可賣。我們以前就住在店鋪樓上,有時候,我會想,現在會不會有共產黨的小孩睡在我床上;如果有,那個小紅衛兵又都讀些什麼樣的書、看什麼樣的電影。《美國隊長》就不用說了,絕對不可能,但他一定看過天行者路克和黑武士用光劍決鬥吧。《星際大戰》的錄影帶我都看過十幾遍了,如果那國家連一次都不給人民看,難怪需要革命。不過母親是不會贊同的。她用紙條將那疊二十元鈔票綑起,說:「我和花太太一樣痛恨共產黨,但她要打的是一場永遠不可能贏的仗。我才不會拿錢打水漂,白白支持一個不可能成功的目標。」
父親起身,將桌上所有鈔票、銅板、支票和食物券通通掃進他每天早上都要背去美國銀行的塑膠皮斜背包。爸媽將賺來的錢部分存在銀行,部分捐給教會,部分匯回去給越南的親戚。他們每隔一段時日就會捎來一封薄薄的信,信裡寫滿密密麻麻的困境,我媽說,簡言之就是沒錢沒食物沒學校沒希望這類的悲劇。這些親戚和爸媽自身的經歷都讓他們深信沒有一個國家能免於災難的侵襲,所以他們還將部分賺來的錢偷偷藏在家裡,以免哪天有什麼可怕的災禍從天而降,一把將美國的銀行消滅得乾乾淨淨。母親將一捆又一捆的百元現鈔包在塑膠袋裡,黏在馬桶水箱的蓋子底下,米桶裡還埋有狗牌大小的黃金。她的玉鐲、二十四K金項鍊、鑽戒則是通通鎖在一只攜帶式的防火保險箱中,又把保險箱藏在屋子底下供水管電線通過的夾層空間。為了轉移宵小的注意,她還布置了些聲東擊西的誘餌,在前門邊的書架高層放了一大只塞滿錢幣的沉重玻璃花瓶,還擺了對黃金手鐲在她梳妝檯上。
她擔心家裡被人打劫的憂慮在去年十月得到了證實。那是個平凡無奇的星期二夜晚,有人敲起家門,那時父親在廚房,剛打開爐火,我比已換上睡衣的母親早幾步來到門前。我從貓眼看出去,只見一名白人說:「有您的信件。」如果他說的是越南語或西班牙語,我絕對不可能開門,但因為他說的是英文,所以我就開了。說時遲那時快,他左手在門上一頂,硬是闖進屋內。那人看上去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一頭稻草似的羽毛剪髮型,長到髮尾落在磨損的牛仔外套領口邊緣。他不比母親高上多少,但體格稍稍結實了些。一開口,聲音就像橡膠鞋底在體育館地板上發出的摩擦聲,刺耳尖銳。
「閃開。」他說,滿頭是汗,右手握著把槍。即便幾十年過去,我依然能清楚憶起那把槍的模樣。他手抖個不停,揮舞著那把點二二黑色手槍,跨過門檻,踢翻門前成堆的鞋子,忘了把門關上。事後,母親推斷他應該是個生手,大概還是個急需錢用的毒蟲。他槍口在我面前掃過,瞄準母親,喝令:「妳會說英語嗎?給我趴下!」
我退開,母親高舉雙手,說:「Khong, khong, khong!」 爸出現了,停在廚房和前門之間。歹徒將槍口轉向爸,命令:「給我趴下。」爸也舉高雙手,跪在地上。「別開槍。」爸用英文說,聲音細如蚊鳴,「求求你,別開槍。」我從沒在教堂以外的地方見父親下跪過,也沒看過媽怕到簌簌發抖,以致滿腦子只有對他們的同情。我知道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他們被人這般羞辱。像是察覺我的思緒般,那人默默將槍口向我轉來,我便也乖乖跪下。現在只剩我媽還站著,背抵在牆上,剛卸完妝的臉上沒有半點血色,胸脯在睡袍之下劇烈起伏,宛如兩尾鰻魚的頭顱,嘴裡只是不停喊著「不」。那人槍口依舊瞄準著我,說:「小鬼,你媽是有什麼毛病?」
母親放聲尖叫。除了她自己之外,所有人都嚇傻原地。她往前一撲,用手推開槍口,肩膀重重撞向歹徒,瞬間奪門而出。搶匪朝門口的書架踉蹌倒去,裝滿錢幣的玻璃花瓶摔落在地,砸個粉碎,一分錢、五分錢、十分錢的銅板和玻璃碎片灑得到處都是。「老天!」那人驚呼。父親趁他轉身望向門口時跳了起來,朝搶匪背後撲去,將他推出門外,然後用力關上家門。「砰!」屋外傳來一聲尖銳短促的槍響,子彈打在人行道上,反彈射入郵筒旁的牆壁裡。幾小時後,警察將子彈挖了出來。
星期日早晨,在我們去教堂前,母親會用英國的百利髮乳和一把黑色王牌平梳將我頭髮梳成服服貼貼的中分頭。這髮型難看死了,活像電影《一窩小屁蛋》裡的阿爾法法,但我沒有抗議,就像警方把母親從鄰居家帶回來時我什麼也沒說一樣。「是我救了咱們一家大小性命,你這膽小鬼!」她衝著爸大吼。我們坐在餐桌前,父親對幫忙做筆錄的警察露出虛弱的笑容。她又揪起我的耳朵,怒罵:「我是怎麼跟你說的,千萬不要給陌生人開門!你就老是把我的話當耳邊風。」那名警察請我幫忙翻譯一下她說了什麼,我揉揉耳朵,回答:「她只是嚇壞了,警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