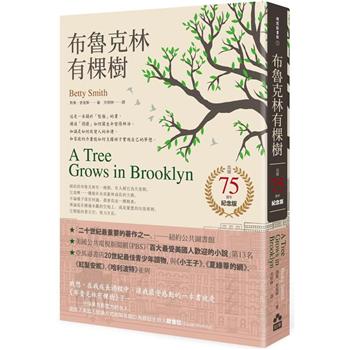寧靜這個詞用於紐約布魯克林恰如其分,尤其是一九一二年的夏天。沉靜這個詞大概更好些,只是對布魯克林的威廉斯堡不大合適。大草原可愛,「仙納度」哻悅耳,但用於布魯克林都不合適。還是只能用寧靜這個詞,特別是夏日的一個星期六下午。
下午的斜陽照在法蘭西.諾蘭家爬滿苔蘚的院子裡,把破舊的木籬笆曬得暖暖的。看著斜射下來的一縷縷陽光,法蘭西心頭湧出一種美好的感覺來。這樣的感覺,她回憶起一首詩歌時也有過;那是一首在學校裡背誦過的詩:
在這片原始森林,
松樹和鐵杉陣陣低語
苔蘚如鬚,
翠綠滿身黃昏中佇立,依稀朦朧如一個個督伊德僧侶。
法蘭西院子裡的樹既不是松樹,也不是鐵杉。樹上的綠色枝條從樹幹向四周發散,枝條上長滿了尖尖的葉子,使得整棵樹看起來如同無數把撐開的綠傘。有人稱它為天堂樹,因為不管它的種子落到什麼地方,都會長出一棵樹來,向著天空努力生長。這樹或長在四周圍滿木籬的空地上,或從棄置的垃圾堆裡鑽出來;它也是唯一能在水泥地上生長的樹。它長得高大茂盛,而且只長在住宅區。
星期天下午,你去散散步,走到一個不錯的住宅區,高雅的住宅區,看到別人家通往院子的鐵門後有這樣一棵小樹,你就知道布魯克林這一帶快變成住宅區了。樹懂,樹會打前鋒。到了後來,便漸漸會有些貧窮的外國人跑來,把破舊的褐砂石房整修成平房,把羽毛褥墊從窗戶裡推出來曬;等到此時天堂樹已經長得鬱鬱蔥蔥了。這種樹習性如此,就像窮人一樣。
法蘭西的院子裡長的就是這種樹。在她三樓的太平梯附近,樹上的小「傘」一個個蜷曲過來,讓一個坐在消防梯上的十一歲女孩覺得自己就住在樹上。夏天的每個星期六下午,法蘭西都這麼想像著。
啊,布魯克林的星期六多麼美好啊!啊,到處都是那麼美好啊!星期六是發薪日,也是個週末假日,卻又不用守星期天那些清規戒律。人們有錢出去買東西,在這一天好好吃一頓飯、喝醉、約會、做愛、熬夜、唱歌、放音樂、打架、跳舞,而且因為次日就是自由自在的一天,還可以睡個懶覺—至少可以睡到晚場的彌撒。
星期天,大部分人會擠著去參加十一點鐘的彌撒。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很少的一些,會去參加六點鐘那場。人們誇他們趕得早,但其實他們不配這樣的誇獎,因為他們根本是在外頭待得太久,回到家的時候都已經是早晨了,所以才去這場彌撒。他們只想趕快應付過去,趕快洗清罪惡,然後回家安安心心睡一天大覺。
法蘭西的星期六是從去垃圾回收站開始的。和其他布魯克林的小孩一樣,她和弟弟尼力會在外頭撿些碎布、紙張、金屬、橡膠等破爛,藏在地下室上鎖的箱子裡,或是藏在床底下。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放學回家的路上,法蘭西總是慢慢走,邊走邊看排水溝,希望能找到菸盒的錫紙或口香糖的包裝紙。之後她會將這些東西放在小罐子的蓋子上熔化;垃圾站不收沒有熔化的錫球,因為很多孩子會將鐵墊圈放在中間增加重量。有時候尼力會找到汽泡礦泉水的罐子,法蘭西就幫他把壺嘴弄下來,熔化出其中的鉛來,要不然垃圾站的人怕汽泡水公司的人找麻煩,不敢回收完整的壺嘴。壺嘴是好貨,化掉後能賣到五分錢。
法蘭西和尼力每天晚上都到地下室,把升降機架上當日收的破爛全倒出來。他們的媽媽是清潔工,所以兩個孩子享有這項特權,能下到地下室去。他們會把架子上的紙張、碎布和能回收的瓶子全都拿走。紙張不值什麼錢,十磅才能賣一分錢;碎布一磅兩分錢;鐵是一磅四分錢。銅是好貨,一磅能賣一毛錢。有時候法蘭西走財運,找到廢棄的煮衣鍋鍋底,就用開罐器將它掰下來,折起,錘打,再折,再錘打。
星期六早晨九點一過,孩子們就從大街小巷鑽出來,紛紛湧到曼哈頓大道這條主街上,再沿著曼哈頓大道慢慢走到斯科爾斯街。有的孩子把破爛直接拿在手上;有的則拖著用木頭肥皂盒做的推車,盒子下頭裝有穩當的木頭輪子;還有幾個推著裝得滿滿的嬰兒車。
法蘭西和尼力兩個人把他們收集到的破爛裝進一只麻袋裡,一人拎著一端在街上拖著走,沿著曼哈頓大道,路過茂吉街、滕.艾耶克街、斯塔格街,最後來到斯科爾斯街。這都是些醜陋的街道,名字倒是很漂亮。每條偏街陋巷裡都會有衣衫襤褸的髒小孩鑽出來,匯入街上的破爛大軍,一同前往卡尼的垃圾站。
他們去的路上會遇到其他空手折返的孩子,這些孩子已經把破爛賣掉,賺來的錢也都花得一點不剩了。現在他們大搖大擺地走回來,還嘲笑起其他小孩。
「撿破爛的!撿破爛的!」
聽到這嘲笑,法蘭西的臉立刻就脹紅了。她知道這些罵人的人自己也是撿破爛的,可是這也無濟於事。其實過一會兒她弟弟也會和他的小夥伴們一起空著手大搖大擺地走回來,同樣嘲笑後來的人,可是這也安慰不了她,她就是覺得很害臊。
卡尼在一個搖搖欲墜的馬棚裡經營他垃圾回收的生意。轉過街角,法蘭西就看到那兩扇大門被鉤子鉤在牆邊,友善地敞開著;那個不起眼的磅秤的指針晃了一下,法蘭西暗自想像那是它對她睞了睞眼,表示歡迎。然後她看到卡尼,他鐵鏽色的頭髮、鐵鏽色的鬍鬚和鐵鏽色的眼睛就守在磅秤邊。卡尼更喜歡女孩子些,如果他伸手捏女孩子臉蛋的時候女孩不退縮,他就會多給一分錢。
因為有可能獲得這額外的好處,尼力閃到一邊,讓法蘭西獨自把麻袋拖進馬棚。卡尼跳上前,把袋子裡的東西倒在地上,然後先在法蘭西臉上捏了一把。當他將破爛堆上磅秤的時候,法蘭西眨了眨眼,好讓眼睛適應馬棚內的黑暗。她能聞到空氣中的苔蘚味和濕碎布的臭味。卡尼眼睛朝磅秤的指針瞟了一眼,然後說了兩個字,也就是他的出價。法蘭西知道他不讓人討價還價,只好點頭答應。卡尼把磅秤上的破爛掃下去,叫她等著,然後自己把廢紙扔到一個角落,碎布扔往另外一個角落,最後再將金屬挑出來。這一切弄完後,他才把手伸進口袋,扯出一個用蠟線拴著的舊皮袋,掏出一枚枚分幣來;分幣都發綠了,本身就像破爛似的。法蘭西低聲說了聲:「謝謝您。」這時候卡尼賊賊地看了她一眼,然後又伸手狠狠捏了她的臉蛋一把。法蘭西忍住沒有退縮。卡尼笑了,又多給了她一分錢。然後他的舉止陡然一變,活力十足地大聲吆喝起來。
「過來,」他對下一個男孩喊道,「把鉛拿出來!」他等著孩子們發笑,「我可不要什麼破銅爛鐵啊!」孩子們十分配合地笑了起來。這笑聲聽來有如迷失羔羊的咩咩叫喚,不過卡尼似乎心滿意足了。
法蘭西走出去,向弟弟報告成果:「他給了我一毛六,還有捏臉給的一分錢。」
「那一分錢歸你。」他說。這是兩人之間很早就有的協定。
法蘭西將一分錢放進洋裝的口袋裡,餘下的交給弟弟。尼力才十歲,比法蘭西小一歲,不過他是男孩,所以錢的事情歸他管。他將這些分幣小心翼翼地分好。
「八分錢放進存錢筒。」這是規定。他們不管在哪裡賺到錢,都要將一半存入存錢筒裡。存錢筒是個錫罐子,釘在衣櫥裡最陰暗的角落。「四分錢歸你,四分錢歸我。」
法蘭西把歸存錢筒的錢用手帕包好,打上結。她看著自己的五分錢,很高興這些錢能換成一個五分硬幣。
尼力把麻袋捲起來,用手臂夾著,衝進查理廉價雜貨店;法蘭西跟在他身後。查理廉價雜貨店是一家廉價糖果店,緊挨著卡尼的垃圾回收站,是專門為了垃圾站這邊的生意而開的。星期六結束後,糖果店的錢筒裡就會裝滿發綠的分幣。根據某個不成文的規定,這店只有男孩才能進去,所以法蘭西並沒有進去,而是靠在門口。
男孩們的年齡從八歲到十四歲不等,看上去都一個樣,全都穿著鬆垮垮的燈籠褲,戴著破破爛爛的鴨舌帽。他們隨處站著,手插在口袋裡,瘦瘦的肩膀用力朝前弓著。他們長大後也會是這個模樣,用一樣的姿勢站在別處。唯一不同的是,長大後他們的嘴邊會總叼著菸,那菸就像是永遠黏在嘴上一般。他們帶著口音說起話來,嘴角的菸就跟著一起一伏。
……
下午的斜陽照在法蘭西.諾蘭家爬滿苔蘚的院子裡,把破舊的木籬笆曬得暖暖的。看著斜射下來的一縷縷陽光,法蘭西心頭湧出一種美好的感覺來。這樣的感覺,她回憶起一首詩歌時也有過;那是一首在學校裡背誦過的詩:
在這片原始森林,
松樹和鐵杉陣陣低語
苔蘚如鬚,
翠綠滿身黃昏中佇立,依稀朦朧如一個個督伊德僧侶。
法蘭西院子裡的樹既不是松樹,也不是鐵杉。樹上的綠色枝條從樹幹向四周發散,枝條上長滿了尖尖的葉子,使得整棵樹看起來如同無數把撐開的綠傘。有人稱它為天堂樹,因為不管它的種子落到什麼地方,都會長出一棵樹來,向著天空努力生長。這樹或長在四周圍滿木籬的空地上,或從棄置的垃圾堆裡鑽出來;它也是唯一能在水泥地上生長的樹。它長得高大茂盛,而且只長在住宅區。
星期天下午,你去散散步,走到一個不錯的住宅區,高雅的住宅區,看到別人家通往院子的鐵門後有這樣一棵小樹,你就知道布魯克林這一帶快變成住宅區了。樹懂,樹會打前鋒。到了後來,便漸漸會有些貧窮的外國人跑來,把破舊的褐砂石房整修成平房,把羽毛褥墊從窗戶裡推出來曬;等到此時天堂樹已經長得鬱鬱蔥蔥了。這種樹習性如此,就像窮人一樣。
法蘭西的院子裡長的就是這種樹。在她三樓的太平梯附近,樹上的小「傘」一個個蜷曲過來,讓一個坐在消防梯上的十一歲女孩覺得自己就住在樹上。夏天的每個星期六下午,法蘭西都這麼想像著。
啊,布魯克林的星期六多麼美好啊!啊,到處都是那麼美好啊!星期六是發薪日,也是個週末假日,卻又不用守星期天那些清規戒律。人們有錢出去買東西,在這一天好好吃一頓飯、喝醉、約會、做愛、熬夜、唱歌、放音樂、打架、跳舞,而且因為次日就是自由自在的一天,還可以睡個懶覺—至少可以睡到晚場的彌撒。
星期天,大部分人會擠著去參加十一點鐘的彌撒。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很少的一些,會去參加六點鐘那場。人們誇他們趕得早,但其實他們不配這樣的誇獎,因為他們根本是在外頭待得太久,回到家的時候都已經是早晨了,所以才去這場彌撒。他們只想趕快應付過去,趕快洗清罪惡,然後回家安安心心睡一天大覺。
法蘭西的星期六是從去垃圾回收站開始的。和其他布魯克林的小孩一樣,她和弟弟尼力會在外頭撿些碎布、紙張、金屬、橡膠等破爛,藏在地下室上鎖的箱子裡,或是藏在床底下。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放學回家的路上,法蘭西總是慢慢走,邊走邊看排水溝,希望能找到菸盒的錫紙或口香糖的包裝紙。之後她會將這些東西放在小罐子的蓋子上熔化;垃圾站不收沒有熔化的錫球,因為很多孩子會將鐵墊圈放在中間增加重量。有時候尼力會找到汽泡礦泉水的罐子,法蘭西就幫他把壺嘴弄下來,熔化出其中的鉛來,要不然垃圾站的人怕汽泡水公司的人找麻煩,不敢回收完整的壺嘴。壺嘴是好貨,化掉後能賣到五分錢。
法蘭西和尼力每天晚上都到地下室,把升降機架上當日收的破爛全倒出來。他們的媽媽是清潔工,所以兩個孩子享有這項特權,能下到地下室去。他們會把架子上的紙張、碎布和能回收的瓶子全都拿走。紙張不值什麼錢,十磅才能賣一分錢;碎布一磅兩分錢;鐵是一磅四分錢。銅是好貨,一磅能賣一毛錢。有時候法蘭西走財運,找到廢棄的煮衣鍋鍋底,就用開罐器將它掰下來,折起,錘打,再折,再錘打。
星期六早晨九點一過,孩子們就從大街小巷鑽出來,紛紛湧到曼哈頓大道這條主街上,再沿著曼哈頓大道慢慢走到斯科爾斯街。有的孩子把破爛直接拿在手上;有的則拖著用木頭肥皂盒做的推車,盒子下頭裝有穩當的木頭輪子;還有幾個推著裝得滿滿的嬰兒車。
法蘭西和尼力兩個人把他們收集到的破爛裝進一只麻袋裡,一人拎著一端在街上拖著走,沿著曼哈頓大道,路過茂吉街、滕.艾耶克街、斯塔格街,最後來到斯科爾斯街。這都是些醜陋的街道,名字倒是很漂亮。每條偏街陋巷裡都會有衣衫襤褸的髒小孩鑽出來,匯入街上的破爛大軍,一同前往卡尼的垃圾站。
他們去的路上會遇到其他空手折返的孩子,這些孩子已經把破爛賣掉,賺來的錢也都花得一點不剩了。現在他們大搖大擺地走回來,還嘲笑起其他小孩。
「撿破爛的!撿破爛的!」
聽到這嘲笑,法蘭西的臉立刻就脹紅了。她知道這些罵人的人自己也是撿破爛的,可是這也無濟於事。其實過一會兒她弟弟也會和他的小夥伴們一起空著手大搖大擺地走回來,同樣嘲笑後來的人,可是這也安慰不了她,她就是覺得很害臊。
卡尼在一個搖搖欲墜的馬棚裡經營他垃圾回收的生意。轉過街角,法蘭西就看到那兩扇大門被鉤子鉤在牆邊,友善地敞開著;那個不起眼的磅秤的指針晃了一下,法蘭西暗自想像那是它對她睞了睞眼,表示歡迎。然後她看到卡尼,他鐵鏽色的頭髮、鐵鏽色的鬍鬚和鐵鏽色的眼睛就守在磅秤邊。卡尼更喜歡女孩子些,如果他伸手捏女孩子臉蛋的時候女孩不退縮,他就會多給一分錢。
因為有可能獲得這額外的好處,尼力閃到一邊,讓法蘭西獨自把麻袋拖進馬棚。卡尼跳上前,把袋子裡的東西倒在地上,然後先在法蘭西臉上捏了一把。當他將破爛堆上磅秤的時候,法蘭西眨了眨眼,好讓眼睛適應馬棚內的黑暗。她能聞到空氣中的苔蘚味和濕碎布的臭味。卡尼眼睛朝磅秤的指針瞟了一眼,然後說了兩個字,也就是他的出價。法蘭西知道他不讓人討價還價,只好點頭答應。卡尼把磅秤上的破爛掃下去,叫她等著,然後自己把廢紙扔到一個角落,碎布扔往另外一個角落,最後再將金屬挑出來。這一切弄完後,他才把手伸進口袋,扯出一個用蠟線拴著的舊皮袋,掏出一枚枚分幣來;分幣都發綠了,本身就像破爛似的。法蘭西低聲說了聲:「謝謝您。」這時候卡尼賊賊地看了她一眼,然後又伸手狠狠捏了她的臉蛋一把。法蘭西忍住沒有退縮。卡尼笑了,又多給了她一分錢。然後他的舉止陡然一變,活力十足地大聲吆喝起來。
「過來,」他對下一個男孩喊道,「把鉛拿出來!」他等著孩子們發笑,「我可不要什麼破銅爛鐵啊!」孩子們十分配合地笑了起來。這笑聲聽來有如迷失羔羊的咩咩叫喚,不過卡尼似乎心滿意足了。
法蘭西走出去,向弟弟報告成果:「他給了我一毛六,還有捏臉給的一分錢。」
「那一分錢歸你。」他說。這是兩人之間很早就有的協定。
法蘭西將一分錢放進洋裝的口袋裡,餘下的交給弟弟。尼力才十歲,比法蘭西小一歲,不過他是男孩,所以錢的事情歸他管。他將這些分幣小心翼翼地分好。
「八分錢放進存錢筒。」這是規定。他們不管在哪裡賺到錢,都要將一半存入存錢筒裡。存錢筒是個錫罐子,釘在衣櫥裡最陰暗的角落。「四分錢歸你,四分錢歸我。」
法蘭西把歸存錢筒的錢用手帕包好,打上結。她看著自己的五分錢,很高興這些錢能換成一個五分硬幣。
尼力把麻袋捲起來,用手臂夾著,衝進查理廉價雜貨店;法蘭西跟在他身後。查理廉價雜貨店是一家廉價糖果店,緊挨著卡尼的垃圾回收站,是專門為了垃圾站這邊的生意而開的。星期六結束後,糖果店的錢筒裡就會裝滿發綠的分幣。根據某個不成文的規定,這店只有男孩才能進去,所以法蘭西並沒有進去,而是靠在門口。
男孩們的年齡從八歲到十四歲不等,看上去都一個樣,全都穿著鬆垮垮的燈籠褲,戴著破破爛爛的鴨舌帽。他們隨處站著,手插在口袋裡,瘦瘦的肩膀用力朝前弓著。他們長大後也會是這個模樣,用一樣的姿勢站在別處。唯一不同的是,長大後他們的嘴邊會總叼著菸,那菸就像是永遠黏在嘴上一般。他們帶著口音說起話來,嘴角的菸就跟著一起一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