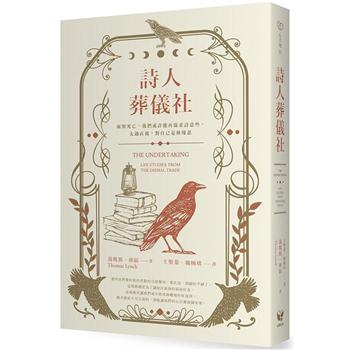第一章 入土為安(摘錄)
……一個人的時間到了就會死,不管是一週裡哪一天,或一年裡哪個月份,如果就季節因素來考量,人也沒有明顯喜歡死在哪個季節。而星星怎麼排列,是不是滿月,或是教會年曆上某個節日也跟死亡沒什麼關係。就死亡的地點來說,哪裡都可以死。有人可以在自己的雪佛蘭車子裡或養老院裡站著或躺著死,也有人死在浴缸裡,在州際公路上,在急診室或手術室,或在寶馬轎車裡。不知道是不是我們把更多的設備跟死亡相提並論,或者是我們更看重死亡這件事,死在一些用縮寫表示的地點似乎比較不一樣,比如說死在加護病房(ICU)好像就比死在格林次布萊爾療養之家來得好,但事實還是一樣,死者不在乎這個。就這點來說,我埋葬和焚化的死者和以前並沒有兩樣,因為他們的時間和空間已經是極不重要的事。其實,喪失空間時間感正是大事即將發生前第一個確切的兆頭。接下來便是停止呼吸。在這個時候,如果是胸部中槍或是外傷休克,肯定要比中風或是冠狀動脈硬化來得引人注目,不過死了之後,怎麼死的就完全不重要了。任何一種死法都行,因為死者不在乎這個。
死的是誰也沒有那麼重要。像「我還好,你沒事吧,差點忘了說,他死了!」這樣的話,是用來安慰生者的。
正因如此,我們才在河裡打撈屍體,在飛機殘骸和爆炸現場搜尋死者。
正因如此,執行任務時失蹤(MIA)比當場宣告死亡(DOA)讓人更痛苦。
也正因如此,我們會開著棺木,齊聲朗讀訃聞。
知情比不知情好,而知道死的是你,比知道死的是我要好上太多。因為如果死的人是我,不管你好不好,或是他好不好,跟我都沒太大關係。你大可以直接轉身走人,因為死者不在乎這個。
當然,生者因為還活著,因為還有保險要操心,所以還是會在乎。現在,你可以看出其中的差異,以及為什麼我還待在這個行業。活著的人是很謹慎的,常常要注意很多事情。死去的人就沒什麼需要在意的,也可能是沒辦法在意了。不管是哪一種,死者不在乎這些。這些都是事實,沒什麼特別,想驗證也沒問題。
我的前岳母本身就是個沒什麼特別,也可以驗證的事實,她老是喜歡像詹姆斯‧卡格尼(注1)那樣虛張聲勢,把一些話掛在嘴邊,像是「我死的時候,只要找個盒子把我丟進去,再找個坑扔了就行了。」不過,每次我只要提醒她,我們其實就是像她說的那樣去處理每個人,她就會一臉不高興,脾氣也變得有點暴躁。
過沒多久,在大家享用肉捲和青豆時,她必定又會冒出這句:「我死的時候,就把我燒了,骨灰撒了就好。」
我前岳母想用這種無所謂的口氣裝勇敢。這時候孩子們會停下刀叉,面面相覷。我太太就會求他老媽:「噢,媽,別這樣說。」我則掏出我的打火機開始把玩。
無獨有偶,我和這個女人的女兒結婚時,幫我證婚的神父和我前岳母是一個樣。這個傢伙熱愛高爾夫,金聖杯和愛爾蘭亞麻布做的法衣,開著酒紅色內裝的黑頭大轎車,總是覬覦主教職位。有一天在離開墓地的時候,突然福至心靈地指示我:「不要為我準備銅棺,不要!先生。不要蘭花,不要玫瑰,也不要加長型禮車。我只要一具素面松木薄棺,一壇安靜的,不焚香也不奏樂的小彌撒,然後把我葬在窮人墓地。不要任何浮誇的排場。」
他解釋,他想要的,是成為一個樸實,智德,虔誠,節儉的典範,這是所有神職人員和基督徒(表面上)應有的美德。我告訴他不需要等到那時候,他今天就可以展開他的典範大業,他可以不再去鄉村俱樂部,不再去公共球場拿著高爾夫球桿亂揮,把他的凱迪拉克布魯姆豪華大車賣掉換一部二手雪佛蘭。然後再遠離他的高檔富樂紳皮鞋,喀什米爾羊毛披肩和頂級肋排,還有歡樂的賓果之夜和教堂建築基金,我的基督啊,那他簡直活脫脫就是聖方濟或者聖安多尼了。結果呢?我那時就說,我很願意在這方面幫忙。我會很高興地把他的積蓄和信用卡都送給教區內需要救助的窮人,萬一接到他不幸的消息,我會按照他的希望好好埋葬他,也不收他的錢,到了那個時候,他也應該習慣了那種簡樸的生活方式。他聽了我的話,只是一言不發地看著我,眼神讓我想到愛爾蘭故事裡的牧師,在他多年前詛咒斯維尼永遠變成小鳥時必定是那副惡狠狠的表情。
當然了,我想告訴這傢伙的話是,當個死的聖人並不比一棵枯死的喜林芋或是一條死掉的蝴蝶魚更合算。活著是很辛苦的,一直都是。聖人活著的時候一直感受著這個苦難塵世中的烈焰與傷痕,禁慾的苦痛與道德的煎熬。等到死了,他們還讓自己的遺骨繼續為世人奔忙,就像我想告訴這個神父的,因為死者不在乎。
只有活人才在乎。
很抱歉我要把這句話一再重複,因為這就是我這個行業的最大重點,那就是,一旦你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就是一切對你做,為你做,和你一起做,跟你有關的事,對你都不再有好壞可言,而我們所做的不管是好是壞,都會隨著時間由生者,以及你死亡時真正在乎這件事情的人來承受。生者必須和它一起活下去,而你不用。他們要接受的是你的死所帶來的悲傷或喜悅,損失或收穫,是回憶裡的傷痛和快樂,還有我們提供喪葬服務之後的清單,和信箱裡等著付錢的支票。
這是事實,不證自明,但所謂的不證自明也只是看來如此,現在想想,最沒辦法理解這個事實的一群人就是那些很久沒聯絡的姻親,教區的神父,在理髮店或是雞尾酒會以及家長會上永遠只會找我搭訕的陌生人,他們總是拚命地,或者覺得有責任讓我瞭解,當他們死掉的時候他們想要一個怎麼樣的葬禮。
就安息吧,我這樣回答。
一旦你死了,就把腳一翹,就此收工,然後讓你的丈夫或妻子,小孩或兄弟姊妹去決定你是要用埋的還是用燒的,是要用大砲打到很遠的地方,還是丟在哪條水溝裡風乾。這時候輪不到你插手,因為死人是不在乎的。
每個正常的人在內心裡對死亡都有種恐懼,那正是人們總是找我預演葬禮的另一個理由。這樣做很健康。可以讓我們不去車陣裡胡搞,我是說,我們應該把這招傳授給孩子們。
有件事在我約會過的女人,地方扶輪社員,和我小孩的玩伴之間廣為流傳,就是我,作為這兒的殯葬師,對於死人有某種不尋常的迷戀,或有某些特殊興趣,或是掌握了一些不為人知的事,甚至對它們產生了深厚的感情。這些人認為,(有些人說不定還有很站得住腳的理由),我要的就是他們的屍體。
這是個有趣的想法。
但事實是這樣的。
我們人類和許多其他物種在活著的時候就會被一連串的苦難折磨,死掉只不過是其中最慘也是最後的一個。這些災難可能包含但不限於以下這些:牙齦炎,結腸梗塞,離婚爭議,被查稅,心裡不舒服,現金流短缺,政治動盪等等,等等,等等。苦難永遠沒完沒了。死人對我的吸引力,和牙醫看見你的爛牙齦,醫生看見你的爛內臟,還有會計師看見你亂成一團的財務報表沒有兩樣。我對苦難已經膩了,不管它是發生在銀行家或律師,牧師或政客身上,因為苦難不在乎你是誰,它無所不在。苦難是空頭支票,是前任配偶,是街頭黑幫,是國稅局,它們就像死人,冷血無情,就像死人,什麼都不在乎。
而千真萬確的事就是死人什麼都不在乎。
的確如此,一點不假,他們理所當然地不在乎。
上個星期日的早上,米羅‧洪斯比死了。洪斯比太太在凌晨兩點鐘打電話過來,說米羅已經「過期」了,問我是不是可以過來看看,說得好像米羅是那種可以更新或是用某種方式就能變好的東西一樣。兩點的時候,我從深層睡眠中被狠狠叫醒,心裡只想拿個廿五分錢塞給米羅,等到早上天亮再叫我。但是米羅已經死了。就在那一刻,那一瞬間,米羅撒手而去,再也不會回來。他留下了洪斯比太太和子女,丟下了他開的自助洗衣店裡的女員工,離開了退伍軍人中心裡的戰友,放棄了共濟會總會長的職位,其他甩開的還有第一浸信會的牧師,郵差,分區管理委員會,市議會,和商會。他把我們所有人都拋在背後,也把我們心中對他的情感,無論是背叛,是體貼,都丟掉了。
米羅死了。
他就像卡通裡演的,眼睛打上一個大大的叉叉,再也不會睜開,燈光就此熄滅,簾幕落下。
沒人幫得上他的忙,他也不會再受到什麼傷害。
米羅就是死了。
正因為如此,我沒有緊張過度,只是平常心地把咖啡喝完,簡單刮了鬍子,戴上霍姆絨帽,穿上大衣,暖一下死亡馬車,接著就為了米羅,在一大清早往高速公路前進。應該說,米羅已經跟此行無關。我去是為了她,為了在同一時刻,同一個瞬間,就像水結了冰一樣,變成了寡婦洪斯比的她。我去是為了她,因為她還會流淚,還會在乎,還會祈禱,也還會付錢給我。
米羅是在一家非常先進的醫院裡去世的。每一扇門上都有標示,告訴經過的人這裡是哪個部門,做的是什麼醫療程序,或是跟身體哪個部分相關的。我喜歡把這些標示的字全部連在一起想,一個接著一個的,最後可以顯示出一個人的身體狀況,不過這些字從來沒湊起來過。米羅剩下的,也就是他的遺體放在地下室,剛好在在「收發處」和「洗衣間」之間。如果米羅還是對什麼事都很感興趣,那麼米羅一定很中意這個地方的標示。米羅的房間稱為「病理室」。
用醫學科技的角度來看死亡,這個字所強調的就是疾病。
我們人類永遠是因身體裡某些地方衰竭,或異常,或什麼東西不足,或出現障礙,或停止工作,或是一些意外事件。這些情況有些是慢性,有些是急性。死亡證明書裡的文字如同某種專門描述缺陷的語言,像米羅的證明上就寫著「心肺功能衰竭」。同樣的,悲痛不已的洪斯比太太會被說成是情緒失控,崩潰,或者瓦解,彷彿她身體裡有一些結構出現了歪斜。那好像在說,死亡和悲傷並不是萬物秩序的一部分,好像說米羅的死和他太太的哭泣,都是,或者說理當是造成麻煩的源頭。對洪斯比太太來說,「表現很好」意味著她努力撐住,抵擋了這場風暴,或是為了孩子堅強起來。我們有很多藥商樂意在這方面幫助她。當然了,對於米羅來說,「表現很好」指的是他回到醫院樓上,苦苦維持下去,讓所有的讀表和顯示器繼續嗶嗶地運作。
可是米羅已經到了樓下,就在收發處和洗衣間之間的房間裡,在裡面一個不鏽鋼抽屜裡,全身從頭到腳包著白色的塑膠布,而且因為他的頭小,肩膀寬,肚子肥,腿又細,加上從腳踝上拖著一條白色的綑綁線,配上大拇指上的牌子,他的樣子,不管怎麼看,就像一尾比實物大很多的精蟲。
我幫他簽了名,帶他離開那裡。某個程度上,我仍然覺得米羅會在乎自己現在的情況,但是我們都很清楚,其實他一點也不在乎,因為死人是不會在乎的。
回到葬儀社,到了樓上的防腐室,門上標示著「非請勿入」,米羅‧洪斯比正靜靜地躺在一張瓷桌上,上方是照明的日光燈。塑膠布已經解開,手腳得以伸展出來,米羅看起來比較像他原來的樣子。眼睛睜得很大,嘴巴開開的,像是受到驚嚇似的回到我們的世界。我把他身上的毛刮乾淨,闔上眼睛和嘴巴。我們把這部分的工作稱為「五官定位」。不論眼睛或嘴巴,都是五官的一部分,現在它們和當初活著時開開合合,專注或表情豐富地想告訴我們什麼的樣子再也不一樣。死的時候,它們要告訴我們的就是,它們什麼也不能做了。最後要仔細處理的是米羅的手,要把雙手交疊之後放在肚臍上,表現出一種放鬆安詳,不需要再操心的姿態。
他的手也是一樣,什麼也不能做了。
我把他的雙手洗乾淨,然後才放到肚臍上。
我太太幾年前搬出去時,孩子留在我的身邊,他們那堆髒兮兮的換洗衣服也一起留下來。在一個小城市裡,這是個大消息。各種正反面流言把這件事炒得沸沸揚揚。但是當人人都在談這件事的時候,卻沒有人知道到底該跟我說什麼。我想他們也很無助。所以他們送來燉菜和燉牛肉,帶我的孩子出門看電影,划獨木舟,然後帶著他們身邊年輕的妹妹來看我。當時米羅就開著他的洗衣店小貨車一週過來繞兩次,這樣持續了兩個月,直到我找到管家為止。米羅會在清早收走五大籃髒衣服,然後在午餐時間前後送回來,乾乾淨淨,摺得平平整整。我沒有要求他這麼做,我跟他不熟,也從來沒有去過他家或他的洗衣店。他太太完全不認識我前妻,而他的孩子也已經老到沒辦法跟我的孩子一起玩了。
管家開始上班之後,我去跟米羅道謝兼付帳單。這段時間的髒衣服份量,清洗,烘乾,洗衣精,漂白水,柔軟精,零零總總的費用加起來,我估計至少也要六十塊美金。我問米羅,他拯救了我的性命和孩子們的生活,讓我們有乾淨衣服穿,有毛巾和床單可以用,這樣收貨送貨,把衣服疊得整整齊齊還依尺寸大小分類,要收多少錢呢?「這就別放在心上了,」米羅這樣說,「做人互相互相吧,『單手洗不到自己,總是需要另一隻手幫忙的。』」
我把米羅的右手放在他的左手上,然後又換過來,最後又換回去。然後我決定怎麼放都無所謂。反正另一隻手總會來幫忙的。
整個打理屍體的過程花了我大約兩小時。
等我完成所有的工作,天已經大亮了。
每個星期一早上,厄尼斯特‧富勒都會到我辦公室來。他在韓戰時受過某種慘無人道的傷害。地方上沒人知道傷害的細節究竟是什麼。厄尼斯特‧富勒沒有跛,也沒缺手斷腳,所以大家認為,大概是他在韓國看見了什麼不該看的,才變成現在這副有點傻氣的模樣,偶爾一臉茫然。他是那種整天都在散步的人,但走到一半會突然收腳停住,只為了要思索垃圾,飲料瓶蓋和口香糖紙的意義。厄尼斯特‧富勒有著緊張兮兮的笑容,握手的時候像條死魚。他戴著棒球帽和厚厚的酒瓶底眼鏡。每個星期日晚上,厄尼斯特會去超市買下收銀臺前所有的小報,那些報上的頭條通常不外乎什麼連體雙胞胎,電影明星或幽浮之類。厄尼斯特不但讀東西很快,還是個數學奇才,但是因為他的戰爭傷害,他從來沒能保住工作,也再沒去應徵。每週一早上,厄尼斯特會把一些頭條新聞的剪報帶來給我看,像是「墓地情報:兩百七十三公斤重的男人砸穿棺底」或是「明星專屬防腐專家表示:貓王不朽」等等。米羅過世的那個星期一早上,厄尼斯特照例帶來剪報,內容是關於西安格利亞某處一個裝滿骨灰的骨灰罈,它會咕噥,呻吟,偶爾還會吹口哨,讓人以為接下來它就要開口說話了。英國的科學家們提不出合理的解釋,雖然他們已經做過一些測試了。那罈骨灰的未亡人和九個孩子一起被撇下,名下毫無房產,但不管怎樣,這時她深信她的親密愛人,那位體積縮小了很多的丈夫想告訴她大樂透的明牌。「傑基絕對不會辜負我們的期待,」她說,「他深愛家人,勝過一切。」報導附了一張雙方合照,一方是寡婦,一方是骨灰罈。一方是生,一方是死。一方是血肉之軀,一方是冰冷銅甕。就像勝利牌留聲機和那隻廣告上出名的狗,她對骨灰罈豎起耳朵,靜靜等待著。
我們總是在等。等待好消息或者明牌。等待一個徵兆或奇蹟,等待我們所愛的亡者捎來一些消息,告訴我們他仍然對人世心心念念。當他們做出一些比較明顯的事的時候,我們會非常快樂,比如說從墳墓站起來,砸穿棺底,或者在我們的清明夢境中現身說話。我們歡喜不盡,彷彿亡者依然牽掛,還有一堆事待辦,彷彿他尚在人間。
但是令人悲傷而且眾所皆知的事實是,我們大部分人都會乖乖待在棺木裡,一死就死很久,骨灰罈和墳墓也永遠不會發出任何聲音。我們是不是理性,有沒有輓歌,墓碑上刻了什麼,有沒有辦大彌撒,和我們上或上不了天堂完全沒有關係。我們生命的意義,和一切相關的回憶,都屬於還活著的人,就像我們喪葬業者所做的也是為了活著的人。無論死去的人還有些什麼,都只留存在活著的人的「相信」裡面。
在這兒,冬天下葬的時候我們會先幫墳土加熱,就像挖掘前的某種前戲,讓揪緊土壤的冰在教堂司事和他的挖土機上場前先放鬆放鬆。我們在星期三葬了米羅,用的是橡木棺材,位置在土壤結冰線的下方。我們心懷感激,因為這場葬禮為米羅這一生畫下了句點。米羅本身變成一種概念,一個他人心中永遠不變的形象,一個過去式,讓未亡人食不下嚥,睡不安枕。他平常流連的地方再也不見他的身影,跟他有關的生活作息無以為繼。那總會來幫忙我們的另一隻手,成了截肢後早已不存在,卻仍隱隱作痛的幻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