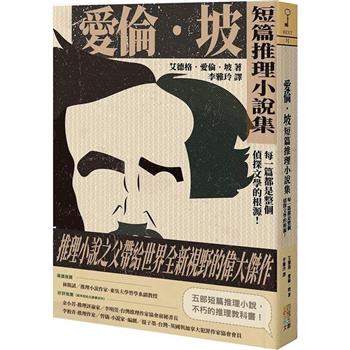〈莫爾格街凶殺案〉
賽蓮唱的是什麼歌,阿基里斯女扮男裝時叫的是什麼名字,縱然這些問題都令人費解,也總能猜破。——托馬斯・布朗爵士
智力特質中所謂的分析能力,本質上很少能被深入分析,我們只能透過它的成效來感受這種能力的存在。當一個人擁有或能展現出卓越的分析能力時,這種能力會為他帶來巨大的快樂和滿足感。就像一個體能出眾的人自豪於肌肉的力量,喜歡參與各種體育活動一樣,擅長分析的人則在解決棘手的問題、釐清錯綜複雜的道德困境中找到他們的榮耀和滿足,即使是最平凡無奇的任務,他們也能汲取樂趣。這樣的人熱愛挑戰謎題、難題和象形文字;他們在解開這些謎題時所展現的聰明才智,對於一般人來說似乎觸及超自然的境界。他們透過洞察方法的本質和精髓來解開謎題,其過程看似全憑直覺,卻又深刻精確。
解謎的才能很可能透過學習數學而顯著提升,尤其是透過學習數學的最高領域——其特點是從結果反推到原因的逆向思維,然而僅將這種思維稱為分析學似乎有失公允,好像分析是該領域所獨有的技能。舉個例子,一位下棋的棋手可以毫不費力地進行遊戲,無需深入分析棋局,這表示認為棋類遊戲能提高智力不過是一種誤解。我現在並非在撰寫論文,只是透過隨意的觀察展開一個特別的故事;因此,我要借此機會來斷言,看似簡單而不具浮誇特質的西洋跳棋,實際上在促進深層思維能力方面或許更有效。西洋棋以其奇特且多樣的移動方式而聞名,牽一髮動全身,但其複雜性常被誤解為深奧(這是常見的誤解)。在下西洋棋時需高度集中注意力,一時疏忽就可能導致劣勢或失敗,棋局中可能的移動選擇不僅繁多且錯綜複雜,因此犯錯的機會也隨之增加;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約九成),贏得比賽的是更專注的棋手,而非那些思維更為敏銳的玩家。反之,在西洋跳棋中,由於移動方式單一且變化較少,一時疏忽的可能性相對減少,注意力也不需如此高度集中,任何一方獲得的優勢,仰賴的都是聰明才智。具體而言,讓我們設想一場西洋跳棋比賽,其中棋盤上僅剩四個國王作為棋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預計棋手不會犯任何疏忽,顯然在這樣的遊戲設定中,假設棋手的技巧相當,那麼勝利只能透過獨具匠心的棋步來實現,這需要倚賴非凡的智力。當分析者面對缺乏可用資源、工具或策略的情境時,他會深入洞悉對手的思考模式,設身處地去想像對方可能採取的策略,並且常常能一眼識破那些唯一能引導對方走入誤區(有時這些策略甚至顯得過於簡單)的方法,進而誘使對手做出匆忙且錯誤的決策。
長久以來,人們普遍認為惠斯特紙牌可以提高所謂的計算能力;且那些高智商的人似乎對這種牌戲擁有難以言喻的熱愛,同時他們對西洋棋抱有一定的輕蔑,認為它過於輕浮。毫無疑問,沒有其他活動能像惠斯特紙牌那樣有效地考驗一個人的分析能力。在基督教世界中,最優秀的西洋棋手可能僅是該領域的佼佼者;然而,擅長惠斯特紙牌的人則顯示出在所有智力競技活動中都擁有勝出的能力。我所指的擅長不僅是牌技高超,還包括對牌局的深刻洞察,以及理解所有可在遊戲中理智利用以獲取優勢的因素,這些因素不僅多樣,而且往往隱藏在普通人難以觸及的思維深處。善於集中注意力的西洋棋玩家在玩惠斯特紙牌時也每每表現出色,因為惠斯特紙牌的規則(這些規則建立在遊戲的基本機制上)清晰明確,易於理解,要求玩家具備出色的記憶力,並能按照這些「規則」進行遊戲,這些技能反映了一個玩家的遊戲水準。然而,超越遵循規則的範疇,分析者的真正能力才得以充分展現,他在靜默中進行大量的觀察和推理,或許其他隊友也做了同樣的事情;而兩者之間所獲得資訊範圍的差異,主要並不取決於推理的有效性,而在於觀察的品質,重點是知道自己觀察的目標是什麼。高段玩家的觀察力並不局限在牌局本身;他們也不會因為專注於牌局而忽視了牌局以外的事物,他們會仔細觀察隊友的臉部表情,將其與對手的表情進行比較,還會細心觀察其他玩家手中牌的組合和排序方式;常根據其他玩家看自己手中牌的方式來判斷他們可能持有的特殊牌,例如王牌和高分牌。隨著牌局的進展,他會留意每個人臉上表情的每一個細微變化,從中搜集思考的線索,包括篤定、驚訝、勝利或失望的表情差異。透過觀察玩家收取一輪贏得的牌,可以判斷出那個玩家是否能在同一花色中再贏一輪牌。他能從玩家把牌丟到桌上的方式中,辨別哪些是虛張聲勢出的牌。玩家不經意說出的話、一張牌的意外掉落或翻轉,可能暗示玩家感到焦慮或疏忽,因此沒有妥善保護自己的牌;其他玩家如何計算贏得的牌數和排列順序,他們的尷尬、猶豫、渴望或恐懼——這些都為觀察者提供了對實際局勢的線索,觀察者似乎憑藉直覺就能捕捉這些線索。在最初的兩三輪牌局之後,此人已經能夠完全掌握每位玩家手中的牌面,並能精準出牌,彷彿其他玩家都將自己的牌面亮給他看一般。
分析能力與豐富的創造力應該明確區分開來,儘管許多分析者擁有出色的創造力,但擁有創造力的人在分析方面卻常常表現出一定的不足。創造力通常透過建構力或組合能力展現,而骨相學家(雖然我並不完全認同他們的觀點)認為創造力是由大腦中的一個獨立器官控制,並將其視為一種原始能力。實際上,從那些智力上接近愚昧的人身上,我們常常可以觀察到這種建構力或組合能力的表現,這成為道德研究作家探討的一個有趣現象。創造力和分析能力之間的差異,遠大於幻想與想像力之間的差異,但這兩者的差異性質卻非常相似。實際上,你會發現那些具有創造力的人總是充滿了幻想,而真正具有想像力的人則在思維方式上以分析為主導。
針對上述提出的論點,我以接下來的故事為讀者提供解釋。
在十九世紀的某一年,從春暖花開至夏日的繁葉陰涼,我將自己留在巴黎這座城市,並認識了一位名叫C・奧古斯特・杜邦的先生,這位年輕紳士出身於一個優秀,甚至可說是顯赫的家族,但由於一連串不幸事件使他陷入貧困的境地,他原本充滿活力的性格也在困境中屈服。他不再參與社交生活,也不想改善自己的財富狀況。因為債權人對他的寬容,讓他保留一小部分遺產;憑藉這點收入以及極為節儉的生活方式,他得以滿足生活基本所需,但也別想購買奢侈品。事實上書本是他唯一的奢侈品,畢竟在巴黎購買書籍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情。
我們第一次相遇是在蒙馬特街上一家不起眼的圖書館,我們剛好都在找一本非常罕見的好書,這個機緣讓我們感覺更加投契。我們一次又一次相約見面,身為一個法國人,他在談論自己時總是自然坦率,他將自己的家族歷史對我娓娓道來,我也對此深感興趣,他的博學廣聞更是令我敬佩萬分;最重要的是,他狂野的熱情和生動的想像力在我內心點燃了火花。我在巴黎尋尋覓覓,終於遇見這樣一位知心好友,對我來說就像獲得了無價之寶;我也坦然向他表達心跡。隨後,我們安排一起居住,直至我在這個城市的停留結束;由於我的經濟狀況相對較好,足以負擔起房租和裝修開支,我們便以一種適合我們共同性格中某種奇特而陰暗的風格來裝飾我們的住所。我們找到一棟外觀怪異且年久失修的大宅,位於聖日耳曼郊區一個偏僻且荒涼的角落,建築本體看似搖搖欲墜,因為人們的迷信而長期荒廢,雖然我們並未深入探究背後的緣由。
如果外界知曉了我們在這棟大宅裡的生活方式,我們很可能會被視為瘋子——雖然是無害的那種。我們過著完全隱居的生活,不接待任何來客,並且絕不透露我們隱居的地點,甚至我的朋友們也對此一無所知;而杜邦已經隱居多年,外界幾乎沒有人知曉他的存在。對我們而言,彼此的存在就是我們唯一的世界。
我的朋友(我還能如何稱呼他呢?)對夜晚懷有一種非比尋常的迷戀,他鍾愛夜晚的深邃黑暗。我也默默地迎合他這奇異的喜好,就像順應他所有其他古怪想法一樣,我任由自己沉浸在他的狂野幻想之中。夜之女神不總是與我們同在;但我們可以假裝她的存在。每當黎明接近,我們便關閉古舊建築中所有凌亂的百葉窗,點燃一對散發著香氣的蠟燭,其微弱而陰森的光芒照亮著我們的空間。我們就在這樣的氛圍中沉浸於夢境之中——閱讀、寫作或對話,直到時鐘提醒我們真正的黑夜即將降臨。然後我們會攜手走上街頭,延續白日的話題,或者徘徊至深夜,尋求在繁華都市的光影交錯中,那由靜觀所帶來的無盡心靈激蕩。
在這些時刻,我不禁對杜邦獨特的分析能力感到驚嘆和敬佩(儘管從他豐富的想像力中,我已能預見他在這方面的才能),他似乎也非常享受於運用這種能力——即便他很少表現出來——同時他也毫不掩飾自己從中得到的樂趣。他經常低聲笑著向我誇耀,聲稱自己能洞悉大多數人的內心,並習慣以直接且令人震驚的方式來證明他對我了解有多深。在這些時刻,他的態度會變得冷漠而疏離;眼神變得空洞,面無表情;平時那富有韻律的男高音會變得尖銳,幾乎達到女高音的高度,若不是發音依然精確清晰,聽起來幾乎有些無禮。觀察他在這些情緒下的行為,常讓我思考古老哲學中所提及的雙面人格,同時幻想杜邦擁有創造性與解決性的雙重人格。
請別誤以為我是在描述某種神祕故事,或者撰寫浪漫小說。我對這位法國人的描述,不過是反映出他在激動或某種思維異常時的狀態。但是要進一步傳達和說明他在特定時刻言論的性質或特點,最好還是透過實際的例子來傳達和說明。
有一夜,我們在帕萊羅亞附近一道骯髒的長街上散步,似乎沉浸在各自的思緒之中,至少有十五分鐘沒有交談,突然間杜邦開口說道:
「他的個頭確實很小,比較適合在綜藝劇院演出。」
「這點毋庸置疑,」我不假思索回答道。剛開始並沒有注意到他方才說的話竟然與我腦中的默想不謀而合(因為我仍深陷在自己的思緒之中),過了一會兒回過神來,我才深感驚訝。
「杜邦,」我嚴肅地說,「這超出我的理解範圍,我真的被你嚇到了,我還以為自己的感官出現了幻覺,你怎麼可能知道我在想什——?」我停頓一下,想確定他是否真的知道我腦中想的人是誰。
「——尚蒂伊,」他說,「你為何要停頓?你當時在內心對自己說他的身形矮小,不適合演出悲劇角色。」
這正是我腦中所想。尚蒂伊是聖丹尼街上一個昔日曾當過皮鞋匠的人,他迷戀上舞台,試圖在克雷必倫的悲劇《薛西斯》中飾演薛西斯一角,為此受到大眾的嘲笑與譏諷。
「請告訴我,拜託,」我驚呼道,「究竟是什麼方法——如果真有這樣的方法——讓你能夠洞悉我的心思。」其實我遠比表現出來的還要驚訝。(未完)
賽蓮唱的是什麼歌,阿基里斯女扮男裝時叫的是什麼名字,縱然這些問題都令人費解,也總能猜破。——托馬斯・布朗爵士
智力特質中所謂的分析能力,本質上很少能被深入分析,我們只能透過它的成效來感受這種能力的存在。當一個人擁有或能展現出卓越的分析能力時,這種能力會為他帶來巨大的快樂和滿足感。就像一個體能出眾的人自豪於肌肉的力量,喜歡參與各種體育活動一樣,擅長分析的人則在解決棘手的問題、釐清錯綜複雜的道德困境中找到他們的榮耀和滿足,即使是最平凡無奇的任務,他們也能汲取樂趣。這樣的人熱愛挑戰謎題、難題和象形文字;他們在解開這些謎題時所展現的聰明才智,對於一般人來說似乎觸及超自然的境界。他們透過洞察方法的本質和精髓來解開謎題,其過程看似全憑直覺,卻又深刻精確。
解謎的才能很可能透過學習數學而顯著提升,尤其是透過學習數學的最高領域——其特點是從結果反推到原因的逆向思維,然而僅將這種思維稱為分析學似乎有失公允,好像分析是該領域所獨有的技能。舉個例子,一位下棋的棋手可以毫不費力地進行遊戲,無需深入分析棋局,這表示認為棋類遊戲能提高智力不過是一種誤解。我現在並非在撰寫論文,只是透過隨意的觀察展開一個特別的故事;因此,我要借此機會來斷言,看似簡單而不具浮誇特質的西洋跳棋,實際上在促進深層思維能力方面或許更有效。西洋棋以其奇特且多樣的移動方式而聞名,牽一髮動全身,但其複雜性常被誤解為深奧(這是常見的誤解)。在下西洋棋時需高度集中注意力,一時疏忽就可能導致劣勢或失敗,棋局中可能的移動選擇不僅繁多且錯綜複雜,因此犯錯的機會也隨之增加;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約九成),贏得比賽的是更專注的棋手,而非那些思維更為敏銳的玩家。反之,在西洋跳棋中,由於移動方式單一且變化較少,一時疏忽的可能性相對減少,注意力也不需如此高度集中,任何一方獲得的優勢,仰賴的都是聰明才智。具體而言,讓我們設想一場西洋跳棋比賽,其中棋盤上僅剩四個國王作為棋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預計棋手不會犯任何疏忽,顯然在這樣的遊戲設定中,假設棋手的技巧相當,那麼勝利只能透過獨具匠心的棋步來實現,這需要倚賴非凡的智力。當分析者面對缺乏可用資源、工具或策略的情境時,他會深入洞悉對手的思考模式,設身處地去想像對方可能採取的策略,並且常常能一眼識破那些唯一能引導對方走入誤區(有時這些策略甚至顯得過於簡單)的方法,進而誘使對手做出匆忙且錯誤的決策。
長久以來,人們普遍認為惠斯特紙牌可以提高所謂的計算能力;且那些高智商的人似乎對這種牌戲擁有難以言喻的熱愛,同時他們對西洋棋抱有一定的輕蔑,認為它過於輕浮。毫無疑問,沒有其他活動能像惠斯特紙牌那樣有效地考驗一個人的分析能力。在基督教世界中,最優秀的西洋棋手可能僅是該領域的佼佼者;然而,擅長惠斯特紙牌的人則顯示出在所有智力競技活動中都擁有勝出的能力。我所指的擅長不僅是牌技高超,還包括對牌局的深刻洞察,以及理解所有可在遊戲中理智利用以獲取優勢的因素,這些因素不僅多樣,而且往往隱藏在普通人難以觸及的思維深處。善於集中注意力的西洋棋玩家在玩惠斯特紙牌時也每每表現出色,因為惠斯特紙牌的規則(這些規則建立在遊戲的基本機制上)清晰明確,易於理解,要求玩家具備出色的記憶力,並能按照這些「規則」進行遊戲,這些技能反映了一個玩家的遊戲水準。然而,超越遵循規則的範疇,分析者的真正能力才得以充分展現,他在靜默中進行大量的觀察和推理,或許其他隊友也做了同樣的事情;而兩者之間所獲得資訊範圍的差異,主要並不取決於推理的有效性,而在於觀察的品質,重點是知道自己觀察的目標是什麼。高段玩家的觀察力並不局限在牌局本身;他們也不會因為專注於牌局而忽視了牌局以外的事物,他們會仔細觀察隊友的臉部表情,將其與對手的表情進行比較,還會細心觀察其他玩家手中牌的組合和排序方式;常根據其他玩家看自己手中牌的方式來判斷他們可能持有的特殊牌,例如王牌和高分牌。隨著牌局的進展,他會留意每個人臉上表情的每一個細微變化,從中搜集思考的線索,包括篤定、驚訝、勝利或失望的表情差異。透過觀察玩家收取一輪贏得的牌,可以判斷出那個玩家是否能在同一花色中再贏一輪牌。他能從玩家把牌丟到桌上的方式中,辨別哪些是虛張聲勢出的牌。玩家不經意說出的話、一張牌的意外掉落或翻轉,可能暗示玩家感到焦慮或疏忽,因此沒有妥善保護自己的牌;其他玩家如何計算贏得的牌數和排列順序,他們的尷尬、猶豫、渴望或恐懼——這些都為觀察者提供了對實際局勢的線索,觀察者似乎憑藉直覺就能捕捉這些線索。在最初的兩三輪牌局之後,此人已經能夠完全掌握每位玩家手中的牌面,並能精準出牌,彷彿其他玩家都將自己的牌面亮給他看一般。
分析能力與豐富的創造力應該明確區分開來,儘管許多分析者擁有出色的創造力,但擁有創造力的人在分析方面卻常常表現出一定的不足。創造力通常透過建構力或組合能力展現,而骨相學家(雖然我並不完全認同他們的觀點)認為創造力是由大腦中的一個獨立器官控制,並將其視為一種原始能力。實際上,從那些智力上接近愚昧的人身上,我們常常可以觀察到這種建構力或組合能力的表現,這成為道德研究作家探討的一個有趣現象。創造力和分析能力之間的差異,遠大於幻想與想像力之間的差異,但這兩者的差異性質卻非常相似。實際上,你會發現那些具有創造力的人總是充滿了幻想,而真正具有想像力的人則在思維方式上以分析為主導。
針對上述提出的論點,我以接下來的故事為讀者提供解釋。
在十九世紀的某一年,從春暖花開至夏日的繁葉陰涼,我將自己留在巴黎這座城市,並認識了一位名叫C・奧古斯特・杜邦的先生,這位年輕紳士出身於一個優秀,甚至可說是顯赫的家族,但由於一連串不幸事件使他陷入貧困的境地,他原本充滿活力的性格也在困境中屈服。他不再參與社交生活,也不想改善自己的財富狀況。因為債權人對他的寬容,讓他保留一小部分遺產;憑藉這點收入以及極為節儉的生活方式,他得以滿足生活基本所需,但也別想購買奢侈品。事實上書本是他唯一的奢侈品,畢竟在巴黎購買書籍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情。
我們第一次相遇是在蒙馬特街上一家不起眼的圖書館,我們剛好都在找一本非常罕見的好書,這個機緣讓我們感覺更加投契。我們一次又一次相約見面,身為一個法國人,他在談論自己時總是自然坦率,他將自己的家族歷史對我娓娓道來,我也對此深感興趣,他的博學廣聞更是令我敬佩萬分;最重要的是,他狂野的熱情和生動的想像力在我內心點燃了火花。我在巴黎尋尋覓覓,終於遇見這樣一位知心好友,對我來說就像獲得了無價之寶;我也坦然向他表達心跡。隨後,我們安排一起居住,直至我在這個城市的停留結束;由於我的經濟狀況相對較好,足以負擔起房租和裝修開支,我們便以一種適合我們共同性格中某種奇特而陰暗的風格來裝飾我們的住所。我們找到一棟外觀怪異且年久失修的大宅,位於聖日耳曼郊區一個偏僻且荒涼的角落,建築本體看似搖搖欲墜,因為人們的迷信而長期荒廢,雖然我們並未深入探究背後的緣由。
如果外界知曉了我們在這棟大宅裡的生活方式,我們很可能會被視為瘋子——雖然是無害的那種。我們過著完全隱居的生活,不接待任何來客,並且絕不透露我們隱居的地點,甚至我的朋友們也對此一無所知;而杜邦已經隱居多年,外界幾乎沒有人知曉他的存在。對我們而言,彼此的存在就是我們唯一的世界。
我的朋友(我還能如何稱呼他呢?)對夜晚懷有一種非比尋常的迷戀,他鍾愛夜晚的深邃黑暗。我也默默地迎合他這奇異的喜好,就像順應他所有其他古怪想法一樣,我任由自己沉浸在他的狂野幻想之中。夜之女神不總是與我們同在;但我們可以假裝她的存在。每當黎明接近,我們便關閉古舊建築中所有凌亂的百葉窗,點燃一對散發著香氣的蠟燭,其微弱而陰森的光芒照亮著我們的空間。我們就在這樣的氛圍中沉浸於夢境之中——閱讀、寫作或對話,直到時鐘提醒我們真正的黑夜即將降臨。然後我們會攜手走上街頭,延續白日的話題,或者徘徊至深夜,尋求在繁華都市的光影交錯中,那由靜觀所帶來的無盡心靈激蕩。
在這些時刻,我不禁對杜邦獨特的分析能力感到驚嘆和敬佩(儘管從他豐富的想像力中,我已能預見他在這方面的才能),他似乎也非常享受於運用這種能力——即便他很少表現出來——同時他也毫不掩飾自己從中得到的樂趣。他經常低聲笑著向我誇耀,聲稱自己能洞悉大多數人的內心,並習慣以直接且令人震驚的方式來證明他對我了解有多深。在這些時刻,他的態度會變得冷漠而疏離;眼神變得空洞,面無表情;平時那富有韻律的男高音會變得尖銳,幾乎達到女高音的高度,若不是發音依然精確清晰,聽起來幾乎有些無禮。觀察他在這些情緒下的行為,常讓我思考古老哲學中所提及的雙面人格,同時幻想杜邦擁有創造性與解決性的雙重人格。
請別誤以為我是在描述某種神祕故事,或者撰寫浪漫小說。我對這位法國人的描述,不過是反映出他在激動或某種思維異常時的狀態。但是要進一步傳達和說明他在特定時刻言論的性質或特點,最好還是透過實際的例子來傳達和說明。
有一夜,我們在帕萊羅亞附近一道骯髒的長街上散步,似乎沉浸在各自的思緒之中,至少有十五分鐘沒有交談,突然間杜邦開口說道:
「他的個頭確實很小,比較適合在綜藝劇院演出。」
「這點毋庸置疑,」我不假思索回答道。剛開始並沒有注意到他方才說的話竟然與我腦中的默想不謀而合(因為我仍深陷在自己的思緒之中),過了一會兒回過神來,我才深感驚訝。
「杜邦,」我嚴肅地說,「這超出我的理解範圍,我真的被你嚇到了,我還以為自己的感官出現了幻覺,你怎麼可能知道我在想什——?」我停頓一下,想確定他是否真的知道我腦中想的人是誰。
「——尚蒂伊,」他說,「你為何要停頓?你當時在內心對自己說他的身形矮小,不適合演出悲劇角色。」
這正是我腦中所想。尚蒂伊是聖丹尼街上一個昔日曾當過皮鞋匠的人,他迷戀上舞台,試圖在克雷必倫的悲劇《薛西斯》中飾演薛西斯一角,為此受到大眾的嘲笑與譏諷。
「請告訴我,拜託,」我驚呼道,「究竟是什麼方法——如果真有這樣的方法——讓你能夠洞悉我的心思。」其實我遠比表現出來的還要驚訝。(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