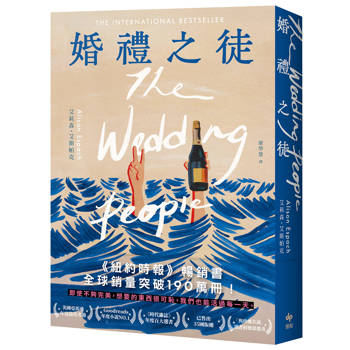週二 開幕洗塵宴
酒店的模樣一如菲比所盼望。古老建築端坐在懸崖邊,彷彿氣派的老狗,耐心等候她到來。她看不到後面的大海,但她知道海就在那裡,就像她回家時剛駛上車道,就感覺到老公在書房裡打字寫稿。
愛是一條隱形繩索,永遠將他們緊緊相繫。
菲比下了計程車,一名身穿酒紅色制服的男員工過來迎接,他的動作如此認真,以致於這一刻感覺像是很久以前就彩排好了。如此一來,她更加確信自己的選擇沒有錯。
「您好,」男員工說,「歡迎光臨康瓦爾度假村。我幫您拿行李?」
「我沒有行李。」菲比說。
離開聖路易斯時,她感覺必須將一切拋在腦後,這件事非常重要──丈夫、房子、行李。她該往前走了,她很清楚,去年離婚聽證結束時,他們說好要各自前行。當時丈夫決絕的語氣令菲比心驚,他只簡單說一句:「好了,保重。」就像郵差送完信之後道別那樣。那之後她什麼都沒辦法做,只能窩在床上喝琴通寧調酒,聽冰箱製冰的聲音。反正她哪裡也不能去。當時正值新冠疫情封城期間,她只有缺琴酒和衛生紙的時候才會出門,每天穿同樣的黑上衣上網課,因為這種時候不就是該穿黑衣嗎?解封之後,她再也想不起來該穿什麼衣服。
此刻,菲比站在十九世紀建造的紐波特豪華酒店前,身上穿著一襲翡翠綠絲質長禮服,整個衣櫥裡只有這件她還能真心感到喜歡,很可能是因為她從來沒有穿過。這件禮服只適合奢華的場合,而他們夫妻從不曾參與那樣的活動。他們兩個都是教授。他們很隨和、很輕鬆。舒舒服服坐在壁爐邊,小貓趴在腿上。他們喜歡平凡的事物,他們不挑,酒吧推薦什麼酒就喝、電視演什麼節目就看,總是選看起來最正常的衣物,因為這不就是穿衣服的目的嗎?證明自己很正常。證明無論發生什麼事,自己都是可以好好穿衣服的人。
然而,搭機來紐波特的那天,菲比一早醒來就知道自己再也不正常了。儘管如此,她還是烤了吐司。洗澡。吹乾頭髮。整理秋季開學第二天授課用的資料。她打開衣櫥看裡面的衣物,當初她之所以買這些衣服,單純因為感覺像是教授上班會穿的。一排排純色上衣,和丈夫穿的衣服一模一樣,只是換成女裝版。她拿出一件灰色襯衫,站在鏡子前面舉起,卻無法說服自己穿上。她無法去上班,無法站在辦公室印表機前撐住臉上認真專注的表情,聽同事長篇大論述說起司在中世紀神學中有著出乎意料的重要性。
她改為穿上翡翠綠長禮服、結婚當天穿過的金色高跟鞋,戴上厚層珍珠項鍊,新婚之夜丈夫曾經將這條項鍊當作蒙眼布放在她的眼睛上。她登機,喝了一杯調得很棒的琴通寧,美味冰涼的調酒下肚,下飛機時她幾乎忘記鞋子磨出的水泡。
「這邊請,女士。」穿酒紅色制服的員工說。
菲比給那個人二十元,他似乎很驚訝,他沒有做什麼就拿到這麼多小費,但是對菲比而言,他所做的事很有意義。已經很久沒有男人一看到她下車就立刻起身迎接。這些年,她回到家時丈夫已經不會從書房出來打招呼了。有人殷勤接待的感覺很棒,就好像她的到來是頭等大事。她走向古老紅磚門階,聽著高跟鞋發出喀喀腳步聲。她一直很想在走進教室時發出這樣的腳步聲,擺出堂皇大氣的派頭,可惜大學室內全鋪了地毯。
她踏上臺階,經過大型黑色立燈與門邊的大理石獅子,她從帷幔間走進大廳,這樣的感覺也很對。就像回到過去的古老世界,雖然不見得比現代好,但至少掛著重重絲絨帷幔。
這時,她看到排隊等候登記入住的人潮。
隊伍很長──一般只有在機場才會這樣大排長龍,俯瞰大海的維多利亞時代豪華酒店很少會有如此的場面。但排隊的人確實很多,隊伍從櫃臺蜿蜒到大廳另一頭,經過充滿歷史感的橡木樓梯。排隊的人感覺也很不對──他們穿著風衣外套、牛仔褲、運動鞋──菲比以前穿的那種正常上衣。絲絨帷幔與牆上鍍金畫框裡的大鬍子男士肖像,使得那些人相形之下平凡到可笑的程度。他們的樣子就是實實在在的現代人,鈦合金強化行李箱將他們牢牢綁在地面上。有些人在滑手機,模樣彷彿準備排隊到天長地久,說不定真的會排那麼久。說不定他們也沒有親人了。現在菲比總是忍不住這麼想──每個人都像她一樣孤獨。
但他們並不孤獨。他們三三兩兩站在一起,有些人手挽著手,有些人一手放在別人的背上。他們很開心,菲比之所以知道,是因為不時會有人高聲說自己很開心。
「吉姆!」一位老先生喊,張開雙臂的動作很像熊。「見到你真開心!」
「嗨,吉姆爺爺。」一個年輕人回覆,隊伍裡的每個人好像都叫做吉姆。兩位吉姆熱情大力擁抱寒暄。「吉姆舅舅呢?已經去打高爾夫了?」
就連櫃臺裡忙碌的女員工感覺也很開心──她認真注視每位客人的雙眼,問他們來度假村的目的,每個人的答案都一樣。於是,她也以同樣的方式回答:「噢,你是來參加婚禮的!真棒!」她的語氣彷彿興奮期待婚禮,說不定她真的很期待。說不定她還很年輕,依然相信自己會是其他人婚禮的主角。菲比年輕時就是那樣,每次參加婚禮都會花一個月煩惱要穿什麼,即使每次她都坐在邊緣地帶。
菲比也去排隊。排在她前面的兩個年輕女子手臂上掛著同款綠色禮服。其中一個依然戴著豹紋頸枕,另一個隨手翻閱《時人》雜誌,她的丸子頭紮得非常高,以致於尾端幾綹亂亂紅髮垂落前額。她們低聲比較誰的飛行旅程最糟,爭論這家酒店到底歷史多悠久,以及為什麼現在凱莉・珍娜那麼夯?就算她真的比金・卡戴珊更辣,又關我們什麼事?
「她有嗎?」頸枕問。「其實我一直覺得她們都有很醜的地方。」
「每個人都一樣吧?」丸子頭說。「所有人都有很醜的地方。就連那些,怎麼說?專業辣妹都有。放在四邊都對。」
「妳是不是想說放諸四海皆準?」
「大概吧。」丸子頭說,即使她知道自己算得上有魅力,但有一件事是她做了五年的心理治療之後,才終於能夠坦誠說出:她笑的時候會露出太多牙齦。
「我沒有注意到耶。」頸枕說。
「因為我從來不會笑得那麼大。」
「我認識妳這麼久了,妳從來沒有放開來笑過?」
「從高中就這樣了。」
隊伍往前移動,菲比抬頭看花格天花板,高度驚人,她不禁納悶要如何清潔。
櫃臺人員再次說:「噢!你們是來參加婚禮的!」菲比這才意識到大廳裡有多少婚禮賓客。數量令人不安,就像她老公熱愛的那部電影《鳥》。一旦看到幾個,就會發現到處都是。婚禮賓客倚靠在內嵌書架上。婚禮賓客拉著超級未來風的行李箱,感覺就算上月球也不會壞。幾個穿酒紅色制服的員工將大量行李箱高高堆起,旁邊有個大大的白色告示牌,上面印著:歡迎蒞臨萊拉與蓋瑞的婚禮。
「不過那個規則不適用於萊拉,」頸枕說,「我真的想不出來她有哪裡醜。」
「沒錯。」丸子頭說。
「妳還記得吧?高三的時尚秀,她獲選當新娘。」
「噢,沒錯。有時候我都忘記了。」
「妳怎麼能忘記?我每個星期都會想起來,實在太詭異了。」
「妳是說輔導老師堅持要陪她走紅毯那件事?」
「不是啦,我是覺得有些人好像天生就要當新娘。」
「印象中輔導老師好像會來參加婚禮。」
「這更詭異。不過也好啦,至少這樣婚禮上會有我真正認識的人。」頸枕說。
「真的。我感覺大家變得好陌生。」丸子頭說。
「真的,疫情開始以後我就覺得,好喔,看來現在我沒朋友了。」
「對吧?現在我唯一瞭解的人只剩我媽了。」
她們大笑,然後繼續說來這裡的飛行過程有多慘,菲比盡可能不理會,專注研究華麗的大廳。婚禮賓客比一般人更吵。
她閉上雙眼。她的腳開始痛了,走出家門之後,她第一次後悔沒有帶一雙好穿的鞋。她的衣櫥裡整整齊齊排了好幾雙,都是海軍藍,無所事事待在家裡。
「妳對新郎有多少瞭解?」頸枕小聲問。
丸子頭只知道萊拉在電話裡簡單提起的那些事,以及她在網路上挖出來的事。
「蓋瑞很無趣,根本沒什麼好挖的。」丸子頭回答,接著小聲說,他是X世代的醫師,髮際線只有一點點後退,感覺起來應該到死都還會有很多頭髮。「萊拉都找妳當伴娘了,妳怎麼能忍住不上網挖他?」
「我戒網了,」頸枕說,「心理醫師的命令。」
「整整兩年?」
「他們訂婚那麼久了?」
「他才剛求婚沒多久,疫情就爆發了。」
隊伍再次緩緩往前移動。
「老天──妳看這個壁紙!」
頸枕表示希望房間面向大海。「我看到一個研究說,看海可以提升幸福感百分之五。」
她們終於安靜下來了。菲比深深感謝她們的沉默。她又可以思考了。她閉起雙眼假裝在廚房裡看著大笑的丈夫,心中滿是愛慕。菲比一直很喜歡他的笑聲,尤其是從遠處傳來的時候。宛如遠方的霧角,提醒她該往哪裡去。但這時一個吉姆大喊:「新娘來了!」
「吉姆!」新娘說。
新娘踏出電梯走進大廳,身上披著一條亮片授帶,上面寫著「新娘」,所以絕不會錯。其實就算沒有也不會弄錯。一看就知道她是新娘,她走路的動作、微笑的表情都昭告著她是新娘,她走向排隊的頸枕與丸子頭,開心轉圈的動作也充滿新娘味,因為在這兩、三天的時間裡,新娘就是可以做這樣的事。此刻她就是明星,她是這許多人花上好幾千元來此的原因。
「看到妳們我好開心啊!」新娘嚷嚷。她張開雙臂擁抱她們,她手腕上掛著好幾個禮物袋,眾多提繩看起來很像海藻編成的手環。
頸枕與丸子頭說得沒錯。菲比無法從新娘身上找出任何醜的地方,或許這就是她醜的地方。她看起來就是新娘應該要有的樣子──一身夏季連身裙襯得她嬌小纖細,底下完全看不出內衣褲的痕跡。一頭金髮編成非常浪漫的繁複髮辮,菲比很想知道她看了多少Instagram上的教學影片。
「妳好美。」丸子頭說。
「謝謝、謝謝,」新娘說,「飛行順利嗎?」
「平安無事。」頸枕撒謊。
因為新娘在場,她們沒有提起一大群海鷗突然飛過來造成的驚恐,也沒有說緊急迫降的驚險。這是她們的責任,她們必須在婚禮期間對新娘撒謊,必須宣稱來這裡的旅程舒適無比,必須在困坐家中無所事事兩年之後表現出非常期待這場紐波特婚禮。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和蓋瑞見面?」丸子頭問。
「晚一點的洗塵宴,他會出席,不用說吧?」
「當然不用說嘍。」頸枕說,她們一起大笑。
新娘將海藻禮物袋送給她們(裡面有「緊急備品」),頸枕和丸子頭從裡面拿出酒瓶,兩人同聲驚呼,不是迷你瓶而是正常瓶。種類全都不同,新娘說明。她上個月和蓋瑞去歐洲旅行時親自挑選的。
蘇格蘭威士忌、西班牙里奧哈紅酒、伏特加。
「噢,真高級。」丸子頭說。
新娘微笑,似乎以自己為榮。因為她和醫師未婚夫去歐洲旅遊時,沒忘記那些比較沒那麼好命的朋友。因為她在歐洲學到哪些酒該喝、哪些不該喝。
「來,妳的。」新娘對菲比說,語氣如此親暱,菲比覺得她好像是小時候親近但很久沒聯絡的親戚。就好像她們曾經一起在爺爺家昏暗的地下室玩西洋棋之類的。她遞給菲比一個禮物袋,然後給她一個非常用力的擁抱,彷彿在練習新娘的擁抱,就像菲比的老公以前會在面試前練習專業握手動作。「只是一點小東西,感謝妳們特地跑來這麼遠的地方。我們很清楚要來這裡有多難!」
其實對菲比而言並不難。她沒有通知郵局停送信件,也沒有雇用鄰居家的小朋友幫忙澆花,更沒有像以前去度假時那樣請巴伯代課。她甚至沒有清掉流理臺上的麵包屑。她只是穿上這件長禮服,走出家門,以前所未有的瀟灑拋下一切。
「噢,我……」菲比想解釋。
「我懂,我知道妳想說什麼。」新娘說。「到底誰會喝巧克力紅酒?」
新娘很好。非常稱職的新娘。經過兩年的極度孤獨,現在突然有人這樣對她說話,菲比嚇了一大跳。那兩年之中,她只能對著電腦螢幕上的一片黑格子問:「什麼是文學?」那些黑格子不知道也不關心,那些黑格子根本沒在聽。「什麼是文學?」菲比問了一次又一次,最後連她自己都搞不清楚答案。
現在她毫無理由收到擁抱與一袋巧克力紅酒。這些年來,連老公都不肯看她的眼睛,現在卻有個陌生美女注視她的雙眼。菲比好想哭,她好希望自己真的是來參加婚禮的。
「不過其實比想像中好喝,」新娘說,「德國人很愛。」
新娘微笑,菲比發現她的兩顆門牙中間卡到食物殘渣。找到了:今天讓新娘很醜的地方。
「下一位?」櫃臺小姐喊。
菲比片刻之後才察覺輪到她了。她看到丸子頭和頸枕已經往電梯走去了。她收下禮物,向新娘道謝之後走向櫃臺。
「妳一定也是來參加婚禮的吧?」櫃臺小姐問。她的名字叫寶琳。
「不是,」菲比承認,「我不是。」
「噢。」寶琳說,她似乎很失望。更正確地說,應該是困惑。她的視線飄向遠處的新娘。「我以為所有今天入住的人都是婚禮賓客。」
「我絕對不是來參加婚禮的。但是我今天早上訂房了。」
「噢,我相信。」寶琳邊說邊敲鍵盤。「我只是在想一定有人出大錯了。搞不好就是我!請見諒,疫情之後我們有點人手不足。」
菲比點頭。「勞工短缺。」
「就是啊。」寶琳說。「好,請問貴姓大名?」
「菲比・史東。」
是真的。這是她的名字,是她這些年來自認屬於她的名字。然而,現在說出來感覺像撒謊,因為史東是老公的姓氏。每當她聽見自己說出這個姓氏,感覺就像靈魂被推出體外,讓她可以像鳥一樣從高處看自己。婚禮賓客一定也這樣看她,她相信即使從高處往下看,他們絕對也能發現她身上醜的地方:她的頭髮。她早該打理了,而且早上完全忘記要梳頭。
「找到了。」寶琳說。她太專心為眼前的客人提供頂級服務,當一位婚禮賓客走進大門之後在菲比身後滑倒,她甚至沒有抬起頭。
「吉姆舅舅!噢,老天!你還好吧?」新娘驚呼。
吉姆舅舅很不好。他躺在地上,大聲喊著他的腳踝受傷了,然後抱怨地板爛透了,根本是狗屎。幾名酒紅色制服的男員工圍著他關心,為地板太滑而一再道歉。沒錯、沒錯,他們說,地板爛透了,不過菲比看得出來,地板絕對是義大利產的大理石。
「好了。」寶琳說。寶琳是大英雄。「妳的房間是咆哮二○年代。」
「每個房間都以時代命名?」菲比問。她想像每個房間都有獨特的髮型、專有的戰爭、不同的股市起伏跌宕、各自表述的女性主義。
「說到這個,其實我不知道每個房間的主題呢!」寶琳說。「我是新來的,現在還看不出房間命名的邏輯。不過這個問題很棒喔。」
她拉開抽屜找出房間鑰匙。
「這是我們的頂樓套房,」她說,「只有這個房間能正面看到大海。」
這番話感覺特別練習過,就好像寶琳對每位房客都會輕聲說一小段話,讓他們感覺得到特殊待遇。只有這個房間配備了鐵路大亨范德比家中使用的書桌。只有這個房間無限供應衛生紙。
「太好了。」菲比說。
「請問妳造訪康瓦爾度假村的目的為何?」
即使菲比早就知道寶琳會這麼問,但還是吃了一驚。之前她想像過入住這裡的感覺,但她沒想到會需要與人交談。基本上,她太久沒練習。
「這裡是我的幸福地點。」菲比脫口而出。這個回答不盡真實,但也並非撒謊。
「噢,妳以前來過?」寶琳問。
「沒有。」菲比說。
兩年前,菲比在一本忘記叫什麼名字的雜誌上,看到這家酒店的廣告,她只有在人工生殖診所候診時才會看那種雜誌。她看著照片裡俯瞰大海的維多利亞時代天蓬大床,心中想著,誰會真的看旅遊雜誌決定去哪裡度假?雖然她不認識這樣的人,卻對他們感到憤怒。然而,幾天後,當心理治療師要求她閉起眼睛描述心中的幸福地點,她想像自己躺在那張天蓬大床上,因為唯有在不曾去過的地方、沒有躺過的床上,她才能想像自己幸福的模樣。
「這裡確實讓人感到幸福。」寶琳說。
菲比拿起鑰匙。她已經聊太久了,也假裝正常太久了。她花了八百元入住這家酒店,不是為了假裝正常。要假裝正常在家就可以了。她感覺自己越來越心累,但寶琳還有一大堆問題。要不要加購Spa療程?要不要預約駐店塔羅大師占卜?要普通枕頭還是椰子枕頭?
「椰子枕頭是什麼?」菲比問。
「裡面有椰子的枕頭。」寶琳說。
「裡面有椰子的枕頭比較好嗎?」她問。
這是她老公會問的問題。這是她的壞習慣,十年婚姻生活的後遺症──總是想像老公會說什麼,即使他不在也一樣,或者該說他不在的時候更是這樣。菲比當初沒想過自己會變成這樣的女人。但過去幾年她學到了教訓:人很難知道自己會變成什麼樣子。
「這種枕頭好很多,」寶琳說,「相信我。我會請人送一個上去。」
菲比走進電梯,門開始關閉時她鬆了一口氣。終於能夠遠離婚禮賓客。終於能做不一樣的事。終於拿到了不是她家的鑰匙。
「電梯等一下!」一個女人大喊。
菲比還沒看到人就知道是新娘。她的語氣彷彿電梯理所當然要等她。但世上沒有理所當然的事,就連新娘也一樣。菲比按下關門鍵,但新娘伸出一隻手企圖擋門。一般電梯卡到東西會自動打開,但這部沒有。或許是因為康瓦爾度假村建造於一八六四年,老酒店沒有半點仁慈,即使對方是新娘也一樣。
「靠!」新娘痛呼。
「噢,老天!」菲比說。她硬是掰開門,難以置信地呆望新娘的手。「妳流血了。」
新娘的手背指節上有道傷口,她像小孩一樣舉起那隻手,接過菲比送上的面紙,沒有道謝。菲比按下按鈕,門重新關上。電梯往上移動,她們沒有交談,新娘的血非常有禮貌,默默流進面紙裡。菲比聽到新娘調整呼吸,看到面紙染上深紅。
酒店的模樣一如菲比所盼望。古老建築端坐在懸崖邊,彷彿氣派的老狗,耐心等候她到來。她看不到後面的大海,但她知道海就在那裡,就像她回家時剛駛上車道,就感覺到老公在書房裡打字寫稿。
愛是一條隱形繩索,永遠將他們緊緊相繫。
菲比下了計程車,一名身穿酒紅色制服的男員工過來迎接,他的動作如此認真,以致於這一刻感覺像是很久以前就彩排好了。如此一來,她更加確信自己的選擇沒有錯。
「您好,」男員工說,「歡迎光臨康瓦爾度假村。我幫您拿行李?」
「我沒有行李。」菲比說。
離開聖路易斯時,她感覺必須將一切拋在腦後,這件事非常重要──丈夫、房子、行李。她該往前走了,她很清楚,去年離婚聽證結束時,他們說好要各自前行。當時丈夫決絕的語氣令菲比心驚,他只簡單說一句:「好了,保重。」就像郵差送完信之後道別那樣。那之後她什麼都沒辦法做,只能窩在床上喝琴通寧調酒,聽冰箱製冰的聲音。反正她哪裡也不能去。當時正值新冠疫情封城期間,她只有缺琴酒和衛生紙的時候才會出門,每天穿同樣的黑上衣上網課,因為這種時候不就是該穿黑衣嗎?解封之後,她再也想不起來該穿什麼衣服。
此刻,菲比站在十九世紀建造的紐波特豪華酒店前,身上穿著一襲翡翠綠絲質長禮服,整個衣櫥裡只有這件她還能真心感到喜歡,很可能是因為她從來沒有穿過。這件禮服只適合奢華的場合,而他們夫妻從不曾參與那樣的活動。他們兩個都是教授。他們很隨和、很輕鬆。舒舒服服坐在壁爐邊,小貓趴在腿上。他們喜歡平凡的事物,他們不挑,酒吧推薦什麼酒就喝、電視演什麼節目就看,總是選看起來最正常的衣物,因為這不就是穿衣服的目的嗎?證明自己很正常。證明無論發生什麼事,自己都是可以好好穿衣服的人。
然而,搭機來紐波特的那天,菲比一早醒來就知道自己再也不正常了。儘管如此,她還是烤了吐司。洗澡。吹乾頭髮。整理秋季開學第二天授課用的資料。她打開衣櫥看裡面的衣物,當初她之所以買這些衣服,單純因為感覺像是教授上班會穿的。一排排純色上衣,和丈夫穿的衣服一模一樣,只是換成女裝版。她拿出一件灰色襯衫,站在鏡子前面舉起,卻無法說服自己穿上。她無法去上班,無法站在辦公室印表機前撐住臉上認真專注的表情,聽同事長篇大論述說起司在中世紀神學中有著出乎意料的重要性。
她改為穿上翡翠綠長禮服、結婚當天穿過的金色高跟鞋,戴上厚層珍珠項鍊,新婚之夜丈夫曾經將這條項鍊當作蒙眼布放在她的眼睛上。她登機,喝了一杯調得很棒的琴通寧,美味冰涼的調酒下肚,下飛機時她幾乎忘記鞋子磨出的水泡。
「這邊請,女士。」穿酒紅色制服的員工說。
菲比給那個人二十元,他似乎很驚訝,他沒有做什麼就拿到這麼多小費,但是對菲比而言,他所做的事很有意義。已經很久沒有男人一看到她下車就立刻起身迎接。這些年,她回到家時丈夫已經不會從書房出來打招呼了。有人殷勤接待的感覺很棒,就好像她的到來是頭等大事。她走向古老紅磚門階,聽著高跟鞋發出喀喀腳步聲。她一直很想在走進教室時發出這樣的腳步聲,擺出堂皇大氣的派頭,可惜大學室內全鋪了地毯。
她踏上臺階,經過大型黑色立燈與門邊的大理石獅子,她從帷幔間走進大廳,這樣的感覺也很對。就像回到過去的古老世界,雖然不見得比現代好,但至少掛著重重絲絨帷幔。
這時,她看到排隊等候登記入住的人潮。
隊伍很長──一般只有在機場才會這樣大排長龍,俯瞰大海的維多利亞時代豪華酒店很少會有如此的場面。但排隊的人確實很多,隊伍從櫃臺蜿蜒到大廳另一頭,經過充滿歷史感的橡木樓梯。排隊的人感覺也很不對──他們穿著風衣外套、牛仔褲、運動鞋──菲比以前穿的那種正常上衣。絲絨帷幔與牆上鍍金畫框裡的大鬍子男士肖像,使得那些人相形之下平凡到可笑的程度。他們的樣子就是實實在在的現代人,鈦合金強化行李箱將他們牢牢綁在地面上。有些人在滑手機,模樣彷彿準備排隊到天長地久,說不定真的會排那麼久。說不定他們也沒有親人了。現在菲比總是忍不住這麼想──每個人都像她一樣孤獨。
但他們並不孤獨。他們三三兩兩站在一起,有些人手挽著手,有些人一手放在別人的背上。他們很開心,菲比之所以知道,是因為不時會有人高聲說自己很開心。
「吉姆!」一位老先生喊,張開雙臂的動作很像熊。「見到你真開心!」
「嗨,吉姆爺爺。」一個年輕人回覆,隊伍裡的每個人好像都叫做吉姆。兩位吉姆熱情大力擁抱寒暄。「吉姆舅舅呢?已經去打高爾夫了?」
就連櫃臺裡忙碌的女員工感覺也很開心──她認真注視每位客人的雙眼,問他們來度假村的目的,每個人的答案都一樣。於是,她也以同樣的方式回答:「噢,你是來參加婚禮的!真棒!」她的語氣彷彿興奮期待婚禮,說不定她真的很期待。說不定她還很年輕,依然相信自己會是其他人婚禮的主角。菲比年輕時就是那樣,每次參加婚禮都會花一個月煩惱要穿什麼,即使每次她都坐在邊緣地帶。
菲比也去排隊。排在她前面的兩個年輕女子手臂上掛著同款綠色禮服。其中一個依然戴著豹紋頸枕,另一個隨手翻閱《時人》雜誌,她的丸子頭紮得非常高,以致於尾端幾綹亂亂紅髮垂落前額。她們低聲比較誰的飛行旅程最糟,爭論這家酒店到底歷史多悠久,以及為什麼現在凱莉・珍娜那麼夯?就算她真的比金・卡戴珊更辣,又關我們什麼事?
「她有嗎?」頸枕問。「其實我一直覺得她們都有很醜的地方。」
「每個人都一樣吧?」丸子頭說。「所有人都有很醜的地方。就連那些,怎麼說?專業辣妹都有。放在四邊都對。」
「妳是不是想說放諸四海皆準?」
「大概吧。」丸子頭說,即使她知道自己算得上有魅力,但有一件事是她做了五年的心理治療之後,才終於能夠坦誠說出:她笑的時候會露出太多牙齦。
「我沒有注意到耶。」頸枕說。
「因為我從來不會笑得那麼大。」
「我認識妳這麼久了,妳從來沒有放開來笑過?」
「從高中就這樣了。」
隊伍往前移動,菲比抬頭看花格天花板,高度驚人,她不禁納悶要如何清潔。
櫃臺人員再次說:「噢!你們是來參加婚禮的!」菲比這才意識到大廳裡有多少婚禮賓客。數量令人不安,就像她老公熱愛的那部電影《鳥》。一旦看到幾個,就會發現到處都是。婚禮賓客倚靠在內嵌書架上。婚禮賓客拉著超級未來風的行李箱,感覺就算上月球也不會壞。幾個穿酒紅色制服的員工將大量行李箱高高堆起,旁邊有個大大的白色告示牌,上面印著:歡迎蒞臨萊拉與蓋瑞的婚禮。
「不過那個規則不適用於萊拉,」頸枕說,「我真的想不出來她有哪裡醜。」
「沒錯。」丸子頭說。
「妳還記得吧?高三的時尚秀,她獲選當新娘。」
「噢,沒錯。有時候我都忘記了。」
「妳怎麼能忘記?我每個星期都會想起來,實在太詭異了。」
「妳是說輔導老師堅持要陪她走紅毯那件事?」
「不是啦,我是覺得有些人好像天生就要當新娘。」
「印象中輔導老師好像會來參加婚禮。」
「這更詭異。不過也好啦,至少這樣婚禮上會有我真正認識的人。」頸枕說。
「真的。我感覺大家變得好陌生。」丸子頭說。
「真的,疫情開始以後我就覺得,好喔,看來現在我沒朋友了。」
「對吧?現在我唯一瞭解的人只剩我媽了。」
她們大笑,然後繼續說來這裡的飛行過程有多慘,菲比盡可能不理會,專注研究華麗的大廳。婚禮賓客比一般人更吵。
她閉上雙眼。她的腳開始痛了,走出家門之後,她第一次後悔沒有帶一雙好穿的鞋。她的衣櫥裡整整齊齊排了好幾雙,都是海軍藍,無所事事待在家裡。
「妳對新郎有多少瞭解?」頸枕小聲問。
丸子頭只知道萊拉在電話裡簡單提起的那些事,以及她在網路上挖出來的事。
「蓋瑞很無趣,根本沒什麼好挖的。」丸子頭回答,接著小聲說,他是X世代的醫師,髮際線只有一點點後退,感覺起來應該到死都還會有很多頭髮。「萊拉都找妳當伴娘了,妳怎麼能忍住不上網挖他?」
「我戒網了,」頸枕說,「心理醫師的命令。」
「整整兩年?」
「他們訂婚那麼久了?」
「他才剛求婚沒多久,疫情就爆發了。」
隊伍再次緩緩往前移動。
「老天──妳看這個壁紙!」
頸枕表示希望房間面向大海。「我看到一個研究說,看海可以提升幸福感百分之五。」
她們終於安靜下來了。菲比深深感謝她們的沉默。她又可以思考了。她閉起雙眼假裝在廚房裡看著大笑的丈夫,心中滿是愛慕。菲比一直很喜歡他的笑聲,尤其是從遠處傳來的時候。宛如遠方的霧角,提醒她該往哪裡去。但這時一個吉姆大喊:「新娘來了!」
「吉姆!」新娘說。
新娘踏出電梯走進大廳,身上披著一條亮片授帶,上面寫著「新娘」,所以絕不會錯。其實就算沒有也不會弄錯。一看就知道她是新娘,她走路的動作、微笑的表情都昭告著她是新娘,她走向排隊的頸枕與丸子頭,開心轉圈的動作也充滿新娘味,因為在這兩、三天的時間裡,新娘就是可以做這樣的事。此刻她就是明星,她是這許多人花上好幾千元來此的原因。
「看到妳們我好開心啊!」新娘嚷嚷。她張開雙臂擁抱她們,她手腕上掛著好幾個禮物袋,眾多提繩看起來很像海藻編成的手環。
頸枕與丸子頭說得沒錯。菲比無法從新娘身上找出任何醜的地方,或許這就是她醜的地方。她看起來就是新娘應該要有的樣子──一身夏季連身裙襯得她嬌小纖細,底下完全看不出內衣褲的痕跡。一頭金髮編成非常浪漫的繁複髮辮,菲比很想知道她看了多少Instagram上的教學影片。
「妳好美。」丸子頭說。
「謝謝、謝謝,」新娘說,「飛行順利嗎?」
「平安無事。」頸枕撒謊。
因為新娘在場,她們沒有提起一大群海鷗突然飛過來造成的驚恐,也沒有說緊急迫降的驚險。這是她們的責任,她們必須在婚禮期間對新娘撒謊,必須宣稱來這裡的旅程舒適無比,必須在困坐家中無所事事兩年之後表現出非常期待這場紐波特婚禮。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和蓋瑞見面?」丸子頭問。
「晚一點的洗塵宴,他會出席,不用說吧?」
「當然不用說嘍。」頸枕說,她們一起大笑。
新娘將海藻禮物袋送給她們(裡面有「緊急備品」),頸枕和丸子頭從裡面拿出酒瓶,兩人同聲驚呼,不是迷你瓶而是正常瓶。種類全都不同,新娘說明。她上個月和蓋瑞去歐洲旅行時親自挑選的。
蘇格蘭威士忌、西班牙里奧哈紅酒、伏特加。
「噢,真高級。」丸子頭說。
新娘微笑,似乎以自己為榮。因為她和醫師未婚夫去歐洲旅遊時,沒忘記那些比較沒那麼好命的朋友。因為她在歐洲學到哪些酒該喝、哪些不該喝。
「來,妳的。」新娘對菲比說,語氣如此親暱,菲比覺得她好像是小時候親近但很久沒聯絡的親戚。就好像她們曾經一起在爺爺家昏暗的地下室玩西洋棋之類的。她遞給菲比一個禮物袋,然後給她一個非常用力的擁抱,彷彿在練習新娘的擁抱,就像菲比的老公以前會在面試前練習專業握手動作。「只是一點小東西,感謝妳們特地跑來這麼遠的地方。我們很清楚要來這裡有多難!」
其實對菲比而言並不難。她沒有通知郵局停送信件,也沒有雇用鄰居家的小朋友幫忙澆花,更沒有像以前去度假時那樣請巴伯代課。她甚至沒有清掉流理臺上的麵包屑。她只是穿上這件長禮服,走出家門,以前所未有的瀟灑拋下一切。
「噢,我……」菲比想解釋。
「我懂,我知道妳想說什麼。」新娘說。「到底誰會喝巧克力紅酒?」
新娘很好。非常稱職的新娘。經過兩年的極度孤獨,現在突然有人這樣對她說話,菲比嚇了一大跳。那兩年之中,她只能對著電腦螢幕上的一片黑格子問:「什麼是文學?」那些黑格子不知道也不關心,那些黑格子根本沒在聽。「什麼是文學?」菲比問了一次又一次,最後連她自己都搞不清楚答案。
現在她毫無理由收到擁抱與一袋巧克力紅酒。這些年來,連老公都不肯看她的眼睛,現在卻有個陌生美女注視她的雙眼。菲比好想哭,她好希望自己真的是來參加婚禮的。
「不過其實比想像中好喝,」新娘說,「德國人很愛。」
新娘微笑,菲比發現她的兩顆門牙中間卡到食物殘渣。找到了:今天讓新娘很醜的地方。
「下一位?」櫃臺小姐喊。
菲比片刻之後才察覺輪到她了。她看到丸子頭和頸枕已經往電梯走去了。她收下禮物,向新娘道謝之後走向櫃臺。
「妳一定也是來參加婚禮的吧?」櫃臺小姐問。她的名字叫寶琳。
「不是,」菲比承認,「我不是。」
「噢。」寶琳說,她似乎很失望。更正確地說,應該是困惑。她的視線飄向遠處的新娘。「我以為所有今天入住的人都是婚禮賓客。」
「我絕對不是來參加婚禮的。但是我今天早上訂房了。」
「噢,我相信。」寶琳邊說邊敲鍵盤。「我只是在想一定有人出大錯了。搞不好就是我!請見諒,疫情之後我們有點人手不足。」
菲比點頭。「勞工短缺。」
「就是啊。」寶琳說。「好,請問貴姓大名?」
「菲比・史東。」
是真的。這是她的名字,是她這些年來自認屬於她的名字。然而,現在說出來感覺像撒謊,因為史東是老公的姓氏。每當她聽見自己說出這個姓氏,感覺就像靈魂被推出體外,讓她可以像鳥一樣從高處看自己。婚禮賓客一定也這樣看她,她相信即使從高處往下看,他們絕對也能發現她身上醜的地方:她的頭髮。她早該打理了,而且早上完全忘記要梳頭。
「找到了。」寶琳說。她太專心為眼前的客人提供頂級服務,當一位婚禮賓客走進大門之後在菲比身後滑倒,她甚至沒有抬起頭。
「吉姆舅舅!噢,老天!你還好吧?」新娘驚呼。
吉姆舅舅很不好。他躺在地上,大聲喊著他的腳踝受傷了,然後抱怨地板爛透了,根本是狗屎。幾名酒紅色制服的男員工圍著他關心,為地板太滑而一再道歉。沒錯、沒錯,他們說,地板爛透了,不過菲比看得出來,地板絕對是義大利產的大理石。
「好了。」寶琳說。寶琳是大英雄。「妳的房間是咆哮二○年代。」
「每個房間都以時代命名?」菲比問。她想像每個房間都有獨特的髮型、專有的戰爭、不同的股市起伏跌宕、各自表述的女性主義。
「說到這個,其實我不知道每個房間的主題呢!」寶琳說。「我是新來的,現在還看不出房間命名的邏輯。不過這個問題很棒喔。」
她拉開抽屜找出房間鑰匙。
「這是我們的頂樓套房,」她說,「只有這個房間能正面看到大海。」
這番話感覺特別練習過,就好像寶琳對每位房客都會輕聲說一小段話,讓他們感覺得到特殊待遇。只有這個房間配備了鐵路大亨范德比家中使用的書桌。只有這個房間無限供應衛生紙。
「太好了。」菲比說。
「請問妳造訪康瓦爾度假村的目的為何?」
即使菲比早就知道寶琳會這麼問,但還是吃了一驚。之前她想像過入住這裡的感覺,但她沒想到會需要與人交談。基本上,她太久沒練習。
「這裡是我的幸福地點。」菲比脫口而出。這個回答不盡真實,但也並非撒謊。
「噢,妳以前來過?」寶琳問。
「沒有。」菲比說。
兩年前,菲比在一本忘記叫什麼名字的雜誌上,看到這家酒店的廣告,她只有在人工生殖診所候診時才會看那種雜誌。她看著照片裡俯瞰大海的維多利亞時代天蓬大床,心中想著,誰會真的看旅遊雜誌決定去哪裡度假?雖然她不認識這樣的人,卻對他們感到憤怒。然而,幾天後,當心理治療師要求她閉起眼睛描述心中的幸福地點,她想像自己躺在那張天蓬大床上,因為唯有在不曾去過的地方、沒有躺過的床上,她才能想像自己幸福的模樣。
「這裡確實讓人感到幸福。」寶琳說。
菲比拿起鑰匙。她已經聊太久了,也假裝正常太久了。她花了八百元入住這家酒店,不是為了假裝正常。要假裝正常在家就可以了。她感覺自己越來越心累,但寶琳還有一大堆問題。要不要加購Spa療程?要不要預約駐店塔羅大師占卜?要普通枕頭還是椰子枕頭?
「椰子枕頭是什麼?」菲比問。
「裡面有椰子的枕頭。」寶琳說。
「裡面有椰子的枕頭比較好嗎?」她問。
這是她老公會問的問題。這是她的壞習慣,十年婚姻生活的後遺症──總是想像老公會說什麼,即使他不在也一樣,或者該說他不在的時候更是這樣。菲比當初沒想過自己會變成這樣的女人。但過去幾年她學到了教訓:人很難知道自己會變成什麼樣子。
「這種枕頭好很多,」寶琳說,「相信我。我會請人送一個上去。」
菲比走進電梯,門開始關閉時她鬆了一口氣。終於能夠遠離婚禮賓客。終於能做不一樣的事。終於拿到了不是她家的鑰匙。
「電梯等一下!」一個女人大喊。
菲比還沒看到人就知道是新娘。她的語氣彷彿電梯理所當然要等她。但世上沒有理所當然的事,就連新娘也一樣。菲比按下關門鍵,但新娘伸出一隻手企圖擋門。一般電梯卡到東西會自動打開,但這部沒有。或許是因為康瓦爾度假村建造於一八六四年,老酒店沒有半點仁慈,即使對方是新娘也一樣。
「靠!」新娘痛呼。
「噢,老天!」菲比說。她硬是掰開門,難以置信地呆望新娘的手。「妳流血了。」
新娘的手背指節上有道傷口,她像小孩一樣舉起那隻手,接過菲比送上的面紙,沒有道謝。菲比按下按鈕,門重新關上。電梯往上移動,她們沒有交談,新娘的血非常有禮貌,默默流進面紙裡。菲比聽到新娘調整呼吸,看到面紙染上深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