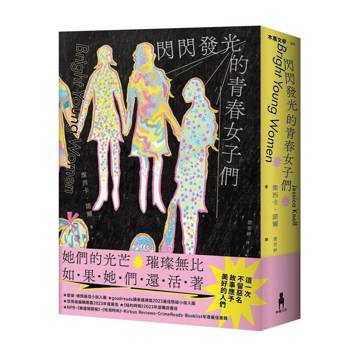佛羅里達州,塔拉哈西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
事發前七小時
每逢週六夜,我們在梳妝打扮時,全都會房門洞開。女孩走進某個房間後,會換一身較短的衣裳走出來。走廊跟軍艦上的通道一樣侷促,充斥著誰有什麼活動、要去哪裡、跟誰去的喧鬧話語。我們的私人臭氧層瀰漫著髮膠和指甲油的氣味,轟轟作響的吹風機烘得牆上的水銀溫度計升高四、五度。我們會把窗戶微微打開讓空氣流通,揶揄隔壁酒吧傳出的音樂;週六夜是迪斯可夜,而迪斯可是老人音樂。英國歌手貝瑞.吉普用他的穿腦假音哼哼唧唧地唱歌,讓人感覺大家都能見到明日的朝陽,要說會有什麼壞事發生,簡直違反統計學;然而實際上,我們屬於數學模型中的「離群值」。
有人用指節在我的房門敲出特殊節奏,伴隨著故作羞赧的嗓音。「好像快下雪了耶。」我正閱讀鋪滿我那張古董立式寫字檯上的志工行程表,聽到話聲抬起頭,看到德妮絲.安多拉站在門口,嬌滴滴地將雙手交握在下腹前方。
「想得美。」我笑著說。德妮絲想找藉口,借穿我的絨羊皮大衣。儘管一九七八年的冬季讓佛羅里達西北區結了厚厚一層冰,佛州與喬治亞州交界處的杜鵑樹都凍死了,卻一直沒冷到真的下雪。
「拜託嘛,潘蜜拉!」德妮絲雙手作出祈禱狀,舉著凍紅的指尖,愈來愈急切地反覆懇求。「拜託嘛、拜託嘛、拜託嘛。我的外套全都不搭。」她轉了一圈證明自己所言不虛。
對於她那天晚上的服裝細節,我完全是後來看了報紙才知道:高領薄上衣紮進牛仔褲,相配
的栗色麂皮腰帶,麂皮靴,蛋白石耳環,以及她心愛的吊飾銀手鍊。我的摯友身高大概有三千公分,體重卻比小時候的我還輕,不過讀到大四時,我已經學會把嫉妒之情當成偏頭痛共存。每當德妮絲認定她需要吸引男性注意時,若是太仔細看她,就會觸發那股眼冒金星的疼痛。
「別逼我求妳嘛。」她輕輕跺腳。「羅傑有向幾個女生打聽,我今晚會不會去。」
我擱下鉛筆。「德妮絲。」我責備地說。
我早已數不清,德妮絲和羅傑有多少回聲明以後不相往來,卻又在某個晚間活動不期而遇;記不清他們用多少溫掉的啤酒和眷戀的凝視,才終於原諒中傷對方的惡毒言詞。但最近這次分手感覺不像分手,更像拿一把不乾淨的菜刀將兩人切斷連結,德妮絲還真的受到了感染,將近一星期,她吃什麼吐什麼,還脫水而住院幾天。我去醫院接她時,她發誓羅傑已永遠從她體內排空。保險起見,我沖了兩次馬桶呢,她當時說,發出虛弱的笑聲,我扶她從醫院的輪椅站起來,坐到汽車前座。
現在,德妮絲可疑地突然聳聳肩,晃到我的窗前。「走到藍綠之屋只有幾個街區,而天氣預報說今晚會下七公分的雪。我會有點冷啦,不過──」她轉開窗閂,手心平貼在玻璃上,留下不久之後世上就沒有任何人符合的指紋。「也許羅傑會自告奮勇幫我取暖。」她面向我,在冷若冰霜的室內挺起胸膛。除非德妮絲的父母週末來看她,她的胸罩一向留在最上層的抽屜裡等著起毛球。
我感覺自己心軟了。「妳能保證穿過之後拿去乾洗嗎?」
「是的,女士,潘完美女士。」德妮絲模仿軍人,將高跟鞋砰地併攏。在她為我取的綽號中,「潘完美」不完全出自善意,這是從黃金時段的熱門廣告抄來的,廣告中的女人剪了羽毛劉海,誇耀那瓶純植物成分的噴霧油,如何為她節省時間、金錢以及熱量。用潘做飯,她一邊嚷嚷,一邊將煎鍋裡的銀皮魚滑入瓷盤,晚餐總是能「潘完美」。
德妮絲是我在佛羅里達州立大學交到的第一個朋友,但我們最近的關係有點僵。泛希臘組織
的領導階層一直有個核心陋習,就是徇私;歷屆會長要求某些會員照章行事,卻又放任自己的好友們無法無天。我參選會長並獲勝後,心知德妮絲以為作為領導者的我,會對她網開一面。結果,我一心想做得比歷屆會長強,希望留下公平無私的美名。那學期,德妮絲被噹的次數超過其他所有會員。每次她蹺掉星期一的全員會議,或是拖延服務活動,彷彿都在挑戰我敢不敢踢掉她。其他女孩看著我們像兩隻雄性白尾鹿,低頭用鹿角對抗。我們的財務有一頭紅棕秀髮,曾打進佛羅里達小姐決賽,從小就在富蘭克林郡打獵,她總勸我們一人先讓步,否則遲早互相卡死,只能把角鋸開。她在野外見過這種狀況。
「大衣就借妳穿吧。」我鬆口說道。
德妮絲像孩子般,開心蹦跳到我的衣櫃前。我覺得自己有如惡劣的後母。她將手臂滑進大衣的絲質襯裡時,陶醉得眼睛往上翻。多虧我母親將人生奉獻在打點這種事上,我有許多漂亮衣服,穿起來像更加柔軟的第二層皮膚一樣合身。要是我衣櫃的半數衣服穿在我身上跟德妮絲穿起來一樣好看,或許我也會在乎穿著打扮。然而現實是我生了張愛爾蘭圓臉,跟我的身材格格不入。對,我脖子以下不是身體,而是身材。我那像蘋果般飽滿又長滿雀斑的臉頰,與前凸後翹的身材實在太不搭,反差大到我經常有種想為此道歉的衝動。我是美女還是普女,取決於是什麼人在盯著我什麼部位。
「妳走之前,能先幫我關上窗戶嗎?」一陣風吹進房間,差點捲走我用不同顏色整理好的行事曆散頁,我趕緊一掌拍桌按住。
德妮絲走到窗邊,戲劇化地作勢將窗框往下壓,邊發出用盡全力的悶哼聲。「卡住了。」德妮絲說。「妳最好跟我一起去,免得在規畫第三十三屆年度捐血活動時凍死。這種死法也太慘了。」
我嘆氣,並非我渴望參加那場吵鬧的兄弟會派對,卻真的必須籌備第三十三屆年度捐血活動而不能去;我嘆氣是不曉得如何讓德妮絲明白,我真的不想去,我最滿足的時刻就是週六晚上坐在被鉛筆刮花的寫字檯前,從打開的房門聽見三十八個女孩準備出門的喧鬧和浮誇,感覺一週將盡時,所有人都能放著音樂、刷上睫毛膏、隔著走廊嘻嘻哈哈,表示我善盡了自己的職責。我喜歡從房間聽那些聲音,聽我們互相挑剔。誰的大拇趾需要除毛,誰如果希望有生之年還能找到人生孩子,就千萬別在公開場合跳舞。
「我不去,妳會玩得比較開心。」我蹩腳地反駁。
「妳知道嗎,總有一天。」德妮絲轉身,老實地關上窗,一頭深色長髮像超級英雄的披風飄揚。「妳的美胸會變成布袋奶,於是妳黯然回首才驚覺──」德妮絲用一聲尖叫收尾,而我的神經系統幾乎沒察覺她有尖叫。當時我們是二十一歲的姊妹會會員,我們尖叫,並不是出了什麼不可思議的可怕災難,而是週六夜令我們亢奮又無憂無慮。從那天之後,我就開始厭惡大部分人期待了一整週的這一天,厭惡它讓人有虛假的安全感,厭惡它讓人產生自由和歡樂的錯誤期待。
前門外的草皮上有兩個姊妹會會員,喘吁吁地拖著一件用布裹住的東西,它的形狀大小跟電影海報差不多;她們在寒冷中施力,臉頰泛紅,放大的瞳孔像是正受到獵捕而心如擂鼓。
「幫幫忙。」她們半笑半喘說。德妮絲和我趕到我們那塊小得可憐的短草皮上迎接她們,這邊緣種了又長又蓬的粉黛亂子草,以備隔壁酒吧的停車場客滿時,遏阻顧客把車停在我們的土地上。這個造景心機實在太有效了,那些從人行道經過,要趁小歇餐館打烊前去吃點東西的學生,都沒有半個人跨進草皮幫忙。
我站到中間,蹲下去抬起包裹底部。德妮絲則只是將兩根手指塞到嘴巴,吹了個尖銳的響哨。兩個走我們的巷弄抄近路的男人猛地煞住腳步。再多造景,也阻止不了別人偷用我們的捷徑,我倒也不能苛責他們。塔拉哈西的街區跟紐約市的大道一樣長,而我知道這個冷知識讓德妮絲很樂。
「我們需要幫手。」德妮絲甩了甩她耗費數小時整理得絲滑柔順的黑髮,屁股往旁邊一扭,這是每個男人都幻想遇到的便車客。
我看到啃得亂七八糟的男生指甲托著我們的違禁物,離我的手指只有幾公分,而我立刻感到重量變輕了。我走到隊伍前方,指揮兩個男人爬上三階門階,然後走進雙扇前門,一邊叮囑:「小心啊,往左邊一點,不對,是另一個左邊!」我們剛把前門新漆成矢車菊藍,搭配門廳壁紙的條紋;而在那一刻,所有人都聚到門廳來──包括本來在廚房裡弄爆米花的女孩、擠在娛樂室沙發上補看週間錄下的《讓世界轉動》肥皂劇的女孩、準備出門而劉海上了髮捲並揮著剛塗完指甲油的手指的女孩。她們一方面想看看為何有騷動,一方面也想偷偷掂量我們從路邊抓來的搬運工,這兩人至少比我們老了八歲,倒也比經常邀我們共進晚餐的那些教授要年輕。
接下來該怎麼辦,大家意見不太一致。德妮絲堅持要兩個男人繼續搬上樓,但依規定,只有搬家日當天的會員家人以及雜務工需要修東西時,才可以讓男性上到二樓。
「潘蜜拉,別這麼死板嘛。」德妮絲央求。「妳也知道要是我們把它留在這裡,還來不及交換就會被他們偷回去了。」雖然這物品裹著床單,我們都知道那是我們學伴兄弟會的裱框拼貼學生照,每位正式會員都穿西裝打領帶,擺出一本正經的表情,畫面中央是響尾蛇配雙劍會徽。這活動我們已經來來回回進行了好幾個月,每棟寓所的會員都要偷走另一棟寓所的拼貼照,留下牆上一塊沾著煤灰的方形,就連強效清潔劑都擦不掉。
德妮絲用畫了眼線的水汪汪眼睛盯著我,眼神彷彿在說:「堵到妳了吧!」十幾年後,我終於當上母親,會認出同樣的伎倆:故意在滿屋子人面前要求妳明知道不允許的事,因為那些人都希望妳成功。我根本不可能拒絕,除非我不在乎所有人都視我為刻薄的老巫婆。
我從喉嚨深處發出哼聲。她好大的膽子,竟然開口要求。
德妮絲張開雙脣,失望地臉色一垮。我對這表情很熟悉,每次德妮絲發現我身為她長久以來的好友,竟擺出會長的架勢,都會露出這模樣。
「男人上樓!」我大喊。德妮絲雙手抓著我肩膀,戲謔地搖晃我表示抗議。她差點就中計了。接著我們就被其他女孩簇擁著推上樓,她們像一群魚在移動,活躍的整體進入樓梯間時變細,到了平臺又散開,然後進到我們前寬後窄的走廊又再度變細。我們一路唱著「男人上樓」,不是齊聲合唱,而是每個獨立的嗓音刺耳地互軋。某個會員(誰也不記得是哪位)總是把那首保羅.麥卡尼的〈樂團上路〉聽成「男人上路」,改個字之後,本會的內部笑話就誕生了。這句話太琅琅上口,隔天早晨,當我昏沉而順從地坐在我們的飯廳裡,還聽到有人在哼唱副歌。那時有一大堆男人上樓,有些穿藍制服,有些穿白色實驗服,管事的則穿便服,他們把染血的地毯割成方形取下,並用鑷子從粗絨毛間夾起一顆顆臼齒。接著,又有另一個人直接唱出來──「男人上樓,男—人上樓!」於是我們笑起來,真的捧腹大笑,笑到有些穿制服的客人都在樓梯間停下動作,望向我們,他們責難的臭臉上摻雜些微憂慮。
拼貼照送到了四號房,也就是執行這起竊案的兩個女孩的房間。我們的搬運工懷疑地打量狹小空間,先用腳跟把房門踢上,再將那件珍寶斜倚在兩張單人床其中一張的床腳。要進入那個房間得側著走,不過我想以我的「身材」,就算側身我也進不去。
「妳們沒有閣樓之類的嗎?」其中一個男人問。
我們有,但把拼貼照留在臥室,如同將一對鹿角掛在牆上──德妮絲向他們解釋。有些女孩已經擠進微開的門縫,拿著相機,為四號房的小鎮英雄拍照留念,英雄本人則咧嘴站在獵物旁擺姿勢,手比空氣槍、秀髮披散在背後,貌似霹靂嬌娃。再過幾小時,他就會試著進入這個房間,卻因為一九四八年那一屆的拼貼照而困難重重──我仍歷歷在目,女孩們偷的是那一年的照片,照片中的男生搽了髮油、戴著牛角框眼鏡。現今,雪倫.賽爾瓦在奧斯汀擔任口腔外科醫師。潔姬.科勒里則是歷史系的終身教授,任教的正是一九七八年冬天陷入恐懼的那間大學。全都多虧了愚蠢的姊妹會惡作劇。
德妮絲堅定走向放在一疊舊雜誌上的琥珀燈座檯燈,轉開螺絲,取下燈罩,將電線繃到最緊,因為她要蹲在照片前面,用燈泡掃描表面,就像有人手持金屬探測器跑去沙灘尋寶。
她敬畏地搖搖頭。「他們就連四〇年代的拼貼照,裱框品質都堪比美術館!」她發自內心憤
慨地叫道。
兩年來,我們都讓藍綠之屋(名稱來自他們窗板和大門的油漆顏色)的男生以為,他們參與的是歷代交情好的姊妹會和兄弟會之間,都會玩的經典友誼竊盜遊戲。但他們有所不知,我們會將他們拼貼照的高級玻璃,掉包成我們的壓克力塑膠玻璃,再提出要交換戰利品。這個差異是我們大二時,德妮絲發現的。
這玻璃太迷人了,當時她用氣音說,惹得學姊們大笑,因為勞勃.瑞福可以用迷人形容,但是⋯⋯玻璃?小大二德妮絲帶著大家浩浩蕩蕩走到我們的展示牆,指出差別在哪裡──看出我們的拼貼照褪色得多厲害嗎?藍綠之屋用的是玻璃,昂貴的博物館級玻璃,保護他們的照片不受日光和塵蟎等元素損害。德妮絲雙主修美術和現代語言,前者一向是她的志願,後者則是去年夏天才加進去的,因為她在《塔拉哈西民主報》讀到,佛羅里達的聖彼得堡要興建一座頂級的達利博物館。德妮絲立刻轉而決定要雙主修現代語言,專修西班牙文;她過完二十歲生日的那個暑假就留在學校,把兩年的學分都補齊了。達利本人即將飛過來面試未來的工作人員,而德妮絲打算以他的母語讓他驚豔。雖然也不令人訝異,總之他們終於見面後,他完全被她征服,雇用她當助理畫廊經理人,畢業後的第一個星期一就開始上班。
「我很懷疑他們會注意到⋯⋯」大二的德妮絲沒把話說完,她夠靈光,知道尚在新人考核期的她不能出面提議該怎麼做。
兄弟會與姊妹會的生活,至今以來都有很多歧異,不過當時的會長總是強調的重大差別,在於校友回饋分會的程度有多高。歷代以來,兄弟會會員在畢業後的經濟實力都優於姊妹會會員,於是一般而言,兄弟會的寓所都傲然擁有較新的家具、頂尖空調設備,以及──「正如我們有一雙鷹眼的姊妹德妮絲.安多拉最近指出的。」下一次開會時,會長一開始就說。「他們連玻璃都比我們更晶瑩剔透。」
那天傍晚,這項計謀獲得允准,而且聽說有人抱怨,至今那些姊妹會女孩仍對這活動樂此不疲。
德妮絲用長指甲輕敲耐用又抗眩光的玻璃,發出近似性感的呻吟聲。「天啊,真是好東西。」她說。
「德妮絲,要我們讓妳跟玻璃獨處嗎?」雪倫面不改色地問。
「去他的羅傑。」德妮絲在透明表面印下一個溼吻。「這塊玻璃和我要幸福美滿、白頭偕老。」
有時候,若我出庭的結果不如人意,而我開始覺得司法畢竟是種謬誤,我就會想起殺害德妮絲的凶手坐上電椅前六小時,達利才剛去世。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查查看就知道了。世界上最知名且古怪的藝術家逝去,代表佛州中部某個人渣被處死絕不是當天的頭條新聞,而他被帶到行刑室的時候,應該會因此悵然若失。比起他自己的自由,比起有機會讓我後悔對他做了什麼,他更想要的是吸引眾人目光。那些不順遂的日子裡,我總愛想像德妮絲身在那個真正的麗人死後會去的地方,而且她設法動了點手腳,讓他的死亡黯然失色,正如同他讓她在世上短暫的生命戛然而止。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這是《讓世界轉動》裡那些潑辣女子教我們的。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
事發前七小時
每逢週六夜,我們在梳妝打扮時,全都會房門洞開。女孩走進某個房間後,會換一身較短的衣裳走出來。走廊跟軍艦上的通道一樣侷促,充斥著誰有什麼活動、要去哪裡、跟誰去的喧鬧話語。我們的私人臭氧層瀰漫著髮膠和指甲油的氣味,轟轟作響的吹風機烘得牆上的水銀溫度計升高四、五度。我們會把窗戶微微打開讓空氣流通,揶揄隔壁酒吧傳出的音樂;週六夜是迪斯可夜,而迪斯可是老人音樂。英國歌手貝瑞.吉普用他的穿腦假音哼哼唧唧地唱歌,讓人感覺大家都能見到明日的朝陽,要說會有什麼壞事發生,簡直違反統計學;然而實際上,我們屬於數學模型中的「離群值」。
有人用指節在我的房門敲出特殊節奏,伴隨著故作羞赧的嗓音。「好像快下雪了耶。」我正閱讀鋪滿我那張古董立式寫字檯上的志工行程表,聽到話聲抬起頭,看到德妮絲.安多拉站在門口,嬌滴滴地將雙手交握在下腹前方。
「想得美。」我笑著說。德妮絲想找藉口,借穿我的絨羊皮大衣。儘管一九七八年的冬季讓佛羅里達西北區結了厚厚一層冰,佛州與喬治亞州交界處的杜鵑樹都凍死了,卻一直沒冷到真的下雪。
「拜託嘛,潘蜜拉!」德妮絲雙手作出祈禱狀,舉著凍紅的指尖,愈來愈急切地反覆懇求。「拜託嘛、拜託嘛、拜託嘛。我的外套全都不搭。」她轉了一圈證明自己所言不虛。
對於她那天晚上的服裝細節,我完全是後來看了報紙才知道:高領薄上衣紮進牛仔褲,相配
的栗色麂皮腰帶,麂皮靴,蛋白石耳環,以及她心愛的吊飾銀手鍊。我的摯友身高大概有三千公分,體重卻比小時候的我還輕,不過讀到大四時,我已經學會把嫉妒之情當成偏頭痛共存。每當德妮絲認定她需要吸引男性注意時,若是太仔細看她,就會觸發那股眼冒金星的疼痛。
「別逼我求妳嘛。」她輕輕跺腳。「羅傑有向幾個女生打聽,我今晚會不會去。」
我擱下鉛筆。「德妮絲。」我責備地說。
我早已數不清,德妮絲和羅傑有多少回聲明以後不相往來,卻又在某個晚間活動不期而遇;記不清他們用多少溫掉的啤酒和眷戀的凝視,才終於原諒中傷對方的惡毒言詞。但最近這次分手感覺不像分手,更像拿一把不乾淨的菜刀將兩人切斷連結,德妮絲還真的受到了感染,將近一星期,她吃什麼吐什麼,還脫水而住院幾天。我去醫院接她時,她發誓羅傑已永遠從她體內排空。保險起見,我沖了兩次馬桶呢,她當時說,發出虛弱的笑聲,我扶她從醫院的輪椅站起來,坐到汽車前座。
現在,德妮絲可疑地突然聳聳肩,晃到我的窗前。「走到藍綠之屋只有幾個街區,而天氣預報說今晚會下七公分的雪。我會有點冷啦,不過──」她轉開窗閂,手心平貼在玻璃上,留下不久之後世上就沒有任何人符合的指紋。「也許羅傑會自告奮勇幫我取暖。」她面向我,在冷若冰霜的室內挺起胸膛。除非德妮絲的父母週末來看她,她的胸罩一向留在最上層的抽屜裡等著起毛球。
我感覺自己心軟了。「妳能保證穿過之後拿去乾洗嗎?」
「是的,女士,潘完美女士。」德妮絲模仿軍人,將高跟鞋砰地併攏。在她為我取的綽號中,「潘完美」不完全出自善意,這是從黃金時段的熱門廣告抄來的,廣告中的女人剪了羽毛劉海,誇耀那瓶純植物成分的噴霧油,如何為她節省時間、金錢以及熱量。用潘做飯,她一邊嚷嚷,一邊將煎鍋裡的銀皮魚滑入瓷盤,晚餐總是能「潘完美」。
德妮絲是我在佛羅里達州立大學交到的第一個朋友,但我們最近的關係有點僵。泛希臘組織
的領導階層一直有個核心陋習,就是徇私;歷屆會長要求某些會員照章行事,卻又放任自己的好友們無法無天。我參選會長並獲勝後,心知德妮絲以為作為領導者的我,會對她網開一面。結果,我一心想做得比歷屆會長強,希望留下公平無私的美名。那學期,德妮絲被噹的次數超過其他所有會員。每次她蹺掉星期一的全員會議,或是拖延服務活動,彷彿都在挑戰我敢不敢踢掉她。其他女孩看著我們像兩隻雄性白尾鹿,低頭用鹿角對抗。我們的財務有一頭紅棕秀髮,曾打進佛羅里達小姐決賽,從小就在富蘭克林郡打獵,她總勸我們一人先讓步,否則遲早互相卡死,只能把角鋸開。她在野外見過這種狀況。
「大衣就借妳穿吧。」我鬆口說道。
德妮絲像孩子般,開心蹦跳到我的衣櫃前。我覺得自己有如惡劣的後母。她將手臂滑進大衣的絲質襯裡時,陶醉得眼睛往上翻。多虧我母親將人生奉獻在打點這種事上,我有許多漂亮衣服,穿起來像更加柔軟的第二層皮膚一樣合身。要是我衣櫃的半數衣服穿在我身上跟德妮絲穿起來一樣好看,或許我也會在乎穿著打扮。然而現實是我生了張愛爾蘭圓臉,跟我的身材格格不入。對,我脖子以下不是身體,而是身材。我那像蘋果般飽滿又長滿雀斑的臉頰,與前凸後翹的身材實在太不搭,反差大到我經常有種想為此道歉的衝動。我是美女還是普女,取決於是什麼人在盯著我什麼部位。
「妳走之前,能先幫我關上窗戶嗎?」一陣風吹進房間,差點捲走我用不同顏色整理好的行事曆散頁,我趕緊一掌拍桌按住。
德妮絲走到窗邊,戲劇化地作勢將窗框往下壓,邊發出用盡全力的悶哼聲。「卡住了。」德妮絲說。「妳最好跟我一起去,免得在規畫第三十三屆年度捐血活動時凍死。這種死法也太慘了。」
我嘆氣,並非我渴望參加那場吵鬧的兄弟會派對,卻真的必須籌備第三十三屆年度捐血活動而不能去;我嘆氣是不曉得如何讓德妮絲明白,我真的不想去,我最滿足的時刻就是週六晚上坐在被鉛筆刮花的寫字檯前,從打開的房門聽見三十八個女孩準備出門的喧鬧和浮誇,感覺一週將盡時,所有人都能放著音樂、刷上睫毛膏、隔著走廊嘻嘻哈哈,表示我善盡了自己的職責。我喜歡從房間聽那些聲音,聽我們互相挑剔。誰的大拇趾需要除毛,誰如果希望有生之年還能找到人生孩子,就千萬別在公開場合跳舞。
「我不去,妳會玩得比較開心。」我蹩腳地反駁。
「妳知道嗎,總有一天。」德妮絲轉身,老實地關上窗,一頭深色長髮像超級英雄的披風飄揚。「妳的美胸會變成布袋奶,於是妳黯然回首才驚覺──」德妮絲用一聲尖叫收尾,而我的神經系統幾乎沒察覺她有尖叫。當時我們是二十一歲的姊妹會會員,我們尖叫,並不是出了什麼不可思議的可怕災難,而是週六夜令我們亢奮又無憂無慮。從那天之後,我就開始厭惡大部分人期待了一整週的這一天,厭惡它讓人有虛假的安全感,厭惡它讓人產生自由和歡樂的錯誤期待。
前門外的草皮上有兩個姊妹會會員,喘吁吁地拖著一件用布裹住的東西,它的形狀大小跟電影海報差不多;她們在寒冷中施力,臉頰泛紅,放大的瞳孔像是正受到獵捕而心如擂鼓。
「幫幫忙。」她們半笑半喘說。德妮絲和我趕到我們那塊小得可憐的短草皮上迎接她們,這邊緣種了又長又蓬的粉黛亂子草,以備隔壁酒吧的停車場客滿時,遏阻顧客把車停在我們的土地上。這個造景心機實在太有效了,那些從人行道經過,要趁小歇餐館打烊前去吃點東西的學生,都沒有半個人跨進草皮幫忙。
我站到中間,蹲下去抬起包裹底部。德妮絲則只是將兩根手指塞到嘴巴,吹了個尖銳的響哨。兩個走我們的巷弄抄近路的男人猛地煞住腳步。再多造景,也阻止不了別人偷用我們的捷徑,我倒也不能苛責他們。塔拉哈西的街區跟紐約市的大道一樣長,而我知道這個冷知識讓德妮絲很樂。
「我們需要幫手。」德妮絲甩了甩她耗費數小時整理得絲滑柔順的黑髮,屁股往旁邊一扭,這是每個男人都幻想遇到的便車客。
我看到啃得亂七八糟的男生指甲托著我們的違禁物,離我的手指只有幾公分,而我立刻感到重量變輕了。我走到隊伍前方,指揮兩個男人爬上三階門階,然後走進雙扇前門,一邊叮囑:「小心啊,往左邊一點,不對,是另一個左邊!」我們剛把前門新漆成矢車菊藍,搭配門廳壁紙的條紋;而在那一刻,所有人都聚到門廳來──包括本來在廚房裡弄爆米花的女孩、擠在娛樂室沙發上補看週間錄下的《讓世界轉動》肥皂劇的女孩、準備出門而劉海上了髮捲並揮著剛塗完指甲油的手指的女孩。她們一方面想看看為何有騷動,一方面也想偷偷掂量我們從路邊抓來的搬運工,這兩人至少比我們老了八歲,倒也比經常邀我們共進晚餐的那些教授要年輕。
接下來該怎麼辦,大家意見不太一致。德妮絲堅持要兩個男人繼續搬上樓,但依規定,只有搬家日當天的會員家人以及雜務工需要修東西時,才可以讓男性上到二樓。
「潘蜜拉,別這麼死板嘛。」德妮絲央求。「妳也知道要是我們把它留在這裡,還來不及交換就會被他們偷回去了。」雖然這物品裹著床單,我們都知道那是我們學伴兄弟會的裱框拼貼學生照,每位正式會員都穿西裝打領帶,擺出一本正經的表情,畫面中央是響尾蛇配雙劍會徽。這活動我們已經來來回回進行了好幾個月,每棟寓所的會員都要偷走另一棟寓所的拼貼照,留下牆上一塊沾著煤灰的方形,就連強效清潔劑都擦不掉。
德妮絲用畫了眼線的水汪汪眼睛盯著我,眼神彷彿在說:「堵到妳了吧!」十幾年後,我終於當上母親,會認出同樣的伎倆:故意在滿屋子人面前要求妳明知道不允許的事,因為那些人都希望妳成功。我根本不可能拒絕,除非我不在乎所有人都視我為刻薄的老巫婆。
我從喉嚨深處發出哼聲。她好大的膽子,竟然開口要求。
德妮絲張開雙脣,失望地臉色一垮。我對這表情很熟悉,每次德妮絲發現我身為她長久以來的好友,竟擺出會長的架勢,都會露出這模樣。
「男人上樓!」我大喊。德妮絲雙手抓著我肩膀,戲謔地搖晃我表示抗議。她差點就中計了。接著我們就被其他女孩簇擁著推上樓,她們像一群魚在移動,活躍的整體進入樓梯間時變細,到了平臺又散開,然後進到我們前寬後窄的走廊又再度變細。我們一路唱著「男人上樓」,不是齊聲合唱,而是每個獨立的嗓音刺耳地互軋。某個會員(誰也不記得是哪位)總是把那首保羅.麥卡尼的〈樂團上路〉聽成「男人上路」,改個字之後,本會的內部笑話就誕生了。這句話太琅琅上口,隔天早晨,當我昏沉而順從地坐在我們的飯廳裡,還聽到有人在哼唱副歌。那時有一大堆男人上樓,有些穿藍制服,有些穿白色實驗服,管事的則穿便服,他們把染血的地毯割成方形取下,並用鑷子從粗絨毛間夾起一顆顆臼齒。接著,又有另一個人直接唱出來──「男人上樓,男—人上樓!」於是我們笑起來,真的捧腹大笑,笑到有些穿制服的客人都在樓梯間停下動作,望向我們,他們責難的臭臉上摻雜些微憂慮。
拼貼照送到了四號房,也就是執行這起竊案的兩個女孩的房間。我們的搬運工懷疑地打量狹小空間,先用腳跟把房門踢上,再將那件珍寶斜倚在兩張單人床其中一張的床腳。要進入那個房間得側著走,不過我想以我的「身材」,就算側身我也進不去。
「妳們沒有閣樓之類的嗎?」其中一個男人問。
我們有,但把拼貼照留在臥室,如同將一對鹿角掛在牆上──德妮絲向他們解釋。有些女孩已經擠進微開的門縫,拿著相機,為四號房的小鎮英雄拍照留念,英雄本人則咧嘴站在獵物旁擺姿勢,手比空氣槍、秀髮披散在背後,貌似霹靂嬌娃。再過幾小時,他就會試著進入這個房間,卻因為一九四八年那一屆的拼貼照而困難重重──我仍歷歷在目,女孩們偷的是那一年的照片,照片中的男生搽了髮油、戴著牛角框眼鏡。現今,雪倫.賽爾瓦在奧斯汀擔任口腔外科醫師。潔姬.科勒里則是歷史系的終身教授,任教的正是一九七八年冬天陷入恐懼的那間大學。全都多虧了愚蠢的姊妹會惡作劇。
德妮絲堅定走向放在一疊舊雜誌上的琥珀燈座檯燈,轉開螺絲,取下燈罩,將電線繃到最緊,因為她要蹲在照片前面,用燈泡掃描表面,就像有人手持金屬探測器跑去沙灘尋寶。
她敬畏地搖搖頭。「他們就連四〇年代的拼貼照,裱框品質都堪比美術館!」她發自內心憤
慨地叫道。
兩年來,我們都讓藍綠之屋(名稱來自他們窗板和大門的油漆顏色)的男生以為,他們參與的是歷代交情好的姊妹會和兄弟會之間,都會玩的經典友誼竊盜遊戲。但他們有所不知,我們會將他們拼貼照的高級玻璃,掉包成我們的壓克力塑膠玻璃,再提出要交換戰利品。這個差異是我們大二時,德妮絲發現的。
這玻璃太迷人了,當時她用氣音說,惹得學姊們大笑,因為勞勃.瑞福可以用迷人形容,但是⋯⋯玻璃?小大二德妮絲帶著大家浩浩蕩蕩走到我們的展示牆,指出差別在哪裡──看出我們的拼貼照褪色得多厲害嗎?藍綠之屋用的是玻璃,昂貴的博物館級玻璃,保護他們的照片不受日光和塵蟎等元素損害。德妮絲雙主修美術和現代語言,前者一向是她的志願,後者則是去年夏天才加進去的,因為她在《塔拉哈西民主報》讀到,佛羅里達的聖彼得堡要興建一座頂級的達利博物館。德妮絲立刻轉而決定要雙主修現代語言,專修西班牙文;她過完二十歲生日的那個暑假就留在學校,把兩年的學分都補齊了。達利本人即將飛過來面試未來的工作人員,而德妮絲打算以他的母語讓他驚豔。雖然也不令人訝異,總之他們終於見面後,他完全被她征服,雇用她當助理畫廊經理人,畢業後的第一個星期一就開始上班。
「我很懷疑他們會注意到⋯⋯」大二的德妮絲沒把話說完,她夠靈光,知道尚在新人考核期的她不能出面提議該怎麼做。
兄弟會與姊妹會的生活,至今以來都有很多歧異,不過當時的會長總是強調的重大差別,在於校友回饋分會的程度有多高。歷代以來,兄弟會會員在畢業後的經濟實力都優於姊妹會會員,於是一般而言,兄弟會的寓所都傲然擁有較新的家具、頂尖空調設備,以及──「正如我們有一雙鷹眼的姊妹德妮絲.安多拉最近指出的。」下一次開會時,會長一開始就說。「他們連玻璃都比我們更晶瑩剔透。」
那天傍晚,這項計謀獲得允准,而且聽說有人抱怨,至今那些姊妹會女孩仍對這活動樂此不疲。
德妮絲用長指甲輕敲耐用又抗眩光的玻璃,發出近似性感的呻吟聲。「天啊,真是好東西。」她說。
「德妮絲,要我們讓妳跟玻璃獨處嗎?」雪倫面不改色地問。
「去他的羅傑。」德妮絲在透明表面印下一個溼吻。「這塊玻璃和我要幸福美滿、白頭偕老。」
有時候,若我出庭的結果不如人意,而我開始覺得司法畢竟是種謬誤,我就會想起殺害德妮絲的凶手坐上電椅前六小時,達利才剛去世。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查查看就知道了。世界上最知名且古怪的藝術家逝去,代表佛州中部某個人渣被處死絕不是當天的頭條新聞,而他被帶到行刑室的時候,應該會因此悵然若失。比起他自己的自由,比起有機會讓我後悔對他做了什麼,他更想要的是吸引眾人目光。那些不順遂的日子裡,我總愛想像德妮絲身在那個真正的麗人死後會去的地方,而且她設法動了點手腳,讓他的死亡黯然失色,正如同他讓她在世上短暫的生命戛然而止。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這是《讓世界轉動》裡那些潑辣女子教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