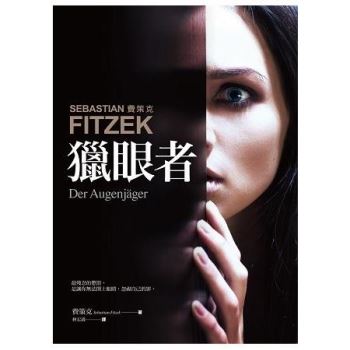***集眼者的驚人轉折:孩子獲救。凶手承認犯行。但是繼續犯案。
幾個月前,他一直在玩致命的捉迷藏,現在「集眼者」的身分真相大白:法蘭克‧拉曼,二十三歲,柏林一家大報的實習生,承認一共犯下四個女性和三個孩童的凶殘謀殺案。
拉曼的犯案過程既令人作嘔又天衣無縫:他先是殺死母親,然後綁架孩子,對父親下了四十五小時又七分鐘的最後通牒,讓他找出孩子的藏匿處。期限一到,受害者就會在被禁錮的地下室裡窒息而死。集眼者之所以有如此駭人的名字,是因為每個被發現的孩子屍體,他們的左眼都不見了。
犯罪心理學者認為,集眼者的病態行為應該是童年經驗所導致的。初步調查顯示,拉曼的成長環境相當惡劣。母親拋棄家庭,父親覺得他的孩子們是個累贅,尤其是拉曼的弟弟,他的左眼因為得了癌症而失明。
有一天,兩兄弟躲到一具廢棄的冷凍櫃裡,他們相信父親一定憂心如焚,很快就會來找他們。可是他們心中盼望的「愛的證明」落空了。他們的父親一無所知,跑去酒館喝了一整晚,兩兄弟沒辦法憑著自己的力氣從冷凍櫃脫身。湊巧有個林務員發現了他們,可是為時已晚。在受困了四十五小時又七分鐘之後,法蘭克‧拉曼的弟弟已經死了。
心理學家認為這個精神創傷就是他後來的犯案動機。拉曼寫了一封信給報社主編坦承犯行:「當然,我承認,我(編者按:還有我的犯行)總是很病態地根據我和我弟弟當時受困的環境來設定遊戲條件。一個對我們而言已經死去的母親,因此我一開始就必須把她驅逐出場。一個不關心孩子的父親。一個藏匿處,裡頭的空氣只能維持四十五小時又七分鐘,以及一具屍體,和我弟弟一樣缺了左眼。」
只不過,由於警政記者亞歷山大‧佐巴赫的介入,在最後一秒鐘阻止了集眼者第四回合的遊戲。多虧佐巴赫鍥而不捨的調查,警方終於發現凶手藏匿雙胞胎兄妹的地點。但是這位記者必須為他們的救援行動付出慘重的代價。當他從電梯井裡救出兩兄妹時,法蘭克‧拉曼已經找到新的受害者:佐巴赫的兒子尤利安。拉曼殺死了尤利安的母親妮琪,然後綁架了尤利安。
從此以後,拉曼就銷聲匿跡。亞歷山大‧佐巴赫如果還想看見他的兒子活著回來,就必須和再一次的最後通牒作戰,而時間正在一分一秒地流逝……「若有別害,就要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以烙還烙,以傷還傷,以打還打。」——《舊約‧出埃及記》21:23-25
「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新約‧馬太福音》5:38-39
***約翰娜.史卓姆
是日溫暖多雲,氣溫十三度,九月颯爽的微風習習。約翰娜‧史卓姆很喜歡這樣的天氣。正是尋死的大好時節。
她坐在花園的長椅上,身旁的男人似乎感覺到她不為人知的想法,即使他們今天還沒有說上一句話。他本來就不是很多話的人。在位於漢堡的醫院四周圍著高牆的花園裡,每天一次,午餐後兩個鐘頭,她可以「伸展一下筋骨」,誠如護士長所說的。在這條坑坑洼洼的小路上散步時得非常小心,它蜿蜒穿過精神療養院的老樹林。昨天那個老維什尼夫斯基才被覆滿秋天落葉的樹根絆倒,撞傷了臀部。「我倒寧願他撞破頭,」她聽到這位失智症病患的看護嘲笑他說:「下次他也這麼不小心就好了。」
就像聖法倫霍普療養院(Sankt Pfarrenhopp)(當地人都取其諧音叫它作「頭上中箭療養院」)(Pfeil im Kopp)裡的每個病人一樣,她也覺得這裡不是自己該待的地方。倒不是因為她自以為沒病,天曉得,她根本就有病,而是因為她對於治療這種事嗤之以鼻。如果面對的只是先後奪走她的尊嚴和健康的酗酒問題,說不定哪一天她甚至可以振作起來,和群魔交戰,用加油站商店利樂包裝的劣酒把牠們淹死。如果她有專業協助的話,當她的丈夫又想要將她綁起來「調教」的時候,或許她甚至可以反擊。在他們的關係剛開始時,她還把它當成一種遊戲,如果那可以讓伴侶開心,或許是尚可接受的事。
她在床上被罵成「三個洞的母馬」、蕩婦、思春的臭婊子,儘管一開始她必須承認很難為情,但是當他對她越來越粗暴時,她卻沒辦法否認自己的確有種莫名的興奮感。打屁股、掐脖子,感覺還不錯。她看到這些動作讓他很興奮,自己也跟著想入非非;她也知道,如果她拒絕在他射精前跪在他面前,他會大發雷霆,而她就有罪受了。他就是想要滿足從色情片學來的幻想。反正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在她意識深處的儲藏室一隅,她隱約明白一切都已經太遲了。她錯過了生命道路上的最後一個岔口,一個可以挽救這一切的岔口,在她完全失控之前。她任憑他百般作賤她,而沒有任何抗議。如果在結婚這麼多年之後,突然對克里斯提昂承認說,她其實不喜歡他的某些嗜好,那會使他發現她是個騙子,因而覺得很受傷(這是想當然耳的事,她心想)。於是她始終沉默以對,欺騙自己說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在八月一個悶熱的夏日,這個希望終於破滅。在假日大採購之後,她滿頭大汗地回家。女兒妮可拉跟著班上同學到波羅的海旅行了,她原本打算在這個寧靜的週五夜晚享受她的披薩和影片(米基‧洛克主演的《天使心》,她丈夫還不知道有這張光碟,是她在大賣場平台花三歐元買的),可是回家一看到客廳裡的不速之客,頓時大失所望。克里斯提昂和法律事務所的兩個同事大剌剌躺在沙發上。他們顯然已經喝掉幾瓶酒。約翰娜沒打算要親他當作見面禮,克里斯提昂老早就不喜歡來這套了。她每次回家時,他總是隨便拍一下她的屁股,後來則是輕輕捏一下她的乳頭。可是今天他做得太過火了。
她再也不記得那天晚上發生的所有事,其中許多事都安然無恙地鎖在她的下意識裡,然而光是留在記憶裡的,就足以讓她至今仍然時常從夢中驚叫醒來。
克里斯提昂站起來,毫無預警地摑了她一巴掌。
「妳讓我們等太久了,妳這頭死母豬,」他裝出責備的語氣,然後轉向他的朋友說:「你們說我們該怎麼處罰我的這個蕩婦?」
約翰娜勉強扮了個鬼臉,以微笑若無其事地表示她的丈夫突如其來的暴力只是個無傷大雅的玩笑。他的律師朋友(他們兩個都西裝筆挺,繫著領帶,胸前口袋塞著方巾;兩個人都戴著婚戒)曖昧地笑了笑。這會兒她才注意到螢幕上正以靜音模式播放著愛情動作片。一個一絲不掛的女性頭上套著皮罩。
「你們想要來點什麼嗎?」約翰娜顫聲問道,直到今天,她仍然不確定這個舉動到底是不是個錯誤。克里斯提昂是不是認為她同意在他的朋友面前表演角色扮演的遊戲。
演出。克里斯提昂把它當成家暴的同義詞。他總是在床上對她輕聲談到他的暴力幻想:他想要在樹林裡把她剝光衣服綁在大樹上,讓她像獵物一樣任由路過的慢跑者蹂躪。他的幻想有時候很可笑(有一次他甚至要她到一家妓院當妓女),因此她從來沒有擔心他會真的那麼做。在八月的那個夏天夜晚,她才明白她錯了。那夜過後,她就開始酗酒。為了麻醉自己。為了遺忘。她最痛苦的一天,也是後來她被安置到聖法倫霍普的導火線,在那四年後,當她失去了工作、所有的人脈關係以及一大半的求生意志,克里斯提昂在廚房餐桌上對她說他要離婚。他愛上一個年輕貌美又聰明的女子,一個女學生,而且不像她這樣自暴自棄。而他當然也要帶走妮可拉,他們正值荳蔻年華的女兒,怎麼也不能留在一個如蕩婦一般對每個男人投懷送抱的墮落的女酒鬼身邊。
她淚如雨下,雙手抖個不停,這次很例外地不是因為血液酒精濃度下降的關係。「你不能這麼做,」她很想對他叫嚷說:「你不可以把我當作破腳墊一樣扔掉,你不可以奪走我的女兒。」可是她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只能發出痛苦的荷荷聲。
克里斯提昂一臉鄙夷地搖搖頭,眼神裡充滿輕蔑。他知道她還沒開始打仗就先輸了。他是個律師,而她只是個精神崩潰的女酒鬼。光是他拍攝的影片,就足以讓每個自由派的家事法庭法官都不得不站在男方這邊,她在影片裡和每個朋友、熟人以及陌生男子雲雨巫山。在影片裡,約翰娜是唯一沒有戴臉罩的人。
妮可拉和克里斯提昂搬出去的兩個月後,在她女兒無聲無息地失蹤之後,她第一次試圖自殺。在第三次自殺失敗之後,正當警方在搜尋妮可拉的時候,她在大白天被送進療養院。
她就這樣在這裡待了半年,由於碰不到酒,至少讓她的身體逐漸康復。她的牙齒都壞了,肝功能指數一直嚴重超標,但是解尿的疼痛一天比一天好轉。戒斷的盜汗情況也不再那麼嚴重,而自從她可以讓人用梳子輕輕梳頭,對外界也不再有那麼多戒心了。可是她仍然處於精神分裂的狀態,一直覺得自己是個人渣。
一個穿著晨袍的人渣,在療養院的花園裡踽踽獨行。
長椅上的老人總是很和善地向她頷首致意,作勢要她坐到他身旁,似乎一點也不在乎她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由於在療養院待得夠久了,約翰娜幾乎覺得自己成了這裡的固定資產。
她至少知道她大多數的「獄友」的名字,可是她至今一直搞不清楚這個坐在她身旁的男子為什麼被送進療養院。她從來沒有在療養院大樓裡遇見他,不管是在走廊或餐廳點餐區,都不曾不期而遇。可是每次她到花園伸展筋骨時,這個看起來很古板的男子總是坐在那裡。腰桿挺得筆直,稀疏的頭髮剪得很體面,髮線就像他的灰呢褲上的折線一樣涇渭分明,他掰了些麵包屑,分給在他腳下活蹦亂跳的鴿子、山雀、椋鳥和麻雀。他不時對約翰娜投以狡黠的微笑,嘴巴裡塞著一塊麵包屑。在他們沉默的交流片刻,她的視線幾乎沒離開過他的眼睛,那雙眼睛看起來比男子自己還要年輕、警醒而且莫測高深,她猜不出他的年紀,大概有五十開外了吧。
今天,他們一如往常地默默比肩而坐,傾聽遠方城市高速公路隆隆車聲,過了一會兒,她主動向他攀談。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當然。」
他的聲音聽起來很友善,讓她想起過世很久的數學家教,一個題目就算解釋了二十遍,他仍舊沒有失去耐心。
「你為什麼進療養院?」
他轉過身,以不尋常的眼神直視著她。「為了妳。」
她哈哈大笑,以為他會馬上收回他的話,說他只是在開玩笑而已。
但是這個男子的神情一直很嚴肅。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不是病人。我是個訪客。」
「那麼你要探望……」她遲疑了一下。「你要探望我嗎?」
「的確是。」
「為什麼?」
「我要對妳證明一件事。」
「什麼事?」
「證明生命到現在為止一直對你很好。」
這個男子的聲音突然再也不那麼親切。他看起來也不再像是個提早退休的人,因為無所事事而每天在花園餵鴿子。
「妳仔細瞧瞧這個。」
他遞給她一張照片。約翰娜看到一張年輕女孩的高解析度照片,她的瞳孔突然變大。
驚駭萬分的她愣了好幾秒鐘,才明白整張照片有多麼殘忍暴力,因為約翰娜腦袋裡的防衛機制拒絕辨認這個不可思議的畫面。
「這張照片妳可以留著,」這個老男人把拍立得照片塞到她手裡。「妳就把它當作是在懲罰妳自己所犯的罪吧。」
他起身整理他的夾克,檢查一下他的灰呢褲的拉鍊。
「對不起,我得回去工作了。如妳所看到的,我和妳女兒的事還沒有完了。」
接著,在約翰娜崩潰尖叫之前,這位訪客一溜煙地走開了。他的步伐輕快、靈活而迅捷。就像一個怡然自得的男子,對自己和他的世界都很滿意。***五個月後的現在
亞歷山大‧佐巴赫(我)
不願面對的真相。最嚇人的恐怖片往往有個無關緊要的名字。很久以前,在我的生活還像個人樣時,我曾經訪問過飽受精神創傷的婦女。雖然她的不幸遭遇──她的不願面對的真相──已經是多年以前的事,她仍然不時會有恐慌發作的現象。拉拉‧懷策曼以前並沒有幽閉恐懼症的問題,可是後來就連在我們報社偌大的辦公室裡,她都會感到呼吸困難。在兩次失敗的訪談開場白之後(我們一直在她難以想像的傷痛的第一個問題上打轉),我們只好中斷訪問,到另一個比較寬敞的地方往下談。就這樣,我在動物園裡的烈日下傾聽一個年輕婦女如夢魘般的故事。「那只是小腹的一個囊腫而已,」她輕聲說,後來我每次想起她在我的錄音帶上的沙啞聲音,總會忍不住打個哆嗦。拉拉的聲音和她的外表搭配得天衣無縫,宛如一個導演為這副孱弱的身體仔細挑選過的。那個創傷使她的心靈千瘡百孔,細看下甚至認不出來那顆心。拉拉太瘦了,皮膚像羊皮紙一樣蒼白,如果她站在光亮處,陽光或許會直接穿透她的身體傾瀉下來。
「我以前不知道世上會有這種事,」她搖搖頭說,宛如至今仍然難以置信。這種例行性的手術,她的外科醫師已經開過幾千次了,她剛開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併發症,至今都和囊腫的摘除無關。
一切就如以前無數次手術一樣進行著。只不過有個差別:拉拉‧懷策曼並沒有失去知覺。至今沒有人知道,麻醉藥的劑量是不是弄錯了,或者是她的體質異常,麻醉藥對她的身體起不了作用。藥劑只是癱瘓她的活動能力。拉拉一直是清醒的,卻苦於說不出話來。她沒辦法告訴別人說她可以感覺到一切:劃開她的肚皮的手術刀,伸進她身體裡撐開切口的不鏽鋼撐開鉗。不到一個鐘頭,傷口就縫起來了。她很想對醫師和護士們咆哮說她痛得不得了,而他們卻在手術中聊起現在在柏林很難找到一家沒有外國孩子的幼稚園。算了。沒有人聽得到她內心的吶喊,至今仍然她心裡震耳欲聾的吶喊。
不願面對的真相。在手術中意識清醒、完全有痛覺、卻說不出話來的病人。
在統計上,這是相當罕見的病例,在小數點後面要加好個零才能表示。只有○.○三%。機率比在大太陽底下遭到雷擊還要低。這個說法至少讓人安心一點,只要人們沒想過還是有萬分之三的可能。在滿座的奧林匹克運動場裡會有三十個人。是很罕見,但不是那麼難以置信。自從那個集眼者,那個殺死我的妻子、綁架我的兒子的男人,把我玩弄在他的股掌之間,我才真正體會到拉拉‧懷策曼當時在手術檯上的感覺。她活生生的被開腸剖肚,而施打的止痛藥的作用只不過像是貼在腰上的痠痛貼布而已。
我們可以試圖以遮掩致命風險的統計數字來麻醉自己。總要有人為那萬分之三的悲劇事件負責吧。而有時候該負責的人就是他自己。他會親眼看到,有如在豔陽天裡遭到雷擊一般,正如在十二月寒風刺骨的這一天,我總算找到集眼者綁架我兒子的藏匿處。他要我在四十五小時又七分鐘內找到尤利安。如果我來晚了,就算是晚個幾分鐘,尤利安也會在他的地牢裡窒息而死。這就是遊戲規則。既變態又不可改變。當我打開隔板踏入黑暗深處,才明白究竟是什麼東西在等著我。
最後期限終了後的七分鐘。
幾個月前,他一直在玩致命的捉迷藏,現在「集眼者」的身分真相大白:法蘭克‧拉曼,二十三歲,柏林一家大報的實習生,承認一共犯下四個女性和三個孩童的凶殘謀殺案。
拉曼的犯案過程既令人作嘔又天衣無縫:他先是殺死母親,然後綁架孩子,對父親下了四十五小時又七分鐘的最後通牒,讓他找出孩子的藏匿處。期限一到,受害者就會在被禁錮的地下室裡窒息而死。集眼者之所以有如此駭人的名字,是因為每個被發現的孩子屍體,他們的左眼都不見了。
犯罪心理學者認為,集眼者的病態行為應該是童年經驗所導致的。初步調查顯示,拉曼的成長環境相當惡劣。母親拋棄家庭,父親覺得他的孩子們是個累贅,尤其是拉曼的弟弟,他的左眼因為得了癌症而失明。
有一天,兩兄弟躲到一具廢棄的冷凍櫃裡,他們相信父親一定憂心如焚,很快就會來找他們。可是他們心中盼望的「愛的證明」落空了。他們的父親一無所知,跑去酒館喝了一整晚,兩兄弟沒辦法憑著自己的力氣從冷凍櫃脫身。湊巧有個林務員發現了他們,可是為時已晚。在受困了四十五小時又七分鐘之後,法蘭克‧拉曼的弟弟已經死了。
心理學家認為這個精神創傷就是他後來的犯案動機。拉曼寫了一封信給報社主編坦承犯行:「當然,我承認,我(編者按:還有我的犯行)總是很病態地根據我和我弟弟當時受困的環境來設定遊戲條件。一個對我們而言已經死去的母親,因此我一開始就必須把她驅逐出場。一個不關心孩子的父親。一個藏匿處,裡頭的空氣只能維持四十五小時又七分鐘,以及一具屍體,和我弟弟一樣缺了左眼。」
只不過,由於警政記者亞歷山大‧佐巴赫的介入,在最後一秒鐘阻止了集眼者第四回合的遊戲。多虧佐巴赫鍥而不捨的調查,警方終於發現凶手藏匿雙胞胎兄妹的地點。但是這位記者必須為他們的救援行動付出慘重的代價。當他從電梯井裡救出兩兄妹時,法蘭克‧拉曼已經找到新的受害者:佐巴赫的兒子尤利安。拉曼殺死了尤利安的母親妮琪,然後綁架了尤利安。
從此以後,拉曼就銷聲匿跡。亞歷山大‧佐巴赫如果還想看見他的兒子活著回來,就必須和再一次的最後通牒作戰,而時間正在一分一秒地流逝……「若有別害,就要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以烙還烙,以傷還傷,以打還打。」——《舊約‧出埃及記》21:23-25
「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新約‧馬太福音》5:38-39
***約翰娜.史卓姆
是日溫暖多雲,氣溫十三度,九月颯爽的微風習習。約翰娜‧史卓姆很喜歡這樣的天氣。正是尋死的大好時節。
她坐在花園的長椅上,身旁的男人似乎感覺到她不為人知的想法,即使他們今天還沒有說上一句話。他本來就不是很多話的人。在位於漢堡的醫院四周圍著高牆的花園裡,每天一次,午餐後兩個鐘頭,她可以「伸展一下筋骨」,誠如護士長所說的。在這條坑坑洼洼的小路上散步時得非常小心,它蜿蜒穿過精神療養院的老樹林。昨天那個老維什尼夫斯基才被覆滿秋天落葉的樹根絆倒,撞傷了臀部。「我倒寧願他撞破頭,」她聽到這位失智症病患的看護嘲笑他說:「下次他也這麼不小心就好了。」
就像聖法倫霍普療養院(Sankt Pfarrenhopp)(當地人都取其諧音叫它作「頭上中箭療養院」)(Pfeil im Kopp)裡的每個病人一樣,她也覺得這裡不是自己該待的地方。倒不是因為她自以為沒病,天曉得,她根本就有病,而是因為她對於治療這種事嗤之以鼻。如果面對的只是先後奪走她的尊嚴和健康的酗酒問題,說不定哪一天她甚至可以振作起來,和群魔交戰,用加油站商店利樂包裝的劣酒把牠們淹死。如果她有專業協助的話,當她的丈夫又想要將她綁起來「調教」的時候,或許她甚至可以反擊。在他們的關係剛開始時,她還把它當成一種遊戲,如果那可以讓伴侶開心,或許是尚可接受的事。
她在床上被罵成「三個洞的母馬」、蕩婦、思春的臭婊子,儘管一開始她必須承認很難為情,但是當他對她越來越粗暴時,她卻沒辦法否認自己的確有種莫名的興奮感。打屁股、掐脖子,感覺還不錯。她看到這些動作讓他很興奮,自己也跟著想入非非;她也知道,如果她拒絕在他射精前跪在他面前,他會大發雷霆,而她就有罪受了。他就是想要滿足從色情片學來的幻想。反正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在她意識深處的儲藏室一隅,她隱約明白一切都已經太遲了。她錯過了生命道路上的最後一個岔口,一個可以挽救這一切的岔口,在她完全失控之前。她任憑他百般作賤她,而沒有任何抗議。如果在結婚這麼多年之後,突然對克里斯提昂承認說,她其實不喜歡他的某些嗜好,那會使他發現她是個騙子,因而覺得很受傷(這是想當然耳的事,她心想)。於是她始終沉默以對,欺騙自己說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在八月一個悶熱的夏日,這個希望終於破滅。在假日大採購之後,她滿頭大汗地回家。女兒妮可拉跟著班上同學到波羅的海旅行了,她原本打算在這個寧靜的週五夜晚享受她的披薩和影片(米基‧洛克主演的《天使心》,她丈夫還不知道有這張光碟,是她在大賣場平台花三歐元買的),可是回家一看到客廳裡的不速之客,頓時大失所望。克里斯提昂和法律事務所的兩個同事大剌剌躺在沙發上。他們顯然已經喝掉幾瓶酒。約翰娜沒打算要親他當作見面禮,克里斯提昂老早就不喜歡來這套了。她每次回家時,他總是隨便拍一下她的屁股,後來則是輕輕捏一下她的乳頭。可是今天他做得太過火了。
她再也不記得那天晚上發生的所有事,其中許多事都安然無恙地鎖在她的下意識裡,然而光是留在記憶裡的,就足以讓她至今仍然時常從夢中驚叫醒來。
克里斯提昂站起來,毫無預警地摑了她一巴掌。
「妳讓我們等太久了,妳這頭死母豬,」他裝出責備的語氣,然後轉向他的朋友說:「你們說我們該怎麼處罰我的這個蕩婦?」
約翰娜勉強扮了個鬼臉,以微笑若無其事地表示她的丈夫突如其來的暴力只是個無傷大雅的玩笑。他的律師朋友(他們兩個都西裝筆挺,繫著領帶,胸前口袋塞著方巾;兩個人都戴著婚戒)曖昧地笑了笑。這會兒她才注意到螢幕上正以靜音模式播放著愛情動作片。一個一絲不掛的女性頭上套著皮罩。
「你們想要來點什麼嗎?」約翰娜顫聲問道,直到今天,她仍然不確定這個舉動到底是不是個錯誤。克里斯提昂是不是認為她同意在他的朋友面前表演角色扮演的遊戲。
演出。克里斯提昂把它當成家暴的同義詞。他總是在床上對她輕聲談到他的暴力幻想:他想要在樹林裡把她剝光衣服綁在大樹上,讓她像獵物一樣任由路過的慢跑者蹂躪。他的幻想有時候很可笑(有一次他甚至要她到一家妓院當妓女),因此她從來沒有擔心他會真的那麼做。在八月的那個夏天夜晚,她才明白她錯了。那夜過後,她就開始酗酒。為了麻醉自己。為了遺忘。她最痛苦的一天,也是後來她被安置到聖法倫霍普的導火線,在那四年後,當她失去了工作、所有的人脈關係以及一大半的求生意志,克里斯提昂在廚房餐桌上對她說他要離婚。他愛上一個年輕貌美又聰明的女子,一個女學生,而且不像她這樣自暴自棄。而他當然也要帶走妮可拉,他們正值荳蔻年華的女兒,怎麼也不能留在一個如蕩婦一般對每個男人投懷送抱的墮落的女酒鬼身邊。
她淚如雨下,雙手抖個不停,這次很例外地不是因為血液酒精濃度下降的關係。「你不能這麼做,」她很想對他叫嚷說:「你不可以把我當作破腳墊一樣扔掉,你不可以奪走我的女兒。」可是她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只能發出痛苦的荷荷聲。
克里斯提昂一臉鄙夷地搖搖頭,眼神裡充滿輕蔑。他知道她還沒開始打仗就先輸了。他是個律師,而她只是個精神崩潰的女酒鬼。光是他拍攝的影片,就足以讓每個自由派的家事法庭法官都不得不站在男方這邊,她在影片裡和每個朋友、熟人以及陌生男子雲雨巫山。在影片裡,約翰娜是唯一沒有戴臉罩的人。
妮可拉和克里斯提昂搬出去的兩個月後,在她女兒無聲無息地失蹤之後,她第一次試圖自殺。在第三次自殺失敗之後,正當警方在搜尋妮可拉的時候,她在大白天被送進療養院。
她就這樣在這裡待了半年,由於碰不到酒,至少讓她的身體逐漸康復。她的牙齒都壞了,肝功能指數一直嚴重超標,但是解尿的疼痛一天比一天好轉。戒斷的盜汗情況也不再那麼嚴重,而自從她可以讓人用梳子輕輕梳頭,對外界也不再有那麼多戒心了。可是她仍然處於精神分裂的狀態,一直覺得自己是個人渣。
一個穿著晨袍的人渣,在療養院的花園裡踽踽獨行。
長椅上的老人總是很和善地向她頷首致意,作勢要她坐到他身旁,似乎一點也不在乎她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由於在療養院待得夠久了,約翰娜幾乎覺得自己成了這裡的固定資產。
她至少知道她大多數的「獄友」的名字,可是她至今一直搞不清楚這個坐在她身旁的男子為什麼被送進療養院。她從來沒有在療養院大樓裡遇見他,不管是在走廊或餐廳點餐區,都不曾不期而遇。可是每次她到花園伸展筋骨時,這個看起來很古板的男子總是坐在那裡。腰桿挺得筆直,稀疏的頭髮剪得很體面,髮線就像他的灰呢褲上的折線一樣涇渭分明,他掰了些麵包屑,分給在他腳下活蹦亂跳的鴿子、山雀、椋鳥和麻雀。他不時對約翰娜投以狡黠的微笑,嘴巴裡塞著一塊麵包屑。在他們沉默的交流片刻,她的視線幾乎沒離開過他的眼睛,那雙眼睛看起來比男子自己還要年輕、警醒而且莫測高深,她猜不出他的年紀,大概有五十開外了吧。
今天,他們一如往常地默默比肩而坐,傾聽遠方城市高速公路隆隆車聲,過了一會兒,她主動向他攀談。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當然。」
他的聲音聽起來很友善,讓她想起過世很久的數學家教,一個題目就算解釋了二十遍,他仍舊沒有失去耐心。
「你為什麼進療養院?」
他轉過身,以不尋常的眼神直視著她。「為了妳。」
她哈哈大笑,以為他會馬上收回他的話,說他只是在開玩笑而已。
但是這個男子的神情一直很嚴肅。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不是病人。我是個訪客。」
「那麼你要探望……」她遲疑了一下。「你要探望我嗎?」
「的確是。」
「為什麼?」
「我要對妳證明一件事。」
「什麼事?」
「證明生命到現在為止一直對你很好。」
這個男子的聲音突然再也不那麼親切。他看起來也不再像是個提早退休的人,因為無所事事而每天在花園餵鴿子。
「妳仔細瞧瞧這個。」
他遞給她一張照片。約翰娜看到一張年輕女孩的高解析度照片,她的瞳孔突然變大。
驚駭萬分的她愣了好幾秒鐘,才明白整張照片有多麼殘忍暴力,因為約翰娜腦袋裡的防衛機制拒絕辨認這個不可思議的畫面。
「這張照片妳可以留著,」這個老男人把拍立得照片塞到她手裡。「妳就把它當作是在懲罰妳自己所犯的罪吧。」
他起身整理他的夾克,檢查一下他的灰呢褲的拉鍊。
「對不起,我得回去工作了。如妳所看到的,我和妳女兒的事還沒有完了。」
接著,在約翰娜崩潰尖叫之前,這位訪客一溜煙地走開了。他的步伐輕快、靈活而迅捷。就像一個怡然自得的男子,對自己和他的世界都很滿意。***五個月後的現在
亞歷山大‧佐巴赫(我)
不願面對的真相。最嚇人的恐怖片往往有個無關緊要的名字。很久以前,在我的生活還像個人樣時,我曾經訪問過飽受精神創傷的婦女。雖然她的不幸遭遇──她的不願面對的真相──已經是多年以前的事,她仍然不時會有恐慌發作的現象。拉拉‧懷策曼以前並沒有幽閉恐懼症的問題,可是後來就連在我們報社偌大的辦公室裡,她都會感到呼吸困難。在兩次失敗的訪談開場白之後(我們一直在她難以想像的傷痛的第一個問題上打轉),我們只好中斷訪問,到另一個比較寬敞的地方往下談。就這樣,我在動物園裡的烈日下傾聽一個年輕婦女如夢魘般的故事。「那只是小腹的一個囊腫而已,」她輕聲說,後來我每次想起她在我的錄音帶上的沙啞聲音,總會忍不住打個哆嗦。拉拉的聲音和她的外表搭配得天衣無縫,宛如一個導演為這副孱弱的身體仔細挑選過的。那個創傷使她的心靈千瘡百孔,細看下甚至認不出來那顆心。拉拉太瘦了,皮膚像羊皮紙一樣蒼白,如果她站在光亮處,陽光或許會直接穿透她的身體傾瀉下來。
「我以前不知道世上會有這種事,」她搖搖頭說,宛如至今仍然難以置信。這種例行性的手術,她的外科醫師已經開過幾千次了,她剛開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併發症,至今都和囊腫的摘除無關。
一切就如以前無數次手術一樣進行著。只不過有個差別:拉拉‧懷策曼並沒有失去知覺。至今沒有人知道,麻醉藥的劑量是不是弄錯了,或者是她的體質異常,麻醉藥對她的身體起不了作用。藥劑只是癱瘓她的活動能力。拉拉一直是清醒的,卻苦於說不出話來。她沒辦法告訴別人說她可以感覺到一切:劃開她的肚皮的手術刀,伸進她身體裡撐開切口的不鏽鋼撐開鉗。不到一個鐘頭,傷口就縫起來了。她很想對醫師和護士們咆哮說她痛得不得了,而他們卻在手術中聊起現在在柏林很難找到一家沒有外國孩子的幼稚園。算了。沒有人聽得到她內心的吶喊,至今仍然她心裡震耳欲聾的吶喊。
不願面對的真相。在手術中意識清醒、完全有痛覺、卻說不出話來的病人。
在統計上,這是相當罕見的病例,在小數點後面要加好個零才能表示。只有○.○三%。機率比在大太陽底下遭到雷擊還要低。這個說法至少讓人安心一點,只要人們沒想過還是有萬分之三的可能。在滿座的奧林匹克運動場裡會有三十個人。是很罕見,但不是那麼難以置信。自從那個集眼者,那個殺死我的妻子、綁架我的兒子的男人,把我玩弄在他的股掌之間,我才真正體會到拉拉‧懷策曼當時在手術檯上的感覺。她活生生的被開腸剖肚,而施打的止痛藥的作用只不過像是貼在腰上的痠痛貼布而已。
我們可以試圖以遮掩致命風險的統計數字來麻醉自己。總要有人為那萬分之三的悲劇事件負責吧。而有時候該負責的人就是他自己。他會親眼看到,有如在豔陽天裡遭到雷擊一般,正如在十二月寒風刺骨的這一天,我總算找到集眼者綁架我兒子的藏匿處。他要我在四十五小時又七分鐘內找到尤利安。如果我來晚了,就算是晚個幾分鐘,尤利安也會在他的地牢裡窒息而死。這就是遊戲規則。既變態又不可改變。當我打開隔板踏入黑暗深處,才明白究竟是什麼東西在等著我。
最後期限終了後的七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