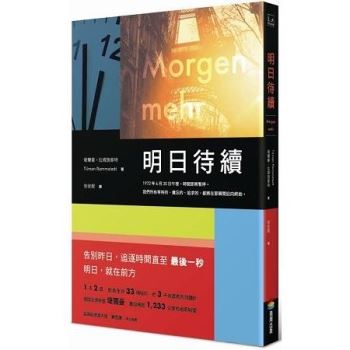1 因故尚未開始
我已經知道所有的事。我知道一切將如何演變。儘管如此我仍不免憂慮,因為有憂慮,就會有警惕。我會在距離地面近三百公尺的高處來到這個世界,會在一個不太重要的體育項目中得到銀牌,會在有史以來最長的車陣中遇到真愛。我知道我最要好的朋友是如何地背叛我,也知道在監獄中過夜,和在夏天裡雙腳被打上石膏的滋味。我知道今年耶誕節,當女孩們第一次送自己購買的禮物給我時,眼裡流露出的興奮與自豪。我知道大海其實沒什麼療癒的功能,也知道當人們輕撫著不再陌生的陌生肌膚時,是何感受。我知道那次決定性的爭吵,還有在地鐵裡第一次聽見有人說我老。我知道四十四年後的重逢,也知道倘若能縱身投入湖中,一切都會變得更加簡單。我知道自己是如何地在兩個謊言中做了錯誤的抉擇,知道拳頭是如何地落在身上。我知道那份疲憊,以及那些年的流逝。我知道有些事難如登天,也知道耐心等待不見得會有結果;當然我也知道自己總是忘記這一點。我知道自己是如何失掉了純潔──我指的不是第一次的性經驗,雖然我也確實有過,而是人們一旦失去,就不會再感到全然幸福的純潔。在加爾各答,我見過大象溫和的眼神,也熟悉所有的鈴聲。在暴風雪中,最後一次言不由衷地說「我愛你」。我以為可以見到上帝,但事實並非如此。我知道車子翻了一圈、兩圈、三圈,甚至更多圈;我知道「現在已經玩完了」,知道這應該是真的,而且可能就在幾天後,在這間淺黃色的、可以看見窗外葡萄園的鄉村醫院病房中結束生命,而這一切也沒什麼稀奇。那將是個星期四的午後,電視機是開著的──其後我就不知道了。我終於不再什麼都知道了。
這將是個充實的人生,至少我是這麼認為。我能原諒自己時而俊美,時而有點太過蒼白。我將對很多事物習以為常,只是在其中少有好事。我很少能有始有終。我身後或許不會留下什麼值得讚揚的,但或許這也沒什麼重要。我將經歷一切;對於這點,我尤其知道得清楚分明。
我願意追憶,追憶那所有屬於我的、適合我的生命歷程。我也願意述說一切,但不是在這裡,而是以後,很久以後,在另外的故事裡──因為現在還有一個小問題尚待解決,那就是:我還未出生。2 我來稍作解釋
如果一個人還未出生,那麼說真的,就算他已經知道了一切,其實也幫助不大。對局外人而言,「知道」好像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所有事物都是那麼一目了然、那麼感人肺腑得毫無意義,沒有什麼是真的與他個人相關,也沒有什麼會直接在他的身上發生。這種境遇是愉悅的,大家都能很快地適應,甚至認為最好還是不要參與這場人生,而是繼續定睛觀看,就像是觀賞水族箱、或是盯著那種可以拿起來使勁搖晃的玻璃雪花球般──雪花球在搖晃後的數秒間風雪交加、景象模糊,就在這幾秒鐘裡,人們可以期待驚奇;只不過在風雪平息後,其實一切仍然如常。
對雪花球內部的世界而言,「一切如常」肯定是個好消息;這表示風雪並未造成無法磨滅的損害,一切都毫髮無傷。對雪花球內部的世界而言,「一切如常」總像是個小小的奇蹟;這又一次的倖存,伴隨著驚嚇、或許還略帶點暈眩,但也幸運得讓人難以置信。
因此,我還是決定要參與其中。我也想要來到這個大千世界,也想要出生。因此,我也希望能被搖晃一次,在鋪天蓋地的大雪中看不見自己的雙手。我希望藉由驚嚇暫時忘掉所有的事,尤其是外人認為雪花球內風暴是無害的看法。我想再一次毫髮無傷地倖免於難。等風雪平息、最後幾片飄搖的雪花落定,一切就能和以往一樣,只不過會更加美麗;一切就能和以往一樣靜謐,只不過會更加安詳。而我的狀態,也肯定會是前所未有地好。我也想體驗一次那種千鈞一髮、劫後餘生的幸運。
但遺憾的是,通往雪花球內部的路途,可一點都不簡單。並不是只要我再次翻轉身體、謹慎就位,然後一切就可以開始;在第一聲啼哭、第一陣沉默後,就是長長的其餘過程。既沒人喜悅、也沒人惶恐,或是以其他情緒盼望著我的到來;其實,根本就沒有人盼望我的到來。我既不是那看上去彷彿火山地貌的超音波照片上,有著起伏律動的小點,也沒使我媽的腹部高高隆起;我沒有勇猛地踢蹬我媽的肚皮,也沒有因為缺乏可從事的活動就撥弄臍帶,以學習適應寂寥;我甚至根本還沒引發我媽晨間的孕吐。我只想順其自然、聽天由命地生長發育。之後,我應該會有九個月的時間來為一切做足準備:比方說,我可以慢慢地思考出生後要說的第一個詞是什麼,這樣才不會在關鍵時刻只是一再地發出「麻麻」或「拔」之類的音節。我不會只滿足於此;我的標準可是很高的。但我現在沒空慢慢思考;我必須時刻全神貫注。必要時,我還得出手幫忙,設法維持常規;或者更重要的是,維持其中的不規律。因為,像我的出生這般錯亂的事,或許無法完全依循常規。目前我的父母對我仍舊一無所知,他們對彼此也都毫無概念──他們甚至從未謀面。無論如何,這個現況得要立即改變。
但我就只有一天的時間可以用來改變;只有一九七二年六月三十日這一天,就是今天。這是我最後的機會。遲了,就再也趕不上出生的時機了。您一定能夠想像,我是不願錯失這個機會的。
糟糕的是──就是現在,這個當下,我媽就快要懷上不是我爸的孩子了。而遠在千里之外的我爸,就快被人用水泥封住雙腳、扔進美因河裡去了。
我已經知道所有的事。我知道一切將如何演變。儘管如此我仍不免憂慮,因為有憂慮,就會有警惕。我會在距離地面近三百公尺的高處來到這個世界,會在一個不太重要的體育項目中得到銀牌,會在有史以來最長的車陣中遇到真愛。我知道我最要好的朋友是如何地背叛我,也知道在監獄中過夜,和在夏天裡雙腳被打上石膏的滋味。我知道今年耶誕節,當女孩們第一次送自己購買的禮物給我時,眼裡流露出的興奮與自豪。我知道大海其實沒什麼療癒的功能,也知道當人們輕撫著不再陌生的陌生肌膚時,是何感受。我知道那次決定性的爭吵,還有在地鐵裡第一次聽見有人說我老。我知道四十四年後的重逢,也知道倘若能縱身投入湖中,一切都會變得更加簡單。我知道自己是如何地在兩個謊言中做了錯誤的抉擇,知道拳頭是如何地落在身上。我知道那份疲憊,以及那些年的流逝。我知道有些事難如登天,也知道耐心等待不見得會有結果;當然我也知道自己總是忘記這一點。我知道自己是如何失掉了純潔──我指的不是第一次的性經驗,雖然我也確實有過,而是人們一旦失去,就不會再感到全然幸福的純潔。在加爾各答,我見過大象溫和的眼神,也熟悉所有的鈴聲。在暴風雪中,最後一次言不由衷地說「我愛你」。我以為可以見到上帝,但事實並非如此。我知道車子翻了一圈、兩圈、三圈,甚至更多圈;我知道「現在已經玩完了」,知道這應該是真的,而且可能就在幾天後,在這間淺黃色的、可以看見窗外葡萄園的鄉村醫院病房中結束生命,而這一切也沒什麼稀奇。那將是個星期四的午後,電視機是開著的──其後我就不知道了。我終於不再什麼都知道了。
這將是個充實的人生,至少我是這麼認為。我能原諒自己時而俊美,時而有點太過蒼白。我將對很多事物習以為常,只是在其中少有好事。我很少能有始有終。我身後或許不會留下什麼值得讚揚的,但或許這也沒什麼重要。我將經歷一切;對於這點,我尤其知道得清楚分明。
我願意追憶,追憶那所有屬於我的、適合我的生命歷程。我也願意述說一切,但不是在這裡,而是以後,很久以後,在另外的故事裡──因為現在還有一個小問題尚待解決,那就是:我還未出生。2 我來稍作解釋
如果一個人還未出生,那麼說真的,就算他已經知道了一切,其實也幫助不大。對局外人而言,「知道」好像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所有事物都是那麼一目了然、那麼感人肺腑得毫無意義,沒有什麼是真的與他個人相關,也沒有什麼會直接在他的身上發生。這種境遇是愉悅的,大家都能很快地適應,甚至認為最好還是不要參與這場人生,而是繼續定睛觀看,就像是觀賞水族箱、或是盯著那種可以拿起來使勁搖晃的玻璃雪花球般──雪花球在搖晃後的數秒間風雪交加、景象模糊,就在這幾秒鐘裡,人們可以期待驚奇;只不過在風雪平息後,其實一切仍然如常。
對雪花球內部的世界而言,「一切如常」肯定是個好消息;這表示風雪並未造成無法磨滅的損害,一切都毫髮無傷。對雪花球內部的世界而言,「一切如常」總像是個小小的奇蹟;這又一次的倖存,伴隨著驚嚇、或許還略帶點暈眩,但也幸運得讓人難以置信。
因此,我還是決定要參與其中。我也想要來到這個大千世界,也想要出生。因此,我也希望能被搖晃一次,在鋪天蓋地的大雪中看不見自己的雙手。我希望藉由驚嚇暫時忘掉所有的事,尤其是外人認為雪花球內風暴是無害的看法。我想再一次毫髮無傷地倖免於難。等風雪平息、最後幾片飄搖的雪花落定,一切就能和以往一樣,只不過會更加美麗;一切就能和以往一樣靜謐,只不過會更加安詳。而我的狀態,也肯定會是前所未有地好。我也想體驗一次那種千鈞一髮、劫後餘生的幸運。
但遺憾的是,通往雪花球內部的路途,可一點都不簡單。並不是只要我再次翻轉身體、謹慎就位,然後一切就可以開始;在第一聲啼哭、第一陣沉默後,就是長長的其餘過程。既沒人喜悅、也沒人惶恐,或是以其他情緒盼望著我的到來;其實,根本就沒有人盼望我的到來。我既不是那看上去彷彿火山地貌的超音波照片上,有著起伏律動的小點,也沒使我媽的腹部高高隆起;我沒有勇猛地踢蹬我媽的肚皮,也沒有因為缺乏可從事的活動就撥弄臍帶,以學習適應寂寥;我甚至根本還沒引發我媽晨間的孕吐。我只想順其自然、聽天由命地生長發育。之後,我應該會有九個月的時間來為一切做足準備:比方說,我可以慢慢地思考出生後要說的第一個詞是什麼,這樣才不會在關鍵時刻只是一再地發出「麻麻」或「拔」之類的音節。我不會只滿足於此;我的標準可是很高的。但我現在沒空慢慢思考;我必須時刻全神貫注。必要時,我還得出手幫忙,設法維持常規;或者更重要的是,維持其中的不規律。因為,像我的出生這般錯亂的事,或許無法完全依循常規。目前我的父母對我仍舊一無所知,他們對彼此也都毫無概念──他們甚至從未謀面。無論如何,這個現況得要立即改變。
但我就只有一天的時間可以用來改變;只有一九七二年六月三十日這一天,就是今天。這是我最後的機會。遲了,就再也趕不上出生的時機了。您一定能夠想像,我是不願錯失這個機會的。
糟糕的是──就是現在,這個當下,我媽就快要懷上不是我爸的孩子了。而遠在千里之外的我爸,就快被人用水泥封住雙腳、扔進美因河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