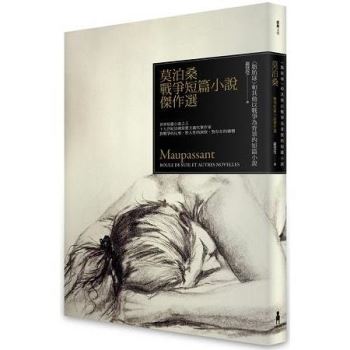脂肪球(Boule de suif)
連續好些天以來,一小撮一小群的殘兵不斷穿過城裡,稱不上隊伍,只能算潰散的烏合之眾。他們的鬍子又長又髒,軍服破爛襤褸,無精打采地走著,沒有軍旗,也不成隊伍。每個都一副殘兵敗將的樣子,疲憊不堪,無法思考也毫無想法,只是依著習慣往前走,若一停下來就會疲倦倒地。他們大多是接到動員令徵招來的民兵,溫和的百姓,平日安享收益的人,現在卻扛著槍枝,身體彎曲成兩半;還有一些是國民防護隊,他們警覺性強,膽子小,一腔熱血,煽動一下就全力攻擊,受到挫敗也就立刻潰逃。當中也有幾個是真正職業軍人,一場激戰中某一師解體的殘兵、悽慘的砲兵和潰散的各類步兵排在一起,不時還可看到戴著閃亮的頭盔的龍騎兵,拖著沉重的腳步,跟在步履稍顯靈活的前線作戰步兵後面。
一團一團的游擊隊也帶著土匪的神氣走過,他們各自打著英雄式的名號:「敗仗復仇者」、「墓中公民」、「死亡分享者」。
他們的首領,戰爭之前做的是布匹或種子的買賣、賣羊脂或肥皂的生意人,因為時勢而進了游擊隊;因為他們有錢、或是鬍子比較長,不分究裡地獲得軍官階級,配上槍,穿上法蘭絨制服,戴上軍階。他們扯著喉嚨討論作戰計畫,自吹自擂自己一肩扛起奄奄一息的法國,但是他們其實有時候還得提防自己的手下,那些傢伙都是十惡不赦的壞蛋,猖狂大膽、無法無天的盜匪。
普魯士軍隊很快要佔領盧昂了,大家都這麼說。
兩個月以來,國民自衛軍在城外附近樹林裡謹慎小心地偵查,草木皆兵,還幾次開槍誤傷了自己的士兵,光一隻兔子出沒草叢,就像面臨大敵似的。他們都各自卸甲歸家,槍枝武器、制服、本來方圓三里公路兩旁保衛、退敵的裝置也突然消失了。
最後一些法國士兵終於渡過塞納河,經過聖歇維(Saint-Sever)和阿夏堡(Bourg-Achard),抵達歐德梅橋(Pont-Audemer);走在隊伍最後面的將軍,萬念俱灰,拿手下這一群衣衫襤褸的殘兵不知如何是好,連自己也因一向以驍勇善戰、無敵不克出名的民族,這次遭到毀滅性的瓦解崩潰而慌亂不已,拖著腳步,旁邊跟著兩個副官。
市區籠罩著一種深沉的平靜和一種駭然而靜肅的等待。許多大腹便便的有錢人,被生意消磨了鬥志,擔憂地等待著勝利者到來,想起廚房裡的烤肉鐵插和切肉大刀若被誤以為是武器,不禁嚇得渾身發抖。生活像是停頓了,店鋪關了門,街上無聲無息。偶爾出現一個居民,被這寂靜嚇到,緊挨著牆壁快速溜過。
焦慮的等待,反而讓人希望敵人快點到來。
在法國軍隊撤退的那天下午,不知從哪兒冒出幾個普魯士槍騎兵,迅速穿過市區。再稍晚一些,就有一堆黑壓壓的人馬從聖卡德林山坡(Sainte-Catherine)下來,另外兩批入侵者也出現在達爾恩達(Darnetal)大路上和吉詠樹林(Bois Guillaume)大路上。這三個前鋒部隊在同時間抵達市政府廣場上會合;隨後,德國軍隊主力來了,一個營接著一個營,強力而有節奏的步伐踏得石板路踱踱響。
一個陌生帶著喉音的口令沿著那些像是死寂荒蕪的房子往上升,然而護窗板後面,卻有許多眼睛窺伺著那些勝利的軍人,那些依據「戰爭律法」而成為整個城市生命財產的主人的軍人。居民們在黝暗的房子裡,驚嚇不已,就像面臨巨大災難,大地崩陷;對抗這種災害,所有人類的智慧和力氣都是無用的。因為每逢一切事物的秩序被顛覆,就不再有安全,人類法律或自然律法所保障的都任由一種無意識的殘忍暴力擺布。地震把整個國民壓在坍塌的房子底下;暴漲的河流捲走溺水的農民、牛的屍體、以及房屋被沖垮的棟樑;打了勝仗的軍隊屠殺自衛的一方,俘虜百姓,用刀搶奪用砲聲向神明致意;這些恐怖災難一而再、再而三破壞人們對永恆正義的信仰,破壞我們所被教育的對上天的庇佑和人類理智的信心。
一個一個小支隊在房屋前敲著門,然後消失在房子裡。這是入侵之後的佔領行為。戰敗者必須開始對戰勝者展現親切友好。過了一段時間,初期的恐怖消失之後,又恢復一種新的平靜。在許多人家,普魯士軍官和主人同桌吃飯。軍官中也有一些是家教良好,為了顧全禮貌,替法國叫屈,說自己根本不願意參加這場戰爭。大家很感激他這樣的情懷,更何況,自己說不定有一天需要他的保護,權且應付著他,或許還能藉此少接待幾個士兵,少幾張嘴吃飯。並且,何苦得罪一個自己完全仰其鼻息的人呢?倘若這樣做,根本不叫勇敢,而是魯莽冒失。──然而盧昂居民已不再魯莽冒失,不再像之前壯烈守護他們城市那時期的勇猛。──大家按照法國人的文明禮節演繹出的最高結論,只要不在公開場合和外國軍人表示親近,關起門在家裡講究禮貌是可以的。一出了門就形同陌路,但在家裡彼此交談,住在家裡的那個德國人因而每晚待得更久一點,和主人一家子一起在壁爐前烤火。
市區甚至慢慢恢復了平常的狀態。法國人還不大出門,但普魯士士兵卻在街上往來不息。此外,好些藍軍服的騎兵軍官傲慢地在石板街上拖著長大軍刀,但是對平民百姓的輕蔑態度,倒也不比去年在同樣那些咖啡館裡喝酒的法國步兵軍官更為明顯。
然而,空氣中有點不一樣,有點飄忽而陌生的東西,一種難以容忍的異樣氣氛,像是一股散發開來的氣味,入侵的氣味。它充斥著私人住宅和公共領域,它改變食物的滋味,它讓人覺得在前往遠方的旅途當中,步向野蠻危險的部落。
戰勝者需索金錢,大筆的錢。居民如數繳納,他們其實很有錢,但是一個諾曼第買賣人愈是有錢,就愈怕犧牲一分一毫,愈害怕看見自己財富的任何一部分轉到另外一個人手裡。
然而,在城市下游兩三法里的河裡,靠近克瓦榭(Croisset)、帝耶卜達勒(Dieppedalle)、或是別薩爾(Biessart)那一帶,經常有船家或漁夫從水底打撈出腫脹穿著軍服的德國人屍體,或是被刀刺死或是被一腳踢死,腦袋被石頭砸爛或是在橋上被推下水裡。河底的汙泥隱埋了這類隱晦、野蠻、卻又合理的報復,不為人知的英雄行徑、無聲的襲擊,比光天化日下的戰役更可怕,卻沒有響亮的榮耀。
對外國入侵者的怨恨,素來能讓某些膽大無畏的人,為了信念不顧性命。這些入侵者雖然以嚴苛的紀律控制著市區,但並沒有做出他們在整個勝利路線沿路所幹的駭人聽聞恐怖行徑,大家漸漸膽子大了,本區商人又開始心念著買賣。好幾個商人在哈佛港(Havre)訂有重大利益的契約,那個城市還在法軍防守之下,他們想試著走陸路到迪耶普(Dieppe),再從那裡坐船到哈佛港。
他們藉由熟識的日耳曼軍官的影響力,得到了總司令簽發的通行證。
因此,十個人到車行訂了位,車行準備了一輛四匹馬拉的公共驛車跑這趟旅途,為了避人耳目,決定星期二天亮之前出發。
好一陣子以來,積雪已經把地凍硬了,星期一下午約三點時,從北方壓過來大朵大朵的黑雲,帶來的雪下個不停,整個晚上、整夜都沒停。
清晨四點半,旅客們聚集在諾曼第旅館的院子裡,這是他們預定上車的地方。
他們都還睡意沉沉,裹著毯子發著抖。黑暗中誰也看不清誰,穿著滿身冬季的厚衣服,讓每個人都像穿著長袍的肥胖教士,不過有兩個旅客認出彼此,第三個也圍上前搭訕,開始聊起天:「我帶了妻子一同上路。」其中一個說。──「我也是。」──「我也是。」第一個又說:「我們不會再回盧昂來了,要是普魯士軍隊欺近哈佛港,我們就逃到英國去。」他們性質相同,所以也都抱著同樣的打算。
然而,馬車一直都還沒套上。馬車伕提著小燈籠不時從一扇烏黑的門走出來,又立刻進了另一扇門。馬蹄頓蹬著地面,但被地上鋪的廄草減低了聲響,屋裡傳來一陣對牲口說話和斥罵的聲音。馬頸上的輕微鈴聲顯示正在上馬具配鞍轡,輕微的鈴聲跟隨著牲口的動作,很快變成明顯而持續急促,有時候靜止一下,又突然亂震一陣子,伴隨著釘了蹄鐵的馬蹄踏著地面的沉悶聲響。
門突然關上了。一切聲響都停止。那些冷得打哆嗦的有錢人也閉上了嘴,凍僵了似的一動也不動。
連綿不斷的雪片像帷幕一般降下,發出閃爍的光芒,隱沒一切形體,在所有物體上面撒了一層綿綿雪花;在這埋在嚴寒之下寂靜的城市裡,什麼都聽不見,只聽見無數飄忽的雪片模糊的簌簌聲,與其說聲音,不如說是感覺,覺得交錯的微小雪花充斥著整個空間,覆蓋了整個大地。
(未完)
連續好些天以來,一小撮一小群的殘兵不斷穿過城裡,稱不上隊伍,只能算潰散的烏合之眾。他們的鬍子又長又髒,軍服破爛襤褸,無精打采地走著,沒有軍旗,也不成隊伍。每個都一副殘兵敗將的樣子,疲憊不堪,無法思考也毫無想法,只是依著習慣往前走,若一停下來就會疲倦倒地。他們大多是接到動員令徵招來的民兵,溫和的百姓,平日安享收益的人,現在卻扛著槍枝,身體彎曲成兩半;還有一些是國民防護隊,他們警覺性強,膽子小,一腔熱血,煽動一下就全力攻擊,受到挫敗也就立刻潰逃。當中也有幾個是真正職業軍人,一場激戰中某一師解體的殘兵、悽慘的砲兵和潰散的各類步兵排在一起,不時還可看到戴著閃亮的頭盔的龍騎兵,拖著沉重的腳步,跟在步履稍顯靈活的前線作戰步兵後面。
一團一團的游擊隊也帶著土匪的神氣走過,他們各自打著英雄式的名號:「敗仗復仇者」、「墓中公民」、「死亡分享者」。
他們的首領,戰爭之前做的是布匹或種子的買賣、賣羊脂或肥皂的生意人,因為時勢而進了游擊隊;因為他們有錢、或是鬍子比較長,不分究裡地獲得軍官階級,配上槍,穿上法蘭絨制服,戴上軍階。他們扯著喉嚨討論作戰計畫,自吹自擂自己一肩扛起奄奄一息的法國,但是他們其實有時候還得提防自己的手下,那些傢伙都是十惡不赦的壞蛋,猖狂大膽、無法無天的盜匪。
普魯士軍隊很快要佔領盧昂了,大家都這麼說。
兩個月以來,國民自衛軍在城外附近樹林裡謹慎小心地偵查,草木皆兵,還幾次開槍誤傷了自己的士兵,光一隻兔子出沒草叢,就像面臨大敵似的。他們都各自卸甲歸家,槍枝武器、制服、本來方圓三里公路兩旁保衛、退敵的裝置也突然消失了。
最後一些法國士兵終於渡過塞納河,經過聖歇維(Saint-Sever)和阿夏堡(Bourg-Achard),抵達歐德梅橋(Pont-Audemer);走在隊伍最後面的將軍,萬念俱灰,拿手下這一群衣衫襤褸的殘兵不知如何是好,連自己也因一向以驍勇善戰、無敵不克出名的民族,這次遭到毀滅性的瓦解崩潰而慌亂不已,拖著腳步,旁邊跟著兩個副官。
市區籠罩著一種深沉的平靜和一種駭然而靜肅的等待。許多大腹便便的有錢人,被生意消磨了鬥志,擔憂地等待著勝利者到來,想起廚房裡的烤肉鐵插和切肉大刀若被誤以為是武器,不禁嚇得渾身發抖。生活像是停頓了,店鋪關了門,街上無聲無息。偶爾出現一個居民,被這寂靜嚇到,緊挨著牆壁快速溜過。
焦慮的等待,反而讓人希望敵人快點到來。
在法國軍隊撤退的那天下午,不知從哪兒冒出幾個普魯士槍騎兵,迅速穿過市區。再稍晚一些,就有一堆黑壓壓的人馬從聖卡德林山坡(Sainte-Catherine)下來,另外兩批入侵者也出現在達爾恩達(Darnetal)大路上和吉詠樹林(Bois Guillaume)大路上。這三個前鋒部隊在同時間抵達市政府廣場上會合;隨後,德國軍隊主力來了,一個營接著一個營,強力而有節奏的步伐踏得石板路踱踱響。
一個陌生帶著喉音的口令沿著那些像是死寂荒蕪的房子往上升,然而護窗板後面,卻有許多眼睛窺伺著那些勝利的軍人,那些依據「戰爭律法」而成為整個城市生命財產的主人的軍人。居民們在黝暗的房子裡,驚嚇不已,就像面臨巨大災難,大地崩陷;對抗這種災害,所有人類的智慧和力氣都是無用的。因為每逢一切事物的秩序被顛覆,就不再有安全,人類法律或自然律法所保障的都任由一種無意識的殘忍暴力擺布。地震把整個國民壓在坍塌的房子底下;暴漲的河流捲走溺水的農民、牛的屍體、以及房屋被沖垮的棟樑;打了勝仗的軍隊屠殺自衛的一方,俘虜百姓,用刀搶奪用砲聲向神明致意;這些恐怖災難一而再、再而三破壞人們對永恆正義的信仰,破壞我們所被教育的對上天的庇佑和人類理智的信心。
一個一個小支隊在房屋前敲著門,然後消失在房子裡。這是入侵之後的佔領行為。戰敗者必須開始對戰勝者展現親切友好。過了一段時間,初期的恐怖消失之後,又恢復一種新的平靜。在許多人家,普魯士軍官和主人同桌吃飯。軍官中也有一些是家教良好,為了顧全禮貌,替法國叫屈,說自己根本不願意參加這場戰爭。大家很感激他這樣的情懷,更何況,自己說不定有一天需要他的保護,權且應付著他,或許還能藉此少接待幾個士兵,少幾張嘴吃飯。並且,何苦得罪一個自己完全仰其鼻息的人呢?倘若這樣做,根本不叫勇敢,而是魯莽冒失。──然而盧昂居民已不再魯莽冒失,不再像之前壯烈守護他們城市那時期的勇猛。──大家按照法國人的文明禮節演繹出的最高結論,只要不在公開場合和外國軍人表示親近,關起門在家裡講究禮貌是可以的。一出了門就形同陌路,但在家裡彼此交談,住在家裡的那個德國人因而每晚待得更久一點,和主人一家子一起在壁爐前烤火。
市區甚至慢慢恢復了平常的狀態。法國人還不大出門,但普魯士士兵卻在街上往來不息。此外,好些藍軍服的騎兵軍官傲慢地在石板街上拖著長大軍刀,但是對平民百姓的輕蔑態度,倒也不比去年在同樣那些咖啡館裡喝酒的法國步兵軍官更為明顯。
然而,空氣中有點不一樣,有點飄忽而陌生的東西,一種難以容忍的異樣氣氛,像是一股散發開來的氣味,入侵的氣味。它充斥著私人住宅和公共領域,它改變食物的滋味,它讓人覺得在前往遠方的旅途當中,步向野蠻危險的部落。
戰勝者需索金錢,大筆的錢。居民如數繳納,他們其實很有錢,但是一個諾曼第買賣人愈是有錢,就愈怕犧牲一分一毫,愈害怕看見自己財富的任何一部分轉到另外一個人手裡。
然而,在城市下游兩三法里的河裡,靠近克瓦榭(Croisset)、帝耶卜達勒(Dieppedalle)、或是別薩爾(Biessart)那一帶,經常有船家或漁夫從水底打撈出腫脹穿著軍服的德國人屍體,或是被刀刺死或是被一腳踢死,腦袋被石頭砸爛或是在橋上被推下水裡。河底的汙泥隱埋了這類隱晦、野蠻、卻又合理的報復,不為人知的英雄行徑、無聲的襲擊,比光天化日下的戰役更可怕,卻沒有響亮的榮耀。
對外國入侵者的怨恨,素來能讓某些膽大無畏的人,為了信念不顧性命。這些入侵者雖然以嚴苛的紀律控制著市區,但並沒有做出他們在整個勝利路線沿路所幹的駭人聽聞恐怖行徑,大家漸漸膽子大了,本區商人又開始心念著買賣。好幾個商人在哈佛港(Havre)訂有重大利益的契約,那個城市還在法軍防守之下,他們想試著走陸路到迪耶普(Dieppe),再從那裡坐船到哈佛港。
他們藉由熟識的日耳曼軍官的影響力,得到了總司令簽發的通行證。
因此,十個人到車行訂了位,車行準備了一輛四匹馬拉的公共驛車跑這趟旅途,為了避人耳目,決定星期二天亮之前出發。
好一陣子以來,積雪已經把地凍硬了,星期一下午約三點時,從北方壓過來大朵大朵的黑雲,帶來的雪下個不停,整個晚上、整夜都沒停。
清晨四點半,旅客們聚集在諾曼第旅館的院子裡,這是他們預定上車的地方。
他們都還睡意沉沉,裹著毯子發著抖。黑暗中誰也看不清誰,穿著滿身冬季的厚衣服,讓每個人都像穿著長袍的肥胖教士,不過有兩個旅客認出彼此,第三個也圍上前搭訕,開始聊起天:「我帶了妻子一同上路。」其中一個說。──「我也是。」──「我也是。」第一個又說:「我們不會再回盧昂來了,要是普魯士軍隊欺近哈佛港,我們就逃到英國去。」他們性質相同,所以也都抱著同樣的打算。
然而,馬車一直都還沒套上。馬車伕提著小燈籠不時從一扇烏黑的門走出來,又立刻進了另一扇門。馬蹄頓蹬著地面,但被地上鋪的廄草減低了聲響,屋裡傳來一陣對牲口說話和斥罵的聲音。馬頸上的輕微鈴聲顯示正在上馬具配鞍轡,輕微的鈴聲跟隨著牲口的動作,很快變成明顯而持續急促,有時候靜止一下,又突然亂震一陣子,伴隨著釘了蹄鐵的馬蹄踏著地面的沉悶聲響。
門突然關上了。一切聲響都停止。那些冷得打哆嗦的有錢人也閉上了嘴,凍僵了似的一動也不動。
連綿不斷的雪片像帷幕一般降下,發出閃爍的光芒,隱沒一切形體,在所有物體上面撒了一層綿綿雪花;在這埋在嚴寒之下寂靜的城市裡,什麼都聽不見,只聽見無數飄忽的雪片模糊的簌簌聲,與其說聲音,不如說是感覺,覺得交錯的微小雪花充斥著整個空間,覆蓋了整個大地。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