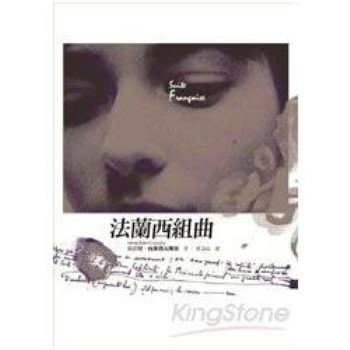第一部曲 六月風暴
1.戰爭
熱啊,巴黎人心裡想。春天的氣息。這是戰爭的夜晚,警報。不過,夜色慢慢消退,戰爭遠著呢。那些睡不著的人們、身陷床榻的病患、兒子上前線的母親、淚已流乾雙眼無神的戀人們,聽見了第一聲警報鈴響。那聲音還只像是一口深呼吸,彷彿從受壓迫的胸膛裡飄出的一絲輕嘆。過了一會兒,天空滿布朝陽。陽光大老遠地從地平線的盡頭放射過來,可說是,不疾不徐!酣睡的人夢見了捲起大浪和鵝卵石的大海,夢見了三月時狂風大作撼動森林的暴風雨,夢見了一群牛,拖著沉重的身軀,搖搖晃晃地奔跑,大地為之震動,就這樣一直到睡意完全消退,他們半睜惺忪雙眼,喃喃的說:
「警報嗎?」
女人比較緊張,比較機靈,她們早就起床了。有些婦女甚至已經關妥窗戶,鎖好擋風百葉窗,回到床上重新睡下了。昨天晚上,六月三日星期一,是戰爭開打以來,巴黎第一次遭到轟炸;不過,民眾頭腦冷靜如常。儘管傳來的消息很糟,大夥都不信。現在若傳出戰爭勝利的消息,大概也沒有人會信。大夥藉著手電筒的燈光替小孩穿衣服。母親雙手抱起沉重溫熱的小小身軀:「來,不怕,不哭喔。」是空襲警報。所有燈火熄滅,然而,在六月金黃澄明的天空下,每一棟屋子、每一條街道,皆無所遁形。至於塞納河,彷彿蒐集了每一顆星散的光點,像片多層鏡面似地將之映照出百倍光芒。窗戶掩護得不夠好,屋頂在淡淡的黑暗中一閃一閃地反光,門上的金屬配件,每個突出的部分都微微地閃耀金光,有些紅綠燈撐得比其他的久,沒有人知道原因。塞納河吸引光,截取光,讓光在它的水波中嬉戲。從高處眺望,川流的白色河水八成像牛奶。有些人認為,它是敵軍戰機辨別方位的地標,也有人認為絕不可能。事實上,我們什麼都不知道。「我要待在床上,」透著濃濃睡意的聲音緩緩飄來,「我才不怕。說真格的,要是萬一,你就吃不了兜著走了。」那些乖乖牌反駁。
新大樓的逃生梯,玻璃帷幕後面,一個、兩個、三個小火光往下走:七樓的住戶忙著逃離高處:儘管法令規定不得開燈,他們還是拿著電燈探路。「我可不想在下樓時摔得鼻青臉腫,你要來嗎,艾蜜兒?」大夥本能地壓低嗓門,好像四下潛伏著敵人的耳目,門一扇接一扇地關上。一些人口密集的地區、地鐵、冒著髒汙氣味的避難所,總是有一群人聚集在那裡;相對地,有錢人則滿足地待在門房的房間裡,大夥兒豎起耳朵,捕捉宣告炸彈落下的轟然巨響,屏氣凝神,弓起身體,一如狩獵夜將近時躲在樹林裡擔心受怕的野獸。貧苦人家並不比富有人家膽小,他們沒有比那些人更眷戀人生,只是柔順盲從些,他們彼此互相需要,相互扶持,一起哀嘆或一起大笑。天光馬上就要大亮,一道銀白雪青的光線爬上鋪石路面,爬上河岸欄杆,爬上聖母院的高塔。沙包堆滿教堂主建物的四周,高度及教堂的一半,蓋住歌劇院外牆上的卡爾坡的舞者群像,堵住凱旋門上〈馬賽曲〉的吶喊。
大砲轟隆迴盪,還在相當遠的地方,接著,砲聲逐漸接近,震得玻璃窗隨之顫抖。新生兒在溫暖的房間裡呱呱落地,那裡的窗戶縫隙全都塞住了,不讓一絲屋內的燈光透到外面,他們的哭聲叫女人忘了警鈴,忘了戰爭。聽在將死的人耳裡,一聲聲的爆炸變成疲軟無力、沒有任何意義的聲響,猶如波浪般一波一波,不時加入迎接將死之人的陰森隱約的竊竊私語中。小孩貼著母親溫暖的側身,睡得安穩,小小的嘴唇發出輕輕的咂嘴聲,模樣像極了吸奶的小羊。警報期間,被臨時棄置街邊的流動蔬果攤推車上滿載花朵。
萬里無雲的朗朗天空,紅紅的太陽再次升起。一顆砲彈發射,現在,砲彈的落點是如此接近巴黎市區了,以至於在每一座紀念碑上棲息的小鳥,受到驚嚇,黑壓壓地整片飛走。高高的天空,黑色大鳥盤旋,其餘時候看不到的大鳥也伸展了被陽光映染成粉紅色的翅膀,接著肥嘟嘟、咕嚕咕嚕直叫的漂亮鴿子和燕子也來了,麻雀安詳地在無人的街道上一蹭一蹭地跳著。塞納河畔,每一棵垂柳枝頭都掛著一串棕色小鳥,無不用盡全力大聲鳴唱。大夥在地下室的最深處,終於聽見遠遠的一聲呼喊,因為距離太遠聲音顯得模糊,聽起來好像是三音鼓號。警報解除了。
大夥在貝黎剛家聽晚間新聞廣播,沒有人開口針對時事發表議論,一片無奈喪氣的沉默。貝黎剛一家是思想正統的保守人士:他們的家庭傳統、意識型態、資產階級和天主教的傳承背景,以及與教會的密切關係(他們的大兒子:菲利普.貝黎剛是神父),所有的一切在在使得他們處處提防共和政府。另一方面,貝黎剛先生的情況——他是某間國立博物館的館長,也使得他傾向支持能帶給為它服務的公僕們榮耀和利益的政權。
好比一隻貓咪,銳利的尖牙底下,小心翼翼地咬住一塊魚,魚身卻到處是刺:食之可怕,棄之可惜。
最後是夏絡特.貝黎剛,她認為唯有男性的大腦才有能力公允地評斷如此詭異嚴重的事件。然而,她的丈夫和她的兒子都不在家;老公到朋友家吃飯,兒子則不在巴黎。至於每日尋常生活裡的大小瑣事則完全由貝黎剛太太做主——像是指揮家務,教育孩子或老公的事業,貝黎剛太太從來不聽旁人的意見;不過,時事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範疇。必須先有權威性的發言告訴她哪些是可以相信的,一旦她標示出正確的路線,即全力以赴,不畏任何艱難。萬一有人鐵證如山,指出她的意見是錯的,也只是露出高傲的冷笑,回稱:「這是我父親告訴我的。我丈夫也多方打聽求證過了。」然後,伸出帶著手套的手,半空微微一揮,討論結束。
丈夫的工作讓她覺得非常有面子(她自己偏好深居簡出的日子,不過,誠如我們慈愛的救世主親身樹立的典範,俗世間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負)。在監督小孩做功課,看著最小的孩子喝完奶,指揮僕人工作等事務的空檔時間裡,她剛剛抵達家門,還沒來得及解下身上的全副武裝。在小一輩的貝黎剛家人的印象裡,他們的母親總是穿戴整齊,一副隨時準備出門的樣子,頭戴帽子,雙手套著白手套(由於她生性節儉,補綴過的手套總飄著一股淡淡的汽油味兒,進過洗染店留下的氣味證據)。
回到那天晚上,她剛剛踏進家門,人就站在客廳,正對著收音機。她穿著一身黑,頭戴當季流行的小帽子,精巧的女帽上綴三朵花,一顆真絲絲球垂掛前緣;帽子底下的那張臉,蒼白焦急,強力控訴歲月的無情和經年的疲憊。她已經四十七歲了,而且是五個孩子的媽。上帝賜予這位女士的髮色,很明顯地,應該是紅棕色調;過去曾經非常細緻的肌膚,經受不住年月的摧殘;剛毅直挺的鼻梁上,點點雀斑散布,貓眼似的綠色眼眸發射銳利的目光。不過,在最後一刻,上天一定是心生動搖了,或是認為閃亮鮮豔的髮色,與貝黎剛太太無懈可擊的道德觀還有她的地位均不相配,決定改成沒有光澤的褐色,暗沉的頭髮在她生完最後一個小孩之後,開始大把大把地掉落。貝黎剛先生是個生活嚴謹的人:宗教的道德規範禁止他擁有過多的欲望,再者,他非常愛惜名聲,從不流連不當場所。所以,貝黎剛家中最小的孩子才兩歲,老大菲利普神父和老么之間,依序還有三個小孩,全部順利的活下來了,其中交雜貝黎剛太太不好意思地稱之為三場意外的三次懷孕,嬰兒在母體內順利地長到足月,一生下卻夭折,三次都讓他們的母親在鬼門關前走了一趟。
此時,充斥著收音機廣播聲響的客廳,格局又大又勻稱,四扇窗面對德雷塞特大道。裡頭的裝潢走懷舊風,大型扶手椅外加金黃色軟墊沙發。陽台附近,停著行走不便、老貝黎剛先生乘坐的輪椅,他歲數大了,偶爾會返老還童,只有在問到他龐大的財產時,他的腦袋才會完全清醒(他是貝黎剛和馬爾岱兩大家族的後裔,里昂馬爾岱世家的繼承人)。不過,無論是戰火或政局的更迭,他完全感覺不到不同。他漫不經心地聽著廣播,有節奏地點頭搖動銀白的漂亮鬍子。小孩呈半圓形圍在母親身後,最小的那個躺在奶媽的懷裡,全員出席。三個兒子都在前線的奶媽抱著老么來跟家人道晚安,同時趁著在客廳逗留的短暫時間,焦急專注地傾聽喇叭裡傳來的字句。
門扉半掩,貝黎剛太太猜得出來門後躲著其他僕人,焦急之情溢於言表的女僕瑪德蓮甚至失了態,踏上了門檻邊,這種觸犯禮法的不當行為,看在貝黎剛太太的眼裡無異是不祥的徵兆。就這樣,好像大難臨頭,大夥不分階級同在一條船上,只差老百姓沒有群起憤慨抗爭。「他們真的太放肆了,」她心想,不免一絲責難。貝黎剛太太是那種信任普通老百姓的資產階級人士。「他們不壞,只是要懂得駕馭他們。」她一副寬宏大量,慈悲為懷的口吻,好像講得是被關在籠子裡的牲畜。她為自己能夠留得住下人而深感自豪,僕人生病,她堅持親自照料。還記得瑪德蓮染上咽喉炎那次,貝黎剛太太親自為她準備漱口劑。白天她勻不出時間來做,只能等到晚上從戲院回來之後處理。瑪德蓮從睡夢中驚醒,事後才對她表達感激之情,貝黎剛太太認為她的道謝詞實在過於冷淡了。但這就是小老百姓,永遠不會滿足,我們愈是想盡辦法要為他們做點事,他們的反應愈見不可捉摸,不知好歹。不過,貝黎剛太太一心只期盼上天能給予她回報。
她轉身對著幽暗的前廳,大發慈悲地說:
「如果你們想聽的話,可以進來聽。」
「謝謝您,夫人。」幾個敬畏的聲音飄然傳來,僕人一個個躡手躡腳地溜進客廳。
瑪德蓮、瑪莉和臥房小廝奧古斯特陸續出現,最後是廚娘瑪麗亞,她為自己手上的魚腥味感到羞愧不已。其實,新聞已經播報完畢了,現在播放的是針對當前「確實嚴重,但還不到危急恐慌的局勢」的評論。收音機傳來的聲音如此圓潤,如此泰然,如此溫靜,每一回說到「法蘭西,祖國和軍隊」這些字眼時,語氣中軍號樂似的振奮聲調在聽眾的心裡散布樂觀的種子。獨樹一格的說話方式,複述著政府公報,關於「敵軍持續以強大火力進攻我方要塞,遭遇我軍頑強的抵抗」的消息,會以輕佻、諷刺、不屑的口吻念前半段,好像在暗示:「總之,他們想讓我們以為是這樣的。」相反地,句子的後半部,會加重每個音節,尤其強調「頑強的」這個形容詞,以及「我軍」之類的字眼,字裡行間傳來的無比信心,讓這些人不禁要想:「我們這樣擔心,真是過於杞人憂天了!」
貝黎剛太太瞥見大夥眼裡的疑問,以及對她的期待,於是堅定的宣布:
「聽起來情況好像沒有很糟!」
她這麼說並不是因為她這麼相信著,而是出自提振周遭民眾的士氣,她責無旁貸。
瑪麗亞和瑪德蓮嘆了一口氣。
「夫人是這麼想的嗎?」
貝黎剛家的老二,雨柏,是個十八歲的大男孩,有著粉嫩白胖的臉頰,他似乎是這裡唯一感到絕望和驚愕的人。他緊張地拿搓成一團的手帕輕拍脖子,不時以刺耳沙啞的聲音大喊:
「怎麼可以這樣!我們怎麼可以這樣坐以待斃!媽,他究竟在等什麼,怎麼還不號召男人拿起武器?從十六到六十歲,所有的男人,就是現在!這才是他們該做的,您不認為嗎,媽?」
說著跑進書房,回來時手上拿著一張大地圖,他把地圖放在桌上展開,激動地估量距離。
「我跟你們說,我們輸定了,穩輸的,除非……」
他重燃起希望。
「我啊,我知道他們想怎麼做了。他終於說,臉上帶著燦爛的笑容,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我看得非常清楚,我們讓他們不斷地挺進,深入,然後以逸待勞地等在這裡,您看,媽!或者……」
「是,是。」他母親說。「快去洗手,梳理一下那絡頭髮,老是落到眼睛前面。看看你這是什麼樣子。」
雨柏忿忿不平地疊起地圖。只有菲利普把他當一回事兒,只有菲利普站在平等的立場上與他溝通。「家人,我恨你們。」他的內心在吶喊。走出客廳的時候,為了洩憤,他一腳踢飛了弟弟柏納的玩具,柏納頓時大哭大鬧。「這樣他才能領略什麼是人生」,雨柏想。奶媽連忙帶柏納、賈桂林和已經貼著她肩膀睡著的小艾曼紐離開客廳。奶媽邁著大步,一手牽著柏納,邊走邊掉淚,為了三個只留有回憶的兒子,三個全為國犧牲的兒子。「只有悲傷和不幸,悲傷和不幸!」她反覆低聲地念著,只見灰白的頭左右輕搖。她扭開浴缸的水龍頭,烘暖小孩的浴袍,嘴裡喃喃的總是同樣的老話,這些話在她看來不僅具體地刻畫出當前政局,更是她人生的縮影:年輕時辛苦種田,守寡,媳婦脾氣不好,打從十六歲起就開始寄人籬下的悽慘人生。
臥房小廝奧古斯特悄悄地回到廚房。故做正經的愚蠢臉上明顯地表現出他對許多事情的極度輕蔑與不屑。貝黎剛太太回到自己的房間。這個活力驚人的女人利用小孩洗澡和開飯前的短短十五分鐘時間,叫賈桂林和柏納複習功課。稚嫩的聲音飄來:「地球是一顆懸浮在虛無中的圓球。」客廳只剩貝黎剛老先生和貓咪艾伯特。這是非常美好的一天,傍晚的落日餘暉輕柔地灑落蓊鬱栗子樹林。艾伯特是隻毛色灰濛的雜種小貓,是小孩子養的寵物,牠似乎興奮過了頭,雀躍不止,四腳朝天地躺在地毯上轉來轉去,跳上煙囪,嚙咬插在藍色大夜壺裡的一朵牡丹花花瓣,一隻狼頭黃銅塑像精巧地鑲嵌在支架一隅,貓咪一個起跳,躍上老人家的扶手椅,在他耳邊喵喵地叫。貝黎剛老先生朝貓咪伸出總是青紫、顫抖、冰涼的手。貓嚇了一跳,一溜煙跑走了。就要開飯了。奧古斯特走過來,將不良於行的老人家推到飯廳。大家陸續就坐,此時,女主人突然停止動作,盛著營養補給液要餵賈桂琳喝的湯匙停在半空中。
「是你們的父親,孩子們。」她聽到鑰匙轉動的聲音。
1.戰爭
熱啊,巴黎人心裡想。春天的氣息。這是戰爭的夜晚,警報。不過,夜色慢慢消退,戰爭遠著呢。那些睡不著的人們、身陷床榻的病患、兒子上前線的母親、淚已流乾雙眼無神的戀人們,聽見了第一聲警報鈴響。那聲音還只像是一口深呼吸,彷彿從受壓迫的胸膛裡飄出的一絲輕嘆。過了一會兒,天空滿布朝陽。陽光大老遠地從地平線的盡頭放射過來,可說是,不疾不徐!酣睡的人夢見了捲起大浪和鵝卵石的大海,夢見了三月時狂風大作撼動森林的暴風雨,夢見了一群牛,拖著沉重的身軀,搖搖晃晃地奔跑,大地為之震動,就這樣一直到睡意完全消退,他們半睜惺忪雙眼,喃喃的說:
「警報嗎?」
女人比較緊張,比較機靈,她們早就起床了。有些婦女甚至已經關妥窗戶,鎖好擋風百葉窗,回到床上重新睡下了。昨天晚上,六月三日星期一,是戰爭開打以來,巴黎第一次遭到轟炸;不過,民眾頭腦冷靜如常。儘管傳來的消息很糟,大夥都不信。現在若傳出戰爭勝利的消息,大概也沒有人會信。大夥藉著手電筒的燈光替小孩穿衣服。母親雙手抱起沉重溫熱的小小身軀:「來,不怕,不哭喔。」是空襲警報。所有燈火熄滅,然而,在六月金黃澄明的天空下,每一棟屋子、每一條街道,皆無所遁形。至於塞納河,彷彿蒐集了每一顆星散的光點,像片多層鏡面似地將之映照出百倍光芒。窗戶掩護得不夠好,屋頂在淡淡的黑暗中一閃一閃地反光,門上的金屬配件,每個突出的部分都微微地閃耀金光,有些紅綠燈撐得比其他的久,沒有人知道原因。塞納河吸引光,截取光,讓光在它的水波中嬉戲。從高處眺望,川流的白色河水八成像牛奶。有些人認為,它是敵軍戰機辨別方位的地標,也有人認為絕不可能。事實上,我們什麼都不知道。「我要待在床上,」透著濃濃睡意的聲音緩緩飄來,「我才不怕。說真格的,要是萬一,你就吃不了兜著走了。」那些乖乖牌反駁。
新大樓的逃生梯,玻璃帷幕後面,一個、兩個、三個小火光往下走:七樓的住戶忙著逃離高處:儘管法令規定不得開燈,他們還是拿著電燈探路。「我可不想在下樓時摔得鼻青臉腫,你要來嗎,艾蜜兒?」大夥本能地壓低嗓門,好像四下潛伏著敵人的耳目,門一扇接一扇地關上。一些人口密集的地區、地鐵、冒著髒汙氣味的避難所,總是有一群人聚集在那裡;相對地,有錢人則滿足地待在門房的房間裡,大夥兒豎起耳朵,捕捉宣告炸彈落下的轟然巨響,屏氣凝神,弓起身體,一如狩獵夜將近時躲在樹林裡擔心受怕的野獸。貧苦人家並不比富有人家膽小,他們沒有比那些人更眷戀人生,只是柔順盲從些,他們彼此互相需要,相互扶持,一起哀嘆或一起大笑。天光馬上就要大亮,一道銀白雪青的光線爬上鋪石路面,爬上河岸欄杆,爬上聖母院的高塔。沙包堆滿教堂主建物的四周,高度及教堂的一半,蓋住歌劇院外牆上的卡爾坡的舞者群像,堵住凱旋門上〈馬賽曲〉的吶喊。
大砲轟隆迴盪,還在相當遠的地方,接著,砲聲逐漸接近,震得玻璃窗隨之顫抖。新生兒在溫暖的房間裡呱呱落地,那裡的窗戶縫隙全都塞住了,不讓一絲屋內的燈光透到外面,他們的哭聲叫女人忘了警鈴,忘了戰爭。聽在將死的人耳裡,一聲聲的爆炸變成疲軟無力、沒有任何意義的聲響,猶如波浪般一波一波,不時加入迎接將死之人的陰森隱約的竊竊私語中。小孩貼著母親溫暖的側身,睡得安穩,小小的嘴唇發出輕輕的咂嘴聲,模樣像極了吸奶的小羊。警報期間,被臨時棄置街邊的流動蔬果攤推車上滿載花朵。
萬里無雲的朗朗天空,紅紅的太陽再次升起。一顆砲彈發射,現在,砲彈的落點是如此接近巴黎市區了,以至於在每一座紀念碑上棲息的小鳥,受到驚嚇,黑壓壓地整片飛走。高高的天空,黑色大鳥盤旋,其餘時候看不到的大鳥也伸展了被陽光映染成粉紅色的翅膀,接著肥嘟嘟、咕嚕咕嚕直叫的漂亮鴿子和燕子也來了,麻雀安詳地在無人的街道上一蹭一蹭地跳著。塞納河畔,每一棵垂柳枝頭都掛著一串棕色小鳥,無不用盡全力大聲鳴唱。大夥在地下室的最深處,終於聽見遠遠的一聲呼喊,因為距離太遠聲音顯得模糊,聽起來好像是三音鼓號。警報解除了。
大夥在貝黎剛家聽晚間新聞廣播,沒有人開口針對時事發表議論,一片無奈喪氣的沉默。貝黎剛一家是思想正統的保守人士:他們的家庭傳統、意識型態、資產階級和天主教的傳承背景,以及與教會的密切關係(他們的大兒子:菲利普.貝黎剛是神父),所有的一切在在使得他們處處提防共和政府。另一方面,貝黎剛先生的情況——他是某間國立博物館的館長,也使得他傾向支持能帶給為它服務的公僕們榮耀和利益的政權。
好比一隻貓咪,銳利的尖牙底下,小心翼翼地咬住一塊魚,魚身卻到處是刺:食之可怕,棄之可惜。
最後是夏絡特.貝黎剛,她認為唯有男性的大腦才有能力公允地評斷如此詭異嚴重的事件。然而,她的丈夫和她的兒子都不在家;老公到朋友家吃飯,兒子則不在巴黎。至於每日尋常生活裡的大小瑣事則完全由貝黎剛太太做主——像是指揮家務,教育孩子或老公的事業,貝黎剛太太從來不聽旁人的意見;不過,時事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範疇。必須先有權威性的發言告訴她哪些是可以相信的,一旦她標示出正確的路線,即全力以赴,不畏任何艱難。萬一有人鐵證如山,指出她的意見是錯的,也只是露出高傲的冷笑,回稱:「這是我父親告訴我的。我丈夫也多方打聽求證過了。」然後,伸出帶著手套的手,半空微微一揮,討論結束。
丈夫的工作讓她覺得非常有面子(她自己偏好深居簡出的日子,不過,誠如我們慈愛的救世主親身樹立的典範,俗世間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負)。在監督小孩做功課,看著最小的孩子喝完奶,指揮僕人工作等事務的空檔時間裡,她剛剛抵達家門,還沒來得及解下身上的全副武裝。在小一輩的貝黎剛家人的印象裡,他們的母親總是穿戴整齊,一副隨時準備出門的樣子,頭戴帽子,雙手套著白手套(由於她生性節儉,補綴過的手套總飄著一股淡淡的汽油味兒,進過洗染店留下的氣味證據)。
回到那天晚上,她剛剛踏進家門,人就站在客廳,正對著收音機。她穿著一身黑,頭戴當季流行的小帽子,精巧的女帽上綴三朵花,一顆真絲絲球垂掛前緣;帽子底下的那張臉,蒼白焦急,強力控訴歲月的無情和經年的疲憊。她已經四十七歲了,而且是五個孩子的媽。上帝賜予這位女士的髮色,很明顯地,應該是紅棕色調;過去曾經非常細緻的肌膚,經受不住年月的摧殘;剛毅直挺的鼻梁上,點點雀斑散布,貓眼似的綠色眼眸發射銳利的目光。不過,在最後一刻,上天一定是心生動搖了,或是認為閃亮鮮豔的髮色,與貝黎剛太太無懈可擊的道德觀還有她的地位均不相配,決定改成沒有光澤的褐色,暗沉的頭髮在她生完最後一個小孩之後,開始大把大把地掉落。貝黎剛先生是個生活嚴謹的人:宗教的道德規範禁止他擁有過多的欲望,再者,他非常愛惜名聲,從不流連不當場所。所以,貝黎剛家中最小的孩子才兩歲,老大菲利普神父和老么之間,依序還有三個小孩,全部順利的活下來了,其中交雜貝黎剛太太不好意思地稱之為三場意外的三次懷孕,嬰兒在母體內順利地長到足月,一生下卻夭折,三次都讓他們的母親在鬼門關前走了一趟。
此時,充斥著收音機廣播聲響的客廳,格局又大又勻稱,四扇窗面對德雷塞特大道。裡頭的裝潢走懷舊風,大型扶手椅外加金黃色軟墊沙發。陽台附近,停著行走不便、老貝黎剛先生乘坐的輪椅,他歲數大了,偶爾會返老還童,只有在問到他龐大的財產時,他的腦袋才會完全清醒(他是貝黎剛和馬爾岱兩大家族的後裔,里昂馬爾岱世家的繼承人)。不過,無論是戰火或政局的更迭,他完全感覺不到不同。他漫不經心地聽著廣播,有節奏地點頭搖動銀白的漂亮鬍子。小孩呈半圓形圍在母親身後,最小的那個躺在奶媽的懷裡,全員出席。三個兒子都在前線的奶媽抱著老么來跟家人道晚安,同時趁著在客廳逗留的短暫時間,焦急專注地傾聽喇叭裡傳來的字句。
門扉半掩,貝黎剛太太猜得出來門後躲著其他僕人,焦急之情溢於言表的女僕瑪德蓮甚至失了態,踏上了門檻邊,這種觸犯禮法的不當行為,看在貝黎剛太太的眼裡無異是不祥的徵兆。就這樣,好像大難臨頭,大夥不分階級同在一條船上,只差老百姓沒有群起憤慨抗爭。「他們真的太放肆了,」她心想,不免一絲責難。貝黎剛太太是那種信任普通老百姓的資產階級人士。「他們不壞,只是要懂得駕馭他們。」她一副寬宏大量,慈悲為懷的口吻,好像講得是被關在籠子裡的牲畜。她為自己能夠留得住下人而深感自豪,僕人生病,她堅持親自照料。還記得瑪德蓮染上咽喉炎那次,貝黎剛太太親自為她準備漱口劑。白天她勻不出時間來做,只能等到晚上從戲院回來之後處理。瑪德蓮從睡夢中驚醒,事後才對她表達感激之情,貝黎剛太太認為她的道謝詞實在過於冷淡了。但這就是小老百姓,永遠不會滿足,我們愈是想盡辦法要為他們做點事,他們的反應愈見不可捉摸,不知好歹。不過,貝黎剛太太一心只期盼上天能給予她回報。
她轉身對著幽暗的前廳,大發慈悲地說:
「如果你們想聽的話,可以進來聽。」
「謝謝您,夫人。」幾個敬畏的聲音飄然傳來,僕人一個個躡手躡腳地溜進客廳。
瑪德蓮、瑪莉和臥房小廝奧古斯特陸續出現,最後是廚娘瑪麗亞,她為自己手上的魚腥味感到羞愧不已。其實,新聞已經播報完畢了,現在播放的是針對當前「確實嚴重,但還不到危急恐慌的局勢」的評論。收音機傳來的聲音如此圓潤,如此泰然,如此溫靜,每一回說到「法蘭西,祖國和軍隊」這些字眼時,語氣中軍號樂似的振奮聲調在聽眾的心裡散布樂觀的種子。獨樹一格的說話方式,複述著政府公報,關於「敵軍持續以強大火力進攻我方要塞,遭遇我軍頑強的抵抗」的消息,會以輕佻、諷刺、不屑的口吻念前半段,好像在暗示:「總之,他們想讓我們以為是這樣的。」相反地,句子的後半部,會加重每個音節,尤其強調「頑強的」這個形容詞,以及「我軍」之類的字眼,字裡行間傳來的無比信心,讓這些人不禁要想:「我們這樣擔心,真是過於杞人憂天了!」
貝黎剛太太瞥見大夥眼裡的疑問,以及對她的期待,於是堅定的宣布:
「聽起來情況好像沒有很糟!」
她這麼說並不是因為她這麼相信著,而是出自提振周遭民眾的士氣,她責無旁貸。
瑪麗亞和瑪德蓮嘆了一口氣。
「夫人是這麼想的嗎?」
貝黎剛家的老二,雨柏,是個十八歲的大男孩,有著粉嫩白胖的臉頰,他似乎是這裡唯一感到絕望和驚愕的人。他緊張地拿搓成一團的手帕輕拍脖子,不時以刺耳沙啞的聲音大喊:
「怎麼可以這樣!我們怎麼可以這樣坐以待斃!媽,他究竟在等什麼,怎麼還不號召男人拿起武器?從十六到六十歲,所有的男人,就是現在!這才是他們該做的,您不認為嗎,媽?」
說著跑進書房,回來時手上拿著一張大地圖,他把地圖放在桌上展開,激動地估量距離。
「我跟你們說,我們輸定了,穩輸的,除非……」
他重燃起希望。
「我啊,我知道他們想怎麼做了。他終於說,臉上帶著燦爛的笑容,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我看得非常清楚,我們讓他們不斷地挺進,深入,然後以逸待勞地等在這裡,您看,媽!或者……」
「是,是。」他母親說。「快去洗手,梳理一下那絡頭髮,老是落到眼睛前面。看看你這是什麼樣子。」
雨柏忿忿不平地疊起地圖。只有菲利普把他當一回事兒,只有菲利普站在平等的立場上與他溝通。「家人,我恨你們。」他的內心在吶喊。走出客廳的時候,為了洩憤,他一腳踢飛了弟弟柏納的玩具,柏納頓時大哭大鬧。「這樣他才能領略什麼是人生」,雨柏想。奶媽連忙帶柏納、賈桂林和已經貼著她肩膀睡著的小艾曼紐離開客廳。奶媽邁著大步,一手牽著柏納,邊走邊掉淚,為了三個只留有回憶的兒子,三個全為國犧牲的兒子。「只有悲傷和不幸,悲傷和不幸!」她反覆低聲地念著,只見灰白的頭左右輕搖。她扭開浴缸的水龍頭,烘暖小孩的浴袍,嘴裡喃喃的總是同樣的老話,這些話在她看來不僅具體地刻畫出當前政局,更是她人生的縮影:年輕時辛苦種田,守寡,媳婦脾氣不好,打從十六歲起就開始寄人籬下的悽慘人生。
臥房小廝奧古斯特悄悄地回到廚房。故做正經的愚蠢臉上明顯地表現出他對許多事情的極度輕蔑與不屑。貝黎剛太太回到自己的房間。這個活力驚人的女人利用小孩洗澡和開飯前的短短十五分鐘時間,叫賈桂林和柏納複習功課。稚嫩的聲音飄來:「地球是一顆懸浮在虛無中的圓球。」客廳只剩貝黎剛老先生和貓咪艾伯特。這是非常美好的一天,傍晚的落日餘暉輕柔地灑落蓊鬱栗子樹林。艾伯特是隻毛色灰濛的雜種小貓,是小孩子養的寵物,牠似乎興奮過了頭,雀躍不止,四腳朝天地躺在地毯上轉來轉去,跳上煙囪,嚙咬插在藍色大夜壺裡的一朵牡丹花花瓣,一隻狼頭黃銅塑像精巧地鑲嵌在支架一隅,貓咪一個起跳,躍上老人家的扶手椅,在他耳邊喵喵地叫。貝黎剛老先生朝貓咪伸出總是青紫、顫抖、冰涼的手。貓嚇了一跳,一溜煙跑走了。就要開飯了。奧古斯特走過來,將不良於行的老人家推到飯廳。大家陸續就坐,此時,女主人突然停止動作,盛著營養補給液要餵賈桂琳喝的湯匙停在半空中。
「是你們的父親,孩子們。」她聽到鑰匙轉動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