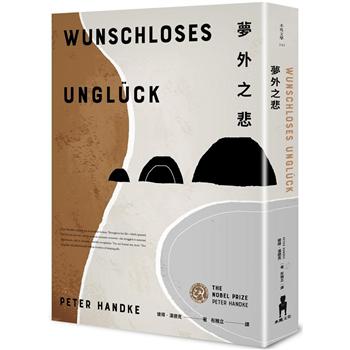凱爾騰州《人民日報》週日版的「綜合消息」欄目,刊載著如下的事情──「週五深夜,A城(G區)一名五十一歲的家庭主婦服用過量的安眠藥自殺。」
我母親過世至今已經快七個星期了。在葬禮上我曾有強烈的慾望想書寫她,我希望這份渴望在還沒退回麻木無語之前就展開工作。那份麻木的無語,是我得知她自殺消息時的反應。是的,展開工作──因為,想書寫我母親的這份渴望,有時會突如其來,有時卻又飄忽不定,因此必須得很努力工作,才不至於讓我太隨心所欲,比如用打字機在紙上不斷敲著同一個字母。然而這種單調的反覆動作對我並沒有幫助,它只會使我更加消極與麻木。當然我也可以離開──在路上、旅途中,即便沒頭沒腦地瞌睡與閒蕩,也不至於讓自己無法忍受。
幾個星期以來,我比平常更容易被激怒,在混亂、寒冷與靜默之中幾乎無法與人交談,每當地上出現一點小毛球或麵包屑,我就彎下腰撿起來。有時我訝異於我所握住的東西並沒有早早從我的手裡落下;想及這場自殺的時候,我會突然變得無感。儘管如此,我仍渴望著那樣的時刻,因為如此一來,麻木感消失,我的頭腦一片清明。那份驚駭讓我又好多了──終於我不再百無聊賴,身體不再抵抗,沒有費力的疏遠,沒有令人傷痛的時光流逝。
在這種時候,最糟糕的莫過於他人的參與,即便是一道目光,甚或一句話。你只能馬上望向他處,或直截了當地堵住他的嘴;因為你需要那感覺──你正經歷的事,它令人費解也無法言傳。唯有如此,我們才會感到那份驚駭是真實且意味深長的。一旦談起這件事情,人們馬上又會覺得無趣,一切突然又變成虛空。然而,我偶爾會沒來由地向人們說起我母親的自殺,若他們妄加評論些什麼,我就會生氣起來,接著,我希望他們最好能轉移注意力,用甚麼其他的東西嘲笑我也好。
就好比詹姆士‧龐德在他最新的一部電影,人們問他,那位被他從樓梯欄杆上丟下去的對手是否死了,他回答:「但願是這樣!」這時我不由得輕鬆地笑了。我一點也不在意人們開死亡的玩笑,甚至這樣讓我覺得舒服。
驚恐的時刻總是非常短暫,更多是不真實的感受,在這些瞬間之後,一切又都閉鎖起來;此時若你身邊有人,就會靈機一動,開始去關心他,彷彿剛剛的沉默對他失禮似的。
自我開始書寫以來,這些狀態似乎漸漸遠離、逝去了,或許正是因為我試著盡可能準確地描寫這些狀態。透過描寫,我開始去回憶它們,如同回憶我生命裡已經結束的一個階段,費力的回想與表達使我壓力重重,乃至過去幾週那些短暫的白日夢已經變得陌生。我時不時也會有這樣的「狀態」──日復一日的想法,那些多年來或數十年來重覆無數次機械式的原初想法,它們突然遠離,意識開始疼痛,它的內裡突然變得如此空洞。
如今這些都過去了,我已不再處於這樣的狀態。每當我書寫,必然會寫到過去,寫到一些歷練過的事,至少,在書寫的時候是這樣的。我從事文學,這份工作所顯現於外的實體存在,向來就是一個回憶與表達的機器。我之所以寫下我母親的故事,一來也是因為我認為自己比隨便一個陌生的採訪者更了解她,以及她死亡的緣由,那些採訪者也許能夠利用宗教、個體心理學或社會學的夢境解析表,毫不費力地解出這樁有趣的自殺案件;再者則是因為我自身的興趣,當我有些事情可做的時候,我就會復甦起來,最後則是因為我跟隨便一個前來採訪的局外人一樣,都把這場自殺當成是一件案例,即便我是以另一種方式。
當然這所有的理由都是信手拈來的,而且可以被其他同樣信手拈來的理由替換。有那樣的短暫時刻,我失語到了極點,並且渴望書寫這些時刻──那種渴望,與我一直以來的書寫的動機並無二致。
參加葬禮的時候,我在我母親的錢包裡找到一張郵局寄件憑證,編號四三二號。週五晚間,她在回家吞藥之前還還寄了一封掛號信到法蘭克福給我,裡面有一份遺囑副本。(為何要用快捷呢?)星期一我在同一家郵局打電話。那是她過世兩天半之後,我看見一卷貼有掛號標籤的黃色捲筒橫放在郵務人員面前──這段時間已經寄出了九封掛號信,此刻接下來的號碼是四百四十二號,這幅景象與我腦海中的數字竟如此相像,以至於我乍看之下覺得混亂,一時間以為一切都不是真的。想告訴別人這些事情的慾望,確實讓我笑顏逐開。那天是如此晴朗,雪色一片,我們吃著肝丸湯;「事情是這樣開始的……」──如果有人這樣開頭,一切就會像是杜撰的,我並不想脅迫聽眾與讀者親身體會,我只想給他們朗讀一段非常奇妙的故事。
我母親過世至今已經快七個星期了。在葬禮上我曾有強烈的慾望想書寫她,我希望這份渴望在還沒退回麻木無語之前就展開工作。那份麻木的無語,是我得知她自殺消息時的反應。是的,展開工作──因為,想書寫我母親的這份渴望,有時會突如其來,有時卻又飄忽不定,因此必須得很努力工作,才不至於讓我太隨心所欲,比如用打字機在紙上不斷敲著同一個字母。然而這種單調的反覆動作對我並沒有幫助,它只會使我更加消極與麻木。當然我也可以離開──在路上、旅途中,即便沒頭沒腦地瞌睡與閒蕩,也不至於讓自己無法忍受。
幾個星期以來,我比平常更容易被激怒,在混亂、寒冷與靜默之中幾乎無法與人交談,每當地上出現一點小毛球或麵包屑,我就彎下腰撿起來。有時我訝異於我所握住的東西並沒有早早從我的手裡落下;想及這場自殺的時候,我會突然變得無感。儘管如此,我仍渴望著那樣的時刻,因為如此一來,麻木感消失,我的頭腦一片清明。那份驚駭讓我又好多了──終於我不再百無聊賴,身體不再抵抗,沒有費力的疏遠,沒有令人傷痛的時光流逝。
在這種時候,最糟糕的莫過於他人的參與,即便是一道目光,甚或一句話。你只能馬上望向他處,或直截了當地堵住他的嘴;因為你需要那感覺──你正經歷的事,它令人費解也無法言傳。唯有如此,我們才會感到那份驚駭是真實且意味深長的。一旦談起這件事情,人們馬上又會覺得無趣,一切突然又變成虛空。然而,我偶爾會沒來由地向人們說起我母親的自殺,若他們妄加評論些什麼,我就會生氣起來,接著,我希望他們最好能轉移注意力,用甚麼其他的東西嘲笑我也好。
就好比詹姆士‧龐德在他最新的一部電影,人們問他,那位被他從樓梯欄杆上丟下去的對手是否死了,他回答:「但願是這樣!」這時我不由得輕鬆地笑了。我一點也不在意人們開死亡的玩笑,甚至這樣讓我覺得舒服。
驚恐的時刻總是非常短暫,更多是不真實的感受,在這些瞬間之後,一切又都閉鎖起來;此時若你身邊有人,就會靈機一動,開始去關心他,彷彿剛剛的沉默對他失禮似的。
自我開始書寫以來,這些狀態似乎漸漸遠離、逝去了,或許正是因為我試著盡可能準確地描寫這些狀態。透過描寫,我開始去回憶它們,如同回憶我生命裡已經結束的一個階段,費力的回想與表達使我壓力重重,乃至過去幾週那些短暫的白日夢已經變得陌生。我時不時也會有這樣的「狀態」──日復一日的想法,那些多年來或數十年來重覆無數次機械式的原初想法,它們突然遠離,意識開始疼痛,它的內裡突然變得如此空洞。
如今這些都過去了,我已不再處於這樣的狀態。每當我書寫,必然會寫到過去,寫到一些歷練過的事,至少,在書寫的時候是這樣的。我從事文學,這份工作所顯現於外的實體存在,向來就是一個回憶與表達的機器。我之所以寫下我母親的故事,一來也是因為我認為自己比隨便一個陌生的採訪者更了解她,以及她死亡的緣由,那些採訪者也許能夠利用宗教、個體心理學或社會學的夢境解析表,毫不費力地解出這樁有趣的自殺案件;再者則是因為我自身的興趣,當我有些事情可做的時候,我就會復甦起來,最後則是因為我跟隨便一個前來採訪的局外人一樣,都把這場自殺當成是一件案例,即便我是以另一種方式。
當然這所有的理由都是信手拈來的,而且可以被其他同樣信手拈來的理由替換。有那樣的短暫時刻,我失語到了極點,並且渴望書寫這些時刻──那種渴望,與我一直以來的書寫的動機並無二致。
參加葬禮的時候,我在我母親的錢包裡找到一張郵局寄件憑證,編號四三二號。週五晚間,她在回家吞藥之前還還寄了一封掛號信到法蘭克福給我,裡面有一份遺囑副本。(為何要用快捷呢?)星期一我在同一家郵局打電話。那是她過世兩天半之後,我看見一卷貼有掛號標籤的黃色捲筒橫放在郵務人員面前──這段時間已經寄出了九封掛號信,此刻接下來的號碼是四百四十二號,這幅景象與我腦海中的數字竟如此相像,以至於我乍看之下覺得混亂,一時間以為一切都不是真的。想告訴別人這些事情的慾望,確實讓我笑顏逐開。那天是如此晴朗,雪色一片,我們吃著肝丸湯;「事情是這樣開始的……」──如果有人這樣開頭,一切就會像是杜撰的,我並不想脅迫聽眾與讀者親身體會,我只想給他們朗讀一段非常奇妙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