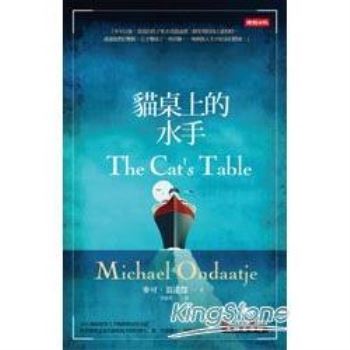我被要求要穿著整齊,才能去鋪著地毯的頭等艙見芙拉薇亞.普林斯。雖然她答應會在旅程中照顧我,但說實話,我們後來總共只見過幾次。現在我被邀請去跟她喝下午茶,她的紙條上還建議我穿乾淨而熨燙過的襯衫,還要穿襪子跟皮鞋。我在四點準時上來到「露台酒吧」。
她打量我,彷彿我在望遠鏡的另一頭似的,渾然不覺我可以清楚看到她的臉部反應。她坐在一張小桌子旁。接下來是她艱難地努力要跟我對話,而我因為緊張而只有單字的回應更無濟於事。我在航程中還開心嗎?我有沒有交到朋友?
我交到兩個朋友,我說。一個男孩子叫卡修斯,另一個叫拉瑪希。
「拉瑪希﹍是那個打板球的家庭,穆斯林的男孩子嗎?」
我說我不知道,但我會問他。我認識的拉瑪希似乎毫無運動方面的天分。他對甜點跟煉乳倒是充滿熱情。想到這裡,我趁著普林斯太太試圖引起服務生注意時,放了幾片餅乾到口袋裡。
「我在你父親還很年輕時就認識他了﹍」她說,但沒有把話說完。我點點頭,但她沒有再說任何關於他的話。
「阿姨﹍」我開口,因為終於知道該如何稱呼她而感到安心。「你知道那個囚犯的事嗎?」
結果證實她跟我一樣急著擺脫閒聊,於是她安頓下來,準備接受比她預期長一點的會面。「多喝點茶,」她喃喃說,於是我喝了一點,雖然我並不喜歡那味道。她透露說,她確實聽說過那個囚犯的事,儘管那本來應該是個祕密。「他受到很嚴密的看守。但是你不用擔心,船上甚至有一位非常資深的英國軍官。」
我等不及要靠過去。「我看過他,」我炫耀說。「在深夜時出來放風。有很嚴密的看守。」
「真的﹍」她拉長了聲音,面對我這麼快又這麼輕易拿出的王牌有點困窘。
「他們說他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我說。
「是,據說他殺了一個法官。」
這比王牌更厲害。我坐在那裡,嘴巴張著。
「一個英國法官。除此以外,我可能不應該多說了。」她補充說。
我的舅舅,我母親的弟弟,是我在可倫坡的監護人。他也是個法官,雖然他是錫蘭人,而不是英國人。英國法官不可以在這島上聽審,因此他應該是來參訪,或者來擔任顧問或諮詢﹍這些有些是芙拉薇亞.普林斯告訴我的,有些則是在頭腦冷靜又擅長邏輯的拉瑪希幫忙下,我們拼湊出來的。
那個囚犯可能是為了阻止那個法官幫忙起訴而殺了他,或許。我這時候實在很想跟我在可倫坡的舅舅說話。事實上我是擔心他自己說不定有生命危險。據說他殺了一個法官!這句話在我腦海裡隆隆作響。
我舅舅是個身軀龐大而個性親切的人。自從我母親好幾年前去了英國之後,我就一直跟他和他太太住在波拉雷葛穆瓦。雖然我們從來不曾有過任何或長或短的親密談天,而且他都忙於扮演公眾人物的角色,但他是個有愛心的人,我在他身邊也覺得很安全。他下班回家,幫自己倒一杯琴酒時,都會讓我負責搖配料,倒進他的杯子裡。我只有一次在他那裡惹上麻煩。那時他在審判一件涉及一個板球選手並引起轟動的謀殺案,而我對我的朋友宣佈說現在被視為被告的嫌犯是無辜的,而當我被問是怎麼知道時,我說是我舅舅說的。我之所以這樣說,與其是要說謊,不如說是因為想鞏固我對這個板球英雄的信心。我的舅舅聽到這件事時,只是不在意地笑了笑,但是堅定地建議我以後不要再這麼做。
回到D艙我的朋友身邊十分鐘後,我就開始款待卡修斯與拉瑪希,跟他們分享那個囚犯的犯罪故事。我在露天游泳池畔講這件事,在乒乓球桌旁也講。但是那天下午,藍斯葛提小姐因為聽到從我的故事傳播出去的漣漪,而攔住了我,讓我開始不那麼確定芙拉薇亞.普林斯所說的,關於這囚犯罪行的版本。「他可能有做,也可能沒有做這種事,」她說。「千萬不要相信可能只是謠言的事。」於是她讓我想到,或許芙拉薇亞.普林斯故意誇大了他的罪行,想要更勝一籌,因為我親眼看到了那個囚犯,所以她故意選擇了一件我可以認同的罪行──殺害法官。如果我舅舅是藥劑師,那她就會說他殺了藥劑師。
那天晚上,我在我的學校考試小冊子寫下第一次的記錄。先前在黛利拉廳,一個乘客在玩牌時攻擊了自己的太太,引發一場混亂。他們在玩紅心遊戲時的挖苦嘲笑變得太過火。他一度企圖勒死她,然後她的一隻耳朵被一根叉子刺穿。我設法跟在事務長後頭,看著他護送那太太穿過一條狹窄的走廊去醫護間,同時用一條餐巾壓在她耳朵上止血,而那丈夫則氣呼呼地大步走回他的船艙。
儘管這件事導致了宵禁,拉瑪希、卡修斯,跟我,當天晚上還是溜出我們的艙房,爬上燈光昏暗而危險的樓梯,等著那個囚犯出現。時間已經將近午夜,我們三個點燃了從一張藤椅上折斷脫落的小枝條,當作香煙吸著。拉瑪希因為有氣喘,因此對此不太熱中,但是卡修斯則興致勃勃,說我們應該在這趟旅程結束前,把整張椅子吸完。一小時後,很顯然囚犯的夜晚散步取消了。我們周圍一片漆黑,但是我們知道怎麼穿過其中。我們安靜地溜到游泳池裡,重新點燃小枝條,仰著背漂浮著。我們像屍體般安靜地望著星星。我們覺得像是游在海裡,而不是在大海當中被圍起來的一座池子裡。(待續)服務生跟我說過我有室友,但是至今仍沒有人來睡另一張床。然後,在第三天晚上,我們還在印度洋上時,艙房內的燈突然大亮,一個自稱是海斯提先生的男人腋下夾著一張折疊牌桌走進來。他叫醒我,把我一把抬到上層床鋪。「幾個朋友要過來玩牌,」他說:「你睡你的覺吧。」但我等著看是誰要來。半小時後,房間裡已經有四個男人安靜而認真地打起橋牌來。桌子周圍幾乎快容納不下他們所有人坐著。他們壓低音量是因為我,但是我很快就在他們叫牌的低語聲中入睡了。
第二天早上,我發現自己又是單獨一人。牌桌已經折起來,靠在牆邊。海斯提有睡覺嗎?他是純粹的乘客,還是船員的一員?結果他原來是負責奧蘭賽號上的犬舍,而且這必定不是多辛苦的工作,因為他大多時間都在看書,或心不在焉地在甲板上的一小塊區域遛狗。於是在午夜過後不久,他的朋友們就會加入他。其中的伊維尼爾先生是幫忙他管理犬舍的助手。另外兩個則是在船上當無線電操作員。他們每天晚上會打幾個小時的牌,然後就安靜地離開。
我鮮少單獨跟海斯提先生在一起。他午夜時出現時,一定覺得我需要休息了,所以他很少會試圖跟我講話,而其他人也都會在幾分鐘後就陸續出現。他經常在東方旅行,而在某個時候染上了穿紗龍的習慣,因此大多數時候他都只在腰間圍一條紗龍,甚至連他朋友來時也是。他會拿出四個烈酒杯,跟一些烈酒。酒瓶跟杯子都會放在地板上,桌上除了撲克牌以外全部都會清空。我會從我在上鋪的略高位置往下看,看到夢家攤開的牌。我看著他們發牌,聽著他們洗牌跟叫牌。不叫﹍一黑桃﹍不叫﹍二梅花﹍不叫﹍二無王牌﹍不叫﹍四方塊﹍不叫﹍五方塊﹍賭倍﹍再賭倍﹍不叫﹍不叫﹍不叫﹍他們很少對話。我記得他們以前都用姓氏彼此稱呼──「托洛先生,」「伊維尼爾先生,」「海斯提先生,」「巴博斯塔先生」──彷彿他們是十九世紀海軍學校裡的學生。
但在後來的航程裡,當我跟我朋友碰到海斯提先生時,他的行為就大不相同。在我們的艙房之外,他會有很多意見,而且經常講個不停。他告訴我們他在「商船大軍」工作的起起伏伏,他跟他一個傑出騎師的前妻的冒險,還有他對獵犬有遠超過對其他任何品種的狗的堅定感情。
但在我們的艙房裡,在午夜時的昏暗燈光下,海斯提先生只會輕聲細語;他在第三晚打牌之後,很有禮貌地將艙房裡明亮的黃色燈泡換成了黯淡的藍色燈光。所以當我進入半睡半醒的領域時,他們會倒著酒,打著一局局橋牌,交換著金錢,而藍色的光讓這些男人都像是在水族箱裡。打完牌之後,他們四個人會去到甲板上抽煙。半小時後,海斯提先生會安靜地溜回房間裡,看一會書,然後才關掉他的床頭燈。(待續)對於有朋友可以碰面的男孩子來說,睡眠就如牢獄。我們對於夜晚很不耐煩,在日出包圍船之前就已經起床。我們迫不及待地想去探索這個宇宙。我躺在床上時,會聽到拉瑪希在門上輕輕的敲門聲,是個暗號。但這暗號實際上毫無意義──這種時間還會是誰?敲兩下,一個長停頓,然後再敲一下。如果我還沒有爬下來開門,就會聽到他做作的咳嗽聲。如果我還是沒應門,就會聽到他低聲說:「九官鳥」,這也變成了我的綽號。
我們會在樓梯旁跟卡修斯碰面,之後不久就會光著腳在頭等艙漫步。頭等艙在早上六點鐘時是無人守衛的宮殿,而我們會在燃燒的光線出現在水平線之前,甚至在甲板上必要的夜燈在破曉時自動閃爍並熄滅之前,就來到這裡。我們脫掉上衣,像針一般鑽入漆成金色的頭等艙游泳池裡,幾乎不激起一絲水花。當我們在剛剛形成的半暗光線中游泳,安靜是絕對必要的。
如果我們可以撐到一小時不被發現,就有機會去掠奪在日光甲板上陳列開來的早餐,把食物高高地疊在盤子上,並偷偷帶走盛著煉乳的銀碗,碗中央的湯匙直挺挺地立在濃稠的煉乳當中。然後我們會爬上吊起的一艘救生艇裡,鑽進帳篷一般的天幕中,享用我們用不正當手段得來的大餐。有一天早上,卡修斯還帶來他在一間交誼廳找到的「金葉」香煙,而教我們如何正確地抽煙。
拉瑪希客氣地拒絕了,因為氣喘的關係,而且他的症狀在我們跟貓桌上其他食客眼中都很明顯。(幾年後我在倫敦見到他時,他的症狀仍是如此明顯。當時我們都已經十三歲或十四歲了,在因為忙著適應異鄉而失去對方的蹤影之後,又再度碰面。即使到這時候,每次我去找他跟他父母與他妹妹瑪西時,他還是不斷染上鄰里間流行的咳嗽或感冒。我們會在英國開始第二段友誼,但這時我們都已經變得不一樣,不再自由自在,不受這世界的現實束縛。而且在某些方面,那時候我跟他妹妹還比較親近,因為瑪西都會陪著我們穿過倫敦南方────到荷倫丘的腳踏車道,到布瑞斯登的麗池電影院,然後到「好市集賣場」,我們會在那裡的食物跟服飾走道奔跑,莫名地亢奮。有些午後,我會跟瑪西坐在他父母位於米爾丘的家裡的一張小沙發上,兩人放在毯子下的手爬到對方身上,一邊假裝看著電視上永無止盡的高爾夫球賽報導。有一天一大早,她來到我跟拉瑪希一起睡的樓上的房間,坐到我床邊,一隻手指伸到她的嘴唇上示意我安靜。拉瑪希就睡在幾呎之外他的床上。我想要起身,但是她一隻手掌把我壓回去,然後開始解開她睡衣上衣的鈕扣,讓我能看到她剛發育的胸部,在窗外樹的倒影中幾乎像是淺綠色。接下來的時間裡,我很清楚地意識到拉瑪希的咳嗽,還有他在睡夢中清喉嚨的吱軋聲,而瑪西,半裸著,充滿恐懼,又無所畏懼地,面對著我,懷著一個人在十三歲做出這樣的姿態時可能會有的任何情緒。)
我們把跟著食物一起偷拿來的餐盤餐刀跟湯匙留在救生艇裡,然後溜回去經濟艙。在之後的一次安全演習中,當船員爬上了救生艇,並把救生艇盪到水面上時,一個服務生終於發現了我們無數次早餐留下的痕跡,也因此有一段時間,船長都要求找尋船上是否有一個偷渡客。
我們越過邊界,從頭等艙回到經濟艙時,甚至還不到八點。我們假裝跟著船的擺動而步履蹣跚。這時候我已經愛上我們的船不斷從一邊晃到一邊的緩慢華爾滋。而除了距離遙遠的芙拉薇亞.普林斯跟愛蜜麗以外,我是單獨一個人這件事,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冒險。我沒有對家庭的責任。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而且拉瑪希、卡修斯跟我已經建立了我們自己的規矩。我們每天至少要做一件被禁止的事。一天才剛剛開始,我們眼前還有許多個小時可以完成這項任務。(待續)我父母拋棄他們的婚姻時,從來沒有人承認,或解釋,但是也沒有隱藏。這件事甚至被當成只是踏錯一步,而非重大事故。所以我父母離婚的詛咒有多少落在我身上,我也不確定。我不記得承擔著那件事的重量。一個男孩子每天早上出門後,就會忙著探索他世界裡不斷開展的地圖。但那確實是很不安定的青春。
我在拉維尼亞山的聖湯瑪斯學院當小寄宿學生時,就很熱愛游泳。我熱愛任何跟水有關的事。校地裡有一條水泥溝渠,豪雨季節的洪水會在溝中急速奔流。這裡因此成為有些寄宿生會參加的一個遊戲的地點。我們會跳進水裡,被洪流帶著往前衝,翻滾,被從一邊丟到另一邊。在下游五十碼處有一條灰色的繩索,讓我們可以抓住繩索,把自己拉上來。在這之後再二十碼,這充滿急速水流的水溝就會變成暗溝,消失在地底下,一直通往黑暗中。到底它通往哪裡,我們始終不知道。
我們可能總共有四個人,會一次又一次地被水溝的洪水往下沖,頭幾乎無法浮在水面上。這是個讓人緊張的遊戲,抓住繩索,爬上來,然後在大雨中再跑回去再來一次。有一次我在靠近繩索時頭沈到水裡,來不及上來抓住繩子。我的手伸在空中,在我快速衝向最終埋在地下的暗溝時,那是我唯一露出來的地方。這就是我註定的死期,那天下午在拉維尼亞山,在三月的豪雨季節當中,如一個占星家預告的。我當時九歲,而即將面臨一趟什麼都看不見的旅程,進入黑暗的地底。一隻手抓住了我還高舉的一隻手臂,我被一個年紀較大的學生拉了起來。他不太在意地叫我們四個離開,然後就在雨中匆匆離開,也沒有多看我們是否聽了他的話。他是誰?我應該說:謝謝你。但是我只是渾身溼透地躺在草地上,喘著氣。
我在那些日子裡是什麼樣子?我沒有來自外界的印記,因此也沒有對自己的認知。如果我必須捏造出一張我自己小時候的照片,應該會是一個光著腳的男孩子,穿著短褲跟棉襯衫,跟幾個村子裡的朋友,在波拉雷葛穆瓦,沿著分隔高原路上車輛與屋子跟花園的發霉牆壁旁,奔跑著。或者也可能只有我一個人,等著他們,眼睛從屋子望向塵土漫佈的街道。
誰明白野生放養的孩子有多滿足?我一出了門,家庭的掌控就立刻鬆脫了。雖然我們自己一定也曾經試圖理解並拼湊出成人的世界,想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為什麼。但是一旦我們走上舷梯,登上奧蘭賽號,我們才一次出於必要地跟大人近距離交鋒。
瑪薩帕
我在跟一個年老的乘客解釋只要兩個動作就能把折疊椅打開的藝術時,瑪薩帕先生悄悄走到我旁邊,手臂挽住我的手臂,要我跟他走。「『從納奇茲到木比耳,』」他警告我,「『從曼斐斯到聖喬伊』﹍」他看到我一臉困惑而停頓下來。
瑪薩帕先生總是突然出現,讓我猝不及防。我在游泳池裡游完一圈時,他會蹲在那裡,抓住我滑溜溜的手臂,把我抓在池邊。「聽我說,你這奇特的孩子,『女人會對你甜言蜜語,睜著無辜的大眼睛』﹍我是在用我的人生經驗保護你。」但是十一歲的我並不覺得受到保護,反而因為知道這些可能而預先受傷。當他跟我們三個人講時更是糟糕,簡直像是世界末日。「我上次旅行回家時,發現一頭新來的騾子在我的地盤撒野﹍你們知道我的意思吧?」我們並不知道。直到他解釋後才明白。但是大多數時候,他都只跟我說話,彷彿只有在我這個「奇特」的男孩子身上,他才能留下印記。在這方面,他可能是對的。
馬克.瑪薩帕會在中午醒來,在黛利拉酒吧吃早餐。「給我兩個『單眼法老煎蛋土司』,跟一瓶納許牌汽水,沒錯,」他會說,一邊嚼幾個配雞尾酒的櫻桃,等著服務生上菜。吃完飯後,他會拿著他的爪哇咖啡到舞廳的鋼琴旁,把杯子放在高音部的琴鍵上。接著,隨著鋼琴和絃推著他向前時,他會對剛好在他旁邊的任何人上課,讓他們認識這個世界上重要而複雜的細節。某一天,課程可能是關於什麼時候應該戴帽子,或者關於拼字。「英文真是無可救藥的語言。無可救藥!拿『埃及』(Egypt)這個字來說吧。就是個大問題。我告訴你怎麼樣才可以每次都拼對。只要對自己背誦『永遠抓好你珍貴的奶子』(Ever Grasping Your Precious Tits)就好。」結果確實,我從來不曾忘記這個句子。甚至在我現在寫這段話時,我還會潛意識地猶豫一下,而在腦海裡大寫這些字母。(待續)但是大多時候,他都是挖出他的音樂知識,解釋四分之三拍的複雜之處,或回憶起他在某一個後台樓梯上跟某個很吸引人的女高音學的某一首歌。所以我們像在接收某種狂熱的傳記。「『我搭火車去旅行,而我想到你,』」他咕噥唱著,而我們以為聽到的是他哀傷憔悴的心。但是今天我知道馬克.瑪薩帕是熱愛結構與旋律的細節,因為並非他人生拜苦路上的每一站都跟失敗的愛情有關。
他是一半西西里血統,一半其他血統,他用他無法追蹤的口音告訴我們。他曾經在歐洲工作,也曾短暫地旅行到南北美洲,甚至到更遠的地方,直到他發現自己來到熱帶,住在一個港口酒吧上面。他教我們〈香港藍調〉的副歌。他有一肚子的歌曲跟人生故事,事實與虛構緊密地融合在一起,讓我們難以分辨。要哄騙我們三個很容易,畢竟我們都是如此赤裸而天真。而且,一天下午,當海上的陽光潑灑在舞廳的地板上時,瑪薩帕先生隨著鋼琴音符喃喃唱著的,有些歌曲中的有些字眼,是我們根本沒聽過的。
賤人。子宮。
他是在跟三個即將邁入青春期的男孩子講話,而他可能很清楚自己擁有的影響力。但是他也傳授給這群年輕的聽眾關於音樂榮耀的故事,而他最讚頌的人莫過於席尼.貝雪。他在巴黎演奏一首曲子時,被指控吹錯了一個音。他的反應是挑戰指控他的人跟他決鬥,卻在接下來的騷動中誤傷一位路人,而被丟進牢裡,遣送回國。「『偉大的貝雪』──他們叫他『暴雪』。你們幾個孩子可能活一輩子,」瑪薩帕說,「都不會看到有人像他這樣捍衛自己的原則。」
我們很著迷,也很驚異於瑪薩帕的歌曲、嘆息,跟閒聊,描繪出的是這樣無邊無際的巨大的愛的戲劇。我們都認定,他之所以在職業生涯中摔了致命一跤,一定是因為受到欺騙,或者因為他對女人的太強烈的愛。
「每個月,月圓月缺。
我說,每個月,月圓月缺。
血液從那賤人的子宮湧出。」
瑪薩帕那天下午唱的歌,感覺有些超越塵世而且難以抹滅,不論那些字句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們只聽了一次,但它就藏在我們心底,像是如石頭堅硬的真相,我們會持續繞路避開這坦率直接的真相,就像我們當時避開一樣。這歌詞(後來我會發現歌詞作者是傑利.羅伊.莫頓)是刀槍不入又滴水不進的。但是我們當時並不明白,因為它的直接讓我們太困惑──那最後一句的字眼,它令人吃驚而致命的韻腳,在重複的開場之後,來得如此精簡有力。我們從他在舞廳裡的身影前消失,突然間意識到服務生站在梯子上為今晚的舞會準備,調整彩色燈光的方向,拉起交錯縱橫在房間上方的,拱形的皺紋彩紙。他們啪啪作響地拉開龐大的白色桌巾,蓋在木頭桌上。在每一張桌子的中央,他們放上一只插著花的花瓶,讓空蕩的房間變得文明而浪漫。瑪薩帕先生沒有跟我們一起離開。他待在鋼琴前,望著琴鍵,沒有察覺在他周圍進行的偽裝。我們知道,不論他今晚要跟交響樂團演奏什麼,都不會是他剛剛為我們演奏的。
馬克.瑪薩帕的藝名──或者如他自己所說的「戰名」──是「陽光草原」。自從有一次他在法國演出時,宣傳海報的印刷出錯之後,他就開始用這個名字。或許當時的舉辦人是想避開他帶有黎凡特地區味道的姓氏。在奧蘭賽號上,船上公佈欄貼出的他的鋼琴課的告示也是稱他為「陽光草原,鋼琴大師」。但是他對於我們這些貓桌的人而言,還是瑪薩帕先生,因為「陽光」跟「草原」實在不是能跟他的本質並存的字眼。他身上並沒有太多樂觀或修剪平整的特質。但是他對音樂的熱情讓我們這桌充滿活力。有一次吃午餐時,他整頓飯都在講「偉大的貝許」決鬥的故事,讓我們大飽耳福。那場一九二八年凌晨時分發生在巴黎的決鬥後來演變成比較像是槍戰──貝許朝著指控他的麥肯垂克的方向開槍,但是子彈擦過他的義大利波沙利諾牌帽子,接著繼續飛行,直到它嵌進一個正要去上班的法國女人的大腿裡。瑪薩帕先生從頭演到尾,用了鹽巴罐跟胡椒罐,還有一片起司,來描繪那子彈飛行的路線。
他有一天下午邀我到他的艙房去聽一些唱片。瑪薩帕告訴我,貝許用的是亞柏特系統的豎笛,而有比較正式而華麗的音色。「正式而華麗,」他一直重複說。他放上一張七十八轉的唱片,跟著音樂低語,指出那些幾乎不可能的變奏與裝飾音。「你聽,他用顫音讓聲音更出來。」我聽不懂,但是肅然起敬。貝許每次重複旋律時,瑪薩帕都會對我示意,「就像陽光照在森林的地上,」我記得他說。他在一個看來很蒼白的行李箱裡翻找,拿出一本書,然後唸出貝許跟一個學生講過的話:「我今天要給你一個音符,」貝許說。「看看你可以用多少種方法吹這個音符──用咆哮的,用塗抹的,把它壓平,讓它變尖銳,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就跟說話一樣。」
然後瑪薩帕告訴我關於那隻狗的事。「牠之前都會跟著貝許上台,在牠的主人演奏時嚎叫﹍也就是因為這樣,貝許才會跟艾林頓公爵(Duke Ellington)拆夥。因為公爵不讓古拉上台,站在燈光下,穿著牠的白色西裝搶盡風頭。」因此為了古拉,貝許離開了艾林頓的樂團,開了「南方裁縫店」,做清潔跟修補的生意,也是音樂家聚集的地方。「他最好的唱片都是在這時候錄的──例如『黑棍子』,『甜心親愛的』。有一天你一定要買齊他所有的唱片。」
然後還有他的性生活。「喔,貝許喜歡重複,最後經常又跟同一個女人在一起﹍各式各樣的女人都想要馴服他。但是你知道,他從十六歲就開始到處去巡迴演奏了,他早就碰過有各種習氣,各種目的的女孩子。」各種習氣與各種目的!從納奇茲到木比耳﹍
我聽著,不了解地點著頭,而瑪薩帕先生則將這種生活方式與音樂技能的楷模緊緊攬在心頭,彷彿它們是裝在一個橢圓形的聖人肖像裡。(待續)C艙
我坐在床鋪上,看著門跟金屬的牆面。傍晚的艙房裡很熱。但我只有在這個時間來這裡,才能獨自一個人。白天大多時間我都忙著跟拉瑪希和卡修斯在一起,有時候是跟瑪薩帕或貓桌上其他的人。而在晚上我經常被我房間裡玩牌的人的低語圍繞。我需要花點時間回想一下。回想一下,讓我記起獨自好奇的舒適。過了一會,我會躺下來,看著上頭距離一兩呎的天花板。我覺得安全,即使我是在大海當中。
有時候,就在黑暗降臨前,我會發現自己單獨在C艙甲板,沒有別人在那裡。我會走到高度到我胸口的欄杆前,看著海水在船身旁奔流。有時候海水會漲到幾乎跟我一樣高,彷彿想將我猛然拉走。我動也不動,即使心裡充滿騷動的恐懼與孤獨。當我在可倫坡郊區的佩塔市場的狹窄巷道裡迷路,或要適應學校裡新的未知的規矩時,也是這樣的情緒。當我看不到海洋時,恐懼就不存在,但是現在海洋在晦暗的光線中升起,包圍住船,在我周圍盤旋纏繞。不論多害怕,我都待在原地,鄰近著匆匆流過的黑暗,一半想將自己往後拉,一半渴望著往前跳進去。
有一次,在我離開錫蘭之前,我看到一艘郵輪在可倫坡港口的遠處燃燒著。整個下午,我看著藍色的乙炔切進那艘船的側腹。我明白我現在所在的這艘船也可能被切成一片片。有一天,我看到懂這些事情的納維爾先生,於是拉了拉他的袖子,問他我們是否安全。他告訴我,奧蘭賽號健康狀況良好,才到它職業生涯的一半而已。它曾經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擔任過軍艦,而在貨艙的某一面牆上,還有一幅很大的粉紅色跟白色的壁畫,畫著裸體女人跨坐在槍炮架上跟坦克上,是一個士兵畫的。那幅畫還在,但是個祕密,因為船上的官員從來不會進去貨艙。
「但是我們不會有事?」
他叫我坐下來,然後在他總是隨身攜帶的藍圖的背面,畫給我看他所說的希臘戰艦,一艘三層槳座的戰船。「這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海船。即使它已經不存在了。它對抗了雅典的敵人,帶回不知名的水果跟作物、新的科學、建築,甚至民主制度。一切都是因為這艘船。它沒有任何裝飾。三層槳座戰船完全忠於它自己──它是一個武器。上面只有划槳手跟弓箭手。但是現在已經找不到這種船的任何痕跡。很多人還在河口的淤泥中尋找這種船,但至今沒有找到任何一艘。它們是用白楊木跟硬的榆木作成,龍骨則是用橡木作成,然後用綠松木彎曲作成骨架。船板是用亞麻繩縫在一起。整個骨架都沒有任何金屬。所以這種船可以在沙灘上燒掉,如果沈到海裡也會完全融解消失。我們的船安全多了。」
不知為何,納維爾先生對一艘古老戰船的描述讓我感到安心。我不再想像自己身在裝飾華麗的奧蘭賽號上,而是在比較自給自足,比較儉約簡單的船上。我是在三層槳座戰船上的划槳手或弓箭手。我們會以這樣的姿態進入阿拉伯海,然後是地中海,而納維爾先生是我們的軍艦指揮官。
那天晚上我突然醒來,我覺得我們正在經過島嶼,而那些島嶼在黑暗中非常靠近。船旁的海浪有種不同的聲響,某種回音的感覺,彷彿它們在回應土地。我打開床旁的黃色燈光,看著我從一本書上描下來的世界地圖。我忘了在地圖上寫下地名。我只知道我們正往西往北前進,遠離可倫坡。(待續)一個澳大利亞人
在破曉前的時刻,當我們已經起床在彷彿空無一人的船上晃蕩時,洞穴般的沙龍會充滿前晚香煙的味道,而拉瑪希、卡修斯跟我已經推著手推車衝來衝去,讓原本寂靜的圖書室吵翻了天。有一天早上,我們突然發現一個穿著溜冰輪鞋的女孩子沿著上甲板的木板周圍,繞著我們飛馳。她似乎一直都比我們更早起床。她滑得越來越快,流暢的步伐考驗著她的平衡,而她似乎完全不理會我們的存在。但在一次轉彎時,她算錯了在轉角跳起,越過錨索的時間,而一頭撞上船尾的欄杆。她站起來,看了一下膝蓋上一道血痕,然後又繼續滑,並瞄了一眼她的手錶。她是澳大利亞人,而我們都被迷住了。我們從來沒目睹過這樣強烈的決心。我們的家庭裡的女性成員都不會這個樣子。後來我們在游泳池裡認出她,她飛速前進,激起連珠炮般的水花。如果她從奧蘭賽號跳入海中,在船旁邊游泳,跟著船同步前進二十分鐘,我們也不會感到驚訝。
我們因此開始起得更早,好看她溜那五十圈或六十圈。溜完之後,她會解開鞋帶,脫掉她的溜冰輪鞋,筋疲力竭滿身大汗,而且完全不脫衣服地走向戶外的淋浴間。她會站在那湧出而噴濺的水中,向左向右地甩著頭,像是一頭穿著衣服的動物。這是一種新的美麗。當她離開時,我們會追蹤著她的腳印,而在我們接近腳印時,它們就已經在新生的陽光中蒸發了。
卡修斯
我現在想到,誰會把孩子取名叫卡修斯。大多數父母都會避免給第一個孩子取這樣的名字。雖然斯里蘭卡一向喜愛結合古典的名字跟錫蘭語的姓氏──所羅門跟賽納卡 ,並不常見,但確實存在。我們的家庭小兒科醫生就叫做蘇格拉底.古納瓦德納。卡修斯這個名字雖然在羅馬時代名聲不佳 ,卻是個唸起來溫和有如低語的名字,不過我在這旅途中認識的年少卡修斯卻相當反偶像崇拜。我從來沒看過他依附任何有權勢的人。他會吸引你採用他對事物的觀點,讓你經由他的眼睛看到這船上的權力階層。例如他就很樂意自己是坐在貓桌的毫無地位的人物。
卡修斯講到拉維尼亞山上的聖湯瑪斯學院時,所流露的精力有如一個人在回憶一場反抗運動。他在學校高我一個年級,因此感覺我們像是分處兩個世界,但是他是年紀較小的學生的燈塔,因為他鮮少被抓到為非作歹。而且當他真的被抓到時,他臉上也不會露出一絲羞愧或謙卑的痕跡。他後來更是名聲大噪,因為他有一次設法把我們的舍監,「竹條」巴納巴斯,鎖在小學的廁所裡好幾個小時,抗議學校裡令人作嘔的廁所(你要蹲在那恐怖的洞上方,然後在完事之後,用一個已經生銹的,泰萊牌金黃糖漿罐子裡的水,清洗自己。「甜的從強者出來,」 我後來永遠記得這糖漿的廣告詞。)
卡修斯一直等到巴納巴斯在早上六點,他慣常蹲廁所的時間,進入地面層的學生廁所後,用一根鐵桿抵住門,接著再用快乾水泥將門鎖包起來。我們聽著我們的舍監用身體撞門。然後他開始喊我們的名字,從他信任的學生喊起。我們每個人都回應說會過去幫忙,但都溜到操場上,不得不到樹叢後去解放,接著有人去游泳,有人則是乖乖地去上早上七點鐘的自習課,這堂課事實上是巴納巴斯神父在那個學期稍早時開始規定的。後來是一個工友不得不用一根板球的球門柱子把水泥敲碎,但那已經是到接近傍晚的時候。我們本來希望到那時候我們的舍監已經被臭氣薰得受不了,昏過去而無法言語。
但是他的復仇行動迅速展開。卡修斯被打了一頓,然後停學一週,但他反而更成為小學部學生的偶像,尤其是因為校長在早晨禮拜的一場令人激動的演說中,整整譴責了他兩分鐘,彷彿他是墮落的天使一般。當然,這件事沒有帶來任何教訓──對任何人都是如此。許多年後,當一個老校友捐錢給聖湯瑪斯學院蓋一座新的板球球場看台時,我的朋友賽納卡說:「他們首先應該蓋幾間像樣的廁所。」
她打量我,彷彿我在望遠鏡的另一頭似的,渾然不覺我可以清楚看到她的臉部反應。她坐在一張小桌子旁。接下來是她艱難地努力要跟我對話,而我因為緊張而只有單字的回應更無濟於事。我在航程中還開心嗎?我有沒有交到朋友?
我交到兩個朋友,我說。一個男孩子叫卡修斯,另一個叫拉瑪希。
「拉瑪希﹍是那個打板球的家庭,穆斯林的男孩子嗎?」
我說我不知道,但我會問他。我認識的拉瑪希似乎毫無運動方面的天分。他對甜點跟煉乳倒是充滿熱情。想到這裡,我趁著普林斯太太試圖引起服務生注意時,放了幾片餅乾到口袋裡。
「我在你父親還很年輕時就認識他了﹍」她說,但沒有把話說完。我點點頭,但她沒有再說任何關於他的話。
「阿姨﹍」我開口,因為終於知道該如何稱呼她而感到安心。「你知道那個囚犯的事嗎?」
結果證實她跟我一樣急著擺脫閒聊,於是她安頓下來,準備接受比她預期長一點的會面。「多喝點茶,」她喃喃說,於是我喝了一點,雖然我並不喜歡那味道。她透露說,她確實聽說過那個囚犯的事,儘管那本來應該是個祕密。「他受到很嚴密的看守。但是你不用擔心,船上甚至有一位非常資深的英國軍官。」
我等不及要靠過去。「我看過他,」我炫耀說。「在深夜時出來放風。有很嚴密的看守。」
「真的﹍」她拉長了聲音,面對我這麼快又這麼輕易拿出的王牌有點困窘。
「他們說他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我說。
「是,據說他殺了一個法官。」
這比王牌更厲害。我坐在那裡,嘴巴張著。
「一個英國法官。除此以外,我可能不應該多說了。」她補充說。
我的舅舅,我母親的弟弟,是我在可倫坡的監護人。他也是個法官,雖然他是錫蘭人,而不是英國人。英國法官不可以在這島上聽審,因此他應該是來參訪,或者來擔任顧問或諮詢﹍這些有些是芙拉薇亞.普林斯告訴我的,有些則是在頭腦冷靜又擅長邏輯的拉瑪希幫忙下,我們拼湊出來的。
那個囚犯可能是為了阻止那個法官幫忙起訴而殺了他,或許。我這時候實在很想跟我在可倫坡的舅舅說話。事實上我是擔心他自己說不定有生命危險。據說他殺了一個法官!這句話在我腦海裡隆隆作響。
我舅舅是個身軀龐大而個性親切的人。自從我母親好幾年前去了英國之後,我就一直跟他和他太太住在波拉雷葛穆瓦。雖然我們從來不曾有過任何或長或短的親密談天,而且他都忙於扮演公眾人物的角色,但他是個有愛心的人,我在他身邊也覺得很安全。他下班回家,幫自己倒一杯琴酒時,都會讓我負責搖配料,倒進他的杯子裡。我只有一次在他那裡惹上麻煩。那時他在審判一件涉及一個板球選手並引起轟動的謀殺案,而我對我的朋友宣佈說現在被視為被告的嫌犯是無辜的,而當我被問是怎麼知道時,我說是我舅舅說的。我之所以這樣說,與其是要說謊,不如說是因為想鞏固我對這個板球英雄的信心。我的舅舅聽到這件事時,只是不在意地笑了笑,但是堅定地建議我以後不要再這麼做。
回到D艙我的朋友身邊十分鐘後,我就開始款待卡修斯與拉瑪希,跟他們分享那個囚犯的犯罪故事。我在露天游泳池畔講這件事,在乒乓球桌旁也講。但是那天下午,藍斯葛提小姐因為聽到從我的故事傳播出去的漣漪,而攔住了我,讓我開始不那麼確定芙拉薇亞.普林斯所說的,關於這囚犯罪行的版本。「他可能有做,也可能沒有做這種事,」她說。「千萬不要相信可能只是謠言的事。」於是她讓我想到,或許芙拉薇亞.普林斯故意誇大了他的罪行,想要更勝一籌,因為我親眼看到了那個囚犯,所以她故意選擇了一件我可以認同的罪行──殺害法官。如果我舅舅是藥劑師,那她就會說他殺了藥劑師。
那天晚上,我在我的學校考試小冊子寫下第一次的記錄。先前在黛利拉廳,一個乘客在玩牌時攻擊了自己的太太,引發一場混亂。他們在玩紅心遊戲時的挖苦嘲笑變得太過火。他一度企圖勒死她,然後她的一隻耳朵被一根叉子刺穿。我設法跟在事務長後頭,看著他護送那太太穿過一條狹窄的走廊去醫護間,同時用一條餐巾壓在她耳朵上止血,而那丈夫則氣呼呼地大步走回他的船艙。
儘管這件事導致了宵禁,拉瑪希、卡修斯,跟我,當天晚上還是溜出我們的艙房,爬上燈光昏暗而危險的樓梯,等著那個囚犯出現。時間已經將近午夜,我們三個點燃了從一張藤椅上折斷脫落的小枝條,當作香煙吸著。拉瑪希因為有氣喘,因此對此不太熱中,但是卡修斯則興致勃勃,說我們應該在這趟旅程結束前,把整張椅子吸完。一小時後,很顯然囚犯的夜晚散步取消了。我們周圍一片漆黑,但是我們知道怎麼穿過其中。我們安靜地溜到游泳池裡,重新點燃小枝條,仰著背漂浮著。我們像屍體般安靜地望著星星。我們覺得像是游在海裡,而不是在大海當中被圍起來的一座池子裡。(待續)服務生跟我說過我有室友,但是至今仍沒有人來睡另一張床。然後,在第三天晚上,我們還在印度洋上時,艙房內的燈突然大亮,一個自稱是海斯提先生的男人腋下夾著一張折疊牌桌走進來。他叫醒我,把我一把抬到上層床鋪。「幾個朋友要過來玩牌,」他說:「你睡你的覺吧。」但我等著看是誰要來。半小時後,房間裡已經有四個男人安靜而認真地打起橋牌來。桌子周圍幾乎快容納不下他們所有人坐著。他們壓低音量是因為我,但是我很快就在他們叫牌的低語聲中入睡了。
第二天早上,我發現自己又是單獨一人。牌桌已經折起來,靠在牆邊。海斯提有睡覺嗎?他是純粹的乘客,還是船員的一員?結果他原來是負責奧蘭賽號上的犬舍,而且這必定不是多辛苦的工作,因為他大多時間都在看書,或心不在焉地在甲板上的一小塊區域遛狗。於是在午夜過後不久,他的朋友們就會加入他。其中的伊維尼爾先生是幫忙他管理犬舍的助手。另外兩個則是在船上當無線電操作員。他們每天晚上會打幾個小時的牌,然後就安靜地離開。
我鮮少單獨跟海斯提先生在一起。他午夜時出現時,一定覺得我需要休息了,所以他很少會試圖跟我講話,而其他人也都會在幾分鐘後就陸續出現。他經常在東方旅行,而在某個時候染上了穿紗龍的習慣,因此大多數時候他都只在腰間圍一條紗龍,甚至連他朋友來時也是。他會拿出四個烈酒杯,跟一些烈酒。酒瓶跟杯子都會放在地板上,桌上除了撲克牌以外全部都會清空。我會從我在上鋪的略高位置往下看,看到夢家攤開的牌。我看著他們發牌,聽著他們洗牌跟叫牌。不叫﹍一黑桃﹍不叫﹍二梅花﹍不叫﹍二無王牌﹍不叫﹍四方塊﹍不叫﹍五方塊﹍賭倍﹍再賭倍﹍不叫﹍不叫﹍不叫﹍他們很少對話。我記得他們以前都用姓氏彼此稱呼──「托洛先生,」「伊維尼爾先生,」「海斯提先生,」「巴博斯塔先生」──彷彿他們是十九世紀海軍學校裡的學生。
但在後來的航程裡,當我跟我朋友碰到海斯提先生時,他的行為就大不相同。在我們的艙房之外,他會有很多意見,而且經常講個不停。他告訴我們他在「商船大軍」工作的起起伏伏,他跟他一個傑出騎師的前妻的冒險,還有他對獵犬有遠超過對其他任何品種的狗的堅定感情。
但在我們的艙房裡,在午夜時的昏暗燈光下,海斯提先生只會輕聲細語;他在第三晚打牌之後,很有禮貌地將艙房裡明亮的黃色燈泡換成了黯淡的藍色燈光。所以當我進入半睡半醒的領域時,他們會倒著酒,打著一局局橋牌,交換著金錢,而藍色的光讓這些男人都像是在水族箱裡。打完牌之後,他們四個人會去到甲板上抽煙。半小時後,海斯提先生會安靜地溜回房間裡,看一會書,然後才關掉他的床頭燈。(待續)對於有朋友可以碰面的男孩子來說,睡眠就如牢獄。我們對於夜晚很不耐煩,在日出包圍船之前就已經起床。我們迫不及待地想去探索這個宇宙。我躺在床上時,會聽到拉瑪希在門上輕輕的敲門聲,是個暗號。但這暗號實際上毫無意義──這種時間還會是誰?敲兩下,一個長停頓,然後再敲一下。如果我還沒有爬下來開門,就會聽到他做作的咳嗽聲。如果我還是沒應門,就會聽到他低聲說:「九官鳥」,這也變成了我的綽號。
我們會在樓梯旁跟卡修斯碰面,之後不久就會光著腳在頭等艙漫步。頭等艙在早上六點鐘時是無人守衛的宮殿,而我們會在燃燒的光線出現在水平線之前,甚至在甲板上必要的夜燈在破曉時自動閃爍並熄滅之前,就來到這裡。我們脫掉上衣,像針一般鑽入漆成金色的頭等艙游泳池裡,幾乎不激起一絲水花。當我們在剛剛形成的半暗光線中游泳,安靜是絕對必要的。
如果我們可以撐到一小時不被發現,就有機會去掠奪在日光甲板上陳列開來的早餐,把食物高高地疊在盤子上,並偷偷帶走盛著煉乳的銀碗,碗中央的湯匙直挺挺地立在濃稠的煉乳當中。然後我們會爬上吊起的一艘救生艇裡,鑽進帳篷一般的天幕中,享用我們用不正當手段得來的大餐。有一天早上,卡修斯還帶來他在一間交誼廳找到的「金葉」香煙,而教我們如何正確地抽煙。
拉瑪希客氣地拒絕了,因為氣喘的關係,而且他的症狀在我們跟貓桌上其他食客眼中都很明顯。(幾年後我在倫敦見到他時,他的症狀仍是如此明顯。當時我們都已經十三歲或十四歲了,在因為忙著適應異鄉而失去對方的蹤影之後,又再度碰面。即使到這時候,每次我去找他跟他父母與他妹妹瑪西時,他還是不斷染上鄰里間流行的咳嗽或感冒。我們會在英國開始第二段友誼,但這時我們都已經變得不一樣,不再自由自在,不受這世界的現實束縛。而且在某些方面,那時候我跟他妹妹還比較親近,因為瑪西都會陪著我們穿過倫敦南方────到荷倫丘的腳踏車道,到布瑞斯登的麗池電影院,然後到「好市集賣場」,我們會在那裡的食物跟服飾走道奔跑,莫名地亢奮。有些午後,我會跟瑪西坐在他父母位於米爾丘的家裡的一張小沙發上,兩人放在毯子下的手爬到對方身上,一邊假裝看著電視上永無止盡的高爾夫球賽報導。有一天一大早,她來到我跟拉瑪希一起睡的樓上的房間,坐到我床邊,一隻手指伸到她的嘴唇上示意我安靜。拉瑪希就睡在幾呎之外他的床上。我想要起身,但是她一隻手掌把我壓回去,然後開始解開她睡衣上衣的鈕扣,讓我能看到她剛發育的胸部,在窗外樹的倒影中幾乎像是淺綠色。接下來的時間裡,我很清楚地意識到拉瑪希的咳嗽,還有他在睡夢中清喉嚨的吱軋聲,而瑪西,半裸著,充滿恐懼,又無所畏懼地,面對著我,懷著一個人在十三歲做出這樣的姿態時可能會有的任何情緒。)
我們把跟著食物一起偷拿來的餐盤餐刀跟湯匙留在救生艇裡,然後溜回去經濟艙。在之後的一次安全演習中,當船員爬上了救生艇,並把救生艇盪到水面上時,一個服務生終於發現了我們無數次早餐留下的痕跡,也因此有一段時間,船長都要求找尋船上是否有一個偷渡客。
我們越過邊界,從頭等艙回到經濟艙時,甚至還不到八點。我們假裝跟著船的擺動而步履蹣跚。這時候我已經愛上我們的船不斷從一邊晃到一邊的緩慢華爾滋。而除了距離遙遠的芙拉薇亞.普林斯跟愛蜜麗以外,我是單獨一個人這件事,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冒險。我沒有對家庭的責任。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而且拉瑪希、卡修斯跟我已經建立了我們自己的規矩。我們每天至少要做一件被禁止的事。一天才剛剛開始,我們眼前還有許多個小時可以完成這項任務。(待續)我父母拋棄他們的婚姻時,從來沒有人承認,或解釋,但是也沒有隱藏。這件事甚至被當成只是踏錯一步,而非重大事故。所以我父母離婚的詛咒有多少落在我身上,我也不確定。我不記得承擔著那件事的重量。一個男孩子每天早上出門後,就會忙著探索他世界裡不斷開展的地圖。但那確實是很不安定的青春。
我在拉維尼亞山的聖湯瑪斯學院當小寄宿學生時,就很熱愛游泳。我熱愛任何跟水有關的事。校地裡有一條水泥溝渠,豪雨季節的洪水會在溝中急速奔流。這裡因此成為有些寄宿生會參加的一個遊戲的地點。我們會跳進水裡,被洪流帶著往前衝,翻滾,被從一邊丟到另一邊。在下游五十碼處有一條灰色的繩索,讓我們可以抓住繩索,把自己拉上來。在這之後再二十碼,這充滿急速水流的水溝就會變成暗溝,消失在地底下,一直通往黑暗中。到底它通往哪裡,我們始終不知道。
我們可能總共有四個人,會一次又一次地被水溝的洪水往下沖,頭幾乎無法浮在水面上。這是個讓人緊張的遊戲,抓住繩索,爬上來,然後在大雨中再跑回去再來一次。有一次我在靠近繩索時頭沈到水裡,來不及上來抓住繩子。我的手伸在空中,在我快速衝向最終埋在地下的暗溝時,那是我唯一露出來的地方。這就是我註定的死期,那天下午在拉維尼亞山,在三月的豪雨季節當中,如一個占星家預告的。我當時九歲,而即將面臨一趟什麼都看不見的旅程,進入黑暗的地底。一隻手抓住了我還高舉的一隻手臂,我被一個年紀較大的學生拉了起來。他不太在意地叫我們四個離開,然後就在雨中匆匆離開,也沒有多看我們是否聽了他的話。他是誰?我應該說:謝謝你。但是我只是渾身溼透地躺在草地上,喘著氣。
我在那些日子裡是什麼樣子?我沒有來自外界的印記,因此也沒有對自己的認知。如果我必須捏造出一張我自己小時候的照片,應該會是一個光著腳的男孩子,穿著短褲跟棉襯衫,跟幾個村子裡的朋友,在波拉雷葛穆瓦,沿著分隔高原路上車輛與屋子跟花園的發霉牆壁旁,奔跑著。或者也可能只有我一個人,等著他們,眼睛從屋子望向塵土漫佈的街道。
誰明白野生放養的孩子有多滿足?我一出了門,家庭的掌控就立刻鬆脫了。雖然我們自己一定也曾經試圖理解並拼湊出成人的世界,想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為什麼。但是一旦我們走上舷梯,登上奧蘭賽號,我們才一次出於必要地跟大人近距離交鋒。
瑪薩帕
我在跟一個年老的乘客解釋只要兩個動作就能把折疊椅打開的藝術時,瑪薩帕先生悄悄走到我旁邊,手臂挽住我的手臂,要我跟他走。「『從納奇茲到木比耳,』」他警告我,「『從曼斐斯到聖喬伊』﹍」他看到我一臉困惑而停頓下來。
瑪薩帕先生總是突然出現,讓我猝不及防。我在游泳池裡游完一圈時,他會蹲在那裡,抓住我滑溜溜的手臂,把我抓在池邊。「聽我說,你這奇特的孩子,『女人會對你甜言蜜語,睜著無辜的大眼睛』﹍我是在用我的人生經驗保護你。」但是十一歲的我並不覺得受到保護,反而因為知道這些可能而預先受傷。當他跟我們三個人講時更是糟糕,簡直像是世界末日。「我上次旅行回家時,發現一頭新來的騾子在我的地盤撒野﹍你們知道我的意思吧?」我們並不知道。直到他解釋後才明白。但是大多數時候,他都只跟我說話,彷彿只有在我這個「奇特」的男孩子身上,他才能留下印記。在這方面,他可能是對的。
馬克.瑪薩帕會在中午醒來,在黛利拉酒吧吃早餐。「給我兩個『單眼法老煎蛋土司』,跟一瓶納許牌汽水,沒錯,」他會說,一邊嚼幾個配雞尾酒的櫻桃,等著服務生上菜。吃完飯後,他會拿著他的爪哇咖啡到舞廳的鋼琴旁,把杯子放在高音部的琴鍵上。接著,隨著鋼琴和絃推著他向前時,他會對剛好在他旁邊的任何人上課,讓他們認識這個世界上重要而複雜的細節。某一天,課程可能是關於什麼時候應該戴帽子,或者關於拼字。「英文真是無可救藥的語言。無可救藥!拿『埃及』(Egypt)這個字來說吧。就是個大問題。我告訴你怎麼樣才可以每次都拼對。只要對自己背誦『永遠抓好你珍貴的奶子』(Ever Grasping Your Precious Tits)就好。」結果確實,我從來不曾忘記這個句子。甚至在我現在寫這段話時,我還會潛意識地猶豫一下,而在腦海裡大寫這些字母。(待續)但是大多時候,他都是挖出他的音樂知識,解釋四分之三拍的複雜之處,或回憶起他在某一個後台樓梯上跟某個很吸引人的女高音學的某一首歌。所以我們像在接收某種狂熱的傳記。「『我搭火車去旅行,而我想到你,』」他咕噥唱著,而我們以為聽到的是他哀傷憔悴的心。但是今天我知道馬克.瑪薩帕是熱愛結構與旋律的細節,因為並非他人生拜苦路上的每一站都跟失敗的愛情有關。
他是一半西西里血統,一半其他血統,他用他無法追蹤的口音告訴我們。他曾經在歐洲工作,也曾短暫地旅行到南北美洲,甚至到更遠的地方,直到他發現自己來到熱帶,住在一個港口酒吧上面。他教我們〈香港藍調〉的副歌。他有一肚子的歌曲跟人生故事,事實與虛構緊密地融合在一起,讓我們難以分辨。要哄騙我們三個很容易,畢竟我們都是如此赤裸而天真。而且,一天下午,當海上的陽光潑灑在舞廳的地板上時,瑪薩帕先生隨著鋼琴音符喃喃唱著的,有些歌曲中的有些字眼,是我們根本沒聽過的。
賤人。子宮。
他是在跟三個即將邁入青春期的男孩子講話,而他可能很清楚自己擁有的影響力。但是他也傳授給這群年輕的聽眾關於音樂榮耀的故事,而他最讚頌的人莫過於席尼.貝雪。他在巴黎演奏一首曲子時,被指控吹錯了一個音。他的反應是挑戰指控他的人跟他決鬥,卻在接下來的騷動中誤傷一位路人,而被丟進牢裡,遣送回國。「『偉大的貝雪』──他們叫他『暴雪』。你們幾個孩子可能活一輩子,」瑪薩帕說,「都不會看到有人像他這樣捍衛自己的原則。」
我們很著迷,也很驚異於瑪薩帕的歌曲、嘆息,跟閒聊,描繪出的是這樣無邊無際的巨大的愛的戲劇。我們都認定,他之所以在職業生涯中摔了致命一跤,一定是因為受到欺騙,或者因為他對女人的太強烈的愛。
「每個月,月圓月缺。
我說,每個月,月圓月缺。
血液從那賤人的子宮湧出。」
瑪薩帕那天下午唱的歌,感覺有些超越塵世而且難以抹滅,不論那些字句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們只聽了一次,但它就藏在我們心底,像是如石頭堅硬的真相,我們會持續繞路避開這坦率直接的真相,就像我們當時避開一樣。這歌詞(後來我會發現歌詞作者是傑利.羅伊.莫頓)是刀槍不入又滴水不進的。但是我們當時並不明白,因為它的直接讓我們太困惑──那最後一句的字眼,它令人吃驚而致命的韻腳,在重複的開場之後,來得如此精簡有力。我們從他在舞廳裡的身影前消失,突然間意識到服務生站在梯子上為今晚的舞會準備,調整彩色燈光的方向,拉起交錯縱橫在房間上方的,拱形的皺紋彩紙。他們啪啪作響地拉開龐大的白色桌巾,蓋在木頭桌上。在每一張桌子的中央,他們放上一只插著花的花瓶,讓空蕩的房間變得文明而浪漫。瑪薩帕先生沒有跟我們一起離開。他待在鋼琴前,望著琴鍵,沒有察覺在他周圍進行的偽裝。我們知道,不論他今晚要跟交響樂團演奏什麼,都不會是他剛剛為我們演奏的。
馬克.瑪薩帕的藝名──或者如他自己所說的「戰名」──是「陽光草原」。自從有一次他在法國演出時,宣傳海報的印刷出錯之後,他就開始用這個名字。或許當時的舉辦人是想避開他帶有黎凡特地區味道的姓氏。在奧蘭賽號上,船上公佈欄貼出的他的鋼琴課的告示也是稱他為「陽光草原,鋼琴大師」。但是他對於我們這些貓桌的人而言,還是瑪薩帕先生,因為「陽光」跟「草原」實在不是能跟他的本質並存的字眼。他身上並沒有太多樂觀或修剪平整的特質。但是他對音樂的熱情讓我們這桌充滿活力。有一次吃午餐時,他整頓飯都在講「偉大的貝許」決鬥的故事,讓我們大飽耳福。那場一九二八年凌晨時分發生在巴黎的決鬥後來演變成比較像是槍戰──貝許朝著指控他的麥肯垂克的方向開槍,但是子彈擦過他的義大利波沙利諾牌帽子,接著繼續飛行,直到它嵌進一個正要去上班的法國女人的大腿裡。瑪薩帕先生從頭演到尾,用了鹽巴罐跟胡椒罐,還有一片起司,來描繪那子彈飛行的路線。
他有一天下午邀我到他的艙房去聽一些唱片。瑪薩帕告訴我,貝許用的是亞柏特系統的豎笛,而有比較正式而華麗的音色。「正式而華麗,」他一直重複說。他放上一張七十八轉的唱片,跟著音樂低語,指出那些幾乎不可能的變奏與裝飾音。「你聽,他用顫音讓聲音更出來。」我聽不懂,但是肅然起敬。貝許每次重複旋律時,瑪薩帕都會對我示意,「就像陽光照在森林的地上,」我記得他說。他在一個看來很蒼白的行李箱裡翻找,拿出一本書,然後唸出貝許跟一個學生講過的話:「我今天要給你一個音符,」貝許說。「看看你可以用多少種方法吹這個音符──用咆哮的,用塗抹的,把它壓平,讓它變尖銳,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就跟說話一樣。」
然後瑪薩帕告訴我關於那隻狗的事。「牠之前都會跟著貝許上台,在牠的主人演奏時嚎叫﹍也就是因為這樣,貝許才會跟艾林頓公爵(Duke Ellington)拆夥。因為公爵不讓古拉上台,站在燈光下,穿著牠的白色西裝搶盡風頭。」因此為了古拉,貝許離開了艾林頓的樂團,開了「南方裁縫店」,做清潔跟修補的生意,也是音樂家聚集的地方。「他最好的唱片都是在這時候錄的──例如『黑棍子』,『甜心親愛的』。有一天你一定要買齊他所有的唱片。」
然後還有他的性生活。「喔,貝許喜歡重複,最後經常又跟同一個女人在一起﹍各式各樣的女人都想要馴服他。但是你知道,他從十六歲就開始到處去巡迴演奏了,他早就碰過有各種習氣,各種目的的女孩子。」各種習氣與各種目的!從納奇茲到木比耳﹍
我聽著,不了解地點著頭,而瑪薩帕先生則將這種生活方式與音樂技能的楷模緊緊攬在心頭,彷彿它們是裝在一個橢圓形的聖人肖像裡。(待續)C艙
我坐在床鋪上,看著門跟金屬的牆面。傍晚的艙房裡很熱。但我只有在這個時間來這裡,才能獨自一個人。白天大多時間我都忙著跟拉瑪希和卡修斯在一起,有時候是跟瑪薩帕或貓桌上其他的人。而在晚上我經常被我房間裡玩牌的人的低語圍繞。我需要花點時間回想一下。回想一下,讓我記起獨自好奇的舒適。過了一會,我會躺下來,看著上頭距離一兩呎的天花板。我覺得安全,即使我是在大海當中。
有時候,就在黑暗降臨前,我會發現自己單獨在C艙甲板,沒有別人在那裡。我會走到高度到我胸口的欄杆前,看著海水在船身旁奔流。有時候海水會漲到幾乎跟我一樣高,彷彿想將我猛然拉走。我動也不動,即使心裡充滿騷動的恐懼與孤獨。當我在可倫坡郊區的佩塔市場的狹窄巷道裡迷路,或要適應學校裡新的未知的規矩時,也是這樣的情緒。當我看不到海洋時,恐懼就不存在,但是現在海洋在晦暗的光線中升起,包圍住船,在我周圍盤旋纏繞。不論多害怕,我都待在原地,鄰近著匆匆流過的黑暗,一半想將自己往後拉,一半渴望著往前跳進去。
有一次,在我離開錫蘭之前,我看到一艘郵輪在可倫坡港口的遠處燃燒著。整個下午,我看著藍色的乙炔切進那艘船的側腹。我明白我現在所在的這艘船也可能被切成一片片。有一天,我看到懂這些事情的納維爾先生,於是拉了拉他的袖子,問他我們是否安全。他告訴我,奧蘭賽號健康狀況良好,才到它職業生涯的一半而已。它曾經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擔任過軍艦,而在貨艙的某一面牆上,還有一幅很大的粉紅色跟白色的壁畫,畫著裸體女人跨坐在槍炮架上跟坦克上,是一個士兵畫的。那幅畫還在,但是個祕密,因為船上的官員從來不會進去貨艙。
「但是我們不會有事?」
他叫我坐下來,然後在他總是隨身攜帶的藍圖的背面,畫給我看他所說的希臘戰艦,一艘三層槳座的戰船。「這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海船。即使它已經不存在了。它對抗了雅典的敵人,帶回不知名的水果跟作物、新的科學、建築,甚至民主制度。一切都是因為這艘船。它沒有任何裝飾。三層槳座戰船完全忠於它自己──它是一個武器。上面只有划槳手跟弓箭手。但是現在已經找不到這種船的任何痕跡。很多人還在河口的淤泥中尋找這種船,但至今沒有找到任何一艘。它們是用白楊木跟硬的榆木作成,龍骨則是用橡木作成,然後用綠松木彎曲作成骨架。船板是用亞麻繩縫在一起。整個骨架都沒有任何金屬。所以這種船可以在沙灘上燒掉,如果沈到海裡也會完全融解消失。我們的船安全多了。」
不知為何,納維爾先生對一艘古老戰船的描述讓我感到安心。我不再想像自己身在裝飾華麗的奧蘭賽號上,而是在比較自給自足,比較儉約簡單的船上。我是在三層槳座戰船上的划槳手或弓箭手。我們會以這樣的姿態進入阿拉伯海,然後是地中海,而納維爾先生是我們的軍艦指揮官。
那天晚上我突然醒來,我覺得我們正在經過島嶼,而那些島嶼在黑暗中非常靠近。船旁的海浪有種不同的聲響,某種回音的感覺,彷彿它們在回應土地。我打開床旁的黃色燈光,看著我從一本書上描下來的世界地圖。我忘了在地圖上寫下地名。我只知道我們正往西往北前進,遠離可倫坡。(待續)一個澳大利亞人
在破曉前的時刻,當我們已經起床在彷彿空無一人的船上晃蕩時,洞穴般的沙龍會充滿前晚香煙的味道,而拉瑪希、卡修斯跟我已經推著手推車衝來衝去,讓原本寂靜的圖書室吵翻了天。有一天早上,我們突然發現一個穿著溜冰輪鞋的女孩子沿著上甲板的木板周圍,繞著我們飛馳。她似乎一直都比我們更早起床。她滑得越來越快,流暢的步伐考驗著她的平衡,而她似乎完全不理會我們的存在。但在一次轉彎時,她算錯了在轉角跳起,越過錨索的時間,而一頭撞上船尾的欄杆。她站起來,看了一下膝蓋上一道血痕,然後又繼續滑,並瞄了一眼她的手錶。她是澳大利亞人,而我們都被迷住了。我們從來沒目睹過這樣強烈的決心。我們的家庭裡的女性成員都不會這個樣子。後來我們在游泳池裡認出她,她飛速前進,激起連珠炮般的水花。如果她從奧蘭賽號跳入海中,在船旁邊游泳,跟著船同步前進二十分鐘,我們也不會感到驚訝。
我們因此開始起得更早,好看她溜那五十圈或六十圈。溜完之後,她會解開鞋帶,脫掉她的溜冰輪鞋,筋疲力竭滿身大汗,而且完全不脫衣服地走向戶外的淋浴間。她會站在那湧出而噴濺的水中,向左向右地甩著頭,像是一頭穿著衣服的動物。這是一種新的美麗。當她離開時,我們會追蹤著她的腳印,而在我們接近腳印時,它們就已經在新生的陽光中蒸發了。
卡修斯
我現在想到,誰會把孩子取名叫卡修斯。大多數父母都會避免給第一個孩子取這樣的名字。雖然斯里蘭卡一向喜愛結合古典的名字跟錫蘭語的姓氏──所羅門跟賽納卡 ,並不常見,但確實存在。我們的家庭小兒科醫生就叫做蘇格拉底.古納瓦德納。卡修斯這個名字雖然在羅馬時代名聲不佳 ,卻是個唸起來溫和有如低語的名字,不過我在這旅途中認識的年少卡修斯卻相當反偶像崇拜。我從來沒看過他依附任何有權勢的人。他會吸引你採用他對事物的觀點,讓你經由他的眼睛看到這船上的權力階層。例如他就很樂意自己是坐在貓桌的毫無地位的人物。
卡修斯講到拉維尼亞山上的聖湯瑪斯學院時,所流露的精力有如一個人在回憶一場反抗運動。他在學校高我一個年級,因此感覺我們像是分處兩個世界,但是他是年紀較小的學生的燈塔,因為他鮮少被抓到為非作歹。而且當他真的被抓到時,他臉上也不會露出一絲羞愧或謙卑的痕跡。他後來更是名聲大噪,因為他有一次設法把我們的舍監,「竹條」巴納巴斯,鎖在小學的廁所裡好幾個小時,抗議學校裡令人作嘔的廁所(你要蹲在那恐怖的洞上方,然後在完事之後,用一個已經生銹的,泰萊牌金黃糖漿罐子裡的水,清洗自己。「甜的從強者出來,」 我後來永遠記得這糖漿的廣告詞。)
卡修斯一直等到巴納巴斯在早上六點,他慣常蹲廁所的時間,進入地面層的學生廁所後,用一根鐵桿抵住門,接著再用快乾水泥將門鎖包起來。我們聽著我們的舍監用身體撞門。然後他開始喊我們的名字,從他信任的學生喊起。我們每個人都回應說會過去幫忙,但都溜到操場上,不得不到樹叢後去解放,接著有人去游泳,有人則是乖乖地去上早上七點鐘的自習課,這堂課事實上是巴納巴斯神父在那個學期稍早時開始規定的。後來是一個工友不得不用一根板球的球門柱子把水泥敲碎,但那已經是到接近傍晚的時候。我們本來希望到那時候我們的舍監已經被臭氣薰得受不了,昏過去而無法言語。
但是他的復仇行動迅速展開。卡修斯被打了一頓,然後停學一週,但他反而更成為小學部學生的偶像,尤其是因為校長在早晨禮拜的一場令人激動的演說中,整整譴責了他兩分鐘,彷彿他是墮落的天使一般。當然,這件事沒有帶來任何教訓──對任何人都是如此。許多年後,當一個老校友捐錢給聖湯瑪斯學院蓋一座新的板球球場看台時,我的朋友賽納卡說:「他們首先應該蓋幾間像樣的廁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