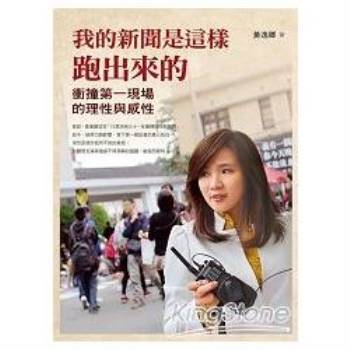我在布里斯托的逃亡
恆爺:
我得跟你報告一下,在你離開人世四年多,我終究成了媒體逃兵,辭去工作來到英國留學。之所以下了這個決定,是因為我愈活愈惶恐,因為我心中始終存在著對你的承諾:我三十歲時要回答你是否還想活下去。時限將至,我驚覺自己還沒去過埃及,也沒到過希臘,我的人生除了工作,經歷少得可憐,我簡直是以逃亡的心情離開台灣的。逃亡前,我每天跑新聞、播新聞、睡覺也夢新聞,壓力累積到一個瓶頸,現在還三不五時夢到我在凱道倒扁現場憋著一天的尿無法如廁。
人生要追尋的精采是什麼?我不想每天在風吹雨淋的凱道前度過,想去英國當個咖啡妹,這樣算是失敗的人生嗎?迎向而立之年,我還在尋找答案,目前我可以確定的是,當我打開英國宿舍窗戶,看見一隻狐狸蹦蹦跳跳地穿過草原時,心中猛地湧現一陣狂喜,我感到只要看到這個畫面,似乎一切都值得了。
2008.1 寫於英國布里斯托
採訪任務
@任務:倒扁新聞的主線採訪與轉播。
@時間:二○○六年八月至十一月。
@地點:凱達格蘭大道與台北車站的新聞連線點來回。
@經驗值:記者生涯中連線頻率最高時期,一天最高紀錄連線五十次,平均每十五分鐘就連線一次。
精神與體力的交戰
台灣解嚴之後,電視新聞台蓬勃發展,「倒扁事件」可說是少見的大規模串連與轉播,而我當時被指派主跑倒扁主線新聞。
那段時間的工作型態大概是這樣的:連續幾天下午一點半上班,半夜兩點下班,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接著又連續幾天從清晨六點一直工作到晚上七點半。
作息紊亂、體力透支不在話下,最該死的是倒扁現場的雨幾乎未曾停過。根本不用穿高跟鞋或辣妹裝,也不用化上美美的妝,每天就是穿著歐巴桑涼鞋和短褲外加雨衣,反正不管怎麼穿都會被淋溼,而臉上的妝不到一個小時,也統統被雨水洗乾淨。
其次,這起事件中的「靜坐」 活動可是一點也不安靜,除了高喊口號、激昂演說,再加上空檔時間不斷播放倒扁歌曲,三不五時還來個現場開唱,就算我的聽力沒有嚴重受損,精神也快被長期的巨浪聲響搞到崩潰,儘管如此,阿扁還是沒有下台。
精神與體力的交戰還不夠,各家新聞台鋪天蓋地大做倒扁新聞,一個小時至少連線四到五次,一天下來可以連線五十次,二十幾天下來,連線達上千次,日日夜夜、夜夜日日,最傷的是喉嚨,往往到晚上已經不知所云,聲音不僅分岔沙啞,還低了八度,有磁性的咧。
逃亡種子萌芽
二○○六年九月十五日,倒扁總部展開圍城之役,發動百萬人上街頭螢光遊行嗆扁。
發動時間在傍晚六點,我照例已在凱道前守候一整天,隨著時間愈來愈逼近圍城轉播,我的膀胱卻很不爭氣,脹到我實在憋不住。
向導播報備後,我看看時間,下午五點二十分,嗯,距離開播還有一段時間。我先往流動廁所方向看去,依舊大排長龍,我當下立刻往二二八公園衝擠過去。
但那天的圍城聲勢太浩大了,館前路上也湧進了滿滿的民眾,我愈擠愈覺得不對勁。好不容易擠到二二八公園的公共廁所時,不禁哀嚎一聲,排隊上廁所的隊伍已經延伸到捷運站口了。
我開始緊張,試圖把握僅剩一點的時間,往公園另一頭找廁所。此時我雖然氣喘吁吁,意志卻相當集中,目標就是:我-要-上-廁-所!
就在冒雨在公園裡衝來衝去時,刺耳的耳機聲又響起:「快回來啊!家裡要連線了!快啊!」
衝刺的腳步頓時有如賽車甩尾般,我當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望著淒風苦雨的二二八公園,我只能憋著尿往回跑。
看著在雨中漫步的情侶及躲在涼亭裡下棋話家常的人,剎那間心裡的淒苦又多了一點點;好羨慕他們,起碼還有上廁所的自由。
街頭倒扁運動讓我早已算不清憋了幾回尿,又有多少次體力不支,休息的念頭漸漸成型。
我暗想,也許「逃亡」是邁向三十歲後的人生正確的第一步。於是,我決定飛向英國布里斯托。
但當時一位政治圈友人在我出國前對我說:「記住我的話,你會後悔的!」
我不服氣地回瞪他:「有什麼好後悔的?」
「你現在又是記者、又是主播,有重要的採訪路線和公司栽培,你一離開,馬上就會有人補位啦。等你回國,從零開始,什麼都沒了,這就叫做『職場現實』。」
我何嘗沒有想過這點?可是我想找到三十歲後快樂與成功的意義。
狐狸的衝擊
記得恆爺曾經送我一片吉他大師吉姆克勞契(Jim Crose)的CD,「他是個傳奇人物,做過卡車司機、店員,還因為打工造成手指受傷,身體有了缺陷,卻還努力研究出不影響彈奏的指法,成了民謠吉他大師。但很可惜,他只活了三十歲。」
「好可惜。」我回答。
恆爺繼續說:「是啊,人要懂得及時行樂。好好想想你確定要走新聞業嗎?既沒有生活品質,還得拿健康換金錢。你看我,時間全投入了工作,失去好多啊!但話說回來,」恆爺正經地說:「如果你選擇走下去,既來之則安之,就好好感受媒體工作的酸甜苦辣吧!」
隔年的恆爺與吉姆克勞契(Jim Croce)同樣英年早逝,他的這番話反覆在我腦海迴盪至今。
某個夏日午後,英國的空氣瀰漫著乾燥的草香,我走到窗邊深呼吸一口氣,突然看到了狐狸。對英國一無所知的我一時愣住了。那是狐狸?是狗吧?
我以為自己眼花了,但那狐狸日後在我宿舍附近又出現好幾回,我這才知道英國許多地方,在街頭看到狐狸比看到流浪狗更稀鬆平常。
我自以為視野很寬廣,其實根本沒有真正見識過這個世界。
對於三十歲以後的人生,也許很多人睜大眼睛關注的是薪水有多高、頭銜有多大,而我在乎的確只是安靜地體驗人生。
恆爺啊,我還沒有參透。
評價自己的人生
直到二○○九年,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我帶著「不能再浪費時間」的心態與問號,終究還是回到媒體圈。
二○一○年的某一天,面對三十歲後的茫然與沮喪,我坐在台北市仁愛路巷弄裡一間日本居酒屋裡,而我的對面正是施明德。
這場餐敘中,施明德談著笑著怨嘆著也意氣風發著,尤其對於許多人埋怨他當年未帶頭衝進總統府,仍有滿滿的不吐不快:「如果當時我衝進去,讓阿扁有機會把反貪腐轉變為藍綠或統獨的戰爭,搞得天下大亂,我將成為更大的罪人。」
有人將他視為政壇悲劇的失敗者,也有人把他奉為浪漫理想的成功實踐家,他的浮沉人生是公開的,外界可以任意評價他的成敗。
但重要的是,他如何評價自己走過的路呢?
席間他送了我與友人兩本書,我打開書頁,映入眼簾一行字讓我眼前一亮,似乎給了我部分答案:
「逸卿小姐,信心是生命中最強烈的魅力與智慧。 施明德 2010.10.13」
我抬起頭,與施明德對上眼,兩人似乎心領神會地相視而笑。
不管曾經傷痕累累或是被捧在手心上,不管是在布里斯托或在新聞現場,人生的評價都應該是自己給的。
我眼前又浮現那隻在草地上蹦蹦跳的狐狸,若有所悟。
倒扁運動事件簿
起源:
在二○○四至○八年陳水扁總統第二任期內,第一家庭因涉嫌貪汙而引爆的社會運動,由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發動,訴求陳水扁下台。
形態:
施明德發動百元募款籌措倒扁經費,從二○○六年八月十二日在二二八公園召開記者會宣布倒扁開始,歷經九月九日凱道靜坐、九月十五日圍城之役、十月十日總統府前天下圍攻,到倒扁全台遍地開花,倒扁風潮如巨尾紅龍橫掃全台。直到該年十二月,施明德展開自囚,改變倒扁型態,街頭運動遂告結束,倒扁熱潮退燒。
效應:
這起運動可說是國內電視媒體少見的大規模轉播報導,也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但陳水扁最後並未下台,也重挫了倒扁士氣。雖然訴求號召「反貪腐」,以「和平,非暴力 」為街頭運動的指導原則,然而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倒扁激情一度將社會帶入暴力邊緣。儘管未發生真正的大規模衝突,但零星衝突不斷。由於運動延燒數月,眾多警力終日鎮守維持秩序,一度還發生警察過勞猝死的悲劇。媒體觀察筆記:你我都是收視率的共犯結構
倒扁風雲期間,全台灣的新聞彷彿只有這件事,其他的國際、社會、民間消費等消息統統不見了,這當然不符合新聞的比例原則,但為什麼新聞台還能做得如此鋪天蓋地?
說穿了就是因為收視率,只要觀眾膩了,倒扁新聞的比重自然也會降低。
是的,閱聽人早就罵翻了這種以收視率為依歸的現象,可是為什麼媒體始終厚顏不改呢?
這其實就是媒體內部的無奈。
二○一二年五月,我播到一條新聞,內容是一個國小男童每天為了照顧重病的媽媽,學校午休時還趕回家幫忙家務,之後再衝回學校上課。小小年紀的他不喊苦,只希望媽媽的病趕快好起來,讓他能夠再一次好好地在媽媽懷裡撒嬌。
這條新聞令我鼻酸,認定閱聽人應該也會有相同感受,想必這樣的社會關懷面報導會帶來收視率吧?
但隔天收視率出爐,這條新聞在我當節的播報時段中,從原本平均每分鐘零點六的收視率數字,腰斬到只剩下零點三四。我很不解地跟編輯發牢騷:「這則新聞不好看嗎?大家對小男孩的遭遇都這麼無感嗎? 」
編輯只能無奈苦笑。
新聞部每天從上到下無不像揣測情人的心意一樣,努力猜想閱聽人下一分鐘想看什麼,從經驗中摸索,編排新聞大菜。只是不管當天多麼有自信地端出拿手菜,只要收視率報表出來,數字表現不佳,一切的努力都是枉然。
我不是要為電視台「以收視率為依歸」的生態辯解,而是希望大家了解,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下,媒體人如何在現實與理想中找到平衡。
所謂的現實就是廣告收入,這是新聞台的命脈,而決定廣告主下單的指標即為尼爾森收視率表現,如果長期收視率不佳,廣告主自然減少下單。公司的財源沒了,誰還做得了新聞?新聞的確被收視率綁架了,但決定收視率高低的並不是新聞台,而是手握遙控器的人。矛盾的是,閱聽人又指著許多高收視率的新聞說:「這些都是垃圾新聞!」
這宛如鬼打牆的無解習題究竟是怎麼回事?以我個人「沒有學理依據,純粹實務觀察」的思維來看,其實台灣的收視率怪象,就是電視台、尼爾森與閱聽人之間的共犯結構。
閱聽人收看新聞時有兩種面向,一種是閱聽人「該知道的」新聞,像是國際大事、政治動向、科技新知或民生消費訊息等,這類往往是閱聽人經過理性抉擇後希望從新聞中獲取的知識,亦即ㄧ般大眾認為電視台應該播出的新聞,較具公眾利益與教育色彩。另一種則是「想知道的」新聞,此種新聞類型有更多能夠滿足閱聽人感官刺激的腥羶色報導,在收視率表現上普遍都不錯,卻常遭民眾批評報導太多。
問題是,當電視台大氣魄地做了許多民眾「該知道的」新聞,收視率卻不買帳,只見其他競爭對手僅是播了小小的八卦新聞就收視狂飆。電視台的窘,有誰能明瞭?
台灣這個蕞爾小島擁有八個二十四小時播出的新聞台,數量之高可說是全球之最,換句話說,新聞台之間的競爭也是全球最激烈,然而勝負的依據卻只有尼爾森收視率。如果光是對電視台揮舞道德大旗,呼籲媒體寧可不賺錢、也該播出沒有收視率的重要新聞,恐怕是一種隔岸觀火的高調。
更務實來檢視這個問題,台灣的新聞台究竟能做出什麼樣的改變?
在尼爾森收視率仍是目前唯一評量的標準之下,新聞台不得不以此為依歸,然後從中求取新聞質感的增加。譬如國際新聞的收視表現在各節新聞中往往並不討喜,於是改以「專題報導」的方式來呈現,培養收視觀眾群,長久下來,閱聽人就會知道什麼時候可看到重要的國際新聞報導。不少新聞台已經在做這樣的努力。
那麼閱聽人可以改變這個亂象嗎?當然可以。當大家(尤其是尼爾森收視戶)願意停留在所謂「有深度又想了解」的新聞久一點,讓結果反映在收視率數字上,新聞工作者們絕對樂於不再掙扎做那些所謂的「垃圾新聞」。
或者我們可以期待,未來在評估新聞媒體經營績效的工具能夠更多樣化。台灣大學新聞所副教授林照真曾提出一個思考觀點,現今作為新聞收看主要依據的尼爾森收視率調查其實是一種廣告調查,廣告主不會看新聞內容物是什麼,因此若將廣告調查的工具與邏輯,拿來做為新聞內容調查的參考架構,其實並不精準。
收視率的「共犯結構」只要有一個環節鬆動,就有改變的契機。想要看什麼樣的新聞菜餚,從今天起,閱聽人別再被動接收了,你會發現,其實自己也能主動改變閱聽世界。
讓我們一起努力。
恆爺:
我得跟你報告一下,在你離開人世四年多,我終究成了媒體逃兵,辭去工作來到英國留學。之所以下了這個決定,是因為我愈活愈惶恐,因為我心中始終存在著對你的承諾:我三十歲時要回答你是否還想活下去。時限將至,我驚覺自己還沒去過埃及,也沒到過希臘,我的人生除了工作,經歷少得可憐,我簡直是以逃亡的心情離開台灣的。逃亡前,我每天跑新聞、播新聞、睡覺也夢新聞,壓力累積到一個瓶頸,現在還三不五時夢到我在凱道倒扁現場憋著一天的尿無法如廁。
人生要追尋的精采是什麼?我不想每天在風吹雨淋的凱道前度過,想去英國當個咖啡妹,這樣算是失敗的人生嗎?迎向而立之年,我還在尋找答案,目前我可以確定的是,當我打開英國宿舍窗戶,看見一隻狐狸蹦蹦跳跳地穿過草原時,心中猛地湧現一陣狂喜,我感到只要看到這個畫面,似乎一切都值得了。
2008.1 寫於英國布里斯托
採訪任務
@任務:倒扁新聞的主線採訪與轉播。
@時間:二○○六年八月至十一月。
@地點:凱達格蘭大道與台北車站的新聞連線點來回。
@經驗值:記者生涯中連線頻率最高時期,一天最高紀錄連線五十次,平均每十五分鐘就連線一次。
精神與體力的交戰
台灣解嚴之後,電視新聞台蓬勃發展,「倒扁事件」可說是少見的大規模串連與轉播,而我當時被指派主跑倒扁主線新聞。
那段時間的工作型態大概是這樣的:連續幾天下午一點半上班,半夜兩點下班,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接著又連續幾天從清晨六點一直工作到晚上七點半。
作息紊亂、體力透支不在話下,最該死的是倒扁現場的雨幾乎未曾停過。根本不用穿高跟鞋或辣妹裝,也不用化上美美的妝,每天就是穿著歐巴桑涼鞋和短褲外加雨衣,反正不管怎麼穿都會被淋溼,而臉上的妝不到一個小時,也統統被雨水洗乾淨。
其次,這起事件中的「靜坐」 活動可是一點也不安靜,除了高喊口號、激昂演說,再加上空檔時間不斷播放倒扁歌曲,三不五時還來個現場開唱,就算我的聽力沒有嚴重受損,精神也快被長期的巨浪聲響搞到崩潰,儘管如此,阿扁還是沒有下台。
精神與體力的交戰還不夠,各家新聞台鋪天蓋地大做倒扁新聞,一個小時至少連線四到五次,一天下來可以連線五十次,二十幾天下來,連線達上千次,日日夜夜、夜夜日日,最傷的是喉嚨,往往到晚上已經不知所云,聲音不僅分岔沙啞,還低了八度,有磁性的咧。
逃亡種子萌芽
二○○六年九月十五日,倒扁總部展開圍城之役,發動百萬人上街頭螢光遊行嗆扁。
發動時間在傍晚六點,我照例已在凱道前守候一整天,隨著時間愈來愈逼近圍城轉播,我的膀胱卻很不爭氣,脹到我實在憋不住。
向導播報備後,我看看時間,下午五點二十分,嗯,距離開播還有一段時間。我先往流動廁所方向看去,依舊大排長龍,我當下立刻往二二八公園衝擠過去。
但那天的圍城聲勢太浩大了,館前路上也湧進了滿滿的民眾,我愈擠愈覺得不對勁。好不容易擠到二二八公園的公共廁所時,不禁哀嚎一聲,排隊上廁所的隊伍已經延伸到捷運站口了。
我開始緊張,試圖把握僅剩一點的時間,往公園另一頭找廁所。此時我雖然氣喘吁吁,意志卻相當集中,目標就是:我-要-上-廁-所!
就在冒雨在公園裡衝來衝去時,刺耳的耳機聲又響起:「快回來啊!家裡要連線了!快啊!」
衝刺的腳步頓時有如賽車甩尾般,我當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望著淒風苦雨的二二八公園,我只能憋著尿往回跑。
看著在雨中漫步的情侶及躲在涼亭裡下棋話家常的人,剎那間心裡的淒苦又多了一點點;好羨慕他們,起碼還有上廁所的自由。
街頭倒扁運動讓我早已算不清憋了幾回尿,又有多少次體力不支,休息的念頭漸漸成型。
我暗想,也許「逃亡」是邁向三十歲後的人生正確的第一步。於是,我決定飛向英國布里斯托。
但當時一位政治圈友人在我出國前對我說:「記住我的話,你會後悔的!」
我不服氣地回瞪他:「有什麼好後悔的?」
「你現在又是記者、又是主播,有重要的採訪路線和公司栽培,你一離開,馬上就會有人補位啦。等你回國,從零開始,什麼都沒了,這就叫做『職場現實』。」
我何嘗沒有想過這點?可是我想找到三十歲後快樂與成功的意義。
狐狸的衝擊
記得恆爺曾經送我一片吉他大師吉姆克勞契(Jim Crose)的CD,「他是個傳奇人物,做過卡車司機、店員,還因為打工造成手指受傷,身體有了缺陷,卻還努力研究出不影響彈奏的指法,成了民謠吉他大師。但很可惜,他只活了三十歲。」
「好可惜。」我回答。
恆爺繼續說:「是啊,人要懂得及時行樂。好好想想你確定要走新聞業嗎?既沒有生活品質,還得拿健康換金錢。你看我,時間全投入了工作,失去好多啊!但話說回來,」恆爺正經地說:「如果你選擇走下去,既來之則安之,就好好感受媒體工作的酸甜苦辣吧!」
隔年的恆爺與吉姆克勞契(Jim Croce)同樣英年早逝,他的這番話反覆在我腦海迴盪至今。
某個夏日午後,英國的空氣瀰漫著乾燥的草香,我走到窗邊深呼吸一口氣,突然看到了狐狸。對英國一無所知的我一時愣住了。那是狐狸?是狗吧?
我以為自己眼花了,但那狐狸日後在我宿舍附近又出現好幾回,我這才知道英國許多地方,在街頭看到狐狸比看到流浪狗更稀鬆平常。
我自以為視野很寬廣,其實根本沒有真正見識過這個世界。
對於三十歲以後的人生,也許很多人睜大眼睛關注的是薪水有多高、頭銜有多大,而我在乎的確只是安靜地體驗人生。
恆爺啊,我還沒有參透。
評價自己的人生
直到二○○九年,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我帶著「不能再浪費時間」的心態與問號,終究還是回到媒體圈。
二○一○年的某一天,面對三十歲後的茫然與沮喪,我坐在台北市仁愛路巷弄裡一間日本居酒屋裡,而我的對面正是施明德。
這場餐敘中,施明德談著笑著怨嘆著也意氣風發著,尤其對於許多人埋怨他當年未帶頭衝進總統府,仍有滿滿的不吐不快:「如果當時我衝進去,讓阿扁有機會把反貪腐轉變為藍綠或統獨的戰爭,搞得天下大亂,我將成為更大的罪人。」
有人將他視為政壇悲劇的失敗者,也有人把他奉為浪漫理想的成功實踐家,他的浮沉人生是公開的,外界可以任意評價他的成敗。
但重要的是,他如何評價自己走過的路呢?
席間他送了我與友人兩本書,我打開書頁,映入眼簾一行字讓我眼前一亮,似乎給了我部分答案:
「逸卿小姐,信心是生命中最強烈的魅力與智慧。 施明德 2010.10.13」
我抬起頭,與施明德對上眼,兩人似乎心領神會地相視而笑。
不管曾經傷痕累累或是被捧在手心上,不管是在布里斯托或在新聞現場,人生的評價都應該是自己給的。
我眼前又浮現那隻在草地上蹦蹦跳的狐狸,若有所悟。
倒扁運動事件簿
起源:
在二○○四至○八年陳水扁總統第二任期內,第一家庭因涉嫌貪汙而引爆的社會運動,由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發動,訴求陳水扁下台。
形態:
施明德發動百元募款籌措倒扁經費,從二○○六年八月十二日在二二八公園召開記者會宣布倒扁開始,歷經九月九日凱道靜坐、九月十五日圍城之役、十月十日總統府前天下圍攻,到倒扁全台遍地開花,倒扁風潮如巨尾紅龍橫掃全台。直到該年十二月,施明德展開自囚,改變倒扁型態,街頭運動遂告結束,倒扁熱潮退燒。
效應:
這起運動可說是國內電視媒體少見的大規模轉播報導,也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但陳水扁最後並未下台,也重挫了倒扁士氣。雖然訴求號召「反貪腐」,以「和平,非暴力 」為街頭運動的指導原則,然而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倒扁激情一度將社會帶入暴力邊緣。儘管未發生真正的大規模衝突,但零星衝突不斷。由於運動延燒數月,眾多警力終日鎮守維持秩序,一度還發生警察過勞猝死的悲劇。媒體觀察筆記:你我都是收視率的共犯結構
倒扁風雲期間,全台灣的新聞彷彿只有這件事,其他的國際、社會、民間消費等消息統統不見了,這當然不符合新聞的比例原則,但為什麼新聞台還能做得如此鋪天蓋地?
說穿了就是因為收視率,只要觀眾膩了,倒扁新聞的比重自然也會降低。
是的,閱聽人早就罵翻了這種以收視率為依歸的現象,可是為什麼媒體始終厚顏不改呢?
這其實就是媒體內部的無奈。
二○一二年五月,我播到一條新聞,內容是一個國小男童每天為了照顧重病的媽媽,學校午休時還趕回家幫忙家務,之後再衝回學校上課。小小年紀的他不喊苦,只希望媽媽的病趕快好起來,讓他能夠再一次好好地在媽媽懷裡撒嬌。
這條新聞令我鼻酸,認定閱聽人應該也會有相同感受,想必這樣的社會關懷面報導會帶來收視率吧?
但隔天收視率出爐,這條新聞在我當節的播報時段中,從原本平均每分鐘零點六的收視率數字,腰斬到只剩下零點三四。我很不解地跟編輯發牢騷:「這則新聞不好看嗎?大家對小男孩的遭遇都這麼無感嗎? 」
編輯只能無奈苦笑。
新聞部每天從上到下無不像揣測情人的心意一樣,努力猜想閱聽人下一分鐘想看什麼,從經驗中摸索,編排新聞大菜。只是不管當天多麼有自信地端出拿手菜,只要收視率報表出來,數字表現不佳,一切的努力都是枉然。
我不是要為電視台「以收視率為依歸」的生態辯解,而是希望大家了解,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下,媒體人如何在現實與理想中找到平衡。
所謂的現實就是廣告收入,這是新聞台的命脈,而決定廣告主下單的指標即為尼爾森收視率表現,如果長期收視率不佳,廣告主自然減少下單。公司的財源沒了,誰還做得了新聞?新聞的確被收視率綁架了,但決定收視率高低的並不是新聞台,而是手握遙控器的人。矛盾的是,閱聽人又指著許多高收視率的新聞說:「這些都是垃圾新聞!」
這宛如鬼打牆的無解習題究竟是怎麼回事?以我個人「沒有學理依據,純粹實務觀察」的思維來看,其實台灣的收視率怪象,就是電視台、尼爾森與閱聽人之間的共犯結構。
閱聽人收看新聞時有兩種面向,一種是閱聽人「該知道的」新聞,像是國際大事、政治動向、科技新知或民生消費訊息等,這類往往是閱聽人經過理性抉擇後希望從新聞中獲取的知識,亦即ㄧ般大眾認為電視台應該播出的新聞,較具公眾利益與教育色彩。另一種則是「想知道的」新聞,此種新聞類型有更多能夠滿足閱聽人感官刺激的腥羶色報導,在收視率表現上普遍都不錯,卻常遭民眾批評報導太多。
問題是,當電視台大氣魄地做了許多民眾「該知道的」新聞,收視率卻不買帳,只見其他競爭對手僅是播了小小的八卦新聞就收視狂飆。電視台的窘,有誰能明瞭?
台灣這個蕞爾小島擁有八個二十四小時播出的新聞台,數量之高可說是全球之最,換句話說,新聞台之間的競爭也是全球最激烈,然而勝負的依據卻只有尼爾森收視率。如果光是對電視台揮舞道德大旗,呼籲媒體寧可不賺錢、也該播出沒有收視率的重要新聞,恐怕是一種隔岸觀火的高調。
更務實來檢視這個問題,台灣的新聞台究竟能做出什麼樣的改變?
在尼爾森收視率仍是目前唯一評量的標準之下,新聞台不得不以此為依歸,然後從中求取新聞質感的增加。譬如國際新聞的收視表現在各節新聞中往往並不討喜,於是改以「專題報導」的方式來呈現,培養收視觀眾群,長久下來,閱聽人就會知道什麼時候可看到重要的國際新聞報導。不少新聞台已經在做這樣的努力。
那麼閱聽人可以改變這個亂象嗎?當然可以。當大家(尤其是尼爾森收視戶)願意停留在所謂「有深度又想了解」的新聞久一點,讓結果反映在收視率數字上,新聞工作者們絕對樂於不再掙扎做那些所謂的「垃圾新聞」。
或者我們可以期待,未來在評估新聞媒體經營績效的工具能夠更多樣化。台灣大學新聞所副教授林照真曾提出一個思考觀點,現今作為新聞收看主要依據的尼爾森收視率調查其實是一種廣告調查,廣告主不會看新聞內容物是什麼,因此若將廣告調查的工具與邏輯,拿來做為新聞內容調查的參考架構,其實並不精準。
收視率的「共犯結構」只要有一個環節鬆動,就有改變的契機。想要看什麼樣的新聞菜餚,從今天起,閱聽人別再被動接收了,你會發現,其實自己也能主動改變閱聽世界。
讓我們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