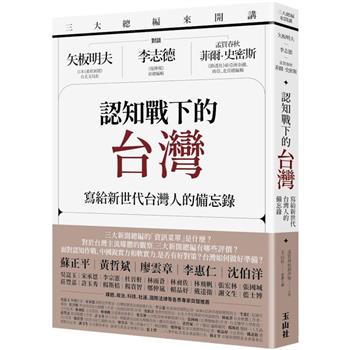第一章 認知戰時代
第二節 台灣媒體現況與假新聞
6. 偏頗、仇恨、有聞必錄、假新聞、娛樂化⋯⋯台灣媒體有救嗎?
喬伊斯:所以像《路透社》或《產經》這種傳統媒體的做法,我想現在在台灣的媒體應該是非常少見了。比方說我記得還在當記者的時候,每天早上要開一個會,然後到下午的時候還要開一個會。新聞會議是這樣子,就是分社社長從他的位子上站起來宣布開晨間會議,大家放下手邊的工作很快討論一下今天有什麼大新聞。誰誰誰有沒有辦法去哪裡參加記者會,沒有辦法的話誰誰誰要去支援,大概五分鐘、十分鐘吧。然後到快下班之前,還會再來個五分鐘、十分鐘,檢討一下今天做了什麼事情,明天會有什麼大新聞。
我不曉得台灣媒體現在的工作模式如何,網路世代應該也不一樣了,不過我看電視上發問的記者,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專業可言,問的問題常常非常愚蠢。他們跟政治人物或是受訪者講話的態度也是一點都不專業,這個問題我覺得在台灣非常普遍。
我不當記者很久了,不過比方說我派駐新加坡,或者我在東南亞採訪的時候,好像也沒有看到這麼不專業的情況,台灣許多記者是很沒有專業、沒有素養的。不知道現在的日本,年輕記者是不是跟台灣的一樣,有類似的情形嗎?
矢板明夫:不知道,我到台灣也發現這種現象,台灣記者都是超級年輕的,而且基本上,就是年輕女孩子特別多。我個人認為,比如說我在日本的時候,去《產經新聞》社會部幫忙,我們要調查一個完全不懂的議題、幫忙查證一些資料的時候,我們報社會有該領域相關人士的電話、住址的共用檔案。比方說,我如果是調到一個地方去跑警察線,那麼基本上我們的記者會把所有警察幹部的地址、電話蒐集整理完備,共享給該線的記者,我們藉此可以晚上到他們家去採訪,這都是年年積累、一個個找到的消息情報。
但是在台灣,我會被同樣一家電視台的記者要十五次手機,因為每次來訪的人都不一樣,每次都重新來一遍:「啊,矢板先生您好,我是記者某某某,我們可以交換一下Line嗎?」就是今天採訪這個消息,明天採訪那個消息,又來要我的電話、我的Line。有時候他們到我家門口要進行拍攝,雖然是同一家電視台,地址又要我再給一次,就是他們每個人之間互相都沒有分享資訊。
但是在日本的話,如果是我負責這個議題的話,比如說《產經新聞》負責中國報導的幾位記者,都是一個團隊,也許今天我去,也許明天A去、後天B去⋯⋯就一定是這個團隊的那幾位記者,但是台灣記者好像就是「今天誰值班誰去」那種感覺。所以說,訊息的共有在台灣是沒有的。另外一個,就是你講了很多基本的知識也要從頭再講一遍,好像對於特定議題的專業資訊積累不多,因為很年輕的女孩子幾年以後就轉成主播,或者去選里長啊,或者是跨界當公關經理⋯⋯(眾人大笑)有各種各樣的其他職涯發展可能性。然後又換一批年輕人,這個部分是沒有積累的。
喬伊斯:最近的例子就是台北市政府的副發言人徐政璿三十歲,他說他是資深媒體人,經手過上萬篇的稿子之類的,這讓很多真正的資深媒體人不以為然,我記得馮光遠就發文大大地諷刺了一番。
菲爾以前在輔大的學生是徐的同學,這個學生去了澳洲,最近回來找我們出去吃飯。他說:「喬伊斯妳知道嗎?『學姊』黃瀞瑩跟這個副發言人都是我同班同學。」我說:「哇,人家那麼厲害,你現在在幹嘛?」他說:「我現在在一家餐廳裡面學做壽司。」跟他一樣大的同學,號稱都當過記者,一個當過副發言人然後當市議員,現在又有一個當了副發言人。
他們到底有什麼樣的資歷我不是很清楚,或許他們在新聞方面曾經有優秀或是傑出的表現?也許他們的公關或者表達能力很好,我也看不出來。在新聞方面,你一方面說新聞記者沒有太多的素養或者累積的知識,但偏偏又有這麼多的政治人物或者是企業,去找些沒有經驗的花瓶草包當他的發言人,只因為他們曾經當過記者。所以這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造成很多年輕貌美腦袋空空,特別是女孩子去當記者,因為她們知道很快就會因為外貌被找去做別的事情。
李志德:我覺得可以講回最初劉文正的那個事情,為什麼被迫要用單一消息來源(single source story)?因為沒有人有第二消息來源(second source),也就是說,你夠資深了才有second source。
所以在劉文正的新聞裡面,誰最先開始懷疑?是《聯合報》的楊起鳳,她是夠資深的,雖然她一開始也相信了夏玉順講的話。新聞就先做,然後她打了第二個、第三個電話。然後這第二、第三個電話說:「咦?不對喔。」所以最一開始發現不對的是《聯合報》的一位資深記者,這位資深記者她一直留在這個工作上。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的主要媒體裡面,這種資深的記者,要不你就去當長官,每天忙著做行政工作,要不就根本沒有辦法長久地留在這個位置上,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如果比較一下《路透社》裡面,待五年以上的記者有多少?十年以上的有多少?日本五年以上、十年以上資歷的記者有多少?台灣五年以上、十年以上資歷的記者又有多少?我覺得這個一看就知道了,就是說,記者的資深程度決定了他的專業程度嘛。
第二個就是說,你沒有資深的記者也就算了,其他還包括路線的部署,其實現在全部都在往後撤。譬如說以日本NHK來講,NHK肯定在地方有佈線。我不知道他的部署有多密集,不過你很難想像,日本有哪一個地方縣市只有一個記者或者甚至沒有記者的。但是台灣現在的電視台,哪怕號稱全國性的電視台,都很少在一個縣市能夠維持派駐一個記者,包括《公共電視》在內。這個是我對於蔡英文政府、對於文化部最不滿的地方,就是說經過了八年執政,我們的公視沒有辦法在每一個縣市都有足夠的地方記者。
正常情況下,地方政治應該是地方記者要監督的,但是我們的政府不願意投資在非常基礎的建設上面,讓我們每一個地方都有足夠的記者,而且是「公廣集團來的記者」——所以我不怕你這些縣市政府,我也不跟你縣市政府拿標案,也不拿業配,我就是監督你!蔡英文執政八年連這件事都做不到,不可原諒。
菲爾:是的,我也是認為這樣,台灣的新聞沒有被嚴肅對待,例如電視上我看到的主播長相都差不多,我懷疑他們是不是同一個工廠製造出來的。
台灣媒體和民主一樣,還是非常年輕,目前還是受國民黨建制派的影響,許多人長大的環境或多或少有意無意,都在這個影響之下,建制派的組織仍然控制著許多政治事務。
在英國,你早上去車站,有《社會主義工人報》(Socialist Worker)這種非常左翼報紙,也可以看到法西斯主義的東西,還有介於兩者之間的媒體,人們有非常廣泛的選擇。和台灣相比,英國媒體非常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一九六六年問世、單頁雙面印刷的《倫敦公報》 (London Gazette )被認為是英國的第一份報紙,因此英國媒體的深入和廣泛是有跡可循的。但即使歷史悠久非常成熟,在某種程度上不少英國媒體,尤其是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報紙,也還是建制派的一部分,他們往往是右翼。
就社會階層而言,例如高級法官、高級警察,這類建制派通常也是右翼保守派。但是除此之外,也有像《路透社》和其他一些媒體這樣沒有傾向的主要媒體,還有 BBC,在某種程度上也算。
根據我對台灣的認識,建制派的影響一樣是真實存在的。擁有實權的人是建制派的一部分,也就是國民黨。建制派這些人當年掌控著戒嚴時期的台灣,許多人是在那個環境下長大的,所以建制派仍然對整個政治局勢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包括媒體。
民進黨即使現在執政也還不是建制派,因為民進黨不是像國民黨這樣的老牌政黨,就我所知他們雖然在國會是多數,但是在地方政府還是少數。這一點從在媒體的影響力就看得出來,建制派不希望真相一直流傳開來,他們想控制媒體,這就是問題。
國民黨和媒體政治傾向的關係,有歷史的因素在裡面。在英國媒體也是如此,甚至包括教會也屬於建制派,你可以看到,所有有權力的人都傾向於成為建制派的一部分,例如傳統的英國媒體大亨,都是有權勢,社會階層較高的人。
在美國也可以看到這個情形,例如福斯電視台。主要的右翼媒體是當權派,而在那些根本沒有公平新聞的國家,媒體是當權派經營的。我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台灣有這個現象,在英國也還是。
李志德:我們這個部分是從假新聞開始談,剛剛聽完一輪,包括我自己所講的,在菲爾講話的時候,我突然有一個感想,我認為很不幸,因為我們所講的「假新聞其實是由多種因素產生的」,討論台灣的狀況時就會發現,我們所有的因素都是最適合假新聞成長的,也就是說台灣是一個各方面都適合假新聞快速成長的環境,所以我們今天承受了這個後果。
第二節 台灣媒體現況與假新聞
6. 偏頗、仇恨、有聞必錄、假新聞、娛樂化⋯⋯台灣媒體有救嗎?
喬伊斯:所以像《路透社》或《產經》這種傳統媒體的做法,我想現在在台灣的媒體應該是非常少見了。比方說我記得還在當記者的時候,每天早上要開一個會,然後到下午的時候還要開一個會。新聞會議是這樣子,就是分社社長從他的位子上站起來宣布開晨間會議,大家放下手邊的工作很快討論一下今天有什麼大新聞。誰誰誰有沒有辦法去哪裡參加記者會,沒有辦法的話誰誰誰要去支援,大概五分鐘、十分鐘吧。然後到快下班之前,還會再來個五分鐘、十分鐘,檢討一下今天做了什麼事情,明天會有什麼大新聞。
我不曉得台灣媒體現在的工作模式如何,網路世代應該也不一樣了,不過我看電視上發問的記者,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專業可言,問的問題常常非常愚蠢。他們跟政治人物或是受訪者講話的態度也是一點都不專業,這個問題我覺得在台灣非常普遍。
我不當記者很久了,不過比方說我派駐新加坡,或者我在東南亞採訪的時候,好像也沒有看到這麼不專業的情況,台灣許多記者是很沒有專業、沒有素養的。不知道現在的日本,年輕記者是不是跟台灣的一樣,有類似的情形嗎?
矢板明夫:不知道,我到台灣也發現這種現象,台灣記者都是超級年輕的,而且基本上,就是年輕女孩子特別多。我個人認為,比如說我在日本的時候,去《產經新聞》社會部幫忙,我們要調查一個完全不懂的議題、幫忙查證一些資料的時候,我們報社會有該領域相關人士的電話、住址的共用檔案。比方說,我如果是調到一個地方去跑警察線,那麼基本上我們的記者會把所有警察幹部的地址、電話蒐集整理完備,共享給該線的記者,我們藉此可以晚上到他們家去採訪,這都是年年積累、一個個找到的消息情報。
但是在台灣,我會被同樣一家電視台的記者要十五次手機,因為每次來訪的人都不一樣,每次都重新來一遍:「啊,矢板先生您好,我是記者某某某,我們可以交換一下Line嗎?」就是今天採訪這個消息,明天採訪那個消息,又來要我的電話、我的Line。有時候他們到我家門口要進行拍攝,雖然是同一家電視台,地址又要我再給一次,就是他們每個人之間互相都沒有分享資訊。
但是在日本的話,如果是我負責這個議題的話,比如說《產經新聞》負責中國報導的幾位記者,都是一個團隊,也許今天我去,也許明天A去、後天B去⋯⋯就一定是這個團隊的那幾位記者,但是台灣記者好像就是「今天誰值班誰去」那種感覺。所以說,訊息的共有在台灣是沒有的。另外一個,就是你講了很多基本的知識也要從頭再講一遍,好像對於特定議題的專業資訊積累不多,因為很年輕的女孩子幾年以後就轉成主播,或者去選里長啊,或者是跨界當公關經理⋯⋯(眾人大笑)有各種各樣的其他職涯發展可能性。然後又換一批年輕人,這個部分是沒有積累的。
喬伊斯:最近的例子就是台北市政府的副發言人徐政璿三十歲,他說他是資深媒體人,經手過上萬篇的稿子之類的,這讓很多真正的資深媒體人不以為然,我記得馮光遠就發文大大地諷刺了一番。
菲爾以前在輔大的學生是徐的同學,這個學生去了澳洲,最近回來找我們出去吃飯。他說:「喬伊斯妳知道嗎?『學姊』黃瀞瑩跟這個副發言人都是我同班同學。」我說:「哇,人家那麼厲害,你現在在幹嘛?」他說:「我現在在一家餐廳裡面學做壽司。」跟他一樣大的同學,號稱都當過記者,一個當過副發言人然後當市議員,現在又有一個當了副發言人。
他們到底有什麼樣的資歷我不是很清楚,或許他們在新聞方面曾經有優秀或是傑出的表現?也許他們的公關或者表達能力很好,我也看不出來。在新聞方面,你一方面說新聞記者沒有太多的素養或者累積的知識,但偏偏又有這麼多的政治人物或者是企業,去找些沒有經驗的花瓶草包當他的發言人,只因為他們曾經當過記者。所以這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造成很多年輕貌美腦袋空空,特別是女孩子去當記者,因為她們知道很快就會因為外貌被找去做別的事情。
李志德:我覺得可以講回最初劉文正的那個事情,為什麼被迫要用單一消息來源(single source story)?因為沒有人有第二消息來源(second source),也就是說,你夠資深了才有second source。
所以在劉文正的新聞裡面,誰最先開始懷疑?是《聯合報》的楊起鳳,她是夠資深的,雖然她一開始也相信了夏玉順講的話。新聞就先做,然後她打了第二個、第三個電話。然後這第二、第三個電話說:「咦?不對喔。」所以最一開始發現不對的是《聯合報》的一位資深記者,這位資深記者她一直留在這個工作上。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的主要媒體裡面,這種資深的記者,要不你就去當長官,每天忙著做行政工作,要不就根本沒有辦法長久地留在這個位置上,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如果比較一下《路透社》裡面,待五年以上的記者有多少?十年以上的有多少?日本五年以上、十年以上資歷的記者有多少?台灣五年以上、十年以上資歷的記者又有多少?我覺得這個一看就知道了,就是說,記者的資深程度決定了他的專業程度嘛。
第二個就是說,你沒有資深的記者也就算了,其他還包括路線的部署,其實現在全部都在往後撤。譬如說以日本NHK來講,NHK肯定在地方有佈線。我不知道他的部署有多密集,不過你很難想像,日本有哪一個地方縣市只有一個記者或者甚至沒有記者的。但是台灣現在的電視台,哪怕號稱全國性的電視台,都很少在一個縣市能夠維持派駐一個記者,包括《公共電視》在內。這個是我對於蔡英文政府、對於文化部最不滿的地方,就是說經過了八年執政,我們的公視沒有辦法在每一個縣市都有足夠的地方記者。
正常情況下,地方政治應該是地方記者要監督的,但是我們的政府不願意投資在非常基礎的建設上面,讓我們每一個地方都有足夠的記者,而且是「公廣集團來的記者」——所以我不怕你這些縣市政府,我也不跟你縣市政府拿標案,也不拿業配,我就是監督你!蔡英文執政八年連這件事都做不到,不可原諒。
菲爾:是的,我也是認為這樣,台灣的新聞沒有被嚴肅對待,例如電視上我看到的主播長相都差不多,我懷疑他們是不是同一個工廠製造出來的。
台灣媒體和民主一樣,還是非常年輕,目前還是受國民黨建制派的影響,許多人長大的環境或多或少有意無意,都在這個影響之下,建制派的組織仍然控制著許多政治事務。
在英國,你早上去車站,有《社會主義工人報》(Socialist Worker)這種非常左翼報紙,也可以看到法西斯主義的東西,還有介於兩者之間的媒體,人們有非常廣泛的選擇。和台灣相比,英國媒體非常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一九六六年問世、單頁雙面印刷的《倫敦公報》 (London Gazette )被認為是英國的第一份報紙,因此英國媒體的深入和廣泛是有跡可循的。但即使歷史悠久非常成熟,在某種程度上不少英國媒體,尤其是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報紙,也還是建制派的一部分,他們往往是右翼。
就社會階層而言,例如高級法官、高級警察,這類建制派通常也是右翼保守派。但是除此之外,也有像《路透社》和其他一些媒體這樣沒有傾向的主要媒體,還有 BBC,在某種程度上也算。
根據我對台灣的認識,建制派的影響一樣是真實存在的。擁有實權的人是建制派的一部分,也就是國民黨。建制派這些人當年掌控著戒嚴時期的台灣,許多人是在那個環境下長大的,所以建制派仍然對整個政治局勢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包括媒體。
民進黨即使現在執政也還不是建制派,因為民進黨不是像國民黨這樣的老牌政黨,就我所知他們雖然在國會是多數,但是在地方政府還是少數。這一點從在媒體的影響力就看得出來,建制派不希望真相一直流傳開來,他們想控制媒體,這就是問題。
國民黨和媒體政治傾向的關係,有歷史的因素在裡面。在英國媒體也是如此,甚至包括教會也屬於建制派,你可以看到,所有有權力的人都傾向於成為建制派的一部分,例如傳統的英國媒體大亨,都是有權勢,社會階層較高的人。
在美國也可以看到這個情形,例如福斯電視台。主要的右翼媒體是當權派,而在那些根本沒有公平新聞的國家,媒體是當權派經營的。我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台灣有這個現象,在英國也還是。
李志德:我們這個部分是從假新聞開始談,剛剛聽完一輪,包括我自己所講的,在菲爾講話的時候,我突然有一個感想,我認為很不幸,因為我們所講的「假新聞其實是由多種因素產生的」,討論台灣的狀況時就會發現,我們所有的因素都是最適合假新聞成長的,也就是說台灣是一個各方面都適合假新聞快速成長的環境,所以我們今天承受了這個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