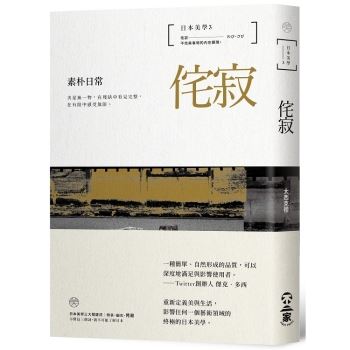〈和敬清寂〉
和,是和諧、愉悅。
茶道的可貴之處之一,在於打破日本封建時代嚴格的階級制度。在茶室中,人無分貴賤,茶禪一味,佛我一如。禪宗主張淡泊、無用,以不念利益的清淨本心,去體驗和的境地。茶道將禪宗的自然觀化為藝術形式,一方茶室在空間上收斂了人心的距離,讓美的環境與人格奏出「和」的樂章。
在茶道中,「和」支配了整個過程,不僅形式上要和諧,精神上也要愉悅,茶室中的精神就在和之下建立。和,也存在於視覺、嗅覺、聽覺、觸覺中。舉例來說,茶室斜頂低檐的設計只讓少許日光進入,室內的光線柔和,茶室內部一切的色調都樸素,賓客的衣著不能唐突,讓空間適合冥想;瀰漫在茶室中的氣味,不會太過強烈;茶室外,風聲與茶爐沸水聲相和;茶碗的優劣,不在於外形而是手感,茶會主人會思考賓客握起茶碗時感受到的重量、溫度、觸感。
進入茶室,必須先經過躙口,躙口的設計極為狹小,用意即是讓參與者將地位或財富置於室外。進入茶室就是和平的世界,茶會中所有人地位平等,抱持敬意……
〈不易流行的根本意義〉
追求新奇的點,追求超越新舊的平靜,是「不易」;追隨時刻變化的風尚並有嶄新發揮者,是「流行」。俳諧追求新,在不斷的變化下具流行性,因此具有不易的本質。不易,是俳諧需要實現的永恆的價值,而流行,則是在此實踐下不斷變化的樣貌。──松尾芭蕉
在斷絕與一切「生命」的體驗與交涉下,思考純粹的自然,或寂然不動、萬古不易的實在性才具有可能性。當然,在哲學上,這個問題還有種種議論空間,但俳諧不是哲學,在這一點上,它並不是要表示一種明確的世界觀。
我們可以想像,俳諧受到佛教思想、老莊思想深厚的影響,寂當中的自然感情或世界感情,是在千變萬化的自然現象中,看出所有千古不易、寂莫不易的事物(或許是有如「虛無」的深淵),並將它的發展導向隱微曖昧與預感的方向。就寂的藝術本質而言,一方面它隨著變化的「生」流動,高度地實現了想掌握自然姿態的企圖;另一方面,它暗示了一種與形而上、萬古不易的寂然相對的強烈預感。寂,企圖藉由極度純化、精練的藝術手段,掌握這個世界的直接與真實。然而,即使是最低限的客觀表現手段,「體驗的現實」本身,重要的到底不是表現內容,而是落於「表現的素材」。舉例來說,一個色彩的色調到了一定程度,飽和度無法再提高,但是如果把它與對照色並列,在我們的眼中它的色調就會顯得更鮮明……
然而,在我看來,傑出的俳句中,經常能感覺到一種如影隨形的東西,假如我們把它視為句子的「姿」的問題(「姿」這個詞非常曖昧,但絕對不單純等於「形式」)來看待,並就此來看影子的深淺濃淡,那麼必然也會涉及芭蕉俳論中的「不易流行」。在這個問題上,向井去來(見註1)等人的「不易流行」論,視野過於局限於形式論。而服部土芳在《三冊子》(見註2)中說:「不拘於變化流行,立於誠的是姿。」此句話亦說明了「不易」包含的深刻意義。
在寂的藝術表現中,生的體驗,會永遠地流動並照出新的光。在永劫不易的「古老」中表現的美,也就是「寂」的本質所在。至此,「寂」的「宿」、「老」、「古」的概念,就超越了人類的「生命」或「精神」的情感價值,透過一種形而上的實在的預感,往完全特定的方向轉化為美學。
下文中芭蕉的許多名句,若是在心中細細玩味,可以感受到「不易流行」的妙諦,也就是生動的體驗流動的底處,橫洩著深淵般的靜謐,是蒼古幽寂。
「古老池塘啊,一隻青蛙跳下水,咚」
「滲入岩石或閑寂中的,是蟬的聲音」
「鳥棲枯枝,秋日的黃昏」
「海邊落日下,鴨鳴聲聲白」
【註1】向井去來(1651—1704):江戶時代中期俳人,松尾芭蕉的門生,著有《去來抄》、《旅寢論》等俳論書。
【註2】《三冊子》:江戶時代中期俳人福部土芳(1657—1730)所著的俳諧論書,分為《赤冊子》《白冊子》《黑冊子》三冊,各別闡述俳諧由源起乃至松尾芭蕉風格成立的流變,松尾芭蕉與自身的文學理論,以及心得雜記。
和,是和諧、愉悅。
茶道的可貴之處之一,在於打破日本封建時代嚴格的階級制度。在茶室中,人無分貴賤,茶禪一味,佛我一如。禪宗主張淡泊、無用,以不念利益的清淨本心,去體驗和的境地。茶道將禪宗的自然觀化為藝術形式,一方茶室在空間上收斂了人心的距離,讓美的環境與人格奏出「和」的樂章。
在茶道中,「和」支配了整個過程,不僅形式上要和諧,精神上也要愉悅,茶室中的精神就在和之下建立。和,也存在於視覺、嗅覺、聽覺、觸覺中。舉例來說,茶室斜頂低檐的設計只讓少許日光進入,室內的光線柔和,茶室內部一切的色調都樸素,賓客的衣著不能唐突,讓空間適合冥想;瀰漫在茶室中的氣味,不會太過強烈;茶室外,風聲與茶爐沸水聲相和;茶碗的優劣,不在於外形而是手感,茶會主人會思考賓客握起茶碗時感受到的重量、溫度、觸感。
進入茶室,必須先經過躙口,躙口的設計極為狹小,用意即是讓參與者將地位或財富置於室外。進入茶室就是和平的世界,茶會中所有人地位平等,抱持敬意……
〈不易流行的根本意義〉
追求新奇的點,追求超越新舊的平靜,是「不易」;追隨時刻變化的風尚並有嶄新發揮者,是「流行」。俳諧追求新,在不斷的變化下具流行性,因此具有不易的本質。不易,是俳諧需要實現的永恆的價值,而流行,則是在此實踐下不斷變化的樣貌。──松尾芭蕉
在斷絕與一切「生命」的體驗與交涉下,思考純粹的自然,或寂然不動、萬古不易的實在性才具有可能性。當然,在哲學上,這個問題還有種種議論空間,但俳諧不是哲學,在這一點上,它並不是要表示一種明確的世界觀。
我們可以想像,俳諧受到佛教思想、老莊思想深厚的影響,寂當中的自然感情或世界感情,是在千變萬化的自然現象中,看出所有千古不易、寂莫不易的事物(或許是有如「虛無」的深淵),並將它的發展導向隱微曖昧與預感的方向。就寂的藝術本質而言,一方面它隨著變化的「生」流動,高度地實現了想掌握自然姿態的企圖;另一方面,它暗示了一種與形而上、萬古不易的寂然相對的強烈預感。寂,企圖藉由極度純化、精練的藝術手段,掌握這個世界的直接與真實。然而,即使是最低限的客觀表現手段,「體驗的現實」本身,重要的到底不是表現內容,而是落於「表現的素材」。舉例來說,一個色彩的色調到了一定程度,飽和度無法再提高,但是如果把它與對照色並列,在我們的眼中它的色調就會顯得更鮮明……
然而,在我看來,傑出的俳句中,經常能感覺到一種如影隨形的東西,假如我們把它視為句子的「姿」的問題(「姿」這個詞非常曖昧,但絕對不單純等於「形式」)來看待,並就此來看影子的深淺濃淡,那麼必然也會涉及芭蕉俳論中的「不易流行」。在這個問題上,向井去來(見註1)等人的「不易流行」論,視野過於局限於形式論。而服部土芳在《三冊子》(見註2)中說:「不拘於變化流行,立於誠的是姿。」此句話亦說明了「不易」包含的深刻意義。
在寂的藝術表現中,生的體驗,會永遠地流動並照出新的光。在永劫不易的「古老」中表現的美,也就是「寂」的本質所在。至此,「寂」的「宿」、「老」、「古」的概念,就超越了人類的「生命」或「精神」的情感價值,透過一種形而上的實在的預感,往完全特定的方向轉化為美學。
下文中芭蕉的許多名句,若是在心中細細玩味,可以感受到「不易流行」的妙諦,也就是生動的體驗流動的底處,橫洩著深淵般的靜謐,是蒼古幽寂。
「古老池塘啊,一隻青蛙跳下水,咚」
「滲入岩石或閑寂中的,是蟬的聲音」
「鳥棲枯枝,秋日的黃昏」
「海邊落日下,鴨鳴聲聲白」
【註1】向井去來(1651—1704):江戶時代中期俳人,松尾芭蕉的門生,著有《去來抄》、《旅寢論》等俳論書。
【註2】《三冊子》:江戶時代中期俳人福部土芳(1657—1730)所著的俳諧論書,分為《赤冊子》《白冊子》《黑冊子》三冊,各別闡述俳諧由源起乃至松尾芭蕉風格成立的流變,松尾芭蕉與自身的文學理論,以及心得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