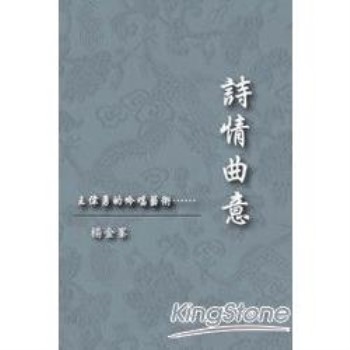緒 論
詩
是用朗誦、吟誦還是詠唱,都有其風味以及樂趣,這種音樂性十足的文學體,其實就是一首歌的歌詞。雖然中國的音樂理論發展早於東周,並且已趨完備,根據一些古文獻的考證,如《呂覽》、《樂記》 等證明至少在秦帝國成立之前,五聲十二律的樂音結構已經十分成熟。我們知道西方從七聲音樂發展到完整音律體系的出現,過程不下千年,甚至於到今日為止,西方的十二音律還沒有單獨的音名,但在西元十世紀之後,西方修道院修士們從一條紅線開始,創造了記錄音樂的線譜系統,並且成為目前最有效能的記譜技法。這種源自曲線紐碼 (cheironomic neume) 的記譜技術,有效地以比擬空間的方式,呈現個別樂音彼此之間的關係,引用視覺的形象類比出音樂的結構,成為西方音樂理論的發展基礎,促使隨之而來的各種音樂理論出現,然而中國仍然停留在文字譜的階段,並沒有發展出完備而通行的作曲法則,一般的音樂理論是經驗法則的歸納整理,進而形成系統性理論,根據系統性理論的推演,可以得出進一步的理論發展。目前中國傳統音樂的作曲法,其中較為明確的,是根據聲韻與聲調進行創作的詩詞吟唱,詞文創作等於提供詩人吟唱新調的依據,詩人即是作曲家,至於不諳聲律的文士也可以按固定的讀冊調填寫新詞,那就不是作曲,是填詞。
歌曲創作從十分講究聲調,到完全不考慮聲調與音調的關係,有著不同程度的音樂現象,分別是古典詩詞要求聲調與音調完全相符;其次,一般歌謠容許部分的偏誤;最後,是完全不考慮聲調的人聲音樂。
工尺譜,文字記音譜,只記述音樂的骨架音;另一種文字譜是聲名譜,兩者性質一樣,只是把工尺換為聲名 (宮商角徵羽)。演唱時,其節奏與實際聲音佐以即興的詮釋,同一人唱同一工尺譜,也會有不同的變化。【靜夜思】的工尺譜並不是取自古籍,而是根據工尺譜的記譜原則,將通行的鹿港調【靜夜思】吟唱曲調,採譯為工尺。本書其他幾首工尺譜皆然。這是還原、分析的工作,找出吟唱曲調的骨架音,以工尺記譜。為方便【靜夜思】工尺譜與五線譜的對照,製作譜例 2,其節拍並不確定。
諸如鹿港讀冊調的情況,工尺譜只記述音樂的框架,其實,實際演唱時,有一定程度的即興成分,若以西方五線譜的標準來評度,工尺譜僅是記錄基本的樂音,而不是完整的音樂;換個立場,這種記譜的態度,也給了演奏家最大的表現空間,充分地呈現出中國的音樂美學觀。傳統戲曲與音樂演奏最適合工尺譜的特性,我們可以在youtube網上聽到新北市二重國中南管團指導老師陳筱玟的影音教學,演唱【娘子有心】的工尺譜。 對於工尺譜陌生的人而言,聽起來很像是在唱一首歌,而歌詞就是「上、尺、工、凡、六、五、乙」,因為唱出來的樂音是有變化的,不同於西方一個音名只有一個相對音高的形態。影片開頭聽到的第一個譜字是「乙」,但是,改用西方記譜法表示,其實是la, mi兩個音,這種記譜與實際演唱的差異,使得很多學西樂的孩子不太能理解,為什麼老樂人每次唱同一首工尺時,總會有一些不同的變化出現。清楚了工尺譜的道理,也就清楚了部分的中國音樂美學觀;這種美學態度最終發展出幫腔式複音樂音──支聲複音 (heterophone,或譯為異音音樂)。南管音樂就是一個例子,一管 (洞簫)、二弦、三弦、四弦 (琵琶) 都演奏同一份譜,但也各自依據樂器的特質,以及聲部所扮演的音樂角色,而有各自的旋律變化,這種充滿生命力的音樂反映出文字譜的特性。東、西方人文環境的差異,誕生出不同的記譜法則,可見,工尺譜與五線譜背後含帶著文化的特質,西式五線譜以類比概念將音樂轉換為可視的圖象,有助於邏輯思考;工尺譜以字符表示樂音,形成簡單的提示作用,實際的音樂仍然保有相當的即興可能性,同一工尺可以搭配不同情意的詞文,佐以語言聲調的特質,形成多樣化的音樂表現。
此外,由於南管簫形制固定,以致南管的工尺譜向來被視為固定調唱譜,「乙」聲對應G音;「固定唱名法、首調唱名法」與「絕對音感、相對音感」的關係有些需要重新釐清,說起來還有點複雜:我們不能把固定唱名法和絕對音感兩者直接劃上等號,對絕對音感者而言440hz就是唱la,而固定唱名法也要求鋼琴上A鍵必須唱為la,不要忘了,A鍵左右的黑鍵,也都有唱為la的機會。南管音樂因洞簫型制 所限,使得工尺有了固定對應的樂音,然而,這只是形式上的固定唱名法,不表示演奏者具有絕對音感的能力,更不表示南管樂人唱「乙」音,就是五線譜的某音。自從西方音樂理論引進中國後,不少學者在研究南管時,習慣使用較為普及的西樂理論名稱,以致普遍認為南管工尺有其相對應的西樂音名,影片中陳老師以南管琵琶來伴奏,沒有先與洞簫對音,起音較高,導致「乙」字唱到接近la的音高,對於相對音感者而言,根本就聽不出來唱譜有什麼問題,學界習慣將「乙」字對應sol的概念,在此並沒有任何的實質意義,只對於絕對音感者或使用五線譜的人,南管固定唱名的問題才會形成理解上的焦點,此時工尺譜字需要譯成五線譜上的那個音,才具有理論上的意義與價值。
古老的音樂多數以歌曲為主,無聲調的西方印歐語系有格利果聖歌 (gregorian chant),中國的旋律型聲調語言自然而然以聲調做為旋律的基礎。語言即是歌調。語言所具備的音樂性,有音調高低、節奏迴蕩、音色多樣等特質。一般日常出現的閩南語對話,高、低音約在五度範圍;語言中成組的詞彙,乃至句式產生的呼吸,都具有節奏的效果;因為聲韻 發聲位置的不同,加上腔體共鳴的效果,人聲最能酣暢淋漓表現情感,是音色最為豐富的樂器,這應該就是桓溫 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的原由。古樂器所使用的材料以及當時工藝技術的成熟度等因素,使得絲絃樂器的表現力 不如竹管樂器,而人聲又以多變音色、隨心所欲的音量變化,勝出絲竹樂器;隨著樂器製作的工藝技術提昇後,人聲的表現力也就不一定比器樂強,要看是採什麼樣的標準,我們只要比較木笛 (recorder) 和長笛 (flute) 的表現力,即可明白其間的差異。然而,人聲也因為器樂演進,受到了一定影響,像是美聲唱法 (belcanto) 係因應器樂的強大音量,在歌劇表演中,必須將人聲發聲的共鳴技巧推到臻境,以抗衡器樂的音量,器樂與聲樂長期時間的相互影響,使得聲樂曲也出現了器樂的慣用音形,W. A. Mozart 歌劇《魔笛》(Die Zauberflote) 夜后演唱的著名詠嘆調【仇恨的火焰】(Der Holle Rache) 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樂曲;反觀旋律型聲調語言所衍生出來的聲樂曲,當然也會充分呈現聲調對音樂的影響。
漢藏語系的聲調可分為平聲、滑聲和迴聲,再加上短收束的聲調 (入聲調),可有多種變化,閩南語聲調以高平聲、中平聲、低平聲、下滑聲、上滑聲及入聲 (平聲收短、高上滑聲) 為主。應用這些聲調時,都必須考慮前後音的關係,基本上不會完全符合音高的走勢。聲調與音樂的結合,亦受到「詞組」單位的影響,詞組會侷限節奏的應用,以及聽者對詞文內容的辨識度。簡單地說,節奏會影響我們的辨識能力,閩南語以入聲聲調最具有特殊性。為了簡化說明,先不考慮詞組關係,只觀照於入聲字的唱法;由於普通話的入聲聲調已失,不需要加意處理,使得普通話的詩詞吟唱曲調,少了某些音形特徵,音樂中各類音形的應用即是產生音樂風格的一項要素,所以不同語言環境所產生的歌曲,其實是各自具有一些不易說清楚的質性,雖然偶爾會聽到這方面的論述,但多半是描述感覺,較少論理分析。同一首歌曲使用不同語言演唱,多少可以呈現詮釋的方言聲音特徵,例如鄧雨賢的【十八姑娘一朵花】,大家熟悉國語版的聲音,其實這首歌最初係以日語歌詞寫成,後來又有閩南語及粵語的版本,日語版的演唱聽起來是「粘乎乎、軟柔而嬌」,國語版的聲音則是每個音節都斷得乾乾淨淨地,這種現象除了是演唱者的詮釋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國語本來就比日語強調抑揚頓挫的語音,因此曲調中的重音節會被凸顯出來,演唱者只要略加強調,聽起來就是顆粒分明的感覺,自然而然就少了日語嬌柔纏綿的情意;再比較閩南語版的詮釋,入聲字使得聲音的分隔感更為清楚。此處僅以【十八姑娘一朵花】為例,說明語言對於音樂意味的影響,並不是全面性的比較,換不同的曲調,像是臺灣的南管曲風,閩南語也可以表現出軟綿的意味,畢竟影響音樂意味的因素甚多,並非只有語言一項。
吟唱閩南古典詩詞曲調,能不能把入聲字表現出來,涉及到旋律型聲調語言的特質,我們以王偉勇先生的聲音資料為藍本,分析幾個入聲字的詮釋,整理出閩南語幾種處理入聲聲調的手法。大抵上可分為:
1. 頓音並收聲 (頓斷音 );
2. 頓音斷,再補聲延音;
3. 長音加頓聲。即頓音不斷聲,這種唱法是先處理入聲聲調的感覺,再拉長音,用於需要長音表現的時候。
4. 尾音頓斷。先拉長音,收尾時加頓斷音;
5. 裝飾音。使用碎音 (碎滑音)、迴音等裝飾音強調入聲字,音樂進行中出現裝飾音,必然形成一個注意點,在演唱時略稍使力再急收音量。
以王先生在2011年9月24日「異地vs.在地藝術風格表現音樂會」上獻唱岳飛【滿江紅】為例,歌曲開頭兩句「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髮」是入聲字,直接用頓斷節奏處理,這個短重的小停頓讓隨後的字,衝出氣勢。其後為了表現歌曲的句法,拉長「歇」與「烈」兩入聲字,這是因應音樂句型需要所做的詮釋,但為了凸顯入聲聲調的特性,就以上述表現法的第四種,急收突強來表現句尾的入聲字。然而,近來的閩南歌謠並沒有這麼講究入聲聲調的處理,人們憑著認知的偏誤,修正聽到的歌詞,儘管入聲字唱成其他的聲調,但是辨認歌詞文本的過程,模糊比對了記憶裏的文字,還是可以識別出入聲字。
詩
是用朗誦、吟誦還是詠唱,都有其風味以及樂趣,這種音樂性十足的文學體,其實就是一首歌的歌詞。雖然中國的音樂理論發展早於東周,並且已趨完備,根據一些古文獻的考證,如《呂覽》、《樂記》 等證明至少在秦帝國成立之前,五聲十二律的樂音結構已經十分成熟。我們知道西方從七聲音樂發展到完整音律體系的出現,過程不下千年,甚至於到今日為止,西方的十二音律還沒有單獨的音名,但在西元十世紀之後,西方修道院修士們從一條紅線開始,創造了記錄音樂的線譜系統,並且成為目前最有效能的記譜技法。這種源自曲線紐碼 (cheironomic neume) 的記譜技術,有效地以比擬空間的方式,呈現個別樂音彼此之間的關係,引用視覺的形象類比出音樂的結構,成為西方音樂理論的發展基礎,促使隨之而來的各種音樂理論出現,然而中國仍然停留在文字譜的階段,並沒有發展出完備而通行的作曲法則,一般的音樂理論是經驗法則的歸納整理,進而形成系統性理論,根據系統性理論的推演,可以得出進一步的理論發展。目前中國傳統音樂的作曲法,其中較為明確的,是根據聲韻與聲調進行創作的詩詞吟唱,詞文創作等於提供詩人吟唱新調的依據,詩人即是作曲家,至於不諳聲律的文士也可以按固定的讀冊調填寫新詞,那就不是作曲,是填詞。
歌曲創作從十分講究聲調,到完全不考慮聲調與音調的關係,有著不同程度的音樂現象,分別是古典詩詞要求聲調與音調完全相符;其次,一般歌謠容許部分的偏誤;最後,是完全不考慮聲調的人聲音樂。
工尺譜,文字記音譜,只記述音樂的骨架音;另一種文字譜是聲名譜,兩者性質一樣,只是把工尺換為聲名 (宮商角徵羽)。演唱時,其節奏與實際聲音佐以即興的詮釋,同一人唱同一工尺譜,也會有不同的變化。【靜夜思】的工尺譜並不是取自古籍,而是根據工尺譜的記譜原則,將通行的鹿港調【靜夜思】吟唱曲調,採譯為工尺。本書其他幾首工尺譜皆然。這是還原、分析的工作,找出吟唱曲調的骨架音,以工尺記譜。為方便【靜夜思】工尺譜與五線譜的對照,製作譜例 2,其節拍並不確定。
諸如鹿港讀冊調的情況,工尺譜只記述音樂的框架,其實,實際演唱時,有一定程度的即興成分,若以西方五線譜的標準來評度,工尺譜僅是記錄基本的樂音,而不是完整的音樂;換個立場,這種記譜的態度,也給了演奏家最大的表現空間,充分地呈現出中國的音樂美學觀。傳統戲曲與音樂演奏最適合工尺譜的特性,我們可以在youtube網上聽到新北市二重國中南管團指導老師陳筱玟的影音教學,演唱【娘子有心】的工尺譜。 對於工尺譜陌生的人而言,聽起來很像是在唱一首歌,而歌詞就是「上、尺、工、凡、六、五、乙」,因為唱出來的樂音是有變化的,不同於西方一個音名只有一個相對音高的形態。影片開頭聽到的第一個譜字是「乙」,但是,改用西方記譜法表示,其實是la, mi兩個音,這種記譜與實際演唱的差異,使得很多學西樂的孩子不太能理解,為什麼老樂人每次唱同一首工尺時,總會有一些不同的變化出現。清楚了工尺譜的道理,也就清楚了部分的中國音樂美學觀;這種美學態度最終發展出幫腔式複音樂音──支聲複音 (heterophone,或譯為異音音樂)。南管音樂就是一個例子,一管 (洞簫)、二弦、三弦、四弦 (琵琶) 都演奏同一份譜,但也各自依據樂器的特質,以及聲部所扮演的音樂角色,而有各自的旋律變化,這種充滿生命力的音樂反映出文字譜的特性。東、西方人文環境的差異,誕生出不同的記譜法則,可見,工尺譜與五線譜背後含帶著文化的特質,西式五線譜以類比概念將音樂轉換為可視的圖象,有助於邏輯思考;工尺譜以字符表示樂音,形成簡單的提示作用,實際的音樂仍然保有相當的即興可能性,同一工尺可以搭配不同情意的詞文,佐以語言聲調的特質,形成多樣化的音樂表現。
此外,由於南管簫形制固定,以致南管的工尺譜向來被視為固定調唱譜,「乙」聲對應G音;「固定唱名法、首調唱名法」與「絕對音感、相對音感」的關係有些需要重新釐清,說起來還有點複雜:我們不能把固定唱名法和絕對音感兩者直接劃上等號,對絕對音感者而言440hz就是唱la,而固定唱名法也要求鋼琴上A鍵必須唱為la,不要忘了,A鍵左右的黑鍵,也都有唱為la的機會。南管音樂因洞簫型制 所限,使得工尺有了固定對應的樂音,然而,這只是形式上的固定唱名法,不表示演奏者具有絕對音感的能力,更不表示南管樂人唱「乙」音,就是五線譜的某音。自從西方音樂理論引進中國後,不少學者在研究南管時,習慣使用較為普及的西樂理論名稱,以致普遍認為南管工尺有其相對應的西樂音名,影片中陳老師以南管琵琶來伴奏,沒有先與洞簫對音,起音較高,導致「乙」字唱到接近la的音高,對於相對音感者而言,根本就聽不出來唱譜有什麼問題,學界習慣將「乙」字對應sol的概念,在此並沒有任何的實質意義,只對於絕對音感者或使用五線譜的人,南管固定唱名的問題才會形成理解上的焦點,此時工尺譜字需要譯成五線譜上的那個音,才具有理論上的意義與價值。
古老的音樂多數以歌曲為主,無聲調的西方印歐語系有格利果聖歌 (gregorian chant),中國的旋律型聲調語言自然而然以聲調做為旋律的基礎。語言即是歌調。語言所具備的音樂性,有音調高低、節奏迴蕩、音色多樣等特質。一般日常出現的閩南語對話,高、低音約在五度範圍;語言中成組的詞彙,乃至句式產生的呼吸,都具有節奏的效果;因為聲韻 發聲位置的不同,加上腔體共鳴的效果,人聲最能酣暢淋漓表現情感,是音色最為豐富的樂器,這應該就是桓溫 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的原由。古樂器所使用的材料以及當時工藝技術的成熟度等因素,使得絲絃樂器的表現力 不如竹管樂器,而人聲又以多變音色、隨心所欲的音量變化,勝出絲竹樂器;隨著樂器製作的工藝技術提昇後,人聲的表現力也就不一定比器樂強,要看是採什麼樣的標準,我們只要比較木笛 (recorder) 和長笛 (flute) 的表現力,即可明白其間的差異。然而,人聲也因為器樂演進,受到了一定影響,像是美聲唱法 (belcanto) 係因應器樂的強大音量,在歌劇表演中,必須將人聲發聲的共鳴技巧推到臻境,以抗衡器樂的音量,器樂與聲樂長期時間的相互影響,使得聲樂曲也出現了器樂的慣用音形,W. A. Mozart 歌劇《魔笛》(Die Zauberflote) 夜后演唱的著名詠嘆調【仇恨的火焰】(Der Holle Rache) 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樂曲;反觀旋律型聲調語言所衍生出來的聲樂曲,當然也會充分呈現聲調對音樂的影響。
漢藏語系的聲調可分為平聲、滑聲和迴聲,再加上短收束的聲調 (入聲調),可有多種變化,閩南語聲調以高平聲、中平聲、低平聲、下滑聲、上滑聲及入聲 (平聲收短、高上滑聲) 為主。應用這些聲調時,都必須考慮前後音的關係,基本上不會完全符合音高的走勢。聲調與音樂的結合,亦受到「詞組」單位的影響,詞組會侷限節奏的應用,以及聽者對詞文內容的辨識度。簡單地說,節奏會影響我們的辨識能力,閩南語以入聲聲調最具有特殊性。為了簡化說明,先不考慮詞組關係,只觀照於入聲字的唱法;由於普通話的入聲聲調已失,不需要加意處理,使得普通話的詩詞吟唱曲調,少了某些音形特徵,音樂中各類音形的應用即是產生音樂風格的一項要素,所以不同語言環境所產生的歌曲,其實是各自具有一些不易說清楚的質性,雖然偶爾會聽到這方面的論述,但多半是描述感覺,較少論理分析。同一首歌曲使用不同語言演唱,多少可以呈現詮釋的方言聲音特徵,例如鄧雨賢的【十八姑娘一朵花】,大家熟悉國語版的聲音,其實這首歌最初係以日語歌詞寫成,後來又有閩南語及粵語的版本,日語版的演唱聽起來是「粘乎乎、軟柔而嬌」,國語版的聲音則是每個音節都斷得乾乾淨淨地,這種現象除了是演唱者的詮釋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國語本來就比日語強調抑揚頓挫的語音,因此曲調中的重音節會被凸顯出來,演唱者只要略加強調,聽起來就是顆粒分明的感覺,自然而然就少了日語嬌柔纏綿的情意;再比較閩南語版的詮釋,入聲字使得聲音的分隔感更為清楚。此處僅以【十八姑娘一朵花】為例,說明語言對於音樂意味的影響,並不是全面性的比較,換不同的曲調,像是臺灣的南管曲風,閩南語也可以表現出軟綿的意味,畢竟影響音樂意味的因素甚多,並非只有語言一項。
吟唱閩南古典詩詞曲調,能不能把入聲字表現出來,涉及到旋律型聲調語言的特質,我們以王偉勇先生的聲音資料為藍本,分析幾個入聲字的詮釋,整理出閩南語幾種處理入聲聲調的手法。大抵上可分為:
1. 頓音並收聲 (頓斷音 );
2. 頓音斷,再補聲延音;
3. 長音加頓聲。即頓音不斷聲,這種唱法是先處理入聲聲調的感覺,再拉長音,用於需要長音表現的時候。
4. 尾音頓斷。先拉長音,收尾時加頓斷音;
5. 裝飾音。使用碎音 (碎滑音)、迴音等裝飾音強調入聲字,音樂進行中出現裝飾音,必然形成一個注意點,在演唱時略稍使力再急收音量。
以王先生在2011年9月24日「異地vs.在地藝術風格表現音樂會」上獻唱岳飛【滿江紅】為例,歌曲開頭兩句「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髮」是入聲字,直接用頓斷節奏處理,這個短重的小停頓讓隨後的字,衝出氣勢。其後為了表現歌曲的句法,拉長「歇」與「烈」兩入聲字,這是因應音樂句型需要所做的詮釋,但為了凸顯入聲聲調的特性,就以上述表現法的第四種,急收突強來表現句尾的入聲字。然而,近來的閩南歌謠並沒有這麼講究入聲聲調的處理,人們憑著認知的偏誤,修正聽到的歌詞,儘管入聲字唱成其他的聲調,但是辨認歌詞文本的過程,模糊比對了記憶裏的文字,還是可以識別出入聲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