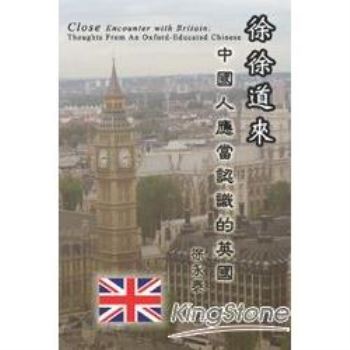徐徐道來/徐永泰
這一本書是在我的“牛津留痕”一書出版(2003)三年後,也就是2006年之後的心得和思路的匯集。在此必須要特別一提的是,2006 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重要決定年,因為這年是我在1974拿了牛津大學的哲學碩士(M.Litt.)的三十二年後,決定再重返牛津大學,修讀了經濟史博士(D.Phil.)。以一個當時已經快邁入六十歲的我,重新進入博士班與年輕人為伍,在研究所裡與教授,和種種學術書本刊物,共渡過近四年的孤寂和拼搏歲月,說不容易,一點兒也不為過;在這一本書的第一章裡,我將當時掙扎矛盾的心路歷程,和最終取得博士的經過,做了一個實況還原的報導。
我先後在1970、1980,直到2010年,跨過四十年頭,分別在英國渡過將近九年的光景:1971-1974年先是在牛津大學研究所做學生,畢業後的1977-1978年在倫敦工作,2006年秋天又開始牛津大學博士班研究生的生涯,在2006到2010年之間,護照上的英國移民局蓋章的數目告訴我,來回英國多達23次,可以說,我對英國這個國家並不陌生。甚至可以說我對英國的認知和認識,超過一般留學生。這個在牛津大學的最後四年生涯記錄,雖然可以做為我想寫這一本書的背景和收集寫作資料的基礎,但是,它並不是這本書的主題,我的主要期望是藉著這本書讓讀者對英國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像是一篇學術論文一樣,我最先想到的是,看這本書的讀者會問,為什麼要寫這一本書?為什麼要寫英國的歷史文化種種?現在資訊這麼發達,只要上網查查,就能了解英國的一般知識,有必要再做詮釋,再畫蛇添足嗎?我的回答是:“有必要”。我們國人對英國了解的不夠多,或者說我們了解的還真的太少,或者我們不想去多了解,因為我們怕面對中國曾經與英國互動的那一段歷史,太叫人傷痛,太不想重提檢討;或者說,我們了解英國,遠遠沒有英國了解中國的多。我常想這一個問題,我們中國對英國的了解多少,是不是斤斤兩兩地決定了我們中國的歷史命運?當然這種說法,需要很多的舉證,很多的論點,再多的學術報告和博士論文,也難以達到目的。宏觀近代歷史,我們中國深受英國殖民主義的影響,實在是不爭的事實。從英國十九世紀中工業革命開始,全球推展殖民主義,掠奪弱小國家或地區各種資源,領土版圖擴充,從歐洲英倫海峽出發,遍及全球五大洲,當其勢力進入亞洲之際,印度首先成為它的殖民地基地,透過殖民白手套東印度公司,再穿過東南亞,來到中國,以印度和東南亞種植的鴉片,做為其商船和戰艇燃料的交換品。鴉片戰爭(1839-42年)中國的大門從此洞開;兩次英法聯軍(1858 & 1860年),中日甲午戰爭(1894年),中俄密約(1896年),義和團和八國聯軍(1900年),導致最後的滿清專制王朝的終結(1911年),後來中華民國的成立也是短短的曇花一現,緊接著是中國軍閥割據,內戰與抗日戰爭交叉拖垮中國的底氣,一直到 1980年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在中國的南方深圳起始,中國元氣才開始慢慢復原興盛。
中國人對待這一段中國近代史的態度,我粗分以下三種:第一種是不想去再細細地去看,因為太傷痛,太難過,不看可以不必觸動那曾經被灼燙的民族疤痕;第二種是現在中國已經慢慢改善,甚至強大起來了,那麼又何必再往過去看?第三種是想看看過去的創傷,是否能夠學到一些經驗,不再犯過去的錯誤。我不贊同第一和第二種,但是在第三種裡面,我們必須花很多的時間和努力,來做分析,比較,只看自己民族的被傷害是不夠的,必須看看那傷害我們的民族是怎麼思考,怎麼行動的。
我常想一個問題;我們對日本侵略中國疆土,屠殺強姦中國人民的種種行徑,像是在腦海中永遠除不去的記憶,隨時都可以拿出來看,拿出來惱恨。中國受到鄰居日本的欺負,是不是中國當時是個軟柿子?那麼導致讓中國一蹶不振的英國,來自於跨過三洋二洲,萬里之外的殖民始祖--英國,我們幾乎又全忘了?1937年中日戰爭開始,英國與國民黨政府在中南半島居然又成了聯盟來對付日本,這種矛盾的關係,我們沒有好好省思。中華民國在1911年成立的時候,英國一直到1935年才正式承認,1937年才在南京設立領事館。可是在當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的時候,英國卻又是率先與中國建立關係的西方國家之一。她的“沒有永久敵人,也沒有永久朋友”的外交思維,到底告訴了我們什麼?在全球的殖民主義裡,英國絕對是中國近代興亡衰敗史的始作蛹者,和最大的影響勢力。我在台灣政大研究所,和英國牛津大學研究求學時,每當讀到中國近代史的這一段渾渾噩噩的悲慘歲月和絕望難已的年代,心裡總是揪成一團,即使在1970年代,赴英國讀書之始使,心理仍是五味雜陳,愛恨交錯,說不出是喜是悲?
我的青年時代在牛津成長,我的思維在英國成熟,當然孤寂歲月在那一段日子中讓我比較情緒化,對人和事物的看法,難免有時偏激。可也就是那一段日子,讓我記錄下當時的英國人文點點滴滴,如今看來又以“牛津留痕”的內容,重新審視,可以比較和看出我當初沒有注意到的地方。當時我下筆的時候,我開始注意到,英國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國家,在文化和歷史方面不說,就是在地理環境,地形交通,生活習慣,語言文字,和待人接物等方方面面都不是很容易說清楚的,很多說英語的美國人,待在英國數十年,也還沒有搞清楚英國的一點點。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大英帝國歷史的轉折點,大戰後,英國也開始隨著世界的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影響而變化。殖民地紛紛獨立,各自為政。英國也因此大大地傷了元氣,氣還沒有喘過來,接著希特勒的納粹黨引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是讓英國再次一下子摔了個大跤。雖然是二次大戰的戰勝國,但原有的勢力,看來不再持續,從大戰結束後的數十年,英國國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不搭調的平行發展,更是叫人看得眼花繚亂。
是不是因為英國不再是十九世紀的全球霸主,讓我們對這個國家不再或減少了關注?還是因為我們對她的了解不夠,就認為她已經真的衰敗無能,把我們的注意力全放在美國身上了?我常想這個問題,到底可不可以找到答案。這本書探討的方向很多,它不是純學術性的,因為太學術的,缺乏普羅大眾讀者的共鳴,但它也絕對不是順手拈來,不嚴肅就也無論點基礎。倒不如說它是一個通過思想上的詮釋,把我們中國人對英國體制文化和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將不清楚的盲點澄清,有誤解的地方更正,在有欠公允之處還以公正,有低估的層面給予正確的定位。當然,這裡面必須是公正和客觀的,我們自己必須反省自己對英國的認知有多少,對它在這世界舞台中的角色是什麼,不止是一個陳腔敘述而已,必須是一個全盤品質和表現的評估。
我在2003年寫的書“牛津留痕”裡的有一篇“英國人保守嗎?”,曾經是這樣敘述英國的:問“英國人是不是保守的?”倒不如問我們自己的觀念與他們的觀念有多少不同。對於理性的接受與應用的幅度誰大?我個人以為英國人在群體利益的追求上表現的是理性,在個人生活上所追求的和期望的是安靜與次序,獨立和創造,只有在種族優越感的自我陶醉下所反應的才是“保守”。我四十年前的看法,如今看來,也許稍有改變,並沒有偏失。
一個曾經擁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四億五千萬)的殖民霸權,和統治世界四分之一領域的大不列顛,一個曾經是日不落國的大英帝國,它如今還留下什麼?這真是值得推敲的問題。維多利亞王朝(Queen Victoria)傳承的議會制度,看來在未來的世代,還不會消失。英語的推廣,英國文化的延續,看來也並?有斷了層。甚至大英國協的組織,仍舊存在和擴充。在1931年以後成立的英國國協(British Commonwealth)還有五十四個國家。甚至在1949年的倫敦會議裡還推崇當時的喬治六世,為英協的領袖。國際上的各種標準,譬如銀行金融法,保險制度,船運系統和法規,以及數不盡的組織和模式,都以英國的創始規章和陸續的完善為依據。一個七千萬人不到的海島國家,一個幅員不到日本三分之二的領土,到底具有多少世界舞台的經濟,政治,軍事,和科技上的影響力?這真是越想越有趣的問題,我真誠地希望我們看到的不只是披頭士(Beatles)、迷你裙、職業足球、陳年威士忌、哈利.波特、白金漢宮的衛士更換、英國女王的生日、黛安娜王妃的死亡之謎、威廉王子的婚禮,我希望中國人了解的英國不止是這些。
回過頭來,看看我們中國如何受到英國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那更是數說不盡。先撇開政治上的種種因果關係、經濟上在中國的關稅制度、銀行金融體系、保險法規,到處都看到英國過去留下的影子。在社會上,在中國的社交圈流行的運動,舞蹈,稱呼,也躲不過英國人的影響力反射。語言上,中國和台灣一直到近幾十年,才把英國的“Wade-Giles”拼音法捨棄,採取世界普用的漢字羅馬拼音。很多人到如今可能都還不清楚,他的張姓為什麼是拼成Chang,而不是Zhang。姓徐的,拼成Hsu,而不是Xu。關於這些,我會在這一本書中慢慢解說。
這本書總共有十章,第一章裡我將我在牛津三十年前後的生活對比和心得分享,這可能是最主觀的,最情緒的自我檢驗,那不是讀者需要了解或認識的英國,那只是一個學子的生活經歷,唯一與一般留學生不一樣的是,我先後去同一個地方唸書,中間相隔32年。為什麼要去,去了的思維方式是否不一樣,會在這一章裡,找到答案。在這一章裡,也告訴讀者我寫這本書的背景和思維基礎。
接著,我由淺入深帶著讀者暸解中國人應當認識的英國:從歐洲之內,還是歐洲之外的英國?(第二章)探討英國人的歸屬感是在歐洲還是獨立於歐洲之外?歐洲人眼中的英國,拿破崙怎麼評論她?看看除了美國和亞非洲,還有什麼其他的視野,能夠把英國定位得更恰當。開始說起,重新探討一個民主的歷史發展(第三章)與表現在現代英國的生活和社會裡的實際反映,由英國社會主義的穩定根源--貧窮法案(第四章),英國的牛津與統治階級淵源與臍帶關係(第五章),談到英國酒館文化的真諦和它的名與實(第六章)我們也在這個前殖民主義的始祖家裡,找找看看她還有沒有殖民的殘念(第七章)。我企圖把讀者帶進大英博物館,看看英國怎麼把這個世界各地文化歷史,濃縮到你可以一目然。也進一步了解英國是如何收刮世界文化遺產,又如何矛盾地處理這些展示品的(第八章)。我也像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記者一樣,探討BBC如何從帝國主義蛻變, 而重新以世界的宏觀作公平的訴求(第九章);我也介紹英國人非常驕傲的全民信託基金會(National Trust),告訴大家英國人民不同凡響的社會主義的思維,如何保護文化遺產和自然景觀 (第十章)。這都是個很有趣的題目,讓我們怎麼去認識這一個曾經讓近代中國做了一百年的噩夢:遠在萬里之外的英倫三島。
總的來說,這本書的目的是讓讀者,尤其是懂中文,了解中國文化的人,特別是我們華夏子民,對英國有更進一步的了解,確實認識這個曾經影響近代中國衰敗百年不振的大不列顛的過去和現在,也相對的對我們自己在世界的舞台上,有更進一步的自省反思,如果我們真實對待自己,那也許是好事,在歷史上,我們能有一個清晰的,客觀的和理性的看法,讓我們不在歷史的巨輪下重蹈覆轍,讓我們華人於未來的歲月裡,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我們朝向世界的理性的榜樣或趨勢發展。這也許是這一本書希望達到的目標之一。
現在,讓我徐徐道來……
===
第一章:“回到未來”:“牛津留痕”三十年前與後
“那條彎彎長長的路,引我到了你的門前,它從未消失,我曾經看過的,總是在夢中帶我去你那兒。那夜刮起狂風,暴雨漂過後,留下了我滿眶淚水。我孤獨地站在那裡,為什麼找不到回家的路?多少日子我一個人單獨地過?,多少次我獨自地哭了,多少方法我曾試過,還是要我走回這彎彎長長的路。我站在那裡很久很久了,別再讓我等啊,帶我回到你的門前吧。” ”--英國披頭士保羅.麥卡尼 (Paul McCartney)
再赴牛津的原由:噩夢連連
2003年我出版了第一本““牛津留痕”,那是記載我1971-1974年在牛津大學讀書時的經歷和感想,書出版之後,我有了一種新的念頭,我第一次拿到牛津碩士時候是1974年,接著在美國的船運公司工作了7年,1981年開始自己創業,到了2003年出書的時候,已經有了將近30年的工作經歷,我始終覺得我自己學得還不夠,有機會的話,我還是要去唸書,最好再讀點有用的,可以思想的。
事實上,從英國畢業之後,我到了美國,無論打工也好,自己創業也好,我的睡眠品質一直很差,經常半夜做夢驚醒,奇怪的是夢中總是圍繞著那一段在牛津大學三年半的痛苦經歷,那包括了學業研究的過程和壓力,英國天氣的寒冷和潮濕,英國食物的難以下嚥,生活環境的不適,和經濟狀況的窘困。雖然我最終是畢業了,可是我總是覺得我在英國這三年半的學業成績是“慘勝”,所以每次夢到在牛津的日子,我就一身冷汗驚醒和傷感地回顧,這種半夜噩夢的情況,持續了將近三十年。有一次我對我的私人醫生提起,他告訴我,我現在的生活穩定,經濟條件還算優渥,也許我最好是再去牛津大學過一次無憂無慮或比較健康的生活,從心裡把我在牛津的苦日子,徹底翻盤,我的噩夢現象就會改善。我當時還半信半疑,後來諮詢了一些心理醫生,他們也同意這是一種治療方法,但是不知道要透過什麼樣的方法,花多久的時間和多大的代價。像是“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電影一樣,我要跨過時空,飛回到三十年前的日子,再過一次。
2004年牛津大學在紐約有一個校友會,我與Murad Sunalp 一起飛到紐約,Murad是我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的同學,目前是眼科醫生,在加州中部執業。我們白天參加了校友會的座談會,晚上又赴聖約翰學院單獨舉辦的學院校友聚餐。碰到的同學,因為不同年次,晚餐聚會與校友的談話內容,就圍繞著聖約翰學院。 院長Sir Michael Scholar 走過來寒暄,問起我目前從事哪一行,生活如何等等。我心血來潮,突然問起院長,如果我現在以校友身份回去做做研究,有機會嗎?院長很直接的回答我說,你為什麼不乾脆回牛津大學再唸一個學位?
回牛津再讀一個學位?我當時心想,我已經56歲,雖然讀書所需要的經濟條件不再是個問題,但是我的確因為事業的關係,很久沒有碰書本了,現在再來唸書,還行嗎?我再問院長,如果我想,那麼我該怎麼進行?院長說,現在申請牛津大學,都是網上進行,如果申請被大學入學部門接受,申請書會繼續由大學轉到聖約翰學院,如果到了聖約翰,他保證一定會提供宿舍給我。牛津大學很小,八百年的歷史建築,不容許拆建和擴充,宿舍少而緊張,每年只能接受四千人左右,申請的程序是多層的,第一,必須通過入學部門的許可。第二,必須通過各學院的許可。第一關是學科的鑑定,第二關是學院的審核,第二關非常關鍵,如果不過,就沒有宿舍的分配,沒有宿舍的分配,那麼什麼都白搭,在牛津大學唸書,住在外面是不可能的,一般的研究生都有要求至少住兩年的規定。當院長給了我這個宿舍的口頭承諾後,我相當高興,那麼剩下的就看我自己能不能找一個研究項目,被學校接受。這是我決定再度申請牛津大學的第一個契機。
申請與年齡的考量
2005年的5月我開始申請牛津大學2006年度的入學許可,我在申請的時候,沒有告訴任何人,包括我的家人,我想申請只是一個形式,如果失敗,也不影響我的目前生活,申請成功,我可以去,如果公司忙我也可以不去,這個學位對一個已經有事業的我來說並不是非拿不可的,所以選擇權在我,我完全不在意。不像一般學生同時去申請很多學校,我只申請了一個大學,就是牛津,我慢慢地寫我的讀書計劃,我知道那是申請讀博士班最重要的一環。也因為如此,我的構思和在企業界的經驗,讓我在申請的時候,填寫的內容與實際應用最接近,所以申請的手續對我來說,比年輕的學子容易多了。我決定寫一個汽車發動機與汽車工業相關性的論文,題目選定,就待牛津大學幫我尋找適合的導師,不久牛津大學認為我的題目有創意,找到兩位能夠指導我的導師,在這一方面,算是蠻順利的。
比較麻煩的是在推薦信方面:首先,學校要求三封學術界的介紹信函,試想,我已經57歲,教過我的師長,不是已經作古,就是退休不知道到哪兒去了。還好,我找到以前我讀政大時候的王俊助教,這時他已經是政大的系主任,王老師非常幫忙,說你自己寫吧,我簽字就好。這是第一封,搞定。第二封,我找了美國汽車業汽車協會的主席,Ms. Karen Fierst,她也一口答應,寫了過來,這封信在申請上來說,算是蠻勉強的。第三封我實在找不出最適合和能夠幫我寫的人。我想起聖約翰的院長Sir Michael Scholar,他雖然沒有教過我,做過我的導師,但是至少他鼓勵過我重新來牛津大學申請。我寫了封信給他請求,他也欣然答應。他在寫完之後,寄給牛津大學的同時,給了我一份副本,內容簡潔,但是讀起來非常有趣:
“......徐永泰先生曾經在1974年聖約翰學院拿過碩士,現在在美國工作,他顯示出他強烈的企圖心,和想要繼續研究和追求讀博士的意願。我贊同徐先生的意願。我覺得徐先生讀博士的申請,絕對不能以他的年紀作為拒絕他的理由。”
我後來想,牛津大學再次接受我唸博士,這一封介紹信是很關鍵的。
2006年的5月,牛津大學和聖約翰學院同時通知我被錄取。我一時反應不過來,因為公司業務很忙,作為公司的總裁,我不能說去唸書就放下一切,畢竟公司還有一百多員工,我的唸書是全職的,如果公司經營不善,那麼唸這個學位,就會變成搞垮公司的最大原因。我想了又想,只好與內人麗韡商量。她說可以暫時代我擔當起公司的職務,可是懷疑我去牛津大學這樣嚴格的學府,已經快到耳順之年的我,身體吃得消嗎?腦力還應付得了嗎?書唸得下去唸不下去?我對她說,連聖約翰學院院長Sir Michael Scholar 都告訴牛津大學不可以我的年紀,來判斷我唸書的能力。我把院長的介紹信給她看。告訴她,如果真唸不下去,我就返回,沒有什麼損失。公司的業務已上軌道,從電腦的網路看公司的營運狀況,也不是問題。
在七月的時候,我下定決心,去吧。
這一本書是在我的“牛津留痕”一書出版(2003)三年後,也就是2006年之後的心得和思路的匯集。在此必須要特別一提的是,2006 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重要決定年,因為這年是我在1974拿了牛津大學的哲學碩士(M.Litt.)的三十二年後,決定再重返牛津大學,修讀了經濟史博士(D.Phil.)。以一個當時已經快邁入六十歲的我,重新進入博士班與年輕人為伍,在研究所裡與教授,和種種學術書本刊物,共渡過近四年的孤寂和拼搏歲月,說不容易,一點兒也不為過;在這一本書的第一章裡,我將當時掙扎矛盾的心路歷程,和最終取得博士的經過,做了一個實況還原的報導。
我先後在1970、1980,直到2010年,跨過四十年頭,分別在英國渡過將近九年的光景:1971-1974年先是在牛津大學研究所做學生,畢業後的1977-1978年在倫敦工作,2006年秋天又開始牛津大學博士班研究生的生涯,在2006到2010年之間,護照上的英國移民局蓋章的數目告訴我,來回英國多達23次,可以說,我對英國這個國家並不陌生。甚至可以說我對英國的認知和認識,超過一般留學生。這個在牛津大學的最後四年生涯記錄,雖然可以做為我想寫這一本書的背景和收集寫作資料的基礎,但是,它並不是這本書的主題,我的主要期望是藉著這本書讓讀者對英國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像是一篇學術論文一樣,我最先想到的是,看這本書的讀者會問,為什麼要寫這一本書?為什麼要寫英國的歷史文化種種?現在資訊這麼發達,只要上網查查,就能了解英國的一般知識,有必要再做詮釋,再畫蛇添足嗎?我的回答是:“有必要”。我們國人對英國了解的不夠多,或者說我們了解的還真的太少,或者我們不想去多了解,因為我們怕面對中國曾經與英國互動的那一段歷史,太叫人傷痛,太不想重提檢討;或者說,我們了解英國,遠遠沒有英國了解中國的多。我常想這一個問題,我們中國對英國的了解多少,是不是斤斤兩兩地決定了我們中國的歷史命運?當然這種說法,需要很多的舉證,很多的論點,再多的學術報告和博士論文,也難以達到目的。宏觀近代歷史,我們中國深受英國殖民主義的影響,實在是不爭的事實。從英國十九世紀中工業革命開始,全球推展殖民主義,掠奪弱小國家或地區各種資源,領土版圖擴充,從歐洲英倫海峽出發,遍及全球五大洲,當其勢力進入亞洲之際,印度首先成為它的殖民地基地,透過殖民白手套東印度公司,再穿過東南亞,來到中國,以印度和東南亞種植的鴉片,做為其商船和戰艇燃料的交換品。鴉片戰爭(1839-42年)中國的大門從此洞開;兩次英法聯軍(1858 & 1860年),中日甲午戰爭(1894年),中俄密約(1896年),義和團和八國聯軍(1900年),導致最後的滿清專制王朝的終結(1911年),後來中華民國的成立也是短短的曇花一現,緊接著是中國軍閥割據,內戰與抗日戰爭交叉拖垮中國的底氣,一直到 1980年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在中國的南方深圳起始,中國元氣才開始慢慢復原興盛。
中國人對待這一段中國近代史的態度,我粗分以下三種:第一種是不想去再細細地去看,因為太傷痛,太難過,不看可以不必觸動那曾經被灼燙的民族疤痕;第二種是現在中國已經慢慢改善,甚至強大起來了,那麼又何必再往過去看?第三種是想看看過去的創傷,是否能夠學到一些經驗,不再犯過去的錯誤。我不贊同第一和第二種,但是在第三種裡面,我們必須花很多的時間和努力,來做分析,比較,只看自己民族的被傷害是不夠的,必須看看那傷害我們的民族是怎麼思考,怎麼行動的。
我常想一個問題;我們對日本侵略中國疆土,屠殺強姦中國人民的種種行徑,像是在腦海中永遠除不去的記憶,隨時都可以拿出來看,拿出來惱恨。中國受到鄰居日本的欺負,是不是中國當時是個軟柿子?那麼導致讓中國一蹶不振的英國,來自於跨過三洋二洲,萬里之外的殖民始祖--英國,我們幾乎又全忘了?1937年中日戰爭開始,英國與國民黨政府在中南半島居然又成了聯盟來對付日本,這種矛盾的關係,我們沒有好好省思。中華民國在1911年成立的時候,英國一直到1935年才正式承認,1937年才在南京設立領事館。可是在當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的時候,英國卻又是率先與中國建立關係的西方國家之一。她的“沒有永久敵人,也沒有永久朋友”的外交思維,到底告訴了我們什麼?在全球的殖民主義裡,英國絕對是中國近代興亡衰敗史的始作蛹者,和最大的影響勢力。我在台灣政大研究所,和英國牛津大學研究求學時,每當讀到中國近代史的這一段渾渾噩噩的悲慘歲月和絕望難已的年代,心裡總是揪成一團,即使在1970年代,赴英國讀書之始使,心理仍是五味雜陳,愛恨交錯,說不出是喜是悲?
我的青年時代在牛津成長,我的思維在英國成熟,當然孤寂歲月在那一段日子中讓我比較情緒化,對人和事物的看法,難免有時偏激。可也就是那一段日子,讓我記錄下當時的英國人文點點滴滴,如今看來又以“牛津留痕”的內容,重新審視,可以比較和看出我當初沒有注意到的地方。當時我下筆的時候,我開始注意到,英國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國家,在文化和歷史方面不說,就是在地理環境,地形交通,生活習慣,語言文字,和待人接物等方方面面都不是很容易說清楚的,很多說英語的美國人,待在英國數十年,也還沒有搞清楚英國的一點點。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大英帝國歷史的轉折點,大戰後,英國也開始隨著世界的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影響而變化。殖民地紛紛獨立,各自為政。英國也因此大大地傷了元氣,氣還沒有喘過來,接著希特勒的納粹黨引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是讓英國再次一下子摔了個大跤。雖然是二次大戰的戰勝國,但原有的勢力,看來不再持續,從大戰結束後的數十年,英國國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不搭調的平行發展,更是叫人看得眼花繚亂。
是不是因為英國不再是十九世紀的全球霸主,讓我們對這個國家不再或減少了關注?還是因為我們對她的了解不夠,就認為她已經真的衰敗無能,把我們的注意力全放在美國身上了?我常想這個問題,到底可不可以找到答案。這本書探討的方向很多,它不是純學術性的,因為太學術的,缺乏普羅大眾讀者的共鳴,但它也絕對不是順手拈來,不嚴肅就也無論點基礎。倒不如說它是一個通過思想上的詮釋,把我們中國人對英國體制文化和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將不清楚的盲點澄清,有誤解的地方更正,在有欠公允之處還以公正,有低估的層面給予正確的定位。當然,這裡面必須是公正和客觀的,我們自己必須反省自己對英國的認知有多少,對它在這世界舞台中的角色是什麼,不止是一個陳腔敘述而已,必須是一個全盤品質和表現的評估。
我在2003年寫的書“牛津留痕”裡的有一篇“英國人保守嗎?”,曾經是這樣敘述英國的:問“英國人是不是保守的?”倒不如問我們自己的觀念與他們的觀念有多少不同。對於理性的接受與應用的幅度誰大?我個人以為英國人在群體利益的追求上表現的是理性,在個人生活上所追求的和期望的是安靜與次序,獨立和創造,只有在種族優越感的自我陶醉下所反應的才是“保守”。我四十年前的看法,如今看來,也許稍有改變,並沒有偏失。
一個曾經擁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四億五千萬)的殖民霸權,和統治世界四分之一領域的大不列顛,一個曾經是日不落國的大英帝國,它如今還留下什麼?這真是值得推敲的問題。維多利亞王朝(Queen Victoria)傳承的議會制度,看來在未來的世代,還不會消失。英語的推廣,英國文化的延續,看來也並?有斷了層。甚至大英國協的組織,仍舊存在和擴充。在1931年以後成立的英國國協(British Commonwealth)還有五十四個國家。甚至在1949年的倫敦會議裡還推崇當時的喬治六世,為英協的領袖。國際上的各種標準,譬如銀行金融法,保險制度,船運系統和法規,以及數不盡的組織和模式,都以英國的創始規章和陸續的完善為依據。一個七千萬人不到的海島國家,一個幅員不到日本三分之二的領土,到底具有多少世界舞台的經濟,政治,軍事,和科技上的影響力?這真是越想越有趣的問題,我真誠地希望我們看到的不只是披頭士(Beatles)、迷你裙、職業足球、陳年威士忌、哈利.波特、白金漢宮的衛士更換、英國女王的生日、黛安娜王妃的死亡之謎、威廉王子的婚禮,我希望中國人了解的英國不止是這些。
回過頭來,看看我們中國如何受到英國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那更是數說不盡。先撇開政治上的種種因果關係、經濟上在中國的關稅制度、銀行金融體系、保險法規,到處都看到英國過去留下的影子。在社會上,在中國的社交圈流行的運動,舞蹈,稱呼,也躲不過英國人的影響力反射。語言上,中國和台灣一直到近幾十年,才把英國的“Wade-Giles”拼音法捨棄,採取世界普用的漢字羅馬拼音。很多人到如今可能都還不清楚,他的張姓為什麼是拼成Chang,而不是Zhang。姓徐的,拼成Hsu,而不是Xu。關於這些,我會在這一本書中慢慢解說。
這本書總共有十章,第一章裡我將我在牛津三十年前後的生活對比和心得分享,這可能是最主觀的,最情緒的自我檢驗,那不是讀者需要了解或認識的英國,那只是一個學子的生活經歷,唯一與一般留學生不一樣的是,我先後去同一個地方唸書,中間相隔32年。為什麼要去,去了的思維方式是否不一樣,會在這一章裡,找到答案。在這一章裡,也告訴讀者我寫這本書的背景和思維基礎。
接著,我由淺入深帶著讀者暸解中國人應當認識的英國:從歐洲之內,還是歐洲之外的英國?(第二章)探討英國人的歸屬感是在歐洲還是獨立於歐洲之外?歐洲人眼中的英國,拿破崙怎麼評論她?看看除了美國和亞非洲,還有什麼其他的視野,能夠把英國定位得更恰當。開始說起,重新探討一個民主的歷史發展(第三章)與表現在現代英國的生活和社會裡的實際反映,由英國社會主義的穩定根源--貧窮法案(第四章),英國的牛津與統治階級淵源與臍帶關係(第五章),談到英國酒館文化的真諦和它的名與實(第六章)我們也在這個前殖民主義的始祖家裡,找找看看她還有沒有殖民的殘念(第七章)。我企圖把讀者帶進大英博物館,看看英國怎麼把這個世界各地文化歷史,濃縮到你可以一目然。也進一步了解英國是如何收刮世界文化遺產,又如何矛盾地處理這些展示品的(第八章)。我也像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記者一樣,探討BBC如何從帝國主義蛻變, 而重新以世界的宏觀作公平的訴求(第九章);我也介紹英國人非常驕傲的全民信託基金會(National Trust),告訴大家英國人民不同凡響的社會主義的思維,如何保護文化遺產和自然景觀 (第十章)。這都是個很有趣的題目,讓我們怎麼去認識這一個曾經讓近代中國做了一百年的噩夢:遠在萬里之外的英倫三島。
總的來說,這本書的目的是讓讀者,尤其是懂中文,了解中國文化的人,特別是我們華夏子民,對英國有更進一步的了解,確實認識這個曾經影響近代中國衰敗百年不振的大不列顛的過去和現在,也相對的對我們自己在世界的舞台上,有更進一步的自省反思,如果我們真實對待自己,那也許是好事,在歷史上,我們能有一個清晰的,客觀的和理性的看法,讓我們不在歷史的巨輪下重蹈覆轍,讓我們華人於未來的歲月裡,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我們朝向世界的理性的榜樣或趨勢發展。這也許是這一本書希望達到的目標之一。
現在,讓我徐徐道來……
===
第一章:“回到未來”:“牛津留痕”三十年前與後
“那條彎彎長長的路,引我到了你的門前,它從未消失,我曾經看過的,總是在夢中帶我去你那兒。那夜刮起狂風,暴雨漂過後,留下了我滿眶淚水。我孤獨地站在那裡,為什麼找不到回家的路?多少日子我一個人單獨地過?,多少次我獨自地哭了,多少方法我曾試過,還是要我走回這彎彎長長的路。我站在那裡很久很久了,別再讓我等啊,帶我回到你的門前吧。” ”--英國披頭士保羅.麥卡尼 (Paul McCartney)
再赴牛津的原由:噩夢連連
2003年我出版了第一本““牛津留痕”,那是記載我1971-1974年在牛津大學讀書時的經歷和感想,書出版之後,我有了一種新的念頭,我第一次拿到牛津碩士時候是1974年,接著在美國的船運公司工作了7年,1981年開始自己創業,到了2003年出書的時候,已經有了將近30年的工作經歷,我始終覺得我自己學得還不夠,有機會的話,我還是要去唸書,最好再讀點有用的,可以思想的。
事實上,從英國畢業之後,我到了美國,無論打工也好,自己創業也好,我的睡眠品質一直很差,經常半夜做夢驚醒,奇怪的是夢中總是圍繞著那一段在牛津大學三年半的痛苦經歷,那包括了學業研究的過程和壓力,英國天氣的寒冷和潮濕,英國食物的難以下嚥,生活環境的不適,和經濟狀況的窘困。雖然我最終是畢業了,可是我總是覺得我在英國這三年半的學業成績是“慘勝”,所以每次夢到在牛津的日子,我就一身冷汗驚醒和傷感地回顧,這種半夜噩夢的情況,持續了將近三十年。有一次我對我的私人醫生提起,他告訴我,我現在的生活穩定,經濟條件還算優渥,也許我最好是再去牛津大學過一次無憂無慮或比較健康的生活,從心裡把我在牛津的苦日子,徹底翻盤,我的噩夢現象就會改善。我當時還半信半疑,後來諮詢了一些心理醫生,他們也同意這是一種治療方法,但是不知道要透過什麼樣的方法,花多久的時間和多大的代價。像是“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電影一樣,我要跨過時空,飛回到三十年前的日子,再過一次。
2004年牛津大學在紐約有一個校友會,我與Murad Sunalp 一起飛到紐約,Murad是我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的同學,目前是眼科醫生,在加州中部執業。我們白天參加了校友會的座談會,晚上又赴聖約翰學院單獨舉辦的學院校友聚餐。碰到的同學,因為不同年次,晚餐聚會與校友的談話內容,就圍繞著聖約翰學院。 院長Sir Michael Scholar 走過來寒暄,問起我目前從事哪一行,生活如何等等。我心血來潮,突然問起院長,如果我現在以校友身份回去做做研究,有機會嗎?院長很直接的回答我說,你為什麼不乾脆回牛津大學再唸一個學位?
回牛津再讀一個學位?我當時心想,我已經56歲,雖然讀書所需要的經濟條件不再是個問題,但是我的確因為事業的關係,很久沒有碰書本了,現在再來唸書,還行嗎?我再問院長,如果我想,那麼我該怎麼進行?院長說,現在申請牛津大學,都是網上進行,如果申請被大學入學部門接受,申請書會繼續由大學轉到聖約翰學院,如果到了聖約翰,他保證一定會提供宿舍給我。牛津大學很小,八百年的歷史建築,不容許拆建和擴充,宿舍少而緊張,每年只能接受四千人左右,申請的程序是多層的,第一,必須通過入學部門的許可。第二,必須通過各學院的許可。第一關是學科的鑑定,第二關是學院的審核,第二關非常關鍵,如果不過,就沒有宿舍的分配,沒有宿舍的分配,那麼什麼都白搭,在牛津大學唸書,住在外面是不可能的,一般的研究生都有要求至少住兩年的規定。當院長給了我這個宿舍的口頭承諾後,我相當高興,那麼剩下的就看我自己能不能找一個研究項目,被學校接受。這是我決定再度申請牛津大學的第一個契機。
申請與年齡的考量
2005年的5月我開始申請牛津大學2006年度的入學許可,我在申請的時候,沒有告訴任何人,包括我的家人,我想申請只是一個形式,如果失敗,也不影響我的目前生活,申請成功,我可以去,如果公司忙我也可以不去,這個學位對一個已經有事業的我來說並不是非拿不可的,所以選擇權在我,我完全不在意。不像一般學生同時去申請很多學校,我只申請了一個大學,就是牛津,我慢慢地寫我的讀書計劃,我知道那是申請讀博士班最重要的一環。也因為如此,我的構思和在企業界的經驗,讓我在申請的時候,填寫的內容與實際應用最接近,所以申請的手續對我來說,比年輕的學子容易多了。我決定寫一個汽車發動機與汽車工業相關性的論文,題目選定,就待牛津大學幫我尋找適合的導師,不久牛津大學認為我的題目有創意,找到兩位能夠指導我的導師,在這一方面,算是蠻順利的。
比較麻煩的是在推薦信方面:首先,學校要求三封學術界的介紹信函,試想,我已經57歲,教過我的師長,不是已經作古,就是退休不知道到哪兒去了。還好,我找到以前我讀政大時候的王俊助教,這時他已經是政大的系主任,王老師非常幫忙,說你自己寫吧,我簽字就好。這是第一封,搞定。第二封,我找了美國汽車業汽車協會的主席,Ms. Karen Fierst,她也一口答應,寫了過來,這封信在申請上來說,算是蠻勉強的。第三封我實在找不出最適合和能夠幫我寫的人。我想起聖約翰的院長Sir Michael Scholar,他雖然沒有教過我,做過我的導師,但是至少他鼓勵過我重新來牛津大學申請。我寫了封信給他請求,他也欣然答應。他在寫完之後,寄給牛津大學的同時,給了我一份副本,內容簡潔,但是讀起來非常有趣:
“......徐永泰先生曾經在1974年聖約翰學院拿過碩士,現在在美國工作,他顯示出他強烈的企圖心,和想要繼續研究和追求讀博士的意願。我贊同徐先生的意願。我覺得徐先生讀博士的申請,絕對不能以他的年紀作為拒絕他的理由。”
我後來想,牛津大學再次接受我唸博士,這一封介紹信是很關鍵的。
2006年的5月,牛津大學和聖約翰學院同時通知我被錄取。我一時反應不過來,因為公司業務很忙,作為公司的總裁,我不能說去唸書就放下一切,畢竟公司還有一百多員工,我的唸書是全職的,如果公司經營不善,那麼唸這個學位,就會變成搞垮公司的最大原因。我想了又想,只好與內人麗韡商量。她說可以暫時代我擔當起公司的職務,可是懷疑我去牛津大學這樣嚴格的學府,已經快到耳順之年的我,身體吃得消嗎?腦力還應付得了嗎?書唸得下去唸不下去?我對她說,連聖約翰學院院長Sir Michael Scholar 都告訴牛津大學不可以我的年紀,來判斷我唸書的能力。我把院長的介紹信給她看。告訴她,如果真唸不下去,我就返回,沒有什麼損失。公司的業務已上軌道,從電腦的網路看公司的營運狀況,也不是問題。
在七月的時候,我下定決心,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