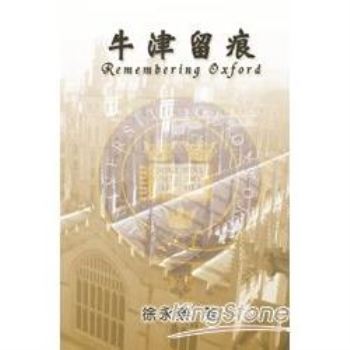寒星之訴
一九七一年六月的某天晚上,當我把決定去英國唸書的意思告訴媽時,她真的驚住了。不解地望著我,她說:「為什麼要去英國,一個沒邦交的國家?為什麼不去美國,你不是已經申請到美國學校的入學許可和免費獎學金嗎?你哥哥也在美國,可以照顧你,你若去英國,無親無友地,誰理睬你?你能自己管自己嗎?我實在不相信。我也不懂,為什麼不去美一國?大家都去……」
對於母親這一連串的問題,我實在難以回答,只有抱歉地說:
「對不起,媽,我已決定了。」
媽的表情很悵然,她從不強加她的意願給我。懷疑地,難過地,她又問:
「你真的決定了?」
我點頭。
媽求助似地看著一言不發的爸爸,從她的眼中,我可以看出她希望爸爸說些影響我的話。想不到,爸卻完全站在我這一邊,他說:
「小孩子大了,自有主張。只要出國唸書,去英去美都是一樣,沒什麼好擔憂的。
我感激地望瞭望爸爸,爸爸也望瞭望我,問:
「有沒有其他去英國的同學?」
「我不知道,但總有三、五個吧,我想。」在當時,我確實不認得任何一個可以同路的夥伴。憑著想像,總以為有人也不向東飛吧?
「你聽聽,」媽的眼淚迸在眼角上,「連個同學都沒有,一個人,孤單單地,跑到一個沒邦交的國家,人地生疏、沒人照顧,連說話都沒有對象,叫我怎麼放心?……」
說到這裏,媽的眼淚就在我面前落了下來。
這一幕的點點滴滴,至今還深深地印在我腦海中。對於媽的關心及顧慮,只有抱以無限的歉意。我,還是搭上了往歐洲的飛機。
的確,媽說的也全是事實,放棄去美,不但連我的好友難以置信,就是我自己,到現在都還驚訝我當初哪裏來的決斷力,放棄了我申請將近一年的美國學校入學許可及獎學金。事實上,這些「本錢」也下得很大。三月起我就捧著託福參考書忙進忙出,考過之後,又埋頭死啃留考科目的書籍,接著又破第三關——GRE。
應付考試,除了看書還是看書,但是申請學校的手續卻是枯燥煩人的。打信、填寫表格、查資料、請人寫介紹信、寄成績單、寫自傳、作讀書計劃、信件來往……等等這些絕大多數赴美留學生必經之途,雖然我每一步都走過,但在有了結果時,卻放棄了初衷。
使我改變初衷的原因也很簡單,那就是我心中給終不承認,也不相信去美國留學對大學畢業生就是唯一正途。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我想從這個社會風氣的潮流中跳出來,看看留美狂熱對這個社會的影響,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還有我要看看我們不太注意的另一個世界……歐洲。
早就知道來英國唸書,孤寂是免不了的,但哪裏想到在留學生講習班那一期四百多人中,我竟是唯一到「沒落的大不列顛」去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同學走向了新大陸——「黃金及膝」的美國。受訓中的「分組座談會」對我也就變成了「獨思」的時刻。
也早就知道,往歐洲的留學生是欣賞不到搭留美包機或班機,在臺北機場由成千上萬的送行者鑲織成的盛大場面。但哪裏想到,當自己搭乘由臺北赴香港晚上十時開的班機時,整個機場送客室,除了送我的親友外,就見不著幾個旅客了。這種懸殊的情況,使我在心底深處,不禁發出自問:是否我走上岔路了?是否我被反社會潮流的潛意識逼上了「歧途」?是否因為怕孤寂可能會動搖了我「自擇」前途的信心,而我卻仍剛愎自用?
我否定了這些想法,告訴自己:「小子,你現在是往西去,即使一個人橫渡印度洋,飛過歐洲大陸,這也是你自己的決定。假如你會為你用理智做的抉擇感到懷疑的話,那麼你也是個盲從的傢伙!」
坐在由香港飛倫敦的飛機上,我在心中開始計劃一些新東西。因為我知道在今後遇見的許多外國人中,有許多是需要用「地圖」來告訴他們,我從「哪兒」來的:還有許多人:是需要用耐心及友誼說服他們,我是代表中國的一個中國人;還有一部分人,是需要用自己的表現及能力去壓制他們的優越感的。如何適當、理智地運用自己,是我在飛機上接近二十,小時的行程中,像波濤般不斷衝擊著我的心。
顯然我的估計有了錯誤。在我抵達的那個月份——十月「臺灣」這個名字不僅耳熟,而且廣泛地被人討論著。我不僅沒有成為我原先計劃中採取主動的解說者,倒立刻成了完全的受訪者。一方面我慶幸自己來對了時候,無需費力去告訴別人,我從哪兒來,那是什麼地方。但另外一方面,我深深地感覺到,我面對的情況,及我應對的能力,在程度和需要上相對地都提高了。更因為我是在牛津聖約翰學院裡唯一黑頭髮、黑眼珠、黃皮膚的學生;甚至是唯一的東方人,無形中,我經常成了亞洲問題的「發言人」。我知道我的言行代表著我的國家、我的民族,我同時也影響著這些即將在英國政壇上躍起的青年及他們對中國或亞洲的看法。尤其,在這麼一個無邦交的國度裏,我以一個青年學子的身分,更應該突破現狀來做些「私人外交」。
一九七一年六月的某天晚上,當我把決定去英國唸書的意思告訴媽時,她真的驚住了。不解地望著我,她說:「為什麼要去英國,一個沒邦交的國家?為什麼不去美國,你不是已經申請到美國學校的入學許可和免費獎學金嗎?你哥哥也在美國,可以照顧你,你若去英國,無親無友地,誰理睬你?你能自己管自己嗎?我實在不相信。我也不懂,為什麼不去美一國?大家都去……」
對於母親這一連串的問題,我實在難以回答,只有抱歉地說:
「對不起,媽,我已決定了。」
媽的表情很悵然,她從不強加她的意願給我。懷疑地,難過地,她又問:
「你真的決定了?」
我點頭。
媽求助似地看著一言不發的爸爸,從她的眼中,我可以看出她希望爸爸說些影響我的話。想不到,爸卻完全站在我這一邊,他說:
「小孩子大了,自有主張。只要出國唸書,去英去美都是一樣,沒什麼好擔憂的。
我感激地望瞭望爸爸,爸爸也望瞭望我,問:
「有沒有其他去英國的同學?」
「我不知道,但總有三、五個吧,我想。」在當時,我確實不認得任何一個可以同路的夥伴。憑著想像,總以為有人也不向東飛吧?
「你聽聽,」媽的眼淚迸在眼角上,「連個同學都沒有,一個人,孤單單地,跑到一個沒邦交的國家,人地生疏、沒人照顧,連說話都沒有對象,叫我怎麼放心?……」
說到這裏,媽的眼淚就在我面前落了下來。
這一幕的點點滴滴,至今還深深地印在我腦海中。對於媽的關心及顧慮,只有抱以無限的歉意。我,還是搭上了往歐洲的飛機。
的確,媽說的也全是事實,放棄去美,不但連我的好友難以置信,就是我自己,到現在都還驚訝我當初哪裏來的決斷力,放棄了我申請將近一年的美國學校入學許可及獎學金。事實上,這些「本錢」也下得很大。三月起我就捧著託福參考書忙進忙出,考過之後,又埋頭死啃留考科目的書籍,接著又破第三關——GRE。
應付考試,除了看書還是看書,但是申請學校的手續卻是枯燥煩人的。打信、填寫表格、查資料、請人寫介紹信、寄成績單、寫自傳、作讀書計劃、信件來往……等等這些絕大多數赴美留學生必經之途,雖然我每一步都走過,但在有了結果時,卻放棄了初衷。
使我改變初衷的原因也很簡單,那就是我心中給終不承認,也不相信去美國留學對大學畢業生就是唯一正途。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我想從這個社會風氣的潮流中跳出來,看看留美狂熱對這個社會的影響,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還有我要看看我們不太注意的另一個世界……歐洲。
早就知道來英國唸書,孤寂是免不了的,但哪裏想到在留學生講習班那一期四百多人中,我竟是唯一到「沒落的大不列顛」去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同學走向了新大陸——「黃金及膝」的美國。受訓中的「分組座談會」對我也就變成了「獨思」的時刻。
也早就知道,往歐洲的留學生是欣賞不到搭留美包機或班機,在臺北機場由成千上萬的送行者鑲織成的盛大場面。但哪裏想到,當自己搭乘由臺北赴香港晚上十時開的班機時,整個機場送客室,除了送我的親友外,就見不著幾個旅客了。這種懸殊的情況,使我在心底深處,不禁發出自問:是否我走上岔路了?是否我被反社會潮流的潛意識逼上了「歧途」?是否因為怕孤寂可能會動搖了我「自擇」前途的信心,而我卻仍剛愎自用?
我否定了這些想法,告訴自己:「小子,你現在是往西去,即使一個人橫渡印度洋,飛過歐洲大陸,這也是你自己的決定。假如你會為你用理智做的抉擇感到懷疑的話,那麼你也是個盲從的傢伙!」
坐在由香港飛倫敦的飛機上,我在心中開始計劃一些新東西。因為我知道在今後遇見的許多外國人中,有許多是需要用「地圖」來告訴他們,我從「哪兒」來的:還有許多人:是需要用耐心及友誼說服他們,我是代表中國的一個中國人;還有一部分人,是需要用自己的表現及能力去壓制他們的優越感的。如何適當、理智地運用自己,是我在飛機上接近二十,小時的行程中,像波濤般不斷衝擊著我的心。
顯然我的估計有了錯誤。在我抵達的那個月份——十月「臺灣」這個名字不僅耳熟,而且廣泛地被人討論著。我不僅沒有成為我原先計劃中採取主動的解說者,倒立刻成了完全的受訪者。一方面我慶幸自己來對了時候,無需費力去告訴別人,我從哪兒來,那是什麼地方。但另外一方面,我深深地感覺到,我面對的情況,及我應對的能力,在程度和需要上相對地都提高了。更因為我是在牛津聖約翰學院裡唯一黑頭髮、黑眼珠、黃皮膚的學生;甚至是唯一的東方人,無形中,我經常成了亞洲問題的「發言人」。我知道我的言行代表著我的國家、我的民族,我同時也影響著這些即將在英國政壇上躍起的青年及他們對中國或亞洲的看法。尤其,在這麼一個無邦交的國度裏,我以一個青年學子的身分,更應該突破現狀來做些「私人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