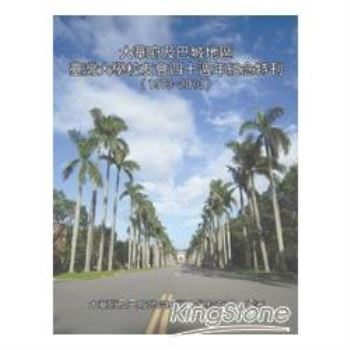高山景行 大氣磅? -懷念校長傅斯年先生
資深校友/江熙民
「國立台灣大學」是寶島台灣的最高學府,它原為日治時代的「台北帝國大學」(乃日本四個著名大學之一)。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收復台灣,將「台北帝國大學」更名為「國立台灣大學」。
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筆者就讀台大經濟學系時,校長為傅斯年先生,教務長是錢思亮先生,訓導長為傅啟學先生。沈剛伯先生為文學院院長,薩孟武先生職掌法學院。當時經濟學系隸屬於法學院(今易名為社會科學院),院址在台北市徐州路二十一號;筆者那時就住在徐州路男生第四宿舍。記得當時文、理、法三學院著名的教授為錢穆、毛子水、勞幹、王叔明、張肖松、趙麗蓮(美籍)、趙蘭坪、張果為、王師復、林霖、盛成、殷海光及筆者之岳父魏喦壽(後任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所長)等幾位專家學者。惟自光復後,台大各學院系每年不斷地擴展,迄民國八十八年底,已發展成十個學院,五十一個學系,八十一個研究所,而教授也相對的增加了數倍;已被選入世界百大之行列。
傅斯年校長字孟真,山東人,為「五四運動」的健將,他是當時被推選的二十名學生代表之一,「五四」那天他首先打進了曹汝霖的住宅。
傅斯年先生在「北大」做學生的時候,深受「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的「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名言之薰陶,從事各項愛國運動。而且抱著一股熱忱,要為文學革命而奮鬥。早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年,他曾創辦並主編「新潮月刊」,公開主張文學革命;力持要發揚近代人的語言,打開已往傳統的束縳,用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政。在政治方面,他主張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自決,反封建、反侵略。「五四」那年的夏天,他考取了山東省的官費,前往英國留學,在「倫敦大學研究院」研究實驗心理學,進而至物理化學和高深的數學,尤其深通科學方法論(詳見羅家倫著「逝者如斯集」)。加上他的國學之博與精,他不但是貫通中西的通才;而且為我國歷史語言學的權威,故被任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之職。
傅先生接長「台大」後,便把「北大」學術自由的校風帶到「台大」。為了發揚學生自動服務社會之精神,首先在訓導處之下,設立一個「課外活動組」,以輔導學生社團之活動。於是校園中各種各樣的社團便紛紛成立。我也不甘寂寞,會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在大二那年,先後組織並主持「經濟學研究會」及「台大國劇社」。後來由大陸轉學「台大」的流亡學生日漸增多,又設立一個「學生生活輔導組」,以解決貧寒同學的食住問題(當時的轉學攷試非常嚴格)。校中的機構和教職員的名額增加了,使全校的經費預算日漸龐大。正是為了這筆龐大的預算,一件不幸的大事突然發生了!
這件事發生在一九五?年(民國三十九年)的下半年。當時「台大」雖是國立大學,但其預算案需要經過「台灣省議會」的審查和通過;而「台大」的校長依法應列席備詢。那時的省議員,素質很差,良莠不齊,地痞居多,質詢時,挑剔再三,言語輕慢,蠻?無理。傅斯年先生以一位著名學者的身份,在「秀才遇到兵」的場合之下,怎能不生氣?況且,他的血壓一向偏高,就在極度憤怒之下,他立時氣喘,突然暈倒在地,不省人事,及至用救護車送他到「台大醫院」,已因腦部溢血過多,回天乏術。一位富於浩然正氣的教育家,尚在五十四歲的壯年,竟然魂歸西天,怎不令人痛惜!何況他是為「台大」而犧牲!?
噩耗一出,全校男女同學不約而同在羅斯福路校本部集合;紛紛排成長龍,前往省議會示威遊行,整個隊伍浩浩蕩蕩蔓延數條大街。我和「學生代聯會」的男同學領頭舉手喊口號:「打到省議會!你們要償命!??」;女同學都跟隨在後,她們一邊走,一邊哭哭啼啼,街上的行人都三、五成群的問長問短,驚歎不已!我們隊伍到達省議會,只見議長李萬居雙手張開攔在大門口,誠惶誠恐,小心翼翼向同學們勸慰,好話連天,惟恐我們打進議場。最後在訓導處的勸告之下,大家才息怒,各自回校。
次日,傅校長的遺體停放在「極樂殯儀館」弔祭三天,我們旳男女同學分作兩班輪流守靈。每天前往弔喪的客人陸續不斷;有的人長吁短嘆,有的人傷心落淚!尤其是統計學專家張果為教授,進門看到遺體,立刻坐倒在地放聲痛哭!驚動了記者們紛紛上前拍照,以便在報上報導,一個人身後弄到千百成群的人來痛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又有幾人能得如此哀榮?
遺體火化後,即葬在校本部的「傅園」(見圖)。並由「學生代聯會」向同學籌款,購買一個大銅鐘呈送校方;安放在墓亭附近,以鐘聲象徵傅斯年校長的音容宛在,正氣長存。
二?一三年十一月於香亭書齋
時年八十六歲
資深校友/江熙民
「國立台灣大學」是寶島台灣的最高學府,它原為日治時代的「台北帝國大學」(乃日本四個著名大學之一)。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收復台灣,將「台北帝國大學」更名為「國立台灣大學」。
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筆者就讀台大經濟學系時,校長為傅斯年先生,教務長是錢思亮先生,訓導長為傅啟學先生。沈剛伯先生為文學院院長,薩孟武先生職掌法學院。當時經濟學系隸屬於法學院(今易名為社會科學院),院址在台北市徐州路二十一號;筆者那時就住在徐州路男生第四宿舍。記得當時文、理、法三學院著名的教授為錢穆、毛子水、勞幹、王叔明、張肖松、趙麗蓮(美籍)、趙蘭坪、張果為、王師復、林霖、盛成、殷海光及筆者之岳父魏喦壽(後任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所長)等幾位專家學者。惟自光復後,台大各學院系每年不斷地擴展,迄民國八十八年底,已發展成十個學院,五十一個學系,八十一個研究所,而教授也相對的增加了數倍;已被選入世界百大之行列。
傅斯年校長字孟真,山東人,為「五四運動」的健將,他是當時被推選的二十名學生代表之一,「五四」那天他首先打進了曹汝霖的住宅。
傅斯年先生在「北大」做學生的時候,深受「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的「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名言之薰陶,從事各項愛國運動。而且抱著一股熱忱,要為文學革命而奮鬥。早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年,他曾創辦並主編「新潮月刊」,公開主張文學革命;力持要發揚近代人的語言,打開已往傳統的束縳,用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政。在政治方面,他主張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自決,反封建、反侵略。「五四」那年的夏天,他考取了山東省的官費,前往英國留學,在「倫敦大學研究院」研究實驗心理學,進而至物理化學和高深的數學,尤其深通科學方法論(詳見羅家倫著「逝者如斯集」)。加上他的國學之博與精,他不但是貫通中西的通才;而且為我國歷史語言學的權威,故被任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之職。
傅先生接長「台大」後,便把「北大」學術自由的校風帶到「台大」。為了發揚學生自動服務社會之精神,首先在訓導處之下,設立一個「課外活動組」,以輔導學生社團之活動。於是校園中各種各樣的社團便紛紛成立。我也不甘寂寞,會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在大二那年,先後組織並主持「經濟學研究會」及「台大國劇社」。後來由大陸轉學「台大」的流亡學生日漸增多,又設立一個「學生生活輔導組」,以解決貧寒同學的食住問題(當時的轉學攷試非常嚴格)。校中的機構和教職員的名額增加了,使全校的經費預算日漸龐大。正是為了這筆龐大的預算,一件不幸的大事突然發生了!
這件事發生在一九五?年(民國三十九年)的下半年。當時「台大」雖是國立大學,但其預算案需要經過「台灣省議會」的審查和通過;而「台大」的校長依法應列席備詢。那時的省議員,素質很差,良莠不齊,地痞居多,質詢時,挑剔再三,言語輕慢,蠻?無理。傅斯年先生以一位著名學者的身份,在「秀才遇到兵」的場合之下,怎能不生氣?況且,他的血壓一向偏高,就在極度憤怒之下,他立時氣喘,突然暈倒在地,不省人事,及至用救護車送他到「台大醫院」,已因腦部溢血過多,回天乏術。一位富於浩然正氣的教育家,尚在五十四歲的壯年,竟然魂歸西天,怎不令人痛惜!何況他是為「台大」而犧牲!?
噩耗一出,全校男女同學不約而同在羅斯福路校本部集合;紛紛排成長龍,前往省議會示威遊行,整個隊伍浩浩蕩蕩蔓延數條大街。我和「學生代聯會」的男同學領頭舉手喊口號:「打到省議會!你們要償命!??」;女同學都跟隨在後,她們一邊走,一邊哭哭啼啼,街上的行人都三、五成群的問長問短,驚歎不已!我們隊伍到達省議會,只見議長李萬居雙手張開攔在大門口,誠惶誠恐,小心翼翼向同學們勸慰,好話連天,惟恐我們打進議場。最後在訓導處的勸告之下,大家才息怒,各自回校。
次日,傅校長的遺體停放在「極樂殯儀館」弔祭三天,我們旳男女同學分作兩班輪流守靈。每天前往弔喪的客人陸續不斷;有的人長吁短嘆,有的人傷心落淚!尤其是統計學專家張果為教授,進門看到遺體,立刻坐倒在地放聲痛哭!驚動了記者們紛紛上前拍照,以便在報上報導,一個人身後弄到千百成群的人來痛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又有幾人能得如此哀榮?
遺體火化後,即葬在校本部的「傅園」(見圖)。並由「學生代聯會」向同學籌款,購買一個大銅鐘呈送校方;安放在墓亭附近,以鐘聲象徵傅斯年校長的音容宛在,正氣長存。
二?一三年十一月於香亭書齋
時年八十六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