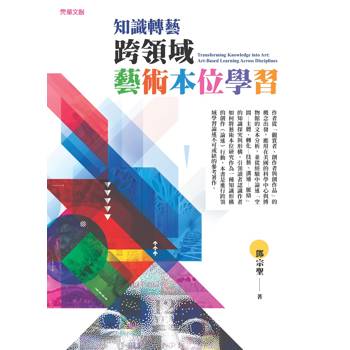【緒 論】
一、楔子
這是一本關於「藝術本位學習」(art-based learning)的研究,這一詞彙基於藝術本位研究觀點與多模式理論結合而成的複合概念。該概念包括「空間╱主題、轉化╱技藝、脈絡╱溝通」(space/subject, transforming/technique, context/communication),這些元素相互交織,圍繞「如何成為獨立學習者」(how to be an independent learner)的主題進行分析與組織。
問題意識的背景是臺灣的教育體制即便經歷了新課綱的改革,實際的教學現場仍然存在主科與副科之間的明顯地位差異。大多數教材的設計依然是依據單一科目進行,而非以整合的方式呈現。這種教學安排往往使師生之間的互動集中在知識的傳遞上,而缺乏協作學習的機會。教師之間不常分享課程設計的權力,偏好強調已知的事實,忽略了對於程序性知識的探討。由於課程設計中探究和實作的時間較少,而知識傳授的內容較多,探索過程經常因時間有限而被壓縮,致使師生在追求效率的前提下,無法進行更多的實驗和嘗試。隨著對學習、成果和評量關注的增加,教師們經常因需要參加個別學生評量、課程引導、在職專業發展、學校會議和規劃活動,而找不到時間將藝術納入教學。教師習慣於圍繞特定單元或主題教授內容。當花費在準備學生通過考試上的時間增加,花在課外活動上的時間就相應減少,這直接影響到藝術學習。在沒有專門藝術老師的學校中,課堂老師通常還負責提供藝術體驗。儘管教師們認識到藝術體驗的重要性及其對學生創造力和學習的影響,但卻已經被工作淹沒,難以將藝術納入教學。
儘管各學科的學習很複雜,但學習本質上是一種探索與創作,自我不會孤立地在學科孤島中求生。因此,脫離學校安排的學科學習系統與空間,可能有助於探討對一種現象──在學科上疊加的多重興趣與感知。相反,研究田野選擇了科學中心與博物館,而不是藝術類的博物館,挑戰常識上的科學與藝術分界。作為思尋知識建檔的探究者,我進入這些邊界,觀察界線的劃定以及模糊的地帶。將此書視為一種如畫、如詩的作品,從創作過程中以成為一個「獨立學習者」為理念,進行田野筆記與專書寫作,以符合研究旨趣。
為什麼是獨立學習者?跨領域學習是在多學科的思維預設下進行,而學科知識代理人在學校機構內的教與學,隱含誰能教、誰要學的知識權力關係,因此使用學習者一詞意圖是一種陌生化的策略,一方面是鬆動教師中心的教與學關係,一方面是打破長期由學校機構代理而構建的學科框架,恢復學習者的主體性,將知識視為一種經驗轉化的創造過程(learning is the process whereby knowledge created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perience)。關於知識權力的問題,不同學科從知識倉儲、傳遞、選擇、分配與支配等屬於知識社會學的想法,儘管它們已經存在很久但不一定被理解,當代跨領域學習論述,如STEM也都有其政治、經濟與社會力量及職業扣連而建立,在學術上企圖懸置這些力量的影響,有必要捨棄「跨領域」而採用「獨立」理解並克服障礙,如果要藝術發揮關鍵作用,就必須考慮個人的背景與獨特性,在界線與邊緣中探索。
此外,為什麼選擇科學中心與博物館作為田野?如果說學習者的用法是鬆動師生的權力關係,科學中心與博物館相較於學校機構,其一直以多模態(multimodality)的溝通方式存在,至少,因為是將物品集合安置在某個地方,並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呈現,在符號學的意義下是多模式的方式組織與溝通。此外,博物館作為學校之外開放的社會空間,而藝術形式在政策價值、教育推廣等目的下進入到空間景觀,允許成群的參與者能透過藝術的體驗認識新興技術(例如奈米技術)和成熟技術(例如衛星),甚至激勵參與者在參與後能夠有所情緒回應與社會行動,為各種類型知識創造吸引力體驗的前提下,學習空間不同於學校的教學行為,反而在「參與、互動」的期待下重新形塑學習活動的體驗,從加入或不加入空間開始,產生選擇不同程度的參與,感覺具主動權利。因此,從接近科學為名的博物館體驗的多樣性,同時評估這些知識的選擇與轉化。透過思維這些作品和在科學中心、博物館的經歷,識別科學場域在溝通對話中企圖澄清的誤解與達成的理解。
據前述,藝術本位學習將不同藝術形式之間的組合視為經驗轉化的知識建構,無論在何種科學中心與博物館,都可能透過書籍、電影、照片、繪畫、表演和裝置等作品,來連結個人認同與群體發展的知識活動,因此無論具體使用何種藝術形式,臺灣過去在關於教室外的藝術本位研究並不多見,且學科系統內的教育工作者專注在其學科給予的教學信念、教學規劃、行為與學生學習成效評估,較少專注在藝術本位學習的議題。
二、對象範圍與方法
進行研究工作前,首要問題是:如何判斷跨領域?
McComas 建議先理解「領域內」(intra-disciplinarity)這一重要概念。此概念意味著判斷「界限」,例如在空氣汙染議題上,可利用物理學來研究空氣流動、利用化學來分析汙染物,並利用生物學來研究化學物質對生命系統的影響。無論事情多麼複雜,涉及多少科學,這些都保持在科學學科內,因為所有科學專業都受相同的基本規則支配(例如提出經驗證據、證明的方法等)。換言之,「領域內」象徵學科在熟悉的範圍內相互跨科,但不會超出學科規則;反之則是「跨領域」意味著在不同學科規則下,價值觀與世界觀的激盪。然而,Akkerman 與 Bakker 將邊界定義為導致互動和行動不連續的社會文化差異。從活動系統(activity systems)來看,邊界的概念具有模糊性,跨越邊界的人(創作者、策展人、學習者等)和邊界物體(活動)處於中間地帶,通常模稜兩可的性質(既不是—也不是)和不確定性都會引發關於意義的對話和協商。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並探索這種不確定性的狀態,我選擇在美國研究期間,專注於ASTC(Association of Science-Technology Centers, ASTC)組織下的科學中心與博物館成員,探索領域知識邊界的藝術實踐,這些成員單位包括自然博物館(涵蓋自然史、天文、地質等科學文化遺產),以及科學工業博物館(展示科學、科技和工業的革命歷程與成果)。這些博物館的展覽形式分為典藏和策展兩種類型,前者主要目的是收藏和研究,後者則強調溝通與服務。此外,還有以公園型態的場館,如國家公園、動物園、海洋生物館和植物園等。這些場館正從傳統的圍欄展示方式轉向更沉浸式和生態化的展示方式。對於這些成員單位來說,常設展是其核心,從靜態描述到動態展示的轉變,意圖在於表達科學主題與藝術的融合。除了常設展覽之外,還有引進展覽的主題展,這些主題展旨在引進企業、基金會、民間組織和學校等社會力量與資源,促進更廣泛的合作與交流。前述場域是領域知識代理人與社群展示知識的地方,也是發生理解或誤解的地方。儘管科學機構強調知識的正確性,但參與者的多樣性也凸顯了科學中心與博物館在將嚴肅知識轉化為藝術形式與人溝通的重要性,但這裡要強調的是,科學中心與博物館往往不太觸及從藝術本位的觀點,而是專注於領域知識傳遞。這樣一來,人與知識之間的關係便被忽視了,展覽策劃主要遵循學科邏輯和專家的觀點,而未能充分考慮到藝術形構知識的參與和體驗。
作為一個田野研究者,在空間中步行時隱藏著醞釀感知和表達的潛力。行走時所遇到的景象和聲音提供了評論和反思,這是一個可擴展的意義建構過程。看似無形的空間,通過各種藝術形式轉化為個人與群體的學習體驗,將藝術本位學習與空間交織在一起,使學習呈現出多種表現形式。如果將這些表現形式的體驗視為一種連結的角色,那麼就能鼓勵學習者以自己感受的方式學習,將這些體驗視為可能的連結。這裡賦予由各種作品組合而成的概念空間一種協作角色,以便與各知識代理人進行對話,並將其視為向學習者展示作品的研究者。透過這些不同的策略,學習者對環境產生了敏感,激發美學想像力,並在當下產生轉化經驗,如拍攝照片、創作文字作品、構思概念等,在空間中步行或隨行移動,似乎也是一種對創作者的採訪。走過陌生的環境,為「參與者、創作者和作品」之間的交流提供了機會,並可能駐足在某一處,進行思維所提供的描述和解釋,觀察和對話。
ASTC 會員群體共享價值的前提下,儘管科學中心與博物館空間很難被完整定義,但這些空間的開放性與包容性使其在向公眾溝通上具有獨特的特點。這些空間旨在促進科學知識的普及與交流,無論年齡、背景,或知識水平如何,均能吸引和參與其中。科學中心與博物館通過多種形式的展覽和活動,創造了一個兼容並包的學習環境,鼓勵訪客探索、思考和互動。科學中心與博物館的空間提供各種教育、享受、反思和知識共享的經驗。在這些空間內,學習者能決定學習什麼、如何學習以及用哪種方式學習。換言之,這些空間傳達了關於學習優先性、價值觀和目的的多種方式。此外,這些空間與教室環境在於社交性和自我選擇性上的本質差異:
前者強調吸引許多人與同行的友人、團體、家人甚至陌生人一起觀看。後者提供個人足夠空間選擇與作品的距離。無論何種形式的作品與裝置,其尺寸和大小提供了不同的空間距離和觀看角度。
儘管各種作品來自不同文化的創作者,其建構的作品為各種概念或知識的表達提供或暗示一些體驗經驗,例如沉浸感、感性地理解。因此,在其中做實際觀察的田野經驗,旨在論述空間與作品的關係是如何為參與者產生學習經驗提供理解的脈絡。透過這些觀察,揭示空間配置和藝術作品如何相互作用,激發參觀者的學習動機和參與感。這些田野經驗不僅涵蓋了觀察和記錄不同展示形式的實踐,並解讀與分析這些知識與藝術實踐的交融。在這樣的研究過程中,體現了學習的動態性和多樣性,以及藝術在教育中的獨特性。
三、藝術本位研究與多模式理論
本書採取藝術本位研究法,將藝術視為多模態溝通的符號資源。溝通中的動作、材料、人工製品(例如圖像、凝視、手勢、動作、音樂、語音、文字、桌子、定位、聲音)及媒體(例如頁面、螢幕、網站、電影)都構成了藝術教育中的視覺證據,用以解釋藝術活動與跨領域論題之間的連結。這些元素不僅僅是靜態的展示,而是動態的過程,體現了藝術如何在多重符號系統中協同工作,創造出豐富而多層次的學習經驗。 接下來,本書將描述美國不同領域知識社群的特徵及其表現變化。這些群體包括各類自然、科學、工業和科技博物館,它們在展示方式、互動形式以及觀眾參與度方面展現了多樣性和創新性。在描述之後,將進一步分析這些案例對於藝術本位跨領域學習的意義,如何利用多模態溝通、協同工作和社會參與,來激發創造力和跨領域思維。
本書研究自然、科學等領域知識範疇,個案來源包括自然史、天文、地理、數學、人體等,分析中將參考不同來源的文獻,主要是自身在田野調查中進行的攝影與錄像檔案作為視覺化脈絡,這些資料有助於確定溝通內容的形成,以及這些內容如何轉化並連結到跨領域的藝術本位學習。這些田野現場資料不僅有助於展品標籤和展板的視覺傳達,避免過多細節的淹沒或冗長描述,還考慮了整體的理解性,而不會陷入特定的知識展覽而產生距離感。
有鑒於此,藝術本位研究將多模式理論應用於描繪觀賞者(viewer)、創作者(maker)與作品(works)之間的相互關係,描繪的目標並非專注於每一個主題作品本身的仔細閱讀,儘管它們在現場可能令人著迷。相反,這裡將專注於圍繞它們組合起來的空間、活動和話語所建立的符號關係,以顯示作品再現特定領域敘說及其知識建構的方式。許多科學中心與博物館的政策已消除或放鬆攝影限制,因此作者會以攝影作為田野筆記,紀錄裝置、空間和展品等視覺證據以論述方式描繪其多模態。描繪時使用部分而非全部的視覺證據,作為展現觀者角度的材料,藉此想像觀者與作品物件互動的空間,不僅建構參與者的位置,還建構其角色身分。聚焦於某些主題的溝通方式,提供了切入點。
如前所述,科學中心與博物館的空間與作品視覺化安排,重新構建參與者之間的關係,無論是消費者、生產者、政策制定者還是問題解決者。當作品與裝置將個人體驗轉變為共享體驗時,它們也可能成為象徵性建構的學習空間。因此,分析將分為三個面向進行:
1.主體—空間
從觀賞者的角度出發,對空間主題的描繪不僅是記錄檔案,更是一種視覺脈絡的敘說。這種敘說可以將讀者帶入對作者經驗反思及觀點分析之間的關係。
2.轉化—技藝
從創作者角度出發,知識的轉化技藝在展示中相互滲透。在空間中,人們可以在藝術作品中找到科學解釋,也可以在科學物件中找到藝術化的技藝。作為多模態溝通的創作者,轉化知識的過程不會將藝術技藝與科學主題之間進行嚴格區分,而是融合體驗作品與空間。
3.脈絡—溝通
從作品本身出發,任何一個作品即便只是簡單傳達目的的溝通,但其本身涉及的文化與社會脈絡也是不可忽視的。除了實際溝通內容外,還有基本的脈絡性問題。這無法用「是或不是」的二元思維來判斷,而需要對「何以致此」進行深入理解。
綜合前述從知識社會學觀點來看,藝術的符號資源連結文化和社會資本,對不同學科的學習產生影響。因此,在分析主體—空間連結時,考慮如何建構教學者不存在的「學習場域」的可能性;在轉化—技藝中,從作品組合的不同方面,反思學習作為考試與測驗的技藝形象,認識到表達的多樣性,以及自我參與是創造性發展的持續過程;脈絡—溝通則是企圖論述不必受限於學科課綱,提供學習變革的論述空間,反思學習者如何能在脈絡中遊走於不同領域間進行思考;作者將應用這樣的框架,透過觀察和分析線索(視覺證據)來反思促進個人解釋的觀點,想像一個學習者在很少或沒有特定知識的情況下,能嘗試有自信地談論作品。沿著這些思路,評估考慮參與知識詮釋的自主性,以感受在思維奔放下成為獨立學習者的潛力。
一、楔子
這是一本關於「藝術本位學習」(art-based learning)的研究,這一詞彙基於藝術本位研究觀點與多模式理論結合而成的複合概念。該概念包括「空間╱主題、轉化╱技藝、脈絡╱溝通」(space/subject, transforming/technique, context/communication),這些元素相互交織,圍繞「如何成為獨立學習者」(how to be an independent learner)的主題進行分析與組織。
問題意識的背景是臺灣的教育體制即便經歷了新課綱的改革,實際的教學現場仍然存在主科與副科之間的明顯地位差異。大多數教材的設計依然是依據單一科目進行,而非以整合的方式呈現。這種教學安排往往使師生之間的互動集中在知識的傳遞上,而缺乏協作學習的機會。教師之間不常分享課程設計的權力,偏好強調已知的事實,忽略了對於程序性知識的探討。由於課程設計中探究和實作的時間較少,而知識傳授的內容較多,探索過程經常因時間有限而被壓縮,致使師生在追求效率的前提下,無法進行更多的實驗和嘗試。隨著對學習、成果和評量關注的增加,教師們經常因需要參加個別學生評量、課程引導、在職專業發展、學校會議和規劃活動,而找不到時間將藝術納入教學。教師習慣於圍繞特定單元或主題教授內容。當花費在準備學生通過考試上的時間增加,花在課外活動上的時間就相應減少,這直接影響到藝術學習。在沒有專門藝術老師的學校中,課堂老師通常還負責提供藝術體驗。儘管教師們認識到藝術體驗的重要性及其對學生創造力和學習的影響,但卻已經被工作淹沒,難以將藝術納入教學。
儘管各學科的學習很複雜,但學習本質上是一種探索與創作,自我不會孤立地在學科孤島中求生。因此,脫離學校安排的學科學習系統與空間,可能有助於探討對一種現象──在學科上疊加的多重興趣與感知。相反,研究田野選擇了科學中心與博物館,而不是藝術類的博物館,挑戰常識上的科學與藝術分界。作為思尋知識建檔的探究者,我進入這些邊界,觀察界線的劃定以及模糊的地帶。將此書視為一種如畫、如詩的作品,從創作過程中以成為一個「獨立學習者」為理念,進行田野筆記與專書寫作,以符合研究旨趣。
為什麼是獨立學習者?跨領域學習是在多學科的思維預設下進行,而學科知識代理人在學校機構內的教與學,隱含誰能教、誰要學的知識權力關係,因此使用學習者一詞意圖是一種陌生化的策略,一方面是鬆動教師中心的教與學關係,一方面是打破長期由學校機構代理而構建的學科框架,恢復學習者的主體性,將知識視為一種經驗轉化的創造過程(learning is the process whereby knowledge created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perience)。關於知識權力的問題,不同學科從知識倉儲、傳遞、選擇、分配與支配等屬於知識社會學的想法,儘管它們已經存在很久但不一定被理解,當代跨領域學習論述,如STEM也都有其政治、經濟與社會力量及職業扣連而建立,在學術上企圖懸置這些力量的影響,有必要捨棄「跨領域」而採用「獨立」理解並克服障礙,如果要藝術發揮關鍵作用,就必須考慮個人的背景與獨特性,在界線與邊緣中探索。
此外,為什麼選擇科學中心與博物館作為田野?如果說學習者的用法是鬆動師生的權力關係,科學中心與博物館相較於學校機構,其一直以多模態(multimodality)的溝通方式存在,至少,因為是將物品集合安置在某個地方,並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呈現,在符號學的意義下是多模式的方式組織與溝通。此外,博物館作為學校之外開放的社會空間,而藝術形式在政策價值、教育推廣等目的下進入到空間景觀,允許成群的參與者能透過藝術的體驗認識新興技術(例如奈米技術)和成熟技術(例如衛星),甚至激勵參與者在參與後能夠有所情緒回應與社會行動,為各種類型知識創造吸引力體驗的前提下,學習空間不同於學校的教學行為,反而在「參與、互動」的期待下重新形塑學習活動的體驗,從加入或不加入空間開始,產生選擇不同程度的參與,感覺具主動權利。因此,從接近科學為名的博物館體驗的多樣性,同時評估這些知識的選擇與轉化。透過思維這些作品和在科學中心、博物館的經歷,識別科學場域在溝通對話中企圖澄清的誤解與達成的理解。
據前述,藝術本位學習將不同藝術形式之間的組合視為經驗轉化的知識建構,無論在何種科學中心與博物館,都可能透過書籍、電影、照片、繪畫、表演和裝置等作品,來連結個人認同與群體發展的知識活動,因此無論具體使用何種藝術形式,臺灣過去在關於教室外的藝術本位研究並不多見,且學科系統內的教育工作者專注在其學科給予的教學信念、教學規劃、行為與學生學習成效評估,較少專注在藝術本位學習的議題。
二、對象範圍與方法
進行研究工作前,首要問題是:如何判斷跨領域?
McComas 建議先理解「領域內」(intra-disciplinarity)這一重要概念。此概念意味著判斷「界限」,例如在空氣汙染議題上,可利用物理學來研究空氣流動、利用化學來分析汙染物,並利用生物學來研究化學物質對生命系統的影響。無論事情多麼複雜,涉及多少科學,這些都保持在科學學科內,因為所有科學專業都受相同的基本規則支配(例如提出經驗證據、證明的方法等)。換言之,「領域內」象徵學科在熟悉的範圍內相互跨科,但不會超出學科規則;反之則是「跨領域」意味著在不同學科規則下,價值觀與世界觀的激盪。然而,Akkerman 與 Bakker 將邊界定義為導致互動和行動不連續的社會文化差異。從活動系統(activity systems)來看,邊界的概念具有模糊性,跨越邊界的人(創作者、策展人、學習者等)和邊界物體(活動)處於中間地帶,通常模稜兩可的性質(既不是—也不是)和不確定性都會引發關於意義的對話和協商。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並探索這種不確定性的狀態,我選擇在美國研究期間,專注於ASTC(Association of Science-Technology Centers, ASTC)組織下的科學中心與博物館成員,探索領域知識邊界的藝術實踐,這些成員單位包括自然博物館(涵蓋自然史、天文、地質等科學文化遺產),以及科學工業博物館(展示科學、科技和工業的革命歷程與成果)。這些博物館的展覽形式分為典藏和策展兩種類型,前者主要目的是收藏和研究,後者則強調溝通與服務。此外,還有以公園型態的場館,如國家公園、動物園、海洋生物館和植物園等。這些場館正從傳統的圍欄展示方式轉向更沉浸式和生態化的展示方式。對於這些成員單位來說,常設展是其核心,從靜態描述到動態展示的轉變,意圖在於表達科學主題與藝術的融合。除了常設展覽之外,還有引進展覽的主題展,這些主題展旨在引進企業、基金會、民間組織和學校等社會力量與資源,促進更廣泛的合作與交流。前述場域是領域知識代理人與社群展示知識的地方,也是發生理解或誤解的地方。儘管科學機構強調知識的正確性,但參與者的多樣性也凸顯了科學中心與博物館在將嚴肅知識轉化為藝術形式與人溝通的重要性,但這裡要強調的是,科學中心與博物館往往不太觸及從藝術本位的觀點,而是專注於領域知識傳遞。這樣一來,人與知識之間的關係便被忽視了,展覽策劃主要遵循學科邏輯和專家的觀點,而未能充分考慮到藝術形構知識的參與和體驗。
作為一個田野研究者,在空間中步行時隱藏著醞釀感知和表達的潛力。行走時所遇到的景象和聲音提供了評論和反思,這是一個可擴展的意義建構過程。看似無形的空間,通過各種藝術形式轉化為個人與群體的學習體驗,將藝術本位學習與空間交織在一起,使學習呈現出多種表現形式。如果將這些表現形式的體驗視為一種連結的角色,那麼就能鼓勵學習者以自己感受的方式學習,將這些體驗視為可能的連結。這裡賦予由各種作品組合而成的概念空間一種協作角色,以便與各知識代理人進行對話,並將其視為向學習者展示作品的研究者。透過這些不同的策略,學習者對環境產生了敏感,激發美學想像力,並在當下產生轉化經驗,如拍攝照片、創作文字作品、構思概念等,在空間中步行或隨行移動,似乎也是一種對創作者的採訪。走過陌生的環境,為「參與者、創作者和作品」之間的交流提供了機會,並可能駐足在某一處,進行思維所提供的描述和解釋,觀察和對話。
ASTC 會員群體共享價值的前提下,儘管科學中心與博物館空間很難被完整定義,但這些空間的開放性與包容性使其在向公眾溝通上具有獨特的特點。這些空間旨在促進科學知識的普及與交流,無論年齡、背景,或知識水平如何,均能吸引和參與其中。科學中心與博物館通過多種形式的展覽和活動,創造了一個兼容並包的學習環境,鼓勵訪客探索、思考和互動。科學中心與博物館的空間提供各種教育、享受、反思和知識共享的經驗。在這些空間內,學習者能決定學習什麼、如何學習以及用哪種方式學習。換言之,這些空間傳達了關於學習優先性、價值觀和目的的多種方式。此外,這些空間與教室環境在於社交性和自我選擇性上的本質差異:
前者強調吸引許多人與同行的友人、團體、家人甚至陌生人一起觀看。後者提供個人足夠空間選擇與作品的距離。無論何種形式的作品與裝置,其尺寸和大小提供了不同的空間距離和觀看角度。
儘管各種作品來自不同文化的創作者,其建構的作品為各種概念或知識的表達提供或暗示一些體驗經驗,例如沉浸感、感性地理解。因此,在其中做實際觀察的田野經驗,旨在論述空間與作品的關係是如何為參與者產生學習經驗提供理解的脈絡。透過這些觀察,揭示空間配置和藝術作品如何相互作用,激發參觀者的學習動機和參與感。這些田野經驗不僅涵蓋了觀察和記錄不同展示形式的實踐,並解讀與分析這些知識與藝術實踐的交融。在這樣的研究過程中,體現了學習的動態性和多樣性,以及藝術在教育中的獨特性。
三、藝術本位研究與多模式理論
本書採取藝術本位研究法,將藝術視為多模態溝通的符號資源。溝通中的動作、材料、人工製品(例如圖像、凝視、手勢、動作、音樂、語音、文字、桌子、定位、聲音)及媒體(例如頁面、螢幕、網站、電影)都構成了藝術教育中的視覺證據,用以解釋藝術活動與跨領域論題之間的連結。這些元素不僅僅是靜態的展示,而是動態的過程,體現了藝術如何在多重符號系統中協同工作,創造出豐富而多層次的學習經驗。 接下來,本書將描述美國不同領域知識社群的特徵及其表現變化。這些群體包括各類自然、科學、工業和科技博物館,它們在展示方式、互動形式以及觀眾參與度方面展現了多樣性和創新性。在描述之後,將進一步分析這些案例對於藝術本位跨領域學習的意義,如何利用多模態溝通、協同工作和社會參與,來激發創造力和跨領域思維。
本書研究自然、科學等領域知識範疇,個案來源包括自然史、天文、地理、數學、人體等,分析中將參考不同來源的文獻,主要是自身在田野調查中進行的攝影與錄像檔案作為視覺化脈絡,這些資料有助於確定溝通內容的形成,以及這些內容如何轉化並連結到跨領域的藝術本位學習。這些田野現場資料不僅有助於展品標籤和展板的視覺傳達,避免過多細節的淹沒或冗長描述,還考慮了整體的理解性,而不會陷入特定的知識展覽而產生距離感。
有鑒於此,藝術本位研究將多模式理論應用於描繪觀賞者(viewer)、創作者(maker)與作品(works)之間的相互關係,描繪的目標並非專注於每一個主題作品本身的仔細閱讀,儘管它們在現場可能令人著迷。相反,這裡將專注於圍繞它們組合起來的空間、活動和話語所建立的符號關係,以顯示作品再現特定領域敘說及其知識建構的方式。許多科學中心與博物館的政策已消除或放鬆攝影限制,因此作者會以攝影作為田野筆記,紀錄裝置、空間和展品等視覺證據以論述方式描繪其多模態。描繪時使用部分而非全部的視覺證據,作為展現觀者角度的材料,藉此想像觀者與作品物件互動的空間,不僅建構參與者的位置,還建構其角色身分。聚焦於某些主題的溝通方式,提供了切入點。
如前所述,科學中心與博物館的空間與作品視覺化安排,重新構建參與者之間的關係,無論是消費者、生產者、政策制定者還是問題解決者。當作品與裝置將個人體驗轉變為共享體驗時,它們也可能成為象徵性建構的學習空間。因此,分析將分為三個面向進行:
1.主體—空間
從觀賞者的角度出發,對空間主題的描繪不僅是記錄檔案,更是一種視覺脈絡的敘說。這種敘說可以將讀者帶入對作者經驗反思及觀點分析之間的關係。
2.轉化—技藝
從創作者角度出發,知識的轉化技藝在展示中相互滲透。在空間中,人們可以在藝術作品中找到科學解釋,也可以在科學物件中找到藝術化的技藝。作為多模態溝通的創作者,轉化知識的過程不會將藝術技藝與科學主題之間進行嚴格區分,而是融合體驗作品與空間。
3.脈絡—溝通
從作品本身出發,任何一個作品即便只是簡單傳達目的的溝通,但其本身涉及的文化與社會脈絡也是不可忽視的。除了實際溝通內容外,還有基本的脈絡性問題。這無法用「是或不是」的二元思維來判斷,而需要對「何以致此」進行深入理解。
綜合前述從知識社會學觀點來看,藝術的符號資源連結文化和社會資本,對不同學科的學習產生影響。因此,在分析主體—空間連結時,考慮如何建構教學者不存在的「學習場域」的可能性;在轉化—技藝中,從作品組合的不同方面,反思學習作為考試與測驗的技藝形象,認識到表達的多樣性,以及自我參與是創造性發展的持續過程;脈絡—溝通則是企圖論述不必受限於學科課綱,提供學習變革的論述空間,反思學習者如何能在脈絡中遊走於不同領域間進行思考;作者將應用這樣的框架,透過觀察和分析線索(視覺證據)來反思促進個人解釋的觀點,想像一個學習者在很少或沒有特定知識的情況下,能嘗試有自信地談論作品。沿著這些思路,評估考慮參與知識詮釋的自主性,以感受在思維奔放下成為獨立學習者的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