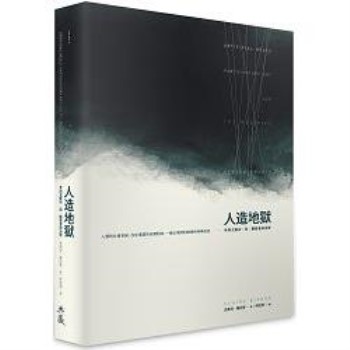從這本書所探討的例子衍生出來的主流敘事是很負面的:讓參與式藝術裡的觀眾起作用,是在反駁一個迷思性的相反概念,也就是被動的、旁觀的消費。因此,參與是一個橫跨現代的更大敘事的一部分:「藝術必須指向沉思,指向觀看,指向被現代生活的奇觀麻痺了的群眾的被動性。」這個讓觀眾在參與式藝術裡起作用的欲望,同時也是要讓他們擺脫主流意識型態秩序導致的異化狀態的驅力,不管那秩序是消費者資本主義、極權主義的社會主義或是軍事獨裁。從這個前提開始,參與式藝術旨在恢復和實現共同的社會投入的一個社區的、集體的空間。但是方式有所不同:不是透過社會衝擊的構成主義動作,提出另一條路,以對抗世界的不義,或者透過虛無主義式地誇大異化現象,以它自己的方式去否定世界的不義和悖理。兩者的作品都要形塑一個集體的、共同作者的、參與式的社會體系,但是前者是肯定性的(透過烏托邦式的實現),後者則是間接的(透過否定的否定﹝negation of negation﹞)。
我在講授關於這個主題的課程以後,一直在問一個問題:對於藝術作品而言,是改變一個人的生活比較好,或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比較好?這本書所描繪的參與式藝術的歷史,讓我們得以和這個問題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及整個二十世紀典型的「藝術與現實生活」論辯的最新發展。這個緊張關係(加上平等和品質、參與和旁觀)意味著社會判斷和藝術判斷並沒有那麼容易匯流;的確,它們必須有不同的判準。這個僵局浮現在關於參與式藝術和社會投入式藝術的紙上論辯和小組討論裡。有些藝術家、策展人和評論家認為,好的計畫應該可以滿足「超我」介入改善社會的想法;如果社會行為者做不到,藝術就有責任接手。在此框架裡,他們的判斷是基於一個人道主義的倫理,經常是受到基督宗教的鼓舞。重要的是提出改善的解決之道,不管是不是短期的,而不只是揭發矛盾的社會真相。有些藝術家、策展人和評論家認為,評斷是以對藝術作品的合理回應為基礎,無論是否在其脈絡當中。在這個結構裡,倫理是無關緊要的東西,因為藝術一直被認為是在挑戰既有的價值體系,包括道德的問題;設計新的語言,以表現和質疑社會矛盾,是更重要的事。社會論述指摘藝術論述,說它既離經叛道又效果不彰,因為僅僅揭露、複雜和反映世界,那是不夠的;重要的是改變它。而藝術論述則批評社會論述,說它頑固地執著於既有的範疇,只注意到微觀政治的動作,而忽略了作為「去異化」的潛在場所的感官直接性。佔上風的不是社會良知,就是質疑社會良知的個人權利。藝術和社會的關係基礎不是道德就是自由。波坦斯基和恰佩羅在認知上區分藝術和社會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也反映了這個二元性。藝術的批判植基於十九世紀的波希米亞主義,擷取了對於資本主義的兩種憤怒來源:一方面是幻想的破滅和不真實,另一方面則是壓迫。他們說,藝術的批判「突顯了意義的失落,尤其是對於美和有價值的事物的感受能力,這個失落則是衍生自標準化以及全面的商品化,不僅影響了日常物品,更及於藝術作品……和人類」。為了對抗這個狀態,藝術家的批判鼓吹「藝術家的自由,拒絕以倫理玷污美感,拒絕向時空屈服,也拒絕向任何形式的工作屈服」。相對的,社會批判則是引用對於資本主義不同的憤怒來源:個人利益的利己主義,以及勞動階級在史無前例的富裕社會裡越來越貧窮的問題。這種社會批判想當然爾反對藝術家的道德中立、個人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波坦斯基和恰佩羅提醒我們,藝術批判和社會批判並不是直接相容的,而且持續處於緊張關係之中。
藝術和社會批判之間的齟齬,在若干歷史階段裡特別明顯地反覆出現,可見於本書的個案分析。參與式藝術的誕生可以說是這個齟齬的表徵,也特別容易出現在政治轉型和動盪不安的時期:在法西斯主義崛起以前的幾年裡,1917年俄國革命的後續,遍地開花、以1968年為高峰的社會異議,以及它在1970年代的餘波蕩漾。在每個歷史時期,藝術都採取不同的形式,因為它要否定不同的藝術和社會政治的對象。在我們的時代裡,它的反覆出現則是伴隨著共產主義垮台而顯然缺少可行的左派替代主張、當代「後政治」共識的產生,以及藝術和教育鋪天蓋地的市場化。但是這個處境有個弔詭之處,那就是西方國家裡的參與反而比較接近新自由主義政府的民粹議題。即使參與式藝術家不約而同地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人們卻只是從形式上理解他們灌注在其作品裡的價值(反對個人主義和商品對象),而沒有認識到,該藝術創作的許多其他面向其實和新自由主義最近的形式更加吻合(網路、流動性、計畫作品、情感性勞動﹝affective labour﹞)。在二十世紀裡,隨著這個基礎的轉變,在每個歷史時期裡,對於參與的身分也有不同的想像:從民眾(1910年代)到群眾(1920年代),到人民(1960年代後期和1970年代),到社會邊緣人(1980年代),到社區(1990年代),到現在的自願參與者,他們的參與是實境電視和社會網路的文化的延伸。從觀眾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把它描繪成從要求一個角色的觀眾(表現在對於一直控制著舞台的前衛藝術家的厭惡)轉變到一個樂於接受由藝術家為他們設計陌生經驗的觀眾,又轉變為被鼓勵成為作品的共同作者的觀眾(偶爾甚至會付費給參加者)。它可以視為對於觀眾的激勵和主動性日增的史詩敘事,但是也可以說我們越來越願意接受藝術家的意志,而人們的身體也在服務性經濟裡越來越商品化(因為自願的參與也是一種不支薪的勞動)。它和民主自身的坎坷命運顯然很類似,那是和參與經常相提並論的一個語詞:從要求被承認,到表現,到兩願地消費自己的形象,無論是在藝術作品裡,或是在Facebook、Flickr,或是實境電視。我們不妨以安東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的《一與其他》(One and Other, 2009)的媒體報導為例,該計畫讓民眾持續佔據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的「第四基座」,每個人在上頭站一個小時,接力展演一百天。34,520個應徵者來自2,400個地方,佔據基座的行動持續上傳到網路。雖然葛姆雷說《一與其他》是「讓人們有機會挑戰他們的自我感以及如何將它傳達給更廣大的世界的公共空間」,《衛報》則頗為持平地將該計畫形容為「推特藝術」(Twitter Art)。在每個人都可以將他們的想法傳送給所有人知道的世界裡,我們面對的不是群眾的賦權,而是一連串平庸化的自我。「參與」根本不是「奇觀」的對立面,現在反而和它沆瀣一氣。在二十世紀裡,隨著這個基礎的轉變,在每個歷史時期裡,對於參與的身分也有不同的想像:從民眾(1910年代)到群眾(1920年代),到人民(1960年代後期和1970年代),到社會邊緣人(1980年代),到社區(1990年代),到現在的自願參與者,他們的參與是實境電視和社會網路的文化的延伸。從觀眾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把它描繪成從要求一個角色的觀眾(表現在對於一直控制著舞台的前衛藝術家的厭惡)轉變到一個樂於接受由藝術家為他們設計陌生經驗的觀眾,又轉變為被鼓勵成為作品的共同作者的觀眾(偶爾甚至會付費給參加者)。它可以視為對於觀眾的激勵和主動性日增的史詩敘事,但是也可以說我們越來越願意接受藝術家的意志,而人們的身體也在服務性經濟裡越來越商品化(因為自願的參與也是一種不支薪的勞動)。它和民主自身的坎坷命運顯然很類似,那是和參與經常相提並論的一個語詞:從要求被承認,到表現,到兩願地消費自己的形象,無論是在藝術作品裡,或是在Facebook、Flickr,或是實境電視。我們不妨以安東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的《一與其他》(One and Other, 2009)的媒體報導為例,該計畫讓民眾持續佔據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的「第四基座」,每個人在上頭站一個小時,接力展演一百天。34,520個應徵者來自2,400個地方,佔據基座的行動持續上傳到網路。雖然葛姆雷說《一與其他》是「讓人們有機會挑戰他們的自我感以及如何將它傳達給更廣大的世界的公共空間」,《衛報》則頗為持平地將該計畫形容為「推特藝術」(Twitter Art)。在每個人都可以將他們的想法傳送給所有人知道的世界裡,我們面對的不是群眾的賦權,而是一連串平庸化的自我。「參與」根本不是「奇觀」的對立面,現在反而和它沆瀣一氣。奇觀和參與的再度攜手,使得藝術批判和社會批判的緊張關係益顯必要。參與式藝術歷史裡許多最著名的計畫,都在顛覆作為該論述的基礎的對立性(個人和集體、作者和觀看者、主動和被動、現實生活和藝術),但不是要澈底瓦解它們。如是,他們維持了藝術批判和社會批判的緊張關係。瓜達里的「橫截性」的典範透過這些藝術操作提供了這類的思考:他不談作為範疇的藝術,而著重於藝術和其他學科的交涉,同時質疑藝術和社會,雖然同時也重申藝術有自己的價值世界。洪席耶則有另一種想法:美學國度在構成上即是矛盾的,穿梭在自律「以及」他律之間(「只要美感經驗是那個『以及』的經驗,它就有作用」)。他說,在藝術、劇場和教育裡,必須有個中介的事物,置於藝術家的想法和觀看者的感受以及詮釋之間:「這個奇觀是個第三項(third term),其他兩個關係項可以指涉它,但是有避免任何『等於』或『沒有扭曲的』傳遞。它是它們之間的中介,一個第三項的中介在整個知性解放的過程裡至關緊要……將它們串聯在一起的東西,必須同時也將它們分開。」哲學家則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另一個用以同時思考藝術和社會的架構;對於他們而言,藝術和社會是沒辦法和解的,而是維持一種緊張關係。
我在講授關於這個主題的課程以後,一直在問一個問題:對於藝術作品而言,是改變一個人的生活比較好,或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比較好?這本書所描繪的參與式藝術的歷史,讓我們得以和這個問題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及整個二十世紀典型的「藝術與現實生活」論辯的最新發展。這個緊張關係(加上平等和品質、參與和旁觀)意味著社會判斷和藝術判斷並沒有那麼容易匯流;的確,它們必須有不同的判準。這個僵局浮現在關於參與式藝術和社會投入式藝術的紙上論辯和小組討論裡。有些藝術家、策展人和評論家認為,好的計畫應該可以滿足「超我」介入改善社會的想法;如果社會行為者做不到,藝術就有責任接手。在此框架裡,他們的判斷是基於一個人道主義的倫理,經常是受到基督宗教的鼓舞。重要的是提出改善的解決之道,不管是不是短期的,而不只是揭發矛盾的社會真相。有些藝術家、策展人和評論家認為,評斷是以對藝術作品的合理回應為基礎,無論是否在其脈絡當中。在這個結構裡,倫理是無關緊要的東西,因為藝術一直被認為是在挑戰既有的價值體系,包括道德的問題;設計新的語言,以表現和質疑社會矛盾,是更重要的事。社會論述指摘藝術論述,說它既離經叛道又效果不彰,因為僅僅揭露、複雜和反映世界,那是不夠的;重要的是改變它。而藝術論述則批評社會論述,說它頑固地執著於既有的範疇,只注意到微觀政治的動作,而忽略了作為「去異化」的潛在場所的感官直接性。佔上風的不是社會良知,就是質疑社會良知的個人權利。藝術和社會的關係基礎不是道德就是自由。波坦斯基和恰佩羅在認知上區分藝術和社會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也反映了這個二元性。藝術的批判植基於十九世紀的波希米亞主義,擷取了對於資本主義的兩種憤怒來源:一方面是幻想的破滅和不真實,另一方面則是壓迫。他們說,藝術的批判「突顯了意義的失落,尤其是對於美和有價值的事物的感受能力,這個失落則是衍生自標準化以及全面的商品化,不僅影響了日常物品,更及於藝術作品……和人類」。為了對抗這個狀態,藝術家的批判鼓吹「藝術家的自由,拒絕以倫理玷污美感,拒絕向時空屈服,也拒絕向任何形式的工作屈服」。相對的,社會批判則是引用對於資本主義不同的憤怒來源:個人利益的利己主義,以及勞動階級在史無前例的富裕社會裡越來越貧窮的問題。這種社會批判想當然爾反對藝術家的道德中立、個人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波坦斯基和恰佩羅提醒我們,藝術批判和社會批判並不是直接相容的,而且持續處於緊張關係之中。
藝術和社會批判之間的齟齬,在若干歷史階段裡特別明顯地反覆出現,可見於本書的個案分析。參與式藝術的誕生可以說是這個齟齬的表徵,也特別容易出現在政治轉型和動盪不安的時期:在法西斯主義崛起以前的幾年裡,1917年俄國革命的後續,遍地開花、以1968年為高峰的社會異議,以及它在1970年代的餘波蕩漾。在每個歷史時期,藝術都採取不同的形式,因為它要否定不同的藝術和社會政治的對象。在我們的時代裡,它的反覆出現則是伴隨著共產主義垮台而顯然缺少可行的左派替代主張、當代「後政治」共識的產生,以及藝術和教育鋪天蓋地的市場化。但是這個處境有個弔詭之處,那就是西方國家裡的參與反而比較接近新自由主義政府的民粹議題。即使參與式藝術家不約而同地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人們卻只是從形式上理解他們灌注在其作品裡的價值(反對個人主義和商品對象),而沒有認識到,該藝術創作的許多其他面向其實和新自由主義最近的形式更加吻合(網路、流動性、計畫作品、情感性勞動﹝affective labour﹞)。在二十世紀裡,隨著這個基礎的轉變,在每個歷史時期裡,對於參與的身分也有不同的想像:從民眾(1910年代)到群眾(1920年代),到人民(1960年代後期和1970年代),到社會邊緣人(1980年代),到社區(1990年代),到現在的自願參與者,他們的參與是實境電視和社會網路的文化的延伸。從觀眾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把它描繪成從要求一個角色的觀眾(表現在對於一直控制著舞台的前衛藝術家的厭惡)轉變到一個樂於接受由藝術家為他們設計陌生經驗的觀眾,又轉變為被鼓勵成為作品的共同作者的觀眾(偶爾甚至會付費給參加者)。它可以視為對於觀眾的激勵和主動性日增的史詩敘事,但是也可以說我們越來越願意接受藝術家的意志,而人們的身體也在服務性經濟裡越來越商品化(因為自願的參與也是一種不支薪的勞動)。它和民主自身的坎坷命運顯然很類似,那是和參與經常相提並論的一個語詞:從要求被承認,到表現,到兩願地消費自己的形象,無論是在藝術作品裡,或是在Facebook、Flickr,或是實境電視。我們不妨以安東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的《一與其他》(One and Other, 2009)的媒體報導為例,該計畫讓民眾持續佔據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的「第四基座」,每個人在上頭站一個小時,接力展演一百天。34,520個應徵者來自2,400個地方,佔據基座的行動持續上傳到網路。雖然葛姆雷說《一與其他》是「讓人們有機會挑戰他們的自我感以及如何將它傳達給更廣大的世界的公共空間」,《衛報》則頗為持平地將該計畫形容為「推特藝術」(Twitter Art)。在每個人都可以將他們的想法傳送給所有人知道的世界裡,我們面對的不是群眾的賦權,而是一連串平庸化的自我。「參與」根本不是「奇觀」的對立面,現在反而和它沆瀣一氣。在二十世紀裡,隨著這個基礎的轉變,在每個歷史時期裡,對於參與的身分也有不同的想像:從民眾(1910年代)到群眾(1920年代),到人民(1960年代後期和1970年代),到社會邊緣人(1980年代),到社區(1990年代),到現在的自願參與者,他們的參與是實境電視和社會網路的文化的延伸。從觀眾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把它描繪成從要求一個角色的觀眾(表現在對於一直控制著舞台的前衛藝術家的厭惡)轉變到一個樂於接受由藝術家為他們設計陌生經驗的觀眾,又轉變為被鼓勵成為作品的共同作者的觀眾(偶爾甚至會付費給參加者)。它可以視為對於觀眾的激勵和主動性日增的史詩敘事,但是也可以說我們越來越願意接受藝術家的意志,而人們的身體也在服務性經濟裡越來越商品化(因為自願的參與也是一種不支薪的勞動)。它和民主自身的坎坷命運顯然很類似,那是和參與經常相提並論的一個語詞:從要求被承認,到表現,到兩願地消費自己的形象,無論是在藝術作品裡,或是在Facebook、Flickr,或是實境電視。我們不妨以安東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的《一與其他》(One and Other, 2009)的媒體報導為例,該計畫讓民眾持續佔據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的「第四基座」,每個人在上頭站一個小時,接力展演一百天。34,520個應徵者來自2,400個地方,佔據基座的行動持續上傳到網路。雖然葛姆雷說《一與其他》是「讓人們有機會挑戰他們的自我感以及如何將它傳達給更廣大的世界的公共空間」,《衛報》則頗為持平地將該計畫形容為「推特藝術」(Twitter Art)。在每個人都可以將他們的想法傳送給所有人知道的世界裡,我們面對的不是群眾的賦權,而是一連串平庸化的自我。「參與」根本不是「奇觀」的對立面,現在反而和它沆瀣一氣。奇觀和參與的再度攜手,使得藝術批判和社會批判的緊張關係益顯必要。參與式藝術歷史裡許多最著名的計畫,都在顛覆作為該論述的基礎的對立性(個人和集體、作者和觀看者、主動和被動、現實生活和藝術),但不是要澈底瓦解它們。如是,他們維持了藝術批判和社會批判的緊張關係。瓜達里的「橫截性」的典範透過這些藝術操作提供了這類的思考:他不談作為範疇的藝術,而著重於藝術和其他學科的交涉,同時質疑藝術和社會,雖然同時也重申藝術有自己的價值世界。洪席耶則有另一種想法:美學國度在構成上即是矛盾的,穿梭在自律「以及」他律之間(「只要美感經驗是那個『以及』的經驗,它就有作用」)。他說,在藝術、劇場和教育裡,必須有個中介的事物,置於藝術家的想法和觀看者的感受以及詮釋之間:「這個奇觀是個第三項(third term),其他兩個關係項可以指涉它,但是有避免任何『等於』或『沒有扭曲的』傳遞。它是它們之間的中介,一個第三項的中介在整個知性解放的過程裡至關緊要……將它們串聯在一起的東西,必須同時也將它們分開。」哲學家則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另一個用以同時思考藝術和社會的架構;對於他們而言,藝術和社會是沒辦法和解的,而是維持一種緊張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