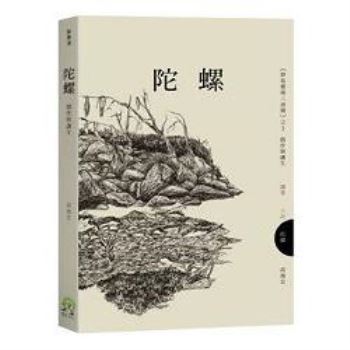前言
創作的持續,是對困境的延遲表决
我不知道妳有沒有看過淹大水時紅螞蟻逃命的策略?牠們以卵繭為筏,互相齧咬著、抓著彼此,以身體織成一顆網狀的球,漂浮在水上,以抵達可能的陸地。那也是我的小文學策略,也是我對書的想像……。
――黃錦樹
書是一套違規的現代主義
如何讓這十年來荒原般的創作,成為一本「書」?
比起自己同時期出版的《小說:台籍日本兵張正光與我》和《諸眾:東亞藝術佔領行動》,雖然前者是類似底層研究的「假小說」,後者為非論文式的藝術佔領研究,但兩者格式清楚,成書之結構亦單純。但《陀螺》就難了。這本「書」既有十年來的作品圖片、錄像,又有自己和他人的評論,為了不讓書變成「作品集」、「插圖專輯」,且避免淪為雜燴式的告白絮語,在這過程中,將作品編成一本書,是一個重新從「質」的角度,觀看作品檔案與檔案之間可能存在的潛在關係。
想起黃錦樹寫的「以身體織成一顆網狀的球」。相對於《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那本「先小說、後馬共」的文類,其實我的《陀螺》是由許多相互指點又好像彼此不認識的「短篇」所組成的「長篇」。但是黃錦樹更耐人尋味地說道,相較於長篇,他更喜歡書,因為那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整體。我的理解是,無論文章與文章之間有何關連性,長篇仍是「某種敘事」。但是,書這個東西就更複雜了,它不僅是商品,具有拿在手上可翻閱的物質性,也包含影像如何再現於平面紙張、章節與章節之間彼此存在的張力,同時也具有「一體性的假設」。因此我能想像,書是現代主義的邊界,既包覆於作者中心論的邏輯,同時又可能是某種逃離,如同那一球球的紅螞蟻。在處理《陀螺》這本書時,不僅要面對「如何讓作品集成為一本書」的困境,也必須重新想像什麼是書?或許,《陀螺》可能只是一顆織成球狀的通透體,在裡面,每件看似無關、解離的作品或書寫的深處,總有一堆莫名的力量在「幹拐子」,彷彿一種共同的面相推著這顆蟻球前進。也許那個所謂的「共同面向」,正是創作本身的困境。
《陀螺》的三個面相
這本書分為〈失址〉、〈幽舟〉、〈仕紳〉三個部分。〈失址〉包含了近年來關於歷史、廢棄產業空間之創作、拍攝與書寫,表面上與自己關注的新自由主義研究相關,但是更為基進也更激烈地,與母親成為一個「1995年被大陸進口內衣擊垮」的本地內衣攤販,有著無法分離的憤怒。因此,所謂「廢墟」創作,對我而言,其精神結構多半源自於此。在我的觀點中,廢墟與美學無關。
〈幽舟〉是《陀螺》裡最隱晦的部分,原因在於許多創作的發生往往是「連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但它確實又理智地發生了。在此以羅蘭.巴特(R. Barthes)的「幽舟」來說明:
我不能說出自己的、完整的愛情故事,我是個只能起頭的詩人。這個故事的結尾,正如同我自身的死亡一樣,只有別人知道。
〈幽舟〉隱含著自己對於創作者勞動狀況的些許感傷,要說有一絲的自艾自憐也好,但我很清楚這種哀傷絕非臣服(subjection),或因喪失某物而起,而是一股讓自己更積極推往社會、人群的力量與形貌。
此外,〈幽舟〉裡也包含一些關於「身體」的論述,與其他無法說清楚的。
〈仕紳〉則收錄了幾件與都市仕紳化(gentrification)相關的行動紀錄和文章。來自於2010年的「花博」給予芸芸眾生的啟發,促使我一步步串起所謂「文化治理」下,我們作為「藝術蟻民」的種種活動,不過是一群在龐大的藝術機制、「讓生」機器裡面「ㄆㄤˋ」(轉)的活鬼。仕紳化的本質不只是中產階級化、私有化、土地商品化,也內含著更難捕捉、細緻的意識帝國。現在我更清楚,今日帝國主義的結構根本與「玩具回力鏢」的設計如出一轍,不僅犧牲了他者,同時反身轉向每一個蟻民個體,「讓個體帝國主義化」、「讓個體分攤帝國的憂慮」。〈仕紳〉聚焦的議題便是今日新自由主義的「自我美學」及奉「絕對增益」為圭臬的土地開發之邏輯。
十年前的泡沫
《陀螺》的出版,遙遙呼應了十年前的作品集──《泡沫》。
不知是被雷打到或其他莫名的原因,我開始了以「十年」為單位整理自己的創作,心想可能也剩下不到幾回十年的創作了,因此這次特別用心編輯《陀螺》、《小說》和《諸眾》這三本書。過程中經常被一個問題所驚醒:「如果立志一輩子做創作者,那你要做什麼?」2004年出版《泡沫》時,可能是因為初生之犢不畏虎,我完全耽溺於學院式的幻象裡,好像堅持藝術的理念便能超越人世間的困頓。
《泡沫》出版後意外得了某個藝術獎項,頗有機會「出頭天」,然而我卻經歷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時期。所謂「創作低潮」,指的是當「一輩子立志做創作者」的信念突然失去了方向感,不斷遭受現實殘酷的折磨時,便會出現無法(來不及)填補的憂鬱感,開始懷疑起《泡沫》裡過去十年一切的藝術勞動。那段期間,自己活像一隻冬眠的烏龜,以很低的物質欲望過活,僅能淨空腸道,專注地活著。有一陣子病況嚴重,甚至搬到礁溪療養,力圖甦醒,但終究失敗。
時過境遷,今日以《陀螺》奮力擲向十年前的《泡沫》,我重新體會到,「一輩子立志做個創作者」正如一紙與世界所簽的「情感合約」,在沒有公證人也無法後悔的處境下,不斷地尋找續約的動力。藝術創作的持續很可能只是對困境的延遲表决,不斷地產生如同葛林賓斯基(M. Gribinski)在《現實的困擾》裡指出的「替代物」(L’Ersatzreifen)。據說,一次大戰時替代物這個字意味著:準備參戰和犧牲的士兵(ersatz)。假如藝術的世界依然存在著真誠的創作,那麼,在不斷替代之中,它的真實樣貌是什麼?
是因為這份創作的生命合約所衍生的困境。
從2004年的《泡沫》看今日,從十多年來台灣藝術場域話語模式看今日,台灣藝術場域話語模式的演變具有考掘學的意義。「社會」、「公共」、「政治」等概念的突顯,意味著短短十年間,藝術的世界集體朝向政治經濟學式的知識而發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社會階級、貧富強烈分化,另一方面則是「批判」成為知識顯學。假如《泡沫》建構了身體與概念藝術的獨立與孤絕性,以為可以取代那平庸不堪的日常生活,那麼從我自己的觀點來看,《陀螺》這本書廣泛觸及了政治經濟學式的創作議題。因此,它的替代物,毫無疑問是對無政府共產失能、失效困境下的想像,甚至情感。
我揣想著,也許理論是某種近似檔案與精神官能症交錯下的產物,文字是兩者的替代物,「書」則不小心指出現代主義不過是一個備胎。那《陀螺》呢?它受困於一個沒辦法說清楚,「所有困境的總和」,如人、如生,不轉則死。
創作的持續,是對困境的延遲表决
我不知道妳有沒有看過淹大水時紅螞蟻逃命的策略?牠們以卵繭為筏,互相齧咬著、抓著彼此,以身體織成一顆網狀的球,漂浮在水上,以抵達可能的陸地。那也是我的小文學策略,也是我對書的想像……。
――黃錦樹
書是一套違規的現代主義
如何讓這十年來荒原般的創作,成為一本「書」?
比起自己同時期出版的《小說:台籍日本兵張正光與我》和《諸眾:東亞藝術佔領行動》,雖然前者是類似底層研究的「假小說」,後者為非論文式的藝術佔領研究,但兩者格式清楚,成書之結構亦單純。但《陀螺》就難了。這本「書」既有十年來的作品圖片、錄像,又有自己和他人的評論,為了不讓書變成「作品集」、「插圖專輯」,且避免淪為雜燴式的告白絮語,在這過程中,將作品編成一本書,是一個重新從「質」的角度,觀看作品檔案與檔案之間可能存在的潛在關係。
想起黃錦樹寫的「以身體織成一顆網狀的球」。相對於《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那本「先小說、後馬共」的文類,其實我的《陀螺》是由許多相互指點又好像彼此不認識的「短篇」所組成的「長篇」。但是黃錦樹更耐人尋味地說道,相較於長篇,他更喜歡書,因為那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整體。我的理解是,無論文章與文章之間有何關連性,長篇仍是「某種敘事」。但是,書這個東西就更複雜了,它不僅是商品,具有拿在手上可翻閱的物質性,也包含影像如何再現於平面紙張、章節與章節之間彼此存在的張力,同時也具有「一體性的假設」。因此我能想像,書是現代主義的邊界,既包覆於作者中心論的邏輯,同時又可能是某種逃離,如同那一球球的紅螞蟻。在處理《陀螺》這本書時,不僅要面對「如何讓作品集成為一本書」的困境,也必須重新想像什麼是書?或許,《陀螺》可能只是一顆織成球狀的通透體,在裡面,每件看似無關、解離的作品或書寫的深處,總有一堆莫名的力量在「幹拐子」,彷彿一種共同的面相推著這顆蟻球前進。也許那個所謂的「共同面向」,正是創作本身的困境。
《陀螺》的三個面相
這本書分為〈失址〉、〈幽舟〉、〈仕紳〉三個部分。〈失址〉包含了近年來關於歷史、廢棄產業空間之創作、拍攝與書寫,表面上與自己關注的新自由主義研究相關,但是更為基進也更激烈地,與母親成為一個「1995年被大陸進口內衣擊垮」的本地內衣攤販,有著無法分離的憤怒。因此,所謂「廢墟」創作,對我而言,其精神結構多半源自於此。在我的觀點中,廢墟與美學無關。
〈幽舟〉是《陀螺》裡最隱晦的部分,原因在於許多創作的發生往往是「連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但它確實又理智地發生了。在此以羅蘭.巴特(R. Barthes)的「幽舟」來說明:
我不能說出自己的、完整的愛情故事,我是個只能起頭的詩人。這個故事的結尾,正如同我自身的死亡一樣,只有別人知道。
〈幽舟〉隱含著自己對於創作者勞動狀況的些許感傷,要說有一絲的自艾自憐也好,但我很清楚這種哀傷絕非臣服(subjection),或因喪失某物而起,而是一股讓自己更積極推往社會、人群的力量與形貌。
此外,〈幽舟〉裡也包含一些關於「身體」的論述,與其他無法說清楚的。
〈仕紳〉則收錄了幾件與都市仕紳化(gentrification)相關的行動紀錄和文章。來自於2010年的「花博」給予芸芸眾生的啟發,促使我一步步串起所謂「文化治理」下,我們作為「藝術蟻民」的種種活動,不過是一群在龐大的藝術機制、「讓生」機器裡面「ㄆㄤˋ」(轉)的活鬼。仕紳化的本質不只是中產階級化、私有化、土地商品化,也內含著更難捕捉、細緻的意識帝國。現在我更清楚,今日帝國主義的結構根本與「玩具回力鏢」的設計如出一轍,不僅犧牲了他者,同時反身轉向每一個蟻民個體,「讓個體帝國主義化」、「讓個體分攤帝國的憂慮」。〈仕紳〉聚焦的議題便是今日新自由主義的「自我美學」及奉「絕對增益」為圭臬的土地開發之邏輯。
十年前的泡沫
《陀螺》的出版,遙遙呼應了十年前的作品集──《泡沫》。
不知是被雷打到或其他莫名的原因,我開始了以「十年」為單位整理自己的創作,心想可能也剩下不到幾回十年的創作了,因此這次特別用心編輯《陀螺》、《小說》和《諸眾》這三本書。過程中經常被一個問題所驚醒:「如果立志一輩子做創作者,那你要做什麼?」2004年出版《泡沫》時,可能是因為初生之犢不畏虎,我完全耽溺於學院式的幻象裡,好像堅持藝術的理念便能超越人世間的困頓。
《泡沫》出版後意外得了某個藝術獎項,頗有機會「出頭天」,然而我卻經歷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時期。所謂「創作低潮」,指的是當「一輩子立志做創作者」的信念突然失去了方向感,不斷遭受現實殘酷的折磨時,便會出現無法(來不及)填補的憂鬱感,開始懷疑起《泡沫》裡過去十年一切的藝術勞動。那段期間,自己活像一隻冬眠的烏龜,以很低的物質欲望過活,僅能淨空腸道,專注地活著。有一陣子病況嚴重,甚至搬到礁溪療養,力圖甦醒,但終究失敗。
時過境遷,今日以《陀螺》奮力擲向十年前的《泡沫》,我重新體會到,「一輩子立志做個創作者」正如一紙與世界所簽的「情感合約」,在沒有公證人也無法後悔的處境下,不斷地尋找續約的動力。藝術創作的持續很可能只是對困境的延遲表决,不斷地產生如同葛林賓斯基(M. Gribinski)在《現實的困擾》裡指出的「替代物」(L’Ersatzreifen)。據說,一次大戰時替代物這個字意味著:準備參戰和犧牲的士兵(ersatz)。假如藝術的世界依然存在著真誠的創作,那麼,在不斷替代之中,它的真實樣貌是什麼?
是因為這份創作的生命合約所衍生的困境。
從2004年的《泡沫》看今日,從十多年來台灣藝術場域話語模式看今日,台灣藝術場域話語模式的演變具有考掘學的意義。「社會」、「公共」、「政治」等概念的突顯,意味著短短十年間,藝術的世界集體朝向政治經濟學式的知識而發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社會階級、貧富強烈分化,另一方面則是「批判」成為知識顯學。假如《泡沫》建構了身體與概念藝術的獨立與孤絕性,以為可以取代那平庸不堪的日常生活,那麼從我自己的觀點來看,《陀螺》這本書廣泛觸及了政治經濟學式的創作議題。因此,它的替代物,毫無疑問是對無政府共產失能、失效困境下的想像,甚至情感。
我揣想著,也許理論是某種近似檔案與精神官能症交錯下的產物,文字是兩者的替代物,「書」則不小心指出現代主義不過是一個備胎。那《陀螺》呢?它受困於一個沒辦法說清楚,「所有困境的總和」,如人、如生,不轉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