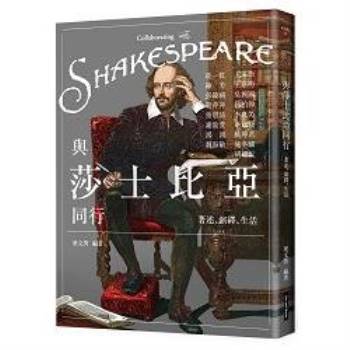把時代的荒謬放進哈姆雷特——鴻鴻訪談
◎:梁文菁 ▲ :鴻鴻
◎ 我們從比較早的時期開始聊好了,您的畢業製作《射天》改編自《哈姆雷特》,在當時的板橋台北縣立文化中心演出。我們現在從台灣莎士比亞資料庫上,還可以看到節目單等相關資料。想先請問您,當時為什麼想改編《哈姆雷特》?
▲ 可能要從我自己最早的莎士比亞經驗開始談起。我是一九八二年念第一屆的國立藝術學院,在那個年代另外一個戲劇系就是文化大學戲劇系,他們每年的學期公演,一定是做莎士比亞。那時候我也去當時的藝術館,就是現在的南海劇場,看了好幾齣他們做的莎劇。因為導演的方式很老派,表演的方式很煽情,就是一個非常老派的話劇演法,所以一開始對莎士比亞的第一印象是很差的。這個印象後來花了很大的力氣才扭轉過來。
在課堂上接觸到莎士比亞是因為賴聲川老師。他教我們西洋劇場史,他自己是莎士比亞的專家,尤其對於莎士比亞那種悲喜交錯、悲喜交融的寫作方式,非常有心得,所以透過他導讀,我覺得對莎士比亞有了一個比較好的印象。但真正決定我畢業製作會做《哈姆雷特》,是因為當時看了黑澤明的《蜘蛛巢城》跟《亂》。
尤其是《蜘蛛巢城》,我印象非常深刻,它讓我回想起小時候喜歡讀的演義小說,像是《東周列國志》,就是講戰國時期的那種說客、不同的國家用心計在攻防。如果黑澤明可以把《馬克白》放到日本的戰國時代,那我其實也可以把《哈姆雷特》直接放到中國的戰國時代,所以當時就決定做那麼一個改編。
但這樣一來,莎士比亞原本的台詞,很多就不合用了,等於整個要重寫。所以我是根據它原有的場次,做了很多轉換。就像黑澤明把三個女巫變成一個搖著紡車的日本女巫,其實是意義上與場面調度上有很大的改變,我也有這樣的改變。比如說戲中戲變成一場太卜,就是當時巫師祭神的儀式,然後被附體,整個就是讓它中國化跟現代化。說起來很奇怪,放置到中國的古代,反而是我把它現代化的一種方式,因為對我來說,至少有兩個層次:也就是先把莎士比亞從西方的古典轉移到中國的古典,然後再拉到中國的當代,其實是當時台灣的處境。踉蹌的哈姆雷特(小標)
作品的台灣性比較來自於演員。我選了一個個頭很小的演員陳明才,演我的哈姆雷特。當時大概所有的老師都反對,包括我們的系主任、我的指導老師,他們都覺得哈姆雷特應該要有英雄氣質。我說我就是要一個沒有英雄氣質的哈姆雷特,因為我覺得任何人都可能,莫名其妙地被背上責任,要去為上一代復仇。
那正是我在大五畢業、要去當兵前夕的心情,就覺得我要去當兵、要去面對打共匪的責任,那這些人到底跟我是什麼關係?我變成一個軍人,我要去面對的敵人,是我上一代的恩怨,我覺得那非常荒謬,有一種時代的荒謬感。所以我把這件事情放進了《哈姆雷特》。在我的戲裡王子叫作孟辛,孟辛公子變成一個不適任的復仇者,其實這也是很多人對於哈姆雷特的詮釋方式,覺得他其實是不能勝任的。
我用他的個頭矮小,強調了這樣的不能勝任,陳明才是滿口台灣國語,跟台灣的現實有一個比較接近的狀態。他拿到父親賜給他的一把劍跟一副盔甲,他穿上那個盔甲,復完仇才能脫下來,但那個盔甲顯然是一個偉大的盔甲,他穿上去之後,整個人幾乎沒辦法走路要跌倒,劍他也拖著根本舉不起來,就這麼一副狼狽踉蹌的狀態要去復仇。我想我給哈姆雷特最重要的詮釋在這上面。
其他很多部分就是細節上面的改換。例如,奧菲莉亞(Ophelia)變成少姬,裡面有一些歌舞的場景,可以襯托她發瘋時的跳舞跟唱歌。因為那時我也在迷馬奎斯(G. G. Márquez),就用了一些魔幻寫實場景,比如說,把奧菲莉亞的死,變成大家聽到她在十里外的河邊唱歌,傳進宮中。當然,更多是把《東周列國志》裡戰國的氣氛帶進來,像是一開始的兩個兵,我塑造成一個老兵、一個新兵,藉著他們的對白,把當時戰國時代互相攻伐的氛圍講出來。
不同於《哈姆雷特》將丹麥跟挪威、波蘭的戰爭藏在背景,只露一點苗頭出來;在我的戲裡,王子一開始就是主角,就是在打仗。在這個狀態裡,叔叔篡位的行動變成有正當性,因為原本的老王其實是不問世事、只顧著自己修行的狀態,有點老子。很積極的弟弟就覺得這樣國家會亡,所以把哥哥幹掉,然後要勵精圖治,也讓篡位有它政治上的意涵,是為了讓國家導向另外一個方向。對於王子孟辛來說,他要復仇的對象,其實是他可能比較認同的父親形象,弒父的矛盾,更增加他的伊底帕斯情結。
所以孟辛後來沒有辦法用他自己的力量去翻盤時,他就選擇逃走,直接進到敵國,變成一個說客,像是吳三桂引清兵入關這樣的角色,但這個謀略後來導致了整個國家的覆亡。這些屬於中國的元素在裡面都起了一種比較關鍵性的作用,他扭轉了莎士比亞很多戲劇的情境。
我記得當時在我們系主任姚一葦老師眼裡,這些轉變他覺得大逆不道,所以我做完《射天》之後,姚老師就發下重語,以後絕對不能讓學生再這麼大膽地改寫莎士比亞,他覺得是一個很失敗的嘗試。
◎ 那時候外文系的老師們也都看了這個演出嗎?
▲ 有,應該有看,彭鏡禧老師等等。其實那時候藝術學院做任何東西、甚至課堂呈現,也都有很多外面的劇場人跑來看。因為大家都很好奇這一屆的成果到底是怎樣,像金士傑、黃建業等等。
◎ 這些跟你合作的人,不少都繼續在劇場裡面工作,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他們嗎?
▲ 原本的《哈姆雷特》就是兩個女主角,皇后跟奧菲莉亞,我找了蕭艾來演皇后,蔣薇華演奧菲莉亞。李永豐演太卜,就是巫師的角色,非常出色,因為他就是有一種可以呼風喚雨的氣質。還有王道南演波隆尼爾(Polonius),王學城演國王,更不要說陳明才演王子。
阿才在裡面的表現非常非常獨特,一方面是他的個人氣質,一方面他的表演方法跟別人不太一樣,有一點接近被附身的表演狀態,所以他每次排每次都不一樣,跟他對戲的人,尤其像蔣薇華,就非常辛苦。那個時候我們在蘆洲排,排到後來,阿才甚至有一種就是真的被附身的狀態,他在生活中間都顛顛倒倒。
他說他在蘆洲的校舍裡會看到一些戰國時代的幽靈,到快演出的時候他幾乎都不能排練,那時候我們都很擔心,然後在想怎麼換角的問題。可是我硬著頭皮說,他不排沒關係,我們其他部分繼續排。後來到了進劇場裝台的時候,他站到台上,他說:「歐!其實一切都是假的。」他才回過神來,可以做這個表演。
◎ 好迷幻。你會想再做一次《哈姆雷特》嗎?
▲ 我後來有考慮要再做,但是可能就完全不會用《射天》的方式,而會做原來的文本。我希望做得更野蠻一點、更情慾一點、更本能的東西跑出來多一點。◎ 《哈姆雷特》是台灣較常見的莎劇演出,有沒有哪一個製作讓你印象深刻?
▲ 台灣看到的這些《哈姆雷特》,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歐斯特麥耶的版本,是柏林列寧廣場劇院的製作。一來因為它非常有創意,用第五幕挖墳的場景開始,關於死亡,先用一個幫死掉的國王挖墳給凸顯出來。而且第一句台詞就是「To be or not to be.」,我覺得非常的大膽、非常的強悍。
演哈姆雷特的演員也很厲害,整個台都快要被他吃掉了。他讓我看到現代人的心智陷於癲狂邊緣的一種狀態,一種當代人的感受。它好像只用了六個演員,來重複扮演其中不同角色,包括兩個女性角色是同一個演員,我覺得這點也非常厲害。他找到了角色跟角色之間的連結性,對於哈姆雷特來說,這些人的意義在某些方面是連結起來的。
拿莎士比亞當劇團的試金石(小標)
◎ 後來其實您就沒有沒有再做莎士比亞製作,但是您在二○○三年策劃了「莎士比亞在台北」。
▲ 其實「莎士比亞在台北」是源自於國家劇院的邀約。他們想要開始嘗試策展人制,因為之前實驗劇場的展演都是他們自己邀約,可能也覺得到了某種瓶頸,或者想要看看不同的觀點。一開始找我,我覺得是因為我在二○○○年的時候,策展過一系列台灣文學劇場,主要在皇冠劇場及實驗劇場演出。那次得到的評價還不錯,所以他們就找我,看看能不能再策劃一個系列。
那時候我想要做「莎士比亞在台北」,因為我覺得從八○到九○年代到進入新世紀之後,每個劇團自己的風格有點確定了,而且演員的表演功力也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機會,可以拿莎士比亞當每個劇團的試金石,或者讓大家可以衝撞一次,然後看能不能再往上。所以我就跟自己當時比較欣賞的幾個導演談,後來確定下來的,是王嘉明做《泰特斯》、呂柏伸做《馬克白》、符宏征做《李爾王》、王榮裕做《羅密歐與茱麗葉》,以及郭文泰《美麗的莎士比亞》。我記得《泰特斯》應該是我推薦給嘉明的劇本,因為當時他覺得莎士比亞好像不知道有什麼好做的。我就跟他說,有一些比較冷門的劇本其實還滿殘酷、滿有趣的,推薦給他這個劇本。事隔一、兩個月,他就說他看了劇本,的確覺得很有意思,所以他決定做《泰特斯》。但是做法卻是我一開始沒有料想到的,他用了布袋戲、人偶,最後把夾子小應也放進去,做了一個「夾子/布袋版」。
他的手法,包括使用空間的方法,讓舞台的多面有觀眾,對當時的劇場來說,算是一個滿興奮的事情。然後他把幾乎所有人的臉都蒙起來,用偶戲的方式在表演。我覺得沒有做到百分之百成功,因為這個戲其實滿長的,如果表演的程式不夠精細,或者是不夠豐富時,看到後來會有一種單調的危機。但我覺得嘉明也很聰明,他也用夾子小應去把這種單調打破。
呂柏伸把《馬克白》改成《女巫奏鳴曲》,因為當時他們受到波蘭的表演訓練,也是葛羅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後來流傳下來的訓練方式的影響。他們也從國外請老師來做工作坊,嘗試用一種身體跟聲音的集體表演方式來做《馬克白》,我覺得是滿詩意、滿儀式化的一種方式。
符宏征其實掛了兩個團,「外表坊時驗團」是宏征當時的團,還有跟吳忠良「身聲演繹社」合作,用了擊鼓的方式。《李爾王》的情節在裡面被刪掉滿多,變成一段一段,用音樂帶領著戲劇往前走。在這麼一個大家聯演的狀況裡,由於彼此都想要突出自己的風格,所以我想他們做了比較大的改編。
但除了金枝。金枝的改編可以說比較不是在文本上,而是在詮釋上面。羅密歐與茱麗葉兩家為什麼是世仇呢?因為一個是本省一個是外省,這樣子的衝突。但是我覺得在演出當中,這個政治層次、意識層次沒有繼續發展,只是用了這個背景,其實還是照著莎劇的脈絡走,但是表演方式是熟悉的、比較台客的表演方式。我覺得這個作品變成幾個作品中,可以說最貼近莎士比亞原本的。後來他們可能覺得做了這樣還不滿足,所以乾脆重新寫一次,就是後來的《玉梅與天來》。河床劇團的《美麗的莎士比亞》,我覺得是最有創意的,而且在美感、詮釋上面都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我自己非常喜歡這個演出。雖然說對很多觀眾來說,河床那種不太講話的、意在言外的方式,在當時有點難接受。但河床已經發展了一段時間,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把它放到一個平台上,跟其他相對來說大家比較熟悉的劇團放在一起,來凸顯河床的獨特之處。比如說河床就做了三個莎士比亞的頭套,所以場上有時候會有三個莎士比亞同時出現,他的詮釋在於莎士比亞的寫作跟後來的人對寫作的詮釋中間的落差。
有些畫面讓我印象深刻,比如說莎士比亞坐在那邊,一個女孩子跪在他面前嘴巴張開,他用他的筆蘸著女孩子舌頭裡面紅色的汁液在書寫。我覺得這個其實有一種強烈的性意象、虐待的意象,或者是一個作家跟現實的關係等等,是一個非常豐富的意象。後來就有莎士比亞把他的頭拿下來,在那邊扭來扭去,把頭套整個揉成一團;讓我們看到莎士比亞對於自己被定型的樣貌,他不見得會滿意,或者也可以說後來的人不斷地去詮釋莎士比亞,他早就變形了。
由於河床用的是一種高度意象化的表演方式,我相信不同的觀眾看到這些畫面都會有不同的感受,去回應到莎士比亞這個議題的方方面面。郭文泰本來是說他絕對不會做莎士比亞,因為莎士比亞是一個語言落落長的⋯⋯
◎ 跟他們風格好像不太⋯⋯
▲ 對,跟他風格完全不合。對我來說,策展人這個角色如果有一點重要性的話,也應該是在這邊。就是他會拿不同的題目去挑戰一些團體,讓他們欣然接受挑戰後,就可以做到一些原本都不會做的事情。因為,如果他們做的是原本就會做的事情,策這個展其實意義不大,我覺得把他們兜在一起,可以讓大家看到,台灣這些劇團面對所謂世界殿堂級作品時,各自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登高,然後可以用不同的對話方式。
◎ 于善祿在討論「莎士比亞在台北」的時候,他覺得這一系列是文學與小劇場的集合,可以幫小劇場展開新的空間。您自己覺得呢?▲ 因為所謂台灣的小劇場,早期應該是從棄絕文本或是說棄絕經典這個方式,走出自己的一條路。但是小劇場也有一些人,比如說,像黎煥雄、魏瑛娟,對文本都還滿敏感的。可能我自己比較會在歐洲看戲,我看到這些所謂偉大的、厲害的當代導演,其實全都是攻經典殺出一條血路出來。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的劇場也可以試試看,不見得會是一條主流,但是我們時候到了,做一次嘗試,應該也不錯。
在台灣,或是說用中文演莎士比亞,有一個先天的障礙,就是語言的障礙。但語言的障礙我覺得用原文也未必沒有,因為也不是這麼當代的英語,對觀眾來說也是一種挑戰。但是對於中文的讀者來說,我們不太習慣講話這麼饒舌,或在話語中間用這麼多的比喻,用這麼多的語言趣味去講一件事情。其實我記得用中文演出最有趣的一個莎士比亞,是早期民心劇場王小棣導演做的《莎士比亞之夜》,一開始就是羅北安走出來,他劈哩啪啦講了大概三分鐘的話,但是我們一個字也聽不懂,為什麼呢?
◎ 講中文嗎?
▲ 不是不是,為什麼呢?他講完之後,他就說,這個其實是把一整段莎士比亞的台詞從最後一個念到第一個字。小棣導演就用這種方式,一開始就攤開來說,我們聽莎士比亞的困難在哪裡,我們就像鴨子聽雷一樣,其實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但這個階段過去之後,她再回去用她的方式,選了一些莎士比亞重要的片段、一些人際關係,拿來做了一個排列組合,然後做了一整晚的莎士比亞的情節,比較從情節、人情去玩。因為她一開始開了一個語言的玩笑,大家反而放鬆了,真的比較可以進入那個情境。我覺得小棣導演可能對語言非常敏感,或者說對台灣人怎麼聽用中文演外國戲中間的這個落差,她特別去處理這個部分,會讓我覺得她是真正面對這個議題。
莎士比亞的愛情百科全書(小標)
◎ 您除了劇場工作以外,也是一位詩人,請問莎士比亞對您自己的創作與生活是否有影響?
▲ 我覺得可能還是從當初賴聲川老師引導的那個觀點切入。莎士比亞他悲喜交錯跟悲喜交融這一點真的是滿厲害。後來在我大概所有的劇場創作裡,都在走這麼一條路,就是說,即使是一個非常沉重的主題,但我都在中間找到一種側面切入。然後去調戲它、去跟它遊戲、互動,找到一些縫隙空間,去玩出一種劇場的趣味可能。莎士比亞做了最好的示範,在他所謂的悲劇裡頭,你都看到很多很有趣的片段,跟很有趣的小人物的塑造。尤其是裡面出現的那些小配角,一個一個其實都滿有意思的,像是《哈姆雷特》裡面的羅生(Rosencrantz)與吉爾(Guildenstern),或者是《馬克白》裡面那個開門的人。
這些人物都在不該他們出現的時候出現了,告訴我們歷史不是只有英雄人物的偉大敘事而已,歷史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參與;而且生活本來就是你在當下很難說是悲還是喜,你用不同的角度看,永遠有不同的詮釋的可能。這樣的觀點,大概就可以貫穿在我所有的劇場跟電影創作裡頭。
◎ 那麼,您會推薦哪一個劇本作為莎劇的入門?
▲ 我在學校教劇本分析時,《仲夏夜之夢》是我必教的。裡面所有的對比都非常清楚也非常巧妙,而且裡面的主角是年輕人,所以對於年輕讀者來說非常有親和力,你完全可以看到裡面莎士比亞是如何在嘲弄愛情。如果說《神鵰俠侶》是金庸的愛情百科全書,那《仲夏夜之夢》就是莎士比亞的愛情百科全書。
它讓我們看到這種情竇初開、一團混亂的男女關係,也看到這種婚後多年像仙王仙后這種怨偶的關係,等於把愛情的很多面向,嫉妒、背叛、不可預知性、朝生暮死等等全部都展現出來。還有理想的層面、征伐的層面、情慾的層面,全部都表現出來了,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而且裡面也有一個段落是我自己最喜歡的,應該是莎士比亞寫得最好的段落,就是當波頓(Bottom)從夢中醒來的時候講了一段話,那段話裡面就是所有的感官都互相交融、彼此錯置,我覺得那是最早的象徵主義的詩作。
◎:梁文菁 ▲ :鴻鴻
◎ 我們從比較早的時期開始聊好了,您的畢業製作《射天》改編自《哈姆雷特》,在當時的板橋台北縣立文化中心演出。我們現在從台灣莎士比亞資料庫上,還可以看到節目單等相關資料。想先請問您,當時為什麼想改編《哈姆雷特》?
▲ 可能要從我自己最早的莎士比亞經驗開始談起。我是一九八二年念第一屆的國立藝術學院,在那個年代另外一個戲劇系就是文化大學戲劇系,他們每年的學期公演,一定是做莎士比亞。那時候我也去當時的藝術館,就是現在的南海劇場,看了好幾齣他們做的莎劇。因為導演的方式很老派,表演的方式很煽情,就是一個非常老派的話劇演法,所以一開始對莎士比亞的第一印象是很差的。這個印象後來花了很大的力氣才扭轉過來。
在課堂上接觸到莎士比亞是因為賴聲川老師。他教我們西洋劇場史,他自己是莎士比亞的專家,尤其對於莎士比亞那種悲喜交錯、悲喜交融的寫作方式,非常有心得,所以透過他導讀,我覺得對莎士比亞有了一個比較好的印象。但真正決定我畢業製作會做《哈姆雷特》,是因為當時看了黑澤明的《蜘蛛巢城》跟《亂》。
尤其是《蜘蛛巢城》,我印象非常深刻,它讓我回想起小時候喜歡讀的演義小說,像是《東周列國志》,就是講戰國時期的那種說客、不同的國家用心計在攻防。如果黑澤明可以把《馬克白》放到日本的戰國時代,那我其實也可以把《哈姆雷特》直接放到中國的戰國時代,所以當時就決定做那麼一個改編。
但這樣一來,莎士比亞原本的台詞,很多就不合用了,等於整個要重寫。所以我是根據它原有的場次,做了很多轉換。就像黑澤明把三個女巫變成一個搖著紡車的日本女巫,其實是意義上與場面調度上有很大的改變,我也有這樣的改變。比如說戲中戲變成一場太卜,就是當時巫師祭神的儀式,然後被附體,整個就是讓它中國化跟現代化。說起來很奇怪,放置到中國的古代,反而是我把它現代化的一種方式,因為對我來說,至少有兩個層次:也就是先把莎士比亞從西方的古典轉移到中國的古典,然後再拉到中國的當代,其實是當時台灣的處境。踉蹌的哈姆雷特(小標)
作品的台灣性比較來自於演員。我選了一個個頭很小的演員陳明才,演我的哈姆雷特。當時大概所有的老師都反對,包括我們的系主任、我的指導老師,他們都覺得哈姆雷特應該要有英雄氣質。我說我就是要一個沒有英雄氣質的哈姆雷特,因為我覺得任何人都可能,莫名其妙地被背上責任,要去為上一代復仇。
那正是我在大五畢業、要去當兵前夕的心情,就覺得我要去當兵、要去面對打共匪的責任,那這些人到底跟我是什麼關係?我變成一個軍人,我要去面對的敵人,是我上一代的恩怨,我覺得那非常荒謬,有一種時代的荒謬感。所以我把這件事情放進了《哈姆雷特》。在我的戲裡王子叫作孟辛,孟辛公子變成一個不適任的復仇者,其實這也是很多人對於哈姆雷特的詮釋方式,覺得他其實是不能勝任的。
我用他的個頭矮小,強調了這樣的不能勝任,陳明才是滿口台灣國語,跟台灣的現實有一個比較接近的狀態。他拿到父親賜給他的一把劍跟一副盔甲,他穿上那個盔甲,復完仇才能脫下來,但那個盔甲顯然是一個偉大的盔甲,他穿上去之後,整個人幾乎沒辦法走路要跌倒,劍他也拖著根本舉不起來,就這麼一副狼狽踉蹌的狀態要去復仇。我想我給哈姆雷特最重要的詮釋在這上面。
其他很多部分就是細節上面的改換。例如,奧菲莉亞(Ophelia)變成少姬,裡面有一些歌舞的場景,可以襯托她發瘋時的跳舞跟唱歌。因為那時我也在迷馬奎斯(G. G. Márquez),就用了一些魔幻寫實場景,比如說,把奧菲莉亞的死,變成大家聽到她在十里外的河邊唱歌,傳進宮中。當然,更多是把《東周列國志》裡戰國的氣氛帶進來,像是一開始的兩個兵,我塑造成一個老兵、一個新兵,藉著他們的對白,把當時戰國時代互相攻伐的氛圍講出來。
不同於《哈姆雷特》將丹麥跟挪威、波蘭的戰爭藏在背景,只露一點苗頭出來;在我的戲裡,王子一開始就是主角,就是在打仗。在這個狀態裡,叔叔篡位的行動變成有正當性,因為原本的老王其實是不問世事、只顧著自己修行的狀態,有點老子。很積極的弟弟就覺得這樣國家會亡,所以把哥哥幹掉,然後要勵精圖治,也讓篡位有它政治上的意涵,是為了讓國家導向另外一個方向。對於王子孟辛來說,他要復仇的對象,其實是他可能比較認同的父親形象,弒父的矛盾,更增加他的伊底帕斯情結。
所以孟辛後來沒有辦法用他自己的力量去翻盤時,他就選擇逃走,直接進到敵國,變成一個說客,像是吳三桂引清兵入關這樣的角色,但這個謀略後來導致了整個國家的覆亡。這些屬於中國的元素在裡面都起了一種比較關鍵性的作用,他扭轉了莎士比亞很多戲劇的情境。
我記得當時在我們系主任姚一葦老師眼裡,這些轉變他覺得大逆不道,所以我做完《射天》之後,姚老師就發下重語,以後絕對不能讓學生再這麼大膽地改寫莎士比亞,他覺得是一個很失敗的嘗試。
◎ 那時候外文系的老師們也都看了這個演出嗎?
▲ 有,應該有看,彭鏡禧老師等等。其實那時候藝術學院做任何東西、甚至課堂呈現,也都有很多外面的劇場人跑來看。因為大家都很好奇這一屆的成果到底是怎樣,像金士傑、黃建業等等。
◎ 這些跟你合作的人,不少都繼續在劇場裡面工作,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他們嗎?
▲ 原本的《哈姆雷特》就是兩個女主角,皇后跟奧菲莉亞,我找了蕭艾來演皇后,蔣薇華演奧菲莉亞。李永豐演太卜,就是巫師的角色,非常出色,因為他就是有一種可以呼風喚雨的氣質。還有王道南演波隆尼爾(Polonius),王學城演國王,更不要說陳明才演王子。
阿才在裡面的表現非常非常獨特,一方面是他的個人氣質,一方面他的表演方法跟別人不太一樣,有一點接近被附身的表演狀態,所以他每次排每次都不一樣,跟他對戲的人,尤其像蔣薇華,就非常辛苦。那個時候我們在蘆洲排,排到後來,阿才甚至有一種就是真的被附身的狀態,他在生活中間都顛顛倒倒。
他說他在蘆洲的校舍裡會看到一些戰國時代的幽靈,到快演出的時候他幾乎都不能排練,那時候我們都很擔心,然後在想怎麼換角的問題。可是我硬著頭皮說,他不排沒關係,我們其他部分繼續排。後來到了進劇場裝台的時候,他站到台上,他說:「歐!其實一切都是假的。」他才回過神來,可以做這個表演。
◎ 好迷幻。你會想再做一次《哈姆雷特》嗎?
▲ 我後來有考慮要再做,但是可能就完全不會用《射天》的方式,而會做原來的文本。我希望做得更野蠻一點、更情慾一點、更本能的東西跑出來多一點。◎ 《哈姆雷特》是台灣較常見的莎劇演出,有沒有哪一個製作讓你印象深刻?
▲ 台灣看到的這些《哈姆雷特》,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歐斯特麥耶的版本,是柏林列寧廣場劇院的製作。一來因為它非常有創意,用第五幕挖墳的場景開始,關於死亡,先用一個幫死掉的國王挖墳給凸顯出來。而且第一句台詞就是「To be or not to be.」,我覺得非常的大膽、非常的強悍。
演哈姆雷特的演員也很厲害,整個台都快要被他吃掉了。他讓我看到現代人的心智陷於癲狂邊緣的一種狀態,一種當代人的感受。它好像只用了六個演員,來重複扮演其中不同角色,包括兩個女性角色是同一個演員,我覺得這點也非常厲害。他找到了角色跟角色之間的連結性,對於哈姆雷特來說,這些人的意義在某些方面是連結起來的。
拿莎士比亞當劇團的試金石(小標)
◎ 後來其實您就沒有沒有再做莎士比亞製作,但是您在二○○三年策劃了「莎士比亞在台北」。
▲ 其實「莎士比亞在台北」是源自於國家劇院的邀約。他們想要開始嘗試策展人制,因為之前實驗劇場的展演都是他們自己邀約,可能也覺得到了某種瓶頸,或者想要看看不同的觀點。一開始找我,我覺得是因為我在二○○○年的時候,策展過一系列台灣文學劇場,主要在皇冠劇場及實驗劇場演出。那次得到的評價還不錯,所以他們就找我,看看能不能再策劃一個系列。
那時候我想要做「莎士比亞在台北」,因為我覺得從八○到九○年代到進入新世紀之後,每個劇團自己的風格有點確定了,而且演員的表演功力也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機會,可以拿莎士比亞當每個劇團的試金石,或者讓大家可以衝撞一次,然後看能不能再往上。所以我就跟自己當時比較欣賞的幾個導演談,後來確定下來的,是王嘉明做《泰特斯》、呂柏伸做《馬克白》、符宏征做《李爾王》、王榮裕做《羅密歐與茱麗葉》,以及郭文泰《美麗的莎士比亞》。我記得《泰特斯》應該是我推薦給嘉明的劇本,因為當時他覺得莎士比亞好像不知道有什麼好做的。我就跟他說,有一些比較冷門的劇本其實還滿殘酷、滿有趣的,推薦給他這個劇本。事隔一、兩個月,他就說他看了劇本,的確覺得很有意思,所以他決定做《泰特斯》。但是做法卻是我一開始沒有料想到的,他用了布袋戲、人偶,最後把夾子小應也放進去,做了一個「夾子/布袋版」。
他的手法,包括使用空間的方法,讓舞台的多面有觀眾,對當時的劇場來說,算是一個滿興奮的事情。然後他把幾乎所有人的臉都蒙起來,用偶戲的方式在表演。我覺得沒有做到百分之百成功,因為這個戲其實滿長的,如果表演的程式不夠精細,或者是不夠豐富時,看到後來會有一種單調的危機。但我覺得嘉明也很聰明,他也用夾子小應去把這種單調打破。
呂柏伸把《馬克白》改成《女巫奏鳴曲》,因為當時他們受到波蘭的表演訓練,也是葛羅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後來流傳下來的訓練方式的影響。他們也從國外請老師來做工作坊,嘗試用一種身體跟聲音的集體表演方式來做《馬克白》,我覺得是滿詩意、滿儀式化的一種方式。
符宏征其實掛了兩個團,「外表坊時驗團」是宏征當時的團,還有跟吳忠良「身聲演繹社」合作,用了擊鼓的方式。《李爾王》的情節在裡面被刪掉滿多,變成一段一段,用音樂帶領著戲劇往前走。在這麼一個大家聯演的狀況裡,由於彼此都想要突出自己的風格,所以我想他們做了比較大的改編。
但除了金枝。金枝的改編可以說比較不是在文本上,而是在詮釋上面。羅密歐與茱麗葉兩家為什麼是世仇呢?因為一個是本省一個是外省,這樣子的衝突。但是我覺得在演出當中,這個政治層次、意識層次沒有繼續發展,只是用了這個背景,其實還是照著莎劇的脈絡走,但是表演方式是熟悉的、比較台客的表演方式。我覺得這個作品變成幾個作品中,可以說最貼近莎士比亞原本的。後來他們可能覺得做了這樣還不滿足,所以乾脆重新寫一次,就是後來的《玉梅與天來》。河床劇團的《美麗的莎士比亞》,我覺得是最有創意的,而且在美感、詮釋上面都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我自己非常喜歡這個演出。雖然說對很多觀眾來說,河床那種不太講話的、意在言外的方式,在當時有點難接受。但河床已經發展了一段時間,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把它放到一個平台上,跟其他相對來說大家比較熟悉的劇團放在一起,來凸顯河床的獨特之處。比如說河床就做了三個莎士比亞的頭套,所以場上有時候會有三個莎士比亞同時出現,他的詮釋在於莎士比亞的寫作跟後來的人對寫作的詮釋中間的落差。
有些畫面讓我印象深刻,比如說莎士比亞坐在那邊,一個女孩子跪在他面前嘴巴張開,他用他的筆蘸著女孩子舌頭裡面紅色的汁液在書寫。我覺得這個其實有一種強烈的性意象、虐待的意象,或者是一個作家跟現實的關係等等,是一個非常豐富的意象。後來就有莎士比亞把他的頭拿下來,在那邊扭來扭去,把頭套整個揉成一團;讓我們看到莎士比亞對於自己被定型的樣貌,他不見得會滿意,或者也可以說後來的人不斷地去詮釋莎士比亞,他早就變形了。
由於河床用的是一種高度意象化的表演方式,我相信不同的觀眾看到這些畫面都會有不同的感受,去回應到莎士比亞這個議題的方方面面。郭文泰本來是說他絕對不會做莎士比亞,因為莎士比亞是一個語言落落長的⋯⋯
◎ 跟他們風格好像不太⋯⋯
▲ 對,跟他風格完全不合。對我來說,策展人這個角色如果有一點重要性的話,也應該是在這邊。就是他會拿不同的題目去挑戰一些團體,讓他們欣然接受挑戰後,就可以做到一些原本都不會做的事情。因為,如果他們做的是原本就會做的事情,策這個展其實意義不大,我覺得把他們兜在一起,可以讓大家看到,台灣這些劇團面對所謂世界殿堂級作品時,各自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登高,然後可以用不同的對話方式。
◎ 于善祿在討論「莎士比亞在台北」的時候,他覺得這一系列是文學與小劇場的集合,可以幫小劇場展開新的空間。您自己覺得呢?▲ 因為所謂台灣的小劇場,早期應該是從棄絕文本或是說棄絕經典這個方式,走出自己的一條路。但是小劇場也有一些人,比如說,像黎煥雄、魏瑛娟,對文本都還滿敏感的。可能我自己比較會在歐洲看戲,我看到這些所謂偉大的、厲害的當代導演,其實全都是攻經典殺出一條血路出來。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的劇場也可以試試看,不見得會是一條主流,但是我們時候到了,做一次嘗試,應該也不錯。
在台灣,或是說用中文演莎士比亞,有一個先天的障礙,就是語言的障礙。但語言的障礙我覺得用原文也未必沒有,因為也不是這麼當代的英語,對觀眾來說也是一種挑戰。但是對於中文的讀者來說,我們不太習慣講話這麼饒舌,或在話語中間用這麼多的比喻,用這麼多的語言趣味去講一件事情。其實我記得用中文演出最有趣的一個莎士比亞,是早期民心劇場王小棣導演做的《莎士比亞之夜》,一開始就是羅北安走出來,他劈哩啪啦講了大概三分鐘的話,但是我們一個字也聽不懂,為什麼呢?
◎ 講中文嗎?
▲ 不是不是,為什麼呢?他講完之後,他就說,這個其實是把一整段莎士比亞的台詞從最後一個念到第一個字。小棣導演就用這種方式,一開始就攤開來說,我們聽莎士比亞的困難在哪裡,我們就像鴨子聽雷一樣,其實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但這個階段過去之後,她再回去用她的方式,選了一些莎士比亞重要的片段、一些人際關係,拿來做了一個排列組合,然後做了一整晚的莎士比亞的情節,比較從情節、人情去玩。因為她一開始開了一個語言的玩笑,大家反而放鬆了,真的比較可以進入那個情境。我覺得小棣導演可能對語言非常敏感,或者說對台灣人怎麼聽用中文演外國戲中間的這個落差,她特別去處理這個部分,會讓我覺得她是真正面對這個議題。
莎士比亞的愛情百科全書(小標)
◎ 您除了劇場工作以外,也是一位詩人,請問莎士比亞對您自己的創作與生活是否有影響?
▲ 我覺得可能還是從當初賴聲川老師引導的那個觀點切入。莎士比亞他悲喜交錯跟悲喜交融這一點真的是滿厲害。後來在我大概所有的劇場創作裡,都在走這麼一條路,就是說,即使是一個非常沉重的主題,但我都在中間找到一種側面切入。然後去調戲它、去跟它遊戲、互動,找到一些縫隙空間,去玩出一種劇場的趣味可能。莎士比亞做了最好的示範,在他所謂的悲劇裡頭,你都看到很多很有趣的片段,跟很有趣的小人物的塑造。尤其是裡面出現的那些小配角,一個一個其實都滿有意思的,像是《哈姆雷特》裡面的羅生(Rosencrantz)與吉爾(Guildenstern),或者是《馬克白》裡面那個開門的人。
這些人物都在不該他們出現的時候出現了,告訴我們歷史不是只有英雄人物的偉大敘事而已,歷史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參與;而且生活本來就是你在當下很難說是悲還是喜,你用不同的角度看,永遠有不同的詮釋的可能。這樣的觀點,大概就可以貫穿在我所有的劇場跟電影創作裡頭。
◎ 那麼,您會推薦哪一個劇本作為莎劇的入門?
▲ 我在學校教劇本分析時,《仲夏夜之夢》是我必教的。裡面所有的對比都非常清楚也非常巧妙,而且裡面的主角是年輕人,所以對於年輕讀者來說非常有親和力,你完全可以看到裡面莎士比亞是如何在嘲弄愛情。如果說《神鵰俠侶》是金庸的愛情百科全書,那《仲夏夜之夢》就是莎士比亞的愛情百科全書。
它讓我們看到這種情竇初開、一團混亂的男女關係,也看到這種婚後多年像仙王仙后這種怨偶的關係,等於把愛情的很多面向,嫉妒、背叛、不可預知性、朝生暮死等等全部都展現出來。還有理想的層面、征伐的層面、情慾的層面,全部都表現出來了,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而且裡面也有一個段落是我自己最喜歡的,應該是莎士比亞寫得最好的段落,就是當波頓(Bottom)從夢中醒來的時候講了一段話,那段話裡面就是所有的感官都互相交融、彼此錯置,我覺得那是最早的象徵主義的詩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