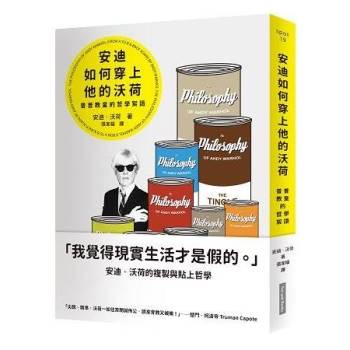1愛(青春期)
在我生命的某個階段,就在五○年代末期,我開始發現身邊朋友所面臨的許多問題,竟然也都跑到了我身上。當時有人無可救藥地愛上有夫之婦,有人向我坦承喜歡同性,而我非常欣賞的一個女人,則是出現嚴重精神分裂的徵兆。在那之前,大概是因為我從未把任何問題給確切定義出來,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有問題;可是在那之後,我卻發現身邊朋友所遇上的疑難雜症,竟然像細菌般一個又一個傳染到我身上來。
我於是決定去看心理醫師(當時我認識好多人都在看心理醫師)。我的想法是—— 如果我真有什麼問題,也應該想辦法先好好定義出來—— 而不是寄生在朋友的問題裡打轉。
我小時候曾歷經三次精神崩潰,每次都間隔一年,分別發生在八歲、九歲和十歲的時候。這三次發病—— 風濕性舞蹈病—— 都是在暑假第一天,年幼的我不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只知道我抱著查理.麥卡錫(Charlie McCarthy)人偶躺在床上,在電台廣播中度過整個夏天。床單上枕頭下,全是還沒剪下來的剪紙人偶。
我爸爸那時候經常到煤礦場出差,所以我很少見到他。我媽則會用濃濃的捷克腔英語,努力讀故事書給我聽,每回她讀完《迪克.崔西》,我總會說「媽媽謝謝」,可是其實她念的內容,我一個字也沒聽懂。我還記得我有一本著色簿,每畫完一頁,我媽就會給我一條賀喜(Hershey’s)巧克力。
回想高中時期,我真的只記得那時候住在賓州的麥基斯港(McKeesport),每天上學都得走上好長一段路,途中還會經過捷克貧民窟,那些老祖母在沿路的曬衣繩上,掛著一件又一件的連身工作服 。我在學校雖然並不特別受人歡迎,但身邊還是有幾個好朋友。那時候我沒什麼好朋友,但我並不想這樣,每次看到其他同學互相傾訴心聲,總會覺得自己好像被冷落了。我想,大概就是因為我不是那種別人會想要談心的類型,所以總是沒人找我傾訴。那時候我和同學們每天都會經過一座橋,橋下全是用過的保險套。我說出心裡的疑惑,問大家橋些那些是什麼東西,同學就只是笑。某年夏天,我在百貨公司找了份工作,替一位叫沃莫(Vollmer)的先生讀《時尚》(Vogue)和《哈潑時尚》(Harper’s Bazaar) ,以及其他來自歐洲的時尚雜誌,幫忙尋找「靈感」。他當時每小時雖然付我五十分錢,但我卻不記得曾經替他找到過什麼新想法。我因為沃莫是紐約人而相當崇拜他,對當時的我來說,來自紐約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但我當時倒也沒有因此想要去紐約闖闖的念頭就是了。
十八歲那年,我朋友把我裝進克羅格超市(Kroger)的購物袋,拎著我上紐約。那時候我還是希望可以和人親近一點,一心想著要和室友當好朋友,彼此互相傾訴心聲,但最後卻總是發現他們不想要朋友,只想多找個人分攤租金。有一陣子我和十七個人分租公寓,住在曼哈頓大道和一○三街路口的地下室,但十七個人裡,竟然沒有一個人願意和我分享生活困境。這十七個也全都是搞創意的小孩,所以我們的公寓多少也有點像藝術公社,照理說搞藝術的人問題應該不少才對,但卻從來沒有人找我傾訴。不過老實講,我那時候的工時很長,所以就算有人願意對我訴說,我搞不好也沒時間聽。無論如何,我還是因為沒有談心朋友,覺得自己孤零零的,有點受傷。
當時我白天四處找工作,晚上則是回家畫圖,畫賀卡、畫水彩,偶爾再到咖啡館看詩歌朗誦,這就是我五○年代的生活。
當時除了漫漫無盡的工時以外,那段日子裡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蟑螂。我前前後後在紐約住了不少間公寓,但每一間蟑螂都好多。有一次我到《哈潑時尚》找當時的主編凱美爾.史諾(Carmel Snow)面試,結果一拉開作品集的拉鍊,裡頭就爬出一隻蟑螂,沿著桌腳窸窣而去。當下的那種羞恥感,我還真是永遠也忘不了。史諾應該是看我好可憐,也就答應僱用我。我有過好多室友。現在我在紐約要是晚上出門約會,都還是會撞見老室友,而這些老室友看見我的約會對象,自我介紹起來也總是那一句:「我是安迪以前的室友。」我臉色頓時發白──當然我已經夠白了。等到一而再再而三在路上遇見老室友,我的那些約會對象也就開始納悶,明明我在他們心中就是個獨行俠,怎麼可能和這麼多人同居過?當然,現在很多人都覺得我就是六○年代的派對常客,一登場少說就有六個「隨扈」在側,到底我怎麼敢宣稱自己是「獨行俠」?—— 且讓我來稍作解釋:我的人生當中有幾段日子是我覺得最合群也最想結交摯友的時期,只可惜不能如願,所以即使我當時看上去總是獨來獨往,說穿了我其實非常想要有朋友在身邊。直到某一天,我心想算了,不如一個人就好,反正別人的心聲也沒什麼好聽的,結果這麼一想,反而許許多多我根本見也沒見過的人,全都找上門來,開始對我傾訴我已經打定主意不去聽的事情。總而言之,我一下定決心開始孤獨的那一刻,我身邊也多了一群各位口中的「追隨者」。
不管是什麼東西,哪天你不要它了,那東西就會自己找上門。我發現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總之我開始覺得自己被朋友的問題傳染,所以我就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找了個心理醫師,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訴他。我講了我這一生以來的大小事情,也告訴他我原本其實什麼毛病也沒有,但現在卻開始染上朋友的問題。他聽完只告訴我會再透過電話約診,到時候再進一步聊聊,可是後來我始終沒有接到那通電話。現在回想,那傢伙明明說要打給我卻沒打,真不專業。那天看完心理醫師之後,我在路上經過梅西百貨(Macy’s)順便逛了一下,殊不知等我走出來時,已經買了我人生第一台電視機。我把這台美國無線電公司(R C A)生產的十九吋黑白電視帶回當時位於東七十五街、恰好在高架地鐵底下的獨居公寓,心裡早就已經把心理醫師忘得一乾二淨。那台電視我從來不關,尤其是朋友打來談心的時候更是不關,因為電視讓我分心的程度,恰好能讓我不再被朋友的苦水與問題所影響。真是像魔法一樣呢。我當時租的公寓就在雪莉女郎酒吧(Shirley’s Pin-Up Bar)的樓上,當時一位叫作美寶.梅爾瑟(Mabel Mercer)的卡巴來(cabaret)爵士樂歌手常光顧這間店,有時還會上台演唱 〈你真可愛〉(You’re So Adorable)。買了電視之後,我的居住安排也起了全新變化。我住的那棟大樓是五層樓高的樓梯公寓,我原本租的是五樓,後來看二樓空了出來,也就一併租了下來,所以現在我家雖然有兩層樓,只是並不連在一起。自從買了電視之後,我就比較常待在有電視的那層樓了。
我決定當獨行俠之後的那些年,我的名聲越來越廣,朋友也越來越多。工作上我表現得還不錯,不只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底下還有幾個幫手,後來幾經輾轉, 這些人也就直接在我的工作室裡住下了。那陣子一切都鬆鬆散散的,很有彈性,工作室裡白天晚上都有人,朋友來看我的時候也帶著朋友一起來。工作室裡的留聲機總是放著歌劇女高音瑪麗亞.卡拉絲(Maria Callas)的曲子;房子裡好多鏡子,好多錫箔。
那時候我的普普藝術宣言已經開始, 所以工作很忙,還有很多畫布要繃,每天從早上十點一路忙到晚上十點,回家睡一覺,隔天再回工作室。結果每每早上一進門,前一晚的人都還在,而且精神還很好,一直與瑪麗亞和鏡子同在。
我正是在這個時期開始意識到一個人能有多瘋狂。比如,竟然有個年輕女孩就在工作室的電梯裡住了下來,一整個禮拜說什麼也不願意離開,直到大家拒絕再送可樂給她喝為止。我其實也搞不清楚這件事究竟代表了什麼,但既然工作室的租金是我付的,我想怎麼說這都算是我的事了,只是別問我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啊永遠也搞不清楚。
我的工作室位於第四十七街和第三大道上,地點相當好,總是可以看見前往聯合國總部抗議的人群。教宗當時也曾途經四十七街,往聖派翠克大教堂前進;赫魯雪夫(Khrushchev)訪美,也是打這裡經過。那是一條良好又寬敞的街道。這個時期,工作室已經開始有各界名人來訪,想窺探這裡夜以繼日的派對,像是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彼得.方達(Peter Fonda)與丹尼斯.霍柏(Dennis Hopper)、巴尼特.紐曼(Barnett Newman)、茱蒂.嘉蘭(Judy Garland)、滾石樂團(the Rolling Stones)等等。另外地下絲絨(Velvet Underground)也開始在我工作室的某個角落練團,不久之後,我們就辦了一場跨媒材路演,還在一九六三年全國巡迴展出。感覺上,後來的一切似乎都在當時萌芽。反文化、次文化、普普運動、超級巨星、藥物、燈光、迪斯可──所有我們認為「年輕、入時」的事物,似乎都在當時萌芽。無論何時何地都有派對正在進行:要是在地下室找不到,那麼派對就一定是在屋頂上;要是地鐵裡沒有派對,那麼一定會有一個在巴士上;要是船上看不見,那麼派對就一定是辦在自由女神像裡。當時人們無時無刻不為出席派對而盛裝打扮。那時候整個下東城才正要褪去移民色彩,脫胎換骨成為潮流勝地,地下絲絨當時常在史丹利的家(Stanley’s the Dom)演出的歌曲也叫作〈為所有明日的派對〉(All Tomorrow’s Parties)—— 「明天派對這麼多,窮女孩該穿什麼才好呢⋯⋯」這曲子是妮可(Nico)唱的,由地下絲絨伴奏,我好喜歡。
那些時日,所有東西都是奢華的,要是沒錢,根本負擔不起像帕拉佛納妮亞(Paraphernalia)等精品店,或是像泰格.摩斯(Tiger Morse)那樣的設計師所設計的服飾。泰格的衣服其實都是她自己從S・克萊(S. Klein)百貨和梅西百貨買回來的兩塊錢洋裝改造而成。衣服買來後,她會先把上頭的緞帶和花飾拆掉,再拿到自己店裡賣,這一賣標價就成了四百元。泰格對飾品也很有一套,隨便從沃爾沃斯百貨(Woolworth’s)買個什麼東西,上頭再畫點碎花樣式,就能賣上五十塊錢。她總能分辨店裡的客人誰會真的掏出錢包,誰又只是隨便看看,而且出奇地準。我就曾經目睹她盯著一位穿得好看、長得也美的女士,結果一秒不到,她就和對方說:「真抱歉,店裡恐怕沒有適合你的東西呢。」她總是能一眼看穿客人。此外,只要是閃著光發著亮的東西她都買──第一位在衣服上放電池、發明電光裙子的人,就是泰格。
六○年代那時,所有人都對彼此充滿興趣,當然其中藥物也扮演了一定角色,無論是初登社交場合的上流名媛或是車夫、不管是女侍還是官人,所有人在忽然之間都眾生平等了。我有一個來自紐澤西州的朋友叫英格麗德,初踏入所謂的表演事業的她就給自己改了姓。她稱自己為英格麗德.超級巨星(Ingrid Superstar),我相當確定巨星這個詞就是她發明的,至少我常跟人說,誰要是能在英格麗德出名以前的報紙上找到「超級巨星」這個字,歡迎剪下來給我看。那時候,我們兩個參加的派對越多,她的巨星名號就越常見報,不出多久,「超級巨星」這個詞就開始在媒體上流行。我幾個禮拜前還接到英格麗德的電話,她現在在做縫紉活,但「超級巨星」這名字卻仍然是進行式,是不是相當了不起?
六○年代的時候,所有人都對彼此充滿興趣。
七○年代的時候,所有人拋棄了彼此。
六○年代是喧囂的。
七○年代是十分虛空。
我第一次買電視之後,便不再執著於與人親近。當時的我已經受到太多傷害,是只有在你太在乎的時候,才會受到傷害的那種程度。我想我當初的確是把人際關係看得太重了,在那段還沒有人聽過「普普藝術」、「地下電影」或者「巨星」的年代,我讓自己太過在乎。
就那樣在五○年代末期,我和我的電視陷入熱戀,而且這段感情一直持續到今天,直到現在我的臥房裡一次都還可以同時擺上多達四部電視機。然而我和電視只是熱戀而已,若是要說論及婚嫁的對象,還要到一九六四年才真正有譜。那一年,我買了人生第一台錄音機。我的老婆──或說我的錄音機──和我至今已經攜手走過十個年頭。很多人都不懂我平常說「我們」的時候,其實講的就是我和我那台錄音機。
買了錄音機以後,我所剩的感情生活也都跟著結束,但我其實樂見這樣的發展。因為自此之後,對我而言什麼事都不成問題了—— 因為任何問題都可以錄下來,而問題只要一錄下來,就不再是問題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一個有趣的錄音。這個大家都知道,並且願意為了錄音而表演。到最後哪些人講的問題是真的,哪些人又只是為了錄音而誇大其辭,你都分辨不出了。更棒的是,他們真的出了問題、或者只是在演戲,就連當事人都傻傻分不清了。
我想,在六○年代的時候,人們都忘記了感情應有的樣子,而且我不認為自此之後他們可以想得起來。我想,人一旦從某個特定角度看過感情的樣子,你就再也不可能覺得感情是真的。這大概就是我所經歷的轉變。
我其實也不曉得自己能不能愛,但六○年代過去之後, 我再也不去想「愛」了 。
然而,我卻開始對某些人著迷。六○年代的時候,有一個人比所有人都更讓我著迷,而我所經歷的那種著迷,也許和某種類型的愛,確實非常相似。
在我生命的某個階段,就在五○年代末期,我開始發現身邊朋友所面臨的許多問題,竟然也都跑到了我身上。當時有人無可救藥地愛上有夫之婦,有人向我坦承喜歡同性,而我非常欣賞的一個女人,則是出現嚴重精神分裂的徵兆。在那之前,大概是因為我從未把任何問題給確切定義出來,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有問題;可是在那之後,我卻發現身邊朋友所遇上的疑難雜症,竟然像細菌般一個又一個傳染到我身上來。
我於是決定去看心理醫師(當時我認識好多人都在看心理醫師)。我的想法是—— 如果我真有什麼問題,也應該想辦法先好好定義出來—— 而不是寄生在朋友的問題裡打轉。
我小時候曾歷經三次精神崩潰,每次都間隔一年,分別發生在八歲、九歲和十歲的時候。這三次發病—— 風濕性舞蹈病—— 都是在暑假第一天,年幼的我不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只知道我抱著查理.麥卡錫(Charlie McCarthy)人偶躺在床上,在電台廣播中度過整個夏天。床單上枕頭下,全是還沒剪下來的剪紙人偶。
我爸爸那時候經常到煤礦場出差,所以我很少見到他。我媽則會用濃濃的捷克腔英語,努力讀故事書給我聽,每回她讀完《迪克.崔西》,我總會說「媽媽謝謝」,可是其實她念的內容,我一個字也沒聽懂。我還記得我有一本著色簿,每畫完一頁,我媽就會給我一條賀喜(Hershey’s)巧克力。
回想高中時期,我真的只記得那時候住在賓州的麥基斯港(McKeesport),每天上學都得走上好長一段路,途中還會經過捷克貧民窟,那些老祖母在沿路的曬衣繩上,掛著一件又一件的連身工作服 。我在學校雖然並不特別受人歡迎,但身邊還是有幾個好朋友。那時候我沒什麼好朋友,但我並不想這樣,每次看到其他同學互相傾訴心聲,總會覺得自己好像被冷落了。我想,大概就是因為我不是那種別人會想要談心的類型,所以總是沒人找我傾訴。那時候我和同學們每天都會經過一座橋,橋下全是用過的保險套。我說出心裡的疑惑,問大家橋些那些是什麼東西,同學就只是笑。某年夏天,我在百貨公司找了份工作,替一位叫沃莫(Vollmer)的先生讀《時尚》(Vogue)和《哈潑時尚》(Harper’s Bazaar) ,以及其他來自歐洲的時尚雜誌,幫忙尋找「靈感」。他當時每小時雖然付我五十分錢,但我卻不記得曾經替他找到過什麼新想法。我因為沃莫是紐約人而相當崇拜他,對當時的我來說,來自紐約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但我當時倒也沒有因此想要去紐約闖闖的念頭就是了。
十八歲那年,我朋友把我裝進克羅格超市(Kroger)的購物袋,拎著我上紐約。那時候我還是希望可以和人親近一點,一心想著要和室友當好朋友,彼此互相傾訴心聲,但最後卻總是發現他們不想要朋友,只想多找個人分攤租金。有一陣子我和十七個人分租公寓,住在曼哈頓大道和一○三街路口的地下室,但十七個人裡,竟然沒有一個人願意和我分享生活困境。這十七個也全都是搞創意的小孩,所以我們的公寓多少也有點像藝術公社,照理說搞藝術的人問題應該不少才對,但卻從來沒有人找我傾訴。不過老實講,我那時候的工時很長,所以就算有人願意對我訴說,我搞不好也沒時間聽。無論如何,我還是因為沒有談心朋友,覺得自己孤零零的,有點受傷。
當時我白天四處找工作,晚上則是回家畫圖,畫賀卡、畫水彩,偶爾再到咖啡館看詩歌朗誦,這就是我五○年代的生活。
當時除了漫漫無盡的工時以外,那段日子裡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蟑螂。我前前後後在紐約住了不少間公寓,但每一間蟑螂都好多。有一次我到《哈潑時尚》找當時的主編凱美爾.史諾(Carmel Snow)面試,結果一拉開作品集的拉鍊,裡頭就爬出一隻蟑螂,沿著桌腳窸窣而去。當下的那種羞恥感,我還真是永遠也忘不了。史諾應該是看我好可憐,也就答應僱用我。我有過好多室友。現在我在紐約要是晚上出門約會,都還是會撞見老室友,而這些老室友看見我的約會對象,自我介紹起來也總是那一句:「我是安迪以前的室友。」我臉色頓時發白──當然我已經夠白了。等到一而再再而三在路上遇見老室友,我的那些約會對象也就開始納悶,明明我在他們心中就是個獨行俠,怎麼可能和這麼多人同居過?當然,現在很多人都覺得我就是六○年代的派對常客,一登場少說就有六個「隨扈」在側,到底我怎麼敢宣稱自己是「獨行俠」?—— 且讓我來稍作解釋:我的人生當中有幾段日子是我覺得最合群也最想結交摯友的時期,只可惜不能如願,所以即使我當時看上去總是獨來獨往,說穿了我其實非常想要有朋友在身邊。直到某一天,我心想算了,不如一個人就好,反正別人的心聲也沒什麼好聽的,結果這麼一想,反而許許多多我根本見也沒見過的人,全都找上門來,開始對我傾訴我已經打定主意不去聽的事情。總而言之,我一下定決心開始孤獨的那一刻,我身邊也多了一群各位口中的「追隨者」。
不管是什麼東西,哪天你不要它了,那東西就會自己找上門。我發現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總之我開始覺得自己被朋友的問題傳染,所以我就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找了個心理醫師,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訴他。我講了我這一生以來的大小事情,也告訴他我原本其實什麼毛病也沒有,但現在卻開始染上朋友的問題。他聽完只告訴我會再透過電話約診,到時候再進一步聊聊,可是後來我始終沒有接到那通電話。現在回想,那傢伙明明說要打給我卻沒打,真不專業。那天看完心理醫師之後,我在路上經過梅西百貨(Macy’s)順便逛了一下,殊不知等我走出來時,已經買了我人生第一台電視機。我把這台美國無線電公司(R C A)生產的十九吋黑白電視帶回當時位於東七十五街、恰好在高架地鐵底下的獨居公寓,心裡早就已經把心理醫師忘得一乾二淨。那台電視我從來不關,尤其是朋友打來談心的時候更是不關,因為電視讓我分心的程度,恰好能讓我不再被朋友的苦水與問題所影響。真是像魔法一樣呢。我當時租的公寓就在雪莉女郎酒吧(Shirley’s Pin-Up Bar)的樓上,當時一位叫作美寶.梅爾瑟(Mabel Mercer)的卡巴來(cabaret)爵士樂歌手常光顧這間店,有時還會上台演唱 〈你真可愛〉(You’re So Adorable)。買了電視之後,我的居住安排也起了全新變化。我住的那棟大樓是五層樓高的樓梯公寓,我原本租的是五樓,後來看二樓空了出來,也就一併租了下來,所以現在我家雖然有兩層樓,只是並不連在一起。自從買了電視之後,我就比較常待在有電視的那層樓了。
我決定當獨行俠之後的那些年,我的名聲越來越廣,朋友也越來越多。工作上我表現得還不錯,不只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底下還有幾個幫手,後來幾經輾轉, 這些人也就直接在我的工作室裡住下了。那陣子一切都鬆鬆散散的,很有彈性,工作室裡白天晚上都有人,朋友來看我的時候也帶著朋友一起來。工作室裡的留聲機總是放著歌劇女高音瑪麗亞.卡拉絲(Maria Callas)的曲子;房子裡好多鏡子,好多錫箔。
那時候我的普普藝術宣言已經開始, 所以工作很忙,還有很多畫布要繃,每天從早上十點一路忙到晚上十點,回家睡一覺,隔天再回工作室。結果每每早上一進門,前一晚的人都還在,而且精神還很好,一直與瑪麗亞和鏡子同在。
我正是在這個時期開始意識到一個人能有多瘋狂。比如,竟然有個年輕女孩就在工作室的電梯裡住了下來,一整個禮拜說什麼也不願意離開,直到大家拒絕再送可樂給她喝為止。我其實也搞不清楚這件事究竟代表了什麼,但既然工作室的租金是我付的,我想怎麼說這都算是我的事了,只是別問我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啊永遠也搞不清楚。
我的工作室位於第四十七街和第三大道上,地點相當好,總是可以看見前往聯合國總部抗議的人群。教宗當時也曾途經四十七街,往聖派翠克大教堂前進;赫魯雪夫(Khrushchev)訪美,也是打這裡經過。那是一條良好又寬敞的街道。這個時期,工作室已經開始有各界名人來訪,想窺探這裡夜以繼日的派對,像是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彼得.方達(Peter Fonda)與丹尼斯.霍柏(Dennis Hopper)、巴尼特.紐曼(Barnett Newman)、茱蒂.嘉蘭(Judy Garland)、滾石樂團(the Rolling Stones)等等。另外地下絲絨(Velvet Underground)也開始在我工作室的某個角落練團,不久之後,我們就辦了一場跨媒材路演,還在一九六三年全國巡迴展出。感覺上,後來的一切似乎都在當時萌芽。反文化、次文化、普普運動、超級巨星、藥物、燈光、迪斯可──所有我們認為「年輕、入時」的事物,似乎都在當時萌芽。無論何時何地都有派對正在進行:要是在地下室找不到,那麼派對就一定是在屋頂上;要是地鐵裡沒有派對,那麼一定會有一個在巴士上;要是船上看不見,那麼派對就一定是辦在自由女神像裡。當時人們無時無刻不為出席派對而盛裝打扮。那時候整個下東城才正要褪去移民色彩,脫胎換骨成為潮流勝地,地下絲絨當時常在史丹利的家(Stanley’s the Dom)演出的歌曲也叫作〈為所有明日的派對〉(All Tomorrow’s Parties)—— 「明天派對這麼多,窮女孩該穿什麼才好呢⋯⋯」這曲子是妮可(Nico)唱的,由地下絲絨伴奏,我好喜歡。
那些時日,所有東西都是奢華的,要是沒錢,根本負擔不起像帕拉佛納妮亞(Paraphernalia)等精品店,或是像泰格.摩斯(Tiger Morse)那樣的設計師所設計的服飾。泰格的衣服其實都是她自己從S・克萊(S. Klein)百貨和梅西百貨買回來的兩塊錢洋裝改造而成。衣服買來後,她會先把上頭的緞帶和花飾拆掉,再拿到自己店裡賣,這一賣標價就成了四百元。泰格對飾品也很有一套,隨便從沃爾沃斯百貨(Woolworth’s)買個什麼東西,上頭再畫點碎花樣式,就能賣上五十塊錢。她總能分辨店裡的客人誰會真的掏出錢包,誰又只是隨便看看,而且出奇地準。我就曾經目睹她盯著一位穿得好看、長得也美的女士,結果一秒不到,她就和對方說:「真抱歉,店裡恐怕沒有適合你的東西呢。」她總是能一眼看穿客人。此外,只要是閃著光發著亮的東西她都買──第一位在衣服上放電池、發明電光裙子的人,就是泰格。
六○年代那時,所有人都對彼此充滿興趣,當然其中藥物也扮演了一定角色,無論是初登社交場合的上流名媛或是車夫、不管是女侍還是官人,所有人在忽然之間都眾生平等了。我有一個來自紐澤西州的朋友叫英格麗德,初踏入所謂的表演事業的她就給自己改了姓。她稱自己為英格麗德.超級巨星(Ingrid Superstar),我相當確定巨星這個詞就是她發明的,至少我常跟人說,誰要是能在英格麗德出名以前的報紙上找到「超級巨星」這個字,歡迎剪下來給我看。那時候,我們兩個參加的派對越多,她的巨星名號就越常見報,不出多久,「超級巨星」這個詞就開始在媒體上流行。我幾個禮拜前還接到英格麗德的電話,她現在在做縫紉活,但「超級巨星」這名字卻仍然是進行式,是不是相當了不起?
六○年代的時候,所有人都對彼此充滿興趣。
七○年代的時候,所有人拋棄了彼此。
六○年代是喧囂的。
七○年代是十分虛空。
我第一次買電視之後,便不再執著於與人親近。當時的我已經受到太多傷害,是只有在你太在乎的時候,才會受到傷害的那種程度。我想我當初的確是把人際關係看得太重了,在那段還沒有人聽過「普普藝術」、「地下電影」或者「巨星」的年代,我讓自己太過在乎。
就那樣在五○年代末期,我和我的電視陷入熱戀,而且這段感情一直持續到今天,直到現在我的臥房裡一次都還可以同時擺上多達四部電視機。然而我和電視只是熱戀而已,若是要說論及婚嫁的對象,還要到一九六四年才真正有譜。那一年,我買了人生第一台錄音機。我的老婆──或說我的錄音機──和我至今已經攜手走過十個年頭。很多人都不懂我平常說「我們」的時候,其實講的就是我和我那台錄音機。
買了錄音機以後,我所剩的感情生活也都跟著結束,但我其實樂見這樣的發展。因為自此之後,對我而言什麼事都不成問題了—— 因為任何問題都可以錄下來,而問題只要一錄下來,就不再是問題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一個有趣的錄音。這個大家都知道,並且願意為了錄音而表演。到最後哪些人講的問題是真的,哪些人又只是為了錄音而誇大其辭,你都分辨不出了。更棒的是,他們真的出了問題、或者只是在演戲,就連當事人都傻傻分不清了。
我想,在六○年代的時候,人們都忘記了感情應有的樣子,而且我不認為自此之後他們可以想得起來。我想,人一旦從某個特定角度看過感情的樣子,你就再也不可能覺得感情是真的。這大概就是我所經歷的轉變。
我其實也不曉得自己能不能愛,但六○年代過去之後, 我再也不去想「愛」了 。
然而,我卻開始對某些人著迷。六○年代的時候,有一個人比所有人都更讓我著迷,而我所經歷的那種著迷,也許和某種類型的愛,確實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