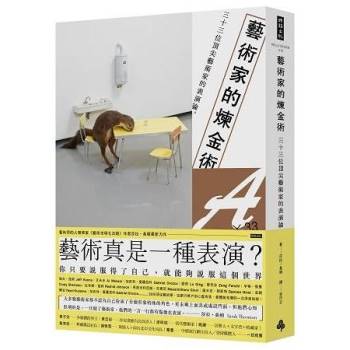SCENE 1 場景 1
Jeff Koons 傑夫‧昆斯
二〇〇九年七月一個燠熱的傍晚,倫敦維多利亞‧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 Albert Museum)的大禮堂內擠滿了人。台下的觀眾恰可均分為兩類;一類是穿著諷世T恤的藝術系學生,一類是穿著休閒鞋的退休人士。傑夫‧昆斯(Jeff Koons)走上講台時,他們都報以熱烈掌聲。昆斯的鬍鬚剃得乾乾淨淨,膚色曬得黝黑而有精神。他穿著黑色的古馳(Gucci)名牌西裝,一排釦子都扣得好好的,西裝裡面是白色襯衫、打著深色領帶。二十年前,當藝術家都穿著牛仔褲和皮夾克時,昆斯就打破紐約藝術界這項不成文的規定,出入都穿著剪裁入時的訂製西裝。藝術家沒有制服,但是當時大家心中都有默契:不要看起來像生意人。
昆斯對著球形麥克風說:「能夠出席這項盛會,真是莫大的榮譽。去年我在凡爾賽宮有展覽,接著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柏林的新國家美術館(Neue Nationalgalerie)、芝加哥當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Chicago)等地也有展出。」藝術家在談話中秀一點風光的履歷、列舉最近的生涯高峰,是常有的事。「在這些地方展過之後,來到英國蛇形藝廊(Serpentine Gallery)辦展,再理想不過。這是個非常令人興奮的經驗,我非常感激。」他的口氣像個搖滾樂明星,在每一場次的演出地點都有一番美麗的說詞,讓人聽起來非常受用。(註:昆斯的《卜派》(Popeye)系列當時在蛇形藝廊展出,因展場沒有演講廳,於是借用維多利亞‧亞伯特博物館的大禮堂舉辦活動。)
昆斯幻燈秀的開場白是:「我想我從自己的繪畫歷程開始談起。」他最先放的是二〇〇二年的作品《海豚》(Dolphin)。出現在大銀幕上的《海豚》是一尊雕塑作品,一個看起來有點像在游泳池裡的充氣玩具、用黃色的金屬鏈條吊起來的海豚,它的下方還有一個掛滿不鏽鋼鍋與鋼盆的鐵架。《海豚》的原件是塑膠雕塑,但此刻出現在觀眾眼前的是一個精工打造、色澤勻稱的鋁製翻版,吊掛用的鐵鍊和下方的廚房用具全是「現成貨」,換句話說,全是在商店裡買來的由工廠生產的大眾化商品,再被融入藝術作品之中。他提到自己於一九五五年出生在美國賓州,並指向現場後方,向觀眾介紹他的母親葛洛莉亞(Gloria)。昆斯的許多藝術活動葛洛莉亞都會出席。幾分鐘後,他形容《海豚》是「母性的維納斯」、它的兩片魚鰭就像「兩個小奶頭」。昆斯演講中沒有使用任何紙頭小抄。他告訴大家他的父親是一名室內裝潢師,開了一家家具店,因此他在成長過程中自然就培養出「美感」。小時候就懂得金色和青色給人的感覺「不同於」棕色或黑色。他姐姐凱倫(Karen)各方面都比他優秀,直到有一天昆斯畫了一張畫,讓父母刮目相看,他們從畫中看到兒子有點天分。他對大家解釋說,「父母的誇獎讓我有了某種自覺」。常有人說藝術家除了從事藝術創作外,做什麼都不行,昆斯話中的弦外之音是:藝術是他唯一能夠競爭的領域。
昆斯又舉了其他幾個令他頓悟與開竅的例子:進了藝術學校後不久,他跟全班同學前往巴爾的摩美術館(Baltimore Museum of Art)參觀。展出的畫家大多數他都不熟悉,「我覺察到自己對藝術一無所知,但是那一刻並沒有讓我滅頂。」他想創作的是「不需要先決條件的藝術」;他絕不要讓人在藝術前感覺渺小,「我要觀者感覺我們的文化背景完全沒有問題!」他滿面含笑地對大家說,然後談起他於一九八八年開始創作的第七系列《平庸》(Banality,亦有譯作《媚俗》)。這一系列作品是以泰迪熊、頑皮豹、農場動物和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為造型的彩繪木雕或磁雕,透過這些作品,普普藝術走進了美國都市郊區的住家,融入家居甜膩裝飾的領域。這些迎合大眾口味的人物與動物造型都各有三套,以便同時在紐約、芝加哥和德國科隆作完全一樣的展出。隨著《平庸》系列的推出,昆斯也以另外一種方式悖離了藝術世界的傳統。為這一系列作宣傳時,他在廣告中「現身說法」,有效的建立了他的公共人物的風貌。他在次文化上樹立了惡名,但也讓他名聲大噪,終而名利雙收。他針對美國和全球性的最重要的當代藝術雜誌,製作了四種不同的廣告:對最具學術地位的《藝術論壇》(Artforum),他為自己打造的形象是小學老師,在他身後黑板上寫著的口號是:「剝削大眾」、「平庸媚俗是救主」;為《美國藝術》(Art in America),他擺出略顯疲憊的性感偶像的架勢,夾在兩個穿著比基尼泳裝的豐滿女郎中間;為《藝術消息》(ARTnews),他的形象是穿著浴袍的花花公子,四週有花環環繞,春風得意;在為義大利雜誌《閃亮藝術》(Flash Art)裡,他不惜自貶身份,抱起一隻大母豬和小豬。昆斯這樣不避嫌自我宣傳,行徑大膽,卻非史無前例。這樣的廣告手法讓人想起「一般觀念」(General Idea)當年是如何打知名度的。「一般觀念」是一個同性戀當代藝術三人小組,他們曾三人同床,在被子外露出三張乾淨的面孔。他們三人也拍攝過黑眼圈的小狗像。一般人都認為,藝術家是誠實的典範、廣告是天花亂墜集大成,因此,「一般觀念」和昆斯都是向這項觀念挑戰、做出新的詮釋;他們質疑藝術世界的既定立場——藝術作品比藝術家重要,並厚顏自我行銷,看看這樣做會不會殺傷信譽。大禮堂太熱了,觀眾都拿起報紙、筆記本甚至夾腳拖來搧涼。而昆斯卻連領帶也不鬆;不但沒有汗流浹背,反而是臉上發光,又按了一張幻燈片。這一張是他和有「小白菜」之稱的義大利脫星伊羅娜‧史特拉(Ilona Staller,亦有譯為「史脫樂」者)的裸體合照。昆斯曾與後來當上義大利國會議員的史特拉有過一段露水姻緣。一九八九年昆斯有一項作品叫《影像世界:藝術與媒體文化》(Image World: Art and Media Culture)在紐約惠特尼美國藝術館(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展出。這個作品原本是紐約麥迪森廣告街(Madison Avenue)上的一幅廣告看板,為一部昆斯與小白菜合拍的杜撰性電影《天堂製造》(Made in Heaven)宣傳。這也是昆斯《天堂製造》系列的第一幅作品,接下來還有一九九一年的雕塑《淫穢—昆斯在上》(Dirty—Jeff on Top ,一九九一年)與繪畫《小白菜的私處》(Ilona’s Asshole,一九九一年);藝術家的情婦充當畫家的裸體模特兒不是新聞,但是畫家騎在太太身上倒是前所未聞。他後來告訴我說:「要當電影明星的捷徑是拍一部色情電影;在我腦子裡,這就是參與美國通俗文化。」
昆斯播放一張張《天堂製造》幻燈片之際,並未討論它們的暴露或是猜測這些作品對他的藝術事業有什麼影響,他反而回到他最鍾愛的一項話題——接納。他說:「我的前妻曾經從事色情電影,但是她這個人絕對完美,這是一個完美的超越平台。」他一邊說,食指一邊滑過嘴唇:「我想嘗試溝通的是:擁抱肉慾、不帶罪惡和羞恥感,是多麼重要。」昆斯接著講到《卜派》系列。他從二〇〇二年開始從事這一系列的創作,在蛇形藝廊首次亮相,而這次演講就是為了配合展出而舉辦。他視《卜派》系列為家庭性質——對家庭而言,它「更親切」。這一系列作品無論是雕塑或是繪畫,特色都是它們看起來像充氣玩具。昆斯小時候,父母曾經給他買了一塊浮板,幫助他學游泳。他深愛浮板的「解放效果」,這種可以當作救生圈來戴的漂浮器帶給他一種「平衡的感覺」。對昆斯來說,它們也像「人」一樣。他幾乎是帶著宗教性的熱忱說:「我們也是充氣的器物;吸氣,有氣象徵著樂觀;吐氣,就是死亡的象徵。」他還從情色的角度就充血現象有所發揮,觀眾聽的有點坐立不安。他說:「網路上有一大堆性物戀的東西都可以拿來當游泳池玩具了。」他還開玩笑的說,「因為洩氣變軟」,就不免有幾分悲劇色彩了。
系列作品中的每一項藝術創作,昆斯都一一解釋說到他會聯想到的人、史、事、物。基本上聯想分作兩大類:一是指涉藝術史談到的、現代畫壇上的重要藝術家,一是影射性器官與各種交合姿態。例如他說,這些畫家都是響噹噹的人物,在座的觀眾都耳熟能詳,他謙虛地先作聲明表示,不希望聽眾看完所有關於他的介紹後就昏頭轉向,然後指出他的作品與賽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馬塞爾‧杜象(Marcel Duchamp)、法蘭西斯‧畢卡比亞(Francis Picabia)、胡安‧米羅(Joan Miró)、亞歷山大‧考爾德(Alexander Calder)、羅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唐諾‧賈德(Donald Judd)、羅伯特‧羅森柏格(Robert Rauschenberg)、羅伊‧李奇登斯坦(Roy Lichtenstein)、詹姆斯•羅森奎斯特(James Rosenquist)與安迪沃荷(Andy Warhol)的作品之間的關係。昆斯特別提到吉姆‧納特(Jim Nutt)和艾德‧帕斯克(Ed Paschke)。他曾經在芝加哥藝術學院(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受教於這兩位藝術家,「帕斯克會帶我到刺青店和脫衣舞夜店,讓我接觸他的創作靈感來源。」細數與藝術大師關聯的同時,昆斯還一邊加上佛洛伊德式的詮釋,而且講得十分詳細。他最喜歡的形容詞是「陰柔」、「陽剛」、「硬」、「軟」、「濕」、「乾」等等。一件作品若有兩版時,他會說作品有「兩個姿勢」;他的雕塑和繪畫讓他想起「陰唇」、「交合」、「雙腿張開」、「閹割」、「孔」、「子宮」、「骨盤」;更不用說許多充氣藝術品是可以「穿入的」。奇特的是,昆斯用一種理所當然的語氣訴說著這一切,他的臉上一派純真,看起來一點也不會給人猥褻的感覺。
昆斯的神情自若,談吐有條不紊,讓人有一種錯覺,感覺說話的人其實是一個飾演昆斯的演員。而他照本宣科、缺乏即興,也真讓人覺得他是在照劇本演戲,少了那種即興自然和誠實坦率的感覺。這一套其實安迪沃荷最會。他在公開場合談話時刻意營造出一種空洞、言之無物的形象,說話時語調總是冷冷的,充滿了警語,喜歡製造一種沒有一個「真」安迪沃荷的印象。他在《安迪沃荷的普普人生》(The Philosophy of Andy Warhol)說:「我相信自己如果看鏡子什麼也看不見。人常叫我做鏡子,如果鏡子目視鏡子,在哪裡會看到什麼?」能把沃荷式的角色矛盾理論操弄得如此出神入化,除了昆斯以外,還真沒幾個。
昆斯再對著銀幕按了按遙控器,銀幕上出現的是這次說明會的最後一張幻燈片《吊鉤》(Sling Hook,二〇〇七—〇九年)。它是一個充氣海豚和龍蝦的鋁製雕塑,被鐵鍊倒掛——表示它們不是已被宰殺,就是有一種被綁在一起的和樂。昆斯以一種極其平穩的語氣,幾乎是舒緩人心的聲音說:「在我的想像中,我一直都認為到了生命那最後的一刻,一切都變得很清楚;焦慮除去了,看見了新天地。」昆斯經常提到行為的焦慮,有時他似乎是針對藝術成就而言,有時好像又是針對性功能。他說:「接納,焦慮便除去;一切皆無不可、一切都有戲唱。我對藝術的整體了解都在於接納。」SCENE 2 場景2
Ai Weiwei 艾未未
艾未未是個拒絕接受現狀的人。在昆斯演說幾週後,艾未未在上海社會科學院裡展現了他根本不把「接納」二字放在眼裡。若要在昆斯與艾未未之間做個比較,前者可用「有禮」、後者可用「粗魯」來形容;前者清楚的把重點放在他的藝術品上,絕口不提政治,後者卻一再把他的作品導引到倫理的脈絡裡。艾未未出生於一九五七年,幾乎跟昆斯一樣大,雖然兩人都深愛杜象、都善於操弄大眾傳播媒體,但他們對權力的反應卻是南轅北轍。
此刻艾未未坐在學術會議的講台上,椅子前面有一張桌子。他穿著一件粉紅色的T恤,蓋住他圓鼓鼓的肚子,外面是一件寬鬆的黑外套和棉質長褲。灰色的鬍鬚為他平添了一股哲人的氣息。在中國留鬍子的人不多,在中國,鬍子可能讓人聯想到孔夫子或是古巴前總統卡斯楚(Fidel Castro)。
召開這場「設計中國」(Designing China)學術討論會的是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教授亞巴斯(Ackbar Abbas),現場的觀眾大約一半是華人,也有幾位歐洲學者和一些美國研究生。亞巴斯在引介艾未未時說:「艾未未創作了許多藝術品。他是北京奧運鳥巢體育館的設計顧問,也在北京附近的『草場地』興建了一處藝術園區。他常在此接待友人,有時也得跟公安碰面。」艾未未自己則照了幾張亞巴斯和觀眾的相片。亞巴斯說:「我不知道今天他會談些什麼,但我希望他會談艾未未。」
艾未未的目光轉向亞巴斯身旁的田霏宇(Philip Tinari)。田霏宇是策展人,也是艾未未今天的翻譯。哈佛大學畢業的田霏宇戴著時髦的粗框眼鏡,手指頭放在蘋果電腦的鍵盤上,艾未未用中文發表的談話的英文翻譯經由這部電腦傳出去。艾未未用中文說:「大家早。我不準備發表演說,因為我看到『設計中國』的主題,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麼意思。我看你也可以說它是『草泥馬(X你媽)中國。』」聽眾有點不知所措地笑了。艾未未對中國都市計劃缺乏人道關懷的批評,一向不留情面。當他發表意見完畢後,便雙手抱胸,板起身子向後坐,等英文翻譯完。他說:「每次我來上海,我就會想起來為什麼我那麼討厭它。」艾未未住在北京,這番似乎沒有必要的侮辱言辭讓現場氣氛僵住。他說:「上海自認公開、國際化,但事實上上海還是封建心態。」艾未未有七十多個部落格,在部落格中他提到因為寫部落格他的人權被侵犯,又提到汶川大地震時,他是怎樣被四川公安粗暴對待。維權鬥士譚作人被指控煽動顛覆政府權力,一周前艾未未去成都為譚作人審案作證,他說:「開審那天凌晨三點,公安來到我住的旅館,敲開了房間的門。我要求他們給我看他們的警證,卻被暴力對待。」公安拘留了艾未未,不准他在審判中提出證據。他說:「我們的極權政府利用一黨專政方式達成它的目的;中國看可能起來光鮮亮麗,實際上卻是無法無天的黑暗。」
艾未未的頭上有一大道傷痕,是公安對他動粗的結果。挨揍的當下,艾未未並不知道自己已經腦出血,後來還得為此動手術。我不知是不是因為身體上的不舒服加上警察的粗暴,讓他變得更直言無諱。田霏宇經常為艾未未翻譯,對他知之甚深,後來他向我解釋說,住進中國勞改營、拘留感化所之後,艾未未經常心情不好,他說:「除了官府衙門外,艾未未最不喜歡的就是學術界。」
艾未未拿著他的手機念了一段東西,然後抬起頭說:「如果我們要談「設計中國」這個話題,我想我們需要從基本的公平、人權和自由開始。這些基本觀點中國依然欠缺,不管它經濟有多成功。」講了十分鐘後,他突然停了下來,說:「我想現在最好開放來問問題。」喜歡互動的艾未未趨身向前,彷彿要向觀眾挑戰。台下一片寂然,隨即有人小心翼翼地鼓起掌來。
艾未未喜歡驚世駭俗。他最知名的自畫像題目是《失手》(Dropping a Han Dynasty Urn,一九九五年)。作品一共是三幀黑白照片,照片裡,他拿著一尊有兩千年歷史的漢朝古瓶,然後雙手一鬆,把它砸碎了。對珍惜文化瑰寶的人來說,這簡直是匪夷所思,然而,照片裡艾未未雖然面無表情,以此認為他厭棄過去卻是大錯特錯,其實艾未未對在共產黨文化大革命破四舊運動中被掃除的文物,是極為尊敬的,一九九〇年代他也靠買賣古董維生,後來他還建立起一種藝術的新種類,田霏宇稱之為「古代成品」。艾未未將西方商品的商標如可口可樂商標移植到古董器皿上,也找到一些傳統匠人使用古法去做出超現實的多足雕塑。掌聲停止後,亞巴斯站起來,建議大家說:「艾未未將一些我們迴避的話題攤在桌面上,我們不妨直接討論這些話題。」亞巴斯是一位經驗老道的老師,我感覺他好像閉著眼睛都能主持一場成果豐碩的研討會。他接著說:「這裡的事情既不是有法也不是無法,一切都在半法律狀態。」艾未未喝了一些塑膠瓶裡的礦泉水,田霏宇對聽眾說,艾未未也樂意接受英文發問。他是會英文的,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三年之間曾經在紐約住過十二年。
終於第一排有一位年長的美國男士問:「西方人應該在中國做些什麼?」艾未未從喉嚨裡低低地發出一些「嗯」的聲音,然後說:「我對西方民主沒有任何幻覺⋯⋯我的建議是:到處走走、照照相片、吃點好吃的中國菜、然後告訴你的朋友你在中國玩的好極了。」艾未未討厭作假,喜歡開玩笑,是個思想上的自由派。針對下一個問題,他說:「我們在選舉上沒有民主可言,沒有言論自由或媒體自由。如果這些問題你不理會,說了也等於放屁。」一位英文帶着輕微德國口音的女士說:「你的批判是負面、有爭議性的,是那種驚世駭俗、滾一邊去的態度,但是你是位藝術家,能不能談一談您建設性的創作方式?」
艾未未想要迴避,然後很快的跟田霏宇用中文交談了一下,田霏宇替他回答說:「批評和找麻煩,在中國人的情況裡就是一種積極創造的活動。在過程當中是冒著生命危險的。」艾未未舉三人為例——陳光誠、譚作人和劉曉波來說明,這三人不是被拘留,就是遭到軟禁,「任何人認為政治干預是消極的或只是以『去你的』態度來面對,都是錯誤的。⋯⋯我從事過許多建築和博物館計劃,包括上個月剛在東京森美術館(Mori Art Museum)和十月馬上就要落成的慕尼黑美術館(Haus der Kunst)。我參與大型創造,不僅是我們今天所談的事。」
接下來是一名蓄短髮、戴眼鏡的女性發言,她說了一堆恭維和用藝術術語堆砌起來的話之後終於切入正題,詢問艾未未他的「藝術干預」如何提倡社會正義和人權。艾未未一直把雙手插在口袋裡,此刻回答問題也是如此。他說:「闡述、解釋我的作品的人不是我。如果你有興趣,你自己去看一看。我做的每一件作品都跟我最基本的信念有關;如果作品不能表達那個信念,它就不值得做。」
Jeff Koons 傑夫‧昆斯
二〇〇九年七月一個燠熱的傍晚,倫敦維多利亞‧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 Albert Museum)的大禮堂內擠滿了人。台下的觀眾恰可均分為兩類;一類是穿著諷世T恤的藝術系學生,一類是穿著休閒鞋的退休人士。傑夫‧昆斯(Jeff Koons)走上講台時,他們都報以熱烈掌聲。昆斯的鬍鬚剃得乾乾淨淨,膚色曬得黝黑而有精神。他穿著黑色的古馳(Gucci)名牌西裝,一排釦子都扣得好好的,西裝裡面是白色襯衫、打著深色領帶。二十年前,當藝術家都穿著牛仔褲和皮夾克時,昆斯就打破紐約藝術界這項不成文的規定,出入都穿著剪裁入時的訂製西裝。藝術家沒有制服,但是當時大家心中都有默契:不要看起來像生意人。
昆斯對著球形麥克風說:「能夠出席這項盛會,真是莫大的榮譽。去年我在凡爾賽宮有展覽,接著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柏林的新國家美術館(Neue Nationalgalerie)、芝加哥當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Chicago)等地也有展出。」藝術家在談話中秀一點風光的履歷、列舉最近的生涯高峰,是常有的事。「在這些地方展過之後,來到英國蛇形藝廊(Serpentine Gallery)辦展,再理想不過。這是個非常令人興奮的經驗,我非常感激。」他的口氣像個搖滾樂明星,在每一場次的演出地點都有一番美麗的說詞,讓人聽起來非常受用。(註:昆斯的《卜派》(Popeye)系列當時在蛇形藝廊展出,因展場沒有演講廳,於是借用維多利亞‧亞伯特博物館的大禮堂舉辦活動。)
昆斯幻燈秀的開場白是:「我想我從自己的繪畫歷程開始談起。」他最先放的是二〇〇二年的作品《海豚》(Dolphin)。出現在大銀幕上的《海豚》是一尊雕塑作品,一個看起來有點像在游泳池裡的充氣玩具、用黃色的金屬鏈條吊起來的海豚,它的下方還有一個掛滿不鏽鋼鍋與鋼盆的鐵架。《海豚》的原件是塑膠雕塑,但此刻出現在觀眾眼前的是一個精工打造、色澤勻稱的鋁製翻版,吊掛用的鐵鍊和下方的廚房用具全是「現成貨」,換句話說,全是在商店裡買來的由工廠生產的大眾化商品,再被融入藝術作品之中。他提到自己於一九五五年出生在美國賓州,並指向現場後方,向觀眾介紹他的母親葛洛莉亞(Gloria)。昆斯的許多藝術活動葛洛莉亞都會出席。幾分鐘後,他形容《海豚》是「母性的維納斯」、它的兩片魚鰭就像「兩個小奶頭」。昆斯演講中沒有使用任何紙頭小抄。他告訴大家他的父親是一名室內裝潢師,開了一家家具店,因此他在成長過程中自然就培養出「美感」。小時候就懂得金色和青色給人的感覺「不同於」棕色或黑色。他姐姐凱倫(Karen)各方面都比他優秀,直到有一天昆斯畫了一張畫,讓父母刮目相看,他們從畫中看到兒子有點天分。他對大家解釋說,「父母的誇獎讓我有了某種自覺」。常有人說藝術家除了從事藝術創作外,做什麼都不行,昆斯話中的弦外之音是:藝術是他唯一能夠競爭的領域。
昆斯又舉了其他幾個令他頓悟與開竅的例子:進了藝術學校後不久,他跟全班同學前往巴爾的摩美術館(Baltimore Museum of Art)參觀。展出的畫家大多數他都不熟悉,「我覺察到自己對藝術一無所知,但是那一刻並沒有讓我滅頂。」他想創作的是「不需要先決條件的藝術」;他絕不要讓人在藝術前感覺渺小,「我要觀者感覺我們的文化背景完全沒有問題!」他滿面含笑地對大家說,然後談起他於一九八八年開始創作的第七系列《平庸》(Banality,亦有譯作《媚俗》)。這一系列作品是以泰迪熊、頑皮豹、農場動物和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為造型的彩繪木雕或磁雕,透過這些作品,普普藝術走進了美國都市郊區的住家,融入家居甜膩裝飾的領域。這些迎合大眾口味的人物與動物造型都各有三套,以便同時在紐約、芝加哥和德國科隆作完全一樣的展出。隨著《平庸》系列的推出,昆斯也以另外一種方式悖離了藝術世界的傳統。為這一系列作宣傳時,他在廣告中「現身說法」,有效的建立了他的公共人物的風貌。他在次文化上樹立了惡名,但也讓他名聲大噪,終而名利雙收。他針對美國和全球性的最重要的當代藝術雜誌,製作了四種不同的廣告:對最具學術地位的《藝術論壇》(Artforum),他為自己打造的形象是小學老師,在他身後黑板上寫著的口號是:「剝削大眾」、「平庸媚俗是救主」;為《美國藝術》(Art in America),他擺出略顯疲憊的性感偶像的架勢,夾在兩個穿著比基尼泳裝的豐滿女郎中間;為《藝術消息》(ARTnews),他的形象是穿著浴袍的花花公子,四週有花環環繞,春風得意;在為義大利雜誌《閃亮藝術》(Flash Art)裡,他不惜自貶身份,抱起一隻大母豬和小豬。昆斯這樣不避嫌自我宣傳,行徑大膽,卻非史無前例。這樣的廣告手法讓人想起「一般觀念」(General Idea)當年是如何打知名度的。「一般觀念」是一個同性戀當代藝術三人小組,他們曾三人同床,在被子外露出三張乾淨的面孔。他們三人也拍攝過黑眼圈的小狗像。一般人都認為,藝術家是誠實的典範、廣告是天花亂墜集大成,因此,「一般觀念」和昆斯都是向這項觀念挑戰、做出新的詮釋;他們質疑藝術世界的既定立場——藝術作品比藝術家重要,並厚顏自我行銷,看看這樣做會不會殺傷信譽。大禮堂太熱了,觀眾都拿起報紙、筆記本甚至夾腳拖來搧涼。而昆斯卻連領帶也不鬆;不但沒有汗流浹背,反而是臉上發光,又按了一張幻燈片。這一張是他和有「小白菜」之稱的義大利脫星伊羅娜‧史特拉(Ilona Staller,亦有譯為「史脫樂」者)的裸體合照。昆斯曾與後來當上義大利國會議員的史特拉有過一段露水姻緣。一九八九年昆斯有一項作品叫《影像世界:藝術與媒體文化》(Image World: Art and Media Culture)在紐約惠特尼美國藝術館(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展出。這個作品原本是紐約麥迪森廣告街(Madison Avenue)上的一幅廣告看板,為一部昆斯與小白菜合拍的杜撰性電影《天堂製造》(Made in Heaven)宣傳。這也是昆斯《天堂製造》系列的第一幅作品,接下來還有一九九一年的雕塑《淫穢—昆斯在上》(Dirty—Jeff on Top ,一九九一年)與繪畫《小白菜的私處》(Ilona’s Asshole,一九九一年);藝術家的情婦充當畫家的裸體模特兒不是新聞,但是畫家騎在太太身上倒是前所未聞。他後來告訴我說:「要當電影明星的捷徑是拍一部色情電影;在我腦子裡,這就是參與美國通俗文化。」
昆斯播放一張張《天堂製造》幻燈片之際,並未討論它們的暴露或是猜測這些作品對他的藝術事業有什麼影響,他反而回到他最鍾愛的一項話題——接納。他說:「我的前妻曾經從事色情電影,但是她這個人絕對完美,這是一個完美的超越平台。」他一邊說,食指一邊滑過嘴唇:「我想嘗試溝通的是:擁抱肉慾、不帶罪惡和羞恥感,是多麼重要。」昆斯接著講到《卜派》系列。他從二〇〇二年開始從事這一系列的創作,在蛇形藝廊首次亮相,而這次演講就是為了配合展出而舉辦。他視《卜派》系列為家庭性質——對家庭而言,它「更親切」。這一系列作品無論是雕塑或是繪畫,特色都是它們看起來像充氣玩具。昆斯小時候,父母曾經給他買了一塊浮板,幫助他學游泳。他深愛浮板的「解放效果」,這種可以當作救生圈來戴的漂浮器帶給他一種「平衡的感覺」。對昆斯來說,它們也像「人」一樣。他幾乎是帶著宗教性的熱忱說:「我們也是充氣的器物;吸氣,有氣象徵著樂觀;吐氣,就是死亡的象徵。」他還從情色的角度就充血現象有所發揮,觀眾聽的有點坐立不安。他說:「網路上有一大堆性物戀的東西都可以拿來當游泳池玩具了。」他還開玩笑的說,「因為洩氣變軟」,就不免有幾分悲劇色彩了。
系列作品中的每一項藝術創作,昆斯都一一解釋說到他會聯想到的人、史、事、物。基本上聯想分作兩大類:一是指涉藝術史談到的、現代畫壇上的重要藝術家,一是影射性器官與各種交合姿態。例如他說,這些畫家都是響噹噹的人物,在座的觀眾都耳熟能詳,他謙虛地先作聲明表示,不希望聽眾看完所有關於他的介紹後就昏頭轉向,然後指出他的作品與賽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馬塞爾‧杜象(Marcel Duchamp)、法蘭西斯‧畢卡比亞(Francis Picabia)、胡安‧米羅(Joan Miró)、亞歷山大‧考爾德(Alexander Calder)、羅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唐諾‧賈德(Donald Judd)、羅伯特‧羅森柏格(Robert Rauschenberg)、羅伊‧李奇登斯坦(Roy Lichtenstein)、詹姆斯•羅森奎斯特(James Rosenquist)與安迪沃荷(Andy Warhol)的作品之間的關係。昆斯特別提到吉姆‧納特(Jim Nutt)和艾德‧帕斯克(Ed Paschke)。他曾經在芝加哥藝術學院(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受教於這兩位藝術家,「帕斯克會帶我到刺青店和脫衣舞夜店,讓我接觸他的創作靈感來源。」細數與藝術大師關聯的同時,昆斯還一邊加上佛洛伊德式的詮釋,而且講得十分詳細。他最喜歡的形容詞是「陰柔」、「陽剛」、「硬」、「軟」、「濕」、「乾」等等。一件作品若有兩版時,他會說作品有「兩個姿勢」;他的雕塑和繪畫讓他想起「陰唇」、「交合」、「雙腿張開」、「閹割」、「孔」、「子宮」、「骨盤」;更不用說許多充氣藝術品是可以「穿入的」。奇特的是,昆斯用一種理所當然的語氣訴說著這一切,他的臉上一派純真,看起來一點也不會給人猥褻的感覺。
昆斯的神情自若,談吐有條不紊,讓人有一種錯覺,感覺說話的人其實是一個飾演昆斯的演員。而他照本宣科、缺乏即興,也真讓人覺得他是在照劇本演戲,少了那種即興自然和誠實坦率的感覺。這一套其實安迪沃荷最會。他在公開場合談話時刻意營造出一種空洞、言之無物的形象,說話時語調總是冷冷的,充滿了警語,喜歡製造一種沒有一個「真」安迪沃荷的印象。他在《安迪沃荷的普普人生》(The Philosophy of Andy Warhol)說:「我相信自己如果看鏡子什麼也看不見。人常叫我做鏡子,如果鏡子目視鏡子,在哪裡會看到什麼?」能把沃荷式的角色矛盾理論操弄得如此出神入化,除了昆斯以外,還真沒幾個。
昆斯再對著銀幕按了按遙控器,銀幕上出現的是這次說明會的最後一張幻燈片《吊鉤》(Sling Hook,二〇〇七—〇九年)。它是一個充氣海豚和龍蝦的鋁製雕塑,被鐵鍊倒掛——表示它們不是已被宰殺,就是有一種被綁在一起的和樂。昆斯以一種極其平穩的語氣,幾乎是舒緩人心的聲音說:「在我的想像中,我一直都認為到了生命那最後的一刻,一切都變得很清楚;焦慮除去了,看見了新天地。」昆斯經常提到行為的焦慮,有時他似乎是針對藝術成就而言,有時好像又是針對性功能。他說:「接納,焦慮便除去;一切皆無不可、一切都有戲唱。我對藝術的整體了解都在於接納。」SCENE 2 場景2
Ai Weiwei 艾未未
艾未未是個拒絕接受現狀的人。在昆斯演說幾週後,艾未未在上海社會科學院裡展現了他根本不把「接納」二字放在眼裡。若要在昆斯與艾未未之間做個比較,前者可用「有禮」、後者可用「粗魯」來形容;前者清楚的把重點放在他的藝術品上,絕口不提政治,後者卻一再把他的作品導引到倫理的脈絡裡。艾未未出生於一九五七年,幾乎跟昆斯一樣大,雖然兩人都深愛杜象、都善於操弄大眾傳播媒體,但他們對權力的反應卻是南轅北轍。
此刻艾未未坐在學術會議的講台上,椅子前面有一張桌子。他穿著一件粉紅色的T恤,蓋住他圓鼓鼓的肚子,外面是一件寬鬆的黑外套和棉質長褲。灰色的鬍鬚為他平添了一股哲人的氣息。在中國留鬍子的人不多,在中國,鬍子可能讓人聯想到孔夫子或是古巴前總統卡斯楚(Fidel Castro)。
召開這場「設計中國」(Designing China)學術討論會的是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教授亞巴斯(Ackbar Abbas),現場的觀眾大約一半是華人,也有幾位歐洲學者和一些美國研究生。亞巴斯在引介艾未未時說:「艾未未創作了許多藝術品。他是北京奧運鳥巢體育館的設計顧問,也在北京附近的『草場地』興建了一處藝術園區。他常在此接待友人,有時也得跟公安碰面。」艾未未自己則照了幾張亞巴斯和觀眾的相片。亞巴斯說:「我不知道今天他會談些什麼,但我希望他會談艾未未。」
艾未未的目光轉向亞巴斯身旁的田霏宇(Philip Tinari)。田霏宇是策展人,也是艾未未今天的翻譯。哈佛大學畢業的田霏宇戴著時髦的粗框眼鏡,手指頭放在蘋果電腦的鍵盤上,艾未未用中文發表的談話的英文翻譯經由這部電腦傳出去。艾未未用中文說:「大家早。我不準備發表演說,因為我看到『設計中國』的主題,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麼意思。我看你也可以說它是『草泥馬(X你媽)中國。』」聽眾有點不知所措地笑了。艾未未對中國都市計劃缺乏人道關懷的批評,一向不留情面。當他發表意見完畢後,便雙手抱胸,板起身子向後坐,等英文翻譯完。他說:「每次我來上海,我就會想起來為什麼我那麼討厭它。」艾未未住在北京,這番似乎沒有必要的侮辱言辭讓現場氣氛僵住。他說:「上海自認公開、國際化,但事實上上海還是封建心態。」艾未未有七十多個部落格,在部落格中他提到因為寫部落格他的人權被侵犯,又提到汶川大地震時,他是怎樣被四川公安粗暴對待。維權鬥士譚作人被指控煽動顛覆政府權力,一周前艾未未去成都為譚作人審案作證,他說:「開審那天凌晨三點,公安來到我住的旅館,敲開了房間的門。我要求他們給我看他們的警證,卻被暴力對待。」公安拘留了艾未未,不准他在審判中提出證據。他說:「我們的極權政府利用一黨專政方式達成它的目的;中國看可能起來光鮮亮麗,實際上卻是無法無天的黑暗。」
艾未未的頭上有一大道傷痕,是公安對他動粗的結果。挨揍的當下,艾未未並不知道自己已經腦出血,後來還得為此動手術。我不知是不是因為身體上的不舒服加上警察的粗暴,讓他變得更直言無諱。田霏宇經常為艾未未翻譯,對他知之甚深,後來他向我解釋說,住進中國勞改營、拘留感化所之後,艾未未經常心情不好,他說:「除了官府衙門外,艾未未最不喜歡的就是學術界。」
艾未未拿著他的手機念了一段東西,然後抬起頭說:「如果我們要談「設計中國」這個話題,我想我們需要從基本的公平、人權和自由開始。這些基本觀點中國依然欠缺,不管它經濟有多成功。」講了十分鐘後,他突然停了下來,說:「我想現在最好開放來問問題。」喜歡互動的艾未未趨身向前,彷彿要向觀眾挑戰。台下一片寂然,隨即有人小心翼翼地鼓起掌來。
艾未未喜歡驚世駭俗。他最知名的自畫像題目是《失手》(Dropping a Han Dynasty Urn,一九九五年)。作品一共是三幀黑白照片,照片裡,他拿著一尊有兩千年歷史的漢朝古瓶,然後雙手一鬆,把它砸碎了。對珍惜文化瑰寶的人來說,這簡直是匪夷所思,然而,照片裡艾未未雖然面無表情,以此認為他厭棄過去卻是大錯特錯,其實艾未未對在共產黨文化大革命破四舊運動中被掃除的文物,是極為尊敬的,一九九〇年代他也靠買賣古董維生,後來他還建立起一種藝術的新種類,田霏宇稱之為「古代成品」。艾未未將西方商品的商標如可口可樂商標移植到古董器皿上,也找到一些傳統匠人使用古法去做出超現實的多足雕塑。掌聲停止後,亞巴斯站起來,建議大家說:「艾未未將一些我們迴避的話題攤在桌面上,我們不妨直接討論這些話題。」亞巴斯是一位經驗老道的老師,我感覺他好像閉著眼睛都能主持一場成果豐碩的研討會。他接著說:「這裡的事情既不是有法也不是無法,一切都在半法律狀態。」艾未未喝了一些塑膠瓶裡的礦泉水,田霏宇對聽眾說,艾未未也樂意接受英文發問。他是會英文的,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三年之間曾經在紐約住過十二年。
終於第一排有一位年長的美國男士問:「西方人應該在中國做些什麼?」艾未未從喉嚨裡低低地發出一些「嗯」的聲音,然後說:「我對西方民主沒有任何幻覺⋯⋯我的建議是:到處走走、照照相片、吃點好吃的中國菜、然後告訴你的朋友你在中國玩的好極了。」艾未未討厭作假,喜歡開玩笑,是個思想上的自由派。針對下一個問題,他說:「我們在選舉上沒有民主可言,沒有言論自由或媒體自由。如果這些問題你不理會,說了也等於放屁。」一位英文帶着輕微德國口音的女士說:「你的批判是負面、有爭議性的,是那種驚世駭俗、滾一邊去的態度,但是你是位藝術家,能不能談一談您建設性的創作方式?」
艾未未想要迴避,然後很快的跟田霏宇用中文交談了一下,田霏宇替他回答說:「批評和找麻煩,在中國人的情況裡就是一種積極創造的活動。在過程當中是冒著生命危險的。」艾未未舉三人為例——陳光誠、譚作人和劉曉波來說明,這三人不是被拘留,就是遭到軟禁,「任何人認為政治干預是消極的或只是以『去你的』態度來面對,都是錯誤的。⋯⋯我從事過許多建築和博物館計劃,包括上個月剛在東京森美術館(Mori Art Museum)和十月馬上就要落成的慕尼黑美術館(Haus der Kunst)。我參與大型創造,不僅是我們今天所談的事。」
接下來是一名蓄短髮、戴眼鏡的女性發言,她說了一堆恭維和用藝術術語堆砌起來的話之後終於切入正題,詢問艾未未他的「藝術干預」如何提倡社會正義和人權。艾未未一直把雙手插在口袋裡,此刻回答問題也是如此。他說:「闡述、解釋我的作品的人不是我。如果你有興趣,你自己去看一看。我做的每一件作品都跟我最基本的信念有關;如果作品不能表達那個信念,它就不值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