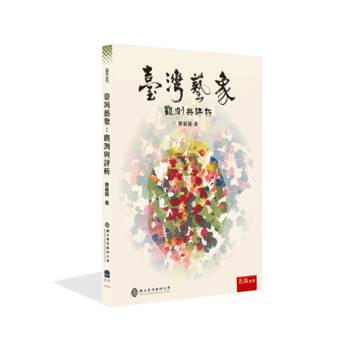七、緣與運—蒲添生的《妻子》塑像(節錄)
搭架疊泥
這尊僅24 公分高的半身像,表面保留著泥塑的清晰痕跡。在方寸間,若無近距離端視,還真不知道有如此多的細節。轉折凹凸之處,手法到位,用心經營,似乎有著不言而喻的情節,等待有緣人來閱讀。說到「緣」字,這件作品的前世今生隱藏著萬縷千絲的故事。凡「緣」必「運」,這小小的身軀還得承受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2023) 式「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的試煉,時代與個體交織出的情愫,糾結又悸動。
年輕女子表情自然,眉宇間可以看出端莊賢淑的氣質。嘴角猶如蒙娜麗莎般的微微笑,帶點靦腆,容易讓人忽略其內斂的神情。一般來說,這是標準化的肖像製作,手掌約莫可以握住的小肖像有時作為實際放大的摹本。等身大的半身像有紀念性質,縮小版的則顯得小巧可愛,另有一番把玩趣味。胸像源自於西元前3 世紀的希臘化時期,西元前1世紀左右的羅馬時期半身肖像則以寫實著稱;前者有著鮮明的宗教、政治的個性,後者則開始有了人間的情性。如今,大小半身像的塑造不再是王公貴族的特權,也不需要冠冕堂皇的理由才能製作。普通人同樣可以為自己或為別人塑像,意義也不必那麼嚴肅,親情、愛情、友情、熱情、溫情都可以傳達。
既然生活成為創作題材,雕像的故事也就活潑了起來,有更多的人情世故可茲分享。英國詩人藝術家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的名詩中曾言:「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無限掌中置,剎那成永恆。」同樣的,任何一件藝術作品可以很有故事也就理所當然了,雖然不需要壯闊或蕩氣迴腸。英國藝術史學者貢布里希(Ernst Gombrich, 1909-2001)在其1950年巨著《藝術的故事》開宗明義:「真的沒有藝術這回事,只有藝術家們。所謂藝術作品不是些神祕活動的結果,而是人為了人所製造的事物。」所言甚是,我們若不能從藝術中獲得人間悲歡離合、愛恨情仇以及生老病死的啟發,若藝術只剩下偉大,有何偉大可言?偉大可以瞻仰、神祕可以想像,平凡才能親近。我寧可倒過來,先平凡,再來神祕及偉大,因為我們是人,必須感受人性的脈搏。或者,我們常聽到的平凡中的偉大、偉大中的平凡,這種複合概念更深刻、更觸動人心。另外,表達是一種創造性的作為;我們常會用「製造」(made)來描述吾人所生產的各式各樣的物品,我們則會用「創造」(create)對應藝術品。生產物品,創造藝術品;生產反映人類的生存能力,創造則是凸顯人類的生命價值,一體兩面。藝術如物品般被製造出來,但經由創造的洗禮而獨具一格。藝術表達可以透過天馬行空的方式來反映具超越性的世界觀和宇宙觀,可以不必拘泥於現實與利害關係,卻對人的生存意義有極大的延展性。
構思塑形
蒲浩志館長邀請我撰寫有關於他父親蒲添生(1912-1996) 的雕塑藝術,我另類請求:借我一件作品回去琢磨。他爽快答應,於是有了這個小小的實驗,就暫且稱之為「藝術陪伴計畫」吧!
到蒲添生雕塑紀念館選件,幾個目標都挺有趣,婦女小雕像最引人注目。那是蒲館長的母親,剛出嫁的模樣。從他的口中緩緩說出的每一個橋段都如此戲劇性,所謂天上人間,其實也是人間天上。故事不長,卻讓人愛不釋「耳」,至少我個人是願意聽一百遍的。
之所以迷人,是因為這座小雕像藏著一段姻緣,除了百年修來的共枕眠,還是因為有藝術緣分的關係。藝術扮演起月下老人的角色,而且真的是一尊老者雕像牽的線,很少聽到吧?
原來,蒲添生為嘉義蘇友讓(1883-1945) 先生塑像,製作時為1939年,正是這位年輕新秀醞積能量之際。他跟隨朝倉文夫(1883-1964) 漫長的八年時間中進入了第五個年頭。在「朝倉雕塑塾」的規矩是三年雜務之後才從石膏頭像臨摹起,沒有耐心和熱情,絕對過不了這一關。對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來說,此時需要的是磨練的機會,用來證明日本雕塑大師接受唯一臺籍青年的決定沒有錯;當然也有輸人不輸陣、不要給臺灣人丟臉的志氣。1939 年的日本雕塑家聯盟會員名簿裡,「朝倉雕塑塾」登載21 位師生,其中包括蒲添生,證實他已經是朝倉家族的一員了。
如日中天的朝倉文夫,倍受尊重,有「日本羅丹」、「日本現代雕塑之父」的稱號。法國羅丹(Auguste Rodin, 1840-1917) 以雕塑明顯的肌理聞名於世,將人性的糾結與掙扎的情感表露得淋漓盡致。這位「日本羅丹」則較為理性沉著,平靜外表之下蘊含動能,以迷人的細節、溫暖的平凡著稱。沒有背景襯托,只憑簡單的姿態來呈現複雜的藝術表現與深刻的意涵,是需要高度技巧與細膩心思來交互鋪陳的。朝倉也結合「理想之美」,展現西洋古典主義中典型與完美的概念,可以說是感性與理性兼具。1979年,近百位臺灣藝術家談「印象最深刻的作品」,蒲添生就點名朝倉文夫的《守墓者》。
承襲名師,藝高膽大,蒲添生把蘇先生的神情刻劃得維妙維肖,眼神、表情、氣質,栩栩如生,的確是件佳作。雖然是位從事木材生意的商人,蘇友讓可是道道地地的業餘文人,詩書畫頗多浸淫,是嘉社、鴉社畫會成員。在一批塵封多年的陳澄波書畫收藏裡也包含幾件蘇的作品,結體穩重大方,內容義正詞嚴,碑帖風格並用,不阿性格或可想見一般。他也是陳澄波長女陳紫薇(1919-1998)的書法老師,17歲的少女規規矩矩地寫下「千峰鳥路寒梅雨,五月蟬聲送麥秋」的詩句,活脫像老師的筆調。不謀而合,1931年陳澄波《我的家庭》中,坐在最右邊的紫薇拿的是書帖。
半身像完成後,蘇友讓便邀約陳澄波前來評價,欲聽聽藝術家專業的看法。見此塑像,陳澄波讚賞有加。既然知道是青年俊才蒲添生,心裡便有了別人想也想不到的主意:把長女紫薇許配給他!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乘龍快婿就街坊裡,不必眾裡尋他千百度。藝術因果成就了藝術姻緣,在世界藝術史中,這樣的例子並不多見,更何況是臺灣。
其實陳澄波也不是初次認識蒲添生。他曾經在嘉義玉川公學校(現崇文國小)短暫擔任老師期間教過這小孩子,算是師生關係。1928年又同是春萌畫會的畫友,因為這小伙子挺有「繪根」,17 歲時參加美展還獲獎,其實是從小在裱畫店耳濡目染所累積的經驗。1934 年陳澄波赴東京參加帝展活動,和添生再度見了面,相談甚歡,更加深對他的好印象。其實那一年蒲添生有重大抉擇:他毅然從帝國美術學校繪畫科轉雕塑科,之後在朝倉文夫工作室當起了學徒,從頭學起。回想三年前的1931 年,20 歲的蒲添生利用替自家「文錦裱畫店」收款之後不告而別到日本學藝。用現在的話是「捲款潛逃」,逃走的目的不是為了利益,為的是追求藝術理想。無獨有偶,同住在嘉義美街前輩林玉山也是在1926 年不告而別的。一繪畫一雕塑,兩人日後都成為臺灣美術運動的關鍵推手。
雖然認識蒲添生,為愛女覓夫婿自然還是得慎重其事。陳澄波乾脆委請蘇友讓先生居間說媒。1939 年7 月6 日的提親書信上則有保證人陳崑樹寫著詳細內容。誠意、誠信盡在其中:
陳澄波先生:拜啟,祝賀益昌盛。至於上次蒲君回京後,承聞令嬡要嫁給添生君一事,我也勸他早日決定。由於收入方面考慮而客氣,最近收入也增多,我也積極勸為良緣,因此依蒲君說:「那就煩請先生代為正式提親。如受承諾,就請你八、九月來京時一齊陪伴來。」如果承蒙承諾,煩請電報通報添生君本人,並出示此信給蒲君雙親。此信是根據蒲君依賴而寫,因此可以信賴。但因婚姻是極大重要,為了慎重起見,特請蒲君捺印為證。懇請承諾並直接回音給蒲君本人。
其實,此期間還有「日本婆」對蒲添生這位「臺灣郎」心生好感且有所表示,但因考慮文化差異而作罷。陳先生並且保證:「蒲君在東京沒有和異性有戀愛關係,請放心。」好人做到底,送佛就該送上西天。早在日本發展商務的這位好心的長輩還贈送三張船票,想必是一張回臺娶親,另外兩張是讓小倆口婚後相偕去日本過新生活的安排。以這種方式促成一對新人,在現在開放的時代都很罕見,真是充滿人情味的臺灣鄉親。很快的,才子佳人於8月31日結婚,藝術女史張李德和(1893-1972)擔任介紹人,眾多親朋好友在「文錦裱具師」牌號下留影,見證了這段臺灣美術史上的藝術聯姻佳話。
除了嫁妝,陳澄波以一張53公分寬、31.5公分高的油畫《駱駝》相贈,兩隻駱駝一低頭一抬頭,似乎很有默契。亞熱帶臺灣少見這種沙漠動物,陳澄波創作中也幾乎未出現過類似主題的繪畫,看來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是特別給這對新人的特別勉勵。一般來說,鴛鴦通常是新婚致賀的象徵,但以駱駝圖像相贈其實更寓意深遠,強調任重道遠的精神,正如婚姻之路,亦如人生之路。當然,藝術之路也是如此,需忍受嚴酷的考驗,一步一腳印,終能成功到達目的地。大藝術家畫風不但獨特,行事作風也迥異,替女兒找丈夫靠一尊塑像,而不是媒人;送新人的畫作不是蝴蝶鴛鴦,而是一對盡責耐操的駱駝。
翻銅的肖像背後註記:「昭和16年 四月一日 添生作」。1941年石膏雕像在日本完成後便交由陳澄波帶回。蒲添生當時表示,岳父把寶貝女兒交給他,而這座雕像留在陳身邊就可以常伴在側。這一年,蒲添生受陳夏雨(1915-2000)之邀回臺發展藝術事業。2010年蒲添生雕塑紀念館成立後,石膏像翻製成銅像。
翻模修飾
曾見過這尊小雕像的王白淵(1902-1965),認為它表現出高度的藝術感,在蒲氏創作中讓人刮目相看:
〈P 夫人〉係蒲氏自己太太的胸像,不是豔麗之美人,卻是各部均整之寧靜女性,表現柔軟,女性之脂肪值及各部筋肉之互相關係亦有表現出來,而形成著優美之線條。
這麼小巧而靜雅的作品,為摯親而做而不為其他特定目的,何以有如此深邃的涵義?
21 歲的陳紫薇比翁婿小七歲,人生路程再次起步。作品完成時間是甜蜜新婚的第二年,長女秀齡也剛出世,家庭正美滿成形之中。相處一年多,開始相互熟悉,也摸索著為人父母的角色。這件作品如何模塑牽手的印象?如何描寫當時的情態?2012 年「藝無止境—蒲添生家族故事展」寫道:「以其最擅長的泥土觸感來表達,相當傳神地掌握了這位初為人母的少婦心理的變化與神態的自然。」7 另外,蒲添生紀念館的說明簿裡也分析:「顯露蒲氏對新婚妻子柔情而保守之愛意,以最擅長的泥土觸感來表達。率真樸實,輪廓柔和,面面俱到,散發臺灣女性嫻靜之美。」兩段評論都相當貼切到位。如何從無言的雕像表面之蛛絲馬跡來追索神態、關係與氣質?雕塑品的外在反映了作品的內在氣質,並且也留下線索讓觀者循跡創作者的手法與意念。所謂魔鬼藏在細節裡,其實天使也藏在細節之中。因為小而美,稍不注意,可觀之處很容易溜走。這趟藝術陪伴計畫走得慢又長,於是,蒲夫人的雕像就在筆者的桌上安安靜靜地擺了兩個月。
雕塑的確需要空間感知與觸覺輔助才能掌握。探索變成方法,理解成為理論。不用太急太快,行動有時是思想的敵人。印度古諺有云:「走慢一點,讓靈魂跟上來。」細節的咀嚼可以是走向雕塑評論方法或路徑的試金石。
臉龐並不光滑,由無數的小切面構成小地方的轉折,下巴、嘴唇、人中、鼻梁、臉頰、顴骨、眼眶、眼臉、眉棱、額頭⋯⋯處處留痕,要在極小的面積表現著實不易。作者顯然不在於形塑完美女性形象,而是企圖掌握真實—身邊親密伴侶的「真面目」。
搭架疊泥
這尊僅24 公分高的半身像,表面保留著泥塑的清晰痕跡。在方寸間,若無近距離端視,還真不知道有如此多的細節。轉折凹凸之處,手法到位,用心經營,似乎有著不言而喻的情節,等待有緣人來閱讀。說到「緣」字,這件作品的前世今生隱藏著萬縷千絲的故事。凡「緣」必「運」,這小小的身軀還得承受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2023) 式「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的試煉,時代與個體交織出的情愫,糾結又悸動。
年輕女子表情自然,眉宇間可以看出端莊賢淑的氣質。嘴角猶如蒙娜麗莎般的微微笑,帶點靦腆,容易讓人忽略其內斂的神情。一般來說,這是標準化的肖像製作,手掌約莫可以握住的小肖像有時作為實際放大的摹本。等身大的半身像有紀念性質,縮小版的則顯得小巧可愛,另有一番把玩趣味。胸像源自於西元前3 世紀的希臘化時期,西元前1世紀左右的羅馬時期半身肖像則以寫實著稱;前者有著鮮明的宗教、政治的個性,後者則開始有了人間的情性。如今,大小半身像的塑造不再是王公貴族的特權,也不需要冠冕堂皇的理由才能製作。普通人同樣可以為自己或為別人塑像,意義也不必那麼嚴肅,親情、愛情、友情、熱情、溫情都可以傳達。
既然生活成為創作題材,雕像的故事也就活潑了起來,有更多的人情世故可茲分享。英國詩人藝術家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的名詩中曾言:「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無限掌中置,剎那成永恆。」同樣的,任何一件藝術作品可以很有故事也就理所當然了,雖然不需要壯闊或蕩氣迴腸。英國藝術史學者貢布里希(Ernst Gombrich, 1909-2001)在其1950年巨著《藝術的故事》開宗明義:「真的沒有藝術這回事,只有藝術家們。所謂藝術作品不是些神祕活動的結果,而是人為了人所製造的事物。」所言甚是,我們若不能從藝術中獲得人間悲歡離合、愛恨情仇以及生老病死的啟發,若藝術只剩下偉大,有何偉大可言?偉大可以瞻仰、神祕可以想像,平凡才能親近。我寧可倒過來,先平凡,再來神祕及偉大,因為我們是人,必須感受人性的脈搏。或者,我們常聽到的平凡中的偉大、偉大中的平凡,這種複合概念更深刻、更觸動人心。另外,表達是一種創造性的作為;我們常會用「製造」(made)來描述吾人所生產的各式各樣的物品,我們則會用「創造」(create)對應藝術品。生產物品,創造藝術品;生產反映人類的生存能力,創造則是凸顯人類的生命價值,一體兩面。藝術如物品般被製造出來,但經由創造的洗禮而獨具一格。藝術表達可以透過天馬行空的方式來反映具超越性的世界觀和宇宙觀,可以不必拘泥於現實與利害關係,卻對人的生存意義有極大的延展性。
構思塑形
蒲浩志館長邀請我撰寫有關於他父親蒲添生(1912-1996) 的雕塑藝術,我另類請求:借我一件作品回去琢磨。他爽快答應,於是有了這個小小的實驗,就暫且稱之為「藝術陪伴計畫」吧!
到蒲添生雕塑紀念館選件,幾個目標都挺有趣,婦女小雕像最引人注目。那是蒲館長的母親,剛出嫁的模樣。從他的口中緩緩說出的每一個橋段都如此戲劇性,所謂天上人間,其實也是人間天上。故事不長,卻讓人愛不釋「耳」,至少我個人是願意聽一百遍的。
之所以迷人,是因為這座小雕像藏著一段姻緣,除了百年修來的共枕眠,還是因為有藝術緣分的關係。藝術扮演起月下老人的角色,而且真的是一尊老者雕像牽的線,很少聽到吧?
原來,蒲添生為嘉義蘇友讓(1883-1945) 先生塑像,製作時為1939年,正是這位年輕新秀醞積能量之際。他跟隨朝倉文夫(1883-1964) 漫長的八年時間中進入了第五個年頭。在「朝倉雕塑塾」的規矩是三年雜務之後才從石膏頭像臨摹起,沒有耐心和熱情,絕對過不了這一關。對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來說,此時需要的是磨練的機會,用來證明日本雕塑大師接受唯一臺籍青年的決定沒有錯;當然也有輸人不輸陣、不要給臺灣人丟臉的志氣。1939 年的日本雕塑家聯盟會員名簿裡,「朝倉雕塑塾」登載21 位師生,其中包括蒲添生,證實他已經是朝倉家族的一員了。
如日中天的朝倉文夫,倍受尊重,有「日本羅丹」、「日本現代雕塑之父」的稱號。法國羅丹(Auguste Rodin, 1840-1917) 以雕塑明顯的肌理聞名於世,將人性的糾結與掙扎的情感表露得淋漓盡致。這位「日本羅丹」則較為理性沉著,平靜外表之下蘊含動能,以迷人的細節、溫暖的平凡著稱。沒有背景襯托,只憑簡單的姿態來呈現複雜的藝術表現與深刻的意涵,是需要高度技巧與細膩心思來交互鋪陳的。朝倉也結合「理想之美」,展現西洋古典主義中典型與完美的概念,可以說是感性與理性兼具。1979年,近百位臺灣藝術家談「印象最深刻的作品」,蒲添生就點名朝倉文夫的《守墓者》。
承襲名師,藝高膽大,蒲添生把蘇先生的神情刻劃得維妙維肖,眼神、表情、氣質,栩栩如生,的確是件佳作。雖然是位從事木材生意的商人,蘇友讓可是道道地地的業餘文人,詩書畫頗多浸淫,是嘉社、鴉社畫會成員。在一批塵封多年的陳澄波書畫收藏裡也包含幾件蘇的作品,結體穩重大方,內容義正詞嚴,碑帖風格並用,不阿性格或可想見一般。他也是陳澄波長女陳紫薇(1919-1998)的書法老師,17歲的少女規規矩矩地寫下「千峰鳥路寒梅雨,五月蟬聲送麥秋」的詩句,活脫像老師的筆調。不謀而合,1931年陳澄波《我的家庭》中,坐在最右邊的紫薇拿的是書帖。
半身像完成後,蘇友讓便邀約陳澄波前來評價,欲聽聽藝術家專業的看法。見此塑像,陳澄波讚賞有加。既然知道是青年俊才蒲添生,心裡便有了別人想也想不到的主意:把長女紫薇許配給他!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乘龍快婿就街坊裡,不必眾裡尋他千百度。藝術因果成就了藝術姻緣,在世界藝術史中,這樣的例子並不多見,更何況是臺灣。
其實陳澄波也不是初次認識蒲添生。他曾經在嘉義玉川公學校(現崇文國小)短暫擔任老師期間教過這小孩子,算是師生關係。1928年又同是春萌畫會的畫友,因為這小伙子挺有「繪根」,17 歲時參加美展還獲獎,其實是從小在裱畫店耳濡目染所累積的經驗。1934 年陳澄波赴東京參加帝展活動,和添生再度見了面,相談甚歡,更加深對他的好印象。其實那一年蒲添生有重大抉擇:他毅然從帝國美術學校繪畫科轉雕塑科,之後在朝倉文夫工作室當起了學徒,從頭學起。回想三年前的1931 年,20 歲的蒲添生利用替自家「文錦裱畫店」收款之後不告而別到日本學藝。用現在的話是「捲款潛逃」,逃走的目的不是為了利益,為的是追求藝術理想。無獨有偶,同住在嘉義美街前輩林玉山也是在1926 年不告而別的。一繪畫一雕塑,兩人日後都成為臺灣美術運動的關鍵推手。
雖然認識蒲添生,為愛女覓夫婿自然還是得慎重其事。陳澄波乾脆委請蘇友讓先生居間說媒。1939 年7 月6 日的提親書信上則有保證人陳崑樹寫著詳細內容。誠意、誠信盡在其中:
陳澄波先生:拜啟,祝賀益昌盛。至於上次蒲君回京後,承聞令嬡要嫁給添生君一事,我也勸他早日決定。由於收入方面考慮而客氣,最近收入也增多,我也積極勸為良緣,因此依蒲君說:「那就煩請先生代為正式提親。如受承諾,就請你八、九月來京時一齊陪伴來。」如果承蒙承諾,煩請電報通報添生君本人,並出示此信給蒲君雙親。此信是根據蒲君依賴而寫,因此可以信賴。但因婚姻是極大重要,為了慎重起見,特請蒲君捺印為證。懇請承諾並直接回音給蒲君本人。
其實,此期間還有「日本婆」對蒲添生這位「臺灣郎」心生好感且有所表示,但因考慮文化差異而作罷。陳先生並且保證:「蒲君在東京沒有和異性有戀愛關係,請放心。」好人做到底,送佛就該送上西天。早在日本發展商務的這位好心的長輩還贈送三張船票,想必是一張回臺娶親,另外兩張是讓小倆口婚後相偕去日本過新生活的安排。以這種方式促成一對新人,在現在開放的時代都很罕見,真是充滿人情味的臺灣鄉親。很快的,才子佳人於8月31日結婚,藝術女史張李德和(1893-1972)擔任介紹人,眾多親朋好友在「文錦裱具師」牌號下留影,見證了這段臺灣美術史上的藝術聯姻佳話。
除了嫁妝,陳澄波以一張53公分寬、31.5公分高的油畫《駱駝》相贈,兩隻駱駝一低頭一抬頭,似乎很有默契。亞熱帶臺灣少見這種沙漠動物,陳澄波創作中也幾乎未出現過類似主題的繪畫,看來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是特別給這對新人的特別勉勵。一般來說,鴛鴦通常是新婚致賀的象徵,但以駱駝圖像相贈其實更寓意深遠,強調任重道遠的精神,正如婚姻之路,亦如人生之路。當然,藝術之路也是如此,需忍受嚴酷的考驗,一步一腳印,終能成功到達目的地。大藝術家畫風不但獨特,行事作風也迥異,替女兒找丈夫靠一尊塑像,而不是媒人;送新人的畫作不是蝴蝶鴛鴦,而是一對盡責耐操的駱駝。
翻銅的肖像背後註記:「昭和16年 四月一日 添生作」。1941年石膏雕像在日本完成後便交由陳澄波帶回。蒲添生當時表示,岳父把寶貝女兒交給他,而這座雕像留在陳身邊就可以常伴在側。這一年,蒲添生受陳夏雨(1915-2000)之邀回臺發展藝術事業。2010年蒲添生雕塑紀念館成立後,石膏像翻製成銅像。
翻模修飾
曾見過這尊小雕像的王白淵(1902-1965),認為它表現出高度的藝術感,在蒲氏創作中讓人刮目相看:
〈P 夫人〉係蒲氏自己太太的胸像,不是豔麗之美人,卻是各部均整之寧靜女性,表現柔軟,女性之脂肪值及各部筋肉之互相關係亦有表現出來,而形成著優美之線條。
這麼小巧而靜雅的作品,為摯親而做而不為其他特定目的,何以有如此深邃的涵義?
21 歲的陳紫薇比翁婿小七歲,人生路程再次起步。作品完成時間是甜蜜新婚的第二年,長女秀齡也剛出世,家庭正美滿成形之中。相處一年多,開始相互熟悉,也摸索著為人父母的角色。這件作品如何模塑牽手的印象?如何描寫當時的情態?2012 年「藝無止境—蒲添生家族故事展」寫道:「以其最擅長的泥土觸感來表達,相當傳神地掌握了這位初為人母的少婦心理的變化與神態的自然。」7 另外,蒲添生紀念館的說明簿裡也分析:「顯露蒲氏對新婚妻子柔情而保守之愛意,以最擅長的泥土觸感來表達。率真樸實,輪廓柔和,面面俱到,散發臺灣女性嫻靜之美。」兩段評論都相當貼切到位。如何從無言的雕像表面之蛛絲馬跡來追索神態、關係與氣質?雕塑品的外在反映了作品的內在氣質,並且也留下線索讓觀者循跡創作者的手法與意念。所謂魔鬼藏在細節裡,其實天使也藏在細節之中。因為小而美,稍不注意,可觀之處很容易溜走。這趟藝術陪伴計畫走得慢又長,於是,蒲夫人的雕像就在筆者的桌上安安靜靜地擺了兩個月。
雕塑的確需要空間感知與觸覺輔助才能掌握。探索變成方法,理解成為理論。不用太急太快,行動有時是思想的敵人。印度古諺有云:「走慢一點,讓靈魂跟上來。」細節的咀嚼可以是走向雕塑評論方法或路徑的試金石。
臉龐並不光滑,由無數的小切面構成小地方的轉折,下巴、嘴唇、人中、鼻梁、臉頰、顴骨、眼眶、眼臉、眉棱、額頭⋯⋯處處留痕,要在極小的面積表現著實不易。作者顯然不在於形塑完美女性形象,而是企圖掌握真實—身邊親密伴侶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