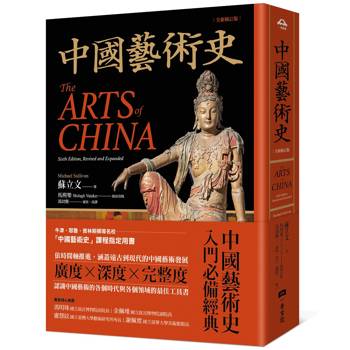【審校序】
文∕馮幼衡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考古系博士、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退休教授、本書審校.改譯)
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的《中國藝術史》(The Arts of China)這本書對我而言,饒富紀念意義。它是我剛去美國在馬利蘭大學修習中國繪畫史時,任課老師金洪南博士所開的三本教科書之一。另外兩本分別是席克曼(Lawrence Sickman)與索伯(Alexander Soper)合著的《中國藝術與建築》(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李雪曼(Sherman Lee )寫的《遠東藝術史》(A History of Far Eastern Art)。我很快發現這三本書雖各有所長(第二本書在雕塑與建築上別有見地,尤其是南北朝的佛教藝術那一段寫得最好,但繪畫上就顯得資料太過陳舊。第三本則在繪畫與器物上有所闡發,只是旁及日本及印度,難免在專精度上顯得分散),但是多年來對我最有用也一直不離不棄的,還是蘇立文的這本《中國藝術史》。翻閱我那本一九八四年購入的版本(一九七九年出的第三版二刷),與現在我負責審校與改譯、也是如今仍在美國擔當大學教科書重任的第六版,不同的版本,顯示它在四十年間陸續擴充的結果,充分見證了此書歷久彌新的實用性。
我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攻讀中國藝術史博士學位以後,由於鑽研宋代,進入閱讀專書的階段,暫別了這本引領我入門的著作多年。直到我完成學業,進入大學授課後,我又開始需要參考這本通史性質的書,也在此時,我發現它的版本其實不斷在更新中。它的更新不但反映了學界對中國藝術的新發現與見解,也包含歷年來中國大陸考古發掘的重大發現,說是刷新了吾人對中國新石器時代及上古史的認識,亦不為過。
比如說,八○年代我所擁有的舊版中,對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描述僅及於彩陶文化與黑陶文化,對比之下,如今的新版,不但包含了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還有三星堆文化(新石器時代晚期延續至青銅時期)等重大考古發現。在青銅器方面,舊版雖有商代青銅器型的分類,也納入了羅樾(Max Loehr)最負盛名的商代青銅器可依其裝飾風格分為五期的理論,然而新版中卻將歷年來的考古發現,包括青銅器由最早的形式出現在河南偃師二里頭,到鄭州二里岡的煥然大備,以至安陽時期的發展到全盛時期,井然有序的羅列出青銅器發展的脈絡與遺址,對應著羅樾的分期理論,方知其所言不虛。書中更清晰列出了這五個時期的饕餮紋飾圖形,並且依考古發現將羅樾由一至五依序先後發生的風格,修正為也有例外,例如安陽時期婦好墓中的器形,同時具備三、四、五期三種風格,讓有興趣的讀者他日若進入博物館參觀青銅器時,得以據此分辨出商代器皿的早中晚期,讓讀者一方面可以把羅樾的理論化為實際,一方面又可理解藝術史中,風格分析的妙用,實為大幸!
蘇立文教授在西方藝術史學者中,以研究中國二十世紀繪畫知名。他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出版了《二十世紀的中國繪畫》(Chinese Ar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他將中國近代畫家劃分為「改革派」與「傳統派」的主張一直通行了四十年,直到晚近才受到萬靑力(1945-2017)與方聞(1930-2018)師的挑戰,後兩位學者皆認為對中國近代繪畫貢獻最大的是「傳統派」畫家,而非蘇利文認為代表西化與進步的「改革派」。不過在本書的二十世紀篇章中,蘇立文對「改革派」與「傳統派」持平看待,他固然強調了西方對中國畫家的影響,但也重視中國藝術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傳統如何不斷以現代的新形式出現。舊版中現代繪畫僅及於文革前夕的《收租院》(1965年),新版卻收錄了大陸改革開放以後中港臺的作品,從徐斌的《無字天書》到朱銘的雕刻以及蔡國強的裝置藝術(2004年)。
雖然此書是本通史,而非某個時代或議題的專論,蘇立文還是透露出他的史觀。蘇立文也寫過《東方與西方藝術之相遇》(The Meet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rt, 1973),所以對此議題並不陌生,他認為中國不會產生西方那樣將個人主義發展到極致的精采作品,因為中國的藝術家既反抗,但也部分接受社會對個人的制約,「就是在那些限制之中產生了過去偉大的中國藝術,也許未來偉大的藝術還是會在這樣的情況下繼續出現」。而對中國古代藝術,他的總結是:「社會和諧是總體的訴求。只有當和諧不復存在,也就是朝代傾覆社會劇變,或者壓迫不堪承受之時,個人主義才會發出強烈的吶喊」。我想為他的看法做個註腳,正是晚唐,蒙元和晚明這些動盪不安,社會至暗的時刻,產生了歷史上最驚世駭俗,也最深刻動人的藝術作品。
另外,在歷代畫家作品的選件上,作者也將近年來學界討論較多的作品及研究成果予以納入(相較於舊版), 而在陶瓷、工藝與建築的介紹上,作者也都汰舊換新,包含近年來的考古發現,如汝窯的遺址,以及外銷貿易瓷的途徑等,讓讀者更易理解東西藝術交流的歷史及相互交流所帶來之的影響等。
或許有讀者會問,為何要閱讀一本由西方學者所寫的中國藝術史?難道沒有中文的同類著作嗎?我的回答是,這涉及研究方法的問題,因為傳統的中文作者, 習慣用「文字」來處理「圖像」的歷史,總是從師承、生平、作品目錄及文字紀錄著手。但西方訓練有素的藝術史學者建構的是「圖像」的歷史,圖像自有其歷史,如果不熟悉圖像的歷史,如何撰寫一部藝術史呢?圖像的分析有其方法和技巧,蘇立文此書,並沒有太涉及嚴謹的結構分析理論,但做到了一般的形式及風格分析,相信很容易為讀者所接受與理解。而就廣度與完整度而言,蘇立文的這本《中國藝術史》仍是目前為止,認識中國藝術的各個時代和各個領域最佳,也最值得推薦的一本工具書。
最後,我說明一下本書的修訂是基於原譯,但我秉著兩個原則:一、必須根據原作不能曲解,二、必須忠於專業,所以不得不做大幅度的修正。另外,我對原作舉例米友仁作品時,有不同之見解,遂以作註方式附上個人認為較合適的米友仁代表作,以及蘇立文教授認為宋代書法的主要影響為「王羲之與隸書」,與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也作註附上「王羲之、顏真卿與鍾繇」,謹供讀者參考,一併說明於上。
文∕馮幼衡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考古系博士、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退休教授、本書審校.改譯)
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的《中國藝術史》(The Arts of China)這本書對我而言,饒富紀念意義。它是我剛去美國在馬利蘭大學修習中國繪畫史時,任課老師金洪南博士所開的三本教科書之一。另外兩本分別是席克曼(Lawrence Sickman)與索伯(Alexander Soper)合著的《中國藝術與建築》(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李雪曼(Sherman Lee )寫的《遠東藝術史》(A History of Far Eastern Art)。我很快發現這三本書雖各有所長(第二本書在雕塑與建築上別有見地,尤其是南北朝的佛教藝術那一段寫得最好,但繪畫上就顯得資料太過陳舊。第三本則在繪畫與器物上有所闡發,只是旁及日本及印度,難免在專精度上顯得分散),但是多年來對我最有用也一直不離不棄的,還是蘇立文的這本《中國藝術史》。翻閱我那本一九八四年購入的版本(一九七九年出的第三版二刷),與現在我負責審校與改譯、也是如今仍在美國擔當大學教科書重任的第六版,不同的版本,顯示它在四十年間陸續擴充的結果,充分見證了此書歷久彌新的實用性。
我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攻讀中國藝術史博士學位以後,由於鑽研宋代,進入閱讀專書的階段,暫別了這本引領我入門的著作多年。直到我完成學業,進入大學授課後,我又開始需要參考這本通史性質的書,也在此時,我發現它的版本其實不斷在更新中。它的更新不但反映了學界對中國藝術的新發現與見解,也包含歷年來中國大陸考古發掘的重大發現,說是刷新了吾人對中國新石器時代及上古史的認識,亦不為過。
比如說,八○年代我所擁有的舊版中,對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描述僅及於彩陶文化與黑陶文化,對比之下,如今的新版,不但包含了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還有三星堆文化(新石器時代晚期延續至青銅時期)等重大考古發現。在青銅器方面,舊版雖有商代青銅器型的分類,也納入了羅樾(Max Loehr)最負盛名的商代青銅器可依其裝飾風格分為五期的理論,然而新版中卻將歷年來的考古發現,包括青銅器由最早的形式出現在河南偃師二里頭,到鄭州二里岡的煥然大備,以至安陽時期的發展到全盛時期,井然有序的羅列出青銅器發展的脈絡與遺址,對應著羅樾的分期理論,方知其所言不虛。書中更清晰列出了這五個時期的饕餮紋飾圖形,並且依考古發現將羅樾由一至五依序先後發生的風格,修正為也有例外,例如安陽時期婦好墓中的器形,同時具備三、四、五期三種風格,讓有興趣的讀者他日若進入博物館參觀青銅器時,得以據此分辨出商代器皿的早中晚期,讓讀者一方面可以把羅樾的理論化為實際,一方面又可理解藝術史中,風格分析的妙用,實為大幸!
蘇立文教授在西方藝術史學者中,以研究中國二十世紀繪畫知名。他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出版了《二十世紀的中國繪畫》(Chinese Ar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他將中國近代畫家劃分為「改革派」與「傳統派」的主張一直通行了四十年,直到晚近才受到萬靑力(1945-2017)與方聞(1930-2018)師的挑戰,後兩位學者皆認為對中國近代繪畫貢獻最大的是「傳統派」畫家,而非蘇利文認為代表西化與進步的「改革派」。不過在本書的二十世紀篇章中,蘇立文對「改革派」與「傳統派」持平看待,他固然強調了西方對中國畫家的影響,但也重視中國藝術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傳統如何不斷以現代的新形式出現。舊版中現代繪畫僅及於文革前夕的《收租院》(1965年),新版卻收錄了大陸改革開放以後中港臺的作品,從徐斌的《無字天書》到朱銘的雕刻以及蔡國強的裝置藝術(2004年)。
雖然此書是本通史,而非某個時代或議題的專論,蘇立文還是透露出他的史觀。蘇立文也寫過《東方與西方藝術之相遇》(The Meet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rt, 1973),所以對此議題並不陌生,他認為中國不會產生西方那樣將個人主義發展到極致的精采作品,因為中國的藝術家既反抗,但也部分接受社會對個人的制約,「就是在那些限制之中產生了過去偉大的中國藝術,也許未來偉大的藝術還是會在這樣的情況下繼續出現」。而對中國古代藝術,他的總結是:「社會和諧是總體的訴求。只有當和諧不復存在,也就是朝代傾覆社會劇變,或者壓迫不堪承受之時,個人主義才會發出強烈的吶喊」。我想為他的看法做個註腳,正是晚唐,蒙元和晚明這些動盪不安,社會至暗的時刻,產生了歷史上最驚世駭俗,也最深刻動人的藝術作品。
另外,在歷代畫家作品的選件上,作者也將近年來學界討論較多的作品及研究成果予以納入(相較於舊版), 而在陶瓷、工藝與建築的介紹上,作者也都汰舊換新,包含近年來的考古發現,如汝窯的遺址,以及外銷貿易瓷的途徑等,讓讀者更易理解東西藝術交流的歷史及相互交流所帶來之的影響等。
或許有讀者會問,為何要閱讀一本由西方學者所寫的中國藝術史?難道沒有中文的同類著作嗎?我的回答是,這涉及研究方法的問題,因為傳統的中文作者, 習慣用「文字」來處理「圖像」的歷史,總是從師承、生平、作品目錄及文字紀錄著手。但西方訓練有素的藝術史學者建構的是「圖像」的歷史,圖像自有其歷史,如果不熟悉圖像的歷史,如何撰寫一部藝術史呢?圖像的分析有其方法和技巧,蘇立文此書,並沒有太涉及嚴謹的結構分析理論,但做到了一般的形式及風格分析,相信很容易為讀者所接受與理解。而就廣度與完整度而言,蘇立文的這本《中國藝術史》仍是目前為止,認識中國藝術的各個時代和各個領域最佳,也最值得推薦的一本工具書。
最後,我說明一下本書的修訂是基於原譯,但我秉著兩個原則:一、必須根據原作不能曲解,二、必須忠於專業,所以不得不做大幅度的修正。另外,我對原作舉例米友仁作品時,有不同之見解,遂以作註方式附上個人認為較合適的米友仁代表作,以及蘇立文教授認為宋代書法的主要影響為「王羲之與隸書」,與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也作註附上「王羲之、顏真卿與鍾繇」,謹供讀者參考,一併說明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