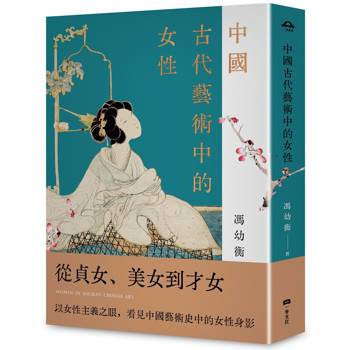女性與中國傳統繪畫瑣談(節錄)
性別研究與女性主義在西方世界蔚為風氣,早已行之有年。在美國的校園裡,結合性別研究與藝術史的課程,不但是藝術史系中一定會出現的選項,更是熱門而廣受學生歡迎的課程。但是這類課程在臺灣並不多見,尤其以女性主義角度看中國藝術史更是鮮見,可能因為中文世界對性別研究不似西方世界早已累積多年的歷史及深厚的基礎,因此結合藝術史的研究也就乏人嘗試。
筆者曾在大學開設「性別研究與傳統中國藝術」的課程,除了以西方漢學界已經開拓的對傳統中國女性的研究為基礎外,也結合歷代的藝術史發展,希望能為藝術史的研究,在傳統的角度之外,開啟一扇新的視窗。
在性別研究與傳統中國藝術方面有開疆拓土之功的首推魏瑪莎(Marsha Weidner,一九四五─)教授,她於一九八八年籌畫了一項傳統中國女畫家的畫展,在全美東西岸四大博物館展出,並為此展出版了一本目錄《玉臺縱覽:中國女畫家1300 –1912》(Views from Jade Terrace: Chinese Women Artists 1300–1912)。在此書中,她針對中國女畫家的社會背景及歷史定位作了詳盡的剖析。魏氏首先為西方讀者介紹中國藝術史上獨特的現象—文人畫,並指出若非藝事成為士大夫階級的娛樂,而係全由職業畫家包辦的話,女性畫家能嶄露頭角的機會微乎其微矣。因為傳統女性一向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而文人階級提供了一種在自己家庭裡也可以「游於藝」的方式,讓女性的才藝得以發揮。
相較之下,中國傳統女畫家所面對的障礙,比起西方有志於繪畫的女性要少很多。因為西方女性經常面臨學院制度的排斥,種種限制使得女性不得其門而入,接受和男性一般嚴謹的訓練。而中國女性則幸運得多,她們不但和其父兄配偶一樣,可以終生浸淫於此,還可以靠家庭與社會的網絡傳播,得到名聲與揄揚。只是魏氏也指出,中國傳統女畫家終究仍然只是傳統的延續者而非傳統的創造者。究其原因,自然還是由於傳統社會父權主義的思想作祟。不但纏足的習俗使得傳統婦女的行動受限,女性的活動完全被排除於公領域之外,並且以自我犧牲及柔弱為美德的觀念,則使得女性的思想也受到禁錮。這些情況都讓傳統女性無論在心理與知識上無法和男性一較高下,取得一代宗師的地位。
至於中國傳統女畫家的生平,經常可在歷代墓誌銘、叢書、地方誌、收藏家目錄等處找到,記載中必定附有女畫家丈夫的姓名,就像介紹男性畫家時一定會提到他所任的官職一樣。但是這些記載大都抄來抄去,行文是刻板和陳套的敘述,不過提一下她的籍貫、師友、畫作的題材與風格,或是她的美德、美貌、名氣等等浮泛之詞。即便有她同時代作者所作的記述,也很難讓人從中得知畫家本人的個性與她在真實人生中的遭遇。相形之下,男性畫家自傳雖也公式化,但有關他們的記載卻詳盡得多,此外男性參加科考、任官、旅遊、退休都會在官方記錄或私人寫作中留下痕跡。女畫家在這方面是相形見絀的,她的傳記中既沒有突出的事件也無鮮明的個性;即便是藉著母以子貴或因德行、才華出眾而得以傳世者,也依舊僅是歷史巨流中的一個小小註腳而已。
在一般畫史中或依朝代列舉的著作中,總是最先介紹皇室成員,然後是各個主流的團體,最後才輪到方外(和尚)、異域人及女性。即便畫家依姓氏及特長而區分,女性也永遠被置於每一種畫家的最後。
明清之際,女性識字率大增,女畫家的人數也激增。從文字記載中,呈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女畫家典型:一是明末才子冒襄(一六一一─一六九三,字辟疆,號巢民)所著的︿影梅菴憶語﹀中,把他的姬人董小宛(白;一六二四─一六五一)描繪成既美麗又有才華、溫柔又服從的愛人兼知己,還是心甘情願地伺候他母親、元配、妹妹們的奴隸。在這份不乏理想化色彩的回憶中,才貌雙全的女畫家與才子結合成為神仙伴侶,他們的生活中充滿了浪漫、詩情與藝術。相對地,另一種敘述則勾勒出一幅作為服從的女兒、柔順的妻子、自我犧牲的母親、貞潔的寡婦的形象。比如說,乾隆皇帝的重臣錢陳群(一六八六─一七七四)為他母親陳書(一六六○─一七三六)所作的傳記便是最好的代表。董小宛作為一代青樓名妓,又青春早逝,自然成為形象浪漫的女主角;而陳書出身世家,育有三子,活了七十六歲,也必然化為他兒子筆下儒家美德的典範。錢陳群不厭其煩地詳述其母良好的出身教養、對長輩孝順、對子女無怨無悔的付出,以及在油燈前一面織布、一面課子的畫面,反而她今日受人所重視的繪畫才華沒並有得到太多的著墨。
至於繪畫題材對女性倒是沒有太多限制,所有的傳統中國繪畫題材:人物、山水、花鳥、界畫、畜獸都對女性畫家開放。男性所使用的任何繪畫題材,對女性而言沒有不合適或太困難的問題,她們不曾面對西方女畫家所面對的困擾,因為西方藝術以人體描繪為大宗,而社會的設限使得她們無法得到從事此項具挑戰性的題材所必須的訓練。
人像畫在女畫家大量出現時,已成為中國歷史上次要的繪畫題材。宋代以後,一流的男畫家紛紛將主要的創造力發揮在山水畫上。而且中國女畫家即使對人像畫有興趣,也不必像西方女畫家必須面對裸體人像的問題。可以說,山水畫之於中國女畫家,就有如裸體人像之於西方女畫家,成為東西女畫家的罩門。山水與裸體人像,兩者既是東西藝術中極重要的題材,但又因為社會的禁忌,使得女性難以和男性站在相同的立足點上,一較高下。西方女畫家因為無法接觸裸體模特兒,因而使得她們描繪人體的功力,在歷史上很長的一個階段裡,無法和男性畫家相提並論。而中國女性則因纏足的關係,既無體力探訪名山勝水,深宅大院的禁錮也阻絕了她們對外面世界的觀察。
所幸,畫山水並不一定需要有和自然直接接觸的一手經驗。女性畫家仍可像明清時期的男畫家一樣,經由臨摹古人的作品、或從《芥子園畫譜》中習得作畫的方法。如陳書就畫得一手元四大家之一王蒙式的山水,使得她足以與同時代的正統派畫家齊名。
明清畫花鳥的女畫家為數眾多,不但因為長久以來,在文學篇章及詩句中,女子與花卉的聯想和比喻關係早就根深柢固,也因為商業市場的需要。很多女畫家都是得自家學,如十八世紀兩位出色而多產的惲冰(活動於一六九二─一七四二)及馬筌(活動於十八世紀上半)都是,她們並不是因為本身女性的傾向而喜歡花鳥,而是因男性家長為著名花鳥畫家的關係。惲冰是惲壽平(一六三三─一六九○)的曾孫女,而馬筌則是馬元馭(一六六九─一七二二)之女。
女畫家之能成名多半也要靠男性的揄揚,不管畫家是青樓女子或大家閨秀,若想使自己的作品超出地域性的限制或留諸後世,就得仰賴具影響力的男性為之宣傳。如陳書便是一例,她的作品雖在生前她所居住的地區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但若非她的兒子錢陳群和她的學生張庚(一六八五─一七六○)的關係,她不可能有今天的能見度。錢陳群不斷地向乾隆皇帝推薦其母的繪畫作品,終於使得陳書的畫作成為清代皇室收藏中數目最多的女性畫家作品。張庚則在他有關清前期畫史的《國朝畫徵錄》中收錄了陳書的傳記。
男性藝術史家及評論家在討論女性畫家時,使用的是和形容男性畫家差不多的傳統方式:她們家學淵源、自小是神童、作品有大師之風、前朝大畫家的化身、筆底驚風雨、畫作可居妙品逸品等等,偶爾也有開一代新風氣的評語。除此之外,也有些針對女性而發的觀察,如錢大昕(一七二八─一八○四)稱善人物畫的仇氏為「女性中的李公麟(宋代文人畫家)」,畫評家也經常用雅、淡、純、淨、纖等詞藻形容女性作品。王文治(一七三○─一八○二)稱文俶(一五九五─一六三四)的畫一看就知道是出於女性之手,還說即使男性大師也無法複製她的作品。她的傳人必須是女性,如駱綺蘭(一七五六─一八二○)及王玉燕(活動於十八世紀晚期)等。
另一種評語則不免有性別歧視的意味。如秦祖永《桐蔭論畫》,介紹陳書時竟稱「閨秀筆墨非板即弱,南樓老人(陳書)庶幾得中。」明代出身金陵(南京)的妓女林奴兒被評為「筆力雖未至,亦女流所難得。」這些傳統評論的口氣,以及女性畫家總是被置於畫史最後一隅的現象,使得近代西方學者對中國傳統女性畫家採取了輕忽的態度。喜龍仁(Osvald Sirén)於一九五六至五八年間出版的《中國繪畫:大師與原則》(Chinese Painting: 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s)一書中討論明清繪畫時,大概覺得只有青樓女子值得一提,他如此形容名妓薛素素(約一五七五─一六五三)的作品:「很難讓人想像是出於女性之手。」其餘閨秀畫家即使繪畫成就與薛相當,但如果生平較為平淡就被忽略或草草帶過。另外,西方傳教士、旅行家,以及西方人有關東方的敘述總向讀者傳達中國女性被壓抑及無知的形象,使得上述情況更加嚴重。還有中國女性畫家大半精熟於花鳥畫,但花鳥在中國的地位遠比在西方為高;而且中國女性畫家大多活躍於明清時期,而西方學者先前總認為這是中國藝術由盛而衰的時期,不值得認真考慮。種種原因延遲了他們對中國女性畫家的研究。
可是如果女性畫家只是中國藝術史的弱勢和非主流,而且從未取得大師級的地位,為何我們還要如此大費周章地去研究她們?魏氏的答案是我們應有更寬廣的思考,而不必自限於傳統的狹隘觀點—即藝術史乃以某種特定形式、題材表現出一系列偉大的作品的歷史。中國的女畫家和歐美女畫家一樣,當然是值得研究的對象,因為她們創造出優美的作品,且成為其文化中重要的資產。而經過西方學者近年來的披荊斬棘,他們對西方女性畫家的研究成果,實為我們今日欲研究中國的女畫家者鋪路,使我們在研究方向與方法上皆有前例可循。
性別研究與女性主義在西方世界蔚為風氣,早已行之有年。在美國的校園裡,結合性別研究與藝術史的課程,不但是藝術史系中一定會出現的選項,更是熱門而廣受學生歡迎的課程。但是這類課程在臺灣並不多見,尤其以女性主義角度看中國藝術史更是鮮見,可能因為中文世界對性別研究不似西方世界早已累積多年的歷史及深厚的基礎,因此結合藝術史的研究也就乏人嘗試。
筆者曾在大學開設「性別研究與傳統中國藝術」的課程,除了以西方漢學界已經開拓的對傳統中國女性的研究為基礎外,也結合歷代的藝術史發展,希望能為藝術史的研究,在傳統的角度之外,開啟一扇新的視窗。
在性別研究與傳統中國藝術方面有開疆拓土之功的首推魏瑪莎(Marsha Weidner,一九四五─)教授,她於一九八八年籌畫了一項傳統中國女畫家的畫展,在全美東西岸四大博物館展出,並為此展出版了一本目錄《玉臺縱覽:中國女畫家1300 –1912》(Views from Jade Terrace: Chinese Women Artists 1300–1912)。在此書中,她針對中國女畫家的社會背景及歷史定位作了詳盡的剖析。魏氏首先為西方讀者介紹中國藝術史上獨特的現象—文人畫,並指出若非藝事成為士大夫階級的娛樂,而係全由職業畫家包辦的話,女性畫家能嶄露頭角的機會微乎其微矣。因為傳統女性一向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而文人階級提供了一種在自己家庭裡也可以「游於藝」的方式,讓女性的才藝得以發揮。
相較之下,中國傳統女畫家所面對的障礙,比起西方有志於繪畫的女性要少很多。因為西方女性經常面臨學院制度的排斥,種種限制使得女性不得其門而入,接受和男性一般嚴謹的訓練。而中國女性則幸運得多,她們不但和其父兄配偶一樣,可以終生浸淫於此,還可以靠家庭與社會的網絡傳播,得到名聲與揄揚。只是魏氏也指出,中國傳統女畫家終究仍然只是傳統的延續者而非傳統的創造者。究其原因,自然還是由於傳統社會父權主義的思想作祟。不但纏足的習俗使得傳統婦女的行動受限,女性的活動完全被排除於公領域之外,並且以自我犧牲及柔弱為美德的觀念,則使得女性的思想也受到禁錮。這些情況都讓傳統女性無論在心理與知識上無法和男性一較高下,取得一代宗師的地位。
至於中國傳統女畫家的生平,經常可在歷代墓誌銘、叢書、地方誌、收藏家目錄等處找到,記載中必定附有女畫家丈夫的姓名,就像介紹男性畫家時一定會提到他所任的官職一樣。但是這些記載大都抄來抄去,行文是刻板和陳套的敘述,不過提一下她的籍貫、師友、畫作的題材與風格,或是她的美德、美貌、名氣等等浮泛之詞。即便有她同時代作者所作的記述,也很難讓人從中得知畫家本人的個性與她在真實人生中的遭遇。相形之下,男性畫家自傳雖也公式化,但有關他們的記載卻詳盡得多,此外男性參加科考、任官、旅遊、退休都會在官方記錄或私人寫作中留下痕跡。女畫家在這方面是相形見絀的,她的傳記中既沒有突出的事件也無鮮明的個性;即便是藉著母以子貴或因德行、才華出眾而得以傳世者,也依舊僅是歷史巨流中的一個小小註腳而已。
在一般畫史中或依朝代列舉的著作中,總是最先介紹皇室成員,然後是各個主流的團體,最後才輪到方外(和尚)、異域人及女性。即便畫家依姓氏及特長而區分,女性也永遠被置於每一種畫家的最後。
明清之際,女性識字率大增,女畫家的人數也激增。從文字記載中,呈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女畫家典型:一是明末才子冒襄(一六一一─一六九三,字辟疆,號巢民)所著的︿影梅菴憶語﹀中,把他的姬人董小宛(白;一六二四─一六五一)描繪成既美麗又有才華、溫柔又服從的愛人兼知己,還是心甘情願地伺候他母親、元配、妹妹們的奴隸。在這份不乏理想化色彩的回憶中,才貌雙全的女畫家與才子結合成為神仙伴侶,他們的生活中充滿了浪漫、詩情與藝術。相對地,另一種敘述則勾勒出一幅作為服從的女兒、柔順的妻子、自我犧牲的母親、貞潔的寡婦的形象。比如說,乾隆皇帝的重臣錢陳群(一六八六─一七七四)為他母親陳書(一六六○─一七三六)所作的傳記便是最好的代表。董小宛作為一代青樓名妓,又青春早逝,自然成為形象浪漫的女主角;而陳書出身世家,育有三子,活了七十六歲,也必然化為他兒子筆下儒家美德的典範。錢陳群不厭其煩地詳述其母良好的出身教養、對長輩孝順、對子女無怨無悔的付出,以及在油燈前一面織布、一面課子的畫面,反而她今日受人所重視的繪畫才華沒並有得到太多的著墨。
至於繪畫題材對女性倒是沒有太多限制,所有的傳統中國繪畫題材:人物、山水、花鳥、界畫、畜獸都對女性畫家開放。男性所使用的任何繪畫題材,對女性而言沒有不合適或太困難的問題,她們不曾面對西方女畫家所面對的困擾,因為西方藝術以人體描繪為大宗,而社會的設限使得她們無法得到從事此項具挑戰性的題材所必須的訓練。
人像畫在女畫家大量出現時,已成為中國歷史上次要的繪畫題材。宋代以後,一流的男畫家紛紛將主要的創造力發揮在山水畫上。而且中國女畫家即使對人像畫有興趣,也不必像西方女畫家必須面對裸體人像的問題。可以說,山水畫之於中國女畫家,就有如裸體人像之於西方女畫家,成為東西女畫家的罩門。山水與裸體人像,兩者既是東西藝術中極重要的題材,但又因為社會的禁忌,使得女性難以和男性站在相同的立足點上,一較高下。西方女畫家因為無法接觸裸體模特兒,因而使得她們描繪人體的功力,在歷史上很長的一個階段裡,無法和男性畫家相提並論。而中國女性則因纏足的關係,既無體力探訪名山勝水,深宅大院的禁錮也阻絕了她們對外面世界的觀察。
所幸,畫山水並不一定需要有和自然直接接觸的一手經驗。女性畫家仍可像明清時期的男畫家一樣,經由臨摹古人的作品、或從《芥子園畫譜》中習得作畫的方法。如陳書就畫得一手元四大家之一王蒙式的山水,使得她足以與同時代的正統派畫家齊名。
明清畫花鳥的女畫家為數眾多,不但因為長久以來,在文學篇章及詩句中,女子與花卉的聯想和比喻關係早就根深柢固,也因為商業市場的需要。很多女畫家都是得自家學,如十八世紀兩位出色而多產的惲冰(活動於一六九二─一七四二)及馬筌(活動於十八世紀上半)都是,她們並不是因為本身女性的傾向而喜歡花鳥,而是因男性家長為著名花鳥畫家的關係。惲冰是惲壽平(一六三三─一六九○)的曾孫女,而馬筌則是馬元馭(一六六九─一七二二)之女。
女畫家之能成名多半也要靠男性的揄揚,不管畫家是青樓女子或大家閨秀,若想使自己的作品超出地域性的限制或留諸後世,就得仰賴具影響力的男性為之宣傳。如陳書便是一例,她的作品雖在生前她所居住的地區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但若非她的兒子錢陳群和她的學生張庚(一六八五─一七六○)的關係,她不可能有今天的能見度。錢陳群不斷地向乾隆皇帝推薦其母的繪畫作品,終於使得陳書的畫作成為清代皇室收藏中數目最多的女性畫家作品。張庚則在他有關清前期畫史的《國朝畫徵錄》中收錄了陳書的傳記。
男性藝術史家及評論家在討論女性畫家時,使用的是和形容男性畫家差不多的傳統方式:她們家學淵源、自小是神童、作品有大師之風、前朝大畫家的化身、筆底驚風雨、畫作可居妙品逸品等等,偶爾也有開一代新風氣的評語。除此之外,也有些針對女性而發的觀察,如錢大昕(一七二八─一八○四)稱善人物畫的仇氏為「女性中的李公麟(宋代文人畫家)」,畫評家也經常用雅、淡、純、淨、纖等詞藻形容女性作品。王文治(一七三○─一八○二)稱文俶(一五九五─一六三四)的畫一看就知道是出於女性之手,還說即使男性大師也無法複製她的作品。她的傳人必須是女性,如駱綺蘭(一七五六─一八二○)及王玉燕(活動於十八世紀晚期)等。
另一種評語則不免有性別歧視的意味。如秦祖永《桐蔭論畫》,介紹陳書時竟稱「閨秀筆墨非板即弱,南樓老人(陳書)庶幾得中。」明代出身金陵(南京)的妓女林奴兒被評為「筆力雖未至,亦女流所難得。」這些傳統評論的口氣,以及女性畫家總是被置於畫史最後一隅的現象,使得近代西方學者對中國傳統女性畫家採取了輕忽的態度。喜龍仁(Osvald Sirén)於一九五六至五八年間出版的《中國繪畫:大師與原則》(Chinese Painting: 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s)一書中討論明清繪畫時,大概覺得只有青樓女子值得一提,他如此形容名妓薛素素(約一五七五─一六五三)的作品:「很難讓人想像是出於女性之手。」其餘閨秀畫家即使繪畫成就與薛相當,但如果生平較為平淡就被忽略或草草帶過。另外,西方傳教士、旅行家,以及西方人有關東方的敘述總向讀者傳達中國女性被壓抑及無知的形象,使得上述情況更加嚴重。還有中國女性畫家大半精熟於花鳥畫,但花鳥在中國的地位遠比在西方為高;而且中國女性畫家大多活躍於明清時期,而西方學者先前總認為這是中國藝術由盛而衰的時期,不值得認真考慮。種種原因延遲了他們對中國女性畫家的研究。
可是如果女性畫家只是中國藝術史的弱勢和非主流,而且從未取得大師級的地位,為何我們還要如此大費周章地去研究她們?魏氏的答案是我們應有更寬廣的思考,而不必自限於傳統的狹隘觀點—即藝術史乃以某種特定形式、題材表現出一系列偉大的作品的歷史。中國的女畫家和歐美女畫家一樣,當然是值得研究的對象,因為她們創造出優美的作品,且成為其文化中重要的資產。而經過西方學者近年來的披荊斬棘,他們對西方女性畫家的研究成果,實為我們今日欲研究中國的女畫家者鋪路,使我們在研究方向與方法上皆有前例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