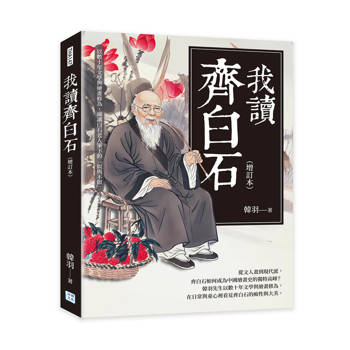「半」字,大有文章
你看,「一城山色半城湖」,「半」字在這裡忽然大了起來;「半畝方塘一鑑開」,「半」字在這裡又忽然小了起來。
你再看,「雲髻半偏新睡覺」,雲髻僅只「半」偏,竟將那嬌柔慵懶、睡眼惺忪的樣子活現了出來。
「猶抱琵琶半遮面」,遮住了這裡,露出了那裡,依違之間,羞澀之狀,逗人想像,足夠咀嚼半天的了。
元代散曲家,一眼瞅中了這個「半」字,將其作為曲牌,名「一半兒」。關漢卿對「一半兒」就頗感興趣,且讀其曲:「多情多緒小冤家,迤逗得人來憔悴煞,說來的話先瞞過咱。怎知他,一半兒真實一半兒假。」一個「半」字,竟將那痴情人的痴樣忽斂忽縱搖曳生姿起來。
王維詩「山色有無中」,字裡行間不見「半」字,實是仍在「半」上做文章。又「有」又「無」,不亦各占一半乎!於是山色空蒙也,天地浩渺也,興人感慨也。
白石老人也曾就「半」字作畫,〈稻束小雞〉一畫中就有個半拉身子的小雞。且莫小瞧這小雞,雖然畫上已有了八九隻小雞,唯牠才是這畫的「畫眼」(詩有「詩眼」,畫也當有「畫眼」)。因為恰是牠的那半拉身子(另半拉身子被稻束遮住了)給了人們暗示——稻束後面可能還有小雞。不僅使人們看到了稻束的前面,又使人們想到了稻束的後面,使畫面的有限空間擴展成了畫面的無限空間。
「似與不似」絮語
讀《齊白石研究》,見有一段文字,抄錄如下:「『似與不似之間』者,本來是董其昌的話頭,所謂『太似不得,不似亦不得』,要處於『似與不似之間』是也。而後,惲壽平接過這個話茬,所謂『其似則近俗,不似則離形』是也。但集大成的,還是王文治。王文治在觀賞了董其昌的臨古帖後題道:『其似與不似之間,乃是一大入處。似者,踐其形也;不似者,符其神也。形與神在若接若不接之間,而真消息出焉。』」我聽到「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這句話,是在一九五○年代。有的說是齊白石說的,有的說齊白石之前也有人說過類似的話,秋風過耳,未深推求。
董其昌除了「似與不似之間」的話頭,還有「生與熟」。所謂「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畫須熟外熟」,像繞口令,難得其要領。
鄭板橋將「生與熟」講得就辯證了些,「畫到生時是熟時」,謂為生和熟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往相反方向轉化。較之董其昌,後來居上。
俄國的什克洛夫斯基,也看到了「生」是個好字眼,說「藝術的技巧就是使物件陌生」。只是「陌生」行嗎?人們看得懂嗎?不如再加個「熟」字,「又生又熟」,既新奇而又親切。
朱光潛將「似與不似」改換成了「不離不即」,謂詩與現實生活的關係保持「不離」,是為了有真實感;保持「不即」,是為了有新奇感。
以上摘引,應說是「語錄」。既為「語錄」,要言不煩,然而隻言片語,難免詞意含混。「似與不似」可作「像與不像」解,可作「形與神」解,可作「意象」解,可作「熟與生」解,也可作「不離不即」解,量身裁衣,視其語境而定。要之,是「之間」的「間」。這個「間」,是恰到好處,「過猶不及」,既不「過」,也不「不及」,做到這一步,真真要看作者的藝術修養功夫了。
「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就字面上看,似是繪畫之法,遠非如此,實是已關聯到作品與欣賞、作者與讀者兩相互動的更深層面,由「技」而「道」了。
已是老生常談,一件藝術作品的完成,是作者和讀者的共同合作。作者的作品,只是完成了創造的一半,另一半則依賴於讀者的再創造。打個比喻,作者的作品只是個「場地」,給讀者的想像力提供充足的活動空間,而讀者則以自己的生活經驗的聯想與作品的暗示相互動,兩相默契,如珠之旋轉於盤而不出於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既是欣賞活動過程,也是藝術作品的完成過程。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的「間」,也就是讀者的想像力馳騁的活動空間。
是、似同音,但「是」不如「似」對人們更有吸引力。「是雨亦無奇,如雨乃可樂」,真物引不起人們關注,不是那物又似那物,才能引起人們的好奇。更有意思的是清人張潮的話:「情必近於痴而始真。」、「近於」也就是「似」,不能真痴,也不能不痴,而是似痴,情乃見真。你看這「似」字有沒有神韻?《藝概》:「東坡〈水龍吟〉起云:『似花還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詞評語,蓋不離不即也。」不離不即,疑似之際,而真消息出焉。齊白石的「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就是「似」,而不是「是」,這話雖不是他首創,但自古迄今明此理的畫家多矣,而能以天才的多樣的繪畫典範驗證之發揚之者,首推齊白石。
「似乎」妙哉
郎紹君著《齊白石研究》,書中有一幅齊白石畫的童趣盎然的〈棕櫚小雞〉,其文字概述是:「一棵棕櫚下,五隻小雞圍住一隻蟈蟈,小雞似乎並不吃牠,只是驚奇於牠是誰,來自何方;蟈蟈伸直觸鬚,挺著後腿,似要跳逃的樣子。」讀後,欣然拍案:「哇哈,『所見略同』,我亦『英雄』乎。」文中用了「似乎」二字,「似乎」者,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不定語也。看那「五隻小雞圍住一隻蟈蟈」,瞪大著眼睛,以人的生活經驗來判斷,不是「驚奇於牠是誰」的好奇心又是什麼;可是小雞有人一樣的腦子、人一樣的好奇心嗎?只有天知道。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於是只能「似乎」了。豈料正是這「似乎」,生發出了小雞與蟈蟈之間的戲劇性。看到蟈蟈都要「驚奇」,定當是啥都不懂的孩子,恍兮惚兮,小雞不也有了孩子氣。而這帶有孩子氣的小雞,比起不是小雞的真的孩子更逗引人,更耐人玩味。何哉?「是雨亦無奇,如雨乃可樂」也。
齊白石曾說過「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畫壇中人,人人皆知,未必人人能解,我就不敢言說「能解」。看了〈棕櫚小雞〉,有點開竅了,畫中的五隻小雞讓我們感到的「似乎」,不正是「似與不似」之妙?
你看,「一城山色半城湖」,「半」字在這裡忽然大了起來;「半畝方塘一鑑開」,「半」字在這裡又忽然小了起來。
你再看,「雲髻半偏新睡覺」,雲髻僅只「半」偏,竟將那嬌柔慵懶、睡眼惺忪的樣子活現了出來。
「猶抱琵琶半遮面」,遮住了這裡,露出了那裡,依違之間,羞澀之狀,逗人想像,足夠咀嚼半天的了。
元代散曲家,一眼瞅中了這個「半」字,將其作為曲牌,名「一半兒」。關漢卿對「一半兒」就頗感興趣,且讀其曲:「多情多緒小冤家,迤逗得人來憔悴煞,說來的話先瞞過咱。怎知他,一半兒真實一半兒假。」一個「半」字,竟將那痴情人的痴樣忽斂忽縱搖曳生姿起來。
王維詩「山色有無中」,字裡行間不見「半」字,實是仍在「半」上做文章。又「有」又「無」,不亦各占一半乎!於是山色空蒙也,天地浩渺也,興人感慨也。
白石老人也曾就「半」字作畫,〈稻束小雞〉一畫中就有個半拉身子的小雞。且莫小瞧這小雞,雖然畫上已有了八九隻小雞,唯牠才是這畫的「畫眼」(詩有「詩眼」,畫也當有「畫眼」)。因為恰是牠的那半拉身子(另半拉身子被稻束遮住了)給了人們暗示——稻束後面可能還有小雞。不僅使人們看到了稻束的前面,又使人們想到了稻束的後面,使畫面的有限空間擴展成了畫面的無限空間。
「似與不似」絮語
讀《齊白石研究》,見有一段文字,抄錄如下:「『似與不似之間』者,本來是董其昌的話頭,所謂『太似不得,不似亦不得』,要處於『似與不似之間』是也。而後,惲壽平接過這個話茬,所謂『其似則近俗,不似則離形』是也。但集大成的,還是王文治。王文治在觀賞了董其昌的臨古帖後題道:『其似與不似之間,乃是一大入處。似者,踐其形也;不似者,符其神也。形與神在若接若不接之間,而真消息出焉。』」我聽到「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這句話,是在一九五○年代。有的說是齊白石說的,有的說齊白石之前也有人說過類似的話,秋風過耳,未深推求。
董其昌除了「似與不似之間」的話頭,還有「生與熟」。所謂「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畫須熟外熟」,像繞口令,難得其要領。
鄭板橋將「生與熟」講得就辯證了些,「畫到生時是熟時」,謂為生和熟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往相反方向轉化。較之董其昌,後來居上。
俄國的什克洛夫斯基,也看到了「生」是個好字眼,說「藝術的技巧就是使物件陌生」。只是「陌生」行嗎?人們看得懂嗎?不如再加個「熟」字,「又生又熟」,既新奇而又親切。
朱光潛將「似與不似」改換成了「不離不即」,謂詩與現實生活的關係保持「不離」,是為了有真實感;保持「不即」,是為了有新奇感。
以上摘引,應說是「語錄」。既為「語錄」,要言不煩,然而隻言片語,難免詞意含混。「似與不似」可作「像與不像」解,可作「形與神」解,可作「意象」解,可作「熟與生」解,也可作「不離不即」解,量身裁衣,視其語境而定。要之,是「之間」的「間」。這個「間」,是恰到好處,「過猶不及」,既不「過」,也不「不及」,做到這一步,真真要看作者的藝術修養功夫了。
「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就字面上看,似是繪畫之法,遠非如此,實是已關聯到作品與欣賞、作者與讀者兩相互動的更深層面,由「技」而「道」了。
已是老生常談,一件藝術作品的完成,是作者和讀者的共同合作。作者的作品,只是完成了創造的一半,另一半則依賴於讀者的再創造。打個比喻,作者的作品只是個「場地」,給讀者的想像力提供充足的活動空間,而讀者則以自己的生活經驗的聯想與作品的暗示相互動,兩相默契,如珠之旋轉於盤而不出於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既是欣賞活動過程,也是藝術作品的完成過程。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的「間」,也就是讀者的想像力馳騁的活動空間。
是、似同音,但「是」不如「似」對人們更有吸引力。「是雨亦無奇,如雨乃可樂」,真物引不起人們關注,不是那物又似那物,才能引起人們的好奇。更有意思的是清人張潮的話:「情必近於痴而始真。」、「近於」也就是「似」,不能真痴,也不能不痴,而是似痴,情乃見真。你看這「似」字有沒有神韻?《藝概》:「東坡〈水龍吟〉起云:『似花還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詞評語,蓋不離不即也。」不離不即,疑似之際,而真消息出焉。齊白石的「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就是「似」,而不是「是」,這話雖不是他首創,但自古迄今明此理的畫家多矣,而能以天才的多樣的繪畫典範驗證之發揚之者,首推齊白石。
「似乎」妙哉
郎紹君著《齊白石研究》,書中有一幅齊白石畫的童趣盎然的〈棕櫚小雞〉,其文字概述是:「一棵棕櫚下,五隻小雞圍住一隻蟈蟈,小雞似乎並不吃牠,只是驚奇於牠是誰,來自何方;蟈蟈伸直觸鬚,挺著後腿,似要跳逃的樣子。」讀後,欣然拍案:「哇哈,『所見略同』,我亦『英雄』乎。」文中用了「似乎」二字,「似乎」者,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不定語也。看那「五隻小雞圍住一隻蟈蟈」,瞪大著眼睛,以人的生活經驗來判斷,不是「驚奇於牠是誰」的好奇心又是什麼;可是小雞有人一樣的腦子、人一樣的好奇心嗎?只有天知道。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於是只能「似乎」了。豈料正是這「似乎」,生發出了小雞與蟈蟈之間的戲劇性。看到蟈蟈都要「驚奇」,定當是啥都不懂的孩子,恍兮惚兮,小雞不也有了孩子氣。而這帶有孩子氣的小雞,比起不是小雞的真的孩子更逗引人,更耐人玩味。何哉?「是雨亦無奇,如雨乃可樂」也。
齊白石曾說過「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畫壇中人,人人皆知,未必人人能解,我就不敢言說「能解」。看了〈棕櫚小雞〉,有點開竅了,畫中的五隻小雞讓我們感到的「似乎」,不正是「似與不似」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