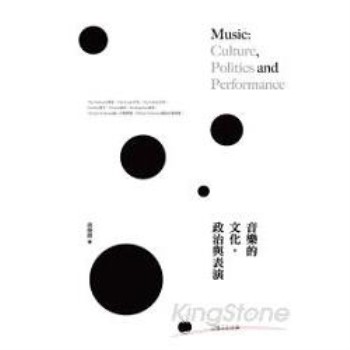作為歌劇裡主要論述的對象,「馬偕博士」在台灣史上具備多重的文化符號,包括他早期引進西方文明、設立學堂暨醫院,成為台灣與西方接觸的歷史證據,不僅如此,這位加拿大長老教會牧師所屬的宗派對台灣民主運動的社會性譬喻,馬偕留給台灣的「遺產」(legacy),於此時此地成為文化製作主題,本身就是一套政權對於傳統記憶的選擇(selection)(借Williams話語),以至於當我們回歸Bourdieu的國家政權�社會空間場域來看,這部劇目文化「選擇」,剛好收編了台灣近程浮出的全球化與在地化課題,並在時空的偶然性裡(contingency),成為一組「選擇」。
作曲家金希文在回憶創作「馬偕」始末時曾提及,由於深感「音樂會與社會脫節」,本身是教友他自2000年始以「馬偕」作為題材創作,不過歷經「許多基金會、企業打了退票」後,轉投向文建會,獲甫接文建會主委、同為音樂家出身的陳郁秀支持,不過這項作品在陳郁秀離開文建會便「淒涼地束之高閣」(陳郁秀,2008),直到2007年陳郁秀轉任中正文化中心董事長,才又獲得演出機會。陳郁秀在首演的專書上以「來自原鄉文化,成就時尚經典」為文,感性地自述她自16歲的北一女少女時期遠赴法國巴黎高等音樂院,卻面臨無從介紹「自己國家的音樂」,因而發心「補修台灣學分」。她以「原鄉」暗示由「文化脈絡、生活型態、風土人文長時間累積出來的經驗、知覺和關懷」,而以「時尚」意指「當代國際趨勢、國際語言、國際品質,它透過當代新科技、新技術、新創意,傳遞昇華出生活哲學及美學風格」,兩種作為她的文化製作主論述,她盼透過《福爾摩莎信簡-黑鬚馬偕》,將由更多人從「原鄉土地」汲取靈感,「讓現在的創作,成為當下的時尚符碼,進而為明日留下經典」(藍麗娟,2004;陳郁秀,2008)。
時空的「偶然性」,導致我們無法處理,若非經歷政黨輪替,或者以陳郁秀歷任台灣師大音樂系教授、藝術學院院長、文建會主委、國家文化總會秘書長及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董事長的身分(呂鈺秀,2008;藍麗娟,2004),在古典音樂場域、文化場域乃至於在政黨輪替後由民進黨主政的國家政權�社會空間場域,所扮演之相當特殊的多重身分;我們其實不確定金希文的創作能否躍上展演舞台,但時空的場域性帶我們進入一項反思性的視野,意即文化的選擇與場域的關係不但是一組結構中的結構,同時也是結構後的「結構」。
同樣地,陳郁秀的文化製作論述「原鄉�時尚」,亦透過《快雪時晴》作為文化劇目展示。《快雪時晴》的製作構想始於吳靜吉任國立中正中正文中心董事長、平珩任藝術總監時期,在陳郁秀任內完成。《快雪時晴》是少見橫跨國家京劇團(國光劇團)與國家交響樂團兩個不同藝術領域的合力之作,創作文本以台北故宮鎮館之寶王羲之名作《快雪時晴帖》作為想像出發,時空跳接了三個從古至今的歷史聚合,包括1949年來台外省族群的離散(diaspora)經驗,透過「哪兒疼咱,哪兒就是咱的家啊」(施如芳,2007)來建構外省族群在台灣的新身分認同。因此,作為文化劇目,它透過京劇與交響樂團的合作,展現它在類型上的「混雜性」(hybridity);透過故宮鎮館之寶《快雪時晴帖》從「唐太宗的昭陵、南宋的秦准河之客舟、清乾隆帝的三希堂,來到台北的故宮」的流散(施如芳,2007),召喚「懷舊」(nostalgia),亦通過地理區域的中國到台灣的「離散」(diaspora),用以構連台灣作為「想像共同體」的時代情緒。當時的中正文化中心藝術總監楊其文(2008)曾為文指出,故事裡一對兒子分別投入對立的陣營,以及歷經征戰後離散他鄉的認同矛盾,「反映的就是一份存在台灣社會中分裂的事實」,他認為該劇寫盡從「夢鄉到原鄉到故鄉到家鄉的心路歷程」,應該是台灣人「認清何處是故鄉的必要旅程」。
《很久沒有敬我了你》則是「台灣認同三部曲」裡,唯一書寫「當代生活」的製作,以台北的漢人音樂總監來到台東卑南尋根,意外認識原住民文化為起點,三者主題不一,但背後創作意理明顯以台灣身分認同的基底,就形式上,它涉及了包括外省、閩南、原住民三大族群的認同議題,並充分接軌台灣當代的大眾文化,是一部充滿「樂士浮生錄」(Buena Vista Social Club)情感,並擁有「海角七號」庶民特質的作品(黃俊銘,2010)。劇情上,苦思排不出下一樂季節目的音樂總監,決定穿越中央山脈,來到卑南山下的南王部落,故事的主軸宛若鄉土文學的場景:豐饒佳美之地,溫熱的酒及豪爽的歌聲,文本透過一位維也納音樂院畢業的國家交響樂團年輕總監(簡文彬)跌入一場尋根之旅作為起點,包括記憶裡的童年有原住民保姆、以及哼不全的旋律,如果往台北地景追溯,或還有原住民在都市叢林恐懼而勤奮的世代身影。
簡文彬作為演出現場的指揮家,亦作為戲劇形式中的台北漢人的總監身分,一個受西方古典音樂訓練的指揮家,他所帶領的「國家交響樂團」作為一支交響樂團編制的樂團;矛盾的是,它根基的台灣,卻非以古典音樂「立國」,成為劇中總監焦慮、排不出曲目的心理根源。這位音樂總監展開維也納、台北至台東部落的追尋之旅,亦暗指多數非西方之古典音樂奏家不斷思索、矛盾,尋找身分認同的旅程。
正典歌劇:台灣風景與全球流動
以「正典歌劇:台灣風景」作始,國家交響樂團開啟了「音樂會形式的歌劇」的新製作模式,「以發揮音樂性為主的音樂廳舞台,捨棄繁雜的布景道具,並且跨界結合國內優秀的藝術工作者,以簡樸的燈光、服裝、演出走位設計,將歌劇還原至其音樂核心」(簡文彬,2002)。它透過與本地的連結合作,在內容意涵上暗示了「台灣在地」的存在(雖不一定以台灣作為場景設定),並藉由與文化明星導演合作,相當程度收編了(incorporate)當代台北主流表演文化的符號。首先,《托斯卡》 雖是十九世紀寫實主義派作曲家普契尼的經典歌劇,但導演林懷民以當代台北為場景,並在空間配置上以中國京劇的「一桌二椅」為主軸,雖然令人意外地,林懷民並未明顯以歐洲流行的「導演歌劇」運作,而採取了傾向保守的敘事立場(黃俊銘,2003),以至於全劇雖然設定在台北黑道社會,若非旁白人及時提醒,並不容易意識十九世紀羅馬與當代台北的差異。林懷民透過「一桌二椅」採取了「輕」的策略,很符合簡文彬作為第一部國家交響樂團推出的「音樂會形式的歌劇」的論述主軸,如同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I.Calvino)曾在留給後世的〈五份給讀者的備忘錄〉(Calvino, 1996)裡,提醒普世讀者「輕」的重要。卡爾維諾言說文學上的所謂「輕」,是將自己揚舉於世界重力之上,以便讓「追求輕盈的歷程成為對生命沉重的對抗」,林懷民則運用這樣的「輕」來對抗經典歌劇文本的沉重以及詮釋上的受限。
林懷民的雲門符號
簡文彬的《托斯卡》在沒有前奏曲引導的三小節裡,已經試圖操練國家交響樂團的最強音(fff; tutta forza)。林懷民所謂的一桌二椅置於舞台前方,與Scarpia一身血紅連成一色,似是無所不在的邪惡軸心:這裡既是男主角Cavaradossi作畫的高台、Scarpia企圖染指托斯卡時也曾被請上桌、末幕成了獄卒向Cavaradossi索賄的地盤。全劇三幕徹頭徹尾,將生命的恐懼與沉重皆鎖在台前孤傲的一桌二椅,這是林懷民的第一種「輕盈」。導演借用燈光作為舞台焦點的轉移,也適時解決了轉場窒礙,及「真實場景」與樂團並置時所必然在形式上的扞格。一幕終場Scarpia預告的流血指令,將光源集中在他一人身上,與散漫天真的歌隊形成對比,反而渲染了邪惡勢力的強度。拉丁文的頌贊兀自在漆黑中詠唱,這是林懷民的第二種「輕盈」。導演似乎放肆讓演員在音樂廳寫生。歌隊從觀眾入口處大方進出、牧童則在三樓包廂區嗚咽般吟唱;林懷民讓Angelotti闖入樂團的「安全範團」啃食7-11國民便當或許容易引來爭議,但是劇末托斯卡從管風琴高台倉然躍入樂池,霎時腥紅光束從管風琴柱迅速蔓延,似是血濺成牆,燦爛光輝,這是林懷民的第三種「輕盈」。
林懷民沒有像他的舞蹈劇場一樣,挪用突出的當代符號,他還是讓浦契尼成為一個「說故事的人」,自己則退居次位,單挑場面調度。作為一種導演策略,林懷民透過《托斯卡》所採納的「雲門」符號,可能展現在「表演訓練」的層次。明顯地,女主角陳妍陵舉手投足看得出取法雲門的神韻,已整合進入國家交響樂團的文化實作,林懷民深諳歌者在起音(attack)時必然的身體準備,而設計更多肢體上的迴旋空間;陳妍陵的聲音優勢在於控制得宜的發聲法及毫無窒礙的聲區轉換,讓她不僅擁有夠格的音量,還能聽到各種暗示性的色澤變化。雖然,陳妍陵可能比較困惑,在她那極抒情的美聲風格與取法於雲門的風格神韻裡,如何當一名複雜的女人托斯卡。
賴聲川的莫札特喜歌劇三部曲
被稱為莫札特喜歌劇三部曲的《費加洛的婚禮》、《唐喬望尼》、《女人皆如此》,由表演工作坊創辦人、前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院長賴聲川執導,《費加洛的婚禮》的時空場景設定於清朝未年的中國,《女人皆如此》則是在二○年代的奢華、民風開放卻又有點禁忌的上海(黃俊銘,2005),透過置於中國的場景,「出現東西方互相吸引的誤會,和文化衝擊的產物」(鍾欣志,2006),兩者分別是性的「解放前」、「性解放後」的對照組。賴聲川在《費加洛的婚禮》與《女人皆如此》中,並未突顯它「台灣性」,但如此混搭中國符號;允許「戲中淫穢、充斥性暗示的劇詞也將照常搬演」及賴聲川所言:「情場男女對愛情困惑的模樣、古今中外都一個樣」 (黃俊銘,2005) ,這位柏克萊大學戲劇系博士出身的知名導演,曾開創以「相聲」作為台灣劇場的懷舊(nostalgia)操演,他所顯現出來那種對於語言的掌握及對大眾流行符號的挪用,反而是道地「台灣性」。
擅長論述的賴聲川,以《費加洛的婚禮》原劇就發生在法國大革命的時代,「社會階級迅速變動、人性焦躁,與清末的革命情境類似」(黃俊銘, 2006),來作為它與東方聯結的依據。他認為僕人的角色永遠比主人聰明,卻永遠是失敗者,但《費加洛的婚禮》突出之處,在於劇裡的費加洛,與主人鬥智最後大獲勝利,「這是階級戰勝的劃時代作品」(黃俊銘,2006)。賴聲川在《女人皆如此》安置了許多men's talk,也有姐妹淘的語言,以至於全劇雖以上海作為文化地景,也以原劇本的義大利語演唱,「觀眾會發現,原來世間男女的談話模式,200年來一直沒變」;他相信「如果莫札特活著,也會同意他這麼做」 (黃俊銘,2005)。而《唐喬望尼》,幾乎保持原作慣常的演出場景,但賴聲川利用「一對『有些問題』的台北夫妻看電視」開始說起(黃俊銘,2004a),來連結它的「台灣場景」,並在歌劇尚末演出前,以劇框外的爵士樂及樂池奏起貝多芬「命運」交響曲,再串接歌劇「唐喬望尼」的序曲,作為開場,全劇宛如《欲望城市》的翻版(賴聲川語,黃俊銘,2004a)。
顯然,賴聲川所執導的莫札特三部曲,是運用於「生活意涵」以及接合社會的階級處境,他極有意識地未陷入如詮釋「歷史劇」般的泥淖,而透過時空轉場來呈現人類恆常的生活時刻,如此「文化」作為劇目的展示方法,一來避免與西方正典歌劇製作「正面對決」,一來它可直接有效地連結人類集體的生活處境,而免除不同文化與社會性場景(context)的誤讀。
至於本研究定位之「正典歌劇:全球流動」的《尼貝龍指環》、《玫瑰騎士》、《卡門》等三部歌劇,就展示意涵來說,它們的文化「效果」並非展示於導演的編創,而是透過國際合作,來完成Appadurai的全球性文化流動,因而它雖然僅是形式性上的聯合製作,但透過符號性的交換、接受與協商,亦在更廣義的表演文本上,呈現多元的意涵,而完成它提煉差異文化、捕捉文化動態性的「效果」。至於《卡門》所顯示的文化意義,恐怕在於它所擁有的廣大知名度,有助於票房表現:它的劇情廣被熟知,它對於人性欲望、愛恨糾結的古老歌頌,歌劇主題「愛情是難馴的飛鳥」很能貼合現代愛情版愛情(黃俊銘,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