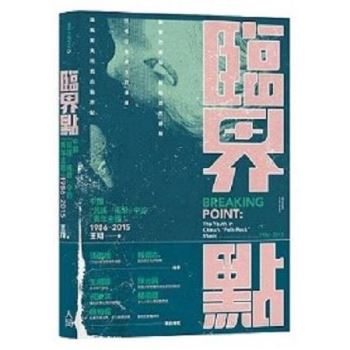篇頭語 世界之夜
王翔
20世紀初,歌手許巍回憶起他向西藏活佛請教,音樂是什麼?活佛回答,是供養。
這段簡短的問答裡面涉及了兩個問題,一個關於信仰,一個關於音樂的性質。這兩個問題,貫穿了我對音樂的體驗。
供養諸佛的音樂是什麼樣子的?這個問題在此暫不展開。在這裡我想指出的是,這段問答把音樂指向了一個超驗的、神聖的維度。
在這個超驗的、神聖的維度上,供養諸佛的音樂才得以成為可能。
因為這個維度的存在,人得以超越一己的悲歡,在血肉之軀裡吟唱出祈禱和供養的音樂。也因為這個維度的存在,人也才會陷入一己的悲歡,在本來空靈之心裡幻化出欲望、誘惑和痛苦。這個推理不知有無道理,我只是在想,黑暗不正是反襯出光明嗎?
我只是無意間想起,古希臘裡,關於海妖的歌聲的神話。傳說船員在過某片深海時,需要把自己捆綁在船上,否則,一旦聽到海妖的歌聲,就會喪失心智,不顧一切地跳進海裡。
那是怎樣誘惑的,又充滿著魔性的歌聲?
那樣的歌聲將人引向自毀和死亡。而在其中,又有著一種怎樣致命的「美」?
如果那些被誘惑跳海的船員,在縱身一躍之前,要表明心跡,他們會說什麼呢?
他們會說,真美啊,我願意,我愛你,我願意為你死去。他們會說出類似這樣的話嗎?
如果他們說出了這樣的話,那麼,海妖歌聲中的誘惑,就已經超越了感官的、情感的刺激,而強大到了一種可以與死亡抗衡的程度。強大到這種程度的誘惑,已經不再是誘惑,而是一種信仰。
我確信你是最美好的。我確信我可以為你去死。我確信你就是我的一切。當這種確信一旦成立,即使在喪失心智的情況下,也可以說,一種信仰已經被確立起來了。
海妖在隱秘的海裡,唱出銷魂致命的歌聲。船員們紛紛跳進海裡。
套用本文的開頭,在這裡,是不是也可以說,船員們用生命,供養了海妖的歌聲?
在這個古希臘的神話裡,我第一次產生一種警覺,原來美妙的歌聲也是可以殺人的。我也第一次意識到,美、音樂、信仰這些事物並不是可以不加觀察、分析就統統接納的。這些事物裡可以產生美好的力量,也可以產生毀滅的力量。記得少年時翻看藝術史,上面寫道,音樂起源於遠古時期的祭祀,起源於人與神靈的溝通。對這個觀點的真偽我不去探討,但論到音樂的功能,論到它在這個神聖的維度上的作用,到現在也是顯而易見的。在現今的各大宗教裡,音樂依然在這個神聖的維度上發聲。佛教的梵唄、基督教的頌歌、伊斯蘭教的禱告,依然在這個世界上存在。
然而,代表著音樂的神聖維度的宗教音樂,並不再是這個世界的主流音樂。
這個世界的主流音樂,是流行音樂。
這種自20世紀20、30年代產生的流行音樂,有著非常龐雜的內容。而其中的主線,是一種面向世俗的,被人聲唱出來的,有詞曲的音樂。它不再是面向神性的,聖潔的音樂,而是面向人間的、世俗的音樂。它回避了偉大的存在,轉而肯定人的地位。它歌唱人的痛苦、歡樂、掙扎,種種心情。在宗教的層面上,種種需要被克服的俗世的情感,轉而成為了審美的對象。比如,對愛人的背叛、失戀的痛苦等等,這些情感在被流行音樂一再歌唱後,得到了確定。失戀的痛苦經過了流行音樂的審美後,是美好的。在全場的合唱中,任何一種情感的缺陷都獲得了強大的精神力量。憎恨、嫉妒、依依不捨、忐忑不安,這種種情感都確定了不可動搖的地位。這是世俗的勝利。在這世俗的勝利合唱中,流行音樂實際上唱出的是,「人是一切的中心」。
在世俗勝利的背後,是傳統宗教信仰者的失落。
在我的印象中,對傳統信仰者的失落,表達得最深切的是20世紀德國哲人海德格爾藉著19世紀詩人荷爾德林的詩,寫出了一個隱喻,「世界之夜」。也是在少年時,我讀到了這個隱喻,混雜著青春的焦灼迷惘,為此感動,還特意買來荷爾德林的殘詩,反覆閱讀。現在我早已忘了他的詩,卻單記得這個隱喻;世界之夜。在我的理解裡,海德格爾所說的,大概是在人失去了對傳統宗教的信仰之後,世界沉入了黑夜的意思。
而這樣的夜,也是世俗的歡樂的夜。
世界之夜。這多麼像是二十世紀後半葉,所發展起來的,流行音樂的背景。
流行音樂的歌唱與聆聽,大多發生在夜裡。下班後,人們打開電視、音響設備,或是戴上耳機。在演唱現場,人們從城市的各個角落趕來,聚在一起。夜幕降臨。舞台上燈光亮起。進入新世紀之後,中國經濟崛起,舞台上的裝備也愈加絢爛。在一個個各大衛視的歌唱選秀節目裡,在一個個被流行音樂充斥的夜裡,看著電視裡那些激動人心的場面,我有時不禁想,如果其中出現了古希臘神話裡海妖的歌聲,又會怎樣?海妖會成為舞台上的神嗎?
我無法想像海妖的歌聲。但我能夠想像的是,如果這時代真有那樣的海妖。那麼毫無疑問,她會成為最成功的巨星。她會理所當然地賺錢,成名,用她的歌聲統治她的臣民。
這個時代的流行歌手,他們沒有對人誘惑至死的力量,但他們在向著那個方向努力。他們需要更多的掌聲、名利、光環。名利是一切的動力,滋養他們的聲音和形象。他們需要在這樣的世界之夜裡閃閃發光。
那些被他們唱出了心聲的歌迷,那些隨著節奏起舞的觀眾,那些一臉陶醉的人,他們為什麼感動?他們圍坐在舞台前,目不轉睛地盯著舞台上那個和他們同為血肉之軀,此刻正閃閃發光的人,歡笑、哭泣、尖叫。他們想要靠近,想要觸及,想要擁抱,他們想離開座位卻又無法離開,被作為觀眾的規範捆綁在座位上,這多麼像是被捆綁在船艙裡的船員。
心已經跳起來了。心快要跳出去了。如果供養意味著調動身心的力量,並讓它向著一個方向釋放的話。那麼,在這裡,顯而易見的是,這些觀眾在用自己身心的燃燒,供養著舞台上的歌手。
在海德格爾所謂的世界之夜,人們不再仰望天穹,轉而崇拜偶像。
這偶像,就是世俗情感的凝聚和化身。
也可以說,人們所崇拜的,是自身的欲望。
而那個在舞台上,看似無所不能的歌手,萬千寵愛在身,實際上,卻是處於眾人欲望的漩渦中心。
眾人的欲望,推動、變化、產生出這樣的舞台。一個人在舞台上,被絢爛的燈光和沸騰的目光包圍。觀眾的熱情中帶著攫取的欲望。他們在歌手身上尋找自身的幻象。他們越愛流行音樂,也就越愛自己。他們的眼睛像品嘗食物一樣,盯著舞台。香港歌手梅豔芳在人生最後的演唱會上說,「我把自己獻給了舞台,獻給了你們。」她身處其中,自然深諳在舞台上與觀眾之間能量流動的方式,以至脫口將表演生涯總結為「奉獻」。奉獻,意味著將自己的身心都交出去。這小小舞台周圍,嗷嗷待脯的觀眾,需要歌手的聲音、表情、心力來滋養。在歌唱的瞬間,嘴巴張開,呼吸伸長,眼望著觀眾,肢體擺動,釋放出身心之力。在這瞬間,歌手把自己交了出去。觀眾的圍觀之力將舞台變成了祭壇。歌手奉獻出自己,將歌聲獻祭給觀眾以欲望之合力所塑造的祭壇。
舞台的實像與祭壇的幻象在我眼前交錯,以至我在看到這種現代演唱會的時候,常常會下意識地產生一種恐怖感。
在諸神消失的世界之夜,依然有祭祀,有祭壇。它們新的形式就是流行音樂演唱會。祭拜的對象由神聖的諸神轉變成了世俗的諸眾。
人們不再祭拜諸神,他們轉而祭拜自己。
在卑微的處境裡,存在著堅強的自戀;在脆弱的身軀裡,存在著無畏的自信。在30年代的上海,被後來者稱為「上海老歌」的流行音樂風靡一時,風塵、舞女、離別、愛戀等元素成為了歌唱的主題。與此同時出現的「群眾音樂」,裹挾著革命的雷霆之聲,也席捲了整個中國。
在意識形態上相互對立的這兩種音樂之間,存在著一個相同之處。那就是它們都是人祭拜自身的音樂。一個是祭拜俗世的情愛,一個是祭拜民族國家的理想。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群眾音樂與它所排斥的上海老歌沒有任何不同,它們一樣是以世俗之人自我為中心。群眾音樂在對人的強調上,甚至超越了上海老歌。它將人塑造成革命者的形象,並將之推進、上升到了造物主的地位。
以自我為中心,以自我為主宰,以自我為信仰。這是一種多麼好的感覺啊!
革命者,是創造新中國的人,是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人,是英雄,是主宰。在這個精神強度中的人,以及在這個強度中所形成的體制,不能是靜止的、緩慢的,而必須是高度運動的。只有高度的運動才可以滿足這種對自我崇拜所形成的空虛。
從人的自我崇拜這個角度來看,流行音樂,是在群眾音樂這裡,在革命音樂這裡,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頂峰。
而這個祭壇所需要的,不僅是歡呼,而是生命。
海德格爾所謂的世界之夜,在新中國的革命者眼裡,卻是豔陽高照的白晝。
諸神,不在天上,而在地上。
他們來自一種新信仰。
在這種新信仰的籠罩下,新中國在運轉了六十年後,開始經濟崛起。新信仰的實踐與得失,此處也暫且不論。一個實際的情況是,中國是在這個新信仰的籠罩下,蛻變、發展、壯大。新信仰所產生的力量,在多年浸淫、衝突、轉化之後,已經進入了國民的精神氣質裡面。在我看來,文革結束之後,經歷了革命洗禮的一代青年,在80年代,進入不同的文化領域,如詩歌、小說、搖滾樂、學術、電影,乃至於對異域宗教的推崇等等。他們呈現出了不同的面貌,但在精神氣質上,卻維繫著新信仰的骨髓和殘骸。
這種精神氣質,這種唯我獨尊所輻射出的,是要將整個世界作為改造對象的雄心。
消除壓迫,消除剝削。有很多激勵人心的口號和信念從中產生。這些信念的實踐,以及從實踐中產生的反思,籠罩了新中國的歷史。這些事情不是我感興趣的。我感興趣的是,這些被新信仰所影響的人的主體位置。
在失去了諸神的夜晚,人將自身上升為神明。
從這樣的主體位置上爆發的歌聲,裹挾著「國家」、「民族」、「理想」、「集體」、「階級」等烙印,席捲了整個國家。這是革命歌曲。
然而,在這個將人塑造為神的「造神運動」中,普通人的心情和欲望卻被改造和壓抑。「一將功成萬骨枯」在這裡有了新的翻版。新神的誕生伴隨著千萬人的供給。
一個新的祭壇誕生了。
在這個新的祭壇上,理想伴隨著鮮血,高亢的歌聲背後有深沉的沉默。
這是中國當代民謠搖滾的舞台。
王翔
20世紀初,歌手許巍回憶起他向西藏活佛請教,音樂是什麼?活佛回答,是供養。
這段簡短的問答裡面涉及了兩個問題,一個關於信仰,一個關於音樂的性質。這兩個問題,貫穿了我對音樂的體驗。
供養諸佛的音樂是什麼樣子的?這個問題在此暫不展開。在這裡我想指出的是,這段問答把音樂指向了一個超驗的、神聖的維度。
在這個超驗的、神聖的維度上,供養諸佛的音樂才得以成為可能。
因為這個維度的存在,人得以超越一己的悲歡,在血肉之軀裡吟唱出祈禱和供養的音樂。也因為這個維度的存在,人也才會陷入一己的悲歡,在本來空靈之心裡幻化出欲望、誘惑和痛苦。這個推理不知有無道理,我只是在想,黑暗不正是反襯出光明嗎?
我只是無意間想起,古希臘裡,關於海妖的歌聲的神話。傳說船員在過某片深海時,需要把自己捆綁在船上,否則,一旦聽到海妖的歌聲,就會喪失心智,不顧一切地跳進海裡。
那是怎樣誘惑的,又充滿著魔性的歌聲?
那樣的歌聲將人引向自毀和死亡。而在其中,又有著一種怎樣致命的「美」?
如果那些被誘惑跳海的船員,在縱身一躍之前,要表明心跡,他們會說什麼呢?
他們會說,真美啊,我願意,我愛你,我願意為你死去。他們會說出類似這樣的話嗎?
如果他們說出了這樣的話,那麼,海妖歌聲中的誘惑,就已經超越了感官的、情感的刺激,而強大到了一種可以與死亡抗衡的程度。強大到這種程度的誘惑,已經不再是誘惑,而是一種信仰。
我確信你是最美好的。我確信我可以為你去死。我確信你就是我的一切。當這種確信一旦成立,即使在喪失心智的情況下,也可以說,一種信仰已經被確立起來了。
海妖在隱秘的海裡,唱出銷魂致命的歌聲。船員們紛紛跳進海裡。
套用本文的開頭,在這裡,是不是也可以說,船員們用生命,供養了海妖的歌聲?
在這個古希臘的神話裡,我第一次產生一種警覺,原來美妙的歌聲也是可以殺人的。我也第一次意識到,美、音樂、信仰這些事物並不是可以不加觀察、分析就統統接納的。這些事物裡可以產生美好的力量,也可以產生毀滅的力量。記得少年時翻看藝術史,上面寫道,音樂起源於遠古時期的祭祀,起源於人與神靈的溝通。對這個觀點的真偽我不去探討,但論到音樂的功能,論到它在這個神聖的維度上的作用,到現在也是顯而易見的。在現今的各大宗教裡,音樂依然在這個神聖的維度上發聲。佛教的梵唄、基督教的頌歌、伊斯蘭教的禱告,依然在這個世界上存在。
然而,代表著音樂的神聖維度的宗教音樂,並不再是這個世界的主流音樂。
這個世界的主流音樂,是流行音樂。
這種自20世紀20、30年代產生的流行音樂,有著非常龐雜的內容。而其中的主線,是一種面向世俗的,被人聲唱出來的,有詞曲的音樂。它不再是面向神性的,聖潔的音樂,而是面向人間的、世俗的音樂。它回避了偉大的存在,轉而肯定人的地位。它歌唱人的痛苦、歡樂、掙扎,種種心情。在宗教的層面上,種種需要被克服的俗世的情感,轉而成為了審美的對象。比如,對愛人的背叛、失戀的痛苦等等,這些情感在被流行音樂一再歌唱後,得到了確定。失戀的痛苦經過了流行音樂的審美後,是美好的。在全場的合唱中,任何一種情感的缺陷都獲得了強大的精神力量。憎恨、嫉妒、依依不捨、忐忑不安,這種種情感都確定了不可動搖的地位。這是世俗的勝利。在這世俗的勝利合唱中,流行音樂實際上唱出的是,「人是一切的中心」。
在世俗勝利的背後,是傳統宗教信仰者的失落。
在我的印象中,對傳統信仰者的失落,表達得最深切的是20世紀德國哲人海德格爾藉著19世紀詩人荷爾德林的詩,寫出了一個隱喻,「世界之夜」。也是在少年時,我讀到了這個隱喻,混雜著青春的焦灼迷惘,為此感動,還特意買來荷爾德林的殘詩,反覆閱讀。現在我早已忘了他的詩,卻單記得這個隱喻;世界之夜。在我的理解裡,海德格爾所說的,大概是在人失去了對傳統宗教的信仰之後,世界沉入了黑夜的意思。
而這樣的夜,也是世俗的歡樂的夜。
世界之夜。這多麼像是二十世紀後半葉,所發展起來的,流行音樂的背景。
流行音樂的歌唱與聆聽,大多發生在夜裡。下班後,人們打開電視、音響設備,或是戴上耳機。在演唱現場,人們從城市的各個角落趕來,聚在一起。夜幕降臨。舞台上燈光亮起。進入新世紀之後,中國經濟崛起,舞台上的裝備也愈加絢爛。在一個個各大衛視的歌唱選秀節目裡,在一個個被流行音樂充斥的夜裡,看著電視裡那些激動人心的場面,我有時不禁想,如果其中出現了古希臘神話裡海妖的歌聲,又會怎樣?海妖會成為舞台上的神嗎?
我無法想像海妖的歌聲。但我能夠想像的是,如果這時代真有那樣的海妖。那麼毫無疑問,她會成為最成功的巨星。她會理所當然地賺錢,成名,用她的歌聲統治她的臣民。
這個時代的流行歌手,他們沒有對人誘惑至死的力量,但他們在向著那個方向努力。他們需要更多的掌聲、名利、光環。名利是一切的動力,滋養他們的聲音和形象。他們需要在這樣的世界之夜裡閃閃發光。
那些被他們唱出了心聲的歌迷,那些隨著節奏起舞的觀眾,那些一臉陶醉的人,他們為什麼感動?他們圍坐在舞台前,目不轉睛地盯著舞台上那個和他們同為血肉之軀,此刻正閃閃發光的人,歡笑、哭泣、尖叫。他們想要靠近,想要觸及,想要擁抱,他們想離開座位卻又無法離開,被作為觀眾的規範捆綁在座位上,這多麼像是被捆綁在船艙裡的船員。
心已經跳起來了。心快要跳出去了。如果供養意味著調動身心的力量,並讓它向著一個方向釋放的話。那麼,在這裡,顯而易見的是,這些觀眾在用自己身心的燃燒,供養著舞台上的歌手。
在海德格爾所謂的世界之夜,人們不再仰望天穹,轉而崇拜偶像。
這偶像,就是世俗情感的凝聚和化身。
也可以說,人們所崇拜的,是自身的欲望。
而那個在舞台上,看似無所不能的歌手,萬千寵愛在身,實際上,卻是處於眾人欲望的漩渦中心。
眾人的欲望,推動、變化、產生出這樣的舞台。一個人在舞台上,被絢爛的燈光和沸騰的目光包圍。觀眾的熱情中帶著攫取的欲望。他們在歌手身上尋找自身的幻象。他們越愛流行音樂,也就越愛自己。他們的眼睛像品嘗食物一樣,盯著舞台。香港歌手梅豔芳在人生最後的演唱會上說,「我把自己獻給了舞台,獻給了你們。」她身處其中,自然深諳在舞台上與觀眾之間能量流動的方式,以至脫口將表演生涯總結為「奉獻」。奉獻,意味著將自己的身心都交出去。這小小舞台周圍,嗷嗷待脯的觀眾,需要歌手的聲音、表情、心力來滋養。在歌唱的瞬間,嘴巴張開,呼吸伸長,眼望著觀眾,肢體擺動,釋放出身心之力。在這瞬間,歌手把自己交了出去。觀眾的圍觀之力將舞台變成了祭壇。歌手奉獻出自己,將歌聲獻祭給觀眾以欲望之合力所塑造的祭壇。
舞台的實像與祭壇的幻象在我眼前交錯,以至我在看到這種現代演唱會的時候,常常會下意識地產生一種恐怖感。
在諸神消失的世界之夜,依然有祭祀,有祭壇。它們新的形式就是流行音樂演唱會。祭拜的對象由神聖的諸神轉變成了世俗的諸眾。
人們不再祭拜諸神,他們轉而祭拜自己。
在卑微的處境裡,存在著堅強的自戀;在脆弱的身軀裡,存在著無畏的自信。在30年代的上海,被後來者稱為「上海老歌」的流行音樂風靡一時,風塵、舞女、離別、愛戀等元素成為了歌唱的主題。與此同時出現的「群眾音樂」,裹挾著革命的雷霆之聲,也席捲了整個中國。
在意識形態上相互對立的這兩種音樂之間,存在著一個相同之處。那就是它們都是人祭拜自身的音樂。一個是祭拜俗世的情愛,一個是祭拜民族國家的理想。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群眾音樂與它所排斥的上海老歌沒有任何不同,它們一樣是以世俗之人自我為中心。群眾音樂在對人的強調上,甚至超越了上海老歌。它將人塑造成革命者的形象,並將之推進、上升到了造物主的地位。
以自我為中心,以自我為主宰,以自我為信仰。這是一種多麼好的感覺啊!
革命者,是創造新中國的人,是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人,是英雄,是主宰。在這個精神強度中的人,以及在這個強度中所形成的體制,不能是靜止的、緩慢的,而必須是高度運動的。只有高度的運動才可以滿足這種對自我崇拜所形成的空虛。
從人的自我崇拜這個角度來看,流行音樂,是在群眾音樂這裡,在革命音樂這裡,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頂峰。
而這個祭壇所需要的,不僅是歡呼,而是生命。
海德格爾所謂的世界之夜,在新中國的革命者眼裡,卻是豔陽高照的白晝。
諸神,不在天上,而在地上。
他們來自一種新信仰。
在這種新信仰的籠罩下,新中國在運轉了六十年後,開始經濟崛起。新信仰的實踐與得失,此處也暫且不論。一個實際的情況是,中國是在這個新信仰的籠罩下,蛻變、發展、壯大。新信仰所產生的力量,在多年浸淫、衝突、轉化之後,已經進入了國民的精神氣質裡面。在我看來,文革結束之後,經歷了革命洗禮的一代青年,在80年代,進入不同的文化領域,如詩歌、小說、搖滾樂、學術、電影,乃至於對異域宗教的推崇等等。他們呈現出了不同的面貌,但在精神氣質上,卻維繫著新信仰的骨髓和殘骸。
這種精神氣質,這種唯我獨尊所輻射出的,是要將整個世界作為改造對象的雄心。
消除壓迫,消除剝削。有很多激勵人心的口號和信念從中產生。這些信念的實踐,以及從實踐中產生的反思,籠罩了新中國的歷史。這些事情不是我感興趣的。我感興趣的是,這些被新信仰所影響的人的主體位置。
在失去了諸神的夜晚,人將自身上升為神明。
從這樣的主體位置上爆發的歌聲,裹挾著「國家」、「民族」、「理想」、「集體」、「階級」等烙印,席捲了整個國家。這是革命歌曲。
然而,在這個將人塑造為神的「造神運動」中,普通人的心情和欲望卻被改造和壓抑。「一將功成萬骨枯」在這裡有了新的翻版。新神的誕生伴隨著千萬人的供給。
一個新的祭壇誕生了。
在這個新的祭壇上,理想伴隨著鮮血,高亢的歌聲背後有深沉的沉默。
這是中國當代民謠搖滾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