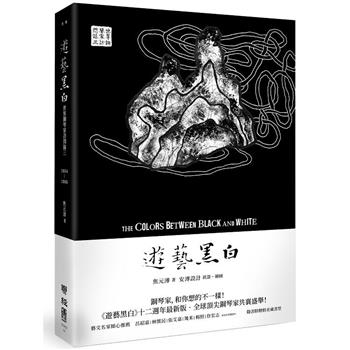第五章 亞洲和中東
前言 從中東走向世界,將世界帶往亞洲
本章可說是本書中筆者最感榮譽的一章:它記錄了台灣、亞洲、中東鋼琴家的頂尖藝術成就,包括在世界舞台的重要里程碑。
同樣出生於1958年,來自黎巴嫩的艾爾巴夏與來自越南的鄧泰山,各自在1978年伊麗莎白大賽與1980年蕭邦大賽獲得冠軍,是中東與東亞音樂家首度在顯赫國際比賽贏得首獎。之後他們精益求精、持續努力,積累出深厚的技藝修為,在今日依舊閃閃發光。然而國際聽眾是否準備好接受來自西方世界以外的古典音樂家?看他們的學習與經歷,太多故事令我們深思。鄧泰山境遇之峰迴路轉,想像力最豐富的小說家聽了大概也要擲筆嘆服;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世界在藝術上早有交流,透過艾爾巴夏的視角來看西方,相信亦可觸類旁通。
同樣值得深思的,是吳菡的習樂因緣與過程。這或許是本書最感人的故事,至少我每次想起都常紅了眼眶:古典音樂真的不是某個階級的專屬,任何人都可以喜愛,欣賞它也只需要喜愛。聽這位林肯中心室內樂集藝術總監為讀者解析室內樂,或許有當今最權威精到的見解。萬分感謝另一位總監大提琴名家芬柯也加入訪問,成為本書108位鋼琴家之外的第109位音樂家,堪稱最豪華的「隱藏版受訪者」。為何本與音樂無關的家庭,能出兩位世界級鋼琴家?讀過陳必先訪問再
來看陳宏寬,相信會更佩服他們的父母與家庭。無論是藝術造詣或克服手傷的過程,陳宏寬在訪問中的分享是音樂課更是人生課。他在演奏與教學都卓然有成,確是名不虛傳。
這些名家也為我的聆賞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我至今依然清晰記得鄧泰山首次來台演出的音色魔法,以及陳宏寬演奏布拉姆斯與巴爾托克《第二號鋼琴協奏曲》的盛況。生於台灣,我自然也在欣賞魏樂富與葉綠娜的現場演出中長大,很高興最後有能力訪問他們──本書初版時,我對「朗讀與音樂」和「朗讀音樂劇」認識不深,誰知十年後自己竟也從事翻譯此類作品,還策劃相關演出。一如賀夫,他們也是論述豐富的作者,希望這篇訪問尚能觸及些許他們還未寫作的議題。
學音樂從來就不只是學演奏,音樂也不只是音樂。看他們長年教學累積出的銳利觀察,建言值得我們深思。
小山實稚惠是本書訪問的兩位日本鋼琴家之一,也是僅在日本學習,卻在柴可夫斯基與蕭邦大賽獲獎的名家,足稱日本最具代表性的音樂家。她純真善良,對音樂有源源不絕的熱情,錘鍊出豐富寬廣的曲目。這是我遇過最樸實可愛的音樂家,希望讀者能多認識這位在日本唱片等身、演奏邀約滿檔的演奏家,傾聽西方文明與大和文化的音樂交流。
……
艾爾巴夏(Abdel Rahman El Bacha, 1958-)
1958年10月23日出生於黎巴嫩首府貝魯特,成長於音樂家庭的艾爾巴夏自幼便展現極高天分,9歲隨莎琪桑(Zvart Sarkissian)學習鋼琴,隔年即和樂團合作演出。他16歲至巴黎高等音樂院學習,得到鋼琴、室內樂、和聲、對位四項一等獎。1978年他以19歲之齡榮獲伊麗莎白大賽冠軍,從此開展國際演出。艾爾巴夏技巧精湛,曾錄製巴赫兩冊《前奏與賦格》、貝多芬鋼琴奏鳴曲與蕭邦鋼琴作品全集、拉威爾鋼琴獨奏與協奏全集、普羅高菲夫鋼琴協奏曲全集等等精彩錄音,獲得諸多唱片大獎。他也是卓然有成的作曲家,目前定居布魯塞爾。
焦元溥(以下簡稱「焦」):我知道您成長在非常有趣的音樂家庭:令尊是嫻熟西方古典音樂的作曲家,令堂則是著名的中東傳統音樂與流行樂歌手。
艾爾巴夏(以下簡稱「艾」):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都是佼佼者,我可說出生在音樂水準極高的環境。我很小的時候就對音樂很感興趣,各種音樂皆然。古典音樂、中東傳統音樂與流行音樂對我而言並沒有高下之分,其中各有傑出與平凡的創作,只要是傑作我都欣賞。以古典音樂來說,家父收藏了很多唱片,包括從蘇聯帶回來的歌劇錄音,轉和LP都有,更有許多樂譜。我能在家對著樂譜聽史特拉汶斯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貝多芬的歌劇與交響樂,因此學得很快。貝魯特以前也就有不錯的藝術環境,1955年成立的巴貝克國際藝術節(Baalbeck International Festival)總有精彩演出,李希特、羅斯卓波維奇、卡拉揚等等都來過。
焦:您何時決定要成為音樂家?我知道您數學也很好,是否也考慮過音樂以外的人生方向?
艾:我雖然喜愛數學,但音樂永遠是首要。我在 13、14歲就展現出過人天賦,老師和父親都注意到我的音樂程度很高,但家父其實不希望我走音樂的路。他覺得這是很辛苦的人生,成家立業都難,鋼琴家的競爭尤其激烈,要有機運才能出頭。但他也沒有阻止我,仍然給我機會讓我到巴黎學習。雖然在他的想像中,我得到學位後就該回到黎巴嫩,找份穩定工作,偶爾開音樂會就好──當然,這不是我對自己的想像,但我必須證明我有能力實現抱負才行。倒是家母總是支持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她有非常好的耳朵,很早就能分辨出我的演奏和他人的不同。
焦:對中東世界而言,古典音樂中哪些作品比較接近您們的個性?
艾:首先是俄國音樂。這是強大、敏感、熱情,感性多過理性的音樂。並不是說俄國音樂不理性,而是理性不是最重要的元素。這和中東民風很接近。柴可夫斯基《悲愴交響曲》和拉赫曼尼諾夫《第二號鋼琴協奏曲》,一向是黎巴嫩最受歡迎的作品。再來就是西班牙音樂。這當然有歷史因素在其中,因為西班牙曾受穆斯林統治約750年。西班牙音樂的即興和歌唱,方式和阿拉伯音樂很相近,甚至行為模式也像,音樂滿是自豪、愛與激情。相較於此,法國音樂就比較冷,中東人普遍而言比較不理解。
焦:您也不理解嗎?
艾:是的。我小時候對俄國音樂很有好感,對德奧作品也很能理解,但始終不了解法國音樂。雖然我的老師在巴黎學習,也教我彈拉威爾《水戲》和德布西《為鋼琴的》組曲,我還是不很懂。既然如此,我就決定也到巴黎學,補強在法國音樂上的知識。我必須說這真是正確的決定,特別是和聲與對位課,讓我徹底認識法國音樂,更愛上拉威爾。在巴黎居住,也讓我熟悉法國人的行為模式,進而了解他們的音樂表現。
焦:您錄製了拉威爾鋼琴獨奏與協奏曲全集,成果相當傑出,可否跟我們分享您對拉威爾的研究心得?
艾:在和聲課上,老師曾特別分析德布西、拉威爾、佛瑞的風格,給我們高音旋律要學生以這三家風格做和聲寫作,因此我真的學到很多。但直到今日,佛瑞的鋼琴獨奏作品仍然和我不親,我喜愛的是他的室內樂、歌曲和《安魂曲》,德布西我也比較愛他的歌曲和管弦樂。拉威爾讓我著迷之處,在於他極其精練的筆法,作品是聲響、和聲、情緒、形式的完美結合,還有無可比擬的配器法。德布西想做真正的法國音樂;拉威爾當然也是法國,但他不只有法國,還有很強的巴斯克元素與古典精神,甚至用到阿拉伯與希臘調式。不過他的個性有一點很特別,就是他對什麼感受愈深,就愈把它藏起來。有人會覺得他的音樂冷,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焦:因此如何妥當表現拉威爾作品中的情感,就至為關鍵。以彈性速度而言,您認為他就是不希望有彈性速度,還是因為當時的演奏家常多用彈性速度,他才刻意嚴格要求演奏者不要用彈性速度?
艾:我認為是後者。拉威爾的作品充滿感情,但並不浪漫。在二十世紀之交,鋼琴家都以相當浪漫的方式演奏,但這不是他的風格。拉威爾若想說什麼,多半是暗示;真要明說,他會說得非常精確,譜上寫明一切,每個音都恰如其分。演奏者要發揮自己最大的才能來實現他的指示,而不是自顧自地浪漫演奏。面對於如此細膩精算的大師,我們要忠實,更該把自己放低,不要以為自己比拉威爾更懂他的作品。
焦:談到生活環境與作曲家,您現在住布魯塞爾,這可曾讓您更接近法朗克等比利時作曲家?
艾:其實沒有,哈哈。法朗克當然是好作曲家,他的和聲屬於十九世紀後期的試驗,想要擴張傳統和聲的範圍。比利時後來的勒庫和庸根(Joseph Jongen, 1873-1953)也是走這路線,或許針有什麼地域性的影響,但這樣的和聲語法對我來說並不自然。就擴張傳統和聲而言,手法最成功的,或許是拉赫曼尼諾夫,可惜大家多半看不到這點。
焦:您在巴黎向赫赫有名的松貢學習。和您之前的學習相比,他是否改造了您的鋼琴技巧?
艾:我是他很特別的學生。我在開始學琴的時候,就很自然地運用整個身體,演奏不同作曲家會用不同的施力方式。我在貝魯特的老師(莎琪桑)為了發展我的手指能力,反而需要限制我運用身體其他部位。對我而言,她是對的,而我也沒有變成傳統法式那種重心完全在手指的演奏。當我到松貢班上,他很驚訝的發現,我的演奏方式簡直就是他的教材,可以當其他學生的模範。才跟他上了兩堂課,松貢就說他不需要教我技巧了,但我們可以討論音樂。這也切合我的需要,因為我在音樂上還有好多要發展探索。
焦:松貢在音樂上如何指導您?
艾:松貢要求忠於樂譜,學生必須彈得非常準確:漸強記號如果從第二個音開始,就不能從第一個音開始大聲;強弱之間如果沒有標示其他術語,那就維持強奏,在弱奏記號出現時突然小聲。如此要求是極端了些,但也訓練我們嚴謹判讀所有指示。此外,他希望演奏如同說故事,不能失去即興感,也要設計戲劇效果,讓觀眾期待故事結果。演奏要呈現不同演員與不同表達,又必須以邏輯整合出具信服力的詮釋。這對鋼琴家格外重要,因為舞台上常只有一人唱獨角戲,必須想辦法讓觀眾聚焦在自己身上。松貢對我很有期待,在我之前,他雖然已有貝洛夫等著名學生,但還沒有人得到著名大賽冠軍。他給了我很多關於比賽的建議,包括如何贏得評審注意,雖然那不是我的風格──對我而言,音樂應該自然發生,為人生帶來快樂,而非旨在成功事業。
焦:您最後也果然在伊麗莎白大賽得到冠軍,還得到「評審一致通過獲得首獎」這樣的榮譽。
艾:我在巴黎高等畢業後,家父本來希望我能馬上回黎巴嫩,但貝魯特已陷入內戰,留在歐洲比較妥當,我也藉此準備比賽。一如我剛剛說的,我必須向父親證明我的能力,首獎自然成為我的夢想。我全力以赴,雖然我也知道我可以是很好的音樂家但沒有任何獎項。比賽奪冠對我意義非凡,這是我個人的榮譽,讓我有開展事業的信心,也是我家庭教育的榮譽,以及黎巴嫩與中東世界的榮譽──這是第一次有來自中東世界的音樂家,在著名國際大賽上奪冠。對受苦於內戰的黎巴嫩而言,這是很大的鼓勵。
焦:您那時本來已經進入巴黎高等音樂院的高級班,松貢卻要您自己發展,不需要在學校學了。
艾:松貢知道我有作曲能力,看過我的作品後也給予很多鼓勵。我想他看出我那時需要從自己內部發展,而不是持續借助外力。
焦:您最近出版了自己鋼琴獨奏作品的錄音,曲風相當清新可喜。可否談談您的創作?
艾:家父是很優秀的作曲家,耳濡目染之下,我從小也想作曲,也被家人鼓勵作曲,只是後來我發現我從演奏、詮釋中得到的快樂,和創作不分軒輊。我對創作沒有什麼大志,只是單純地把我內心浮現的樂思,經過組織後寫下來。我覺得詮釋者都該嘗試作曲。不一定要發表,而是體會如何以有限的記號表達思考,又如何提出具邏輯性的樂念。我常聽到很多演奏雖有不少精彩想法,但想法並不連貫,發展也不合理。如果能自己寫些作品,學習以作曲家的角度看樂曲,相信會有很大幫助。自己寫幾次,再看別人作品,也能知道樂曲中哪些是重點,哪些只是裝飾,也就不會在枝微末節上打轉。
焦:不過那時您已經準備好迎接演奏生涯了嗎?畢竟您才19歲而已。
艾:我那時只有五、六首協奏曲,所以每年我都會給自己兩段時間準備新協奏曲和獨奏會。我很早就知道我學得很快,能維持大量曲目,後來也的確演奏了極多作品,不過現在我只演奏我愛的音樂。我得獎後馬上有不少錄音邀約,但我都拒絕,過了三年我才覺得準備好。
焦:您的第一張錄音是普羅高菲夫最早四部作品:《第一號鋼琴奏鳴曲》(Op. 1)、《四首練習曲》(Op. 2)、《四首作品》(Op. 3)、《四首作品》(Op. 4)以及《A小調稍快板》與《D大調詼諧曲》兩首短曲,出版後立即得到唱片大獎。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仍是水準極高,選曲也極為獨特的專輯。當初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艾:第一張錄音,有如我給世界的音樂名片,我當然戒慎恐懼。普羅高菲夫早期作品技巧非常艱難,可以讓我好好發揮,而我也很肯定自己在風格上不會出錯。松貢就對我說︰「沒有人能批評你的普羅高菲夫。」我在伊麗莎白大賽決賽彈他的《第二號鋼琴協奏曲》,連馬卡洛夫都來恭喜我,稱讚那是「以我們應該演奏的方式演奏」。這讓我很安心,因為普羅高菲夫的確是我最愛的作曲家之一。既然這是最愛,我想盡可能探索他所有的作品,主流與非主流。我必須說,他實在有太多精彩但很少演奏的樂曲,因此這張錄音既向世界介紹鋼琴界的新面孔,也介紹新曲目,無論如何會有價值。
焦:為什麼普羅高菲夫這麼吸引您?
艾:我覺得普羅高菲夫是永遠的青年,音樂洋溢著青春的自由,心理上是帶著微笑的革命者,充滿能量以及對未來的信心,音樂非常健康。莫札特和蕭邦對我來說相當中性,普羅高菲夫則是成熟男人的陽剛,對男孩時期的我很有吸引力,現在我仍深深喜愛。此外,他的音樂都言之有物。以《第二號鋼琴協奏曲》來說,技巧極其困難,但不是為了困難而困難,而是以困難帶出更多表現。蕭邦也是如此,愈難的作品帶出的情感就愈豐富,絕非僅是技巧展示。
焦:您最近又錄了一張普羅高菲夫早期作品,即使在最大聲的強奏,都能保持音色與音質的美好。這實在很不容易。
艾:我天生會避免難聽的聲音,絕對不砸鋼琴。我小時候聽貝多芬交響曲,在最大聲的段落,聲音有厚度而不暴力,仍然很美。這給我很大的啟發。我以前也學過小提琴,音色和歌唱性對我始終很重要。我認為音樂演奏要能為耳朵帶來喜悅與快樂,聲音應該要美好,而這不意味就必須限縮表現力。蕭邦的音樂裡也可找到相當暴力的表達,但他始終要求優美的音色,討厭學生把強奏「彈得像狗叫」。攻擊性、挑釁的音樂,一樣能用美好聲音表現,關鍵在於找到結合兩者的方法。
焦:您怎麼看普羅高菲夫自己的鋼琴演奏錄音?
艾:他錄音時更是作曲家而非鋼琴家,我覺得那些錄音沒有展現他作為鋼琴家的最高水準,《第三號鋼琴協奏曲》也可感受到他的緊張。但即使如此,我們仍可欣賞他的演奏能力以及抒情特質,更重要的是沒有什麼敲擊聲響,在小品中有純粹精練、品味極高的表現。如果他專心演奏,應能和拉赫曼尼諾夫一樣,成為偉大鋼琴家。
焦:如此演奏和李希特──普羅高菲夫偏愛的詮釋者,其實相當不同。您怎麼看這種變化?
艾:李希特當然是令人尊敬的鋼琴家,但他的普羅高菲夫並不令我著迷。他的演奏偏向垂直面,而我更偏好水平面的延展。但無論如何,他是當時蘇聯最重要的鋼琴家,能為普羅高菲夫的作品帶來能見度。我覺得這至少顯示普羅高菲夫的作品能以不同美學表現,不是他的蘇聯時期作品就只能以李希特的方式演奏。
焦:您有最喜愛的鋼琴家嗎?
艾:在我成長時期,我最喜愛李帕第和波里尼,很常聽他們的錄音。不過後來我了解,如果要找到自己的聲音,腦子裡就不能都是別人的聲音。
前言 從中東走向世界,將世界帶往亞洲
本章可說是本書中筆者最感榮譽的一章:它記錄了台灣、亞洲、中東鋼琴家的頂尖藝術成就,包括在世界舞台的重要里程碑。
同樣出生於1958年,來自黎巴嫩的艾爾巴夏與來自越南的鄧泰山,各自在1978年伊麗莎白大賽與1980年蕭邦大賽獲得冠軍,是中東與東亞音樂家首度在顯赫國際比賽贏得首獎。之後他們精益求精、持續努力,積累出深厚的技藝修為,在今日依舊閃閃發光。然而國際聽眾是否準備好接受來自西方世界以外的古典音樂家?看他們的學習與經歷,太多故事令我們深思。鄧泰山境遇之峰迴路轉,想像力最豐富的小說家聽了大概也要擲筆嘆服;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世界在藝術上早有交流,透過艾爾巴夏的視角來看西方,相信亦可觸類旁通。
同樣值得深思的,是吳菡的習樂因緣與過程。這或許是本書最感人的故事,至少我每次想起都常紅了眼眶:古典音樂真的不是某個階級的專屬,任何人都可以喜愛,欣賞它也只需要喜愛。聽這位林肯中心室內樂集藝術總監為讀者解析室內樂,或許有當今最權威精到的見解。萬分感謝另一位總監大提琴名家芬柯也加入訪問,成為本書108位鋼琴家之外的第109位音樂家,堪稱最豪華的「隱藏版受訪者」。為何本與音樂無關的家庭,能出兩位世界級鋼琴家?讀過陳必先訪問再
來看陳宏寬,相信會更佩服他們的父母與家庭。無論是藝術造詣或克服手傷的過程,陳宏寬在訪問中的分享是音樂課更是人生課。他在演奏與教學都卓然有成,確是名不虛傳。
這些名家也為我的聆賞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我至今依然清晰記得鄧泰山首次來台演出的音色魔法,以及陳宏寬演奏布拉姆斯與巴爾托克《第二號鋼琴協奏曲》的盛況。生於台灣,我自然也在欣賞魏樂富與葉綠娜的現場演出中長大,很高興最後有能力訪問他們──本書初版時,我對「朗讀與音樂」和「朗讀音樂劇」認識不深,誰知十年後自己竟也從事翻譯此類作品,還策劃相關演出。一如賀夫,他們也是論述豐富的作者,希望這篇訪問尚能觸及些許他們還未寫作的議題。
學音樂從來就不只是學演奏,音樂也不只是音樂。看他們長年教學累積出的銳利觀察,建言值得我們深思。
小山實稚惠是本書訪問的兩位日本鋼琴家之一,也是僅在日本學習,卻在柴可夫斯基與蕭邦大賽獲獎的名家,足稱日本最具代表性的音樂家。她純真善良,對音樂有源源不絕的熱情,錘鍊出豐富寬廣的曲目。這是我遇過最樸實可愛的音樂家,希望讀者能多認識這位在日本唱片等身、演奏邀約滿檔的演奏家,傾聽西方文明與大和文化的音樂交流。
……
艾爾巴夏(Abdel Rahman El Bacha, 1958-)
1958年10月23日出生於黎巴嫩首府貝魯特,成長於音樂家庭的艾爾巴夏自幼便展現極高天分,9歲隨莎琪桑(Zvart Sarkissian)學習鋼琴,隔年即和樂團合作演出。他16歲至巴黎高等音樂院學習,得到鋼琴、室內樂、和聲、對位四項一等獎。1978年他以19歲之齡榮獲伊麗莎白大賽冠軍,從此開展國際演出。艾爾巴夏技巧精湛,曾錄製巴赫兩冊《前奏與賦格》、貝多芬鋼琴奏鳴曲與蕭邦鋼琴作品全集、拉威爾鋼琴獨奏與協奏全集、普羅高菲夫鋼琴協奏曲全集等等精彩錄音,獲得諸多唱片大獎。他也是卓然有成的作曲家,目前定居布魯塞爾。
焦元溥(以下簡稱「焦」):我知道您成長在非常有趣的音樂家庭:令尊是嫻熟西方古典音樂的作曲家,令堂則是著名的中東傳統音樂與流行樂歌手。
艾爾巴夏(以下簡稱「艾」):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都是佼佼者,我可說出生在音樂水準極高的環境。我很小的時候就對音樂很感興趣,各種音樂皆然。古典音樂、中東傳統音樂與流行音樂對我而言並沒有高下之分,其中各有傑出與平凡的創作,只要是傑作我都欣賞。以古典音樂來說,家父收藏了很多唱片,包括從蘇聯帶回來的歌劇錄音,轉和LP都有,更有許多樂譜。我能在家對著樂譜聽史特拉汶斯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貝多芬的歌劇與交響樂,因此學得很快。貝魯特以前也就有不錯的藝術環境,1955年成立的巴貝克國際藝術節(Baalbeck International Festival)總有精彩演出,李希特、羅斯卓波維奇、卡拉揚等等都來過。
焦:您何時決定要成為音樂家?我知道您數學也很好,是否也考慮過音樂以外的人生方向?
艾:我雖然喜愛數學,但音樂永遠是首要。我在 13、14歲就展現出過人天賦,老師和父親都注意到我的音樂程度很高,但家父其實不希望我走音樂的路。他覺得這是很辛苦的人生,成家立業都難,鋼琴家的競爭尤其激烈,要有機運才能出頭。但他也沒有阻止我,仍然給我機會讓我到巴黎學習。雖然在他的想像中,我得到學位後就該回到黎巴嫩,找份穩定工作,偶爾開音樂會就好──當然,這不是我對自己的想像,但我必須證明我有能力實現抱負才行。倒是家母總是支持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她有非常好的耳朵,很早就能分辨出我的演奏和他人的不同。
焦:對中東世界而言,古典音樂中哪些作品比較接近您們的個性?
艾:首先是俄國音樂。這是強大、敏感、熱情,感性多過理性的音樂。並不是說俄國音樂不理性,而是理性不是最重要的元素。這和中東民風很接近。柴可夫斯基《悲愴交響曲》和拉赫曼尼諾夫《第二號鋼琴協奏曲》,一向是黎巴嫩最受歡迎的作品。再來就是西班牙音樂。這當然有歷史因素在其中,因為西班牙曾受穆斯林統治約750年。西班牙音樂的即興和歌唱,方式和阿拉伯音樂很相近,甚至行為模式也像,音樂滿是自豪、愛與激情。相較於此,法國音樂就比較冷,中東人普遍而言比較不理解。
焦:您也不理解嗎?
艾:是的。我小時候對俄國音樂很有好感,對德奧作品也很能理解,但始終不了解法國音樂。雖然我的老師在巴黎學習,也教我彈拉威爾《水戲》和德布西《為鋼琴的》組曲,我還是不很懂。既然如此,我就決定也到巴黎學,補強在法國音樂上的知識。我必須說這真是正確的決定,特別是和聲與對位課,讓我徹底認識法國音樂,更愛上拉威爾。在巴黎居住,也讓我熟悉法國人的行為模式,進而了解他們的音樂表現。
焦:您錄製了拉威爾鋼琴獨奏與協奏曲全集,成果相當傑出,可否跟我們分享您對拉威爾的研究心得?
艾:在和聲課上,老師曾特別分析德布西、拉威爾、佛瑞的風格,給我們高音旋律要學生以這三家風格做和聲寫作,因此我真的學到很多。但直到今日,佛瑞的鋼琴獨奏作品仍然和我不親,我喜愛的是他的室內樂、歌曲和《安魂曲》,德布西我也比較愛他的歌曲和管弦樂。拉威爾讓我著迷之處,在於他極其精練的筆法,作品是聲響、和聲、情緒、形式的完美結合,還有無可比擬的配器法。德布西想做真正的法國音樂;拉威爾當然也是法國,但他不只有法國,還有很強的巴斯克元素與古典精神,甚至用到阿拉伯與希臘調式。不過他的個性有一點很特別,就是他對什麼感受愈深,就愈把它藏起來。有人會覺得他的音樂冷,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焦:因此如何妥當表現拉威爾作品中的情感,就至為關鍵。以彈性速度而言,您認為他就是不希望有彈性速度,還是因為當時的演奏家常多用彈性速度,他才刻意嚴格要求演奏者不要用彈性速度?
艾:我認為是後者。拉威爾的作品充滿感情,但並不浪漫。在二十世紀之交,鋼琴家都以相當浪漫的方式演奏,但這不是他的風格。拉威爾若想說什麼,多半是暗示;真要明說,他會說得非常精確,譜上寫明一切,每個音都恰如其分。演奏者要發揮自己最大的才能來實現他的指示,而不是自顧自地浪漫演奏。面對於如此細膩精算的大師,我們要忠實,更該把自己放低,不要以為自己比拉威爾更懂他的作品。
焦:談到生活環境與作曲家,您現在住布魯塞爾,這可曾讓您更接近法朗克等比利時作曲家?
艾:其實沒有,哈哈。法朗克當然是好作曲家,他的和聲屬於十九世紀後期的試驗,想要擴張傳統和聲的範圍。比利時後來的勒庫和庸根(Joseph Jongen, 1873-1953)也是走這路線,或許針有什麼地域性的影響,但這樣的和聲語法對我來說並不自然。就擴張傳統和聲而言,手法最成功的,或許是拉赫曼尼諾夫,可惜大家多半看不到這點。
焦:您在巴黎向赫赫有名的松貢學習。和您之前的學習相比,他是否改造了您的鋼琴技巧?
艾:我是他很特別的學生。我在開始學琴的時候,就很自然地運用整個身體,演奏不同作曲家會用不同的施力方式。我在貝魯特的老師(莎琪桑)為了發展我的手指能力,反而需要限制我運用身體其他部位。對我而言,她是對的,而我也沒有變成傳統法式那種重心完全在手指的演奏。當我到松貢班上,他很驚訝的發現,我的演奏方式簡直就是他的教材,可以當其他學生的模範。才跟他上了兩堂課,松貢就說他不需要教我技巧了,但我們可以討論音樂。這也切合我的需要,因為我在音樂上還有好多要發展探索。
焦:松貢在音樂上如何指導您?
艾:松貢要求忠於樂譜,學生必須彈得非常準確:漸強記號如果從第二個音開始,就不能從第一個音開始大聲;強弱之間如果沒有標示其他術語,那就維持強奏,在弱奏記號出現時突然小聲。如此要求是極端了些,但也訓練我們嚴謹判讀所有指示。此外,他希望演奏如同說故事,不能失去即興感,也要設計戲劇效果,讓觀眾期待故事結果。演奏要呈現不同演員與不同表達,又必須以邏輯整合出具信服力的詮釋。這對鋼琴家格外重要,因為舞台上常只有一人唱獨角戲,必須想辦法讓觀眾聚焦在自己身上。松貢對我很有期待,在我之前,他雖然已有貝洛夫等著名學生,但還沒有人得到著名大賽冠軍。他給了我很多關於比賽的建議,包括如何贏得評審注意,雖然那不是我的風格──對我而言,音樂應該自然發生,為人生帶來快樂,而非旨在成功事業。
焦:您最後也果然在伊麗莎白大賽得到冠軍,還得到「評審一致通過獲得首獎」這樣的榮譽。
艾:我在巴黎高等畢業後,家父本來希望我能馬上回黎巴嫩,但貝魯特已陷入內戰,留在歐洲比較妥當,我也藉此準備比賽。一如我剛剛說的,我必須向父親證明我的能力,首獎自然成為我的夢想。我全力以赴,雖然我也知道我可以是很好的音樂家但沒有任何獎項。比賽奪冠對我意義非凡,這是我個人的榮譽,讓我有開展事業的信心,也是我家庭教育的榮譽,以及黎巴嫩與中東世界的榮譽──這是第一次有來自中東世界的音樂家,在著名國際大賽上奪冠。對受苦於內戰的黎巴嫩而言,這是很大的鼓勵。
焦:您那時本來已經進入巴黎高等音樂院的高級班,松貢卻要您自己發展,不需要在學校學了。
艾:松貢知道我有作曲能力,看過我的作品後也給予很多鼓勵。我想他看出我那時需要從自己內部發展,而不是持續借助外力。
焦:您最近出版了自己鋼琴獨奏作品的錄音,曲風相當清新可喜。可否談談您的創作?
艾:家父是很優秀的作曲家,耳濡目染之下,我從小也想作曲,也被家人鼓勵作曲,只是後來我發現我從演奏、詮釋中得到的快樂,和創作不分軒輊。我對創作沒有什麼大志,只是單純地把我內心浮現的樂思,經過組織後寫下來。我覺得詮釋者都該嘗試作曲。不一定要發表,而是體會如何以有限的記號表達思考,又如何提出具邏輯性的樂念。我常聽到很多演奏雖有不少精彩想法,但想法並不連貫,發展也不合理。如果能自己寫些作品,學習以作曲家的角度看樂曲,相信會有很大幫助。自己寫幾次,再看別人作品,也能知道樂曲中哪些是重點,哪些只是裝飾,也就不會在枝微末節上打轉。
焦:不過那時您已經準備好迎接演奏生涯了嗎?畢竟您才19歲而已。
艾:我那時只有五、六首協奏曲,所以每年我都會給自己兩段時間準備新協奏曲和獨奏會。我很早就知道我學得很快,能維持大量曲目,後來也的確演奏了極多作品,不過現在我只演奏我愛的音樂。我得獎後馬上有不少錄音邀約,但我都拒絕,過了三年我才覺得準備好。
焦:您的第一張錄音是普羅高菲夫最早四部作品:《第一號鋼琴奏鳴曲》(Op. 1)、《四首練習曲》(Op. 2)、《四首作品》(Op. 3)、《四首作品》(Op. 4)以及《A小調稍快板》與《D大調詼諧曲》兩首短曲,出版後立即得到唱片大獎。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仍是水準極高,選曲也極為獨特的專輯。當初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艾:第一張錄音,有如我給世界的音樂名片,我當然戒慎恐懼。普羅高菲夫早期作品技巧非常艱難,可以讓我好好發揮,而我也很肯定自己在風格上不會出錯。松貢就對我說︰「沒有人能批評你的普羅高菲夫。」我在伊麗莎白大賽決賽彈他的《第二號鋼琴協奏曲》,連馬卡洛夫都來恭喜我,稱讚那是「以我們應該演奏的方式演奏」。這讓我很安心,因為普羅高菲夫的確是我最愛的作曲家之一。既然這是最愛,我想盡可能探索他所有的作品,主流與非主流。我必須說,他實在有太多精彩但很少演奏的樂曲,因此這張錄音既向世界介紹鋼琴界的新面孔,也介紹新曲目,無論如何會有價值。
焦:為什麼普羅高菲夫這麼吸引您?
艾:我覺得普羅高菲夫是永遠的青年,音樂洋溢著青春的自由,心理上是帶著微笑的革命者,充滿能量以及對未來的信心,音樂非常健康。莫札特和蕭邦對我來說相當中性,普羅高菲夫則是成熟男人的陽剛,對男孩時期的我很有吸引力,現在我仍深深喜愛。此外,他的音樂都言之有物。以《第二號鋼琴協奏曲》來說,技巧極其困難,但不是為了困難而困難,而是以困難帶出更多表現。蕭邦也是如此,愈難的作品帶出的情感就愈豐富,絕非僅是技巧展示。
焦:您最近又錄了一張普羅高菲夫早期作品,即使在最大聲的強奏,都能保持音色與音質的美好。這實在很不容易。
艾:我天生會避免難聽的聲音,絕對不砸鋼琴。我小時候聽貝多芬交響曲,在最大聲的段落,聲音有厚度而不暴力,仍然很美。這給我很大的啟發。我以前也學過小提琴,音色和歌唱性對我始終很重要。我認為音樂演奏要能為耳朵帶來喜悅與快樂,聲音應該要美好,而這不意味就必須限縮表現力。蕭邦的音樂裡也可找到相當暴力的表達,但他始終要求優美的音色,討厭學生把強奏「彈得像狗叫」。攻擊性、挑釁的音樂,一樣能用美好聲音表現,關鍵在於找到結合兩者的方法。
焦:您怎麼看普羅高菲夫自己的鋼琴演奏錄音?
艾:他錄音時更是作曲家而非鋼琴家,我覺得那些錄音沒有展現他作為鋼琴家的最高水準,《第三號鋼琴協奏曲》也可感受到他的緊張。但即使如此,我們仍可欣賞他的演奏能力以及抒情特質,更重要的是沒有什麼敲擊聲響,在小品中有純粹精練、品味極高的表現。如果他專心演奏,應能和拉赫曼尼諾夫一樣,成為偉大鋼琴家。
焦:如此演奏和李希特──普羅高菲夫偏愛的詮釋者,其實相當不同。您怎麼看這種變化?
艾:李希特當然是令人尊敬的鋼琴家,但他的普羅高菲夫並不令我著迷。他的演奏偏向垂直面,而我更偏好水平面的延展。但無論如何,他是當時蘇聯最重要的鋼琴家,能為普羅高菲夫的作品帶來能見度。我覺得這至少顯示普羅高菲夫的作品能以不同美學表現,不是他的蘇聯時期作品就只能以李希特的方式演奏。
焦:您有最喜愛的鋼琴家嗎?
艾:在我成長時期,我最喜愛李帕第和波里尼,很常聽他們的錄音。不過後來我了解,如果要找到自己的聲音,腦子裡就不能都是別人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