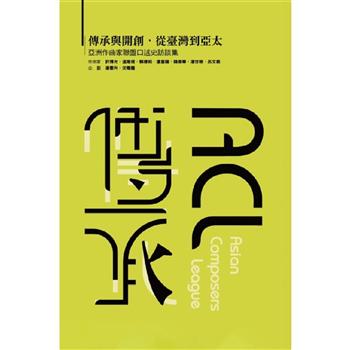(一)許常惠老師與他的教學
許老師的一生,可以說心懷對「生於斯、長於斯」的臺灣摯情、年少居住在日本所產生的情感,以及成年後留學法國文化孕育下的藝術情懷。
論及許老師,就不能不從人類學為背景談起。原住民,日據時代稱之為高砂族或高山族,二戰後,國民政府來臺稱為山胞,並於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一日公布憲法增修條文,將原住民稱呼正式納入憲法。然而地球,從來不專屬於任何生物,人類反而只是地球上的物種之一,誰先來,誰就先居住,也不會是永久,從上古歷史而言,是難以考證與定論的、我認為是不切實際的不平衡之詞,如臺東的八仙洞,發現八千年前的當時居民的骸骨,比現在被定位為原住民更久遠。人類學家研究揣測,這些人數千年前移居婆羅洲、幾內亞、或是更遠的澳洲,地理上從環狀太平洋島群延伸下去,成為現今概括性稱之為南島語系波里尼西亞人(Polynesian)。靠海的民族最能跨越洲際,藉由乘航的載運即可到海的另一端,對遠古的住民而言,海就是可以連接島與島的媒介。河洛人初到臺灣,以一包香菸或一些物質跟原住民換取如聚眾廣場社口的土地,占得極大的便宜!原住民沒有絕對的對價感,只對山川有感情,部落中必有一個聚眾的大廣場,廣場社口的地絕大部分已不屬於原住民。
人類考古學家陳奇祿先生曾論,自古多以北方人向南方移動,以此推論,現居臺灣的族群們可能有不少具有匈奴、鮮卑、蒙古或中亞各民族血統的後代,若是現今以DNA測定,全世界六十%以上具有來自非洲的血統,這是歷史使然。眾所皆知,臺灣多數居民千年前多來自河洛地區。當年我曾問許常惠老師:「到底我們要如何追尋及剖析民族音樂的根源?」許老師 :「歸根究底,一定要了解你一生所生長的地方,這是出發點。」從這個概念延伸,在音樂上即是「臺灣的民族音樂,是什麼?」千年以來,民族音樂的元素皆由後輩子孫取用因而流傳。可是概念的延伸,多所探尋其它民族音樂,尤其是地理上的鄰近民族族群。當初我與許老師、鍋島吉郎先生共同發起亞洲作曲家聯盟的創立,許老師另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一日創立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並邀請曾永義、史惟亮、採集民謠(民族音樂),其動機及動力皆起於此。
許常惠老師具有臺灣多元文化融和的特質,其中蘊含漢、日、法的文化背景,可說是洋溢著臺灣優質人格特色表象的菁英;許老師的文筆詞彙、意涵深入淺出,日文流暢,法文也是深入熟穩。我十五歲秋天,也是許老師回臺的第一年,跟他開始習樂,算是他從法返國後的第一批學生,如今當年多位同修都逝世了。許老師的上課風格跟別的教授不同,多數來聽課的學生都不只要學習一門技巧,而盼能深邃探究音樂藝術的意境。許老師也具有凝聚力的特質,對學生們亦師亦友。老師也會挑學生,但一到學校上大班課就一視同仁。當年有幾位學生的年齡還比老師年長,如「江浪樂集」李如璋,經營礦油行。陳泗治,是淡江中學校長。
許老師的直率性情,心胸開闊,一喝起酒來,膽子變大;除了音樂,生活上,酒,對他很重要!酒,不只是興趣,是一種主要的生活文化,他對酒有非常濃厚的感情。所謂「許常惠酒的文化」,亦即是與許老師特別有緣的學生,不會在一兩個鐘頭就結束課程,而是上到半天,甚至到深夜,中午晚上一起共餐,之後一起看電影,談論電影、音樂等⋯⋯成為師生生活的一部分,是「C'est La Vie」。回想當年經濟尚未發展的年代,人人都喜歡上許老師開的課,但有些學生沒有錢繳學費,比如李泰祥曾經欠了一年的學費,李爸爸深覺抱歉,特意牽一頭牛到臺北松江路許老師的住所,表示要替李泰祥繳學費。
許老師因材施教,對學生多採自由放任的態度。我的第一個作品是無調性,但有音形動機、旋律線條音作為元素,詞,採用漢朝班婕妤《怨歌行》、及唐代李白詩作《夜坐吟》所譜;許老師以此鼓勵我,並稱這可能是未來的隱性動機。他常說:「年輕人一開始就應該如此著筆。」又言:「作曲,原則上是沒辦法教的,但理論可以學,理論,是後人分析,是事後產生的。然藝術創作是非常自我、非常獨立。」就因如此,許老師對待每個學生,都是依據學生的性格做引導式的教學。
上課的理論內容以經典作品為主,如貝多芬九大交響曲、奏鳴曲,拉威爾管弦樂或華格納歌劇,莫札特的晚期交響曲,尤其是後面三大交響曲。也涵蓋古希臘、羅馬、格雷果聖歌、中古世紀、文藝復興、巴洛克、古典音樂等。由於許老師也是小提琴家,自然也從小提琴或鋼琴、大提琴的室內樂及協奏曲等,都作作品的深層分析。
許常惠老師在法國的名師都是頂尖的音樂教育家,像一代宗師梅湘(Olivier Messiaen)、若利維(André Jolivet)、夏野(Jacques Chailley)1,都是功力紮實深厚的作曲家。許老師當年在巴黎的學習,過程艱辛,生活上也是節約省用。我覺得許老師於一九五九年回臺,對他而言太早了一點,如果他能在歐洲再多待幾年,或許就會在歐洲大發光輝。但反過來,卻覺得在這個時間回來,對臺灣現代音樂的啟發而言,則是最恰當好的時機,我是他非學院派的兩位學生之一,另外一位就是比我小一歲的丘延亮。
我隨許老師密集習樂三年多,漸漸成了他的學務助理,他第一次在臺灣大學演講梅湘作品《杜蘭嘉里拉交響曲》( Turangalila Symphony),我也須做好充分的準備。他反覆討論作曲家的表象與推論其內在真涵,演講聽來真是津津有味,助理這身份也使我受惠良多。兩年後,「現代音樂研究會」成立了,成員在每個月的聚會,都提出一個曲子,一起研論。有一回,在李奎然位於迪化街老家的聚會,我提出了新作《孕》,這首曲子後來由陳學同編舞,也邀請美國指揮家湯瑪斯(Michael Tilson Thomas)來參與研討,和我同年,目前是美國最重要的大指揮家之一。
許老師教導配器,直言法國作曲家拉威爾的配器理論是必要學習,從《波列路》(Boléro)開始,到華格納、理查史特勞斯、史特拉汶斯基等,都要深入學習。而分析旋律,則從不同樂器的轉移,許老師讓我們先把旋律線挑出,然而困難之處在於成分的多寡、輕重,如同燒一盤菜,鹽放多了、糖放少了,味道就不一樣,配器亦同。許老師也指出,音樂與數學、建築、物理皆息息相關,作曲,如同建築,結構體是首要。再者,須有數學觀念,一般而言,作曲家的數學基礎都很好。另一方面則需槓桿原理,忽高忽低,有其物理性;最難以言論的就是靈感,心靈效應,是一種化學。因此,作曲是集化學、數學、物理、建築為一體,也有一說,科學與藝術是一體兩面。
多年在許老師的耳濡目染下和創作,我已有自己精細分析的心得,如素樂(極簡主義),重點在於重複,但難處是在於選擇採用那個音、音組、音量、音色,音長。古典時期音樂重複次數較少,非洲民族音樂則有許多重複,宗教音樂的樂句長而沉穩,引導人的情緒進入一個沉著的狀態,諸如上述的創作方式,皆著重在於拿捏。我的另一作品《樓蘭女》,也採用了這個概念,當劇情尚未展開前,音樂先開始營造氛圍,載以重力打擊樂器、反串、對比衝撞,目的在於挑動情緒,一層一層的疊加,堆積到最後的高潮,再次大轉變,轉折後以民謠風轉換情景,之後轉移到沉靜來彰顯角色心理變化的情境,此作品也部分以電子音樂為媒介。
許老師的一生,可以說心懷對「生於斯、長於斯」的臺灣摯情、年少居住在日本所產生的情感,以及成年後留學法國文化孕育下的藝術情懷。
論及許老師,就不能不從人類學為背景談起。原住民,日據時代稱之為高砂族或高山族,二戰後,國民政府來臺稱為山胞,並於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一日公布憲法增修條文,將原住民稱呼正式納入憲法。然而地球,從來不專屬於任何生物,人類反而只是地球上的物種之一,誰先來,誰就先居住,也不會是永久,從上古歷史而言,是難以考證與定論的、我認為是不切實際的不平衡之詞,如臺東的八仙洞,發現八千年前的當時居民的骸骨,比現在被定位為原住民更久遠。人類學家研究揣測,這些人數千年前移居婆羅洲、幾內亞、或是更遠的澳洲,地理上從環狀太平洋島群延伸下去,成為現今概括性稱之為南島語系波里尼西亞人(Polynesian)。靠海的民族最能跨越洲際,藉由乘航的載運即可到海的另一端,對遠古的住民而言,海就是可以連接島與島的媒介。河洛人初到臺灣,以一包香菸或一些物質跟原住民換取如聚眾廣場社口的土地,占得極大的便宜!原住民沒有絕對的對價感,只對山川有感情,部落中必有一個聚眾的大廣場,廣場社口的地絕大部分已不屬於原住民。
人類考古學家陳奇祿先生曾論,自古多以北方人向南方移動,以此推論,現居臺灣的族群們可能有不少具有匈奴、鮮卑、蒙古或中亞各民族血統的後代,若是現今以DNA測定,全世界六十%以上具有來自非洲的血統,這是歷史使然。眾所皆知,臺灣多數居民千年前多來自河洛地區。當年我曾問許常惠老師:「到底我們要如何追尋及剖析民族音樂的根源?」許老師 :「歸根究底,一定要了解你一生所生長的地方,這是出發點。」從這個概念延伸,在音樂上即是「臺灣的民族音樂,是什麼?」千年以來,民族音樂的元素皆由後輩子孫取用因而流傳。可是概念的延伸,多所探尋其它民族音樂,尤其是地理上的鄰近民族族群。當初我與許老師、鍋島吉郎先生共同發起亞洲作曲家聯盟的創立,許老師另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一日創立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並邀請曾永義、史惟亮、採集民謠(民族音樂),其動機及動力皆起於此。
許常惠老師具有臺灣多元文化融和的特質,其中蘊含漢、日、法的文化背景,可說是洋溢著臺灣優質人格特色表象的菁英;許老師的文筆詞彙、意涵深入淺出,日文流暢,法文也是深入熟穩。我十五歲秋天,也是許老師回臺的第一年,跟他開始習樂,算是他從法返國後的第一批學生,如今當年多位同修都逝世了。許老師的上課風格跟別的教授不同,多數來聽課的學生都不只要學習一門技巧,而盼能深邃探究音樂藝術的意境。許老師也具有凝聚力的特質,對學生們亦師亦友。老師也會挑學生,但一到學校上大班課就一視同仁。當年有幾位學生的年齡還比老師年長,如「江浪樂集」李如璋,經營礦油行。陳泗治,是淡江中學校長。
許老師的直率性情,心胸開闊,一喝起酒來,膽子變大;除了音樂,生活上,酒,對他很重要!酒,不只是興趣,是一種主要的生活文化,他對酒有非常濃厚的感情。所謂「許常惠酒的文化」,亦即是與許老師特別有緣的學生,不會在一兩個鐘頭就結束課程,而是上到半天,甚至到深夜,中午晚上一起共餐,之後一起看電影,談論電影、音樂等⋯⋯成為師生生活的一部分,是「C'est La Vie」。回想當年經濟尚未發展的年代,人人都喜歡上許老師開的課,但有些學生沒有錢繳學費,比如李泰祥曾經欠了一年的學費,李爸爸深覺抱歉,特意牽一頭牛到臺北松江路許老師的住所,表示要替李泰祥繳學費。
許老師因材施教,對學生多採自由放任的態度。我的第一個作品是無調性,但有音形動機、旋律線條音作為元素,詞,採用漢朝班婕妤《怨歌行》、及唐代李白詩作《夜坐吟》所譜;許老師以此鼓勵我,並稱這可能是未來的隱性動機。他常說:「年輕人一開始就應該如此著筆。」又言:「作曲,原則上是沒辦法教的,但理論可以學,理論,是後人分析,是事後產生的。然藝術創作是非常自我、非常獨立。」就因如此,許老師對待每個學生,都是依據學生的性格做引導式的教學。
上課的理論內容以經典作品為主,如貝多芬九大交響曲、奏鳴曲,拉威爾管弦樂或華格納歌劇,莫札特的晚期交響曲,尤其是後面三大交響曲。也涵蓋古希臘、羅馬、格雷果聖歌、中古世紀、文藝復興、巴洛克、古典音樂等。由於許老師也是小提琴家,自然也從小提琴或鋼琴、大提琴的室內樂及協奏曲等,都作作品的深層分析。
許常惠老師在法國的名師都是頂尖的音樂教育家,像一代宗師梅湘(Olivier Messiaen)、若利維(André Jolivet)、夏野(Jacques Chailley)1,都是功力紮實深厚的作曲家。許老師當年在巴黎的學習,過程艱辛,生活上也是節約省用。我覺得許老師於一九五九年回臺,對他而言太早了一點,如果他能在歐洲再多待幾年,或許就會在歐洲大發光輝。但反過來,卻覺得在這個時間回來,對臺灣現代音樂的啟發而言,則是最恰當好的時機,我是他非學院派的兩位學生之一,另外一位就是比我小一歲的丘延亮。
我隨許老師密集習樂三年多,漸漸成了他的學務助理,他第一次在臺灣大學演講梅湘作品《杜蘭嘉里拉交響曲》( Turangalila Symphony),我也須做好充分的準備。他反覆討論作曲家的表象與推論其內在真涵,演講聽來真是津津有味,助理這身份也使我受惠良多。兩年後,「現代音樂研究會」成立了,成員在每個月的聚會,都提出一個曲子,一起研論。有一回,在李奎然位於迪化街老家的聚會,我提出了新作《孕》,這首曲子後來由陳學同編舞,也邀請美國指揮家湯瑪斯(Michael Tilson Thomas)來參與研討,和我同年,目前是美國最重要的大指揮家之一。
許老師教導配器,直言法國作曲家拉威爾的配器理論是必要學習,從《波列路》(Boléro)開始,到華格納、理查史特勞斯、史特拉汶斯基等,都要深入學習。而分析旋律,則從不同樂器的轉移,許老師讓我們先把旋律線挑出,然而困難之處在於成分的多寡、輕重,如同燒一盤菜,鹽放多了、糖放少了,味道就不一樣,配器亦同。許老師也指出,音樂與數學、建築、物理皆息息相關,作曲,如同建築,結構體是首要。再者,須有數學觀念,一般而言,作曲家的數學基礎都很好。另一方面則需槓桿原理,忽高忽低,有其物理性;最難以言論的就是靈感,心靈效應,是一種化學。因此,作曲是集化學、數學、物理、建築為一體,也有一說,科學與藝術是一體兩面。
多年在許老師的耳濡目染下和創作,我已有自己精細分析的心得,如素樂(極簡主義),重點在於重複,但難處是在於選擇採用那個音、音組、音量、音色,音長。古典時期音樂重複次數較少,非洲民族音樂則有許多重複,宗教音樂的樂句長而沉穩,引導人的情緒進入一個沉著的狀態,諸如上述的創作方式,皆著重在於拿捏。我的另一作品《樓蘭女》,也採用了這個概念,當劇情尚未展開前,音樂先開始營造氛圍,載以重力打擊樂器、反串、對比衝撞,目的在於挑動情緒,一層一層的疊加,堆積到最後的高潮,再次大轉變,轉折後以民謠風轉換情景,之後轉移到沉靜來彰顯角色心理變化的情境,此作品也部分以電子音樂為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