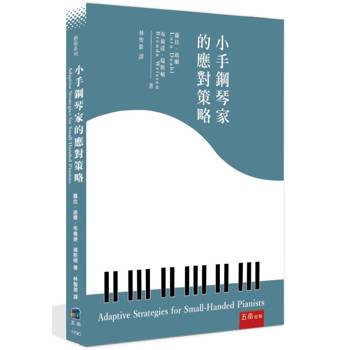第二章 演奏肢體運用之基本原則(節錄)
音樂家以演奏技巧為媒介,將記載於樂譜上或心中的音樂具體轉化為聲音。然而,演奏鋼琴的方式有千千萬萬種;有多少位鋼琴家的存在,便有多少種彈奏鋼琴的方式。本章無意總結闡述這些千變萬化的技巧,也不支持特定學派的演奏方式,而是想從生理學和解剖學的角度來理解鋼琴演奏所需的肢體運用方式,期能清楚地剖析小手鋼琴家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
有效率的演奏法則
在鋼琴被發明後的最初200 年間,演奏技巧的建立主要來自於知名鋼琴家的親身經驗,這些經驗由師徒相承,代代傳遞。自十九世紀起,許多以鋼琴彈奏技巧聞名的大師,包括克雷門悌(Muzio Clementi, 1752-1832)、胡麥爾(Johann Nepomuk Hummel, 1778-1837)、徹爾尼(Carl Czerny, 1791-1857) 和卡爾克布倫納(Friedrich Wilhelm Kalkbrenner, 1785-1849) 等鋼琴家開始出版屬於技巧教程類的練習曲集,在西方音樂教育中被廣泛地流傳和使用。及至二十世紀後,鋼琴家們漸漸傾向於借助科學知識,希望找到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定則。這方面的先驅奧特曼求諸解剖學、物理學以及新興的生物力學等科學的原理,尋求以實證而非主觀的角度來研究鋼琴技巧。奧特曼於1929 年出版的《鋼琴技巧的生理力學》一書受到嚴厲批評,因為這種方法嚴重衝擊了傳統的音樂演奏教育。許多鋼琴家認為,客觀地分析演奏技巧和創造美好音樂是相抵觸的。然而,隨著時代沿革,鋼琴家們漸漸能接受,科學研究對理解人類生理結構上的可能性及限制性是很有幫助的。近年來,音樂界也開始重視頻繁發生的職業傷害,因而越來越多的鋼琴家從生物力學的角度來思考和探索更健康及更有效率的演奏方式。
想要達成這樣的目標,我們需要鑽研一些相關的科學領域,來了解人類生理構造與鋼琴演奏需求的關係。人體工學(ergonomics) 是研究人類、人類的物品與工具,以及他們所處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學科。與人體工學相關的鋼琴演奏研究大多集中在認知/心理動作(cognitive/psychomotor problems)、骨骼肌肉及人體測量學(anthropometric) 等方面:認知/心理動作的研究探討大腦如何吸收和處理外來資訊,而這整個過程又如何影響身體的動作。了解演奏者如何能在練習或演奏時維持足夠的注意力,便是一個認知/心理動作研究與鋼琴演奏的相關實例。又或者當我們想強行超越人類的生理限制時,就會傷筋動骨;要解決這些演奏造成的肌肉骨骼傷害,就要重新找尋並制定符合演奏者身量和能力的演奏方式。人體測量學(anthropometry) 就聚焦研究人體與工作界面的合適度。這個學科通常使用明確的測量單位,包括長度、重量和體積等。對於鋼琴家來說,人體測量學與演奏相關的考量包括椅子和鍵盤之間的距離、譜架相對於視線的高度,當然還有鍵盤與雙手間的相對尺寸。
與人體工學類似,生物力學(biomechanics) 考慮人體的結構、功能和極限。生物力學集結了傳統的工程科學,包括應用力學、連續力學、機械分析和結構分析,將這些研究應用在生物的結構系統上。此外,運動機能學(kinesiology) 和運動學(kinematics) 在生物力學中也十分重要。運動機能學是研究人體運動的學科,而運動學是古典力學的一個分支,描述著點、物體和物群的運動。牛頓的古典力學為這些學科的根源,會於本章後段再加以討論。
以上提及的每個學科都幫助我們更加了解對身體運動有幫助或干擾的因素,並提供了觀點,有利於鋼琴家們評估制定合宜的鋼琴技巧。【表2.1】總結了這些因素,並將於本章擇要詳加討論。
施力動作時,負載的力量、施力頻率和疲勞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影響身體的主要因素。突如其來的一次性強力,例如自樓梯上摔落、足球的強力撞擊或交通事故,都可能造成對身體組織的急性創傷損害。5然而,傷害也可能是由反覆施加的較小力量,逐漸積累而造成的。鋼琴演奏相關的傷害通常是後者。畢竟彈奏鋼琴所使用的力量通常不足以在單次施力中引起急性組織損壞,只是這些不當施力若一而再,再而三,重複累積到一定的量後,即便是輕微的施力也可能引起疼痛或傷害,如【圖2.1】所示。
需要長時間進行重複性工作的職業—例如在電腦鍵盤上打字、在倉庫裡裝卸貨品、在裝配線上操作機器,或是—當然—彈鋼琴,重複性使力傷害(Repetitive Strain Injuries,簡稱RSI)的發生率都很高。重複性使力傷害通常涉及身體的軟組織,例如肩膀、上臂、前臂、手腕和手指的肌腱和神經,但也可能影響這些區域的關節或肌肉。儘管義大利的拉馬齊尼醫師(Bernardino Ramazzini,1633-1714) 在十八世紀就注意到了這個現象,重複性使力傷害要等到在1980年代才受到更多的重視。人體工程學專家確認以下因素是主要風險因素:
.不自然的關節姿勢,包括手腕姿勢偏離。關節扭曲程度越大,受傷的風險便會顯著增加。
.對樞紐關節(hinge joints)(如手腕)強施力量。對車軸關節(pivot joints)(如手肘)強加施力同樣有風險,但程度較輕微。
.在短時間內進行高重複性的動作。隨著時間累積,受傷風險會以指數性飆增。
.個人因素,如神經性疾病、關節炎、循環問題、雌激素分泌降低以及較小的手或手腕尺寸等問題。
若同時有數個以上的問題,受傷的風險更會急劇上升。
人體工學還能讓我們進一步了解肌肉骨骼疲勞與受傷之間的關係,簡單來說,當肌肉無法持續以我們所需的強度或力道出力時,就進入肌肉疲勞的狀態。儘管我們尚未完全理解肌肉疲勞在構成傷害中的確切角色,肌肉疲勞被認為是導致肌肉傷害的風險因素之一。首先,疲勞的感覺難以被量化和描述。此外,如前所述,這些傷害可能是隨著時間長期累積的,甚至是由不費力的小動作逐漸造成的。研究人員認為,當過強或重複過多的外力加諸於健康的身體組織,並超過身體自我修復機制的限度時,肌肉疲勞會加劇漸進性的肌肉損傷。一旦不當外力大於身體所能負荷的閾值,肌肉就開始產生微小的撕裂傷,此時如果不中止不當外力或重複的動作,這些撕裂傷便將擴大,加劇傷害程度。
「身體究竟能承受多少外力」這個問題也很難量化。多強的力道算「強」呢?在人體工學的研究中,力量的大小,通常以百分比來呈現相對於該物體結構組織的最大承載力。不過身體的最大承載力不只無法用確切的數值來定義,個體差異也很大。根據疲勞破壞理論(fatigue failure theory),物體的最大承載力是指經一次性的外力衝擊而導致組織撕裂或損毀的力道。當力道低於這個一次性最大值時,此物體便能接受更多次數的衝擊,才會讓組織斷裂。以這個邏輯繼續向下推,當力道小到一個程度時,重複的施力並不會導致物體組織的傷害。這個相對安全的力道一般被定義為最大承載力的30%。也因此,理論上有一個理想的緩衝區,以此安全的力道反覆施力,並不會導致物體組織損毀疲乏。
然而,就鋼琴演奏面來說,我們不確定這個緩衝區的理想範圍究竟在哪裡。首先,不同於物體,人體能自我修復,不過,修復的速率難以預測,也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加上每個人的狀態也不盡相同。其次,基於道德因素,我們無法損毀人體以測量精準的最大承載力數據。最後,人體的動作仰賴許多肢體的整合,很難只量化單一身體部位所出的力氣,因此也無法計算在執行特定動作時,個別部位動用的力道會占多少最大承載力的百分比。出於以上原因,我們無法精確推斷身體中每個演奏相關部位的最大承載力,自然也無法量化哪裡使用多少力氣,或將重複動作控制在多少次數內,就能落在安全緩衝區中而不受傷。自然,用於彈奏鋼琴的力量不可能大於身體的最大承載力,不然就只能演出一次然後直接受傷。不過,肌肉疲勞明顯地影響鋼琴家的工作效率,並容易導致演奏相關的運動傷害。此外,手小的鋼琴家在演奏時可能更容易產生肌肉疲勞;尤其在需要演奏連續大音程和弦之處更為嚴重。
音樂家以演奏技巧為媒介,將記載於樂譜上或心中的音樂具體轉化為聲音。然而,演奏鋼琴的方式有千千萬萬種;有多少位鋼琴家的存在,便有多少種彈奏鋼琴的方式。本章無意總結闡述這些千變萬化的技巧,也不支持特定學派的演奏方式,而是想從生理學和解剖學的角度來理解鋼琴演奏所需的肢體運用方式,期能清楚地剖析小手鋼琴家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
有效率的演奏法則
在鋼琴被發明後的最初200 年間,演奏技巧的建立主要來自於知名鋼琴家的親身經驗,這些經驗由師徒相承,代代傳遞。自十九世紀起,許多以鋼琴彈奏技巧聞名的大師,包括克雷門悌(Muzio Clementi, 1752-1832)、胡麥爾(Johann Nepomuk Hummel, 1778-1837)、徹爾尼(Carl Czerny, 1791-1857) 和卡爾克布倫納(Friedrich Wilhelm Kalkbrenner, 1785-1849) 等鋼琴家開始出版屬於技巧教程類的練習曲集,在西方音樂教育中被廣泛地流傳和使用。及至二十世紀後,鋼琴家們漸漸傾向於借助科學知識,希望找到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定則。這方面的先驅奧特曼求諸解剖學、物理學以及新興的生物力學等科學的原理,尋求以實證而非主觀的角度來研究鋼琴技巧。奧特曼於1929 年出版的《鋼琴技巧的生理力學》一書受到嚴厲批評,因為這種方法嚴重衝擊了傳統的音樂演奏教育。許多鋼琴家認為,客觀地分析演奏技巧和創造美好音樂是相抵觸的。然而,隨著時代沿革,鋼琴家們漸漸能接受,科學研究對理解人類生理結構上的可能性及限制性是很有幫助的。近年來,音樂界也開始重視頻繁發生的職業傷害,因而越來越多的鋼琴家從生物力學的角度來思考和探索更健康及更有效率的演奏方式。
想要達成這樣的目標,我們需要鑽研一些相關的科學領域,來了解人類生理構造與鋼琴演奏需求的關係。人體工學(ergonomics) 是研究人類、人類的物品與工具,以及他們所處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學科。與人體工學相關的鋼琴演奏研究大多集中在認知/心理動作(cognitive/psychomotor problems)、骨骼肌肉及人體測量學(anthropometric) 等方面:認知/心理動作的研究探討大腦如何吸收和處理外來資訊,而這整個過程又如何影響身體的動作。了解演奏者如何能在練習或演奏時維持足夠的注意力,便是一個認知/心理動作研究與鋼琴演奏的相關實例。又或者當我們想強行超越人類的生理限制時,就會傷筋動骨;要解決這些演奏造成的肌肉骨骼傷害,就要重新找尋並制定符合演奏者身量和能力的演奏方式。人體測量學(anthropometry) 就聚焦研究人體與工作界面的合適度。這個學科通常使用明確的測量單位,包括長度、重量和體積等。對於鋼琴家來說,人體測量學與演奏相關的考量包括椅子和鍵盤之間的距離、譜架相對於視線的高度,當然還有鍵盤與雙手間的相對尺寸。
與人體工學類似,生物力學(biomechanics) 考慮人體的結構、功能和極限。生物力學集結了傳統的工程科學,包括應用力學、連續力學、機械分析和結構分析,將這些研究應用在生物的結構系統上。此外,運動機能學(kinesiology) 和運動學(kinematics) 在生物力學中也十分重要。運動機能學是研究人體運動的學科,而運動學是古典力學的一個分支,描述著點、物體和物群的運動。牛頓的古典力學為這些學科的根源,會於本章後段再加以討論。
以上提及的每個學科都幫助我們更加了解對身體運動有幫助或干擾的因素,並提供了觀點,有利於鋼琴家們評估制定合宜的鋼琴技巧。【表2.1】總結了這些因素,並將於本章擇要詳加討論。
施力動作時,負載的力量、施力頻率和疲勞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影響身體的主要因素。突如其來的一次性強力,例如自樓梯上摔落、足球的強力撞擊或交通事故,都可能造成對身體組織的急性創傷損害。5然而,傷害也可能是由反覆施加的較小力量,逐漸積累而造成的。鋼琴演奏相關的傷害通常是後者。畢竟彈奏鋼琴所使用的力量通常不足以在單次施力中引起急性組織損壞,只是這些不當施力若一而再,再而三,重複累積到一定的量後,即便是輕微的施力也可能引起疼痛或傷害,如【圖2.1】所示。
需要長時間進行重複性工作的職業—例如在電腦鍵盤上打字、在倉庫裡裝卸貨品、在裝配線上操作機器,或是—當然—彈鋼琴,重複性使力傷害(Repetitive Strain Injuries,簡稱RSI)的發生率都很高。重複性使力傷害通常涉及身體的軟組織,例如肩膀、上臂、前臂、手腕和手指的肌腱和神經,但也可能影響這些區域的關節或肌肉。儘管義大利的拉馬齊尼醫師(Bernardino Ramazzini,1633-1714) 在十八世紀就注意到了這個現象,重複性使力傷害要等到在1980年代才受到更多的重視。人體工程學專家確認以下因素是主要風險因素:
.不自然的關節姿勢,包括手腕姿勢偏離。關節扭曲程度越大,受傷的風險便會顯著增加。
.對樞紐關節(hinge joints)(如手腕)強施力量。對車軸關節(pivot joints)(如手肘)強加施力同樣有風險,但程度較輕微。
.在短時間內進行高重複性的動作。隨著時間累積,受傷風險會以指數性飆增。
.個人因素,如神經性疾病、關節炎、循環問題、雌激素分泌降低以及較小的手或手腕尺寸等問題。
若同時有數個以上的問題,受傷的風險更會急劇上升。
人體工學還能讓我們進一步了解肌肉骨骼疲勞與受傷之間的關係,簡單來說,當肌肉無法持續以我們所需的強度或力道出力時,就進入肌肉疲勞的狀態。儘管我們尚未完全理解肌肉疲勞在構成傷害中的確切角色,肌肉疲勞被認為是導致肌肉傷害的風險因素之一。首先,疲勞的感覺難以被量化和描述。此外,如前所述,這些傷害可能是隨著時間長期累積的,甚至是由不費力的小動作逐漸造成的。研究人員認為,當過強或重複過多的外力加諸於健康的身體組織,並超過身體自我修復機制的限度時,肌肉疲勞會加劇漸進性的肌肉損傷。一旦不當外力大於身體所能負荷的閾值,肌肉就開始產生微小的撕裂傷,此時如果不中止不當外力或重複的動作,這些撕裂傷便將擴大,加劇傷害程度。
「身體究竟能承受多少外力」這個問題也很難量化。多強的力道算「強」呢?在人體工學的研究中,力量的大小,通常以百分比來呈現相對於該物體結構組織的最大承載力。不過身體的最大承載力不只無法用確切的數值來定義,個體差異也很大。根據疲勞破壞理論(fatigue failure theory),物體的最大承載力是指經一次性的外力衝擊而導致組織撕裂或損毀的力道。當力道低於這個一次性最大值時,此物體便能接受更多次數的衝擊,才會讓組織斷裂。以這個邏輯繼續向下推,當力道小到一個程度時,重複的施力並不會導致物體組織的傷害。這個相對安全的力道一般被定義為最大承載力的30%。也因此,理論上有一個理想的緩衝區,以此安全的力道反覆施力,並不會導致物體組織損毀疲乏。
然而,就鋼琴演奏面來說,我們不確定這個緩衝區的理想範圍究竟在哪裡。首先,不同於物體,人體能自我修復,不過,修復的速率難以預測,也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加上每個人的狀態也不盡相同。其次,基於道德因素,我們無法損毀人體以測量精準的最大承載力數據。最後,人體的動作仰賴許多肢體的整合,很難只量化單一身體部位所出的力氣,因此也無法計算在執行特定動作時,個別部位動用的力道會占多少最大承載力的百分比。出於以上原因,我們無法精確推斷身體中每個演奏相關部位的最大承載力,自然也無法量化哪裡使用多少力氣,或將重複動作控制在多少次數內,就能落在安全緩衝區中而不受傷。自然,用於彈奏鋼琴的力量不可能大於身體的最大承載力,不然就只能演出一次然後直接受傷。不過,肌肉疲勞明顯地影響鋼琴家的工作效率,並容易導致演奏相關的運動傷害。此外,手小的鋼琴家在演奏時可能更容易產生肌肉疲勞;尤其在需要演奏連續大音程和弦之處更為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