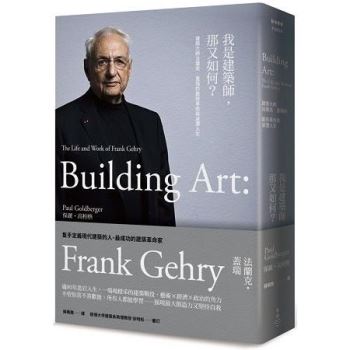蓋瑞不喜歡稱自己是藝術家或雕塑家,他告訴採訪者,部分的原因是「有一些藝術家覺得,為有廁所的建築物冠上『藝術』一詞是對他們的一種冒犯」。在一次早期的訪問中,被問及是否認為自己是個藝術家時,蓋瑞斬釘截鐵地回應「不,我是建築師」,這幾個字幾乎成為持誦的箴言。但毋庸置疑,蓋瑞比大多數建築師更投入創造極富表現力的建築物,而在畢爾包的美術館開幕後,他的名字幾乎與建築即創造表現形式的概念劃上等號。撇開貼標籤不談,認識蓋瑞最久的老朋友之一、洛杉磯藝術家湯尼.伯蘭特(Tony Berlant)坦言,「你可以說法蘭克是在洛杉磯嶄露頭角的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沒第二句話。我認為他就是如此。」另一位洛杉磯雕塑家比利.阿爾本斯頓(Billy Al Bengston)的評價甚至更高:「我想法蘭克是當代世界最頂尖的藝術家。」
好評如潮的畢爾包若帶來任何挑戰,那就是如何避免成為僅僅是個「品牌」,蓋瑞的確是個名牌,繼續以建築師身分向前跨進;對蓋瑞而言,這不只意味著繼續設計建築,而是要做得跟以往一樣有新意,甚至抗拒許多可把他的知名建築物轉成慣用手法,繼而到處複製的機會。「成功比失敗更難應付得多,」蓋瑞曾說。那是他的肺腑之言。蓋瑞不想重複自己的創作,但觀察者一看到畢爾包之後誕生的建築物,同樣擁有奔放弧形形式的金屬、玻璃或石材,就認為無論它們的外觀多麼令人驚豔,都不過是複製前作的模式,這種反應令他泄氣。以蓋瑞的觀點來看,那些建築物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人們認為後畢爾包作品不過是古根漢美術館原創設計的延續,其實他們並不明白蓋瑞真正完成的是創造一種整體而言新的建築語言,在每一棟新建築物中,以略微不同的方式運用該語言來進行某些表達。
建築師和評論家傾向於贊同這個富共鳴的觀點,關於蓋瑞的報導,一般比同世代其他建築師來得好。不過,名氣當然也帶來另一面,蓋瑞的聲譽幾乎可確保那不恰當卻尖刻的稱號「明星建築師」與他的名字如影隨形。這個詞油腔滑調地合併兩個意思:名氣的短暫燦爛與對設計的熱中追求,難怪讓蓋瑞厭惡。他可能是大眾心目中典型的明星建築師,但對他來說,那個詞徹底曲解他的作品,隱喻他的建築無非就是吸睛、華而不實的造形。儘管蓋瑞公開聲稱自己對這個稱號不快,卻不討厭名氣本身,而他有一些行為似乎是計畫好要提高自己的名聲,而不是極力貶低。他允許電視節目《辛普森家庭》編寫一集譏諷他的內容;接受Tiffany & Co.的邀請,為店面及型錄設計珠寶和其他物品;還以最喜愛的運動冰上曲棍球為靈感,設計伏特加酒瓶、手錶和家具。(從加拿大的童年到邁入七十,他都有打冰上曲棍球。)居住洛杉磯六十載後,蓋瑞認識的娛樂圈人脈比一般建築師更廣,他讓導演好友薛尼.波拉克(Sydney Pollack)和一名攝影師跟拍數月,製作向他致敬的紀錄片,波拉克將影片命名為《速寫法蘭克.蓋瑞》(Sketches of Frank Gehry)。
蓋瑞或許是典型的明星建築師,卻熟練地不去表現明星那一面的舉止。二○一四年,蓋瑞的第一個倫敦建案揭幕之際,英國《建築師雜誌》(Architects’ Journal)安排一場攝影訪談,那件作品位於巴特西發電廠(Battersea Power Station),屬住商複合建築群,採訪者問蓋瑞為什麼過去不曾在倫敦設計任何作品。蓋瑞的回答一如往常,顯得滿不在乎又謙卑;他說,沒人問過我。他的回應似乎讓採訪者失望,對方看來是希望蓋瑞藉機咆哮一番,批評大型建築物要在倫敦取得核准程序艱難,有損他尊貴的建築師地位。相反地,蓋瑞的回應比較像是在說,他會樂意做任何設計,即使是小案子,只是一直等待有人打電話詢問而已。他說,那裡可沒有行銷部門在為他宣傳。在影片中,他看上去慈祥甚於雄心壯志,彷彿他是一間小工作室的苦當家,而不是鼎鼎大名的建築師,領導著世界知名的事務所。
這是蓋瑞式的經典演出:反明星化的建築師,再次暗示蓋瑞的性格多麼像是一半萊特與一半伍迪.艾倫的組合。事實上,一方面他會經常抱怨工作不夠多,一方面又在接受英國雜誌訪問的時期,忙著許多不同規模的計畫案;每每發現客戶的案子不夠刺激,或者感覺客戶對他的建築不夠投入,就會予以回絕,不想再談。他對自己的靈活性相當自豪,可是只願意展現給對的客戶,那些事前清楚表示喜歡他的作品,渴望擁有一件法蘭克.蓋瑞的人。如果你想要美國建築師理查.麥爾(Richard Meier)風格的白色時髦華廈,或是諾曼.佛斯特(Norman Foster)風格的玻璃高層建築,抑或美國新古典建築師羅伯特.史特恩(Robert Stern)打造的傳統大樓,找蓋瑞都是毫無意義的。蓋瑞指望業主會自己選擇,但他總是無法百分之百確定,他知道對方能夠自在與他相處,願意放手讓他探索的客戶,才能讓他舒坦地進行工作。
***
蓋瑞多年來在建築圈一直享有盛名,但一九九七年畢爾包古根漢開幕後,他開始急速攀升至名人寶座,成為繼萊特之後最知名的美國建築師。儘管活躍的年代相距四十年,兩人都為同一機構設計出開創性、廣受歡迎的美術館,難免有人把兩位法蘭克拿來相互比較。然而事實上,萊特與蓋瑞的共通點除了名字、對建築的熱情投入,以及發想出有別於過去的新穎設計的天賦異稟,兩人內在的性格一如他們設計的建築物,幾乎沒有任何相似之處。萊特某種程度是獨裁者,政治立場保守,而且自戀;他無力承認過錯,並製造出以自我為中心的小團體,有著如異教崇拜般的虔誠。萊特的態度似乎是,假如你不喜歡他的建築,原因一定是你不懂得欣賞偉大的創作。
蓋瑞較傾向自我懷疑。他渴望關愛和接納,希望自己的建築討人喜歡,有時似乎會把對作品的認同與對他個人的認同這兩件事近乎視為一體看待。「對法蘭克來說,在他內心深處,感覺被需要及被愛是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透過認同他的建築,」蓋瑞的老友芭比絲.湯普森(Babs Thompson)說。如果你不欣賞他的作品,「那麼你就是不了解他,不接受他。」
縱然蓋瑞一輩子都處在焦慮不安中,他的舉止仍顯得輕鬆、低調又和善,鋼鐵般的決心遠不如萊特明顯,往往藏在隨和外表背後,他的老友畫家彼得.亞歷山大(Peter Alexander)把這種「羞怯」的氣質稱為「他溫和謙虛的作風」。萊特不曾被誤以為是謙遜的,蓋瑞則往往相反。
***
法蘭克幾乎從不會以預先設定的形狀展開設計。他喜歡從「玩」開始――描述如何著手進行設計時,「玩」這個字用得比「工作」一詞還頻繁――他把玩各種大小的木塊,毎一塊代表一棟建築物機能規劃的某部分。他接著會堆疊或排列那些木塊,組織成他覺得實用與美感兼具的合宜布局。一方面,這是量體模型;另一方面,是測量一座建築的規劃與預建地所處的區域有多麼契合。唯有這一步驟完成後,他才會開始用更具個人特色的形狀來美化手中的設計。針對畢爾包一案,法蘭克讓陳日榮擔任他的主設計師,象徵他對陳日榮與日俱增的信賴感,那時陳日榮進入事務所工作快六年了,比其他任何人更善於解讀法蘭克的構想,事務所另一名建築師蜜雪兒.考夫曼(Michelle Kaufmann)日後提到。「法蘭克只是畫了一張草圖,陳日榮就能確切知道該怎麼做,」她說。對客戶做簡報時,「陳日榮總是就在法蘭克旁邊,」她回憶說:「這給予法蘭克支持和信心,彷彿是他自己解決了每一個細節。」陳日榮不算是法蘭克的另一個自我,可是法蘭克相信陳日榮的直覺會知道他想要將建案引向哪個方向。他要求陳日榮為畢爾包製作初步的積木模型,那時他人還在西班牙,在預定建地的周圍遊走,思考這塊地與城市的關係。法蘭克因為要前往紐約參加菲力普.強生八十五歲大壽宴會,接著還要到波士頓參加另一場工作會議,不會直接返回洛杉磯,於是陳日榮帶著模型到紐約會合,以便與法蘭克有一天的時間一起工作。他們向建築師艾森曼借用一處辦公室空間,然後法蘭克開始調整積木模型,利用白紙碎片加入帆般的形式。
接下來一整個星期,法蘭克返回洛杉磯的工作崗位,美術館開始浮現成形,眾多簡單的厚紙板或木頭模型不斷傾瀉而出。如同大多數建案,法蘭克會使用模型當作設計工具。雖然事務所快速採用CATIA軟體的專門技術,法蘭克卻不會自己去接觸電腦,他把CATIA完全看成執行用而非創作用的工具。他的進行方式是,跟指派負責某建案的建築師團隊一起檢驗一組相關的模型,集中探究並提出幾項微調的建議,接著模型製造間會產出一組更新版的模型,將他所做的修改具體呈現,然後這個設計過程會從頭來過一遍。
這就是法蘭克面對所有委託案應用的主要設計步驟。雖然就畢爾包競圖方案而言,礙於時限壓縮的關係,法蘭克以一連串快速的判斷,檢視和淘汰各種想法,以至於光是一天往往就有數個模型產生。畢爾包發想設計的初期階段,一如以往許許多多的建案,法蘭克只要有片刻空閒,就會在飛機上或飯店房間繼續手繪速寫草稿,畫出的手繪稿看來也許像塗鴉,卻總是針對設計過程中某個新想法進行的探索,對於設計過程,他從不輕易劃下休止符。他繼續探索的渴求,大多反映出他分秒感受到的不安全感,對每一件尚未確實掌握的工作持續的擔心,以及需要不斷努力的迫切。儘管他喜愛世界的凌亂和矛盾,想藉由自己的建築來讚美這一點,但是說到底,法蘭克本性是充滿動力的完美主義者。何況他喜歡設計過程本身,以及設計仍處於孕育期那種存有無限可能的感覺。任何設計一旦定稿,所有的可能性只會剩下一個,而法蘭克不喜歡放棄一個案子能有多種解決方案,可以走向多元方向的那種感覺。每一座建築理所當然都需要有最終設計才能建成,法蘭克是建築師當中比較特殊的,因為他總是對一項設計程序的結論懷有五味雜陳的心情。對他來說,那一刻不像慶祝理想方案的降臨,反而比較像是期限已到,必須停止追尋更好的做法,不得不放棄其他種種選擇。
***
法蘭克鮮少在公開場合談論自己如何經營事務所,二○○二年受邀參加一場座談會,紀念彼得.路易斯為凱斯西儲大學魏德海管理學院捐建的建築啟用,他決定利用演講機會談論事務所的營運,進一步為自己有效率的做事能力辯護。「我想要談一談我如何經營我的世界,因為它是非常商業化的,你們聽了可能覺得震驚,」法蘭克說道:「大家認為我們是古怪的藝術家,沒有要顧慮的底線,可是我有一間獲利的事務所。」
法蘭克格外引以自豪的事情是,不像許多建築同業,他在生活拮据的情況下開業,手上沒有任何繼承的財富,而他相信這一點給予他一定程度的紀律,同時讓他決定不去剝削任何為他工作的人。他拒絕聘用任何不支薪的實習生。「我也堅持為我工作的員工,都要得到耶誕紅利、年度生活費調漲、休假等等福利。那是從一開始就放進公司文化裡的,」他說道。令他尤其生氣的是,許多建築師經常利用學生當免費勞工,為建築競圖製作設計。他表示,「要招聘願意免費工作的孩子非常容易,我有許多朋友都這麼做。那就好像吸毒。一旦上癮,再也戒不掉。」
法蘭克的收費結構與其他大多數建築事務所不同,為蓋瑞建築事務所擬訂一般的收費,再為他個人參與的設計立定特別的「設計費」。這看起來似乎是在利用他身為設計師的名氣,而且毋庸置疑就是。不過,他將這個做法視為他自己與其他同仁在委託案中角色的區分,並且為不可知的未來鋪路,有一天蓋瑞建築事務所勢必會變成只有合夥人而沒有蓋瑞。然而,那件事還很遙遠。法蘭克沒有打算退休,他表示自己認知到,「假如我離開了,事務所根本沒辦法做我做的事情。那是非常個人化的工作。」他強烈感覺到自己想要幫助年輕的才子發展,在既有的時間內獨立,而他特別稱讚陳日榮,在演講當中形容陳日榮是他旗下所有設計師裡最有天賦也最高深莫測的人。「跟我工作的前五年,他坐在那裡,一個字也沒說,」法蘭克說:「然後我會問他:『你對我們正在做的東西有什麼看法?』他會看著我說:『我不知道,你覺得呢?』這樣的對話又繼續了五年。然後我發現到,他變成一個怪物。他開始到處搬動東西⋯⋯我們那時正在做韓國的一個案子,最後沒有建成〔三星博物館〕,可是每次我出差一趟,回來就看到他搬動整間會議室。他無可挑剔。他的理由令人驚奇。他真的才華橫溢。他晚上不睡覺,隔天早上回來,又開始搬動會議室。」
在法蘭克看來,移動會議室的東西是他喜歡稱之為「玩」的動作,大多是出自本能。「你可以想像,一位嚴肅的執行長,不會把創意精神當成玩。但它就是如此,」他說:「創意,我認為它的特色是,你在尋找某種東西。你有一個目標。你不確定會走向何處。所以當我跟我的同仁聚在一起,開始思考、製作模型等等,就像在玩。」他記得有一次,當事務所正在探索不同的方案來設計華特迪士尼音樂廳時,他竟然播放年代久遠的影集《曠野奇俠》(Rawhide)的主題曲,副歌唱著「走吧,走吧,走吧」,希望歌曲會刺激新的想法。不過,更常見的是,辦公室是安靜的,法蘭克會花很長時間凝視著各種模型,思索可能的選擇,然後提議做些小修改。
雖然法蘭克對陳日榮大為讚賞,也相信陳日榮已經發展出純熟技能預測他可能想要執行的方向,可是他尚未準備好要將事務所的執業交給陳日榮或其他人。對於沒有了法蘭克的蓋瑞建築事務所會如何營運,他的想法相當模糊且不停替換;他喜歡把不同的組織策略當作一種抽象練習來玩,就像他時時拿不同的設計方案組裝一樣,推遲一個決定就是一種手段,維持每個選擇都仍有可能的幻象。在建案方面,客戶終究會強迫他對某個或另一個規劃做出承諾,不過沒有任何力量催促他處理事務所的未來。他的健康狀況良好,而他熟悉的生活方式,就是圍繞著工作、家庭,以及隨著名氣高漲,比以往更加滲入他專業生活的社交圈。
好評如潮的畢爾包若帶來任何挑戰,那就是如何避免成為僅僅是個「品牌」,蓋瑞的確是個名牌,繼續以建築師身分向前跨進;對蓋瑞而言,這不只意味著繼續設計建築,而是要做得跟以往一樣有新意,甚至抗拒許多可把他的知名建築物轉成慣用手法,繼而到處複製的機會。「成功比失敗更難應付得多,」蓋瑞曾說。那是他的肺腑之言。蓋瑞不想重複自己的創作,但觀察者一看到畢爾包之後誕生的建築物,同樣擁有奔放弧形形式的金屬、玻璃或石材,就認為無論它們的外觀多麼令人驚豔,都不過是複製前作的模式,這種反應令他泄氣。以蓋瑞的觀點來看,那些建築物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人們認為後畢爾包作品不過是古根漢美術館原創設計的延續,其實他們並不明白蓋瑞真正完成的是創造一種整體而言新的建築語言,在每一棟新建築物中,以略微不同的方式運用該語言來進行某些表達。
建築師和評論家傾向於贊同這個富共鳴的觀點,關於蓋瑞的報導,一般比同世代其他建築師來得好。不過,名氣當然也帶來另一面,蓋瑞的聲譽幾乎可確保那不恰當卻尖刻的稱號「明星建築師」與他的名字如影隨形。這個詞油腔滑調地合併兩個意思:名氣的短暫燦爛與對設計的熱中追求,難怪讓蓋瑞厭惡。他可能是大眾心目中典型的明星建築師,但對他來說,那個詞徹底曲解他的作品,隱喻他的建築無非就是吸睛、華而不實的造形。儘管蓋瑞公開聲稱自己對這個稱號不快,卻不討厭名氣本身,而他有一些行為似乎是計畫好要提高自己的名聲,而不是極力貶低。他允許電視節目《辛普森家庭》編寫一集譏諷他的內容;接受Tiffany & Co.的邀請,為店面及型錄設計珠寶和其他物品;還以最喜愛的運動冰上曲棍球為靈感,設計伏特加酒瓶、手錶和家具。(從加拿大的童年到邁入七十,他都有打冰上曲棍球。)居住洛杉磯六十載後,蓋瑞認識的娛樂圈人脈比一般建築師更廣,他讓導演好友薛尼.波拉克(Sydney Pollack)和一名攝影師跟拍數月,製作向他致敬的紀錄片,波拉克將影片命名為《速寫法蘭克.蓋瑞》(Sketches of Frank Gehry)。
蓋瑞或許是典型的明星建築師,卻熟練地不去表現明星那一面的舉止。二○一四年,蓋瑞的第一個倫敦建案揭幕之際,英國《建築師雜誌》(Architects’ Journal)安排一場攝影訪談,那件作品位於巴特西發電廠(Battersea Power Station),屬住商複合建築群,採訪者問蓋瑞為什麼過去不曾在倫敦設計任何作品。蓋瑞的回答一如往常,顯得滿不在乎又謙卑;他說,沒人問過我。他的回應似乎讓採訪者失望,對方看來是希望蓋瑞藉機咆哮一番,批評大型建築物要在倫敦取得核准程序艱難,有損他尊貴的建築師地位。相反地,蓋瑞的回應比較像是在說,他會樂意做任何設計,即使是小案子,只是一直等待有人打電話詢問而已。他說,那裡可沒有行銷部門在為他宣傳。在影片中,他看上去慈祥甚於雄心壯志,彷彿他是一間小工作室的苦當家,而不是鼎鼎大名的建築師,領導著世界知名的事務所。
這是蓋瑞式的經典演出:反明星化的建築師,再次暗示蓋瑞的性格多麼像是一半萊特與一半伍迪.艾倫的組合。事實上,一方面他會經常抱怨工作不夠多,一方面又在接受英國雜誌訪問的時期,忙著許多不同規模的計畫案;每每發現客戶的案子不夠刺激,或者感覺客戶對他的建築不夠投入,就會予以回絕,不想再談。他對自己的靈活性相當自豪,可是只願意展現給對的客戶,那些事前清楚表示喜歡他的作品,渴望擁有一件法蘭克.蓋瑞的人。如果你想要美國建築師理查.麥爾(Richard Meier)風格的白色時髦華廈,或是諾曼.佛斯特(Norman Foster)風格的玻璃高層建築,抑或美國新古典建築師羅伯特.史特恩(Robert Stern)打造的傳統大樓,找蓋瑞都是毫無意義的。蓋瑞指望業主會自己選擇,但他總是無法百分之百確定,他知道對方能夠自在與他相處,願意放手讓他探索的客戶,才能讓他舒坦地進行工作。
***
蓋瑞多年來在建築圈一直享有盛名,但一九九七年畢爾包古根漢開幕後,他開始急速攀升至名人寶座,成為繼萊特之後最知名的美國建築師。儘管活躍的年代相距四十年,兩人都為同一機構設計出開創性、廣受歡迎的美術館,難免有人把兩位法蘭克拿來相互比較。然而事實上,萊特與蓋瑞的共通點除了名字、對建築的熱情投入,以及發想出有別於過去的新穎設計的天賦異稟,兩人內在的性格一如他們設計的建築物,幾乎沒有任何相似之處。萊特某種程度是獨裁者,政治立場保守,而且自戀;他無力承認過錯,並製造出以自我為中心的小團體,有著如異教崇拜般的虔誠。萊特的態度似乎是,假如你不喜歡他的建築,原因一定是你不懂得欣賞偉大的創作。
蓋瑞較傾向自我懷疑。他渴望關愛和接納,希望自己的建築討人喜歡,有時似乎會把對作品的認同與對他個人的認同這兩件事近乎視為一體看待。「對法蘭克來說,在他內心深處,感覺被需要及被愛是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透過認同他的建築,」蓋瑞的老友芭比絲.湯普森(Babs Thompson)說。如果你不欣賞他的作品,「那麼你就是不了解他,不接受他。」
縱然蓋瑞一輩子都處在焦慮不安中,他的舉止仍顯得輕鬆、低調又和善,鋼鐵般的決心遠不如萊特明顯,往往藏在隨和外表背後,他的老友畫家彼得.亞歷山大(Peter Alexander)把這種「羞怯」的氣質稱為「他溫和謙虛的作風」。萊特不曾被誤以為是謙遜的,蓋瑞則往往相反。
***
法蘭克幾乎從不會以預先設定的形狀展開設計。他喜歡從「玩」開始――描述如何著手進行設計時,「玩」這個字用得比「工作」一詞還頻繁――他把玩各種大小的木塊,毎一塊代表一棟建築物機能規劃的某部分。他接著會堆疊或排列那些木塊,組織成他覺得實用與美感兼具的合宜布局。一方面,這是量體模型;另一方面,是測量一座建築的規劃與預建地所處的區域有多麼契合。唯有這一步驟完成後,他才會開始用更具個人特色的形狀來美化手中的設計。針對畢爾包一案,法蘭克讓陳日榮擔任他的主設計師,象徵他對陳日榮與日俱增的信賴感,那時陳日榮進入事務所工作快六年了,比其他任何人更善於解讀法蘭克的構想,事務所另一名建築師蜜雪兒.考夫曼(Michelle Kaufmann)日後提到。「法蘭克只是畫了一張草圖,陳日榮就能確切知道該怎麼做,」她說。對客戶做簡報時,「陳日榮總是就在法蘭克旁邊,」她回憶說:「這給予法蘭克支持和信心,彷彿是他自己解決了每一個細節。」陳日榮不算是法蘭克的另一個自我,可是法蘭克相信陳日榮的直覺會知道他想要將建案引向哪個方向。他要求陳日榮為畢爾包製作初步的積木模型,那時他人還在西班牙,在預定建地的周圍遊走,思考這塊地與城市的關係。法蘭克因為要前往紐約參加菲力普.強生八十五歲大壽宴會,接著還要到波士頓參加另一場工作會議,不會直接返回洛杉磯,於是陳日榮帶著模型到紐約會合,以便與法蘭克有一天的時間一起工作。他們向建築師艾森曼借用一處辦公室空間,然後法蘭克開始調整積木模型,利用白紙碎片加入帆般的形式。
接下來一整個星期,法蘭克返回洛杉磯的工作崗位,美術館開始浮現成形,眾多簡單的厚紙板或木頭模型不斷傾瀉而出。如同大多數建案,法蘭克會使用模型當作設計工具。雖然事務所快速採用CATIA軟體的專門技術,法蘭克卻不會自己去接觸電腦,他把CATIA完全看成執行用而非創作用的工具。他的進行方式是,跟指派負責某建案的建築師團隊一起檢驗一組相關的模型,集中探究並提出幾項微調的建議,接著模型製造間會產出一組更新版的模型,將他所做的修改具體呈現,然後這個設計過程會從頭來過一遍。
這就是法蘭克面對所有委託案應用的主要設計步驟。雖然就畢爾包競圖方案而言,礙於時限壓縮的關係,法蘭克以一連串快速的判斷,檢視和淘汰各種想法,以至於光是一天往往就有數個模型產生。畢爾包發想設計的初期階段,一如以往許許多多的建案,法蘭克只要有片刻空閒,就會在飛機上或飯店房間繼續手繪速寫草稿,畫出的手繪稿看來也許像塗鴉,卻總是針對設計過程中某個新想法進行的探索,對於設計過程,他從不輕易劃下休止符。他繼續探索的渴求,大多反映出他分秒感受到的不安全感,對每一件尚未確實掌握的工作持續的擔心,以及需要不斷努力的迫切。儘管他喜愛世界的凌亂和矛盾,想藉由自己的建築來讚美這一點,但是說到底,法蘭克本性是充滿動力的完美主義者。何況他喜歡設計過程本身,以及設計仍處於孕育期那種存有無限可能的感覺。任何設計一旦定稿,所有的可能性只會剩下一個,而法蘭克不喜歡放棄一個案子能有多種解決方案,可以走向多元方向的那種感覺。每一座建築理所當然都需要有最終設計才能建成,法蘭克是建築師當中比較特殊的,因為他總是對一項設計程序的結論懷有五味雜陳的心情。對他來說,那一刻不像慶祝理想方案的降臨,反而比較像是期限已到,必須停止追尋更好的做法,不得不放棄其他種種選擇。
***
法蘭克鮮少在公開場合談論自己如何經營事務所,二○○二年受邀參加一場座談會,紀念彼得.路易斯為凱斯西儲大學魏德海管理學院捐建的建築啟用,他決定利用演講機會談論事務所的營運,進一步為自己有效率的做事能力辯護。「我想要談一談我如何經營我的世界,因為它是非常商業化的,你們聽了可能覺得震驚,」法蘭克說道:「大家認為我們是古怪的藝術家,沒有要顧慮的底線,可是我有一間獲利的事務所。」
法蘭克格外引以自豪的事情是,不像許多建築同業,他在生活拮据的情況下開業,手上沒有任何繼承的財富,而他相信這一點給予他一定程度的紀律,同時讓他決定不去剝削任何為他工作的人。他拒絕聘用任何不支薪的實習生。「我也堅持為我工作的員工,都要得到耶誕紅利、年度生活費調漲、休假等等福利。那是從一開始就放進公司文化裡的,」他說道。令他尤其生氣的是,許多建築師經常利用學生當免費勞工,為建築競圖製作設計。他表示,「要招聘願意免費工作的孩子非常容易,我有許多朋友都這麼做。那就好像吸毒。一旦上癮,再也戒不掉。」
法蘭克的收費結構與其他大多數建築事務所不同,為蓋瑞建築事務所擬訂一般的收費,再為他個人參與的設計立定特別的「設計費」。這看起來似乎是在利用他身為設計師的名氣,而且毋庸置疑就是。不過,他將這個做法視為他自己與其他同仁在委託案中角色的區分,並且為不可知的未來鋪路,有一天蓋瑞建築事務所勢必會變成只有合夥人而沒有蓋瑞。然而,那件事還很遙遠。法蘭克沒有打算退休,他表示自己認知到,「假如我離開了,事務所根本沒辦法做我做的事情。那是非常個人化的工作。」他強烈感覺到自己想要幫助年輕的才子發展,在既有的時間內獨立,而他特別稱讚陳日榮,在演講當中形容陳日榮是他旗下所有設計師裡最有天賦也最高深莫測的人。「跟我工作的前五年,他坐在那裡,一個字也沒說,」法蘭克說:「然後我會問他:『你對我們正在做的東西有什麼看法?』他會看著我說:『我不知道,你覺得呢?』這樣的對話又繼續了五年。然後我發現到,他變成一個怪物。他開始到處搬動東西⋯⋯我們那時正在做韓國的一個案子,最後沒有建成〔三星博物館〕,可是每次我出差一趟,回來就看到他搬動整間會議室。他無可挑剔。他的理由令人驚奇。他真的才華橫溢。他晚上不睡覺,隔天早上回來,又開始搬動會議室。」
在法蘭克看來,移動會議室的東西是他喜歡稱之為「玩」的動作,大多是出自本能。「你可以想像,一位嚴肅的執行長,不會把創意精神當成玩。但它就是如此,」他說:「創意,我認為它的特色是,你在尋找某種東西。你有一個目標。你不確定會走向何處。所以當我跟我的同仁聚在一起,開始思考、製作模型等等,就像在玩。」他記得有一次,當事務所正在探索不同的方案來設計華特迪士尼音樂廳時,他竟然播放年代久遠的影集《曠野奇俠》(Rawhide)的主題曲,副歌唱著「走吧,走吧,走吧」,希望歌曲會刺激新的想法。不過,更常見的是,辦公室是安靜的,法蘭克會花很長時間凝視著各種模型,思索可能的選擇,然後提議做些小修改。
雖然法蘭克對陳日榮大為讚賞,也相信陳日榮已經發展出純熟技能預測他可能想要執行的方向,可是他尚未準備好要將事務所的執業交給陳日榮或其他人。對於沒有了法蘭克的蓋瑞建築事務所會如何營運,他的想法相當模糊且不停替換;他喜歡把不同的組織策略當作一種抽象練習來玩,就像他時時拿不同的設計方案組裝一樣,推遲一個決定就是一種手段,維持每個選擇都仍有可能的幻象。在建案方面,客戶終究會強迫他對某個或另一個規劃做出承諾,不過沒有任何力量催促他處理事務所的未來。他的健康狀況良好,而他熟悉的生活方式,就是圍繞著工作、家庭,以及隨著名氣高漲,比以往更加滲入他專業生活的社交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