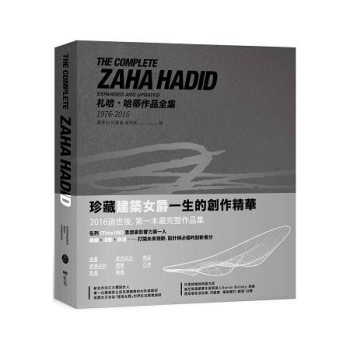引言
超越89度
艾倫‧北斯基(Aaron Betsky)
引爆十分之一秒的瞬間
札哈‧哈蒂(Zaha Hadid)是傑出的電影攝影家。她的目光就像一台攝影機。她用慢動作、平移、高速靠近和特寫鏡頭、跳接和敘事節奏來感受城市。當她描繪圍繞在她身旁的世界時,她刻畫出那些未知的空間。她發掘了潛藏在我們現代世界的事物,並繪製成烏托邦的分鏡腳本。她大膽探索,時而放慢、時而加快日常生活的節奏,並將她的環境透過建築的精準曝光作為一種再現的形式。她建造了有如十分之一秒爆炸的瞬間。
這並非意味著她不是一位建築師。一直以來哈蒂都將目標放在建造,而她的圖面,(早期的畫作和她將結構化身為為肢體語言和奪目造型的手法),更是她進一步邁向構築的推手。然而,她從沒打算過將獨立的物件置入空白基地中。相反地,她的建築是導致空間擴張的高密度聚合體,她壓縮了所有形成建築的能量,從機能到技術服務設施。她的建築可以從這種密度下自由擴展,創造出天馬行空的空間。在那曾經(可能有)私人活動、牆和管線的地方,現在則是劃過地景的碎片和面,打開了一個我們從未想像過的空間。
哈蒂以類似的方式打造她的建築職業之路。她將幼時編織地毯上的回憶,混合進倫敦的建築聯盟學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學習歷程裡。她用二十世紀初藝術家所創作的形式作為構築元素,來從中豎立她抽象記憶中的宮殿。她擷取都市的能量和深刻的地景輪廓,像披風那樣圍繞著她,然後,將這股力量化作探索的出發點,邁向她多角形式的未知領域。
或許有人會說,札哈‧哈蒂是現代主義者,她對創新宣示的方式,是設計出與科技核心緊密結合的開放空間(lofts)。札哈‧哈蒂沒有類型、使用次序、預設立場或是地心引力的包袱:她深信我們可以且應當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一個標榜著以自由至上的世界。我們將自過去中解放,從社會常規的限制中、物理法則中和我們的身體中擺脫。建築,對於像哈蒂這樣的現代主義者,總是在局部構築著這樣的自由世界。
現代主義的三種狀態
傳統上,這樣的現代主義有三種層面。首先,其追隨者相信新的結構。一個好的現代主義者認為,運用科技,我們得以更有效地利用我們的資源(包含我們自身)創造出最大量的盈餘,無論是空間上的還是價值上的。這樣的「過剩」是那永遠的新、未來與烏托邦的史詩般實現。它無形並且是在形體最極簡時才會產生。第二,現代主義者相信新的觀看方式。或許世界已然全新,只是我們沒有認知到這樣的世界。我們慣用被訓練過的方式去察覺我們所見。如果我們能夠用新穎的方法觀看,僅僅透過這樣的行動,我們便可以改變世界。我們必須對我們存在的現實世界打開雙眼、耳朵與心思。於是,我們將能得到那已然存在的自由。第三,現代主義者希望再現現代性的真實。融合上述兩個層面,現代主義者將我們新的感知,轉化成我們已創造形式的再現。這樣的形式是真實的原型,其中事物已被重新排列和溶解,這一刻,除了嶄新之外的事物消失無蹤。以新的方式表現新事物,只要用我們的眼光,就可以建構一個新世界,並居住其中。
現代主義的第三個層面正是札哈‧哈蒂作品的特徵。她沒有發明新型態的構法或技術;而是用顛覆的方式呈現給我們一個新的世界。她在主體和客體的溶解中找到現代主義的根源,並把它們帶到現代地景的舞台上,這個被她重新塑造成一個可以任我們恣意漫遊的地方。
引外入內
然而,哈蒂的作品並不僅擁有伴隨西方根源而來的現代性。出生於伊拉克的她,談及年少時對波斯地毯的著迷,複雜的圖騰打破理解,體現了結合手藝,將真實世界轉化成感性的織面,將簡單的空間帶入生機。值得一提的是,這也無獨有偶地是女性的創作。
我們也可將哈蒂作品的敘事展開,與中國和日本的捲軸畫做比較。現代主義提出從不斷累積的日常活動中,建構能持續改變我們理解真實的感知,而非將特定的秩序固定在事物上。這是一種捲軸畫繪者深諳的創作方式。他們在作品中來回穿梭,專注於微小的細節,從不同的角度將場景多次的展現,將許多分離的元素串連成地景。一波又一波回聲般的線條,混合進創作者的想像之中,在那世界裡改變並回傳,轉化後再送回給觀者。
上述這些傳統觀念皆為二十世紀初藝術家所運用,他們的藝術為哈蒂的圖像式構築元素提供線索。無論是在立體主義、表現主義亦或是超現實主義中,抽象的片段被組合成敘事結構。這些藝術家為他們的世界投下震撼彈 ──杜象的《下樓的裸女》有如札哈‧哈蒂的母系始祖(grandmother)。
哈蒂最直系的建築血統,可說是位於倫敦的建築聯盟學院。她在那裡學習時,這所學校正處在全球建築實驗中心的巔峰位置。承接建築電訊(Archigram)的腳步,彼得•庫克(Peter Cook)、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伯納德•屈米(Bernard Tschumi)和奈傑爾•寇茲(Nigel Coates)等學生和老師們,將現代世界的恍惚動盪編寫成為作品的主題和形式。無所畏懼地再次主張成為現代主義者,藉由不斷講述他們的故事,來試圖捕捉一切源自於我們活動變換中的能量,並為形塑現代性的嘗試增添敘事觀點。
無論作品是軼事與晦澀的(屈米Tschumi),還是表現了神話般拼貼的(庫哈斯 Koolhaas)又或者是宣言的(庫克 Cook),他們都將多重的觀點、具席捲力和表現性的形式、以及技術面的架構一起整合進畫面中,表現的方法則是透過描述而非精確定義。
超越89度
艾倫‧北斯基(Aaron Betsky)
引爆十分之一秒的瞬間
札哈‧哈蒂(Zaha Hadid)是傑出的電影攝影家。她的目光就像一台攝影機。她用慢動作、平移、高速靠近和特寫鏡頭、跳接和敘事節奏來感受城市。當她描繪圍繞在她身旁的世界時,她刻畫出那些未知的空間。她發掘了潛藏在我們現代世界的事物,並繪製成烏托邦的分鏡腳本。她大膽探索,時而放慢、時而加快日常生活的節奏,並將她的環境透過建築的精準曝光作為一種再現的形式。她建造了有如十分之一秒爆炸的瞬間。
這並非意味著她不是一位建築師。一直以來哈蒂都將目標放在建造,而她的圖面,(早期的畫作和她將結構化身為為肢體語言和奪目造型的手法),更是她進一步邁向構築的推手。然而,她從沒打算過將獨立的物件置入空白基地中。相反地,她的建築是導致空間擴張的高密度聚合體,她壓縮了所有形成建築的能量,從機能到技術服務設施。她的建築可以從這種密度下自由擴展,創造出天馬行空的空間。在那曾經(可能有)私人活動、牆和管線的地方,現在則是劃過地景的碎片和面,打開了一個我們從未想像過的空間。
哈蒂以類似的方式打造她的建築職業之路。她將幼時編織地毯上的回憶,混合進倫敦的建築聯盟學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學習歷程裡。她用二十世紀初藝術家所創作的形式作為構築元素,來從中豎立她抽象記憶中的宮殿。她擷取都市的能量和深刻的地景輪廓,像披風那樣圍繞著她,然後,將這股力量化作探索的出發點,邁向她多角形式的未知領域。
或許有人會說,札哈‧哈蒂是現代主義者,她對創新宣示的方式,是設計出與科技核心緊密結合的開放空間(lofts)。札哈‧哈蒂沒有類型、使用次序、預設立場或是地心引力的包袱:她深信我們可以且應當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一個標榜著以自由至上的世界。我們將自過去中解放,從社會常規的限制中、物理法則中和我們的身體中擺脫。建築,對於像哈蒂這樣的現代主義者,總是在局部構築著這樣的自由世界。
現代主義的三種狀態
傳統上,這樣的現代主義有三種層面。首先,其追隨者相信新的結構。一個好的現代主義者認為,運用科技,我們得以更有效地利用我們的資源(包含我們自身)創造出最大量的盈餘,無論是空間上的還是價值上的。這樣的「過剩」是那永遠的新、未來與烏托邦的史詩般實現。它無形並且是在形體最極簡時才會產生。第二,現代主義者相信新的觀看方式。或許世界已然全新,只是我們沒有認知到這樣的世界。我們慣用被訓練過的方式去察覺我們所見。如果我們能夠用新穎的方法觀看,僅僅透過這樣的行動,我們便可以改變世界。我們必須對我們存在的現實世界打開雙眼、耳朵與心思。於是,我們將能得到那已然存在的自由。第三,現代主義者希望再現現代性的真實。融合上述兩個層面,現代主義者將我們新的感知,轉化成我們已創造形式的再現。這樣的形式是真實的原型,其中事物已被重新排列和溶解,這一刻,除了嶄新之外的事物消失無蹤。以新的方式表現新事物,只要用我們的眼光,就可以建構一個新世界,並居住其中。
現代主義的第三個層面正是札哈‧哈蒂作品的特徵。她沒有發明新型態的構法或技術;而是用顛覆的方式呈現給我們一個新的世界。她在主體和客體的溶解中找到現代主義的根源,並把它們帶到現代地景的舞台上,這個被她重新塑造成一個可以任我們恣意漫遊的地方。
引外入內
然而,哈蒂的作品並不僅擁有伴隨西方根源而來的現代性。出生於伊拉克的她,談及年少時對波斯地毯的著迷,複雜的圖騰打破理解,體現了結合手藝,將真實世界轉化成感性的織面,將簡單的空間帶入生機。值得一提的是,這也無獨有偶地是女性的創作。
我們也可將哈蒂作品的敘事展開,與中國和日本的捲軸畫做比較。現代主義提出從不斷累積的日常活動中,建構能持續改變我們理解真實的感知,而非將特定的秩序固定在事物上。這是一種捲軸畫繪者深諳的創作方式。他們在作品中來回穿梭,專注於微小的細節,從不同的角度將場景多次的展現,將許多分離的元素串連成地景。一波又一波回聲般的線條,混合進創作者的想像之中,在那世界裡改變並回傳,轉化後再送回給觀者。
上述這些傳統觀念皆為二十世紀初藝術家所運用,他們的藝術為哈蒂的圖像式構築元素提供線索。無論是在立體主義、表現主義亦或是超現實主義中,抽象的片段被組合成敘事結構。這些藝術家為他們的世界投下震撼彈 ──杜象的《下樓的裸女》有如札哈‧哈蒂的母系始祖(grandmother)。
哈蒂最直系的建築血統,可說是位於倫敦的建築聯盟學院。她在那裡學習時,這所學校正處在全球建築實驗中心的巔峰位置。承接建築電訊(Archigram)的腳步,彼得•庫克(Peter Cook)、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伯納德•屈米(Bernard Tschumi)和奈傑爾•寇茲(Nigel Coates)等學生和老師們,將現代世界的恍惚動盪編寫成為作品的主題和形式。無所畏懼地再次主張成為現代主義者,藉由不斷講述他們的故事,來試圖捕捉一切源自於我們活動變換中的能量,並為形塑現代性的嘗試增添敘事觀點。
無論作品是軼事與晦澀的(屈米Tschumi),還是表現了神話般拼貼的(庫哈斯 Koolhaas)又或者是宣言的(庫克 Cook),他們都將多重的觀點、具席捲力和表現性的形式、以及技術面的架構一起整合進畫面中,表現的方法則是透過描述而非精確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