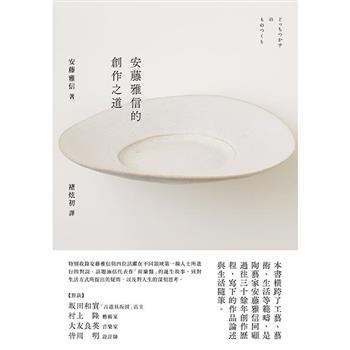● 隧道之中
多治見沒有大學,畢業後回到故鄉的都是繼承家業的長子。在那兒找不到搖滾咖啡館、爵士咖啡館、二手書店這類非主流的店家給不用負責任的小兒子流連,我總是非常渴望次文化的薰陶。
高二那一年,《太陽》月刊讓我對日本文化產生悸動,也打開了聆聽日本搖滾樂的耳朵,並開始覺得「日本這個國家還不至於沒救」。一直到昭和時代快要結束那陣子,大多數的日本人還懷抱著因為明治開國與二戰戰敗對西方國家的自卑感,以及為了與這種自卑相抗衡而產生的纖細又特殊的審美觀,一種認為外國人才不會懂的優越感。如果是現在也許根本不會成為話題,但在七○年代,搖滾樂是否該用日語表現的問題,大眾輿論可是討論得相當認眞,佔據不少報刊的版面。這場意見之爭是由主張要打入國際樂壇,英語歌詞便不可或缺、如此才是正牌搖滾樂的英語派;以及認為就算是旋律與節奏難以合拍,也應該用日語表現的日語派,兩者之間的分歧,在當年可是僵持不下的大問題。
旅美回國後三十歲前的我,分別在銀座與神田租了藝廊,舉辦過三次當代藝術的個展。這幾個展覽的共通點是以亞洲文化的根源為主題,然而在消化不完全、概念也未臻成熟的情況下,作品並不穩定,無法創造出自我風格的輪廓。在同一個時期,我仍持續著雕塑形式的陶藝創作,身為一個日本人,該如何經由陶藝表現當代藝術,我依舊迷惘找不到方向。這時候,我遇上了一本名為《少年藝術》的書。作者寫下了自己在歐洲的所見所聞,書中內容提及全球藝術情勢與從世界看到的日本,令我深受衝擊。透過ART WORLD這個字眼,讓我理解到歐洲當代藝術的現況,甚至有種被逼到牆角的感覺。我認為若要繼續從事當代藝術,應該前往英國;想在精神層面上有所精進,就要去印度,這兩者非擇一不可,否則便無法突破現狀。基於對佛教的興趣,於是我選擇了印度。
那趟印度之旅讓我染上痢疾,到了一個叫作達蘭薩拉(Dharamsala)的城鎭休養。那裡是達賴喇嘛流亡居住之地,我彷彿被引導遇見了藏傳佛教,朝朝暮暮,我開始初級的修行,檢討驗證因與果,體悟了何謂善因有善果、惡因有惡果的道理。這是一種名為觀想法的冥想方式,晨起,確認今天一整日待辦事項的動機與目的,到了晚上,檢討這一天行為的動機與結果是否正確。要回顧檢討的不只是今日,還包括自己的過往,我發現原來自己身為當代藝術家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為想要成名的慾望,這個覺知讓我感到鬆了口氣。
在旅人會前往的西藏圖書館裡,我讀了鈴木大拙的著作《日本的靈性》,明白了透過反覆的動作能將自我消弭的這條道路。這讓我想起透過大量製作日常生活器物來表現的民藝思想,我下定決心,回國後三十到四十歲之間,是奠定基礎的時期,只要有人委託,做什麼我都願意。擁有了無論如何都要持續創作下去的覺悟後,心情彷彿長久置身於隧道中,隱隱約約看見了前方閃爍著微弱的亮光。當我結束八個月的亞洲之旅回到日本,一個製作陶壁的工作找上了門。
● 我們家的習慣
我對新婚生活充滿了各種憧憬。很期待家中母親的料理交棒給妻子後,餐桌是否會出現不同的風景。日本連續劇或電影裡,經常會出現餐桌的場景,我想也是因為由此可探見那個家的習慣與狀態吧。由於座位的安排與使用的食器等等都會展現生活的樣貌,因此我很想好好珍惜餐桌上的風景。我結婚那時正逢泡沫經濟崩潰,鋪張的飮食熱潮已消退,然而餐桌上的食物比起童年還是豐盛了許多。高度經濟成長引發的公害以及食品添加物對健康帶來傷害等等問題,讓大眾對於科技發展開始抱持疑問。不使用農藥與添加物的食材與食品慢慢少量出現在市場上,消費者意識也產生了變化,重視食材、使用能盛裝各國菜色的簡單食器。另一方面,街上的餐廳也開始提供來自世界各地道地的料理。
此外,用餐也從坐在榻榻米與地毯等地面上,改為西式的餐桌與餐椅,擺在桌上的食器形狀與使用方式也有了改變。坐在地上用餐時,小茶几與嘴巴還有食器之間有段距離,因此要舉著筷子將食器拿上拿下,於是造型好拿的碗與缽、中小型的碟子便成為食器的主流。如果是西式的餐桌餐椅,嘴巴與食器之間的距離變近了,用餐無須拿著食器,只要用筷子、刀叉將食物放入口中就可以了。餐桌上也為了減少麻煩而簡化,像是減少食器的數量、幾種料理可以同時裝入一個大盤子,或者是從盛裝的盤皿把菜夾進自己的碗碟裡。正因如此,需要能讓料理看起來很好吃、百搭的器皿。在昭和時期,成為家庭主婦曾經是一種理想,然而隨著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的發布、女性意識的改變,到了平成時代職業婦女增加了,加上父權制度瓦解與家庭宴客增加等人際關係的變化,這些時代背景都對生活帶來一定的影響。
我想像中的器皿,具有多種用途,要看起來像是西式食器,但也可以裝盛有湯汁的菜餚,甚至可以放蛋糕。還要能為料理畫龍點睛、每次使用都能保持新鮮感。雖然是西式食器,但希望能有手作的觸感與質感。我因為到了三十五歲左右才將創作主軸從當代藝術轉為陶藝,某些層面上依舊無法完全擺脫「必須要成為一個能將器皿打造成作品的陶藝家」那種精神上的束縛。然而需要是發明之母,自從找到要製作天天都可以使用的食器這個動機,我終於從枷鎖中解放。
就這樣,我展開了在錯誤中尋找如何製作出自己在吃飯的時候會想用、拿來裝什麼都可以,雋永又耐看的日常食器。我決定要放下用途等先入為主的觀念,燒製在釉藥與造型上有新意、融合東西風格的白釉橢圓盤。
● 重拾喜悅——寫在與皆川明先生的對談之後
我記得二○○九年在岩手縣的山裡見到了皆川明,並就延續百年品牌的想法追問了他許多問題。他給了許多與預料中完全相反,甚至是我過去想都沒想過的解答,讓我懾服於他的眞材實料。那天晚上,我們喝著蘇格蘭威士忌,更進一步深談了許多議題。後來,我們在百草藝廊重逢時一拍即合,我邀請他策畫「minä perhonen+百草藝廊」的定期展,使我們的理念得以成形。從那時起,盡可能讓時裝與織品接近手工製品的皆川先生,跟盡可能把手工製品朝工業產品靠近的妻子明子與我,在享受彼此既遠又近的距離的同時,每一年半就會合作一次。他把這活動命名為「製造的再生」。
活動的基本理念,來自於近江商人常講的「三方共好」。近江是一個富商大賈輩出之地,那裡的商人做生意的理念是:「對賣家好,對買家好,對地方好。」我們第一次在百草藝廊碰面時,我把這件事告訴皆川先生,結果他回答:「我知道。但我想做的是再加上製造者,變成四方共好」。它從「製造(產地)、傳達(賣方)、使用(買方)、貢獻(社會)」的四面循環開重拾喜悅始,時而向左、時而往右不斷再生。
在這次採訪中,皆川先生說他正在努力拓展設計的概念:「近來我認為,如何設計一個充滿喜悅的創造過程,與製作物件同等重要。」在四方共好的過程中,每一個環節都需要加以設計,在此同時,就連每一個階段參與的每一個人,他們是否快樂,也需要設計。在二十世紀,人口不斷增加,所有產業都把重心放在「製造和銷售」,但到了二十一世紀,日本人口持續在下降,比重已逐漸轉向「使用和貢獻於社會」的方向。只要製造了就能賣出去的時代已結束,如今,東西要做得好才賣得掉已是理所當然,生產與消費的過程經由使用者的支持喜愛,能以何種方式回饋社會,這樣的追求已開始成形。各種思考激發出的回饋方式包括了製作時是否能為產品的未來想得更長遠、使用者不只滿足於消費,還會思考這次消費是否對社會造成負擔,另外還包括使用者透過購買來支持用心生產的製作者之餘,是否同時讓生產者因而得到快樂等等。
與日本每年廢棄的十億件新衣相比,手工製作的產品數量相當少,看似沒有必要考慮資源和環境等社會問題,然而這並非僅是產量的問題,製作者的態度決定如何創造出人們的幸福,即使是手工製作也須面對這個問題。以陶器來說,由於需求減少導致產地衰退蕭條,連帶影響到原料與製作工具的供給,連職人與創作者生產製作的喜悅也被剝奪。設計一種四方共好的體制,勢必將成為今後相當重要的課題吧。
喜悅這個詞看似簡單,其實有非常廣泛的含義。我不會停止製造既有的產品,這樣才能讓使用者需要補貨時還能買到;如果咖啡杯的杯把壞了,我也接受重新燒製修繕的委託,只要使用者想繼續用,我便盡力回報這份心意。這些看似都是小事,但讓我慢慢體會一樣東西能被長久使用,不只是使用者,包括製作者也會感受到喜悅。四方共好,要讓大家都能找到喜悅,不只需要各種不同面相的思考,也很花時間,但我認為能持續檢驗是否對每個環節都有好處,慢慢把影響範圍擴大就好。
最近,我與一位千禧世代的創作者聊到「四方共好」的想法,他說「我們是把『友善環境』也加入其中,朝『五方共好』的方向在行動」。了解到製作循環的重心再度轉移,我們的理念似乎橫跨了世代且更加深化,令我感到欣慰不已。
多治見沒有大學,畢業後回到故鄉的都是繼承家業的長子。在那兒找不到搖滾咖啡館、爵士咖啡館、二手書店這類非主流的店家給不用負責任的小兒子流連,我總是非常渴望次文化的薰陶。
高二那一年,《太陽》月刊讓我對日本文化產生悸動,也打開了聆聽日本搖滾樂的耳朵,並開始覺得「日本這個國家還不至於沒救」。一直到昭和時代快要結束那陣子,大多數的日本人還懷抱著因為明治開國與二戰戰敗對西方國家的自卑感,以及為了與這種自卑相抗衡而產生的纖細又特殊的審美觀,一種認為外國人才不會懂的優越感。如果是現在也許根本不會成為話題,但在七○年代,搖滾樂是否該用日語表現的問題,大眾輿論可是討論得相當認眞,佔據不少報刊的版面。這場意見之爭是由主張要打入國際樂壇,英語歌詞便不可或缺、如此才是正牌搖滾樂的英語派;以及認為就算是旋律與節奏難以合拍,也應該用日語表現的日語派,兩者之間的分歧,在當年可是僵持不下的大問題。
旅美回國後三十歲前的我,分別在銀座與神田租了藝廊,舉辦過三次當代藝術的個展。這幾個展覽的共通點是以亞洲文化的根源為主題,然而在消化不完全、概念也未臻成熟的情況下,作品並不穩定,無法創造出自我風格的輪廓。在同一個時期,我仍持續著雕塑形式的陶藝創作,身為一個日本人,該如何經由陶藝表現當代藝術,我依舊迷惘找不到方向。這時候,我遇上了一本名為《少年藝術》的書。作者寫下了自己在歐洲的所見所聞,書中內容提及全球藝術情勢與從世界看到的日本,令我深受衝擊。透過ART WORLD這個字眼,讓我理解到歐洲當代藝術的現況,甚至有種被逼到牆角的感覺。我認為若要繼續從事當代藝術,應該前往英國;想在精神層面上有所精進,就要去印度,這兩者非擇一不可,否則便無法突破現狀。基於對佛教的興趣,於是我選擇了印度。
那趟印度之旅讓我染上痢疾,到了一個叫作達蘭薩拉(Dharamsala)的城鎭休養。那裡是達賴喇嘛流亡居住之地,我彷彿被引導遇見了藏傳佛教,朝朝暮暮,我開始初級的修行,檢討驗證因與果,體悟了何謂善因有善果、惡因有惡果的道理。這是一種名為觀想法的冥想方式,晨起,確認今天一整日待辦事項的動機與目的,到了晚上,檢討這一天行為的動機與結果是否正確。要回顧檢討的不只是今日,還包括自己的過往,我發現原來自己身為當代藝術家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為想要成名的慾望,這個覺知讓我感到鬆了口氣。
在旅人會前往的西藏圖書館裡,我讀了鈴木大拙的著作《日本的靈性》,明白了透過反覆的動作能將自我消弭的這條道路。這讓我想起透過大量製作日常生活器物來表現的民藝思想,我下定決心,回國後三十到四十歲之間,是奠定基礎的時期,只要有人委託,做什麼我都願意。擁有了無論如何都要持續創作下去的覺悟後,心情彷彿長久置身於隧道中,隱隱約約看見了前方閃爍著微弱的亮光。當我結束八個月的亞洲之旅回到日本,一個製作陶壁的工作找上了門。
● 我們家的習慣
我對新婚生活充滿了各種憧憬。很期待家中母親的料理交棒給妻子後,餐桌是否會出現不同的風景。日本連續劇或電影裡,經常會出現餐桌的場景,我想也是因為由此可探見那個家的習慣與狀態吧。由於座位的安排與使用的食器等等都會展現生活的樣貌,因此我很想好好珍惜餐桌上的風景。我結婚那時正逢泡沫經濟崩潰,鋪張的飮食熱潮已消退,然而餐桌上的食物比起童年還是豐盛了許多。高度經濟成長引發的公害以及食品添加物對健康帶來傷害等等問題,讓大眾對於科技發展開始抱持疑問。不使用農藥與添加物的食材與食品慢慢少量出現在市場上,消費者意識也產生了變化,重視食材、使用能盛裝各國菜色的簡單食器。另一方面,街上的餐廳也開始提供來自世界各地道地的料理。
此外,用餐也從坐在榻榻米與地毯等地面上,改為西式的餐桌與餐椅,擺在桌上的食器形狀與使用方式也有了改變。坐在地上用餐時,小茶几與嘴巴還有食器之間有段距離,因此要舉著筷子將食器拿上拿下,於是造型好拿的碗與缽、中小型的碟子便成為食器的主流。如果是西式的餐桌餐椅,嘴巴與食器之間的距離變近了,用餐無須拿著食器,只要用筷子、刀叉將食物放入口中就可以了。餐桌上也為了減少麻煩而簡化,像是減少食器的數量、幾種料理可以同時裝入一個大盤子,或者是從盛裝的盤皿把菜夾進自己的碗碟裡。正因如此,需要能讓料理看起來很好吃、百搭的器皿。在昭和時期,成為家庭主婦曾經是一種理想,然而隨著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的發布、女性意識的改變,到了平成時代職業婦女增加了,加上父權制度瓦解與家庭宴客增加等人際關係的變化,這些時代背景都對生活帶來一定的影響。
我想像中的器皿,具有多種用途,要看起來像是西式食器,但也可以裝盛有湯汁的菜餚,甚至可以放蛋糕。還要能為料理畫龍點睛、每次使用都能保持新鮮感。雖然是西式食器,但希望能有手作的觸感與質感。我因為到了三十五歲左右才將創作主軸從當代藝術轉為陶藝,某些層面上依舊無法完全擺脫「必須要成為一個能將器皿打造成作品的陶藝家」那種精神上的束縛。然而需要是發明之母,自從找到要製作天天都可以使用的食器這個動機,我終於從枷鎖中解放。
就這樣,我展開了在錯誤中尋找如何製作出自己在吃飯的時候會想用、拿來裝什麼都可以,雋永又耐看的日常食器。我決定要放下用途等先入為主的觀念,燒製在釉藥與造型上有新意、融合東西風格的白釉橢圓盤。
● 重拾喜悅——寫在與皆川明先生的對談之後
我記得二○○九年在岩手縣的山裡見到了皆川明,並就延續百年品牌的想法追問了他許多問題。他給了許多與預料中完全相反,甚至是我過去想都沒想過的解答,讓我懾服於他的眞材實料。那天晚上,我們喝著蘇格蘭威士忌,更進一步深談了許多議題。後來,我們在百草藝廊重逢時一拍即合,我邀請他策畫「minä perhonen+百草藝廊」的定期展,使我們的理念得以成形。從那時起,盡可能讓時裝與織品接近手工製品的皆川先生,跟盡可能把手工製品朝工業產品靠近的妻子明子與我,在享受彼此既遠又近的距離的同時,每一年半就會合作一次。他把這活動命名為「製造的再生」。
活動的基本理念,來自於近江商人常講的「三方共好」。近江是一個富商大賈輩出之地,那裡的商人做生意的理念是:「對賣家好,對買家好,對地方好。」我們第一次在百草藝廊碰面時,我把這件事告訴皆川先生,結果他回答:「我知道。但我想做的是再加上製造者,變成四方共好」。它從「製造(產地)、傳達(賣方)、使用(買方)、貢獻(社會)」的四面循環開重拾喜悅始,時而向左、時而往右不斷再生。
在這次採訪中,皆川先生說他正在努力拓展設計的概念:「近來我認為,如何設計一個充滿喜悅的創造過程,與製作物件同等重要。」在四方共好的過程中,每一個環節都需要加以設計,在此同時,就連每一個階段參與的每一個人,他們是否快樂,也需要設計。在二十世紀,人口不斷增加,所有產業都把重心放在「製造和銷售」,但到了二十一世紀,日本人口持續在下降,比重已逐漸轉向「使用和貢獻於社會」的方向。只要製造了就能賣出去的時代已結束,如今,東西要做得好才賣得掉已是理所當然,生產與消費的過程經由使用者的支持喜愛,能以何種方式回饋社會,這樣的追求已開始成形。各種思考激發出的回饋方式包括了製作時是否能為產品的未來想得更長遠、使用者不只滿足於消費,還會思考這次消費是否對社會造成負擔,另外還包括使用者透過購買來支持用心生產的製作者之餘,是否同時讓生產者因而得到快樂等等。
與日本每年廢棄的十億件新衣相比,手工製作的產品數量相當少,看似沒有必要考慮資源和環境等社會問題,然而這並非僅是產量的問題,製作者的態度決定如何創造出人們的幸福,即使是手工製作也須面對這個問題。以陶器來說,由於需求減少導致產地衰退蕭條,連帶影響到原料與製作工具的供給,連職人與創作者生產製作的喜悅也被剝奪。設計一種四方共好的體制,勢必將成為今後相當重要的課題吧。
喜悅這個詞看似簡單,其實有非常廣泛的含義。我不會停止製造既有的產品,這樣才能讓使用者需要補貨時還能買到;如果咖啡杯的杯把壞了,我也接受重新燒製修繕的委託,只要使用者想繼續用,我便盡力回報這份心意。這些看似都是小事,但讓我慢慢體會一樣東西能被長久使用,不只是使用者,包括製作者也會感受到喜悅。四方共好,要讓大家都能找到喜悅,不只需要各種不同面相的思考,也很花時間,但我認為能持續檢驗是否對每個環節都有好處,慢慢把影響範圍擴大就好。
最近,我與一位千禧世代的創作者聊到「四方共好」的想法,他說「我們是把『友善環境』也加入其中,朝『五方共好』的方向在行動」。了解到製作循環的重心再度轉移,我們的理念似乎橫跨了世代且更加深化,令我感到欣慰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