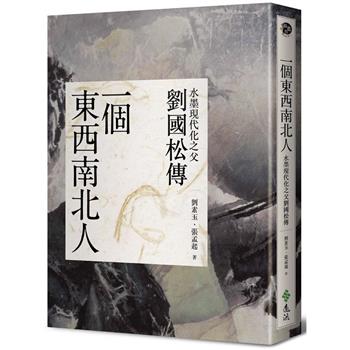13 「也」字輩的美食家
劉國松喜歡吃是出了名的,但是「美食主義者」這種封號似乎適合用在他的身上,因為他從不挑食,他固然喜愛品嚐山珍海味、燕窩魚翅等珍饈佳餚,但是一般小吃、家常小菜,他一樣甘之如飴,而且吃的興高采烈;他又胃口奇佳,食量驚人,而且消化吸收能力特別強,所有現代的養生之道在他身上好像全都失靈,他既不講究定時定量,而且也從不忌嘴,大魚大肉、海產野味,他都大塊朵頤。吃到他特別喜愛的食物,他更是絕不客氣,他有過一次大啖七隻大閘蟹的記錄,被傳為美談。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不必管太多啦! 」
「別人吃講究吃八分飽,我都是要吃十二分飽。」
談到吃,他總是眉開眼笑,不但自己來者不拒,而且也總勸別人開懷大吃,盡情享受,想吃又擔心太多,對於健康反而不利。
「你看看我,吃東西一向百無禁忌,身體卻十分健壯。」他快樂地現身說法。
許多人都不得不承認,與他共同進餐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因為他是那麼喜悅地在享受所有的食物。
他認為所有的食物都有一定的營養價值,也都對人體健康有幫助。他熱愛食物,一如他熱愛繪畫,因此他不知不覺也會把兩者的關係帶進他的畫論當中。
在他那著名的論文<當前中國畫的觀念問題>中,就說過:「一個孩子如要發育正常,偏食都是要不得的,凡是胃口好不忌嘴的,身體一定比較強壯,壽命自然也長多了。」
這是他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參加北京國際水墨畫理論討論會中發表的論文,巧妙地把世界文化比喻為人體所需要的各種養分,「中國畫一定要從舊有僵化形式中解放出來,才能找到生路。如果中國畫家也想要走向世界,成為國際藝壇的一員,首先就要開闊心胸,接受世界各地文化的養分。」
劉國松以實例舉出,西洋藝術到了二十世紀後來居上,就是由於懂得吸收世界文化的養分,經過消化而創造出來的結果,例如梵谷吸收東方繪畫中黑色點和線的技巧,強調筆觸的價值;塞尚吸收東方繪畫二度空間的表現方式,放棄歐洲上千年的三度空間的寫實傳統;馬蒂斯由日本版畫及中國剪紙中得到了單純效果;畢卡索則從非洲黑人原始雕塑中獲得靈感;紐約派畫家更從中國書法的結構中吸取抽象的律動美,創造了震驚世界的抽象表現主義。13 「也」字輩的美食家
劉國松喜歡吃是出了名的,但是「美食主義者」這種封號似乎適合用在他的身上,因為他從不挑食,他固然喜愛品嚐山珍海味、燕窩魚翅等珍饈佳餚,但是一般小吃、家常小菜,他一樣甘之如飴,而且吃的興高采烈;他又胃口奇佳,食量驚人,而且消化吸收能力特別強,所有現代的養生之道在他身上好像全都失靈,他既不講究定時定量,而且也從不忌嘴,大魚大肉、海產野味,他都大塊朵頤。吃到他特別喜愛的食物,他更是絕不客氣,他有過一次大啖七隻大閘蟹的記錄,被傳為美談。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不必管太多啦! 」
「別人吃講究吃八分飽,我都是要吃十二分飽。」
談到吃,他總是眉開眼笑,不但自己來者不拒,而且也總勸別人開懷大吃,盡情享受,想吃又擔心太多,對於健康反而不利。
「你看看我,吃東西一向百無禁忌,身體卻十分健壯。」他快樂地現身說法。
許多人都不得不承認,與他共同進餐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因為他是那麼喜悅地在享受所有的食物。
他認為所有的食物都有一定的營養價值,也都對人體健康有幫助。他熱愛食物,一如他熱愛繪畫,因此他不知不覺也會把兩者的關係帶進他的畫論當中。
在他那著名的論文<當前中國畫的觀念問題>中,就說過:「一個孩子如要發育正常,偏食都是要不得的,凡是胃口好不忌嘴的,身體一定比較強壯,壽命自然也長多了。」
這是他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參加北京國際水墨畫理論討論會中發表的論文,巧妙地把世界文化比喻為人體所需要的各種養分,「中國畫一定要從舊有僵化形式中解放出來,才能找到生路。如果中國畫家也想要走向世界,成為國際藝壇的一員,首先就要開闊心胸,接受世界各地文化的養分。」
劉國松以實例舉出,西洋藝術到了二十世紀後來居上,就是由於懂得吸收世界文化的養分,經過消化而創造出來的結果,例如梵谷吸收東方繪畫中黑色點和線的技巧,強調筆觸的價值;塞尚吸收東方繪畫二度空間的表現方式,放棄歐洲上千年的三度空間的寫實傳統;馬蒂斯由日本版畫及中國剪紙中得到了單純效果;畢卡索則從非洲黑人原始雕塑中獲得靈感;紐約派畫家更從中國書法的結構中吸取抽象的律動美,創造了震驚世界的抽象表現主義。
劉國松所指出的方向非常明確,中國畫想要趕上進步,甚至超越西方,當然必須不斷拚命吸收各種養分。
「劉國松啊,就是貪吃啦! 還要講一大堆大道理。」
提到自己的名畫家丈夫,黎模華經常不留餘地的大力批評。她一直保留著年輕學生時代的習慣,指名道姓稱呼她的另一半;從來不會在人前誇讚自己的先生,則是她的另外一個習慣。如果說劉國松是快人快語的話,那麼黎模華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她常常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指出劉國松的種種毛病。
「老說自己的先生有多好,那樣子真丟臉。」
她也不喜歡劉國松在大家面前對她表現得十分體貼,那一樣也很丟臉,例如,她最討厭劉國松當著大家的面幫她夾菜,害得她好難為情。可是劉國松總是改不了這個毛病。
劉令徽則觀察說:「我看我爸,真的吃得很不健康,可是我爸身體真的很好,到現在去做檢查都還非常正常。所以我們就認為不是每個人的體質都一樣。」她認為,劉國松的體質好,這是有點先天的優勢,他吃了很多高膽固醇、高油脂的食物,膽固醇比她媽還要低,他也沒有高血脂的問題,可能是大量喝綠茶的關係。
「我們都覺得很奇怪,他在大吃大喝的狀況下,指數都很標準。我們還是會提醒他,你是很幸運,可是你還是要注意一下;可是相反來看,若他身體沒有問題,我們是不是還要他改變生活習慣?也許,他體力這麼好,跟他吃得多也有關。」
對於太太老罵他吃太多,劉國松毫不在意,反而說:「吃得多,又能吸收消化,表示身體健康。」他舉例說,許多鼎鼎大名的老畫家,都很能吃,身體比誰都硬朗,活得比誰都長壽。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他應中國畫研究院之邀,參加該院的成立大會與展覽,這是他首次與大陸的前輩畫家見面,包括李可染、劉海粟、陸儼少、吳作人等等,除了觀摩畫藝、交換作畫心得讓他大開眼界之外,還讓他發現一件非常令人驚訝的事。
「那些前輩畫家一個個都能吃,吃得比我這個年輕人還要多。」
劉國松後來得到一個結論,凡是愈能吃的,生命力就愈強,也就愈有創造力,他們在藝術上的表現也就愈精彩。有了這個結論之後,他從此就更吃得無所忌諱。
劉國松愛吃,太太黎模華則是會燒;劉國松豪爽熱情,黎模華也不遑多讓。劉國松交遊廣闊,常常呼朋引伴,包括後生晚輩,到家裡作客,甚至有時都沒有先通知太太,就把人家請到家裡吃飯,而黎模華總是有辦法變出一桌好菜,熱情款待,賓主盡歡。
由於他們兩人都好客,又能夠夫唱婦隨,無縫接軌,所以家裡經常高朋滿座,劉國松的朋友橫跨兩岸三地,他在香港的家,就成為中、港、臺,甚至是國際友人,如朱德群等各地友人往來的最佳聚點,尤其當時臺灣的朋友們到訪香港,經常到劉國松家聚會,更難得的是從大陸來香港的朋友,因為當年能夠到香港很不容易,例如吳冠中首次到香港舉辦展覽時,熱情的劉國松就邀請到自己家裡作客。不只是藝術家經常在劉國松家聚餐,還有作家、詩人、報人,如余光中、林海音、胡菊人等,也有電影界聞人,如導演胡金銓、白景瑞等;更有其他領域人士,如科學家楊振寧於一九八五年在中文大學做訪問學人時,剛好與劉國松住同一棟樓,兩人雖然研究的領域不同,卻互相談得來而結為好友,這位諾貝爾獎得主當然也享受過黎模華的好手藝,二○○七年劉國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個展時,楊振寧還親自出席剪綵,足見他與劉國松的好交情。
黎模華不僅是手藝精湛,而且用料不惜工本,出自大戶人家的她從小就很大氣,尤其認為請客絕對不可以小裡小氣,所以花再多的錢也在所不惜。她說:「菜要燒得好吃,關鍵就是講究食材。」
劉國松算是成名早,開始賣畫早,畫又賣的好的畫家,到美國巡迴展覽之後,物質條件相對於同時代的臺灣畫家,當然要好很多,但儘管不缺錢用,夫妻倆的生活還是相當簡樸。黎模華高級一點的衣服、皮包,劉國松的手錶、皮鞋,只要是好的,都是大女兒送的,他們自己都捨不得買。劉國松夫妻認為,節儉是由早年就養成的習慣,也沒什不好。
可是有兩樣劉國松夫婦不省,一是吃,二是和畫有關的支出。舉凡畫冊、裝裱、畫框等,劉國松都要求最好的品質,黎模華形容他為了要求畫冊最高品質,「花錢不眨眼」,想當年剛結婚不久,家裡存款不到一萬元,他印個畫冊居然花了四萬元。吃呢,不管是在外面吃館子,或是自己買材料回家煮,劉國松夫婦都不手軟。
對於劉國松夫婦獨特的消費性格,大女兒令徽觀察入微,她說:「我媽、我爸花錢和別人不太一樣,他們在穿著上尤其捨不得,通常好的衣服都是我買給他們的。很多生活用品也很節儉,也捨不得開名牌汽車。唯獨就是捨得吃,在食物上面也很大方,我媽買魚翅、燕窩等,都很大手筆。」
其實劉國松夫婦的這種消費習慣跟很多老一輩沒兩樣,只是比較極端一些。以劉國松在國際藝壇上的地位及身價,要穿什麼名牌服飾、開什麼高級名車,都不是問題。常有朋友們勸他不要太節省,隨便賣一張畫就抵得過一部上百萬的好車了,他總是依然故我。一直到快要八十歲了,基於安全考量,才買了一部歐洲休旅車,但平常幾乎都捨不得開,照樣開著一部老舊的福特汽車,即使小毛病不少,也照開不誤。
「不是因為買不起,而是真的捨不得。」劉令徽知道,父母是苦出來的,節儉已經是生活習慣了,而改變習慣是很困難的。不過有一點,她父母跟別人很不一樣,就是特別捨得花錢印畫冊。
「我媽媽常提到,爸爸的第一本畫冊是借錢印的,花了好多錢,他一點也不含糊,我覺得這是我爸敬業的地方。」劉令徽不但覺得爸爸的敬業態度很可貴,她媽媽全力支持爸爸花大錢印畫冊,也是很了不起,這的確不是一般女性做得到的。
劉國松好客,朋友、學生又多,常邀朋友回家吃飯。甚至有時忙,邀了客人回家用餐,不但忘了先告訴太太,自己還比客人晚回家。黎模華只好練就一身臨時變魔術般的手藝,能遷就冰箱中僅有的材料,馬上變出一桌菜來;如果來客是事先預約的,那當然就更豐盛了。
對於黎模華的手藝,劉國松是贊不絕口,如數家珍。一九八○年,劉國松夫婦第三次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班。有一次,應寫作班主持人聶華苓邀請請,黎模華一個人為來自各國的詩人、作家,準備了五十人份的自助餐。她使出渾身解數,烤箱裡同時烤兩隻鴨,三個鍋裡蒸著三條魚,抽空還可以在另一鍋炸東西,一會兒再換快炒。鴨烤熟了再換雞,等鴨吃完了,雞火候也到了,正好上桌,火候、時間掌握的恰到好處、有條不紊,而且色香味俱全,令在場的賓客大為佩服。
劉國松還記得那次的盛宴,他太太要做燻魚,就叫他去愛荷華河去釣,那條河的魚之多,簡直多如過江之鯽。他很快就釣了四條魚回來,黎模華料理之後,發現可能不夠五十人吃,就叫劉國松而去釣兩條。劉國松記得,他臨出門時,先前釣回來的四條魚已經下鍋了,當他再釣兩條回來時,一轉眼,六條魚竟然同時上桌了,而且火候味道還都一樣好。
「我太太的手藝真是了不得啊!」劉國松一點都不吝於讚美太太。
劉令徽說,她想寫一篇〈白開水與酸辣湯〉的文章,談談父母的婚姻互動。劉國松則想寫一篇〈從牛肉燴餅到螞蟻上樹〉的文章,談談他們夫妻相處情趣。牛肉燴餅可說是黎模華對劉國松種下好感的「定情之食物」,對劉國松的意義自不待言。螞蟻上樹這道家常菜又有何值得特書之處?劉國松是山東人,對麵食、粉絲類的食物情有獨鍾,上館子就愛點螞蟻上樹這種好吃又不貴的菜。但是結婚之後就再也吃不到了,因為婚後夫妻倆上館子,每當劉國松要點螞蟻上樹時,老是被太太阻止,理由很充足:「螞蟻上樹太普通,材料也便宜,又不難作,回家做就好了。在外面吃飯,就是要點自己做不出,或是難做的。要吃螞蟻上樹,我回家做給你吃就好了。」可是,回家她就就忘了;忘歸忘,下一次上館子劉國松要點這道菜,太太還是反對。
一直到一九九二年,劉國松由香港中文大學退休,準備返臺定居前夕,他們去一家常去的四川館子,劉國松又要點螞蟻上樹,太太依舊攔阻,劉國松終於忍不住對她說:「親愛的太太,我每次要點這個菜,你都不讓我點,都說要回家做給我吃,可是我們結婚已經三十年了,我還是沒吃到,今天總該讓我吃了吧?」黎模華聽了也不禁大笑起來,劉國松這時才真的開開心心的吃了螞蟻上樹。
劉國松是真的挺愛吃粉絲,吃螃蟹粉絲煲,他都一個勁吃粉絲呢。吃完了,幸福的摸摸肚子,然後有點不好意思的說:「唉呀,不小心又吃多了!」
劉國松經常自我調侃地說,在家裡論起吃這件事,他是屬於「也」字輩的。何謂「也」字輩?原來是黎模華心疼三個小孩,在家裡燒菜,以小孩喜歡的菜色優先,就連吃飯時間也盡量配合小孩的作息,在叫劉國松吃菜的時候,常說:「你也吃這個吧。」要不就是有客人來,太太特別下廚,為客人燒些好菜,那時劉國松「也」可以沾點口福。
自嘲是「也」字輩的劉國松,其實是在溫柔的抗議太太從不專門為他燒點好菜吃。然而抗議歸抗議,可以看得出來,他十分疼愛妻兒子女,因此在家吃飯,甘於淪為「也」字輩;從另一方面更可以看出,他確實是胃口奇佳,縱然吃遍山珍海味、大魚大肉,就連清湯寡水、酸甜苦辣,及至剩菜殘羹,都來者不拒,照單全收,而且還都能消化吸收,因而體格健壯,精力充沛,也唯有這樣得天獨厚的本領,才能擔當「也」字輩大任。劉國松雖然聲稱「從不挑食」,其實很懂得享受美食,遇到自己特別喜歡的佳肴,胃口更是奇大無比,他更是美食的行動派,例如他愛吃螃蟹,直到現在,每年香港產黃油蟹的季節,不論多忙,他都專程搭飛機去吃。由於他在香港居住過二十多年,對香港的美食如數家珍,津津樂道,像是他最愛的一家北京菜館子鹿鳴春,每次造訪香港,往往一下飛機,就一定先去報到;離開香港時,也設法再去大吃一頓,還要另外打包一鍋滿滿的雞煲翅回臺灣。黎模華說,劉國松每次離港前去鹿鳴春吃晚餐,都要吃到打飽嗝了才覺得滿意,然後上了回臺灣的飛機,他照樣把飛機上的整份晚餐全部吃光光。
「胃口大得真嚇人,說起來簡直令人難為情 !」黎模華常常取笑劉國松是大胃王,很愛爆料老公大啖美食的奇聞趣事,儘管如此,她實在不得不承認,劉國松天生就很有口福,不像她自己很多食物都不敢碰,例如羊肉、蛇肉,及一大堆叫不出名字的野味等。
劉國松所指出的方向非常明確,中國畫想要趕上進步,甚至超越西方,當然必須不斷拚命吸收各種養分。
「劉國松啊,就是貪吃啦! 還要講一大堆大道理。」
提到自己的名畫家丈夫,黎模華經常不留餘地的大力批評。她一直保留著年輕學生時代的習慣,指名道姓稱呼她的另一半;從來不會在人前誇讚自己的先生,則是她的另外一個習慣。如果說劉國松是快人快語的話,那麼黎模華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她常常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指出劉國松的種種毛病。
「老說自己的先生有多好,那樣子真丟臉。」
她也不喜歡劉國松在大家面前對她表現得十分體貼,那一樣也很丟臉,例如,她最討厭劉國松當著大家的面幫她夾菜,害得她好難為情。可是劉國松總是改不了這個毛病。
劉令徽則觀察說:「我看我爸,真的吃得很不健康,可是我爸身體真的很好,到現在去做檢查都還非常正常。所以我們就認為不是每個人的體質都一樣。」她認為,劉國松的體質好,這是有點先天的優勢,他吃了很多高膽固醇、高油脂的食物,膽固醇比她媽還要低,他也沒有高血脂的問題,可能是大量喝綠茶的關係。
「我們都覺得很奇怪,他在大吃大喝的狀況下,指數都很標準。我們還是會提醒他,你是很幸運,可是你還是要注意一下;可是相反來看,若他身體沒有問題,我們是不是還要他改變生活習慣?也許,他體力這麼好,跟他吃得多也有關。」
對於太太老罵他吃太多,劉國松毫不在意,反而說:「吃得多,又能吸收消化,表示身體健康。」他舉例說,許多鼎鼎大名的老畫家,都很能吃,身體比誰都硬朗,活得比誰都長壽。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他應中國畫研究院之邀,參加該院的成立大會與展覽,這是他首次與大陸的前輩畫家見面,包括李可染、劉海粟、陸儼少、吳作人等等,除了觀摩畫藝、交換作畫心得讓他大開眼界之外,還讓他發現一件非常令人驚訝的事。
「那些前輩畫家一個個都能吃,吃得比我這個年輕人還要多。」
劉國松後來得到一個結論,凡是愈能吃的,生命力就愈強,也就愈有創造力,他們在藝術上的表現也就愈精彩。有了這個結論之後,他從此就更吃得無所忌諱。劉國松愛吃,太太黎模華則是會燒;劉國松豪爽熱情,黎模華也不遑多讓。劉國松交遊廣闊,常常呼朋引伴,包括後生晚輩,到家裡作客,甚至有時都沒有先通知太太,就把人家請到家裡吃飯,而黎模華總是有辦法變出一桌好菜,熱情款待,賓主盡歡。
由於他們兩人都好客,又能夠夫唱婦隨,無縫接軌,所以家裡經常高朋滿座,劉國松的朋友橫跨兩岸三地,他在香港的家,就成為中、港、臺,甚至是國際友人,如朱德群等各地友人往來的最佳聚點,尤其當時臺灣的朋友們到訪香港,經常到劉國松家聚會,更難得的是從大陸來香港的朋友,因為當年能夠到香港很不容易,例如吳冠中首次到香港舉辦展覽時,熱情的劉國松就邀請到自己家裡作客。不只是藝術家經常在劉國松家聚餐,還有作家、詩人、報人,如余光中、林海音、胡菊人等,也有電影界聞人,如導演胡金銓、白景瑞等;更有其他領域人士,如科學家楊振寧於一九八五年在中文大學做訪問學人時,剛好與劉國松住同一棟樓,兩人雖然研究的領域不同,卻互相談得來而結為好友,這位諾貝爾獎得主當然也享受過黎模華的好手藝,二○○七年劉國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個展時,楊振寧還親自出席剪綵,足見他與劉國松的好交情。
黎模華不僅是手藝精湛,而且用料不惜工本,出自大戶人家的她從小就很大氣,尤其認為請客絕對不可以小裡小氣,所以花再多的錢也在所不惜。她說:「菜要燒得好吃,關鍵就是講究食材。」
劉國松算是成名早,開始賣畫早,畫又賣的好的畫家,到美國巡迴展覽之後,物質條件相對於同時代的臺灣畫家,當然要好很多,但儘管不缺錢用,夫妻倆的生活還是相當簡樸。黎模華高級一點的衣服、皮包,劉國松的手錶、皮鞋,只要是好的,都是大女兒送的,他們自己都捨不得買。劉國松夫妻認為,節儉是由早年就養成的習慣,也沒什不好。
可是有兩樣劉國松夫婦不省,一是吃,二是和畫有關的支出。舉凡畫冊、裝裱、畫框等,劉國松都要求最好的品質,黎模華形容他為了要求畫冊最高品質,「花錢不眨眼」,想當年剛結婚不久,家裡存款不到一萬元,他印個畫冊居然花了四萬元。吃呢,不管是在外面吃館子,或是自己買材料回家煮,劉國松夫婦都不手軟。對於劉國松夫婦獨特的消費性格,大女兒令徽觀察入微,她說:「我媽、我爸花錢和別人不太一樣,他們在穿著上尤其捨不得,通常好的衣服都是我買給他們的。很多生活用品也很節儉,也捨不得開名牌汽車。唯獨就是捨得吃,在食物上面也很大方,我媽買魚翅、燕窩等,都很大手筆。」
其實劉國松夫婦的這種消費習慣跟很多老一輩沒兩樣,只是比較極端一些。以劉國松在國際藝壇上的地位及身價,要穿什麼名牌服飾、開什麼高級名車,都不是問題。常有朋友們勸他不要太節省,隨便賣一張畫就抵得過一部上百萬的好車了,他總是依然故我。一直到快要八十歲了,基於安全考量,才買了一部歐洲休旅車,但平常幾乎都捨不得開,照樣開著一部老舊的福特汽車,即使小毛病不少,也照開不誤。
「不是因為買不起,而是真的捨不得。」劉令徽知道,父母是苦出來的,節儉已經是生活習慣了,而改變習慣是很困難的。不過有一點,她父母跟別人很不一樣,就是特別捨得花錢印畫冊。
「我媽媽常提到,爸爸的第一本畫冊是借錢印的,花了好多錢,他一點也不含糊,我覺得這是我爸敬業的地方。」劉令徽不但覺得爸爸的敬業態度很可貴,她媽媽全力支持爸爸花大錢印畫冊,也是很了不起,這的確不是一般女性做得到的。
劉國松好客,朋友、學生又多,常邀朋友回家吃飯。甚至有時忙,邀了客人回家用餐,不但忘了先告訴太太,自己還比客人晚回家。黎模華只好練就一身臨時變魔術般的手藝,能遷就冰箱中僅有的材料,馬上變出一桌菜來;如果來客是事先預約的,那當然就更豐盛了。
對於黎模華的手藝,劉國松是贊不絕口,如數家珍。一九八○年,劉國松夫婦第三次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班。有一次,應寫作班主持人聶華苓邀請請,黎模華一個人為來自各國的詩人、作家,準備了五十人份的自助餐。她使出渾身解數,烤箱裡同時烤兩隻鴨,三個鍋裡蒸著三條魚,抽空還可以在另一鍋炸東西,一會兒再換快炒。鴨烤熟了再換雞,等鴨吃完了,雞火候也到了,正好上桌,火候、時間掌握的恰到好處、有條不紊,而且色香味俱全,令在場的賓客大為佩服。劉國松還記得那次的盛宴,他太太要做燻魚,就叫他去愛荷華河去釣,那條河的魚之多,簡直多如過江之鯽。他很快就釣了四條魚回來,黎模華料理之後,發現可能不夠五十人吃,就叫劉國松而去釣兩條。劉國松記得,他臨出門時,先前釣回來的四條魚已經下鍋了,當他再釣兩條回來時,一轉眼,六條魚竟然同時上桌了,而且火候味道還都一樣好。
「我太太的手藝真是了不得啊!」劉國松一點都不吝於讚美太太。
劉令徽說,她想寫一篇〈白開水與酸辣湯〉的文章,談談父母的婚姻互動。劉國松則想寫一篇〈從牛肉燴餅到螞蟻上樹〉的文章,談談他們夫妻相處情趣。牛肉燴餅可說是黎模華對劉國松種下好感的「定情之食物」,對劉國松的意義自不待言。螞蟻上樹這道家常菜又有何值得特書之處?劉國松是山東人,對麵食、粉絲類的食物情有獨鍾,上館子就愛點螞蟻上樹這種好吃又不貴的菜。但是結婚之後就再也吃不到了,因為婚後夫妻倆上館子,每當劉國松要點螞蟻上樹時,老是被太太阻止,理由很充足:「螞蟻上樹太普通,材料也便宜,又不難作,回家做就好了。在外面吃飯,就是要點自己做不出,或是難做的。要吃螞蟻上樹,我回家做給你吃就好了。」可是,回家她就就忘了;忘歸忘,下一次上館子劉國松要點這道菜,太太還是反對。
一直到一九九二年,劉國松由香港中文大學退休,準備返臺定居前夕,他們去一家常去的四川館子,劉國松又要點螞蟻上樹,太太依舊攔阻,劉國松終於忍不住對她說:「親愛的太太,我每次要點這個菜,你都不讓我點,都說要回家做給我吃,可是我們結婚已經三十年了,我還是沒吃到,今天總該讓我吃了吧?」黎模華聽了也不禁大笑起來,劉國松這時才真的開開心心的吃了螞蟻上樹。
劉國松是真的挺愛吃粉絲,吃螃蟹粉絲煲,他都一個勁吃粉絲呢。吃完了,幸福的摸摸肚子,然後有點不好意思的說:「唉呀,不小心又吃多了!」
劉國松經常自我調侃地說,在家裡論起吃這件事,他是屬於「也」字輩的。何謂「也」字輩?原來是黎模華心疼三個小孩,在家裡燒菜,以小孩喜歡的菜色優先,就連吃飯時間也盡量配合小孩的作息,在叫劉國松吃菜的時候,常說:「你也吃這個吧。」要不就是有客人來,太太特別下廚,為客人燒些好菜,那時劉國松「也」可以沾點口福。自嘲是「也」字輩的劉國松,其實是在溫柔的抗議太太從不專門為他燒點好菜吃。然而抗議歸抗議,可以看得出來,他十分疼愛妻兒子女,因此在家吃飯,甘於淪為「也」字輩;從另一方面更可以看出,他確實是胃口奇佳,縱然吃遍山珍海味、大魚大肉,就連清湯寡水、酸甜苦辣,及至剩菜殘羹,都來者不拒,照單全收,而且還都能消化吸收,因而體格健壯,精力充沛,也唯有這樣得天獨厚的本領,才能擔當「也」字輩大任。劉國松雖然聲稱「從不挑食」,其實很懂得享受美食,遇到自己特別喜歡的佳肴,胃口更是奇大無比,他更是美食的行動派,例如他愛吃螃蟹,直到現在,每年香港產黃油蟹的季節,不論多忙,他都專程搭飛機去吃。由於他在香港居住過二十多年,對香港的美食如數家珍,津津樂道,像是他最愛的一家北京菜館子鹿鳴春,每次造訪香港,往往一下飛機,就一定先去報到;離開香港時,也設法再去大吃一頓,還要另外打包一鍋滿滿的雞煲翅回臺灣。黎模華說,劉國松每次離港前去鹿鳴春吃晚餐,都要吃到打飽嗝了才覺得滿意,然後上了回臺灣的飛機,他照樣把飛機上的整份晚餐全部吃光光。
「胃口大得真嚇人,說起來簡直令人難為情 !」黎模華常常取笑劉國松是大胃王,很愛爆料老公大啖美食的奇聞趣事,儘管如此,她實在不得不承認,劉國松天生就很有口福,不像她自己很多食物都不敢碰,例如羊肉、蛇肉,及一大堆叫不出名字的野味等。
劉國松喜歡吃是出了名的,但是「美食主義者」這種封號似乎適合用在他的身上,因為他從不挑食,他固然喜愛品嚐山珍海味、燕窩魚翅等珍饈佳餚,但是一般小吃、家常小菜,他一樣甘之如飴,而且吃的興高采烈;他又胃口奇佳,食量驚人,而且消化吸收能力特別強,所有現代的養生之道在他身上好像全都失靈,他既不講究定時定量,而且也從不忌嘴,大魚大肉、海產野味,他都大塊朵頤。吃到他特別喜愛的食物,他更是絕不客氣,他有過一次大啖七隻大閘蟹的記錄,被傳為美談。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不必管太多啦! 」
「別人吃講究吃八分飽,我都是要吃十二分飽。」
談到吃,他總是眉開眼笑,不但自己來者不拒,而且也總勸別人開懷大吃,盡情享受,想吃又擔心太多,對於健康反而不利。
「你看看我,吃東西一向百無禁忌,身體卻十分健壯。」他快樂地現身說法。
許多人都不得不承認,與他共同進餐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因為他是那麼喜悅地在享受所有的食物。
他認為所有的食物都有一定的營養價值,也都對人體健康有幫助。他熱愛食物,一如他熱愛繪畫,因此他不知不覺也會把兩者的關係帶進他的畫論當中。
在他那著名的論文<當前中國畫的觀念問題>中,就說過:「一個孩子如要發育正常,偏食都是要不得的,凡是胃口好不忌嘴的,身體一定比較強壯,壽命自然也長多了。」
這是他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參加北京國際水墨畫理論討論會中發表的論文,巧妙地把世界文化比喻為人體所需要的各種養分,「中國畫一定要從舊有僵化形式中解放出來,才能找到生路。如果中國畫家也想要走向世界,成為國際藝壇的一員,首先就要開闊心胸,接受世界各地文化的養分。」
劉國松以實例舉出,西洋藝術到了二十世紀後來居上,就是由於懂得吸收世界文化的養分,經過消化而創造出來的結果,例如梵谷吸收東方繪畫中黑色點和線的技巧,強調筆觸的價值;塞尚吸收東方繪畫二度空間的表現方式,放棄歐洲上千年的三度空間的寫實傳統;馬蒂斯由日本版畫及中國剪紙中得到了單純效果;畢卡索則從非洲黑人原始雕塑中獲得靈感;紐約派畫家更從中國書法的結構中吸取抽象的律動美,創造了震驚世界的抽象表現主義。13 「也」字輩的美食家
劉國松喜歡吃是出了名的,但是「美食主義者」這種封號似乎適合用在他的身上,因為他從不挑食,他固然喜愛品嚐山珍海味、燕窩魚翅等珍饈佳餚,但是一般小吃、家常小菜,他一樣甘之如飴,而且吃的興高采烈;他又胃口奇佳,食量驚人,而且消化吸收能力特別強,所有現代的養生之道在他身上好像全都失靈,他既不講究定時定量,而且也從不忌嘴,大魚大肉、海產野味,他都大塊朵頤。吃到他特別喜愛的食物,他更是絕不客氣,他有過一次大啖七隻大閘蟹的記錄,被傳為美談。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不必管太多啦! 」
「別人吃講究吃八分飽,我都是要吃十二分飽。」
談到吃,他總是眉開眼笑,不但自己來者不拒,而且也總勸別人開懷大吃,盡情享受,想吃又擔心太多,對於健康反而不利。
「你看看我,吃東西一向百無禁忌,身體卻十分健壯。」他快樂地現身說法。
許多人都不得不承認,與他共同進餐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因為他是那麼喜悅地在享受所有的食物。
他認為所有的食物都有一定的營養價值,也都對人體健康有幫助。他熱愛食物,一如他熱愛繪畫,因此他不知不覺也會把兩者的關係帶進他的畫論當中。
在他那著名的論文<當前中國畫的觀念問題>中,就說過:「一個孩子如要發育正常,偏食都是要不得的,凡是胃口好不忌嘴的,身體一定比較強壯,壽命自然也長多了。」
這是他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參加北京國際水墨畫理論討論會中發表的論文,巧妙地把世界文化比喻為人體所需要的各種養分,「中國畫一定要從舊有僵化形式中解放出來,才能找到生路。如果中國畫家也想要走向世界,成為國際藝壇的一員,首先就要開闊心胸,接受世界各地文化的養分。」
劉國松以實例舉出,西洋藝術到了二十世紀後來居上,就是由於懂得吸收世界文化的養分,經過消化而創造出來的結果,例如梵谷吸收東方繪畫中黑色點和線的技巧,強調筆觸的價值;塞尚吸收東方繪畫二度空間的表現方式,放棄歐洲上千年的三度空間的寫實傳統;馬蒂斯由日本版畫及中國剪紙中得到了單純效果;畢卡索則從非洲黑人原始雕塑中獲得靈感;紐約派畫家更從中國書法的結構中吸取抽象的律動美,創造了震驚世界的抽象表現主義。
劉國松所指出的方向非常明確,中國畫想要趕上進步,甚至超越西方,當然必須不斷拚命吸收各種養分。
「劉國松啊,就是貪吃啦! 還要講一大堆大道理。」
提到自己的名畫家丈夫,黎模華經常不留餘地的大力批評。她一直保留著年輕學生時代的習慣,指名道姓稱呼她的另一半;從來不會在人前誇讚自己的先生,則是她的另外一個習慣。如果說劉國松是快人快語的話,那麼黎模華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她常常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指出劉國松的種種毛病。
「老說自己的先生有多好,那樣子真丟臉。」
她也不喜歡劉國松在大家面前對她表現得十分體貼,那一樣也很丟臉,例如,她最討厭劉國松當著大家的面幫她夾菜,害得她好難為情。可是劉國松總是改不了這個毛病。
劉令徽則觀察說:「我看我爸,真的吃得很不健康,可是我爸身體真的很好,到現在去做檢查都還非常正常。所以我們就認為不是每個人的體質都一樣。」她認為,劉國松的體質好,這是有點先天的優勢,他吃了很多高膽固醇、高油脂的食物,膽固醇比她媽還要低,他也沒有高血脂的問題,可能是大量喝綠茶的關係。
「我們都覺得很奇怪,他在大吃大喝的狀況下,指數都很標準。我們還是會提醒他,你是很幸運,可是你還是要注意一下;可是相反來看,若他身體沒有問題,我們是不是還要他改變生活習慣?也許,他體力這麼好,跟他吃得多也有關。」
對於太太老罵他吃太多,劉國松毫不在意,反而說:「吃得多,又能吸收消化,表示身體健康。」他舉例說,許多鼎鼎大名的老畫家,都很能吃,身體比誰都硬朗,活得比誰都長壽。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他應中國畫研究院之邀,參加該院的成立大會與展覽,這是他首次與大陸的前輩畫家見面,包括李可染、劉海粟、陸儼少、吳作人等等,除了觀摩畫藝、交換作畫心得讓他大開眼界之外,還讓他發現一件非常令人驚訝的事。
「那些前輩畫家一個個都能吃,吃得比我這個年輕人還要多。」
劉國松後來得到一個結論,凡是愈能吃的,生命力就愈強,也就愈有創造力,他們在藝術上的表現也就愈精彩。有了這個結論之後,他從此就更吃得無所忌諱。
劉國松愛吃,太太黎模華則是會燒;劉國松豪爽熱情,黎模華也不遑多讓。劉國松交遊廣闊,常常呼朋引伴,包括後生晚輩,到家裡作客,甚至有時都沒有先通知太太,就把人家請到家裡吃飯,而黎模華總是有辦法變出一桌好菜,熱情款待,賓主盡歡。
由於他們兩人都好客,又能夠夫唱婦隨,無縫接軌,所以家裡經常高朋滿座,劉國松的朋友橫跨兩岸三地,他在香港的家,就成為中、港、臺,甚至是國際友人,如朱德群等各地友人往來的最佳聚點,尤其當時臺灣的朋友們到訪香港,經常到劉國松家聚會,更難得的是從大陸來香港的朋友,因為當年能夠到香港很不容易,例如吳冠中首次到香港舉辦展覽時,熱情的劉國松就邀請到自己家裡作客。不只是藝術家經常在劉國松家聚餐,還有作家、詩人、報人,如余光中、林海音、胡菊人等,也有電影界聞人,如導演胡金銓、白景瑞等;更有其他領域人士,如科學家楊振寧於一九八五年在中文大學做訪問學人時,剛好與劉國松住同一棟樓,兩人雖然研究的領域不同,卻互相談得來而結為好友,這位諾貝爾獎得主當然也享受過黎模華的好手藝,二○○七年劉國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個展時,楊振寧還親自出席剪綵,足見他與劉國松的好交情。
黎模華不僅是手藝精湛,而且用料不惜工本,出自大戶人家的她從小就很大氣,尤其認為請客絕對不可以小裡小氣,所以花再多的錢也在所不惜。她說:「菜要燒得好吃,關鍵就是講究食材。」
劉國松算是成名早,開始賣畫早,畫又賣的好的畫家,到美國巡迴展覽之後,物質條件相對於同時代的臺灣畫家,當然要好很多,但儘管不缺錢用,夫妻倆的生活還是相當簡樸。黎模華高級一點的衣服、皮包,劉國松的手錶、皮鞋,只要是好的,都是大女兒送的,他們自己都捨不得買。劉國松夫妻認為,節儉是由早年就養成的習慣,也沒什不好。
可是有兩樣劉國松夫婦不省,一是吃,二是和畫有關的支出。舉凡畫冊、裝裱、畫框等,劉國松都要求最好的品質,黎模華形容他為了要求畫冊最高品質,「花錢不眨眼」,想當年剛結婚不久,家裡存款不到一萬元,他印個畫冊居然花了四萬元。吃呢,不管是在外面吃館子,或是自己買材料回家煮,劉國松夫婦都不手軟。
對於劉國松夫婦獨特的消費性格,大女兒令徽觀察入微,她說:「我媽、我爸花錢和別人不太一樣,他們在穿著上尤其捨不得,通常好的衣服都是我買給他們的。很多生活用品也很節儉,也捨不得開名牌汽車。唯獨就是捨得吃,在食物上面也很大方,我媽買魚翅、燕窩等,都很大手筆。」
其實劉國松夫婦的這種消費習慣跟很多老一輩沒兩樣,只是比較極端一些。以劉國松在國際藝壇上的地位及身價,要穿什麼名牌服飾、開什麼高級名車,都不是問題。常有朋友們勸他不要太節省,隨便賣一張畫就抵得過一部上百萬的好車了,他總是依然故我。一直到快要八十歲了,基於安全考量,才買了一部歐洲休旅車,但平常幾乎都捨不得開,照樣開著一部老舊的福特汽車,即使小毛病不少,也照開不誤。
「不是因為買不起,而是真的捨不得。」劉令徽知道,父母是苦出來的,節儉已經是生活習慣了,而改變習慣是很困難的。不過有一點,她父母跟別人很不一樣,就是特別捨得花錢印畫冊。
「我媽媽常提到,爸爸的第一本畫冊是借錢印的,花了好多錢,他一點也不含糊,我覺得這是我爸敬業的地方。」劉令徽不但覺得爸爸的敬業態度很可貴,她媽媽全力支持爸爸花大錢印畫冊,也是很了不起,這的確不是一般女性做得到的。
劉國松好客,朋友、學生又多,常邀朋友回家吃飯。甚至有時忙,邀了客人回家用餐,不但忘了先告訴太太,自己還比客人晚回家。黎模華只好練就一身臨時變魔術般的手藝,能遷就冰箱中僅有的材料,馬上變出一桌菜來;如果來客是事先預約的,那當然就更豐盛了。
對於黎模華的手藝,劉國松是贊不絕口,如數家珍。一九八○年,劉國松夫婦第三次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班。有一次,應寫作班主持人聶華苓邀請請,黎模華一個人為來自各國的詩人、作家,準備了五十人份的自助餐。她使出渾身解數,烤箱裡同時烤兩隻鴨,三個鍋裡蒸著三條魚,抽空還可以在另一鍋炸東西,一會兒再換快炒。鴨烤熟了再換雞,等鴨吃完了,雞火候也到了,正好上桌,火候、時間掌握的恰到好處、有條不紊,而且色香味俱全,令在場的賓客大為佩服。
劉國松還記得那次的盛宴,他太太要做燻魚,就叫他去愛荷華河去釣,那條河的魚之多,簡直多如過江之鯽。他很快就釣了四條魚回來,黎模華料理之後,發現可能不夠五十人吃,就叫劉國松而去釣兩條。劉國松記得,他臨出門時,先前釣回來的四條魚已經下鍋了,當他再釣兩條回來時,一轉眼,六條魚竟然同時上桌了,而且火候味道還都一樣好。
「我太太的手藝真是了不得啊!」劉國松一點都不吝於讚美太太。
劉令徽說,她想寫一篇〈白開水與酸辣湯〉的文章,談談父母的婚姻互動。劉國松則想寫一篇〈從牛肉燴餅到螞蟻上樹〉的文章,談談他們夫妻相處情趣。牛肉燴餅可說是黎模華對劉國松種下好感的「定情之食物」,對劉國松的意義自不待言。螞蟻上樹這道家常菜又有何值得特書之處?劉國松是山東人,對麵食、粉絲類的食物情有獨鍾,上館子就愛點螞蟻上樹這種好吃又不貴的菜。但是結婚之後就再也吃不到了,因為婚後夫妻倆上館子,每當劉國松要點螞蟻上樹時,老是被太太阻止,理由很充足:「螞蟻上樹太普通,材料也便宜,又不難作,回家做就好了。在外面吃飯,就是要點自己做不出,或是難做的。要吃螞蟻上樹,我回家做給你吃就好了。」可是,回家她就就忘了;忘歸忘,下一次上館子劉國松要點這道菜,太太還是反對。
一直到一九九二年,劉國松由香港中文大學退休,準備返臺定居前夕,他們去一家常去的四川館子,劉國松又要點螞蟻上樹,太太依舊攔阻,劉國松終於忍不住對她說:「親愛的太太,我每次要點這個菜,你都不讓我點,都說要回家做給我吃,可是我們結婚已經三十年了,我還是沒吃到,今天總該讓我吃了吧?」黎模華聽了也不禁大笑起來,劉國松這時才真的開開心心的吃了螞蟻上樹。
劉國松是真的挺愛吃粉絲,吃螃蟹粉絲煲,他都一個勁吃粉絲呢。吃完了,幸福的摸摸肚子,然後有點不好意思的說:「唉呀,不小心又吃多了!」
劉國松經常自我調侃地說,在家裡論起吃這件事,他是屬於「也」字輩的。何謂「也」字輩?原來是黎模華心疼三個小孩,在家裡燒菜,以小孩喜歡的菜色優先,就連吃飯時間也盡量配合小孩的作息,在叫劉國松吃菜的時候,常說:「你也吃這個吧。」要不就是有客人來,太太特別下廚,為客人燒些好菜,那時劉國松「也」可以沾點口福。
自嘲是「也」字輩的劉國松,其實是在溫柔的抗議太太從不專門為他燒點好菜吃。然而抗議歸抗議,可以看得出來,他十分疼愛妻兒子女,因此在家吃飯,甘於淪為「也」字輩;從另一方面更可以看出,他確實是胃口奇佳,縱然吃遍山珍海味、大魚大肉,就連清湯寡水、酸甜苦辣,及至剩菜殘羹,都來者不拒,照單全收,而且還都能消化吸收,因而體格健壯,精力充沛,也唯有這樣得天獨厚的本領,才能擔當「也」字輩大任。劉國松雖然聲稱「從不挑食」,其實很懂得享受美食,遇到自己特別喜歡的佳肴,胃口更是奇大無比,他更是美食的行動派,例如他愛吃螃蟹,直到現在,每年香港產黃油蟹的季節,不論多忙,他都專程搭飛機去吃。由於他在香港居住過二十多年,對香港的美食如數家珍,津津樂道,像是他最愛的一家北京菜館子鹿鳴春,每次造訪香港,往往一下飛機,就一定先去報到;離開香港時,也設法再去大吃一頓,還要另外打包一鍋滿滿的雞煲翅回臺灣。黎模華說,劉國松每次離港前去鹿鳴春吃晚餐,都要吃到打飽嗝了才覺得滿意,然後上了回臺灣的飛機,他照樣把飛機上的整份晚餐全部吃光光。
「胃口大得真嚇人,說起來簡直令人難為情 !」黎模華常常取笑劉國松是大胃王,很愛爆料老公大啖美食的奇聞趣事,儘管如此,她實在不得不承認,劉國松天生就很有口福,不像她自己很多食物都不敢碰,例如羊肉、蛇肉,及一大堆叫不出名字的野味等。
劉國松所指出的方向非常明確,中國畫想要趕上進步,甚至超越西方,當然必須不斷拚命吸收各種養分。
「劉國松啊,就是貪吃啦! 還要講一大堆大道理。」
提到自己的名畫家丈夫,黎模華經常不留餘地的大力批評。她一直保留著年輕學生時代的習慣,指名道姓稱呼她的另一半;從來不會在人前誇讚自己的先生,則是她的另外一個習慣。如果說劉國松是快人快語的話,那麼黎模華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她常常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指出劉國松的種種毛病。
「老說自己的先生有多好,那樣子真丟臉。」
她也不喜歡劉國松在大家面前對她表現得十分體貼,那一樣也很丟臉,例如,她最討厭劉國松當著大家的面幫她夾菜,害得她好難為情。可是劉國松總是改不了這個毛病。
劉令徽則觀察說:「我看我爸,真的吃得很不健康,可是我爸身體真的很好,到現在去做檢查都還非常正常。所以我們就認為不是每個人的體質都一樣。」她認為,劉國松的體質好,這是有點先天的優勢,他吃了很多高膽固醇、高油脂的食物,膽固醇比她媽還要低,他也沒有高血脂的問題,可能是大量喝綠茶的關係。
「我們都覺得很奇怪,他在大吃大喝的狀況下,指數都很標準。我們還是會提醒他,你是很幸運,可是你還是要注意一下;可是相反來看,若他身體沒有問題,我們是不是還要他改變生活習慣?也許,他體力這麼好,跟他吃得多也有關。」
對於太太老罵他吃太多,劉國松毫不在意,反而說:「吃得多,又能吸收消化,表示身體健康。」他舉例說,許多鼎鼎大名的老畫家,都很能吃,身體比誰都硬朗,活得比誰都長壽。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他應中國畫研究院之邀,參加該院的成立大會與展覽,這是他首次與大陸的前輩畫家見面,包括李可染、劉海粟、陸儼少、吳作人等等,除了觀摩畫藝、交換作畫心得讓他大開眼界之外,還讓他發現一件非常令人驚訝的事。
「那些前輩畫家一個個都能吃,吃得比我這個年輕人還要多。」
劉國松後來得到一個結論,凡是愈能吃的,生命力就愈強,也就愈有創造力,他們在藝術上的表現也就愈精彩。有了這個結論之後,他從此就更吃得無所忌諱。劉國松愛吃,太太黎模華則是會燒;劉國松豪爽熱情,黎模華也不遑多讓。劉國松交遊廣闊,常常呼朋引伴,包括後生晚輩,到家裡作客,甚至有時都沒有先通知太太,就把人家請到家裡吃飯,而黎模華總是有辦法變出一桌好菜,熱情款待,賓主盡歡。
由於他們兩人都好客,又能夠夫唱婦隨,無縫接軌,所以家裡經常高朋滿座,劉國松的朋友橫跨兩岸三地,他在香港的家,就成為中、港、臺,甚至是國際友人,如朱德群等各地友人往來的最佳聚點,尤其當時臺灣的朋友們到訪香港,經常到劉國松家聚會,更難得的是從大陸來香港的朋友,因為當年能夠到香港很不容易,例如吳冠中首次到香港舉辦展覽時,熱情的劉國松就邀請到自己家裡作客。不只是藝術家經常在劉國松家聚餐,還有作家、詩人、報人,如余光中、林海音、胡菊人等,也有電影界聞人,如導演胡金銓、白景瑞等;更有其他領域人士,如科學家楊振寧於一九八五年在中文大學做訪問學人時,剛好與劉國松住同一棟樓,兩人雖然研究的領域不同,卻互相談得來而結為好友,這位諾貝爾獎得主當然也享受過黎模華的好手藝,二○○七年劉國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個展時,楊振寧還親自出席剪綵,足見他與劉國松的好交情。
黎模華不僅是手藝精湛,而且用料不惜工本,出自大戶人家的她從小就很大氣,尤其認為請客絕對不可以小裡小氣,所以花再多的錢也在所不惜。她說:「菜要燒得好吃,關鍵就是講究食材。」
劉國松算是成名早,開始賣畫早,畫又賣的好的畫家,到美國巡迴展覽之後,物質條件相對於同時代的臺灣畫家,當然要好很多,但儘管不缺錢用,夫妻倆的生活還是相當簡樸。黎模華高級一點的衣服、皮包,劉國松的手錶、皮鞋,只要是好的,都是大女兒送的,他們自己都捨不得買。劉國松夫妻認為,節儉是由早年就養成的習慣,也沒什不好。
可是有兩樣劉國松夫婦不省,一是吃,二是和畫有關的支出。舉凡畫冊、裝裱、畫框等,劉國松都要求最好的品質,黎模華形容他為了要求畫冊最高品質,「花錢不眨眼」,想當年剛結婚不久,家裡存款不到一萬元,他印個畫冊居然花了四萬元。吃呢,不管是在外面吃館子,或是自己買材料回家煮,劉國松夫婦都不手軟。對於劉國松夫婦獨特的消費性格,大女兒令徽觀察入微,她說:「我媽、我爸花錢和別人不太一樣,他們在穿著上尤其捨不得,通常好的衣服都是我買給他們的。很多生活用品也很節儉,也捨不得開名牌汽車。唯獨就是捨得吃,在食物上面也很大方,我媽買魚翅、燕窩等,都很大手筆。」
其實劉國松夫婦的這種消費習慣跟很多老一輩沒兩樣,只是比較極端一些。以劉國松在國際藝壇上的地位及身價,要穿什麼名牌服飾、開什麼高級名車,都不是問題。常有朋友們勸他不要太節省,隨便賣一張畫就抵得過一部上百萬的好車了,他總是依然故我。一直到快要八十歲了,基於安全考量,才買了一部歐洲休旅車,但平常幾乎都捨不得開,照樣開著一部老舊的福特汽車,即使小毛病不少,也照開不誤。
「不是因為買不起,而是真的捨不得。」劉令徽知道,父母是苦出來的,節儉已經是生活習慣了,而改變習慣是很困難的。不過有一點,她父母跟別人很不一樣,就是特別捨得花錢印畫冊。
「我媽媽常提到,爸爸的第一本畫冊是借錢印的,花了好多錢,他一點也不含糊,我覺得這是我爸敬業的地方。」劉令徽不但覺得爸爸的敬業態度很可貴,她媽媽全力支持爸爸花大錢印畫冊,也是很了不起,這的確不是一般女性做得到的。
劉國松好客,朋友、學生又多,常邀朋友回家吃飯。甚至有時忙,邀了客人回家用餐,不但忘了先告訴太太,自己還比客人晚回家。黎模華只好練就一身臨時變魔術般的手藝,能遷就冰箱中僅有的材料,馬上變出一桌菜來;如果來客是事先預約的,那當然就更豐盛了。
對於黎模華的手藝,劉國松是贊不絕口,如數家珍。一九八○年,劉國松夫婦第三次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班。有一次,應寫作班主持人聶華苓邀請請,黎模華一個人為來自各國的詩人、作家,準備了五十人份的自助餐。她使出渾身解數,烤箱裡同時烤兩隻鴨,三個鍋裡蒸著三條魚,抽空還可以在另一鍋炸東西,一會兒再換快炒。鴨烤熟了再換雞,等鴨吃完了,雞火候也到了,正好上桌,火候、時間掌握的恰到好處、有條不紊,而且色香味俱全,令在場的賓客大為佩服。劉國松還記得那次的盛宴,他太太要做燻魚,就叫他去愛荷華河去釣,那條河的魚之多,簡直多如過江之鯽。他很快就釣了四條魚回來,黎模華料理之後,發現可能不夠五十人吃,就叫劉國松而去釣兩條。劉國松記得,他臨出門時,先前釣回來的四條魚已經下鍋了,當他再釣兩條回來時,一轉眼,六條魚竟然同時上桌了,而且火候味道還都一樣好。
「我太太的手藝真是了不得啊!」劉國松一點都不吝於讚美太太。
劉令徽說,她想寫一篇〈白開水與酸辣湯〉的文章,談談父母的婚姻互動。劉國松則想寫一篇〈從牛肉燴餅到螞蟻上樹〉的文章,談談他們夫妻相處情趣。牛肉燴餅可說是黎模華對劉國松種下好感的「定情之食物」,對劉國松的意義自不待言。螞蟻上樹這道家常菜又有何值得特書之處?劉國松是山東人,對麵食、粉絲類的食物情有獨鍾,上館子就愛點螞蟻上樹這種好吃又不貴的菜。但是結婚之後就再也吃不到了,因為婚後夫妻倆上館子,每當劉國松要點螞蟻上樹時,老是被太太阻止,理由很充足:「螞蟻上樹太普通,材料也便宜,又不難作,回家做就好了。在外面吃飯,就是要點自己做不出,或是難做的。要吃螞蟻上樹,我回家做給你吃就好了。」可是,回家她就就忘了;忘歸忘,下一次上館子劉國松要點這道菜,太太還是反對。
一直到一九九二年,劉國松由香港中文大學退休,準備返臺定居前夕,他們去一家常去的四川館子,劉國松又要點螞蟻上樹,太太依舊攔阻,劉國松終於忍不住對她說:「親愛的太太,我每次要點這個菜,你都不讓我點,都說要回家做給我吃,可是我們結婚已經三十年了,我還是沒吃到,今天總該讓我吃了吧?」黎模華聽了也不禁大笑起來,劉國松這時才真的開開心心的吃了螞蟻上樹。
劉國松是真的挺愛吃粉絲,吃螃蟹粉絲煲,他都一個勁吃粉絲呢。吃完了,幸福的摸摸肚子,然後有點不好意思的說:「唉呀,不小心又吃多了!」
劉國松經常自我調侃地說,在家裡論起吃這件事,他是屬於「也」字輩的。何謂「也」字輩?原來是黎模華心疼三個小孩,在家裡燒菜,以小孩喜歡的菜色優先,就連吃飯時間也盡量配合小孩的作息,在叫劉國松吃菜的時候,常說:「你也吃這個吧。」要不就是有客人來,太太特別下廚,為客人燒些好菜,那時劉國松「也」可以沾點口福。自嘲是「也」字輩的劉國松,其實是在溫柔的抗議太太從不專門為他燒點好菜吃。然而抗議歸抗議,可以看得出來,他十分疼愛妻兒子女,因此在家吃飯,甘於淪為「也」字輩;從另一方面更可以看出,他確實是胃口奇佳,縱然吃遍山珍海味、大魚大肉,就連清湯寡水、酸甜苦辣,及至剩菜殘羹,都來者不拒,照單全收,而且還都能消化吸收,因而體格健壯,精力充沛,也唯有這樣得天獨厚的本領,才能擔當「也」字輩大任。劉國松雖然聲稱「從不挑食」,其實很懂得享受美食,遇到自己特別喜歡的佳肴,胃口更是奇大無比,他更是美食的行動派,例如他愛吃螃蟹,直到現在,每年香港產黃油蟹的季節,不論多忙,他都專程搭飛機去吃。由於他在香港居住過二十多年,對香港的美食如數家珍,津津樂道,像是他最愛的一家北京菜館子鹿鳴春,每次造訪香港,往往一下飛機,就一定先去報到;離開香港時,也設法再去大吃一頓,還要另外打包一鍋滿滿的雞煲翅回臺灣。黎模華說,劉國松每次離港前去鹿鳴春吃晚餐,都要吃到打飽嗝了才覺得滿意,然後上了回臺灣的飛機,他照樣把飛機上的整份晚餐全部吃光光。
「胃口大得真嚇人,說起來簡直令人難為情 !」黎模華常常取笑劉國松是大胃王,很愛爆料老公大啖美食的奇聞趣事,儘管如此,她實在不得不承認,劉國松天生就很有口福,不像她自己很多食物都不敢碰,例如羊肉、蛇肉,及一大堆叫不出名字的野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