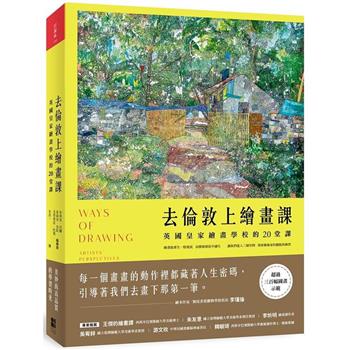畫室空間 STUDIO SPACE
【引言】朱利安.貝爾
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在任何時刻,總會有人在畫畫。有許多人安靜而快樂地忙著繪畫,集中他們的精神,揮灑他們的精力,希望自己正在使用的媒材能夠創造出生動而令人驚喜的效果。我們可以透過觀察學前遊戲小組或小學的美術課程,來看到這種廣泛而常見的繪畫場面。
我們或許也可以看看那些出現在地鐵站內的簽名塗鴉,或者──如果我們從歷史角度來看的話──看看那些舊石器時代的洞穴壁畫。無論是何種情況,過程總是比結果重要。一個人所留下的圖案,會鼓勵另一個人也做出圖案;至於這些新圖案是否貼近或覆蓋了舊圖案都無關緊要。隨著時間推移,受到前人影響而出現的類似圖案雜亂無章地蔓延,匯聚成了一大堆。然而,我們會注意到,在這一大堆圖案中,有些圖案比其他圖案更臻成熟。我們推斷,繪製這些圖案的人投入了更多的心力。他們為個人的癡迷所佔據;某種如夢似幻的東西指使了他們──無論這東西是動物、天使、惡魔或舞動的線條──驅策他們前行,使得他們畫出來的圖案比其他相鄰的作品更為突出。
但如果我們想要深入了解繪畫,那麼在洞穴及地鐵站裡漫遊只是一個開始。舊石器時代已經過去了,如今大多數人在大部分的時間裡,都必須要在有明確定義的空間內工作,而這些空間泰半方方正正。我們所創作的圖像往往要遵循相同的社會規範。一道內牆、一幅架上繪畫、一本書或一面螢幕都有其要遵守的限制。在本節及隨後的另兩節的引言中,我想探討這些不同的框架是如何影響了當代的繪畫實踐,並闡明本書各節所關注的三個區域:畫室、畫室外的世界,以及畫家的身體及心靈。
基於常理,我們應當從建築物內部這樣的環境開始談起,因為可能是為了這樣的環境而出現的諸多圖像,深深影響了我們所謂的藝術作品。寺廟和教堂被設定為封閉而正式的場所,在裡面的信徒會面對平面或立體的神聖圖像,而這種與作品面對面的方式,也延伸到了世俗空間,如宮殿和現今的博物館及畫廊。想想一尊或一幅佛陀、濕婆,抑或聖母瑪利亞的雕像或圖畫,是如何主宰了那些進入禮拜堂祈禱的人的心理;或者一組大理石簷壁飾帶或一幅濕壁畫會如何讓我們不自覺的凝視與沉思。想想全身肖像畫;提香(Titian)或卡拉瓦喬(Caravaggio)為私人客戶製作的歷史題材畫作;或者從馬內(Manet)的時代到菲利浦.葛斯頓(Philip Guston)的時代,那些針對造訪畫廊的公眾所製作的驚人作品等等,是如何激起我們的警覺與認真。所有這些案例都有個問題,那就是這些圖像的製作目的,都是為了能夠讓人站著觀看。這些作品假定你,也就是觀者,站直身軀,雙眼往前看,並且有時間駐足及凝視。這些作品為你提供了與這種靜止狀態相輔相成的體驗:透過眼前平坦而垂直的表面,讓你感受到有著強烈生命力且具備運動能力的存有。與此同時,也讓你感受到同樣在三度空間中束縛了你的地心引力。
許多繪畫,都是根據這個強而有力的公式完成的。觀察性的人體素描,也就是我們最熟悉的繪畫練習,從歷史上來看,最初是一種準備工作,讓畫家得以畫出那種懸掛在牆上、會與我們四目相對的肖像畫;而無論教導者如何教授這種練習,小尺幅的草圖,往往都會反映出我們想要表現在大尺幅畫作中的某些設想。在結構上來說,活生生的人體清楚明確。他們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力量感。他們都具有一定程度的重量感。從解剖學的角度來看,他們都具備了一些常見的不同。為了在平面上畫出栩栩如生的身體,你可能會試著突顯那些不同的要素──要做到這一點,不僅需要細心而專注的觀察力,也需要積極而同理的想像力。如果是在描繪頭部──生命力更微縮的展現之處──難度可能會倍增。
世界上有一定數量的石灰岩甬道裡有炭筆畫作,但有些甬道內的炭筆畫作就是鶴立雞群;世界上有許許多多個牆上有噴漆畫作的混凝土通道,但有些通道裡的噴漆畫作就是不同凡響。一如前述兩個例子,並非所有的人物習作畫,都能呈現出相同的效果。有些習作畫顯示出畫家付出了更多的關注與同理,也許我們可以把這件事情歸因於性格特色,只有某些人才有辦法進入這種快樂的癡迷狀態。此外,在描繪那些活靈活現、栩栩如生的人物形體,以及更要求真實的面部神情時,每一個曾經觀察實物作畫的人都會承認,此事存在著失敗的可能性。曾幾何時,有這麼一些社會,對懸掛於牆上公開展示用的人物肖像畫有所需求,而有一群藝術家專門在生產這類畫作;而也是同樣的這群人,找出了控制前述變數的方法。十五世紀初,在畫家的工作室裡,就出現了人物畫的技藝傳統;到了十六世紀末,這種傳統開始在藝術學院裡形成制度,並設立了描繪裸體模特兒的課程。畫家們可以得到關於正確及錯誤作法的指導,有時還能夠獲得理論依據上的支持。雖然這些藝術學院的做法已經離現在的我們相當遙遠,但它們積累的智慧卻仍能讓我們受益匪淺,甚至可說具有啟發性,值得我們效法。一些當代「工作室」形式的藝術學校內的導師會更進一步,試圖恢復學術上對於「正確」的定義。
為本書撰稿的作者們都知道,畫畫可能會出錯──事實上,無論我們學習得再多,還是有可能一再犯錯。他們通過不同的途徑,都想要畫出「正確的」精彩畫作。然而,他們並沒有提供任何所謂「正確的」做法。我們並不想要解決你所有的問題。我們其實更想鼓勵你去享受這些問題。
之所以會採取這種立場的原因,可以追溯至一段漫長的歷史。舉例來說,我們可以看一下十七世紀中期,普桑在羅馬繪製的那些油畫。這位法國人,向這座城市的偉大壁畫──拉斐爾(Raphael)等人的作品──致敬,但他的做法是有意識地創作一批自成一體的作品,通常是為了能夠出口到他的祖國。正是透過這些作品,「架上繪畫」作為一種典範性藝術形式的想法才得以實現。普桑的作品主張:沒錯,人物具有重要意義,但同樣地,那些人物所處的整個矩形實體也有其意義。站在牆壁前方凝視時,我們或許只能隱約意識到大型畫作中的人物所處的邊界;但架上繪畫的邊界卻十分明確。這種特定的藝術形式,旨在利用其邊界,來協調矩形平面內的所有元素,讓所有人物及各人物之間的負空間(negative space)共同構成公式裡的加號及減號,以得到一個完美的解方。
像普桑的繪畫作品,在創作時就考量到了這種整體的和諧,於是從僅研究人物本身的這種視點,轉移到了關注畫面的整體,無論光影的形式或線條與紙張之間的相互影響,都會納入思索。這就是我們所理解的「構圖」──這是「自成一體」的另一種表現形式,跟大尺幅人物畫像的發人深思有所不同。這是兩種彼此之間可能會互相衝突的繪畫思維。構圖所追求的整體一致性,跟人像畫似乎想要傳達給觀者的感受可能有所不同。這個嚴重衝突的最著名案例,我們可以在塞尚(Cézanne)──一位介於普桑與二十世紀之間的畫家──的作品中看到。在處理畫紙與被觀察的身體之間的緊張關係時,塞尚的手法通常是打破「輪廓」──後者的輪廓──讓不著痕跡的畫紙代表未經修飾的現實。但這與其說是一種可以遵循的標準做法,還不如說是針對一個謎題所提出的致敬行為。藏身在這類行為背後的深沉思考所涉及的難題──一幅畫要怎麼樣才稱得上恰到好處?──只要我們相信繪畫的實踐行為值得栽培,那麼這個問題就將永遠與我們同在。
這個問題之所以揮之不去,是因為「藝術作品」的概念一直存在,而這個概念最為人熟知也最容易理解的形式,可能就被固定在一棟建築物內的某面牆上。之所以要培養繪畫能力,就是要考量到繪畫作品可能處於這種狀態下。一張有機會被掛在牆上展覽的畫作,可以說是一張「圓滿獨立」的畫作:無論是有上色或留白,它畫面上的每一個部分都充滿了意義。然而,通往這種恰到好處的形式的路徑,可能並不包括刻意地將意義(或各種痕跡)附加在畫紙上。每一個經常畫畫的人都可以證明,他們最滿意的作品──也就是那些最精彩而「理想」或「生動」的畫作──很可能是那些最不假思索、無所顧忌、彷彿幾乎可說是毫無意識、漫無目的地畫出來的那些速寫。
這個自相矛盾的情況,沒有確切的解決辦法。能在多大的程度上讓自己進入自發性的創作狀態,是本書的作者們都將反覆探討的問題。然而,在個人的層面上,這個問題或許與繪畫時所處的政治環境息息相關。人們畫畫是件好事。任何人都可以嘗試用這種方法來揮灑他們的精力,而每個人都應該被鼓勵這麼做:無論是否屬於人權範疇,繪畫都是一種快樂的活動,其負面影響要比大多數其他活動要少得多。但是,儘管我們或許想從更多元的角度,去看待校園藝術團體、便條本上的隨興小畫,以及施工圍籬上的塗鴉,將之視為民主的種子、一種自我的表達,但因之而產生的作品卻鮮少聚集在一起,以促成一個有意識的觀眾群體的誕生。而相比之下,那些置放在公共空間裡的、具有號召力的作品,其所追求的正是呼喚出真實存在的觀眾群體。想一想義大利教堂裡壯觀的馬賽克鑲嵌畫作、十字架跟壁畫;想一想《荷拉斯兄弟之誓》(the Oath of the Horatii)和《梅杜薩之筏》(the Raft of the Medusa),達維(David)跟傑利柯(Géricault)以這兩幅偉大的畫作挑戰了巴黎;想一想畢卡索的《格爾尼卡》(Guernica)。如果沒有這種富有挑戰力和想像力的大型作品──無論是視覺藝術還是其它藝術形式──那麼所謂的「公眾」是否存在,都有待商榷。但是,想要完成這類雄心勃勃的大型作品,需要集中的訓練、充足的準備,以及技能的專業化。要實現這樣的野心,就必須要求在特定的環境中,某些畫作要優於其他畫作。也需要等級制度。一所位於當今世界首屈一指的藝術中心的學校,必須面對由此而產生的問題:如何識別出優秀的作品。與此同時,在跟每個創作者交流時,如果這所繪畫學院沒有珍惜跟培養他們的才華──在所有合理的情況下──並「做出成績」,那麼它就失去了其存在意義。在多元主義跟等級制度之間,繪畫學院站在一個微妙的立場。
接下來的文章,都將從不同的角度去探討,畫家可能會如何更有意識地進行繪畫實踐;他們可能會如何集中精神去好好思考繪畫這件事,尤其特別是在畫室這個特定的空間裡。伊絲貝爾.麥耶斯科夫(Ishbel Myerscough)代表了無數的藝術家及潛在藝術家,她講述了自己從源於童年的、無拘無束的繪畫熱情,到發現想像力的必要性的過程。她繼續勾勒出這個自我真理的面貌,並透過對個體進行深入剖析的素描與油畫來表達。油畫家暨版畫家湯瑪斯.紐伯特(Thomas Newbolt)──他的人體畫作都是在畫室裡沒有其他人的情況下完成的──審視了像我們這樣的當代繪畫學校從古老的學院那邊傳承下來的教育性活動:「寫生教室」,也就是一群畫家仔細研究一個通常一動不動、赤身裸體的活人。他考慮到了這種刻意而「人為」的場景背後的限制,並雄辯滔滔地訴說了自己的發現,以及這種活動可能會為畫家帶來的好處。艾琳.霍根(Eileen Hogan)是一位作品主要以風景畫為基礎的藝術家,她探索了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從側面的角度去著手人像描繪:透過聆聽他們與第三方的交談,來強化你對個體的理解。她也回過頭來審視了自己過去對於學術研究的方法及經驗。約翰.萊索爾(John Lessore)是英國的資深具象派畫家,他帶著深刻的評判色彩,對自己一生的繪畫教學進行了反思;並深度思考了技藝(身為工匠的職責)以及冒險(身為藝術家的職責)之間的關係。安.道克(Ann Dowker)遠離了自己的人物藝術作品及這些人物所居住的地方,帶領繪畫學院的學生在倫敦的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作畫。在本書裡,她描述了對這種歐洲傳統的研究,是如何為畫家們提供了一本「視覺辭典」,並提供了自己生動的實例與見解。緊接著,是由伊恩.詹金斯(Ian Jenkins)對取材自雕塑的繪畫,進行了探討,焦點放在帕德嫩神廟內的古典雕塑──作為大英博物館古希臘館的研究員,他對這些雕塑情有獨鍾。在本節最後一篇文章中,藝術家凝視的目光倒轉了過來。經常擔任模特兒的劇作家愛絲莉.林恩(Isley Lynn),沒有將重點放在作畫上,而是以清新脫俗而幽默風趣的方式,說明了被畫的感受。(p.34)
【實踐練習】親密程度會產生的影響 伊絲貝爾.麥耶斯科夫
參與者:一組作畫者(建議)跟一名模特兒
多數情況下,在畫畫的時候,我們會把自己的世界觀,強加在模特兒身上。我們並不認識大部分的人體模特兒,對我們來說,他們是可以仔細觀察並分析的陌生人。這個練習是讓全班同學對模特兒提出問題,目的是畫出更能突顯他們個人特質的畫作。
如果是以小組的方式進行人體寫生,那麼請同學們圍成一個圓圈,讓模特兒待在圓圈中間。模特兒應該要擺六個姿勢,每個姿勢五分鐘,並且每個姿勢都要轉身,好讓每個人都可以從各個角度去觀察、作畫。
接下來,請模特兒擺一個時間較長的姿勢,可以擺兩次相同的姿勢,每次四十五分鐘左右。這時候,畫家們應該要提出一些問題來問模特兒,好能夠更認識他們。不要問太私人的問題。可以問說他們在哪裡長大?有沒有兄弟姊妹?有沒有留過短頭髮?是怎麼選擇今天要穿的衣服?等等。
在這次的練習中,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為了看看畫作是否因為得知了這個資訊,而產生了改變。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不知道這個資訊,我們通常可能會怎麼作畫,並以此進行對比。(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