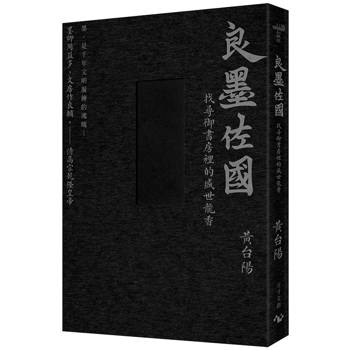第九章 龍香墨傳千古
乾隆帝愛墨,甚至及於墨的存放。前文提到,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內有他在這方面的指示,如「著配有抽屜箱内」、「在花梨木箱内配屜盛裝」、「洋漆長方匣一件内,下屜配得合牌屜兩屜」、「一屜盛夔鳳紅墨一塊」、「配得杉木隔斷屜兩屜」等,十足顯示乾隆追求完美的個性。而這個性,想來該不會放過裝箱後的「標籤」,否則日後如何找出某些墨?
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年)二月初九日的資料可證:「薩姆哈將十色墨計二百六十錠,配得糊錦綾裡紫檀木盤十件,裝在洋漆箱内,上刻『天章寶露』簽。」果然顧及此!在裝墨的洋漆箱上刻「天章寶露」簽,不僅日後易認,也賦予其內各自具名的墨有了整體名稱,如同集錦套墨。只是「天章寶露」之名從何而來,是信口而發、還是有所本?尚無從知曉。然而另套墨所賦予的「龍香」名,卻早已聲震墨壇!這套墨原有八匣,四匣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流落在外的其中一匣(內有十錠墨,各有非「龍香」之名),於二〇二一年北京保利秋拍成交,竟破千萬元人民幣,令人咋舌!這是「龍香」兩字的魅力嗎?
墨與龍香兩字扯上關係,始自唐玄宗李隆基,是墨史一大盛事。「龍香」這兩字可是大有來頭。前文曾提及玄宗登基前曾在潞州戲製墨,此墨日後被撰造祥瑞,說墨上出現蒼蠅大小的小道士遊走,看到他就口稱萬歲。以此沒人見過的神蹟,營造其為真龍天子的輿論,助他奪權。無怪乎事成後玄宗煞有介事定墨名為「龍香劑」。真龍天子手製的香墨,捨此名其誰!
皇帝都出面幫墨打廣告了,想必風起雲湧、帶起一陣浪潮。製墨界──尤其潞州墨商──該趁機推出各式龍香墨,好好撈一筆,騷人墨客當也不落其後,詩詞歌賦齊詠龍香了吧?然而奇怪的是,在現有資料裡,找不到唐代人「共襄盛舉」的紀錄。譬如詩仙李白喜歡好墨,有〈酬張司馬贈墨〉一詩,謝人送他潞州香墨。且他任翰林供俸時曾奉召入宮,寫下〈清平調〉讚頌楊貴妃之美,若當時用的是龍香墨,日後應有可能將該墨寫入詩中吧!
又如百多年後晚唐著名的詩人段成式與溫庭筠,有贈墨的往返書信十五篇存世。他們談到易墨、潞墨,甚至潞墨的知名品牌「松心」,但龍香之名依然無影無蹤。難道龍香兩字乃皇家專用,小老百姓不敢觸及?
█ 9-1.春葱細撚龍香撥
實情並非如此。
當時還有另一個使用龍香的詞──「龍香撥」,絕對為人熟知,卻無人避忌。它以南洋的龍腦香木製成,是用來撥動琵琶、月琴等絃樂器的工具。在唐玄宗死後不久,詩人鄭嵎來到驪山下華清宮北面的宮門──津陽門附近的旅店歇腳,與侍奉過玄宗的老店主話當年,不勝唏噓之餘,隨即寫下以玄宗與楊貴妃為主角的愛情史詩〈津陽門〉。詩中有句:「玉奴琵琶龍香撥,倚歌促酒聲嬌悲。」講的就是楊貴妃(小字玉奴)以「龍香撥」來撥彈琵琶伴歌。
或許你會好奇龍香撥長什麼樣子?開鑿於西元五〇〇年前後、在今河南鞏義的北魏石窟第一窟內,雕刻了樂伎撥彈琵琶,便清楚可見手中的撥子。另日本東大寺正倉院所藏唐代物品,除了琵琶,還有「紅牙撥鏤撥」,是用唐代特有的「撥鏤」工藝染紅象牙、鏤出祥禽瑞獸的撥子,可供參考。至於貴妃所用的龍香撥上有無雕飾?史無明文。但顧名思義,龍腦香香氣芬馥,貴妃持以撥動琵琶,隨著她的纖纖玉指芳香四溢,多情的玄宗怎能不沉迷陶醉?
龍香撥早於龍香墨出現,不知玄宗定「龍香劑」之名時,是否據之得到靈感?但即使如此,龍香墨不敵龍香撥,貴妃的手持勝過玄宗的手製,原因或在安史之亂後,玄宗的聲望驟跌,人人避而遠之,龍香墨隨之乏人聞問。但由唐入宋後,有了轉機!既然都改朝換代了,加上宋代重文輕武,用墨量大增,製墨比唐代發達,龍香墨理應有機會重現人間,與龍香撥再度輝映吧!
█ 9-2.君家猶自搗龍香
為何宋代製墨比唐代發達?
元代愛墨人陸友集自古以來墨的資料寫了《墨史》,列出製墨家一百九十八人。北宋之前的千多年裡,僅二十二人,少得可憐。而北宋不到一百七十年,卻有八十人;南宋一百五十年更是再添九十人。差距如此大,主因在兩宋年間文人愛墨,留下許多紀錄。如北宋狀元蘇易簡《文房四譜》、李孝美《墨譜》、晁貫之《墨經》,以及蔡襄、歐陽脩、蘇東坡、秦觀、陳師道、邵博、蔡絛、何薳、莊綽等人都有不少筆記傳世。
其中不乏言及墨名。如蘇東坡筆記內就提到老長官陳公弼製作了名為「黑龍髓」的墨,馮京委請潘谷製的墨上有「樞庭東閣」名。何薳《春渚紀聞》內,也記載了墨師陳相製「洙泗之珍」墨、九華朱覲做「軟劑出光」墨。所以當時若有名師製出龍香墨,被記錄下來的機率該不會低,為何遍尋不著?
相較之下,龍香撥的恩寵始終不衰。蘇東坡愛墨卻不言龍香,但他的〈宋叔達家聽琵琶〉詩內有:「數絃已品龍香撥,半面猶遮鳳尾槽。」而與蘇東坡合稱「蘇辛」的豪放詞人辛棄疾,其〈賀新郎.賦琵琶〉首句就寫:「鳳尾龍香撥。自開元、〈霓裳曲〉罷,幾番風月。」以玄宗之尊手製的龍香墨卻無人聞問,情何以堪!
宋代到底有無以龍香為名的墨?依後人記載是有的,但可信度低。元末明初大儒陶宗儀在躬耕之餘廣搜資料,所輯《南村輟耕錄》洋洋灑灑數十萬言,云宋神宗趙頊熙寧年間,墨師張遇將龍腦麝香和金箔摻入油煙內,製出「龍香劑」墨上貢。寫得斬釘截鐵,以他的名聲而言此事應為真,但細加推敲卻站不住腳。因為眾多北宋資料,或明或暗都指出張遇是唐末宋初人,與製墨宗師李廷珪約同個時代,不可能活到熙寧時。再者,油煙墨的技術,要到北宋末才小有可觀,南宋才成熟。熙寧年間怎可能以油煙製出好墨?陶宗儀所記,該是以訛傳訛。
到了清代嘉慶、道光年間,湖南新化人鄧顯鶴輯錄湖湘先賢文字所成的《沅湘耆舊集》內,刊出宋代十歲童子鄧熛的〈墨〉詩:「一寸龍香一寸金,仙家傳藥不傳心。」詩內以龍香代表墨,明確將兩者畫上等號。只是鄧熛之名不見他書,是否真宋代人,待考。由於湖湘文風在宋室南渡後始大興,猜想鄧神童至早應為南宋人。而南宋末、元初徽州進士許月卿的〈贈墨士程雲翁〉詩:「滿地干戈正擾攘,君家猶自搗龍香。」也將龍香與墨同等對待,都點出宋末元初之際,民間應已出現以龍香為名的墨。
█ 9-3.龍香上貢奎章裡
元代不重文,但龍香墨的命運卻否極泰來,堂皇進貢給皇帝。忽必烈的玄孫元文宗圖帖睦爾書法不錯,近臣阿榮(蒙古人,時任宰相級的中書參知政事)、康里巎巎(色目人,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經筵官)投其所好,進貢江西豫章朱萬初製的墨。同朝為官的虞集(江西人,南宋名臣虞允文之後,任奎章閣侍書學士)有〈贈朱萬初〉詩:「珥貂鳴珮入明光,新墨初成進御床。」記述其事。阿榮和康里巎巎都不是漢人,怎知朱萬初的墨好?應是虞集在後幫老鄉的忙。朱萬初因此獲官,虞集退休後兩人仍有往來。
朱萬初這墨是否名為「龍香」,虞集沒講,但晚些年的另位江西人吳當(官至江西省參知政事),在〈贈墨工侯務本次虞學士韻〉中引述這段往事:「御床玄璧進龍香,奎閣當年詫豫章。」而由元入明的袁華(明初任蘇州府學訓導)作〈贈劉宗永〉詩:「近代西江朱萬初,龍香上貢奎章裡。」也有所呼應,留下想像空間,好像朱萬初的墨確實名為「龍香」。只是參考其他詩作,如同時代鄭元祐的〈龍香行.贈吳國良〉、乃賢(色目人)的〈江東魏元德所製齊峰墨於上都慈仁殿賜文錦馬湩以寵之既南歸作詩以贈云〉,詩內均有「龍香」。看來當時風行以龍香代稱墨,故終究無法肯定朱萬初的墨名。
不過元代的文化瑰寶──元曲,卻無意間唱出以龍香為名的墨。元雜劇《薩真人夜斷碧桃花》,演的是狀元張道南與徐碧桃的人鬼戀故事,第三折裡薩真人審問徐碧桃鬼魂,問她與張道南相逢時,張道南給了她什麼。只聽徐碧桃唱:「他可便拂金星硯將龍香墨研,染紫霜毫把花箋紙展。」(曲牌〈倘秀才〉)明白唱出「龍香墨」三字,該是以龍香為名的墨。這墨無論是張道南狀元及第時皇帝所賜,或從市面所購,都指出龍香墨在元代確實已重現江湖。
至於龍香撥,到元代聲勢依然不墜。金庸武俠小說《神鵰俠侶》中為情所困的赤煉仙子李莫愁,常掛在嘴上的「問世間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其作者元好問的另作〈滿江紅.再過水南〉就有「金縷唱,龍香撥。雲液暖,瓊杯滑」,顯示出龍香撥之寵,即使在好武的元代也強強滾。
█ 9-4.新樣龍香墨製佳
明太祖朱元璋驅走蒙元後講求文治,對於製墨業該是一大鼓舞。歷史上有人進貢好墨,甚至龍香墨給明太祖嗎?洪武十八年(一三八五年)榜眼練子寧有詩寫道:「侯家妙墨異人方,蚤歲曾供白玉堂。樸樕霜花收兔葉,淋漓天藻動龍香。」由於「白玉堂」在古文中可指皇宮,而「天藻」係天子的文章,故侯伯俊應曾進貢墨,而且皇帝還用過。考證練子寧在高中榜眼後任翰林修撰,建文帝朱允炆時任吏部侍郎,明成祖朱棣殺進南京時不屈而死。基於建文帝在位僅四年,對照詩內「蚤(早)歲」兩字,故可知侯伯俊墨是進貢給太祖。
明太祖、明成祖父子對墨的興趣有多大,還沒見到任何資料提及此事。但明太祖延續元代的匠戶制度,規定各類工匠必須輪流至官方作坊上工,其中當然包含墨匠。嘉靖年編修的《宜興縣志》便曾記載永樂年間的宜興墨師李公實,常奉召到南京為朝廷製墨。正是這類製墨家,為大明王朝製出龍香御墨,首將唐玄宗創製的龍香與御墨結合,成為後人著迷的「新品牌」。
故宮博物院藏有多錠龍香御墨。最早係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元年(一四二六年)所製,其後成化、嘉靖、隆慶、萬曆年亦不乏龍香御墨。估計宣德年後的各朝都製作過龍香御墨,只是大多品質不夠好,年代久遠碎裂,在乾隆時代被毀造新墨了。但值得探討的是,宣德之前有無龍香御墨?
明宣宗雅好文藝,富浪漫氣息。明末文壇領袖錢謙益所編的《列朝詩集小傳》中稱其「遊戲翰墨,點染寫生,遂與宣和(指宋徽宗)爭勝」。不知是否因宋徽宗製作了蘇合油煙墨,使得宣宗也要製墨來與之爭勝。故宮所藏其登基後所製御墨,五百多年來依然完整,可知品質夠好。他曾賜龍香墨給大臣,沈粲(大理寺少卿)與夏原吉(戶部尚書)都留下紀錄。而沈粲詩的首句「新樣龍香墨製佳」,更提供寶貴線索。既然「新樣」,就表示另有舊樣。沈粲在宣德元年獲賜新樣,則舊樣只能製於前朝。鑑於宣宗之父仁宗朱高熾在位僅十個月就謝世,不太可能改樣製墨。舊樣的龍香御墨便極可能出自好大喜功、令編《永樂大典》的成祖,甚至宜興墨師李公實之手。
現存的龍香御墨,圖面設計大同小異。除了寫「龍香御墨」、「XX年製」或「大明XX年製」,就只有龍(或螭)戲珠雕飾、雲紋與火焰紋。形式則大抵為牛舌形、圓形和明穆宗朱載坖隆慶年特有的銀錠式。比起許多民間墨上圖案的多彩多姿,式樣的五花八門,相去甚遠,辜負了大好墨名。但考慮製墨工匠多為奉召前往,即使有工資也很微薄,就不便苛責了!
唐玄宗的悲劇,在明代皇帝眼裡不是顧忌。龍香劑的神蹟,恐怕才是他們所喜。終大明王朝,龍香御墨一枝獨秀,但奇怪的是民間的反應卻非常冷淡。萬曆年製墨極為發達,然而在傳世三大墨書:程君房《程氏墨苑》、方于魯《方氏墨譜》、方瑞生《墨海》內,都不見有龍香墨樣。另,明末抗清而死的麻三衡的《墨志.稽式第六》內,刊出自古到明的二百七十五個墨名,除了已知的「龍香劑」和「龍香御墨」,明代只列徐鳳「碧天龍香」和吳仲暉的「龍香」兩款墨。徐、吳兩人名不見經傳,全然不能與上述三位大師相比。讓人不禁疑惑是什麼原因使得製墨名家都不用龍香之名?難道是不想跟御墨撞名?
█ 9-5.龍香墨灑壁上題
明代對龍香墨的態度是皇家熱、民間冷,到了清代卻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皇家冷,民間熱。
滿清入主中原,承襲了明代由大內製作御墨。康熙的御書處內就設墨作,編制十五人,比明嘉靖年七十七人精簡許多。《內務府墨作則例》極可能制定於康熙年(或更早的明代),後於乾隆年增刪。然而改朝換代後新製的御墨,是否仍冠以龍香?還是另起他名?
康熙、乾隆祖孫兩人文學素養高,對龍香一詞並不陌生。康熙南巡到揚州,參訪歐陽脩所築平山堂時,留有詩句:「文章太守心偏憶,墨灑龍香壁上題。」乾隆欣賞沈周的畫,也寫下:「調粉龍香劑,斯花自寫生。」然而他們當朝所製的御墨,一律不見龍香,只單寫「御墨」。以後各朝所製的御墨愈來愈少,甚至不內製而改用徽墨。所以清代可說是龍香御墨的終結,斷了它在明代的風光日子。
但前面不是說過乾隆帝的龍香御墨?
其實這龍香御墨是後人所按。乾隆只賦予那八匣墨一個標籤:「龍香」,匣裡的個別御墨卻沒有一錠是以之為名。所以乾隆此標籤就像是南宋以來所為,把龍香用作墨的代名詞。乾隆帝本人,從來沒提過「龍香御墨」四字。
且不僅他沒提,連手下人在他面前也不敢提。看來清代皇家對龍香御墨的看法還真奇怪。是不屑?還是有顧忌?是無心於此?還是有意避開?
答案可能都有──不屑與明代諸多平庸荒誕的皇帝為伍;顧忌唐玄宗的悲劇下場,不想觸霉頭;無心蕭規曹隨,有意開創新猷……。於是清代拋棄舊思維,迎向新未來,終於超越明代龍香御墨的呆板窠臼,造出極多優越的御墨。推敲從康熙到乾隆的心態,或許是:即使只是製墨,你漢人擅長,我滿人也能,還做得比前朝好。受我統治,有什麼好抱怨的?別再搞什麼「朱三太子」、「反清復明」的無聊把戲了!
雖然御墨上不見龍香二字,民間製墨卻捨不得此上好「品名」。最早寫上龍香的,恐怕是順治年舉人查去愚。當代研究者王儷閻與蘇強所寫的《明清徽墨研究》內,說查去愚的墨上有隸書「龍香貳昧」。此外也考證汪近聖鑑古齋有「內殿龍香」,汪節菴函璞齋有「古龍香劑」,程怡甫尺木堂有「龍香劑」。再加上北京藝術博物館藏胡開文「龍香劑」,手邊曹素功八世孫雲崖造的「八寶龍香劑」,可說各大墨肆都到齊了。至於文人製墨也沒閒著。尹潤生《墨苑鑒藏錄》有碣洋「龍香劑」,周紹良《清墨談叢》與《蓄墨小言》內分別有查炳輝「古龍香劑」、徐立綱「龍香劑」,以及手邊查瑩(號映山)、顏爾楫(號用川)也都留下見證。唐玄宗地下有知,看到民間如此捧場,想必熱淚盈眶。
至於龍香撥伴隨著琵琶,多為女性操持,顯然不受朝代更替的影響。明、清兩代依然多見於詩文之內,它搭上音樂的列車,超越時空。
乾隆帝愛墨,甚至及於墨的存放。前文提到,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內有他在這方面的指示,如「著配有抽屜箱内」、「在花梨木箱内配屜盛裝」、「洋漆長方匣一件内,下屜配得合牌屜兩屜」、「一屜盛夔鳳紅墨一塊」、「配得杉木隔斷屜兩屜」等,十足顯示乾隆追求完美的個性。而這個性,想來該不會放過裝箱後的「標籤」,否則日後如何找出某些墨?
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年)二月初九日的資料可證:「薩姆哈將十色墨計二百六十錠,配得糊錦綾裡紫檀木盤十件,裝在洋漆箱内,上刻『天章寶露』簽。」果然顧及此!在裝墨的洋漆箱上刻「天章寶露」簽,不僅日後易認,也賦予其內各自具名的墨有了整體名稱,如同集錦套墨。只是「天章寶露」之名從何而來,是信口而發、還是有所本?尚無從知曉。然而另套墨所賦予的「龍香」名,卻早已聲震墨壇!這套墨原有八匣,四匣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流落在外的其中一匣(內有十錠墨,各有非「龍香」之名),於二〇二一年北京保利秋拍成交,竟破千萬元人民幣,令人咋舌!這是「龍香」兩字的魅力嗎?
墨與龍香兩字扯上關係,始自唐玄宗李隆基,是墨史一大盛事。「龍香」這兩字可是大有來頭。前文曾提及玄宗登基前曾在潞州戲製墨,此墨日後被撰造祥瑞,說墨上出現蒼蠅大小的小道士遊走,看到他就口稱萬歲。以此沒人見過的神蹟,營造其為真龍天子的輿論,助他奪權。無怪乎事成後玄宗煞有介事定墨名為「龍香劑」。真龍天子手製的香墨,捨此名其誰!
皇帝都出面幫墨打廣告了,想必風起雲湧、帶起一陣浪潮。製墨界──尤其潞州墨商──該趁機推出各式龍香墨,好好撈一筆,騷人墨客當也不落其後,詩詞歌賦齊詠龍香了吧?然而奇怪的是,在現有資料裡,找不到唐代人「共襄盛舉」的紀錄。譬如詩仙李白喜歡好墨,有〈酬張司馬贈墨〉一詩,謝人送他潞州香墨。且他任翰林供俸時曾奉召入宮,寫下〈清平調〉讚頌楊貴妃之美,若當時用的是龍香墨,日後應有可能將該墨寫入詩中吧!
又如百多年後晚唐著名的詩人段成式與溫庭筠,有贈墨的往返書信十五篇存世。他們談到易墨、潞墨,甚至潞墨的知名品牌「松心」,但龍香之名依然無影無蹤。難道龍香兩字乃皇家專用,小老百姓不敢觸及?
█ 9-1.春葱細撚龍香撥
實情並非如此。
當時還有另一個使用龍香的詞──「龍香撥」,絕對為人熟知,卻無人避忌。它以南洋的龍腦香木製成,是用來撥動琵琶、月琴等絃樂器的工具。在唐玄宗死後不久,詩人鄭嵎來到驪山下華清宮北面的宮門──津陽門附近的旅店歇腳,與侍奉過玄宗的老店主話當年,不勝唏噓之餘,隨即寫下以玄宗與楊貴妃為主角的愛情史詩〈津陽門〉。詩中有句:「玉奴琵琶龍香撥,倚歌促酒聲嬌悲。」講的就是楊貴妃(小字玉奴)以「龍香撥」來撥彈琵琶伴歌。
或許你會好奇龍香撥長什麼樣子?開鑿於西元五〇〇年前後、在今河南鞏義的北魏石窟第一窟內,雕刻了樂伎撥彈琵琶,便清楚可見手中的撥子。另日本東大寺正倉院所藏唐代物品,除了琵琶,還有「紅牙撥鏤撥」,是用唐代特有的「撥鏤」工藝染紅象牙、鏤出祥禽瑞獸的撥子,可供參考。至於貴妃所用的龍香撥上有無雕飾?史無明文。但顧名思義,龍腦香香氣芬馥,貴妃持以撥動琵琶,隨著她的纖纖玉指芳香四溢,多情的玄宗怎能不沉迷陶醉?
龍香撥早於龍香墨出現,不知玄宗定「龍香劑」之名時,是否據之得到靈感?但即使如此,龍香墨不敵龍香撥,貴妃的手持勝過玄宗的手製,原因或在安史之亂後,玄宗的聲望驟跌,人人避而遠之,龍香墨隨之乏人聞問。但由唐入宋後,有了轉機!既然都改朝換代了,加上宋代重文輕武,用墨量大增,製墨比唐代發達,龍香墨理應有機會重現人間,與龍香撥再度輝映吧!
█ 9-2.君家猶自搗龍香
為何宋代製墨比唐代發達?
元代愛墨人陸友集自古以來墨的資料寫了《墨史》,列出製墨家一百九十八人。北宋之前的千多年裡,僅二十二人,少得可憐。而北宋不到一百七十年,卻有八十人;南宋一百五十年更是再添九十人。差距如此大,主因在兩宋年間文人愛墨,留下許多紀錄。如北宋狀元蘇易簡《文房四譜》、李孝美《墨譜》、晁貫之《墨經》,以及蔡襄、歐陽脩、蘇東坡、秦觀、陳師道、邵博、蔡絛、何薳、莊綽等人都有不少筆記傳世。
其中不乏言及墨名。如蘇東坡筆記內就提到老長官陳公弼製作了名為「黑龍髓」的墨,馮京委請潘谷製的墨上有「樞庭東閣」名。何薳《春渚紀聞》內,也記載了墨師陳相製「洙泗之珍」墨、九華朱覲做「軟劑出光」墨。所以當時若有名師製出龍香墨,被記錄下來的機率該不會低,為何遍尋不著?
相較之下,龍香撥的恩寵始終不衰。蘇東坡愛墨卻不言龍香,但他的〈宋叔達家聽琵琶〉詩內有:「數絃已品龍香撥,半面猶遮鳳尾槽。」而與蘇東坡合稱「蘇辛」的豪放詞人辛棄疾,其〈賀新郎.賦琵琶〉首句就寫:「鳳尾龍香撥。自開元、〈霓裳曲〉罷,幾番風月。」以玄宗之尊手製的龍香墨卻無人聞問,情何以堪!
宋代到底有無以龍香為名的墨?依後人記載是有的,但可信度低。元末明初大儒陶宗儀在躬耕之餘廣搜資料,所輯《南村輟耕錄》洋洋灑灑數十萬言,云宋神宗趙頊熙寧年間,墨師張遇將龍腦麝香和金箔摻入油煙內,製出「龍香劑」墨上貢。寫得斬釘截鐵,以他的名聲而言此事應為真,但細加推敲卻站不住腳。因為眾多北宋資料,或明或暗都指出張遇是唐末宋初人,與製墨宗師李廷珪約同個時代,不可能活到熙寧時。再者,油煙墨的技術,要到北宋末才小有可觀,南宋才成熟。熙寧年間怎可能以油煙製出好墨?陶宗儀所記,該是以訛傳訛。
到了清代嘉慶、道光年間,湖南新化人鄧顯鶴輯錄湖湘先賢文字所成的《沅湘耆舊集》內,刊出宋代十歲童子鄧熛的〈墨〉詩:「一寸龍香一寸金,仙家傳藥不傳心。」詩內以龍香代表墨,明確將兩者畫上等號。只是鄧熛之名不見他書,是否真宋代人,待考。由於湖湘文風在宋室南渡後始大興,猜想鄧神童至早應為南宋人。而南宋末、元初徽州進士許月卿的〈贈墨士程雲翁〉詩:「滿地干戈正擾攘,君家猶自搗龍香。」也將龍香與墨同等對待,都點出宋末元初之際,民間應已出現以龍香為名的墨。
█ 9-3.龍香上貢奎章裡
元代不重文,但龍香墨的命運卻否極泰來,堂皇進貢給皇帝。忽必烈的玄孫元文宗圖帖睦爾書法不錯,近臣阿榮(蒙古人,時任宰相級的中書參知政事)、康里巎巎(色目人,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經筵官)投其所好,進貢江西豫章朱萬初製的墨。同朝為官的虞集(江西人,南宋名臣虞允文之後,任奎章閣侍書學士)有〈贈朱萬初〉詩:「珥貂鳴珮入明光,新墨初成進御床。」記述其事。阿榮和康里巎巎都不是漢人,怎知朱萬初的墨好?應是虞集在後幫老鄉的忙。朱萬初因此獲官,虞集退休後兩人仍有往來。
朱萬初這墨是否名為「龍香」,虞集沒講,但晚些年的另位江西人吳當(官至江西省參知政事),在〈贈墨工侯務本次虞學士韻〉中引述這段往事:「御床玄璧進龍香,奎閣當年詫豫章。」而由元入明的袁華(明初任蘇州府學訓導)作〈贈劉宗永〉詩:「近代西江朱萬初,龍香上貢奎章裡。」也有所呼應,留下想像空間,好像朱萬初的墨確實名為「龍香」。只是參考其他詩作,如同時代鄭元祐的〈龍香行.贈吳國良〉、乃賢(色目人)的〈江東魏元德所製齊峰墨於上都慈仁殿賜文錦馬湩以寵之既南歸作詩以贈云〉,詩內均有「龍香」。看來當時風行以龍香代稱墨,故終究無法肯定朱萬初的墨名。
不過元代的文化瑰寶──元曲,卻無意間唱出以龍香為名的墨。元雜劇《薩真人夜斷碧桃花》,演的是狀元張道南與徐碧桃的人鬼戀故事,第三折裡薩真人審問徐碧桃鬼魂,問她與張道南相逢時,張道南給了她什麼。只聽徐碧桃唱:「他可便拂金星硯將龍香墨研,染紫霜毫把花箋紙展。」(曲牌〈倘秀才〉)明白唱出「龍香墨」三字,該是以龍香為名的墨。這墨無論是張道南狀元及第時皇帝所賜,或從市面所購,都指出龍香墨在元代確實已重現江湖。
至於龍香撥,到元代聲勢依然不墜。金庸武俠小說《神鵰俠侶》中為情所困的赤煉仙子李莫愁,常掛在嘴上的「問世間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其作者元好問的另作〈滿江紅.再過水南〉就有「金縷唱,龍香撥。雲液暖,瓊杯滑」,顯示出龍香撥之寵,即使在好武的元代也強強滾。
█ 9-4.新樣龍香墨製佳
明太祖朱元璋驅走蒙元後講求文治,對於製墨業該是一大鼓舞。歷史上有人進貢好墨,甚至龍香墨給明太祖嗎?洪武十八年(一三八五年)榜眼練子寧有詩寫道:「侯家妙墨異人方,蚤歲曾供白玉堂。樸樕霜花收兔葉,淋漓天藻動龍香。」由於「白玉堂」在古文中可指皇宮,而「天藻」係天子的文章,故侯伯俊應曾進貢墨,而且皇帝還用過。考證練子寧在高中榜眼後任翰林修撰,建文帝朱允炆時任吏部侍郎,明成祖朱棣殺進南京時不屈而死。基於建文帝在位僅四年,對照詩內「蚤(早)歲」兩字,故可知侯伯俊墨是進貢給太祖。
明太祖、明成祖父子對墨的興趣有多大,還沒見到任何資料提及此事。但明太祖延續元代的匠戶制度,規定各類工匠必須輪流至官方作坊上工,其中當然包含墨匠。嘉靖年編修的《宜興縣志》便曾記載永樂年間的宜興墨師李公實,常奉召到南京為朝廷製墨。正是這類製墨家,為大明王朝製出龍香御墨,首將唐玄宗創製的龍香與御墨結合,成為後人著迷的「新品牌」。
故宮博物院藏有多錠龍香御墨。最早係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元年(一四二六年)所製,其後成化、嘉靖、隆慶、萬曆年亦不乏龍香御墨。估計宣德年後的各朝都製作過龍香御墨,只是大多品質不夠好,年代久遠碎裂,在乾隆時代被毀造新墨了。但值得探討的是,宣德之前有無龍香御墨?
明宣宗雅好文藝,富浪漫氣息。明末文壇領袖錢謙益所編的《列朝詩集小傳》中稱其「遊戲翰墨,點染寫生,遂與宣和(指宋徽宗)爭勝」。不知是否因宋徽宗製作了蘇合油煙墨,使得宣宗也要製墨來與之爭勝。故宮所藏其登基後所製御墨,五百多年來依然完整,可知品質夠好。他曾賜龍香墨給大臣,沈粲(大理寺少卿)與夏原吉(戶部尚書)都留下紀錄。而沈粲詩的首句「新樣龍香墨製佳」,更提供寶貴線索。既然「新樣」,就表示另有舊樣。沈粲在宣德元年獲賜新樣,則舊樣只能製於前朝。鑑於宣宗之父仁宗朱高熾在位僅十個月就謝世,不太可能改樣製墨。舊樣的龍香御墨便極可能出自好大喜功、令編《永樂大典》的成祖,甚至宜興墨師李公實之手。
現存的龍香御墨,圖面設計大同小異。除了寫「龍香御墨」、「XX年製」或「大明XX年製」,就只有龍(或螭)戲珠雕飾、雲紋與火焰紋。形式則大抵為牛舌形、圓形和明穆宗朱載坖隆慶年特有的銀錠式。比起許多民間墨上圖案的多彩多姿,式樣的五花八門,相去甚遠,辜負了大好墨名。但考慮製墨工匠多為奉召前往,即使有工資也很微薄,就不便苛責了!
唐玄宗的悲劇,在明代皇帝眼裡不是顧忌。龍香劑的神蹟,恐怕才是他們所喜。終大明王朝,龍香御墨一枝獨秀,但奇怪的是民間的反應卻非常冷淡。萬曆年製墨極為發達,然而在傳世三大墨書:程君房《程氏墨苑》、方于魯《方氏墨譜》、方瑞生《墨海》內,都不見有龍香墨樣。另,明末抗清而死的麻三衡的《墨志.稽式第六》內,刊出自古到明的二百七十五個墨名,除了已知的「龍香劑」和「龍香御墨」,明代只列徐鳳「碧天龍香」和吳仲暉的「龍香」兩款墨。徐、吳兩人名不見經傳,全然不能與上述三位大師相比。讓人不禁疑惑是什麼原因使得製墨名家都不用龍香之名?難道是不想跟御墨撞名?
█ 9-5.龍香墨灑壁上題
明代對龍香墨的態度是皇家熱、民間冷,到了清代卻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皇家冷,民間熱。
滿清入主中原,承襲了明代由大內製作御墨。康熙的御書處內就設墨作,編制十五人,比明嘉靖年七十七人精簡許多。《內務府墨作則例》極可能制定於康熙年(或更早的明代),後於乾隆年增刪。然而改朝換代後新製的御墨,是否仍冠以龍香?還是另起他名?
康熙、乾隆祖孫兩人文學素養高,對龍香一詞並不陌生。康熙南巡到揚州,參訪歐陽脩所築平山堂時,留有詩句:「文章太守心偏憶,墨灑龍香壁上題。」乾隆欣賞沈周的畫,也寫下:「調粉龍香劑,斯花自寫生。」然而他們當朝所製的御墨,一律不見龍香,只單寫「御墨」。以後各朝所製的御墨愈來愈少,甚至不內製而改用徽墨。所以清代可說是龍香御墨的終結,斷了它在明代的風光日子。
但前面不是說過乾隆帝的龍香御墨?
其實這龍香御墨是後人所按。乾隆只賦予那八匣墨一個標籤:「龍香」,匣裡的個別御墨卻沒有一錠是以之為名。所以乾隆此標籤就像是南宋以來所為,把龍香用作墨的代名詞。乾隆帝本人,從來沒提過「龍香御墨」四字。
且不僅他沒提,連手下人在他面前也不敢提。看來清代皇家對龍香御墨的看法還真奇怪。是不屑?還是有顧忌?是無心於此?還是有意避開?
答案可能都有──不屑與明代諸多平庸荒誕的皇帝為伍;顧忌唐玄宗的悲劇下場,不想觸霉頭;無心蕭規曹隨,有意開創新猷……。於是清代拋棄舊思維,迎向新未來,終於超越明代龍香御墨的呆板窠臼,造出極多優越的御墨。推敲從康熙到乾隆的心態,或許是:即使只是製墨,你漢人擅長,我滿人也能,還做得比前朝好。受我統治,有什麼好抱怨的?別再搞什麼「朱三太子」、「反清復明」的無聊把戲了!
雖然御墨上不見龍香二字,民間製墨卻捨不得此上好「品名」。最早寫上龍香的,恐怕是順治年舉人查去愚。當代研究者王儷閻與蘇強所寫的《明清徽墨研究》內,說查去愚的墨上有隸書「龍香貳昧」。此外也考證汪近聖鑑古齋有「內殿龍香」,汪節菴函璞齋有「古龍香劑」,程怡甫尺木堂有「龍香劑」。再加上北京藝術博物館藏胡開文「龍香劑」,手邊曹素功八世孫雲崖造的「八寶龍香劑」,可說各大墨肆都到齊了。至於文人製墨也沒閒著。尹潤生《墨苑鑒藏錄》有碣洋「龍香劑」,周紹良《清墨談叢》與《蓄墨小言》內分別有查炳輝「古龍香劑」、徐立綱「龍香劑」,以及手邊查瑩(號映山)、顏爾楫(號用川)也都留下見證。唐玄宗地下有知,看到民間如此捧場,想必熱淚盈眶。
至於龍香撥伴隨著琵琶,多為女性操持,顯然不受朝代更替的影響。明、清兩代依然多見於詩文之內,它搭上音樂的列車,超越時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