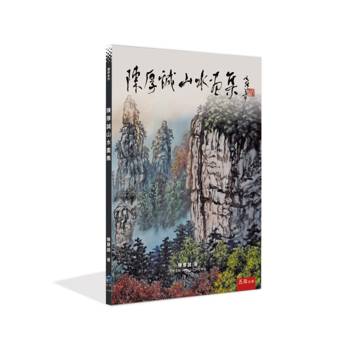創作理念(節錄)
依據《畫山水序》瞭解山水畫較早啟於宗炳的論述,強調山水與心靈相契合的重要因素「自然精神」。由於中國山水畫源於自然是為了近一步理解現實,為的是獲得精神的自由,再來是為了發現自然而托物寄情且關照和欣賞山水,具備了流動性和廣泛性的象徵,所以得到創作者的喜愛。在中國繪畫史上山水畫也漸漸成為獨樹一格的審美理想,是構築在自然裡,因此在宋代時期,是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之境。元代以後畫家的感受漸漸超出於自然之上,有鑑於歷代累積的畫作為其根源,畫家在不必外求現實的情況下, 就足夠創作出比自然更完美或是更符合心境的作品,實現藝術的「師造化」境界。
自然有其景緻,畫者經過轉化的心靈意趣,運筆操墨落實在畫面裡,可見山水畫是一幅充滿精神圖像的構成。畫家關照藝術自然的範疇,為了能具體表現在人所能感知、感動的地方,以各種不同的筆墨手法將山水表現出來。其中模擬原為創作者經歷的過程,它可以講求真實,或是抱著研究自然,甚至是對美感經驗的表述,也可能是為了探尋真理、真實、虛構、想像等各種不同的創作觀念。賦予自然一個有意義的形象,讓觀者感覺到不單只是人所習知的自然固有性質,並且也是畫家個人畫中所表露出來的新境界。包括精神性、真實性或科學性表現的概念等各種顯現自然的方法,可以發現近代繪畫在精神上有較多一些的自我意識,因此對自然的想法也產生了變化,當借用自然的時候,自然似乎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對於自然的創作者的想法了。畫家如何筆繪山川四時景物,畫論中有詳細的討論,山石草木的表現方式都有多樣的變化,除了對具體實象的描繪和模擬外,畫家個人意味深長的想像空間,在視覺中觸發種種情感上的聯想,如宋代郭熙、郭思父子所言:「然則林泉之志,煙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妙手鬱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山光水色,滉漾奪目,此豈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山水畫注重在個人心境的不斷開展,以個人的形象出現,然後完全融入畫面,以自然山水打底稿,來表現活躍心底的自己,兩者相渾相融。
繪者對於外在景色的關注,運用繪畫寫實技法及寫生的精神外,透過意念在心中逐漸準備,而在筆毫墨端形諸形象,都跟創作者的個人想法有直接關係。有些畫家認為,山水繪畫只需要描寫畫家心中理想的山水,而不必去表現特定的實際景色。然而山水畫從它與人們見面開始,就源於對特定點位實景的描繪,它可是在經過了幾個世紀之後,才從五代和宋朝的繪者手中一變而成為體現山水的主題,這可是有循序漸進的演變過程。雖然這樣,縱觀所留下的經典畫作,也並不都完全跳脫畫中山水的地理特徵。反而是依據了作者自己所處區域特有的地形特色,畫家們才經營出各為一家的表現形式。
在山水畫創作裡多半會用線條畫出山形的輪廓,轉化成各種不同皴法來表現山形表面的質地及在形式上的正確。觀察實景寫繪所得的畫面仍是筆者的草稿,大多會在畫室中去重新組合,來表現心目中的山水,所以現實的自然山水在創作過程中仍是會經過筆者的取捨來逐步完成。
實際景象的山水是傳統山水畫對景寫生,用具象的寫實筆墨描繪山水勝景、園林屋宅等客觀景物,這種寫實畫法相對於畫家在觀看之後,依靠眼觀腦記所畫出來的記憶式山水而言,實際景象的山水更具有真實和可辨的比對性。而繪史上所說的實際景象山水並不單是畫家對自然山水複製般的對景寫生,而是經過畫家布局和筆墨皴擦的繪畫呈現,不僅在表現上要經過畫家的精心營造,也在不經意間融入了當代對繪畫的訴求。若要說把實際景象的山水帶到畫中的,可追溯至明朝畫家張宏,他作畫與各個朝代所重視的形式和既定的傳統山水造形不同,趨向於特定的實景描繪,如此所畫出來的山水畫給人一種動態的感觀,好像在畫面之中可概略看出實際的景色。把寫生之後再加以筆墨創作,進去大自然吸取養分,再把實景的實轉化為繪畫的虛,所以在畫中必須融入個人的情感和愜意的畫面,關注客觀世界表象中的美感,讓具象的山水有了生命。對描寫實景的注重,不僅僅只是繪畫風格的創新,這種趨向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歷來傳統形式和不變的造形山水畫法。不僅重視現實的參透與融合,在師法自然的融會貫通裡,注入了自己的心源發現與創造,把傳統筆墨融入多一些真實感的山川的視覺之中,顯現出境界清幽,使畫面增添些許活力。在他作品畫面裡的一些透視畫法也有些立體畫法,但所畫的對象可能還未能實際掌握足夠來明確的描繪,而讓當時的觀者對於所作畫的景象辨識度還無法很高。這些都是後來的人可繼續探索及進展的緣由。
創作山水不僅是要面對自然,而畫面的真實與想像都是山水的表現形式,這之間哪一個重要全看畫家個人的決定。在自然面前畫者甚至觀者的位置,可以因時因地而制宜,若寫生時可視需要不定點移動,如同畫卷較長的畫軸一般,隨著畫卷的開展,視覺焦點也隨之變化,此處已經完全不考慮真實性問題,視角可以由上而下至左而右,隨視覺移動的景觀,屬於全景式構圖,如畫作〈源遠流長〉即是由上而下的視覺移動構圖而成。南朝時期的謝赫對經營位置的說明,是針對畫面結構的安排是否得當,而根據客觀事實,謝赫所講的經營位置應當是以人物畫的作為考量,後來在唐宋時文人畫家逐漸推崇山水畫,漸漸地在作畫題材上轉為山水,強調的是在對象布局構圖的方面。畫面深遠雋永的空間效果如何呈現,作畫時以觀者的角度來安排畫面空間,觀看的角度不同,便決定山水景色的風貌不同。可以說在動筆之前的山水空間布局就已先進行,所謂意在筆先 ,胸有成竹,還有一些循規蹈矩的畫法外,岩石、山壁、樹叢、草木在畫面空間所占幅度,要有主客之分,這樣才能參差錯落、疏密相間、虛實相生,以期達到近觀其質、遠觀其勢的效果。
繪畫裡的空間與自然表現是可以持續探索的,如果討論畫作時只著重在遠近空間的描繪,那麼,實際的山水將在畫作之上,若是從用筆用墨的筆情墨趣來看的話,畫作又將遠勝實際的山水景色。顯然空間的分析不時地引導繪畫表達的進行,空間構成畫面並且區分為遠近大小,但是二維空間的繪畫作品卻要求三維呈現,所以空間必須進行轉化。在視覺透視裡,適當配合光影的變化,既符合科學性又具合理性,由塊面光影和顏色共同構成的立體空間,呈現出真實的景色,同時也解決構圖的問題。再來透視法主要是以幾何學、光影和空氣三種畫法所構成,到了印象派則將情感寄託在光影、色彩的明暗裡。而且按西畫畫法在作畫時,須依照透視學的理法,畫家所站的地方停點有一定,不可左右動,也不可前後移,眼睛可看見的畫,眼睛無法看見的不能畫。所以能逼真實景,一看即可瞭解,遠近大小,條理分明而不紊亂是這種畫的優點,也是其缺點。水墨畫的寫景則是像空拍機一樣,往返回旋飛翔,昇降自如。所以往上可看到山峰的頂端,往下俯視可見悠閒寧靜的住所,近的可見村居樹林,遠處觀看即可見山體,源源不斷的,得心應手,對於長幅橫幅,比較少限制,甚至畫數丈的長卷,也是行得通。在不相衝突下將透視法滲入水墨畫,逐漸變化不留痕跡,即所有畫面中安排視覺景象方式的眼睛所在的地方、觀者所站的位置等用透視畫法,而運筆用墨則用水墨畫法。如此看來透視畫法是眼中之畫,而水墨畫家則屬心中之畫。直到現在,山水畫傾向於描寫胸中丘壑,參照眼中的自然直觀呈現,並賦予自然美的感覺,吾人的知覺特別精於景物的感受,於是表現在文字與山水畫,對外在自然物象進行直觀描繪的同時,亦存在著以自我意志為基礎的創作自由。
以山為德,水為性的涵養心智作為山水畫進展的中心,藉筆墨寫繪山川來愉悅自我,陶冶情懷,所呈現出的山水畫立意雋永,趨向氣韻生動。不少山水畫家都將山作為心性與修養的棲息地,在山林中畫畫,以此來提升意境,用手中筆墨寫繪山水,飽含著審美情趣和自然造化。藉由作品以其饒富生趣的畫面,令觀者徜徉在視覺美學情境之中,感受創作者的精神與內涵。這已不單單是對繪畫的一種追求,更是融入了自己對山川的感悟,憑藉內心從容不迫的創作去寫繪。如此的畫作氤氲蔥鬱、秀美雋永、意境幽遠,筆到意隨,自然流露對山水真實的感覺。蘇軾〈題西林壁〉所言:「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一樣是山,視角不同,形象感受也不同。而自己的山水畫中,山水之間也存在著不同的意境,既能以細緻的方式表現秀美的風格,也能用厚重的筆墨顯現宏壯的氣韻。在意境上追求含蓄與深邃美,於細密秀潤行筆裡,顯出蒼厚華潤和灑脫清新的意韻,寓意蔥鬱自然。人與自然契合,作畫時所表現的畫面即可逐步邁向氣韻生動。筆者覺得山水畫是心靈的寄託,也是內心真摯的反應,可以說是性情的歸宿,靈魂的棲息地,人性的本質供給。因此山水畫是對真實山水的概括總結,畫中山水若掌握真山水的本質,即是掌握了道,所表現出來的意象及藝術,就是要表現自然之道。畫論講的「游於藝」,可說是真正的藝術態度。期待自己作品在保持傳統的筆法墨法與結合水墨畫的意境時,能夠漸漸地體現出磅礡的大氣,使觀者在引起心底漣漪以後,覺得餘韻猶存,以心感物,神與物游。
近期,筆者於繪畫創作上加深對大自然山川的進一步研究,不斷地學習前人及大家之長融入真實山水於畫面構圖,逐漸在畫作中增添部分實景細節豐富畫面才不至於與現實漸行漸遠,並配合筆法粗細變化、墨韻漸層暈染之下合乎情理及墨彩相得益彰,使作品能貼近自然生意又兼有畫面的美感,仍是目前持續努力的方向。此次出版的個人山水畫集,感謝臺灣藝術大學榮譽教授晴嵐林進忠為畫集賜序勉勵。創作的題材主要延續第一集畫冊裡的雲霧、瀑布、溪水、海浪等類型加上湖潭、洞穴和幾幅屋宇、花木等畫作,期盼能增添些許畫冊的新意。
依據《畫山水序》瞭解山水畫較早啟於宗炳的論述,強調山水與心靈相契合的重要因素「自然精神」。由於中國山水畫源於自然是為了近一步理解現實,為的是獲得精神的自由,再來是為了發現自然而托物寄情且關照和欣賞山水,具備了流動性和廣泛性的象徵,所以得到創作者的喜愛。在中國繪畫史上山水畫也漸漸成為獨樹一格的審美理想,是構築在自然裡,因此在宋代時期,是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之境。元代以後畫家的感受漸漸超出於自然之上,有鑑於歷代累積的畫作為其根源,畫家在不必外求現實的情況下, 就足夠創作出比自然更完美或是更符合心境的作品,實現藝術的「師造化」境界。
自然有其景緻,畫者經過轉化的心靈意趣,運筆操墨落實在畫面裡,可見山水畫是一幅充滿精神圖像的構成。畫家關照藝術自然的範疇,為了能具體表現在人所能感知、感動的地方,以各種不同的筆墨手法將山水表現出來。其中模擬原為創作者經歷的過程,它可以講求真實,或是抱著研究自然,甚至是對美感經驗的表述,也可能是為了探尋真理、真實、虛構、想像等各種不同的創作觀念。賦予自然一個有意義的形象,讓觀者感覺到不單只是人所習知的自然固有性質,並且也是畫家個人畫中所表露出來的新境界。包括精神性、真實性或科學性表現的概念等各種顯現自然的方法,可以發現近代繪畫在精神上有較多一些的自我意識,因此對自然的想法也產生了變化,當借用自然的時候,自然似乎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對於自然的創作者的想法了。畫家如何筆繪山川四時景物,畫論中有詳細的討論,山石草木的表現方式都有多樣的變化,除了對具體實象的描繪和模擬外,畫家個人意味深長的想像空間,在視覺中觸發種種情感上的聯想,如宋代郭熙、郭思父子所言:「然則林泉之志,煙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妙手鬱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山光水色,滉漾奪目,此豈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山水畫注重在個人心境的不斷開展,以個人的形象出現,然後完全融入畫面,以自然山水打底稿,來表現活躍心底的自己,兩者相渾相融。
繪者對於外在景色的關注,運用繪畫寫實技法及寫生的精神外,透過意念在心中逐漸準備,而在筆毫墨端形諸形象,都跟創作者的個人想法有直接關係。有些畫家認為,山水繪畫只需要描寫畫家心中理想的山水,而不必去表現特定的實際景色。然而山水畫從它與人們見面開始,就源於對特定點位實景的描繪,它可是在經過了幾個世紀之後,才從五代和宋朝的繪者手中一變而成為體現山水的主題,這可是有循序漸進的演變過程。雖然這樣,縱觀所留下的經典畫作,也並不都完全跳脫畫中山水的地理特徵。反而是依據了作者自己所處區域特有的地形特色,畫家們才經營出各為一家的表現形式。
在山水畫創作裡多半會用線條畫出山形的輪廓,轉化成各種不同皴法來表現山形表面的質地及在形式上的正確。觀察實景寫繪所得的畫面仍是筆者的草稿,大多會在畫室中去重新組合,來表現心目中的山水,所以現實的自然山水在創作過程中仍是會經過筆者的取捨來逐步完成。
實際景象的山水是傳統山水畫對景寫生,用具象的寫實筆墨描繪山水勝景、園林屋宅等客觀景物,這種寫實畫法相對於畫家在觀看之後,依靠眼觀腦記所畫出來的記憶式山水而言,實際景象的山水更具有真實和可辨的比對性。而繪史上所說的實際景象山水並不單是畫家對自然山水複製般的對景寫生,而是經過畫家布局和筆墨皴擦的繪畫呈現,不僅在表現上要經過畫家的精心營造,也在不經意間融入了當代對繪畫的訴求。若要說把實際景象的山水帶到畫中的,可追溯至明朝畫家張宏,他作畫與各個朝代所重視的形式和既定的傳統山水造形不同,趨向於特定的實景描繪,如此所畫出來的山水畫給人一種動態的感觀,好像在畫面之中可概略看出實際的景色。把寫生之後再加以筆墨創作,進去大自然吸取養分,再把實景的實轉化為繪畫的虛,所以在畫中必須融入個人的情感和愜意的畫面,關注客觀世界表象中的美感,讓具象的山水有了生命。對描寫實景的注重,不僅僅只是繪畫風格的創新,這種趨向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歷來傳統形式和不變的造形山水畫法。不僅重視現實的參透與融合,在師法自然的融會貫通裡,注入了自己的心源發現與創造,把傳統筆墨融入多一些真實感的山川的視覺之中,顯現出境界清幽,使畫面增添些許活力。在他作品畫面裡的一些透視畫法也有些立體畫法,但所畫的對象可能還未能實際掌握足夠來明確的描繪,而讓當時的觀者對於所作畫的景象辨識度還無法很高。這些都是後來的人可繼續探索及進展的緣由。
創作山水不僅是要面對自然,而畫面的真實與想像都是山水的表現形式,這之間哪一個重要全看畫家個人的決定。在自然面前畫者甚至觀者的位置,可以因時因地而制宜,若寫生時可視需要不定點移動,如同畫卷較長的畫軸一般,隨著畫卷的開展,視覺焦點也隨之變化,此處已經完全不考慮真實性問題,視角可以由上而下至左而右,隨視覺移動的景觀,屬於全景式構圖,如畫作〈源遠流長〉即是由上而下的視覺移動構圖而成。南朝時期的謝赫對經營位置的說明,是針對畫面結構的安排是否得當,而根據客觀事實,謝赫所講的經營位置應當是以人物畫的作為考量,後來在唐宋時文人畫家逐漸推崇山水畫,漸漸地在作畫題材上轉為山水,強調的是在對象布局構圖的方面。畫面深遠雋永的空間效果如何呈現,作畫時以觀者的角度來安排畫面空間,觀看的角度不同,便決定山水景色的風貌不同。可以說在動筆之前的山水空間布局就已先進行,所謂意在筆先 ,胸有成竹,還有一些循規蹈矩的畫法外,岩石、山壁、樹叢、草木在畫面空間所占幅度,要有主客之分,這樣才能參差錯落、疏密相間、虛實相生,以期達到近觀其質、遠觀其勢的效果。
繪畫裡的空間與自然表現是可以持續探索的,如果討論畫作時只著重在遠近空間的描繪,那麼,實際的山水將在畫作之上,若是從用筆用墨的筆情墨趣來看的話,畫作又將遠勝實際的山水景色。顯然空間的分析不時地引導繪畫表達的進行,空間構成畫面並且區分為遠近大小,但是二維空間的繪畫作品卻要求三維呈現,所以空間必須進行轉化。在視覺透視裡,適當配合光影的變化,既符合科學性又具合理性,由塊面光影和顏色共同構成的立體空間,呈現出真實的景色,同時也解決構圖的問題。再來透視法主要是以幾何學、光影和空氣三種畫法所構成,到了印象派則將情感寄託在光影、色彩的明暗裡。而且按西畫畫法在作畫時,須依照透視學的理法,畫家所站的地方停點有一定,不可左右動,也不可前後移,眼睛可看見的畫,眼睛無法看見的不能畫。所以能逼真實景,一看即可瞭解,遠近大小,條理分明而不紊亂是這種畫的優點,也是其缺點。水墨畫的寫景則是像空拍機一樣,往返回旋飛翔,昇降自如。所以往上可看到山峰的頂端,往下俯視可見悠閒寧靜的住所,近的可見村居樹林,遠處觀看即可見山體,源源不斷的,得心應手,對於長幅橫幅,比較少限制,甚至畫數丈的長卷,也是行得通。在不相衝突下將透視法滲入水墨畫,逐漸變化不留痕跡,即所有畫面中安排視覺景象方式的眼睛所在的地方、觀者所站的位置等用透視畫法,而運筆用墨則用水墨畫法。如此看來透視畫法是眼中之畫,而水墨畫家則屬心中之畫。直到現在,山水畫傾向於描寫胸中丘壑,參照眼中的自然直觀呈現,並賦予自然美的感覺,吾人的知覺特別精於景物的感受,於是表現在文字與山水畫,對外在自然物象進行直觀描繪的同時,亦存在著以自我意志為基礎的創作自由。
以山為德,水為性的涵養心智作為山水畫進展的中心,藉筆墨寫繪山川來愉悅自我,陶冶情懷,所呈現出的山水畫立意雋永,趨向氣韻生動。不少山水畫家都將山作為心性與修養的棲息地,在山林中畫畫,以此來提升意境,用手中筆墨寫繪山水,飽含著審美情趣和自然造化。藉由作品以其饒富生趣的畫面,令觀者徜徉在視覺美學情境之中,感受創作者的精神與內涵。這已不單單是對繪畫的一種追求,更是融入了自己對山川的感悟,憑藉內心從容不迫的創作去寫繪。如此的畫作氤氲蔥鬱、秀美雋永、意境幽遠,筆到意隨,自然流露對山水真實的感覺。蘇軾〈題西林壁〉所言:「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一樣是山,視角不同,形象感受也不同。而自己的山水畫中,山水之間也存在著不同的意境,既能以細緻的方式表現秀美的風格,也能用厚重的筆墨顯現宏壯的氣韻。在意境上追求含蓄與深邃美,於細密秀潤行筆裡,顯出蒼厚華潤和灑脫清新的意韻,寓意蔥鬱自然。人與自然契合,作畫時所表現的畫面即可逐步邁向氣韻生動。筆者覺得山水畫是心靈的寄託,也是內心真摯的反應,可以說是性情的歸宿,靈魂的棲息地,人性的本質供給。因此山水畫是對真實山水的概括總結,畫中山水若掌握真山水的本質,即是掌握了道,所表現出來的意象及藝術,就是要表現自然之道。畫論講的「游於藝」,可說是真正的藝術態度。期待自己作品在保持傳統的筆法墨法與結合水墨畫的意境時,能夠漸漸地體現出磅礡的大氣,使觀者在引起心底漣漪以後,覺得餘韻猶存,以心感物,神與物游。
近期,筆者於繪畫創作上加深對大自然山川的進一步研究,不斷地學習前人及大家之長融入真實山水於畫面構圖,逐漸在畫作中增添部分實景細節豐富畫面才不至於與現實漸行漸遠,並配合筆法粗細變化、墨韻漸層暈染之下合乎情理及墨彩相得益彰,使作品能貼近自然生意又兼有畫面的美感,仍是目前持續努力的方向。此次出版的個人山水畫集,感謝臺灣藝術大學榮譽教授晴嵐林進忠為畫集賜序勉勵。創作的題材主要延續第一集畫冊裡的雲霧、瀑布、溪水、海浪等類型加上湖潭、洞穴和幾幅屋宇、花木等畫作,期盼能增添些許畫冊的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