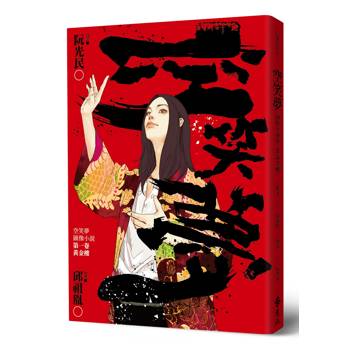《空笑夢》創作對談
漫畫_阮光民✕小說_邱祖胤
Q|祖胤:
在漫畫中看到你對小說的充分理解,然後營造出時代感與轟動感,覺得很感動,閱讀的過程,耳邊彷彿一直有鑼鼓的聲音。你在改編時特別看重哪個部分?是否有一個「入神」的過程?
A|光民:
我不確定是否「入神」,但「傷神」是確定的。
第一次改編時代跨距那麼長,角色眾多的小說,真的讓我產生不知如何下手的不確定感。這種徬徨無助並非周遭的不幫助,而是自己還處於千頭萬緒的不確定,旁人無法幫忙。
小說以角色為篇章,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以列傳的方式來改編,主角天闊就以見證這些大師的角度來一一道出他們之間的交集。
對於小說、戲劇來說或許這樣是可行的。漫畫要這樣處理,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主角光芒會弱,會少了一種主角引領往前推進的感覺。小說中寫的是天闊雖然技藝超群,擁有雙手掌握搬演千軍萬馬的能力,卻也因為命運之手的操控,亦如戲偶般的身不由己,隨著際遇之河而逐流。其實我自己也深深體會到人生確實如此,有許多不可控的變故,漣漪效應般延伸出許多無奈的不得不。不過我希望這些角色在隨波逐流中仍保有自我意識的掙扎,踢腿、划水,讓身軀前往另一個支流覓得生機,再遇見新的際遇。
此刻,我還沒有足夠自信說我能把這部作品的改編做得很好,我也還在河裡,陪著這些角色一起漂流、一起尋覓。
…………………………………………………………………………………………
Q|祖胤:
故事裡有一個部分很動人,就是「家人」。戲班猶如一個大家庭,這是我在小說中未曾強調的,但你在漫畫中特別突顯出來,所有衝突與轉折也源自於此。你的想法是?
A|光民:
「家人」對於人性格的塑造是影響深遠的,情感的交織纏繞也是難分難解的,即使有人嘴巴上、行為上表現出恨透家人,但內心的映照是成正比的在意。
戲台彩樓的結構是有地基、有梁柱、有門窗、有屋頂的空間,具備家的意象。以前看廟口的布袋戲班,一台卡車載著戲台布景,大多是夫妻帶著學齡前的小孩,再帶一兩個學徒。我想,早期鼓樂的成員更多吧,這些人為了演出,跟著移動的家一起山上下海、日晒雨淋、吵鬧怨懟、同喜同悲。這種游牧型態的戲班,讓我覺得凝聚他們的並非全都靠血緣,而是對演戲這件事的共識與彼此認同的維繫。他們相處的時間比起同住一個屋簷下,但天一亮各自去上班、上學的家人更久,情感上牽絆與影響必定更厚實。
每個人都有家或是曾經有家,所以,我覺得故事從家人的角度去切入,讀者對角色的共感會更快,也更容易融入。而「家」的議題,也是我個人很偏愛的題材,每個成員都有名字與稱謂,被賦予稱謂便成為人物角色,角色互動產生情感,情感是故事的根,每個家都是一棵故事樹。
…………………………………………………………………………………………
Q|祖胤:
這次漫畫改作你自己最滿意的部分?
A|光民:
之前接受訪談都會被問到,自創跟改編有什麼不同?我的回答是,兩者差別在於無中生有。
改編已經有故事範圍了,只要掌握好不偏離、不魔改,應該就可以安全完成。不過最近又體悟到,雖然改編已經有原著,但原作者的寫作過程也是無中生有的,如果可以把改編提升到讓讀者在觀看時也感覺這作品像是無中生有的境界,應該會很有趣。例如某位導演翻拍過去導演的作品,或是有位歌手把老歌演繹出新的風味。
或許讀過原著小說的讀者,或漫畫的新讀者從書名或是封面就會知道是在講布袋戲的故事,但是我試圖避免讀者打開書閱讀時,迎面而來的圖像就是布袋戲的元素。我想先演一段像武俠片打鬥的戲,再揭曉是布袋戲。前面的鋪陳,也隱喻著操偶師的功力能把空心的偶演繹像真人的「活」。雖然這樣的鋪陳做法,只能使用一次,但是如果能成為讀者重點的記憶、印象,我覺得就值得了。
因為小說的時空跨距大,改編時也嘗試許多時空切換,我想對於習慣漫畫閱讀者應該沒問題,但我更期待有讀者卡住,而在反覆閱讀對照後才豁然開朗。這種「記住」,會比順順看完,停在心裡更久。
所以,當有讀者卡住後會願意想辦法弄清楚。反而會讓我感到滿意。
…………………………………………………………………………………………
Q|祖胤:
小說中對男女情慾的描述非常克制,但到了漫畫,你倒是畫龍點睛添了顏色,是否有什麼特別的用意?
A|光民:
小說對於角色檯面下感情生活細節,雖沒有多敘述,但讀者在自行腦補時,反而可能是更加露骨的。不過也有可能我是畫面思維的人吧,我會去想像那些沒寫出來的情境畫面。
我一直認為身體是誠實的,身體是一種不用言語說明的履歷。但是人反而常花更多心思,想用更多的手段掩飾身體的誠實。
我曾聽聞早年戲班的軼事,無論萍水相逢的相好或是美其名開枝散葉。在那年代所有合理化的論述,都是為了服務男性,女性卻要壓抑自己,忍受男性的荷爾蒙到處雨露均霑。
所以改編時,我重新梳理各角色們私下的感情線,讓他們關係單純化。
情慾的氛圍,我並不是要踩畫面的界線,而是想表達身體的真誠,當他們在面對自己情感的當下,是誠實的,是自主的表達,我是「自願」成為「屬於」的。
(以上摘錄部分文章)
漫畫_阮光民✕小說_邱祖胤
Q|祖胤:
在漫畫中看到你對小說的充分理解,然後營造出時代感與轟動感,覺得很感動,閱讀的過程,耳邊彷彿一直有鑼鼓的聲音。你在改編時特別看重哪個部分?是否有一個「入神」的過程?
A|光民:
我不確定是否「入神」,但「傷神」是確定的。
第一次改編時代跨距那麼長,角色眾多的小說,真的讓我產生不知如何下手的不確定感。這種徬徨無助並非周遭的不幫助,而是自己還處於千頭萬緒的不確定,旁人無法幫忙。
小說以角色為篇章,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以列傳的方式來改編,主角天闊就以見證這些大師的角度來一一道出他們之間的交集。
對於小說、戲劇來說或許這樣是可行的。漫畫要這樣處理,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主角光芒會弱,會少了一種主角引領往前推進的感覺。小說中寫的是天闊雖然技藝超群,擁有雙手掌握搬演千軍萬馬的能力,卻也因為命運之手的操控,亦如戲偶般的身不由己,隨著際遇之河而逐流。其實我自己也深深體會到人生確實如此,有許多不可控的變故,漣漪效應般延伸出許多無奈的不得不。不過我希望這些角色在隨波逐流中仍保有自我意識的掙扎,踢腿、划水,讓身軀前往另一個支流覓得生機,再遇見新的際遇。
此刻,我還沒有足夠自信說我能把這部作品的改編做得很好,我也還在河裡,陪著這些角色一起漂流、一起尋覓。
…………………………………………………………………………………………
Q|祖胤:
故事裡有一個部分很動人,就是「家人」。戲班猶如一個大家庭,這是我在小說中未曾強調的,但你在漫畫中特別突顯出來,所有衝突與轉折也源自於此。你的想法是?
A|光民:
「家人」對於人性格的塑造是影響深遠的,情感的交織纏繞也是難分難解的,即使有人嘴巴上、行為上表現出恨透家人,但內心的映照是成正比的在意。
戲台彩樓的結構是有地基、有梁柱、有門窗、有屋頂的空間,具備家的意象。以前看廟口的布袋戲班,一台卡車載著戲台布景,大多是夫妻帶著學齡前的小孩,再帶一兩個學徒。我想,早期鼓樂的成員更多吧,這些人為了演出,跟著移動的家一起山上下海、日晒雨淋、吵鬧怨懟、同喜同悲。這種游牧型態的戲班,讓我覺得凝聚他們的並非全都靠血緣,而是對演戲這件事的共識與彼此認同的維繫。他們相處的時間比起同住一個屋簷下,但天一亮各自去上班、上學的家人更久,情感上牽絆與影響必定更厚實。
每個人都有家或是曾經有家,所以,我覺得故事從家人的角度去切入,讀者對角色的共感會更快,也更容易融入。而「家」的議題,也是我個人很偏愛的題材,每個成員都有名字與稱謂,被賦予稱謂便成為人物角色,角色互動產生情感,情感是故事的根,每個家都是一棵故事樹。
…………………………………………………………………………………………
Q|祖胤:
這次漫畫改作你自己最滿意的部分?
A|光民:
之前接受訪談都會被問到,自創跟改編有什麼不同?我的回答是,兩者差別在於無中生有。
改編已經有故事範圍了,只要掌握好不偏離、不魔改,應該就可以安全完成。不過最近又體悟到,雖然改編已經有原著,但原作者的寫作過程也是無中生有的,如果可以把改編提升到讓讀者在觀看時也感覺這作品像是無中生有的境界,應該會很有趣。例如某位導演翻拍過去導演的作品,或是有位歌手把老歌演繹出新的風味。
或許讀過原著小說的讀者,或漫畫的新讀者從書名或是封面就會知道是在講布袋戲的故事,但是我試圖避免讀者打開書閱讀時,迎面而來的圖像就是布袋戲的元素。我想先演一段像武俠片打鬥的戲,再揭曉是布袋戲。前面的鋪陳,也隱喻著操偶師的功力能把空心的偶演繹像真人的「活」。雖然這樣的鋪陳做法,只能使用一次,但是如果能成為讀者重點的記憶、印象,我覺得就值得了。
因為小說的時空跨距大,改編時也嘗試許多時空切換,我想對於習慣漫畫閱讀者應該沒問題,但我更期待有讀者卡住,而在反覆閱讀對照後才豁然開朗。這種「記住」,會比順順看完,停在心裡更久。
所以,當有讀者卡住後會願意想辦法弄清楚。反而會讓我感到滿意。
…………………………………………………………………………………………
Q|祖胤:
小說中對男女情慾的描述非常克制,但到了漫畫,你倒是畫龍點睛添了顏色,是否有什麼特別的用意?
A|光民:
小說對於角色檯面下感情生活細節,雖沒有多敘述,但讀者在自行腦補時,反而可能是更加露骨的。不過也有可能我是畫面思維的人吧,我會去想像那些沒寫出來的情境畫面。
我一直認為身體是誠實的,身體是一種不用言語說明的履歷。但是人反而常花更多心思,想用更多的手段掩飾身體的誠實。
我曾聽聞早年戲班的軼事,無論萍水相逢的相好或是美其名開枝散葉。在那年代所有合理化的論述,都是為了服務男性,女性卻要壓抑自己,忍受男性的荷爾蒙到處雨露均霑。
所以改編時,我重新梳理各角色們私下的感情線,讓他們關係單純化。
情慾的氛圍,我並不是要踩畫面的界線,而是想表達身體的真誠,當他們在面對自己情感的當下,是誠實的,是自主的表達,我是「自願」成為「屬於」的。
(以上摘錄部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