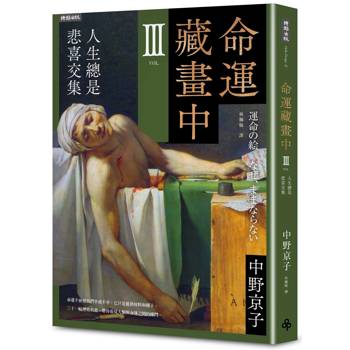當命運悄然降臨
一七九三年是法國大革命爆發後的第四年,在動盪的這一年,以路易十六遭到處決揭開了序幕。隨後法國相繼對英國、荷蘭和西班牙等國宣戰,溫和派的吉倫特黨被逐出政壇,進入雅各賓黨的獨裁統治時期。但在七月,雅各賓黨的領袖馬拉(Jean-Paul Marat)被暗殺了。
馬拉出生於瑞士,父親是義大利人,母親是瑞士人。他從十五歲起就在法國生活,並學習醫學。之後曾在倫敦開業行醫,然後再度返回法國,擔任法國國王弟弟阿圖瓦伯爵(Comte d'Artois)部隊裡的軍醫。
然而馬拉因反政府的言行,他的醫學論文始終無法獲得學術界的認同,這件事進一步加深了他對腐敗王政的憤怒,最後辭去軍醫職務,去當個小鎮醫師。
不久,法國大革命爆發,君主制被推翻,然而原本團結一致反對君主制的資產階級(布爾喬亞)和工人階級,開始出現分歧。馬拉站在工人陣營這一方,認為應該要監督革命的進程。他自行創辦政論報紙《人民之友》,猛烈抨擊資產階級,甚至因此曾被迫流亡國外。
回到法國後,馬拉依舊不改其犀利風格,對吉倫特黨(親資產階級)進行更甚於從前的嚴厲批判,並呼籲勞工階層要繼續採取行動。之後,馬拉當選國民公會議員,深受民眾愛戴,被譽為「最接近人民的革命家」。
但就在吉倫特黨人失勢,馬拉逐漸成為雅各賓黨的掌權者之一後,長年困擾他的皮膚病也日益惡化。他全身奇癢難耐,甚至無法穿著衣物,更別說出席議會了。每天他只能長時間浸泡在含有硫磺的藥浴中,躺在浴缸中撰寫與閱讀報紙上的文章,已成為他的日常。
七月十三日,馬拉收到一封來自名為夏綠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的陌生女子來信,信中寫道:「我是如此不幸,應該有資格請求您援助。」她聲稱自己從諾曼第的康城(Caen),長途跋涉至巴黎,是為了告訴馬拉,有一群逃到康城的吉倫特黨人正密謀發動叛亂,她希望馬拉能出面阻止。
這個消息對於想完全剷除吉倫特殘黨的馬拉來說,無疑是珍貴的資訊。在馬拉還沒來得及回信之前,科黛就已造訪馬拉的住處。當時是晚上七點左右,馬拉聽見從玄關傳來與他同居的情人拒絕科黛要求會面的爭吵聲,於是馬拉在屋內大聲喊道,讓人放她進來。
──這正是命運之門開啟的瞬間。
科黛出生於諾曼第的沒落貴族,全家僅靠一座小農莊的微薄收入過活。母親去世後,十三歲的科黛被送進修道院生活。雖然她看似對於修道院充滿勞動、祈禱與閱讀的規律生活感到滿意,但因為她閱讀的書籍,也有盧梭和普魯塔克的著作,所以她應該早已對政治和社會議題有所關注。
十年後,根據革命政府的規定,教會和修道院都收歸國有,科黛所在的修道院也遭關閉,於是她前往康城與姑媽一起生活,並在那裡認識了吉倫特黨的成員巴爾巴魯(Barbaroux,因為他容貌俊美,所以也有傳言兩人有過戀情,但此說並無明確證據)以及他的同伴。這些從巴黎逃到康城的吉倫特黨人,暗地裡和潛伏在其他城市的同志取得聯繫,謀劃捲土重來的反攻大計。
科黛的家庭雖然並不富裕,但畢竟還是貴族出身,因此對工人階層原本就缺乏認同,或許正因如此,讓她很容易接受巴爾巴魯等人的想法,並在閱讀反雅各賓黨的傳單後,很快得出了結論:如今革命主導權之所以從中產階級轉移到勞動階層,一定是雅各賓黨人,尤其是馬拉這個傢伙,在背後搧風點火造成的。
但科黛接下來展現的行動力,實在令人震驚。離開修道院不過短短兩年,年僅二十四歲的她,獨自策劃並執行了這次的暗殺行動。或許是在修道院中早已習慣保持沉默,科黛並沒有向姑媽或任何人透露過此事的隻字片語。
她搭了整整兩天的馬車抵達巴黎後,便立刻展開行動。她先投宿在廉價旅館,隔天買了一把刀子,接著就前往位於科德利埃街上的馬拉住所。但那次拜訪,科黛被警戒心重的馬拉的情人拒於門外。有了這次經驗,她決定改變計畫,她深知男人不擅長拒絕他人的求助,於是先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請求信給馬拉,並於隔天信件送達馬拉的住處時,再次登門拜訪。儘管這次馬拉的情人依然阻攔科黛進屋,但屋內的馬拉聽見爭執聲後同意她的求見,這次總算成功了。
前面提到,因為馬拉幾乎整天都泡在浴缸裡,所以這場會面也很自然發生在這個極為特殊的場所。科黛年輕貌美,想必應該讓馬拉卸下了心防吧。在只有兩個人的浴室裡,當時馬拉正把科黛敘述的內容,用鵝毛筆記錄下來(浴缸上架有一塊用來充當桌子的木板)。科黛突如其來的襲擊,讓馬拉一刀斃命。從刀刃從肋骨刺入直抵肺部的情況來看,她很可能事前已練習過刺殺的位置與角度。可以說這次行動,科黛做得的確漂亮。
當馬拉的家人聽到聲響衝進浴室時,只見胸口插著刀子的馬拉已經斷氣,而科黛則靜靜地站在原地,絲毫沒有要逃走的打算。
馬拉被暗殺後的第三天,法國新古典主義畫派的大師大衛,接到國民公會希望把此次事件繪製成紀念畫作的委託。大衛也是雅各賓黨人,曾投票贊成處死路易十六,在大革命期間是安全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大衛和雅各賓黨的最高領導人羅伯斯比(Robespierre)的意見一致,他們認為應該將馬拉神格化為殉道者,以推進革命的進程。然後,大衛在親眼目睹已經開始腐爛的馬拉遺體前進行素描,並於三個月後完成了傳世大作〈馬拉之死〉。
大衛將歷史性的一幕,以凍結般的靜止方式,使其成為永恆,這種作畫技巧最適合用來描繪死者。在這幅畫中,大衛對馬拉進行了極大的美化。馬拉和丹東 一樣,都因其貌不揚著稱。但在這幅畫裡,馬拉原本突出的雙眼,如今已安詳地合上,而且還有著不似五十歲中年男子會有的健美肉體與光滑肌膚,但事實上,他全身已經布滿紅疹。據說馬拉的舌頭本來是吐出來的,但大衛並未如實畫出來,不然畫面應該會挺可怕的吧。
那隻無力下垂的手臂,使人聯想到〈聖母憐子像〉(也稱為〈聖殤〉)中,聖母抱著耶穌遺體哀悼的畫面。馬拉右胸的傷口並不深,流出的血也不多。傷口的位置和十字架上的耶穌被羅馬士兵用槍刺擊(為了確認耶穌是否已經死亡)之處相仿。白色的布料也像纏繞在耶穌身上的裹屍布。這一切,無不展現出畫家大衛對於構圖的精心計算。
一七九三年是法國大革命爆發後的第四年,在動盪的這一年,以路易十六遭到處決揭開了序幕。隨後法國相繼對英國、荷蘭和西班牙等國宣戰,溫和派的吉倫特黨被逐出政壇,進入雅各賓黨的獨裁統治時期。但在七月,雅各賓黨的領袖馬拉(Jean-Paul Marat)被暗殺了。
馬拉出生於瑞士,父親是義大利人,母親是瑞士人。他從十五歲起就在法國生活,並學習醫學。之後曾在倫敦開業行醫,然後再度返回法國,擔任法國國王弟弟阿圖瓦伯爵(Comte d'Artois)部隊裡的軍醫。
然而馬拉因反政府的言行,他的醫學論文始終無法獲得學術界的認同,這件事進一步加深了他對腐敗王政的憤怒,最後辭去軍醫職務,去當個小鎮醫師。
不久,法國大革命爆發,君主制被推翻,然而原本團結一致反對君主制的資產階級(布爾喬亞)和工人階級,開始出現分歧。馬拉站在工人陣營這一方,認為應該要監督革命的進程。他自行創辦政論報紙《人民之友》,猛烈抨擊資產階級,甚至因此曾被迫流亡國外。
回到法國後,馬拉依舊不改其犀利風格,對吉倫特黨(親資產階級)進行更甚於從前的嚴厲批判,並呼籲勞工階層要繼續採取行動。之後,馬拉當選國民公會議員,深受民眾愛戴,被譽為「最接近人民的革命家」。
但就在吉倫特黨人失勢,馬拉逐漸成為雅各賓黨的掌權者之一後,長年困擾他的皮膚病也日益惡化。他全身奇癢難耐,甚至無法穿著衣物,更別說出席議會了。每天他只能長時間浸泡在含有硫磺的藥浴中,躺在浴缸中撰寫與閱讀報紙上的文章,已成為他的日常。
七月十三日,馬拉收到一封來自名為夏綠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的陌生女子來信,信中寫道:「我是如此不幸,應該有資格請求您援助。」她聲稱自己從諾曼第的康城(Caen),長途跋涉至巴黎,是為了告訴馬拉,有一群逃到康城的吉倫特黨人正密謀發動叛亂,她希望馬拉能出面阻止。
這個消息對於想完全剷除吉倫特殘黨的馬拉來說,無疑是珍貴的資訊。在馬拉還沒來得及回信之前,科黛就已造訪馬拉的住處。當時是晚上七點左右,馬拉聽見從玄關傳來與他同居的情人拒絕科黛要求會面的爭吵聲,於是馬拉在屋內大聲喊道,讓人放她進來。
──這正是命運之門開啟的瞬間。
科黛出生於諾曼第的沒落貴族,全家僅靠一座小農莊的微薄收入過活。母親去世後,十三歲的科黛被送進修道院生活。雖然她看似對於修道院充滿勞動、祈禱與閱讀的規律生活感到滿意,但因為她閱讀的書籍,也有盧梭和普魯塔克的著作,所以她應該早已對政治和社會議題有所關注。
十年後,根據革命政府的規定,教會和修道院都收歸國有,科黛所在的修道院也遭關閉,於是她前往康城與姑媽一起生活,並在那裡認識了吉倫特黨的成員巴爾巴魯(Barbaroux,因為他容貌俊美,所以也有傳言兩人有過戀情,但此說並無明確證據)以及他的同伴。這些從巴黎逃到康城的吉倫特黨人,暗地裡和潛伏在其他城市的同志取得聯繫,謀劃捲土重來的反攻大計。
科黛的家庭雖然並不富裕,但畢竟還是貴族出身,因此對工人階層原本就缺乏認同,或許正因如此,讓她很容易接受巴爾巴魯等人的想法,並在閱讀反雅各賓黨的傳單後,很快得出了結論:如今革命主導權之所以從中產階級轉移到勞動階層,一定是雅各賓黨人,尤其是馬拉這個傢伙,在背後搧風點火造成的。
但科黛接下來展現的行動力,實在令人震驚。離開修道院不過短短兩年,年僅二十四歲的她,獨自策劃並執行了這次的暗殺行動。或許是在修道院中早已習慣保持沉默,科黛並沒有向姑媽或任何人透露過此事的隻字片語。
她搭了整整兩天的馬車抵達巴黎後,便立刻展開行動。她先投宿在廉價旅館,隔天買了一把刀子,接著就前往位於科德利埃街上的馬拉住所。但那次拜訪,科黛被警戒心重的馬拉的情人拒於門外。有了這次經驗,她決定改變計畫,她深知男人不擅長拒絕他人的求助,於是先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請求信給馬拉,並於隔天信件送達馬拉的住處時,再次登門拜訪。儘管這次馬拉的情人依然阻攔科黛進屋,但屋內的馬拉聽見爭執聲後同意她的求見,這次總算成功了。
前面提到,因為馬拉幾乎整天都泡在浴缸裡,所以這場會面也很自然發生在這個極為特殊的場所。科黛年輕貌美,想必應該讓馬拉卸下了心防吧。在只有兩個人的浴室裡,當時馬拉正把科黛敘述的內容,用鵝毛筆記錄下來(浴缸上架有一塊用來充當桌子的木板)。科黛突如其來的襲擊,讓馬拉一刀斃命。從刀刃從肋骨刺入直抵肺部的情況來看,她很可能事前已練習過刺殺的位置與角度。可以說這次行動,科黛做得的確漂亮。
當馬拉的家人聽到聲響衝進浴室時,只見胸口插著刀子的馬拉已經斷氣,而科黛則靜靜地站在原地,絲毫沒有要逃走的打算。
馬拉被暗殺後的第三天,法國新古典主義畫派的大師大衛,接到國民公會希望把此次事件繪製成紀念畫作的委託。大衛也是雅各賓黨人,曾投票贊成處死路易十六,在大革命期間是安全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大衛和雅各賓黨的最高領導人羅伯斯比(Robespierre)的意見一致,他們認為應該將馬拉神格化為殉道者,以推進革命的進程。然後,大衛在親眼目睹已經開始腐爛的馬拉遺體前進行素描,並於三個月後完成了傳世大作〈馬拉之死〉。
大衛將歷史性的一幕,以凍結般的靜止方式,使其成為永恆,這種作畫技巧最適合用來描繪死者。在這幅畫中,大衛對馬拉進行了極大的美化。馬拉和丹東 一樣,都因其貌不揚著稱。但在這幅畫裡,馬拉原本突出的雙眼,如今已安詳地合上,而且還有著不似五十歲中年男子會有的健美肉體與光滑肌膚,但事實上,他全身已經布滿紅疹。據說馬拉的舌頭本來是吐出來的,但大衛並未如實畫出來,不然畫面應該會挺可怕的吧。
那隻無力下垂的手臂,使人聯想到〈聖母憐子像〉(也稱為〈聖殤〉)中,聖母抱著耶穌遺體哀悼的畫面。馬拉右胸的傷口並不深,流出的血也不多。傷口的位置和十字架上的耶穌被羅馬士兵用槍刺擊(為了確認耶穌是否已經死亡)之處相仿。白色的布料也像纏繞在耶穌身上的裹屍布。這一切,無不展現出畫家大衛對於構圖的精心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