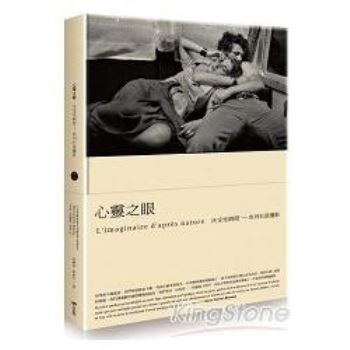決定性瞬間
「在這世上,凡任何事都存在決定性的一刻。」──赫茲樞機主教
我對繪畫一直深感興趣。孩童時期每週四跟週日可以畫畫,其他日子我就夢想著畫畫。跟許多小孩一樣,我有一台盒式布朗尼相機,我只會偶爾使用它,為了在相薄裡填滿假期的回憶。要等到許久之後,我才開始更懂得怎麼透過相機來觀看,我的小世界因而變大許多,假期照片也跟著結束了。
此外還有電影,像是白珍珠擔綱演出的《紐約悲劇》、葛里菲斯的經典作品《凋謝的花朵》、史特羅海姆的早期電影《貪婪》、艾森斯坦的《波坦金戰艦》,以及德黑耶的《聖女貞德殉難記》等等,都讓我學習到如何觀看。之後,我認識了一些擁有阿特傑照片的攝影家,那些影像都讓我印象深刻。我因而買了一個腳架、一塊黑色簾幕、一台上蠟胡桃木的9×12大相機,上面配備了一個鏡頭蓋作為快門之用,這個特殊的裝備只允許我去迎擊那些不動的事物。其他的主題就顯得太過複雜,或者對我而言太過「業餘」。當時我自以為這樣就是獻身給「藝術」了。我自己在顯影盆裡沖洗底片跟印樣,這樣的活兒讓我樂在其中。我幾乎沒多想有些相紙可能反差強烈,而另一些相紙的階調則比較柔和,我那時根本不在意這些;反倒是沒能成功顯影時,鐵定會讓我勃然大怒。
1931年,22歲這年,我起身前往非洲。我在象牙海岸買了一台相機,但一直要到將近一年後回到法國時,才發現裡頭嚴重發霉;所有的照片都疊上一層蕨類般的圖樣。那時我病得不輕,必須靜養休息;一筆小月俸讓我的生活還過得去,攝影純粹作為一己之樂。我發現了萊卡,它變成了我眼睛的延伸,從此便不曾離開我身邊。我會走上一整天路,神經緊繃,隨時捕捉街角發生的景物,活像在搜索現行犯。我尤其渴望抓住一個影像、在這唯一的影像裡呈現出某個蹦現場景的全部精華。從事新聞報導攝影,意謂著用一連串的照片來述說一個故事,這種想法我以前從來沒有過,後來看到同行一些朋友的作品以及攝影刊物,爾後輪到我為這些雜誌社工作,我才漸漸學會怎麼做報導攝影。
我經常東奔西跑,儘管我對旅行不在行。我喜歡慢慢來,在動身前往下一個國家之前好好準備遷徙工作。一旦到了一個地方,我幾乎每次都想就這麼定居下來,以便能夠過上一個更好的當地生活。我沒辦法環遊世界。
1947年,我跟另外五名獨立攝影師創辦了我們的公司:「馬格蘭攝影通訊社」,透過法國乃至於外國的期刊雜誌,把我們所拍下的新聞報導攝影作品傳播開來。我始終還是攝影愛好者,可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玩家了。
新聞報導攝影
新聞報導攝影涵蓋了什麼?有時候光是一張照片,已經擁有足夠的形式精準性與豐富性,內容也能充分獲得共鳴,可以完全自足;但這樣的情況並不多見。可以逬發出火花的主題元素經常都是分散的,我們並沒有權利把它們硬湊在一塊,如果這麼做的話就是舞弊:報導的用處就在於此,在同一個版面裡匯集的各張照片,也將種種互補性元素整合起來。
報導是頭腦、眼睛、內心的連續運作,為了表述一個問題,設定一個事件,賦予某些印象。當人們跟著一個發展中的事件團團轉時,總是相當有趣。人們試圖從中找到解決之道。這有時只花費幾秒鐘時間,有時卻要耗上幾個小時或好些個日子;沒有標準的解決方案,也沒有所謂的秘訣,得像打網球一樣隨時準備好。現實賦予我們如此之多,使得人們非得斷然地割捨、簡化,但是否大家都割捨地恰如其份呢?人們在工作的同時,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必要的。有時候,我們認為自己拍了一張最有力量的照片,可是即使如此,還是會繼續拍下去,只因無法明確預知事件究竟會如何發展。然而要避免掃射似快速而機械的拍攝,才不至於負載太多無用的塗寫把記憶塞滿,妨礙了整體格局的清晰度。
記憶非常重要。每張照片的記憶都與事件踩著同樣的步伐奔馳;在攝影時我們必須確定已經表述一切,沒有留下空缺,否則就會為時已晚,而人們無法逆轉事件或重新來過。
對我們來說,總是有兩種選擇,因此也可能造成兩種可能的悔恨;一是透過觀景窗對照現實世界的時候,另一則是當影像一旦沖放定型,被迫要放棄一些雖然精準、卻不那麼有力的影像。當一切顯得太遲時,我們便清楚知道自己哪裡不足。經常,在攝影時,稍微猶豫,或身體感知一時沒接上事件,就會讓你有一種漏掉整體中某個局部的感受;尤其且更常發生的是,眼睛漫不經心,目光變得渙散,這就足以毀掉一切。
對我們每一個人都一樣,隨著我們的視線拋出,空間開始逐漸擴展直至無限;當下的空間有時強烈打動我們,有時令人無感,隨後很快便在記憶裡封存起來,並且開始質變。在所有表述的方式當中,唯有攝影能將一個確切的瞬間凝凍住。我們把玩那些會消失的東西,而當它們消逝之後,就再也不可能使之重新復活。人們再碰觸不到他的對象;頂多只能從採擷的影像中挑選一些作為新聞報導之用。作家在字句成形前仍有時間在紙上斟酌,也可以將不同的元素連結在一起。在停滯期的時候,腦袋會完全空白一片。對我們來說,那些消失的,就是永遠消失了:而這也是攝影師這份工作的焦慮與主要原創性的來源。我們沒辦法在回到飯店之後重作我們的報導。我們的任務包括了在我們的素描本上──相機的幫助下觀察現實,將之紀錄下來,不藉由取景方式誤導,或利用暗房裡的小撇步。這些把戲在明眼人面前無所遁形。
在一則報導攝影中,每個打擾都得記上一筆,那就像當裁判的人最後自己入了戲。因此必須像狼一樣悄聲接近對象,即使它是一個靜物。收起貓般利爪,但要帶著如鷹銳利目光。不可推擠;因為人們不會在釣魚之前把水攪亂。當然,不能仰賴鎂光燈,即便連光線也要尊重,甚至在沒有光線時亦然。不然的話攝影師就變成了一個讓人無法忍受的冒犯者。這份職業相當程度立足在與人群建立關係之上,一句話就可能毀掉一切,辛苦建立的通道全被關上。這裡必須再強調的是,並沒有一個系統可供規範,除了一件事:讓人們忘記有一台總是在饑渴窺視的相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面對攝影這件事的反應往往大不相同,在整個東方,一個缺乏耐心或單單只是急躁的攝影師,看上去就是個蠢蛋,這是無藥可救的。如果不是分秒必爭,又有人發現你帶著一台相機,這時最好先放下拍照這件事,親切地讓小孩們在你腳邊嬉戲。
主題
主題的存在怎能視而不見?它就是無法被忽視。因為在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乃至於最私人的領域都充滿主題,我們才得以清楚面對所有事情,並誠實地面對我們感受到的。總之,根據你感知到的內容,來選定自己的位置。
主題並不在於蒐集事件,因為事件本身所能提供的趣味並不算多。重要的是從中選擇,在深厚的現實中,掌握出真正的事實。
從攝影來看,最微小的東西可能會成為偉大的主題,關於人類的枝微末節也可以成為樂章的主旋律。我們觀看,並且以一種見證的方式來展示周遭的世界,而事件則會透過本身的功用,激發出形式的有機律動。
至於如何自我表述,可以有一千零一種方式來精煉出吸引我們的東西來,其清新鮮明的感覺難以用言語表達,所以我們就別說了吧……
有那麼一塊領域,已經被繪畫放棄不再鑽研,有些人說是因為攝影的發明所導致;無論如何,攝影確然在圖像形式上佔了一席之地。但人們不能把畫家們放棄他們創作中的一大主題:肖像,歸咎於攝影的發明。
騎裝外套、高筒軍帽,馬匹,即使是最學院派的畫家,如今也對這些東西敬而遠之,梅索尼耶護腿套上的一堆扣子,已經讓他們喘不過氣來。我們這些攝影家,或許跟一個東西周旋的時間遠不如畫家持久,因此並不感到困擾吧?甚至我們還樂在其中,因為透過照相機,我們接受了生活所有的真實面向。人們期望能在自己的肖像中永存不朽,並且把他們的良好形象流傳給後代子孫;如是的願望經常混雜著某種對於魔法的憂慮,我們才有機可乘。
肖像讓人感動的其中一項特質是尋回了人們彼此的相似性,透過環境洩露的點點滴滴顯出他們之間的連續性,不然,也不會在一本家庭相簿裡,把叔叔和他的孫子認成是同一個人。但如果攝影家從外在到內在都達到了反映世間的境界,那是因為人們,借用戲劇用語,「進入了情境」。攝影師必須尊重現場氣氛,整合種種透露地域特徵的環境性,特別要避免人為加工,這會扼殺人性的真實面,同時要讓人忘卻相機的存在以及操控相機的那個人。一個複雜的機械裝置與聚光燈,在我看來,都會妨礙一隻小鳥自由飛出。有什麼東西會比臉上的表情更稍縱即逝呢?往往,在第一次看到一張臉時,那印象都是比較準確的,如果這個印象會隨著我們接觸到更多人而變得益發興味盎然,我們也可能因為對人們的認識逐漸加深,而變得很難去表達他們深刻的性情。我覺得身為一個肖像攝影師是危險的,你只能照著顧客的要求行事,因為他們當中只有少數例外,其餘的人都希望自己看來更帥更美,如此一來所謂的真實將蕩然無存。當顧客對於相機的客觀性抱持戰戰兢兢的心情,同時間攝影師卻在尋找一種心理的敏銳性;這兩種反映交鋒時,就會在同一個攝影師的肖像照之間顯露出某種親族關係,因為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連,與攝影師自身的心理結構脫離不了關係。和諧的獲至,是透過每張臉的不對稱所尋求的平衡,自然也避免了過份的甜美或怪誕。
針對肖像的人為性,我毋寧更喜歡那些在證照攝影館的璃櫥窗裡、一張接著一張彼此緊挨著的大頭照。這些臉孔總是可以讓人提問,並在其中發掘出一種紀錄性,儘管當中找不到人們所期待擁有的詩意。
「在這世上,凡任何事都存在決定性的一刻。」──赫茲樞機主教
我對繪畫一直深感興趣。孩童時期每週四跟週日可以畫畫,其他日子我就夢想著畫畫。跟許多小孩一樣,我有一台盒式布朗尼相機,我只會偶爾使用它,為了在相薄裡填滿假期的回憶。要等到許久之後,我才開始更懂得怎麼透過相機來觀看,我的小世界因而變大許多,假期照片也跟著結束了。
此外還有電影,像是白珍珠擔綱演出的《紐約悲劇》、葛里菲斯的經典作品《凋謝的花朵》、史特羅海姆的早期電影《貪婪》、艾森斯坦的《波坦金戰艦》,以及德黑耶的《聖女貞德殉難記》等等,都讓我學習到如何觀看。之後,我認識了一些擁有阿特傑照片的攝影家,那些影像都讓我印象深刻。我因而買了一個腳架、一塊黑色簾幕、一台上蠟胡桃木的9×12大相機,上面配備了一個鏡頭蓋作為快門之用,這個特殊的裝備只允許我去迎擊那些不動的事物。其他的主題就顯得太過複雜,或者對我而言太過「業餘」。當時我自以為這樣就是獻身給「藝術」了。我自己在顯影盆裡沖洗底片跟印樣,這樣的活兒讓我樂在其中。我幾乎沒多想有些相紙可能反差強烈,而另一些相紙的階調則比較柔和,我那時根本不在意這些;反倒是沒能成功顯影時,鐵定會讓我勃然大怒。
1931年,22歲這年,我起身前往非洲。我在象牙海岸買了一台相機,但一直要到將近一年後回到法國時,才發現裡頭嚴重發霉;所有的照片都疊上一層蕨類般的圖樣。那時我病得不輕,必須靜養休息;一筆小月俸讓我的生活還過得去,攝影純粹作為一己之樂。我發現了萊卡,它變成了我眼睛的延伸,從此便不曾離開我身邊。我會走上一整天路,神經緊繃,隨時捕捉街角發生的景物,活像在搜索現行犯。我尤其渴望抓住一個影像、在這唯一的影像裡呈現出某個蹦現場景的全部精華。從事新聞報導攝影,意謂著用一連串的照片來述說一個故事,這種想法我以前從來沒有過,後來看到同行一些朋友的作品以及攝影刊物,爾後輪到我為這些雜誌社工作,我才漸漸學會怎麼做報導攝影。
我經常東奔西跑,儘管我對旅行不在行。我喜歡慢慢來,在動身前往下一個國家之前好好準備遷徙工作。一旦到了一個地方,我幾乎每次都想就這麼定居下來,以便能夠過上一個更好的當地生活。我沒辦法環遊世界。
1947年,我跟另外五名獨立攝影師創辦了我們的公司:「馬格蘭攝影通訊社」,透過法國乃至於外國的期刊雜誌,把我們所拍下的新聞報導攝影作品傳播開來。我始終還是攝影愛好者,可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玩家了。
新聞報導攝影
新聞報導攝影涵蓋了什麼?有時候光是一張照片,已經擁有足夠的形式精準性與豐富性,內容也能充分獲得共鳴,可以完全自足;但這樣的情況並不多見。可以逬發出火花的主題元素經常都是分散的,我們並沒有權利把它們硬湊在一塊,如果這麼做的話就是舞弊:報導的用處就在於此,在同一個版面裡匯集的各張照片,也將種種互補性元素整合起來。
報導是頭腦、眼睛、內心的連續運作,為了表述一個問題,設定一個事件,賦予某些印象。當人們跟著一個發展中的事件團團轉時,總是相當有趣。人們試圖從中找到解決之道。這有時只花費幾秒鐘時間,有時卻要耗上幾個小時或好些個日子;沒有標準的解決方案,也沒有所謂的秘訣,得像打網球一樣隨時準備好。現實賦予我們如此之多,使得人們非得斷然地割捨、簡化,但是否大家都割捨地恰如其份呢?人們在工作的同時,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必要的。有時候,我們認為自己拍了一張最有力量的照片,可是即使如此,還是會繼續拍下去,只因無法明確預知事件究竟會如何發展。然而要避免掃射似快速而機械的拍攝,才不至於負載太多無用的塗寫把記憶塞滿,妨礙了整體格局的清晰度。
記憶非常重要。每張照片的記憶都與事件踩著同樣的步伐奔馳;在攝影時我們必須確定已經表述一切,沒有留下空缺,否則就會為時已晚,而人們無法逆轉事件或重新來過。
對我們來說,總是有兩種選擇,因此也可能造成兩種可能的悔恨;一是透過觀景窗對照現實世界的時候,另一則是當影像一旦沖放定型,被迫要放棄一些雖然精準、卻不那麼有力的影像。當一切顯得太遲時,我們便清楚知道自己哪裡不足。經常,在攝影時,稍微猶豫,或身體感知一時沒接上事件,就會讓你有一種漏掉整體中某個局部的感受;尤其且更常發生的是,眼睛漫不經心,目光變得渙散,這就足以毀掉一切。
對我們每一個人都一樣,隨著我們的視線拋出,空間開始逐漸擴展直至無限;當下的空間有時強烈打動我們,有時令人無感,隨後很快便在記憶裡封存起來,並且開始質變。在所有表述的方式當中,唯有攝影能將一個確切的瞬間凝凍住。我們把玩那些會消失的東西,而當它們消逝之後,就再也不可能使之重新復活。人們再碰觸不到他的對象;頂多只能從採擷的影像中挑選一些作為新聞報導之用。作家在字句成形前仍有時間在紙上斟酌,也可以將不同的元素連結在一起。在停滯期的時候,腦袋會完全空白一片。對我們來說,那些消失的,就是永遠消失了:而這也是攝影師這份工作的焦慮與主要原創性的來源。我們沒辦法在回到飯店之後重作我們的報導。我們的任務包括了在我們的素描本上──相機的幫助下觀察現實,將之紀錄下來,不藉由取景方式誤導,或利用暗房裡的小撇步。這些把戲在明眼人面前無所遁形。
在一則報導攝影中,每個打擾都得記上一筆,那就像當裁判的人最後自己入了戲。因此必須像狼一樣悄聲接近對象,即使它是一個靜物。收起貓般利爪,但要帶著如鷹銳利目光。不可推擠;因為人們不會在釣魚之前把水攪亂。當然,不能仰賴鎂光燈,即便連光線也要尊重,甚至在沒有光線時亦然。不然的話攝影師就變成了一個讓人無法忍受的冒犯者。這份職業相當程度立足在與人群建立關係之上,一句話就可能毀掉一切,辛苦建立的通道全被關上。這裡必須再強調的是,並沒有一個系統可供規範,除了一件事:讓人們忘記有一台總是在饑渴窺視的相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面對攝影這件事的反應往往大不相同,在整個東方,一個缺乏耐心或單單只是急躁的攝影師,看上去就是個蠢蛋,這是無藥可救的。如果不是分秒必爭,又有人發現你帶著一台相機,這時最好先放下拍照這件事,親切地讓小孩們在你腳邊嬉戲。
主題
主題的存在怎能視而不見?它就是無法被忽視。因為在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乃至於最私人的領域都充滿主題,我們才得以清楚面對所有事情,並誠實地面對我們感受到的。總之,根據你感知到的內容,來選定自己的位置。
主題並不在於蒐集事件,因為事件本身所能提供的趣味並不算多。重要的是從中選擇,在深厚的現實中,掌握出真正的事實。
從攝影來看,最微小的東西可能會成為偉大的主題,關於人類的枝微末節也可以成為樂章的主旋律。我們觀看,並且以一種見證的方式來展示周遭的世界,而事件則會透過本身的功用,激發出形式的有機律動。
至於如何自我表述,可以有一千零一種方式來精煉出吸引我們的東西來,其清新鮮明的感覺難以用言語表達,所以我們就別說了吧……
有那麼一塊領域,已經被繪畫放棄不再鑽研,有些人說是因為攝影的發明所導致;無論如何,攝影確然在圖像形式上佔了一席之地。但人們不能把畫家們放棄他們創作中的一大主題:肖像,歸咎於攝影的發明。
騎裝外套、高筒軍帽,馬匹,即使是最學院派的畫家,如今也對這些東西敬而遠之,梅索尼耶護腿套上的一堆扣子,已經讓他們喘不過氣來。我們這些攝影家,或許跟一個東西周旋的時間遠不如畫家持久,因此並不感到困擾吧?甚至我們還樂在其中,因為透過照相機,我們接受了生活所有的真實面向。人們期望能在自己的肖像中永存不朽,並且把他們的良好形象流傳給後代子孫;如是的願望經常混雜著某種對於魔法的憂慮,我們才有機可乘。
肖像讓人感動的其中一項特質是尋回了人們彼此的相似性,透過環境洩露的點點滴滴顯出他們之間的連續性,不然,也不會在一本家庭相簿裡,把叔叔和他的孫子認成是同一個人。但如果攝影家從外在到內在都達到了反映世間的境界,那是因為人們,借用戲劇用語,「進入了情境」。攝影師必須尊重現場氣氛,整合種種透露地域特徵的環境性,特別要避免人為加工,這會扼殺人性的真實面,同時要讓人忘卻相機的存在以及操控相機的那個人。一個複雜的機械裝置與聚光燈,在我看來,都會妨礙一隻小鳥自由飛出。有什麼東西會比臉上的表情更稍縱即逝呢?往往,在第一次看到一張臉時,那印象都是比較準確的,如果這個印象會隨著我們接觸到更多人而變得益發興味盎然,我們也可能因為對人們的認識逐漸加深,而變得很難去表達他們深刻的性情。我覺得身為一個肖像攝影師是危險的,你只能照著顧客的要求行事,因為他們當中只有少數例外,其餘的人都希望自己看來更帥更美,如此一來所謂的真實將蕩然無存。當顧客對於相機的客觀性抱持戰戰兢兢的心情,同時間攝影師卻在尋找一種心理的敏銳性;這兩種反映交鋒時,就會在同一個攝影師的肖像照之間顯露出某種親族關係,因為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連,與攝影師自身的心理結構脫離不了關係。和諧的獲至,是透過每張臉的不對稱所尋求的平衡,自然也避免了過份的甜美或怪誕。
針對肖像的人為性,我毋寧更喜歡那些在證照攝影館的璃櫥窗裡、一張接著一張彼此緊挨著的大頭照。這些臉孔總是可以讓人提問,並在其中發掘出一種紀錄性,儘管當中找不到人們所期待擁有的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