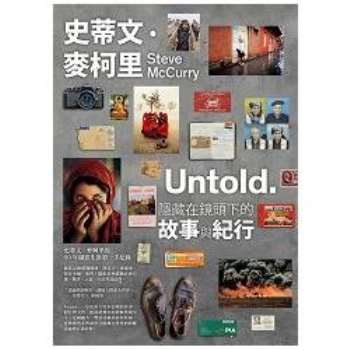911
2011年某個陰鬱的星期一午後,麥柯里歷經三十多個小時跋涉,終於從圖博返回紐約華盛頓廣場公園北側的住處,那天是9月10日,隔天早上醒來,天空一片蔚藍,他從公寓下樓到辦公室。麥柯里回想起:「從辦公室的窗戶就能眺望世貿中心,我正在翻閱郵件時,助理的母親來電:『快看窗戶外頭』,當時是早上9點10分,7分鐘前,聯合航空175號班機撞上曼哈頓下城的世貿南塔,24 分鐘前,美國航空11 號班機撞上世貿北塔。」
麥柯里眼見高樓冒出濃煙,一把抓起相機奔向大樓屋頂,「曼哈頓市區在屋頂上一覽無遺,因此我開始拍照」,這是麥柯里長久職業生涯的直覺,要及時捕捉各個時刻。當天很早拍下的照片裡,人們聚集在華盛頓廣場拱門下,望向南方的世貿中心。消防隊員與救護人員很快將圍繞著兩棟大樓,從高處向下望,每個人都只是一個小點,充滿不祥預兆。在911攻擊的初期照片裡,雙塔背後是湛藍無雲的天空,黑煙向東往布魯克林方向飄過港口。
麥柯里站在屋頂,連續拍攝四十分鐘後,眼前出現了不可置信的畫面,早上9點59分,客機撞擊高樓不到一小時後,南塔倒塌;半小時後,北塔也隨之崩潰。麥柯里說:「我和所有人一樣,無法置信雙塔竟然崩垮,覺得根本不可能」,對他而言,雙塔早已是紐約的日常景觀,許多人也心有同感。「人們在格林威治村常看見雙塔,那是生活的一部分,大樓崩塌就像心遭到撕裂,看著雙塔在眼前消失,完全令人無法相信,尤其還有好多人都在大樓內。」
面對劇烈暴力影像時,我們所見大多只是對事件的印象或印記,例如車禍的碎片、犯罪現場的遺體輪廓、建築炸毀的照片等。如蘇珊.桑塔格所言,攝影史上鮮少有「捕捉到死亡發生片刻,並讓它永存不朽」,但麥柯里的照片正有如此效果,在連續拍攝的照片裡,他凍結雙塔分崩離析的瞬間,也是許多人喪命的瞬間。他在雙塔倒塌之時拍攝的最後照片裡,灰燼如繭包覆著高樓,民眾原本站在幾個街區外查看情況,眼見巨大沙塵來襲,紛紛向北逃竄,而麥柯里卻向南行,「在這種情況之下,勢必要或至少試圖拋開各種情緒,才能做好工作而不會完全癱瘓,讓你的經驗來做主。」他和助理於是前往災變現場。兩人穿梭於建築物後巷及公寓之間,花費一個小時才越過三十個街區抵達現場,「我永遠不會忘記塵土與紙張飄散滿天,警方已畫出封鎖區,不過我們不斷繞行周邊街道,終於進入封鎖線內。」麥柯里在世貿廣場上見到一片狼藉,「一切徹底毀滅,連最後三十層樓或十層樓都沒留下,只剩下骨架,眼前所見都超出理解範圍。」他拍到一名消防隊員走過大樓遺跡,身邊四處只剩下堆填如山的扭曲鋼架、電線、樑柱與管線,景象超乎現實且陌生,麥柯里即便曾赴戰場工作,也沒見過這番情景。紐約各地救護人員陸續抵達,架起臨時設施救治傷患,但「沒有傷患出現,大樓倒塌後,根本無人倖存,或許在沒能逃出雙塔的數千人裡,還有一、兩人生還,也僅此而已。」
雙塔倒塌後的數小時內,警消人員不斷勸說麥柯里離開,即便火勢與煙塵大幅降低能見度,但他每次都回頭找尋其他方式接近現場。他很意外警方仍在傾頹的鋼筋水泥堆裡,試圖尋找生還者,「現場看來毫無希望,在巨大的災害現場,這些微小身影繼續在瓦礫碎石間翻找。」雖然愈來愈疲憊,麥柯里仍繼續拍照直至入夜。之後他回家睡了幾小時,但麥柯里覺得,「我一定要再回去,我在凌晨三點半醒來,沿著西城高速公路步行,附近有幾棟建築物失火,我在水泥護欄旁爬了90 公尺,再剪開鐵絲網。到了另一側之後,我和一群美國防衛隊員同行,因為天色昏暗,我穿著卡其色衣褲,也藏好身上的相機,因此沒人發覺。過程中不斷有人要求我離開,因此我一半時間在拍照,另一半時間在想辦法避免被趕出去。」
麥柯里記錄的影像呈現了兩架客機造成多麼大的衝擊,也傳達出人員傷亡及家屬深切哀慟之情,這些照片細緻且詳細地記錄暴力的後果,觀眾也和攝影師一樣,嘗試去理解這些無法想像的畫面。這些影像反映出麥柯里習慣關注於侵略行動、暴力的餘波、暴力的影響,以及它如何對人民日常生活產生影響,突顯出即便遭遇最劇烈的處境,人性仍能持續向前。9月12日太陽升起後,災變現場在日光之中映著不祥紅光。麥柯里記錄搜救隊員凝視著雙塔遺跡,拍攝地點鄰近南塔倒塌處,他回想起:「當時氣氛相當沉重,我試圖將我感受到的恐懼與失落感轉化為影像。這個事件完全是前所未有的罪禍。」在照片的右下角,一群人站在兩根斷裂的樑柱上;較靠近鏡頭的人正在試圖滅火,在廣大的碎石堆裡,面對希望渺茫的任務,微小的無名人員仍奮勇努力。麥柯里拍下一系列消防員走過以往奧斯汀.托賓廣場所在地,若非黃色制服與紅色火舌,這張作品猶如黑白照,在灰燼籠罩下,呈現如鬼魅般的單一色調。麥柯里表示,「雖然消防員明知許多同事命喪此處,心中震驚與專業態度交雜,但這也正是他們受訓的目的與工作內容。」這個場景承載著緬懷意味,麥柯里的911系列照片總能超越畫面描述的事件,彰顯人類在重大悲劇裡保持堅毅的精神。
由於事件本身不可思議,當時許多民眾都表示如同「在看電影場景」。麥柯里的作品運用近乎電影的色彩與光影,記錄了無比恐懼,以及世界失序的超現實夢魘。世貿中心大廳平時總擠滿數百人,但在畫面裡卻是一片死寂,耀眼光線在煙灰瀰漫中變得柔和,地上滿是塵土與散落紙張,建構出文學般的景象。金融中心對面的自由街情況亦然,麥柯里在此拍下世貿市場大樓斑駁坑疤的外牆,汽車在鄰近街上遭砸毀,救護車與消防車旁都是滅火留下的水窪。麥柯里在9月12日星期三工作了一個早上,但維安層級到了下午轉趨嚴格,警員、防衛隊與消防員人數增加,麥柯里要移動更加不易,在警消人員護送下離開現場後,他屢次嘗試重返未果。
幾天之後,麥柯里的照片透過馬格蘭攝影通訊社的管道,登上世界各地報紙與雜誌,但麥柯里之後多年都不曾再看過那些幻燈片一眼,「它們靜靜放在檔案櫃裡,如今再看到,彷彿靈魂出竅體驗一般,很難相信當天真的發生了那些事。」2001年底,馬格蘭發行《紐約911》專書,集結麥柯里及眾多攝影師的作品,而他的北塔倒塌照片則成為封面。記錄911事件時,麥柯里運用從業生涯多年累積的技巧與資源,包括在排山倒海的障礙中持續向前,靜靜地融入與連結最劇烈和混亂的情況,或在大場面裡保有個別元素的關注,在超出人類控制的事件中找尋人性面向。世貿攻擊是史上記錄最詳細的事件之一,在全球電視上直播,但麥柯里結合藝術性、記者長才,再加上他身為紐約客對這起悲劇的切身感受,讓作品不僅呈現事件客觀恐懼,亦包含個人親身反應。麥柯里的照片從拍攝對象中汲取強大力量,並加入他的藝術洞察力,因為他用心注視著周遭世界,讓所有人也目不轉睛。
2011年某個陰鬱的星期一午後,麥柯里歷經三十多個小時跋涉,終於從圖博返回紐約華盛頓廣場公園北側的住處,那天是9月10日,隔天早上醒來,天空一片蔚藍,他從公寓下樓到辦公室。麥柯里回想起:「從辦公室的窗戶就能眺望世貿中心,我正在翻閱郵件時,助理的母親來電:『快看窗戶外頭』,當時是早上9點10分,7分鐘前,聯合航空175號班機撞上曼哈頓下城的世貿南塔,24 分鐘前,美國航空11 號班機撞上世貿北塔。」
麥柯里眼見高樓冒出濃煙,一把抓起相機奔向大樓屋頂,「曼哈頓市區在屋頂上一覽無遺,因此我開始拍照」,這是麥柯里長久職業生涯的直覺,要及時捕捉各個時刻。當天很早拍下的照片裡,人們聚集在華盛頓廣場拱門下,望向南方的世貿中心。消防隊員與救護人員很快將圍繞著兩棟大樓,從高處向下望,每個人都只是一個小點,充滿不祥預兆。在911攻擊的初期照片裡,雙塔背後是湛藍無雲的天空,黑煙向東往布魯克林方向飄過港口。
麥柯里站在屋頂,連續拍攝四十分鐘後,眼前出現了不可置信的畫面,早上9點59分,客機撞擊高樓不到一小時後,南塔倒塌;半小時後,北塔也隨之崩潰。麥柯里說:「我和所有人一樣,無法置信雙塔竟然崩垮,覺得根本不可能」,對他而言,雙塔早已是紐約的日常景觀,許多人也心有同感。「人們在格林威治村常看見雙塔,那是生活的一部分,大樓崩塌就像心遭到撕裂,看著雙塔在眼前消失,完全令人無法相信,尤其還有好多人都在大樓內。」
面對劇烈暴力影像時,我們所見大多只是對事件的印象或印記,例如車禍的碎片、犯罪現場的遺體輪廓、建築炸毀的照片等。如蘇珊.桑塔格所言,攝影史上鮮少有「捕捉到死亡發生片刻,並讓它永存不朽」,但麥柯里的照片正有如此效果,在連續拍攝的照片裡,他凍結雙塔分崩離析的瞬間,也是許多人喪命的瞬間。他在雙塔倒塌之時拍攝的最後照片裡,灰燼如繭包覆著高樓,民眾原本站在幾個街區外查看情況,眼見巨大沙塵來襲,紛紛向北逃竄,而麥柯里卻向南行,「在這種情況之下,勢必要或至少試圖拋開各種情緒,才能做好工作而不會完全癱瘓,讓你的經驗來做主。」他和助理於是前往災變現場。兩人穿梭於建築物後巷及公寓之間,花費一個小時才越過三十個街區抵達現場,「我永遠不會忘記塵土與紙張飄散滿天,警方已畫出封鎖區,不過我們不斷繞行周邊街道,終於進入封鎖線內。」麥柯里在世貿廣場上見到一片狼藉,「一切徹底毀滅,連最後三十層樓或十層樓都沒留下,只剩下骨架,眼前所見都超出理解範圍。」他拍到一名消防隊員走過大樓遺跡,身邊四處只剩下堆填如山的扭曲鋼架、電線、樑柱與管線,景象超乎現實且陌生,麥柯里即便曾赴戰場工作,也沒見過這番情景。紐約各地救護人員陸續抵達,架起臨時設施救治傷患,但「沒有傷患出現,大樓倒塌後,根本無人倖存,或許在沒能逃出雙塔的數千人裡,還有一、兩人生還,也僅此而已。」
雙塔倒塌後的數小時內,警消人員不斷勸說麥柯里離開,即便火勢與煙塵大幅降低能見度,但他每次都回頭找尋其他方式接近現場。他很意外警方仍在傾頹的鋼筋水泥堆裡,試圖尋找生還者,「現場看來毫無希望,在巨大的災害現場,這些微小身影繼續在瓦礫碎石間翻找。」雖然愈來愈疲憊,麥柯里仍繼續拍照直至入夜。之後他回家睡了幾小時,但麥柯里覺得,「我一定要再回去,我在凌晨三點半醒來,沿著西城高速公路步行,附近有幾棟建築物失火,我在水泥護欄旁爬了90 公尺,再剪開鐵絲網。到了另一側之後,我和一群美國防衛隊員同行,因為天色昏暗,我穿著卡其色衣褲,也藏好身上的相機,因此沒人發覺。過程中不斷有人要求我離開,因此我一半時間在拍照,另一半時間在想辦法避免被趕出去。」
麥柯里記錄的影像呈現了兩架客機造成多麼大的衝擊,也傳達出人員傷亡及家屬深切哀慟之情,這些照片細緻且詳細地記錄暴力的後果,觀眾也和攝影師一樣,嘗試去理解這些無法想像的畫面。這些影像反映出麥柯里習慣關注於侵略行動、暴力的餘波、暴力的影響,以及它如何對人民日常生活產生影響,突顯出即便遭遇最劇烈的處境,人性仍能持續向前。9月12日太陽升起後,災變現場在日光之中映著不祥紅光。麥柯里記錄搜救隊員凝視著雙塔遺跡,拍攝地點鄰近南塔倒塌處,他回想起:「當時氣氛相當沉重,我試圖將我感受到的恐懼與失落感轉化為影像。這個事件完全是前所未有的罪禍。」在照片的右下角,一群人站在兩根斷裂的樑柱上;較靠近鏡頭的人正在試圖滅火,在廣大的碎石堆裡,面對希望渺茫的任務,微小的無名人員仍奮勇努力。麥柯里拍下一系列消防員走過以往奧斯汀.托賓廣場所在地,若非黃色制服與紅色火舌,這張作品猶如黑白照,在灰燼籠罩下,呈現如鬼魅般的單一色調。麥柯里表示,「雖然消防員明知許多同事命喪此處,心中震驚與專業態度交雜,但這也正是他們受訓的目的與工作內容。」這個場景承載著緬懷意味,麥柯里的911系列照片總能超越畫面描述的事件,彰顯人類在重大悲劇裡保持堅毅的精神。
由於事件本身不可思議,當時許多民眾都表示如同「在看電影場景」。麥柯里的作品運用近乎電影的色彩與光影,記錄了無比恐懼,以及世界失序的超現實夢魘。世貿中心大廳平時總擠滿數百人,但在畫面裡卻是一片死寂,耀眼光線在煙灰瀰漫中變得柔和,地上滿是塵土與散落紙張,建構出文學般的景象。金融中心對面的自由街情況亦然,麥柯里在此拍下世貿市場大樓斑駁坑疤的外牆,汽車在鄰近街上遭砸毀,救護車與消防車旁都是滅火留下的水窪。麥柯里在9月12日星期三工作了一個早上,但維安層級到了下午轉趨嚴格,警員、防衛隊與消防員人數增加,麥柯里要移動更加不易,在警消人員護送下離開現場後,他屢次嘗試重返未果。
幾天之後,麥柯里的照片透過馬格蘭攝影通訊社的管道,登上世界各地報紙與雜誌,但麥柯里之後多年都不曾再看過那些幻燈片一眼,「它們靜靜放在檔案櫃裡,如今再看到,彷彿靈魂出竅體驗一般,很難相信當天真的發生了那些事。」2001年底,馬格蘭發行《紐約911》專書,集結麥柯里及眾多攝影師的作品,而他的北塔倒塌照片則成為封面。記錄911事件時,麥柯里運用從業生涯多年累積的技巧與資源,包括在排山倒海的障礙中持續向前,靜靜地融入與連結最劇烈和混亂的情況,或在大場面裡保有個別元素的關注,在超出人類控制的事件中找尋人性面向。世貿攻擊是史上記錄最詳細的事件之一,在全球電視上直播,但麥柯里結合藝術性、記者長才,再加上他身為紐約客對這起悲劇的切身感受,讓作品不僅呈現事件客觀恐懼,亦包含個人親身反應。麥柯里的照片從拍攝對象中汲取強大力量,並加入他的藝術洞察力,因為他用心注視著周遭世界,讓所有人也目不轉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