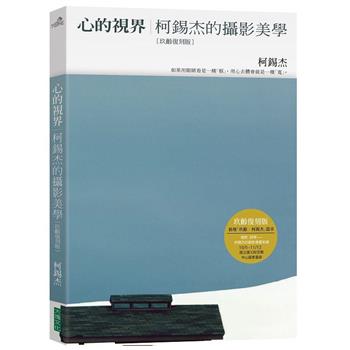脫下一身束縛,我越活越真
我自拍過很多滑稽幽默的照片,譬如在沙漠裡一個人洗澡、或與愛車的合照,或是光溜溜地圍著一條圍裙做飯等等。我發現自己的相貌不斷在改變。幼年時還有一點書生氣,逃兵期間眼神卻顯得叛逆、落拓。到日本時,我感染了他們的風氣,時常穿著西裝。
在台灣拍平面廣告時,我怕攝影棚的熱燈,動不動就脫個精光,留下很多人來瘋的照片。到紐約之後,早早白頭的我,已經有種天地任我行走的解放感,在歐洲流浪時,我脫下了一身的束縛,越活越真。
老實說,我在處事應對上,一點能耐也沒有,常惹潔兮生氣,但她又拿我沒辦法,只能哭笑不得。譬如,我不喜歡死腦筋的人,有時工作上碰見這樣的年輕人,怎麼點都點不開竅,我就把這些話用日語編成打油詩大聲吟唱,對方當然還是聽不懂,連累了在旁的潔兮,她笑也不是、罵也不是,差點憋死了。
我喜歡跟人相處、高談闊論,大家圍繞在我身邊,自然冷落了一旁的潔兮,她有次特別提醒我,以後相偕出門,別把她晾在一邊!我也反省了,她是個才華洋溢的藝術家,我們因藝術而成知己,她卻常年扮演我身邊被忽略的「內人」,很不公平。
趁我還記得她的委屈,恰好有次公開聚會的場合,我就對新象藝術的許博允隆重介紹樊潔兮老師,許博允被我的「大小聲」嚇獃了,潔兮在旁又氣了一場,因為我們三人本來就都很熟,她知道我只是想「表演」一下,表示我有聽進去她的話。
潔兮——藝術之路的人生伴侶
與潔兮新婚在紐約的那段日子,是我們都念念不忘的。某藝術家說我不拍照,就是為了潔兮,這話然而不然。尋獲真愛的我,將潔兮的藝術之路視為第一要務,然而潔兮的藝術光輝不也映照在我的作品上嗎?何況我在照片的轉染法上投入鉅資,只期待會有最好的成品出現,同時也從沒停止鍛鍊我的眼力。
我每天接送潔兮去學舞,那裏聚集了紐約最美的年輕舞者們,我每每看得目不轉睛,潔兮笑我,「你這人......」,我不以為意,美在召喚我,我不得不回應吧?
我這樣到處看,並不是為了拍照,但有需要時馬上能派上用場,譬如我一直很欣賞紐約某個爵士吧裡的女歌手,當日本雜誌請我拍一個專題時,我立刻知道自己要拍的就是她!日本雜誌全由我做主,事後也非常滿意。
當時岳母替我們處理家務,讓我們沒有後顧之憂。而我則以藝術家看藝術家的嚴苛眼光,督促潔兮每日進步,給予意見。
潔兮就是我最好的拍攝對象,在家練舞與拍照是我們關起門的樂事。跟心靈契合的伴侶在一塊,永遠不會覺得無聊。我私下替她拍的照片很少對外發表,時報週刊請我去非洲拍專題時,我決定先練一練手,就帶著潔兮去墨西哥,在美國境內轉飛兩次,才抵達安地斯山脈的尾端,然後徵詢旅館當地人的意見,請了船夫帶我們到了一個無人島,自然絕美的懷抱中,誰都像初生的赤子,回到母親身邊般感到安心、踏實。我們拍得好開心,穿著比基尼的潔兮決定全裸入鏡,我先跟老漁夫說,「我老婆要脫光囉!」他很風趣地問,「那我先鑽到水裡躲起來?」笑壞了我們倆。
在室內拍潔兮,常見她雙眼無辜,像小動物在靜靜凝視,但潔兮如果想拿我拍的照片去當她舞作發表的宣傳照,我常會無賴地拒絕,還故意說些難聽話:「妳都傻傻的!」潔兮聽了又是氣個半死。
經濟上雖不寬裕,但那段日子千金難買。曾有一次我們在街上購物,排隊結賬時有個經紀人前來遞名片,要求潔兮去當手部模特兒。我立刻拒絕,潔兮拿了名片回家,猶豫著說,拍攝的酬勞對我們的經濟會是一大幫助,我堅持說不,潔兮就一笑置之。
當年我對潔兮一見鍾情的就是她極美的一雙手,憑她自身的資質,成為世界頂尖的手模不在話下。然而我更傾心於她的心靈與才華,一個藝術家不該止步於此。潔兮對舞蹈純淨的嚮往與激情,就像她澄淨的凝望一樣,永遠投向遠方,不曾偏離藝術的道路。
等待維納斯
離開義大利時,我憑著好手氣,在賭場籌足了去希臘的旅費。但是我並不知道,即將在希臘邂逅影響我一生的場景。
那是夏天的愛琴海,我在海色、天色和白牆之間,徘徊了二十多分鐘。我知道那裡有我想要的東西,但快門怎麼也按不下去。只好到附近轉一轉,看看海,在那裡呆坐了幾分鐘。終於我回去按了快門。
平常我們從相機的視窗看出去,只是一個小小的image,但是等到透過幻燈機把它放大來看的時候,那一剎那,是優秀作品或一般水準,一目了然。回來後看著這張放大的照片,我知道我突破了自己,完成一張非常好的作品。甚至到現在,我自認為仍沒有一張作品能超越這張。
後來詩人鄭愁予聽了這張照片的故事,他說:「啊,愛琴海是維納斯出現的地方,你在等待維納斯。」
1986年,大陸文學家高行健用自己的畫和我交換了這幅〈等待維納斯〉。他說我的作品景深消失了,令人難以分辨是攝影還是畫。他認為如果我是畫家,也會是很好的畫家。
過去我拍的照片比較熱情澎湃,不論是野柳、月世界,都有一種生命力,我的老朋友、音樂家許常惠說,「像我的人一樣。」但境隨心轉。我在歐洲這段時間所拍的照片,畫面經常非常安靜、簡潔,大自然被抽離到只剩下大面積的色塊、形狀和線條,但是「簡單」中仍富有變化和旋律,有一種「靜的力量」。照片中的生命力轉化為內歛,是可以一直「看進去」的。
這段日子對我來說有點像「修行」,尤其看的都是哲學方面的書,也許因此,透過相機拍出來的東西都有些許「禪」味。但我想,最重要的還是「無心」,「無心」讓我的感受力更為敏銳,可以看到大自然表相以外的深層的美。
那段日子所拍的照片,受到美國攝影雜誌極大的肯定,幫助我在紐約開創了一條極簡主義新攝影風格的路。但拍攝的當下我只是拍自己想拍的,並沒有想到什麼極簡風格,也不知道屬於柯錫杰的人生新頁已經展開。
想像空間
那一天,我開車帶岳母去散心,到紐澤西的海邊,看到一扇窗和一張椅子。我請她過來坐下。因為海風,老人家的帽子一直是戴上的,又因為生病,整個人顯得消沈。我想拍老人的孤獨感。岳母坐在椅子上的黃色身影,很能傳達那種氣氛。拍完後,岳母離開,椅子空蕩蕩地留在原處,我突然感覺,沒有人的空間,好像比有人在的時候,孤獨感更深。我想了幾分鐘,又拍了一張。空無一人的場景,似乎容納了所有人的孤獨。
一般人站在那裡看到這個景時,都會立刻反應,認為海是重點;但我不是,我把黑的部分放得很大,幾乎佔畫面的二分之一。然後海天一線,透露一點點的光,椅子是唯一的焦點。〈觀海〉這一張的三道光影甚至可以看出三種不同的質材:紅磚、木頭、水泥。
1983年拍的這兩張照片——〈黃衫客〉和〈觀海〉——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對比。這兩張基本上是同一個場景,只是一張有人,一張沒有。兩張照片是同一天拍攝,但發表的時間卻相差了23年。
〈黃衫客〉照片洗出來不久後就拿到市立美術館展覽,因為當時覺得〈觀海〉太孤寂了,所以只發表〈黃衫客〉。但是23年後,現在的我更喜歡〈觀海〉。〈觀海〉感覺更有詩意,因為沒有人,反而更有想像空間。
一個人的心靈有太多東西的時候,其實什麼也體會不到。簡單的時候,我們的心才活在一個更大的空間。
既然沒有人,是誰在「觀海」?這裡有多少人來過?他們之中,有多少人在這張椅子上坐過?是什麼樣的人,想著什麼樣的心事,有著什麼樣的體會?正因為沒有一個像「黃衫客」那樣具體的人物在畫面中,更多的可能性被包含在裡面了,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幅對「觀海」的想像,都可以形成一個「觀海」的故事。而那雙觀海的眼睛,透過攝影家的鏡頭,變成觀者的雙眼,觀海的是無數陌生的旅人,是攝影家本人,更是我們自己。而畫面中的視覺焦點——椅子,在那裡不知歷經了多少白天黑夜,承載了無以計數的各式各樣的人,在這張照片中,誰又會說它是沒有生命的呢?它既是一個道具,又是一個主體。
如果沒有〈觀海〉,可能很多人會喜歡〈黃衫客〉。但是兩張照片放在一起,想像空間的力量就很容易體會了。我自己非常喜歡〈觀海〉,看到它的那一剎那,我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存在,因為有我的存在,才有觀海的這個景。
這樣的照片給觀者的想像空間是無限的,每個人看到都會有不同的感受,全部的感受都可以融入到這一張照片裡。所以攝影作品要讓人感覺像讀一首詩,用幾個字就可以想像一個宇宙那麼大的空間。
記錄式的照片是在介紹這個世界,我的照片則是要讓人去體會這個世界。
三個鐘頭只為瞬間
照相館最好的作品往往是家庭合照,大家都坐在那裡安安靜靜的,三兩下就拍出大家都覺得很happy的照片。但攝影家不是這樣。攝影家拍一個人的時候往往要用掉很多很多底片,因為他要的不是紀錄一個人的表相,他要的是追到這個人的人性。在互動的某一剎那,他會即時捕捉對方在當下展露出來的人性。
我拍福特總裁也好、張忠謀也好,我會花三個鐘頭,慢慢把對方拉近,然後讓他放鬆,漸漸回到他真正的自己。
往往要經過三個鐘頭,有時候是兩個鐘頭,我會感覺到我抓到了他整個人生最重要的一剎那。他這個人最重要的特質,不自覺地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狀況下,展露出來。然而這個時候還不能說:「我拍到了!」仍然要繼續拍,我通常至少都會花上兩百張底片。拍到我自己累了,對方也累了。有時候覺得累了的那一刻,他也完全放鬆了,所以最後那幾分鐘很重要,他已經不在乎自己在鏡頭前是什麼樣子,也不會在鏡頭面前假裝某種形象,此時他的內心與表相都一致了,也就是他的特質已經出來了,我就可以很容易地捕捉。但這個時候還不能真的停,我們要繼續追蹤,追蹤到他自己都忘了在拍照,他與攝影家之間的互動,形成一種什麼東西丟出來什麼都是真實的關係。一張捕捉到一個人的「本質」的照片,是永遠看不膩的。
因為「真」,所以那一剎那拍出來的照片最美。肖像照片的美,沒有別的,最珍貴的就在於「真」。所以拍肖像照片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秘訣是開始的時候,彼此都不要想太多,當自己open的時候,對方才會open,兩個人沒有隔閡的時候,就是攝影家抓到對方本質的最好時機。
我拍辜振甫的時候便是如此。我們兩人的互動非常好,他在我面前變成一個可愛的老人、一個長輩,完全沒有那種「一個董事長要我來拍他」的那種權威。他的思想、他的學識、他的風度,都是高水準。而我拍出來的照片,就是他的人生的全部。
東方人通常比較矜持,不會馬上把自己丟出來,所以要花比較長的時間,打破對方的心防。西方人在這個部分就比較放得開。
1968年,我和《魔戒》的製作人Bob Shaye是住樓上樓下的鄰居。Bob很愛電影,那時他進口東歐電影,剛剛成立新線電影公司(NEWLINE CINEMA)來。他太太EVA是瑞典人,在家裡經常不避諱地赤裸著身子。那次拍完他們公司的高級職員後,我請他們帶movie camera到工作室來,因為兩個人都很熱愛電影,既然要為他們拍照,我想camera會用得上。
我用背光來拍。我抓住他們兩人最真實的那一刻,他們的互動、對電影的熱愛,表現得那麼自然。
後來我搬到別的地方去,他們也慢慢一步步地搬到好萊塢,開始拍恐怖片。我們之間不只是老朋友的情感,還有工作上,他有案子都會交給我。後來我要離開紐約回台北時,在一個知名的畫廊展覽,他們也來了。潔兮的演出,他們也一定會到。
我自拍過很多滑稽幽默的照片,譬如在沙漠裡一個人洗澡、或與愛車的合照,或是光溜溜地圍著一條圍裙做飯等等。我發現自己的相貌不斷在改變。幼年時還有一點書生氣,逃兵期間眼神卻顯得叛逆、落拓。到日本時,我感染了他們的風氣,時常穿著西裝。
在台灣拍平面廣告時,我怕攝影棚的熱燈,動不動就脫個精光,留下很多人來瘋的照片。到紐約之後,早早白頭的我,已經有種天地任我行走的解放感,在歐洲流浪時,我脫下了一身的束縛,越活越真。
老實說,我在處事應對上,一點能耐也沒有,常惹潔兮生氣,但她又拿我沒辦法,只能哭笑不得。譬如,我不喜歡死腦筋的人,有時工作上碰見這樣的年輕人,怎麼點都點不開竅,我就把這些話用日語編成打油詩大聲吟唱,對方當然還是聽不懂,連累了在旁的潔兮,她笑也不是、罵也不是,差點憋死了。
我喜歡跟人相處、高談闊論,大家圍繞在我身邊,自然冷落了一旁的潔兮,她有次特別提醒我,以後相偕出門,別把她晾在一邊!我也反省了,她是個才華洋溢的藝術家,我們因藝術而成知己,她卻常年扮演我身邊被忽略的「內人」,很不公平。
趁我還記得她的委屈,恰好有次公開聚會的場合,我就對新象藝術的許博允隆重介紹樊潔兮老師,許博允被我的「大小聲」嚇獃了,潔兮在旁又氣了一場,因為我們三人本來就都很熟,她知道我只是想「表演」一下,表示我有聽進去她的話。
潔兮——藝術之路的人生伴侶
與潔兮新婚在紐約的那段日子,是我們都念念不忘的。某藝術家說我不拍照,就是為了潔兮,這話然而不然。尋獲真愛的我,將潔兮的藝術之路視為第一要務,然而潔兮的藝術光輝不也映照在我的作品上嗎?何況我在照片的轉染法上投入鉅資,只期待會有最好的成品出現,同時也從沒停止鍛鍊我的眼力。
我每天接送潔兮去學舞,那裏聚集了紐約最美的年輕舞者們,我每每看得目不轉睛,潔兮笑我,「你這人......」,我不以為意,美在召喚我,我不得不回應吧?
我這樣到處看,並不是為了拍照,但有需要時馬上能派上用場,譬如我一直很欣賞紐約某個爵士吧裡的女歌手,當日本雜誌請我拍一個專題時,我立刻知道自己要拍的就是她!日本雜誌全由我做主,事後也非常滿意。
當時岳母替我們處理家務,讓我們沒有後顧之憂。而我則以藝術家看藝術家的嚴苛眼光,督促潔兮每日進步,給予意見。
潔兮就是我最好的拍攝對象,在家練舞與拍照是我們關起門的樂事。跟心靈契合的伴侶在一塊,永遠不會覺得無聊。我私下替她拍的照片很少對外發表,時報週刊請我去非洲拍專題時,我決定先練一練手,就帶著潔兮去墨西哥,在美國境內轉飛兩次,才抵達安地斯山脈的尾端,然後徵詢旅館當地人的意見,請了船夫帶我們到了一個無人島,自然絕美的懷抱中,誰都像初生的赤子,回到母親身邊般感到安心、踏實。我們拍得好開心,穿著比基尼的潔兮決定全裸入鏡,我先跟老漁夫說,「我老婆要脫光囉!」他很風趣地問,「那我先鑽到水裡躲起來?」笑壞了我們倆。
在室內拍潔兮,常見她雙眼無辜,像小動物在靜靜凝視,但潔兮如果想拿我拍的照片去當她舞作發表的宣傳照,我常會無賴地拒絕,還故意說些難聽話:「妳都傻傻的!」潔兮聽了又是氣個半死。
經濟上雖不寬裕,但那段日子千金難買。曾有一次我們在街上購物,排隊結賬時有個經紀人前來遞名片,要求潔兮去當手部模特兒。我立刻拒絕,潔兮拿了名片回家,猶豫著說,拍攝的酬勞對我們的經濟會是一大幫助,我堅持說不,潔兮就一笑置之。
當年我對潔兮一見鍾情的就是她極美的一雙手,憑她自身的資質,成為世界頂尖的手模不在話下。然而我更傾心於她的心靈與才華,一個藝術家不該止步於此。潔兮對舞蹈純淨的嚮往與激情,就像她澄淨的凝望一樣,永遠投向遠方,不曾偏離藝術的道路。
等待維納斯
離開義大利時,我憑著好手氣,在賭場籌足了去希臘的旅費。但是我並不知道,即將在希臘邂逅影響我一生的場景。
那是夏天的愛琴海,我在海色、天色和白牆之間,徘徊了二十多分鐘。我知道那裡有我想要的東西,但快門怎麼也按不下去。只好到附近轉一轉,看看海,在那裡呆坐了幾分鐘。終於我回去按了快門。
平常我們從相機的視窗看出去,只是一個小小的image,但是等到透過幻燈機把它放大來看的時候,那一剎那,是優秀作品或一般水準,一目了然。回來後看著這張放大的照片,我知道我突破了自己,完成一張非常好的作品。甚至到現在,我自認為仍沒有一張作品能超越這張。
後來詩人鄭愁予聽了這張照片的故事,他說:「啊,愛琴海是維納斯出現的地方,你在等待維納斯。」
1986年,大陸文學家高行健用自己的畫和我交換了這幅〈等待維納斯〉。他說我的作品景深消失了,令人難以分辨是攝影還是畫。他認為如果我是畫家,也會是很好的畫家。
過去我拍的照片比較熱情澎湃,不論是野柳、月世界,都有一種生命力,我的老朋友、音樂家許常惠說,「像我的人一樣。」但境隨心轉。我在歐洲這段時間所拍的照片,畫面經常非常安靜、簡潔,大自然被抽離到只剩下大面積的色塊、形狀和線條,但是「簡單」中仍富有變化和旋律,有一種「靜的力量」。照片中的生命力轉化為內歛,是可以一直「看進去」的。
這段日子對我來說有點像「修行」,尤其看的都是哲學方面的書,也許因此,透過相機拍出來的東西都有些許「禪」味。但我想,最重要的還是「無心」,「無心」讓我的感受力更為敏銳,可以看到大自然表相以外的深層的美。
那段日子所拍的照片,受到美國攝影雜誌極大的肯定,幫助我在紐約開創了一條極簡主義新攝影風格的路。但拍攝的當下我只是拍自己想拍的,並沒有想到什麼極簡風格,也不知道屬於柯錫杰的人生新頁已經展開。
想像空間
那一天,我開車帶岳母去散心,到紐澤西的海邊,看到一扇窗和一張椅子。我請她過來坐下。因為海風,老人家的帽子一直是戴上的,又因為生病,整個人顯得消沈。我想拍老人的孤獨感。岳母坐在椅子上的黃色身影,很能傳達那種氣氛。拍完後,岳母離開,椅子空蕩蕩地留在原處,我突然感覺,沒有人的空間,好像比有人在的時候,孤獨感更深。我想了幾分鐘,又拍了一張。空無一人的場景,似乎容納了所有人的孤獨。
一般人站在那裡看到這個景時,都會立刻反應,認為海是重點;但我不是,我把黑的部分放得很大,幾乎佔畫面的二分之一。然後海天一線,透露一點點的光,椅子是唯一的焦點。〈觀海〉這一張的三道光影甚至可以看出三種不同的質材:紅磚、木頭、水泥。
1983年拍的這兩張照片——〈黃衫客〉和〈觀海〉——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對比。這兩張基本上是同一個場景,只是一張有人,一張沒有。兩張照片是同一天拍攝,但發表的時間卻相差了23年。
〈黃衫客〉照片洗出來不久後就拿到市立美術館展覽,因為當時覺得〈觀海〉太孤寂了,所以只發表〈黃衫客〉。但是23年後,現在的我更喜歡〈觀海〉。〈觀海〉感覺更有詩意,因為沒有人,反而更有想像空間。
一個人的心靈有太多東西的時候,其實什麼也體會不到。簡單的時候,我們的心才活在一個更大的空間。
既然沒有人,是誰在「觀海」?這裡有多少人來過?他們之中,有多少人在這張椅子上坐過?是什麼樣的人,想著什麼樣的心事,有著什麼樣的體會?正因為沒有一個像「黃衫客」那樣具體的人物在畫面中,更多的可能性被包含在裡面了,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幅對「觀海」的想像,都可以形成一個「觀海」的故事。而那雙觀海的眼睛,透過攝影家的鏡頭,變成觀者的雙眼,觀海的是無數陌生的旅人,是攝影家本人,更是我們自己。而畫面中的視覺焦點——椅子,在那裡不知歷經了多少白天黑夜,承載了無以計數的各式各樣的人,在這張照片中,誰又會說它是沒有生命的呢?它既是一個道具,又是一個主體。
如果沒有〈觀海〉,可能很多人會喜歡〈黃衫客〉。但是兩張照片放在一起,想像空間的力量就很容易體會了。我自己非常喜歡〈觀海〉,看到它的那一剎那,我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存在,因為有我的存在,才有觀海的這個景。
這樣的照片給觀者的想像空間是無限的,每個人看到都會有不同的感受,全部的感受都可以融入到這一張照片裡。所以攝影作品要讓人感覺像讀一首詩,用幾個字就可以想像一個宇宙那麼大的空間。
記錄式的照片是在介紹這個世界,我的照片則是要讓人去體會這個世界。
三個鐘頭只為瞬間
照相館最好的作品往往是家庭合照,大家都坐在那裡安安靜靜的,三兩下就拍出大家都覺得很happy的照片。但攝影家不是這樣。攝影家拍一個人的時候往往要用掉很多很多底片,因為他要的不是紀錄一個人的表相,他要的是追到這個人的人性。在互動的某一剎那,他會即時捕捉對方在當下展露出來的人性。
我拍福特總裁也好、張忠謀也好,我會花三個鐘頭,慢慢把對方拉近,然後讓他放鬆,漸漸回到他真正的自己。
往往要經過三個鐘頭,有時候是兩個鐘頭,我會感覺到我抓到了他整個人生最重要的一剎那。他這個人最重要的特質,不自覺地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狀況下,展露出來。然而這個時候還不能說:「我拍到了!」仍然要繼續拍,我通常至少都會花上兩百張底片。拍到我自己累了,對方也累了。有時候覺得累了的那一刻,他也完全放鬆了,所以最後那幾分鐘很重要,他已經不在乎自己在鏡頭前是什麼樣子,也不會在鏡頭面前假裝某種形象,此時他的內心與表相都一致了,也就是他的特質已經出來了,我就可以很容易地捕捉。但這個時候還不能真的停,我們要繼續追蹤,追蹤到他自己都忘了在拍照,他與攝影家之間的互動,形成一種什麼東西丟出來什麼都是真實的關係。一張捕捉到一個人的「本質」的照片,是永遠看不膩的。
因為「真」,所以那一剎那拍出來的照片最美。肖像照片的美,沒有別的,最珍貴的就在於「真」。所以拍肖像照片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秘訣是開始的時候,彼此都不要想太多,當自己open的時候,對方才會open,兩個人沒有隔閡的時候,就是攝影家抓到對方本質的最好時機。
我拍辜振甫的時候便是如此。我們兩人的互動非常好,他在我面前變成一個可愛的老人、一個長輩,完全沒有那種「一個董事長要我來拍他」的那種權威。他的思想、他的學識、他的風度,都是高水準。而我拍出來的照片,就是他的人生的全部。
東方人通常比較矜持,不會馬上把自己丟出來,所以要花比較長的時間,打破對方的心防。西方人在這個部分就比較放得開。
1968年,我和《魔戒》的製作人Bob Shaye是住樓上樓下的鄰居。Bob很愛電影,那時他進口東歐電影,剛剛成立新線電影公司(NEWLINE CINEMA)來。他太太EVA是瑞典人,在家裡經常不避諱地赤裸著身子。那次拍完他們公司的高級職員後,我請他們帶movie camera到工作室來,因為兩個人都很熱愛電影,既然要為他們拍照,我想camera會用得上。
我用背光來拍。我抓住他們兩人最真實的那一刻,他們的互動、對電影的熱愛,表現得那麼自然。
後來我搬到別的地方去,他們也慢慢一步步地搬到好萊塢,開始拍恐怖片。我們之間不只是老朋友的情感,還有工作上,他有案子都會交給我。後來我要離開紐約回台北時,在一個知名的畫廊展覽,他們也來了。潔兮的演出,他們也一定會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