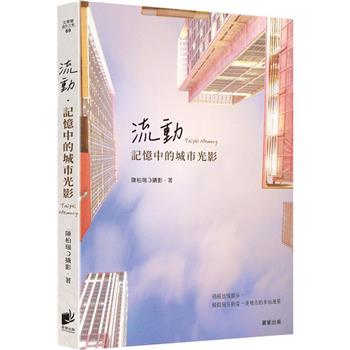四歲,天氣晴
時序回到六十年前的黃昏時刻,金色光芒幻化瞬變,灑落在剛插秧的稻田上,陣陣強風吹拂著芭樂樹,偶爾聽到一些唧喳的麻雀聲與羊叫聲。在大雷雨將至前,媽媽牽著力氣較小的羔羊,二舅則半拖半拉著母羊,將牠們牽入棚內,聽說羊咩咩最害怕淋雨了。
「榮昌,快回家了。」媽媽淋著滂沱大雨跑到鄰居家,吆喝著三舅,三舅卻捨不得離開仍直盯著電視看《勇士們》,反倒媽媽心裡急了,替自己心愛的哥哥擔心,如果晚回家,很可能會被外公毒打一頓。
傍晚雷陣雨漸歇,天空出現彩霞,但見家家戶戶炊煙裊裊。街路上,牽著牛車的人來來去去,有些會在六張犁土地公廟對面、外公開的「黃順發」雜貨店買肉買菜。而外婆早已泡一壺麥茶等著,讓這些辛勞的人們稍微休息一下。
據說,更早在土地公廟前還有臺車軌道,最近的車站就在外公家門口。
只不過在我小時候,原本的稻田開始換成高樓,灌溉的大圳溝也加蓋成為馬路。
那時的我,總喜歡聽著父母對我說著,這些屬於他們那個時代的故事,我也似乎等不及想要親眼看看這個美麗的世界。
屬於我的臺北故事,從這開始。
是清澈,也是最深層的記憶
六張犁是一連結現代與傳統的地方,帶上相機到頂樓拍攝陽光破曉的時刻,還是能夠聽到山邊人家養的雞在啼叫,農村小鎮的風情,依舊留了下來。
大圳溝是那個年代村莊人們的命脈,舊時的家庭主婦會帶著家中的小孩來到圳邊,用無毒的天然肥皂洗衣服,而魚群則在周圍自在優游。有些男士會在較淺的區域摸蜆仔,或是在岸邊垂釣、網撈魚兒。
偶爾,會有誰家過世的貓狗大體,隨著水流漂下,儼然是臺北的小恆河。生命的能量來自大圳溝,而許多的生命也將回歸這條河。我想,對於長輩們來說,這條河是清澈且神聖的。
爸爸說,當時的大圳溝從安順宮後方引出兩條水道,有一說是安順宮的主神託夢予曾祖母,表示得到一個風水龍穴,當地人因而協助建廟。環繞安順宮的這兩條水道,就流經陳家的聚落,兩河道的水平面基準不同高,落差約五十公分到一公尺,高的那條有洗衣池,是洗衣、抓魚的好地方,而低的河道就純粹當成排水溝,兩河道最後在廟旁的嘉興街與和平東路口匯流。
小孩子當時最愛的就是抓魚,爸爸曾抓過「三斑魚」,即今被列為珍貴稀有的保育類蓋斑鬥魚,這讓從小喜歡魚兒的我羨慕不已,真想知道那時的魚種還有哪些?是否與我在臺北各地抓過的不同?是否有色彩鮮艷、黃黑相間、穿梭在石頭間的臺灣石𩼧?是否有俗名為溪哥、紅貓,也就是顏色多元高雅的粗首鱲?
可惜他們並未留下影像紀錄那些過往,因為不久之後,滿布溝渠、河道的臺北,逐漸被汙染,並且加了溝蓋。爸爸說,有次隔壁家改建房子,看到建築工人直接把剩餘的石灰水潑往河溝,同時汙染了兩條溪流,也毒死了許多魚。主幹道大圳溝隨著臺北的發展,也漸漸失去清澈的水質,魚群紛紛消失,僅剩惡臭。現今封蓋的大圳溝,成了信安街,兩岸空地更蓋滿了住宅。
即使如此,我仍是流著六張犁血液的大圳溝岸邊居民,所以一說到抓魚,只要將褲管拉起,不管夏天或冬天,將雙腳泡在沁涼的河水中,就是我對這座城鎮不時會迴盪在腦中最深的回憶之一。
大圳溝雖早已封印,不過現今六張犁某個市場的小水溝裡面,竟然還有孔雀魚與大肚魚,這可是少有人知的事情呢。
回想起來,小時候的我還真的是一個喜愛在水邊穿梭的小孩,最記得與家人互動的記憶,總是在抓魚的時候,如在南港公園附近山邊與家人一起等著魚蝦進魚簍的時間,或在河旁的海鮮餐廳吃著海鮮炒麵,都是與魚兒相關的珍貴回憶。
老照片中的家族記憶
「你看呀,這⋯⋯就是當初第一代來臺灣的祖先。」爸爸說著,而我一臉興奮並好奇地看著爸爸與他拿出的族譜。
原來,早在乾隆年間,祖先就已從泉州安溪遠渡黑水溝,來到了福爾摩沙,來到了我現在生活的這片土地—六張犁。
爸爸有時拿出了他兒時住在三合院的照片,小孩們在榕樹旁調皮爬著,大人則坐在木椅上看著鏡頭。爸爸指著自己與家人,說起偶爾會在喜宴場合看到的遠房親戚,還有我未看過已仙逝的阿祖(曾祖父)。
「一輛腳踏車經過,腳踏車上的人約高一百八,瘦瘦的,穿著西裝、帶著紳士帽,文質彬彬,騎著腳踏車經過了美麗的稻田。」當時我的阿祖是外公的鄰居,我沒看過阿祖,所以有些關於他的故事,除了爸爸會跟我說之外,只能從大舅與其他長輩的口中認識,也是我對他的印象。
阿祖在日治時期是大安區的區長,這顯耀的話題從未斷過。當年,阿祖如何跳級、考上師專當老師,最後變成區長,然後闢建了連結到木柵的那條山路(舊時的軍功路),這些話題通常還會繼續延伸,我與弟弟都能倒背如流。除了祖譜外,我也常常央求爸爸讓我們看看舊時的照片。
祖譜記載著兩百五十年前乾隆年間,陳家祖先們從福建安溪渡過臺灣海峽落腳六張犁的拓墾史。描繪當時六張犁的田園風景,可從大圳溝上游到下游,也就是芳蘭路到現已成為六張犁社會住宅的陸軍保養廠附近。過去六張犁有幾個大姓聚落,從和平東路三段228 巷北順宮附近,能看到幾棟三合院,是屬於外婆家族—高家的聚落2;到了和平東路與信安街口的北邊,也就是六張犁安順宮周邊是陳姓聚落,原本也是幾棟三合院組成,其中一間是曾祖父起蓋的老家,現在已重建為大樓;大圳溝繼續往北順流而下,離大圳溝有點距離的六張犁土地公廟,廟口還保存著一整排的舊建築,是茶路古道至六張犁端的市集中心,其中一間則是外公家。
除了阿祖家的故事外,祖譜同時也提到關於媽媽娘家的故事。外公是從龜山來的小孩,不到十歲就出外打拚,來到六張犁這個地方。當時他在一個小山丘上的店鋪打工,後來自立開了雜貨店,並娶了來自六張犁高家的外婆。
二戰後,物資缺乏,還曾利用廢棄的防空洞建材,自力蓋起家屋,並用美援的奶粉罐當作煮飯鍋、米袋作成衣褲,努力的在這片土地上拚活。在此地紮根後,陸續生了小孩、買了土地,一家人勤奮的在這片土地上共同奮鬥、生活,街坊鄰居也都會到雜貨店買魚、買肉、買菜,如同今日的小型超級市場。
土地公廟前的街屋,每戶人家幾乎都做店面生意,後方則為住家,因此形成了商店聚落。外公家雜貨店是長條型的閩南式平房,店面屋頂鋪紅瓦,樑柱是從福州運來筆直的杉木搭建而成,牆壁則是由紅色的磚塊交錯疊起。位在山腳下的這間雜貨店祖厝,也是小坡道的起點,加上巷口的柑仔店、金紙店等商家,幾乎掌管著六張犁一甲子的柴、米、油、鹽及八卦。
媽媽總說外公跟舅舅那時候很辛苦,冬日天還沒亮,就得到坪林採買橘子,或去養豬場挑選豬隻;當男人們批貨回來,就輪到女人們做事了—要把雙手泡在冷冽的水中搓洗橘子、拔豬毛,然後才開始做早餐、縫衣服⋯⋯久了,原本纖細的雙手,開始長出一層厚厚的繭。
外公的雜貨店,生意日漸興隆,鄰居總說是風水好,因為每遇颱風、豪雨淹大水,總往外公家灌進來。這時,家人就會把大門打開,與其被大水沖毀房屋,不如讓水流過去;等到停雨前,長輩們還得看準時機,在氾濫退去前迅速把泥土清出去,聽說也常有水蛇游到店裡。
由於水災時大水經常灌到雜貨店,街坊都說「遇水則發」,根據當時長輩的說法,水路等同錢路,風生水起,代表錢路也會順著水路進去,因此才說雜貨店生意好是因為風水好。
淹水的往事如煙,每當長輩們回憶話從前,往往只想到泡爛的家具跟被大水沖失的郵票集與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