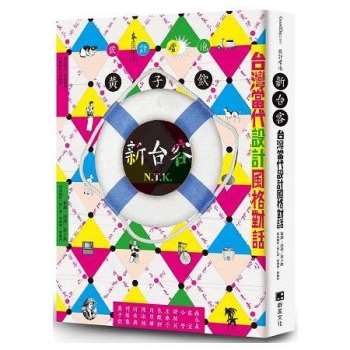〈01解嚴前後的鏡頭翻.何經泰 注視著邊緣,因為故事就在那裡〉
白色恐怖
――來談談「白色檔案」。當初怎麼會想到碰觸白色恐怖,在那個年代,這樣的題材應該還滿敏感的吧?
何:當時應該是解嚴前後,因為在媒體工作的緣故,常常得跑街頭與抗議現場,後來也常去「攤」喝酒,在那裡認識一票藝文圈的人。鍾喬看過我拍的「都市底層」之後,整合了陳界仁、王墨林、藍博洲和我,想要為白色恐怖這些人做一個大型的翻案。攝影找我,劇場就找王墨林,藍博洲負責撰寫文字,陳界仁畫畫,我們一起開會、上課,還找勞動黨的人來給我們演講。他們那些人不是二二八受害的,而是偏左派的、被關的,所以才叫「白色恐怖」。
──那時候就使用「白色恐怖」這個詞了嗎?
何:對,那時就那麼用了。為什麼叫「白色恐怖」呢?因為當時美國的麥卡錫主義打壓左派,白色是資本主義的顏色,而共產黨的代表顏色是紅色,所以白色恐怖就是資本主義對左派的打壓。那時候我們組織了讀書會,決定一起做這個東西。你也知道,展場向來是得提早預定檔期,甚至要一年前就先預約,在我預約檔期後,時間到了,全部人只有我完成,只好我先發表。
「白色檔案」這個系列困難在於,在「都市底層」系列中的人物,你一眼就能夠感受到他們的氛圍;可是「白色檔案」拍的是政治犯,他們與一般人相同,且因為環境的關係很低調,與路上遇到的阿伯沒有兩樣,沒辦法想到他是政治犯。很難透過肖像來傳達他們的能量。所以我很大膽的使用黑布去拍,黑布是抽象語言,代表了壓力、壓迫。並以黑布作為主要元素來貫穿。
工殤
──繼續聊聊「工殤顯影」吧,當初怎麼想到做這個題材?
何:因為那個年代大家流行做三部曲,我前面已經做了「都市底層」、「白色檔案」,也就想再做一個。
「都市底層」探討的層面比較偏向經濟、「白色檔案」則偏向政治。那時我在當記者,常跑社會新聞,認識很多運動團體。而工傷協會剛成立,他們的理念是要義務為勞工打官司、爭取權益。於是我想到要做這個主題,就去說服工傷協會,與他們的主要參與者還有理事長見面,也把我之前的作品給他們看。他們開會以後,同意讓我拍攝,而且全力支持我,於是我就與他們一起合作。由他們詢問會員願不願意拍照,他們安排好了我便去拍。有些剛受傷、還在恢復期的可能不太願意,有些人則是願意的。
──這是你原本就有興趣的題材嗎?
何:對,不過拍這個系列時,也是我最混亂的時期,那個時候碰到要如何呈現題材的困難。比如說,我原本預想進棚內拍他們的身體,但拍了幾個人之後覺得太直接、太強烈了,沒辦法直視。
──是因為拍得太像沙龍,有點像在展示身體?
何:不像是沙龍,是更精緻一點的。最初我覺得應該要把傷害的細節越透露越好,讓觀者能夠感受到傷口的壓力。可是進了攝影棚、照片洗出來以後,覺得這樣呈現太直接。
那時候很煩惱,不知道怎麼處理才好,一直在找材料。直到發現「拍立得55」的底片,就把這個拿出來玩。拍立得是底片裝在裡面,旁邊有兩個滾輪,一拉的時候,藥水會平均讓底片顯影。有時候如果拍壞了,大家會把底片拆出來看。那我就想,可以讓藥水不是很平均地走,也就是由我自己控制藥水,讓它的流動有對話性。試了幾次以後覺得效果還可以,就決定以這個方法做。
所以我拍這些人的方式,是以拍立得連拍十幾、二十張,拿到桌子上,用版畫的滾輪來推藥水,這樣藥水的流動性就會有意外。再從這些照片裡面去選擇呈現比較特別的。
──有點類似瑕疵品的意味。
何:算是把身體上的受傷與藥水的流動做連結,表現生命的不確定性。
只可惜我前面進棚拍攝的那幾位被攝者,已經不太想重複再拍,所以沒辦法,就先將他們的照片洗出來,大約洗二十吋×二十四吋大小,再用拍立得翻拍處理。
──所以這個系列是你開始以破壞的流程來達到精準度。它不是在完整的模式下進行的,反而是用破壞的方式抓到你的需求。不過,你剛才沒講到混亂的部分,所謂很混亂是指哪方面呢?
何:在尋找方法的過程很混亂,當然創作的過程也很混亂。像我們這種做肖像攝影的,必須要有被攝者,如果沒有對象的話,創作就完成不了。
那時我在想,如果我做工殤議題,但找不到拍照對象,這個系列是否還能成立?這個想法關乎我在做三部曲以後,比較少創作的原因。我覺得可能還有抽象的方式可以表達。被攝者
――會是怎麼樣的抽象方式,比如說不要出現人嗎?
何:對,就是不要對象,在沒有對象的情況下也能做出工殤議題的展覽。比如我拍機器、木頭假腳或是類似的裝置、擺設,看能否做出我要討論的議題。當然主軸還是身體,但是改用一些比較抽象的物體來代表,比如部位,或是一些布置。
因為做肖像攝影,雖然有被攝者,但多少還是會受到限制。所以我不想要受限於被攝的人,想要更自由的創作。一直在思考這些,所以很混亂。
――那你嘗試了嗎?
何:嘗試過了,但沒有完成,因為「工殤顯影」這系列剛好有對象可以拍攝(笑)。只是我會同時思考這個層面,萬一這些被拍的人不願意被拍,那麼作品還成立嗎?我能用義肢、部位、局部來完成這個議題嗎?能否用人像以外的手法來傳達?
──我想這是因為你的三個系列都以人為主,因此一定得處理人的問題。而人在其中是關鍵,倘若不處理,直接拍了走人,那共構的力道就會消失。
何:但因為創作者追求的往往是最大的自由度,而報導、肖像,會受限於對象,沒有對象就沒有質感,所以是個難處。
――這讓我想起魂魄的概念,有些創作者將人拍得像是屍體,或者透過合成,讓人呈現屍體的狀態。這關乎如何處理與書寫身體。我覺得你在「工殤顯影」碰觸了很有意思的邊界,就是你自己的邊界。
何:是啊,當時我碰觸到的是自己,所以混亂也是在這個地方。
──你拍「工殤顯影」時會不會按不下快門?
何:倒是還好,如果按不下快門就不會做了。
──拍這個系列時,你很確定被攝者是一個身分。他是要被保留的。
何:因為是在拍攝他本人,所以不能太造次。他是你的拍攝對象,而他呈現的又是他自己的時候,必須得去尊重他,不能讓他感到不舒服。
――所以你覺得這樣的尊重在你的作品裡是必要的,還是你也可以不去尊重?或是你覺得尊重是你想要保留人性的部分?
何:我覺得要尊重。所以前面才提到肖像攝影會因為對象有限制。我的作品鏡頭角度幾乎都是平平的拍過去,因為這是尊重對象。但萬一不是呈現他,而是作為模特兒來拍攝,那或許是不用考慮這點的。
白色恐怖
――來談談「白色檔案」。當初怎麼會想到碰觸白色恐怖,在那個年代,這樣的題材應該還滿敏感的吧?
何:當時應該是解嚴前後,因為在媒體工作的緣故,常常得跑街頭與抗議現場,後來也常去「攤」喝酒,在那裡認識一票藝文圈的人。鍾喬看過我拍的「都市底層」之後,整合了陳界仁、王墨林、藍博洲和我,想要為白色恐怖這些人做一個大型的翻案。攝影找我,劇場就找王墨林,藍博洲負責撰寫文字,陳界仁畫畫,我們一起開會、上課,還找勞動黨的人來給我們演講。他們那些人不是二二八受害的,而是偏左派的、被關的,所以才叫「白色恐怖」。
──那時候就使用「白色恐怖」這個詞了嗎?
何:對,那時就那麼用了。為什麼叫「白色恐怖」呢?因為當時美國的麥卡錫主義打壓左派,白色是資本主義的顏色,而共產黨的代表顏色是紅色,所以白色恐怖就是資本主義對左派的打壓。那時候我們組織了讀書會,決定一起做這個東西。你也知道,展場向來是得提早預定檔期,甚至要一年前就先預約,在我預約檔期後,時間到了,全部人只有我完成,只好我先發表。
「白色檔案」這個系列困難在於,在「都市底層」系列中的人物,你一眼就能夠感受到他們的氛圍;可是「白色檔案」拍的是政治犯,他們與一般人相同,且因為環境的關係很低調,與路上遇到的阿伯沒有兩樣,沒辦法想到他是政治犯。很難透過肖像來傳達他們的能量。所以我很大膽的使用黑布去拍,黑布是抽象語言,代表了壓力、壓迫。並以黑布作為主要元素來貫穿。
工殤
──繼續聊聊「工殤顯影」吧,當初怎麼想到做這個題材?
何:因為那個年代大家流行做三部曲,我前面已經做了「都市底層」、「白色檔案」,也就想再做一個。
「都市底層」探討的層面比較偏向經濟、「白色檔案」則偏向政治。那時我在當記者,常跑社會新聞,認識很多運動團體。而工傷協會剛成立,他們的理念是要義務為勞工打官司、爭取權益。於是我想到要做這個主題,就去說服工傷協會,與他們的主要參與者還有理事長見面,也把我之前的作品給他們看。他們開會以後,同意讓我拍攝,而且全力支持我,於是我就與他們一起合作。由他們詢問會員願不願意拍照,他們安排好了我便去拍。有些剛受傷、還在恢復期的可能不太願意,有些人則是願意的。
──這是你原本就有興趣的題材嗎?
何:對,不過拍這個系列時,也是我最混亂的時期,那個時候碰到要如何呈現題材的困難。比如說,我原本預想進棚內拍他們的身體,但拍了幾個人之後覺得太直接、太強烈了,沒辦法直視。
──是因為拍得太像沙龍,有點像在展示身體?
何:不像是沙龍,是更精緻一點的。最初我覺得應該要把傷害的細節越透露越好,讓觀者能夠感受到傷口的壓力。可是進了攝影棚、照片洗出來以後,覺得這樣呈現太直接。
那時候很煩惱,不知道怎麼處理才好,一直在找材料。直到發現「拍立得55」的底片,就把這個拿出來玩。拍立得是底片裝在裡面,旁邊有兩個滾輪,一拉的時候,藥水會平均讓底片顯影。有時候如果拍壞了,大家會把底片拆出來看。那我就想,可以讓藥水不是很平均地走,也就是由我自己控制藥水,讓它的流動有對話性。試了幾次以後覺得效果還可以,就決定以這個方法做。
所以我拍這些人的方式,是以拍立得連拍十幾、二十張,拿到桌子上,用版畫的滾輪來推藥水,這樣藥水的流動性就會有意外。再從這些照片裡面去選擇呈現比較特別的。
──有點類似瑕疵品的意味。
何:算是把身體上的受傷與藥水的流動做連結,表現生命的不確定性。
只可惜我前面進棚拍攝的那幾位被攝者,已經不太想重複再拍,所以沒辦法,就先將他們的照片洗出來,大約洗二十吋×二十四吋大小,再用拍立得翻拍處理。
──所以這個系列是你開始以破壞的流程來達到精準度。它不是在完整的模式下進行的,反而是用破壞的方式抓到你的需求。不過,你剛才沒講到混亂的部分,所謂很混亂是指哪方面呢?
何:在尋找方法的過程很混亂,當然創作的過程也很混亂。像我們這種做肖像攝影的,必須要有被攝者,如果沒有對象的話,創作就完成不了。
那時我在想,如果我做工殤議題,但找不到拍照對象,這個系列是否還能成立?這個想法關乎我在做三部曲以後,比較少創作的原因。我覺得可能還有抽象的方式可以表達。被攝者
――會是怎麼樣的抽象方式,比如說不要出現人嗎?
何:對,就是不要對象,在沒有對象的情況下也能做出工殤議題的展覽。比如我拍機器、木頭假腳或是類似的裝置、擺設,看能否做出我要討論的議題。當然主軸還是身體,但是改用一些比較抽象的物體來代表,比如部位,或是一些布置。
因為做肖像攝影,雖然有被攝者,但多少還是會受到限制。所以我不想要受限於被攝的人,想要更自由的創作。一直在思考這些,所以很混亂。
――那你嘗試了嗎?
何:嘗試過了,但沒有完成,因為「工殤顯影」這系列剛好有對象可以拍攝(笑)。只是我會同時思考這個層面,萬一這些被拍的人不願意被拍,那麼作品還成立嗎?我能用義肢、部位、局部來完成這個議題嗎?能否用人像以外的手法來傳達?
──我想這是因為你的三個系列都以人為主,因此一定得處理人的問題。而人在其中是關鍵,倘若不處理,直接拍了走人,那共構的力道就會消失。
何:但因為創作者追求的往往是最大的自由度,而報導、肖像,會受限於對象,沒有對象就沒有質感,所以是個難處。
――這讓我想起魂魄的概念,有些創作者將人拍得像是屍體,或者透過合成,讓人呈現屍體的狀態。這關乎如何處理與書寫身體。我覺得你在「工殤顯影」碰觸了很有意思的邊界,就是你自己的邊界。
何:是啊,當時我碰觸到的是自己,所以混亂也是在這個地方。
──你拍「工殤顯影」時會不會按不下快門?
何:倒是還好,如果按不下快門就不會做了。
──拍這個系列時,你很確定被攝者是一個身分。他是要被保留的。
何:因為是在拍攝他本人,所以不能太造次。他是你的拍攝對象,而他呈現的又是他自己的時候,必須得去尊重他,不能讓他感到不舒服。
――所以你覺得這樣的尊重在你的作品裡是必要的,還是你也可以不去尊重?或是你覺得尊重是你想要保留人性的部分?
何:我覺得要尊重。所以前面才提到肖像攝影會因為對象有限制。我的作品鏡頭角度幾乎都是平平的拍過去,因為這是尊重對象。但萬一不是呈現他,而是作為模特兒來拍攝,那或許是不用考慮這點的。